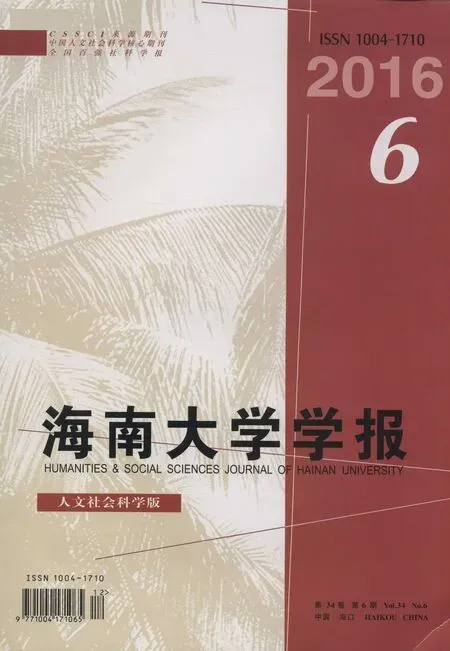现代性批判的范式转换: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2016-03-07刘祥乐
刘祥乐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现代性批判的范式转换: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刘祥乐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基于对现代性规范基础的不同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面对共同的“问题域”即“现代性课题”分别开创了“理性现代性批判”和“资本现代性批判”这两种最为根本的现代性批判理路和范式。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范式虽源出于对黑格尔关于现代性的辩证立场的继承及其所揭示的现代性问题的“再解答”,但在有关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理解、批判方式和重建方案等方面都异质于后者,从而实现了现代性批判的范式转换。澄清此一转换不仅对于在同一思想史视域中重新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而且对于纠正以往意识哲学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惯性解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范式价值。
现代性;理性现代性批判;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转换
学界虽已有学者提出和强调要从现代性或现代性批判的视角或范式——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所源出的思想史视域——解读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①参见罗骞:《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范式——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及其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宋一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但由于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这一哲学主导研究范式的惯性影响,不仅黑格尔与现代性的本质关联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况,而且其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历史关联也始终未能在现代性的思想史论域和视域中得到应有的探讨。笔者认为,现代性批判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总问题”,构成其哲学运思的历史出场语境和基本论域,对他们思想本身的阐释、对他们之间关系的阐释理应将其置于此一视阈之中,由此才能揭示出他们之间的历史性—存在论关联。本文试图基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大致勾勒两者在现代性批判及其范式转换中的关联及其分殊,进而在此一视阈中凸显两者之间的思想史关联,以期突出在“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阐释中,现代性批判视阈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非历史”解读的范式价值和意义。
一、理性抑或资本: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不同界定
正如施特劳斯所说:“现代性最具特色的东西便是其多种多样以及其中的剧变频仍。其种类是如此之多,以至人们会怀疑可否把现代性当做某个统一的东西来谈论”[1],现代性向来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群”。面对多元和多义的现代性,与其像对其他概念那样进行词源学的考察,不如揭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方能真正辨识看似不相似的现代性家族中的“家族相似”。也正是基于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不同理解和指认,马克思与处于主体性哲学之巅的黑格尔根本划界开来,由此为其超越后者而实现现代性批判的范式转换奠定了基础。
“什么是现代性”?提问方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因为它隐匿着理性—主体性原则和概念帝国的强制逻辑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它力图将一切存在物化归为由主体理性所统辖的概念的同质化规定中,进而确证自身。可以说,笛卡尔的“我思”原则的确立不仅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而且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即现代)的来临,这个时代由“上帝立法”的“神义论”(theodicy)转变为“人为自己立法”的“人义论”(anthropodicy),同时“现代”本身也从依附于对古代、中世纪以及宗教末世的言说中摆脱出来而不再具有编年史的年代意义,而是取得自我确证、自我立法的历史形态学意义,即不再作为均质等量的时间概念而更多地是作为标识时代特质的质的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称笛卡尔的我思原则即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现代的自我立场及其主观主义的来源[2],哈贝马斯也因此将孕育“现代的时代意识”的母胎——主体性原则——作为追新逐异的现代性的规范来源[3]41。既然“现代性”奠基于主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本身蕴含着反思和批判的辩证意识,那么“现代性”本身也必然带有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文化基因,使其自身呈现为一个具有内在分裂和自我再生的矛盾结构,亦即成为“自反的现代性”。
的确,现代性是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后者首先从文化精神层面然后延伸到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层面,从而使现代性获得其实体意义的规定和存在论上的内涵。现代科学技术、理性形而上学以及现代性(现代社会是其制度安排和形态学表征)在本质上同出一源,它们都源自理性—主体性原则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和贯穿。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些贯彻主体性原则的历史事件就是现代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启蒙运动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原则和取向,以至于现代性与启蒙成为一体性的,即“启蒙现代性”。“理性之光”唤起了启蒙理性的觉醒,开启了理性祛魅的现代性规划:通过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使人类从自然的必然性奴役和非理性的蒙昧中解脱出来,它确信“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4]。但吊诡的是,启蒙理性用以撰写自由解放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手段即技术现代性却倒转成为目的并致使解放的现代性陷入被消解、蚕食的困境中,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它是从现代性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启蒙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启蒙的辩证法”:作为唯一能够祛除神话的思想和规划,启蒙却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却又重新倒退为新的神话[5](线性目的论的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神话)。启蒙现代性内在的张力和矛盾致使自身成为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和结构,思维方式、心理体验、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多元的现代性本质上根源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即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存在论基础的不同理解。囿于时代局限和意识的内在性之中,秉承主体性哲学传统的黑格尔正是将主体理性这一“观念论副本”把握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并停留于主体性哲学的内部辩证地批判现代性,由此决定了其批判现代性的范式特征及其内在限度。但倘若离开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真正洞察和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建制的变革而只是以这些“唯灵论存在物”来揭露和批判现代性的悖论,那么势必沦为满足于“解释世界”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现代性的隐匿的意识形态同谋。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525,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在根本上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体制,即使是从意识和精神等层面对现代性的界定在根本上也根源于现代生产。正是在此意义上,吉登斯认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7]。利奥塔也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8],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前者就是后者的制度安排和存在论规定,后者则构成前者的学理根据和表达。马克思正是立足于资本现代性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从而完成了对现代性最本质性的批判,使其与“现代性的话语”真正区别开来。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以“资本”这一范畴命名“现代”,使“现代性”获得其历史形态学意义上的规定。在他那里,“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资本现代性”,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和规范基础就蕴含在“资本”之中,资本原则构成现代性的根本原则,资本逻辑演变为现代性的内在逻辑;“资本”在马克思的视阈中不再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纯粹经济学术语,而是成为领会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总体性范畴,在“资本”这一总体性范畴统摄下的现代性批判乃是一种总体性的现代性批判,它贯通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其他论域和主题,并构成其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资本现代性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构成现实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规定,成为“现代性”的本质和根据: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包含着“一部世界史”[9]。资本最初只是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存在,但它一经产生就成为支配一切的最具普遍性的统治力量和经济权力,成为“普照光”。但实际上,“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10],而它只不过是把自身的绝对的社会性质通过物的中介力量投射出来罢了。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最普遍的中介范畴,一切存在物只有在资本的普遍中介和抽象下才能成为社会存在物,也只有在与资本的存在关联中才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从而作为绝对和普遍的力量演变为现代性的基本存在论规定,“抽象成为统治”就表现为资本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支配性法则,资本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在资本成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建制后,现代性的“唯灵论存在”,如思维范式、审美体验、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和叙事方式等就必然统摄于资本这一总体性范畴和存在论规定之中从而具有边缘性和从属性的意义,而对现代性的诸意识形态批判也必然要统摄于资本批判之下。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洞察到了现代性的内在原则和存在论规定,并揭示出了资本的运行法则、内在矛盾和历史限度,从而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之存在的异化生存状况并由此戳穿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假幻象,从而获得了彻底批判现代性的“锁钥”,历史地和唯物地超越了黑格尔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理性界定。
要言之,尽管“现代性”被课题化并不始于对其存在论基础的资本指证,而最初只是停留于现代性的诸意识形态(如理性)规定,但只有在将“资本”这一“现代性”的存在论内涵纳入到对“现代性”及其诸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中,才能更本质地领会它们的本质规定,否则对现代性的批判只能沦为像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即不仅找错了“靶子”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囿于现代性之中沦为“现代性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因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存在论的不同把握,致使两者虽然都本质性地洞察到“现代性的悖论”,却产生了两种异质性的诊疗现代性的病理学方案。
二、黑格尔的理性现代性批判范式
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黑格尔哲学出场的历史语境就是如何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分裂,重建现代的伦理总体性。按哈贝马斯的看法,黑格尔作为“第一个使现代性成为问题”并“开创了现代性话语”[3]43,51的哲学家,他以概念辩证法的形式首次理论地表征了现代性问题,既以“理性”确立了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又开创了理性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范式,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黑格尔哲学以“巨大的历史感”力图弥合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和张力,以理性批判的形式重建现代性的合法性,理性调和成为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基调,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由此构成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泰勒指出:“我们想要透过现代问题和两难困境来认清我们的方向时,那些必然遭遇到的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均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指证了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诊疗方案的价值。(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作者原序第17-18页。)。
作为“使现代性脱离外在于自身的历史规范的迹象并将这一过程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3]43,黑格尔不再把“现代”仅仅作为编年史概念,而是使其获得了历史形态学意义上的分期性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近代的主要论题——“古今之争”在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了划时代的解决[11],他以“新时代”来称颂“现代”,从而将其与古代界划开来。在他看来,现代就是主体理性的时代,主体性和理性就是现代性的根本特质和存在论基础,现代主体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等都奠基其上。面对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权威扫地的矛盾局面,黑格尔坚执理性主义的大旗,将其挺立为现代性的根本原则和规范基础,认为“理性是世界的原则,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12]80,理性构成新时代的原则,主体理性的自由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和划时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13]126-127。尽管黑格尔以之作为理想国家的范型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在那里伦理总体性尚未分裂,但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伦理实体只是一种形式的普遍性,尚沉浸于混沌的自在统一中,缺乏特殊性的中介,并没有使主观性的自由得以发展,而“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13]291。黑格尔对作为“新时代”的现代的充分肯定集中体现在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即启蒙运动及其制度安排层面的展现即法国大革命中,尽管在黑格尔洞见到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和转向保守调和的立场后逐渐成为其批判的对象。他认为这两个历史事件浓缩了现代性的规范原则——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原则,使人类认识到理性这一现代性的根本原则统治着世界,使“‘精神’自己的内容在自由的现实中被理解”[14],代替了宗教权威成为绝对的标准和尺度。
黑格尔不仅以“理性”奠定了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并充分肯定了理性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又洞见到现代性内在的分裂和张力,对现代性的肯定性认同与对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作为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方面构成了黑格尔理性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黑格尔的“现代性”奠基在主体理性的原则上,而后者自身内部就包含着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要求,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必然使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发生合法性危机从而走向自我批判,这就是黑格尔创立的“启蒙辩证法”原则[3]51。处在“新时代”开端的黑格尔深刻地预见到“现代性的困境”:感性和理性的对立、知识和信仰的冲突、自由与必然的分裂、个体理性的膨胀所导致的普遍理性的失落以及主体自由的扩张所带来的“绝对自由的恐怖”和“伦理总体性”的丧失等。
首先,黑格尔指认自启蒙运动到康德哲学所倡导的理性只是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即知性而不是普遍理性、具体理性,而“由知性所建立起来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12]173,它和特殊性之间互为外在对立,这种片面的理性在坚执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化逻辑的基础上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分离开来,以这种片面的、抽象的理性作为精神内核的启蒙运动虽然摧毁了宗教神学的权威,但同时也导致了个体理性的膨胀和普遍理性的丧失并进而瓦解了宗教作为内在和解力量的救赎承诺,使其无法弥合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外在对立并重建宗教的一体化力量,而只是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分裂。其次,以这种抽象理性为原则的理性自然法理论及其作为制度层面表征的现代国家并未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将人从必然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现代所确立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自由,而更重要的是“使自由的原则重新达到纯粹的客观性”,“这种自由的原则还必须加以纯化,并获得其真实的客观性”[15],否则只能囿于纯粹主观性之中,既无法实现个体自由也无法重建伦理实体。黑格尔由此抨击了建立在这种个体主观性和抽象理性基础上的自然法理论和自由主义学说,他指出自然法学家假定的自然状态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粗野的和不自由的状态”,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所理解的意志“仅仅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意志”[13]208,其普遍意志只是“共同的东西,即从作为自觉意志的单个人意志中产生出来的”[13]255,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国家只是以“想象的理性”或抽象理性为基础的因而缺乏实体的普遍性,其最终结果必然是造成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绝对自由的恐怖”。可以说,黑格尔之所以肯定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理性、自由、平等和解放的启蒙现代性理念,而之所以将它作为批判的矛头是因为他洞察到了建立在个体理性和原子式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所导致的普遍理性的失落、所表征的伦理总体性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绝对自由的恐怖等现代性困境。这正是黑格尔通过对现代性的诊断所洞见的“启蒙辩证法”。
面对“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的最高的胜利”[12]33这一时代病变,黑格尔将矛头指向启蒙的抽象理性原则。实际上,在黑格尔的思想深处潜藏着基督教和古希腊城邦制这两种理念*洛维特指证了黑格尔思想底蕴中的基督教和古典城邦制这两种因素在他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26-330页。)关于此点,哈贝马斯对此也作了简短的暗示。(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Cambridge,UK:The MIT Press,1990:30.),他深受耶稣基督“爱的和解”原则的影响,极力寻求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而这一和解的标准就是古希腊的古典城邦制,它体现了普遍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谐以及伦理实体的统一,因此他消解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批判抽象理性和重建现代伦理总体性的方式就是在主体性哲学的内部寻求理性和解的力量,“依靠这种方式,晚期黑格尔不必诉诸其他而只需依赖现代性自身内部的主体性原则就足以对现代性做出诊断”[3]34,即用绝对精神取代抽象理性来整合分裂了的现代性,通过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来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而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在黑格尔看来就集中体现在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中,因此,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批判作为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基础的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用体现绝对精神的理性国家和法来批判表征现代性的内在分裂的市民社会,并以此通过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和解重建伦理总体性的统一,就构成黑格尔诊疗现代性的方案。
黑格尔认为,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看,市民社会只是伦理实体发展阶段中的“分裂或现象”[13]41,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特殊中介环节,它既是家庭和私人领域的超越者,同时其形式普遍性的内在限度决定它必须以体现具体普遍性和代表普遍理性的国家为前提。市民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形式性作为各自独立的原则,只是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其内部实则潜藏着现代性内在分裂的根源: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分裂所导致的伦理实体的丧失。这些内在分裂现实地集聚于市民社会这一特殊性的场域——“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利益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3]309,因此它只是助长了生存于其中的原子式个人的利己主义和个体理性的膨胀,奠基在自然法权和启蒙理性基础上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等理念只具有形式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其结果是造成了普遍理性的失落和伦理总体性的丧失,加剧了现代性自身的内在分裂。而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依靠作为体现绝对精神的实体性普遍物的国家才能消解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内在分裂,从而瓦解抽象理性的统治,重建现代人之生存的有机团契的伦理共同体。他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13]253,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实体性的统一”,它不再是市民社会阶段的形式的、否定性的自由,而是“自由的现实化”[13]258或者说是“具体自由的现实”[13]260,而只有在绝对精神发展到它的“地上神物”即国家环节,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融合、普遍理性的实现所达成的伦理实体的统一才能实现,而这正是现代国家的原则,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13]260。缘此,作为绝对理性的现实化的国家弥合了以形式理性为内核的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在主体性哲学的内部消解了“现代性的悖论”。
在主体性哲学内部确立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和内在逻辑,并囿于主体性哲学之中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这构成了黑格尔理性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但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只是以泛逻辑的神秘主义方式完成了其概念辩证法的演绎,“把现象中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16]114,“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16]22,并没有真正克服和消解现代性的内在分裂,也没有完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要求,而是陷入到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窠臼中。用绝对理性的辩证运动克服理性的抽象性和形式性只是在观念层面的变革,如此一来,“膨胀成绝对理性的合理性把现代性获得自我确证的前提中立化了”,“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和钝化了哲学的批判功能。最终,哲学脱离其所处的时代,毁灭了其对于时代的兴趣,剥夺了其自我批判、更新的要求。站在时代高度的哲学消除其批判的重要性导致时代问题失去了挑战”[3]42-43,在理性限度内部寻求和解的黑格尔最终没有跳出自己所处的“罗陀斯岛”,其理性现代性批判最终蜕变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马克思则承接黑格尔理性现代性批判所遗留下来的现代性问题并继承其批判意识,在现代性批判的谱系中实现了范式的根本转换。
三、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
在马克思的文本群中几乎找不到概念化的“现代性”范畴,但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却是现代性的。可以说,现代性批判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总问题”,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而重建现代性构成马克思哲学“总问题”所昭示的终极指向,这构成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的根本特质,由此实现了对黑格尔理性现代性批判的范式转换。
作为“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17],马克思不是把哲学问题专题化的哲学家,而是把时代问题哲学化的思想家。马克思哲学所完成的“形而上学的颠倒”就在于使哲学的重心从追寻世界“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转向对人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实践解答,从探求至终究极的解释原则转向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存在论关切,以“改造世界”的新哲学终结了传统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通过揭示出产生现代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根源来批判现代形而上学,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来批判和扬弃其现实的存在论基础,这正是马克思所开创的现代性批判范式的革命意义。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既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而是一种与黑格尔的理性现代性批判相同的辩证批判,这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特点,即马克思集现代性的产儿、批判者和重建者于一身。他在资本现代性发轫之初就预见到并揭示了“现代性的悖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18]。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作为历史性的资本现代性对于重建现代性的意义,即现代资本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使人们从封建宗法的依附关系中、从对自然和宗教的蒙昧迷信中摆脱出来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关系,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自由王国”不是回到原始的“丰富性”,也不是从虚无中产生出来,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对资本现代性的积极扬弃中,是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证获得形式自由和解放的个人却在资本现代性中承受着异化的生存境况,变成“逃避自由”的“单面人”,陷入“理性的牢笼”和“进步强制”的宰制与戕害之中,自由和解放的现代性承诺和宏大叙事沦为资本现代性的牺牲品,这便是马克思所洞察到的“现代性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规定,现代性是以资本为其存在基础的。资本是“现代之子”,但同时却又颠倒为“现代之母”,“现代性的悖论”就蕴藏在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即资本之中,“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向等等……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19]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层面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探讨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及其限度,指认资本的主体本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中潜在地包含着资本现代性的一切矛盾,随着它们之间矛盾和对立关系的发展,“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6]172,而这一矛盾和对立就潜藏在资本现代性由以成立的核心原理即抽象劳动中:现代性以资本作为本质根据,而资本只不过是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因此,当马克思不再把私有财产作为先行前提而是追问其来源和本质时,马克思就由此“超出”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黑格尔哲学同样无批判地表达了抽象劳动的原理从而与国民经济学殊途同归,在对“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6]124的“现代性现象学”的追问和“还原”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由此奠定了其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特征。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同于只是囿于形而上学的内部(如黑格尔)或者只是局限于人的生存处境的存在体验(如海德格尔)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而是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外部揭示出其得以成立的存在论建制从而真正实现了“形而上学的颠倒”。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现代性的合法性得以成立的双重结构,它们之间“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20],对其中一方的批判必然本质性地关涉到对另一方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所实现的双重批判就成为一种内在贯穿的总体性批判。同时正像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一样,马克思对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同谋的批判也必然呈现出辩证的批判姿态,这集中体现在《巴黎手稿》中。在其中,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和对现代人的生存异化状况的存在论批判同时内在地关联着对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作为知性科学的古典经济学把劳动作为财富的主体本质这一“诚实”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它掩盖劳动异化这一“伪善”的意识形态性质,从而通过揭示这种“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所陷入到的二律背反指证其作为从属于资本现代性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本质;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在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即黑格尔哲学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法及其过程意识和中介思想把握到了现代劳动的本质及其对于理解和建构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证它并没有揭示和扬弃抽象劳动的消极性,而只是停留于“抽象的精神劳动”的概念帝国的演绎中,从而与国民经济学站在一起沦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及其重建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认和批判了这种否定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并以辩证的立场重新规划了有别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现代性的未完成方案——“哲学共产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正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深化和发展,在其中,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及其辩证性、总体性,使得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和基本特征由此凸现出来。在现代性批判这一“总问题”的贯穿下,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断裂”,而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联也就不是所谓形而上学内部的区别,而是触及思想史基础的历史性的存在论差别。
由于未能洞见到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本质关联,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给当今各种现代性批判话语提供了曲解、修正和伪装的可能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它不是被还原为经济决定论的客观主义就是被置换为阶级主体的唯意志主义;不是被误解为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就是被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同道。与此同时,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范式被曲解为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从而伴随“后革命时代”的到来沦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一范式及其实践指向的革命意义由此极大地流失了,而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内在的差别也就被遮蔽了。正如伯曼所说:“成为充分的现代就是反现代:从马克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如果没有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极其明显的现实的憎恶和抗争,就不可能理解和拥抱它的诸种可能性”[21]。马克思是以现代性批判的方式,通过将阶级主体革命的实践诉求诉诸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分析和意识形态话语的解构之中,并以此重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有着根本区别,最多只能说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质言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及其辩证立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肖像,诚如伊格尔顿所说,在批判现代性的激进思潮中,“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它既是启蒙运动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从而既与抱持怀旧—倒退倾向的浪漫主义相对立,又与抱持进步—技术倾向的现代化理论相抵触[22]。
四、余 论
以往,囿于意识哲学的研究范式以及传统哲学教科书的限制,致使现代性批判视阈或范式在阐释黑格尔和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中的长期“缺席”,而“黑格尔—马克思问题”也始终处于传统形而上学阴影的遮蔽之中。笔者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在现代性发轫之初开创了现代性批判谱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批判范式,现代性批判构成他们共同的“问题域”,构成阐释两者本身的思想和透视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存在论视角,而勾画两者之间在现代性批判中发生的范式转换不仅对于揭示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对于强调现代性批判视阈的研究范式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1 ] 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83-84.
[2]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76.
[3]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M].Cambridge,UK:The MIT Press,1990.
[4]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21.
[5]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9.
[8]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共游戏[M].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7.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8.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2.
[11]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M].张志伟,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5.
[12]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4]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12.
[1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54.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M].陈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0.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6.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5-96.
[20] 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学术月刊,2006(2):48.
[21]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8:14.
[22]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8.
[责任编辑:张文光]
Paradigm Shift about Critique of Modernity: From Hegel to Marx
LIU Xiang-le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With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modernity, Hegel and Marx, in face of the common “problematique”, namely “subject of modernity”, separately initiate “rational critique of modernity” and “capital critique of modernity” as two fundamental methodologies or paradigms. Although inheriting from dialectical position of Hegel’s modernity and his 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issues Hegel puts forward, Marx is different from Hegel in understanding the ontological bases, critical modes and reconstructive patterns of modernity, therefore realizing the paradigm shift about critique of modernity. Clarifying the shift bears the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and paradigmatic values for not only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Marx under the same horiz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but rectifying previous inertial interpretations of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problem of Hegel-Marx”.
modernity; rational critique of modernity; capital critique of modernity; paradigm shift
2016-06-23
B516
A
1004-1710(2016)06-0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