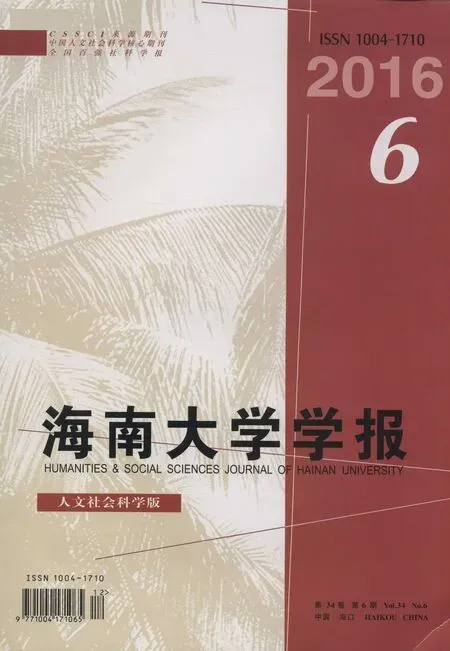从王鸣盛与吴镇的交游看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2016-03-07杨齐
杨 齐
(甘肃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 甘肃 定西 743000)
从王鸣盛与吴镇的交游看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杨 齐
(甘肃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 甘肃 定西 743000)
沈德潜去世以后,袁枚的性灵诗学风靡诗坛,但格调诗学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王鸣盛在读到仍然坚持格调的西北作家吴镇的诗集后,主动与吴镇建交。通过考察两人的交往始末,可以深入探讨格调诗学在乾嘉之际的生存状态,而吴镇以及好友杨芳灿融合格调与性灵的诗学观变化,彰显了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王鸣盛;吴镇;乾嘉之际;嘉道诗学;格调诗学;性灵诗学
乾嘉著名学者、诗人王鸣盛(1722—1797年),早年好诗,曾师从格调派领袖沈德潜,被沈德潜列为“吴中七子”之首。王鸣盛秉承其师格调诗学理论,主风雅格调,诗宗盛唐,吟咏非常丰富,著有《西沚居士集》等,存诗二十四卷。王鸣盛辞官后专门从事经史研究,师从乾嘉著名学者惠栋,以汉学考证方法治史,撰有《十七史商榷》和《蛾术篇》两部史学名著,与钱大昕、赵翼并称为乾嘉史学三大家。走向史学研究之后的王鸣盛并未中断诗歌写作,也没有远离诗坛,仍然与诗坛保持着联系。在七十余岁高龄时,主动写信与西北诗人吴镇建交,并以弟自称,实为乾嘉诗坛一大佳话。吴镇(1721—1797年),字信辰,号松厓,别号松花道人,甘肃临洮人,擅长诗文,被誉为“西州诗学之大宗”[1]3916,亦是乾嘉之际关陇诗坛领袖,有《松花庵全集》存世。吴镇诗学汉魏盛唐,论诗重风雅格调,尤其精研格律,受格调诗学影响较深。王鸣盛与吴镇同尚格调诗学,考察其交往始末,对深入探讨乾嘉之际格调诗学的生存状态以及一窥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王鸣盛与吴镇的交往始末考
王鸣盛知道吴镇其人其诗,时间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前。在乾隆三十八年给刘壬诗集写的序中,王鸣盛提到了吴镇:“三秦诗派,本朝称盛,如李天生、王幼华、王山史、孙豹人,盖未易更仆数矣。予宦游南北,于洮阳得吴子信辰诗,叹其绝伦,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2]。吴镇《松厓文稿》中《刘戒亭诗序》摘引了这段话,并感叹:“西庄素未识予而倾倒如是,洵神交之李邕、王翰也,因录之以志感”[3]。刘壬是吴镇好友“关中四杰”之一刘绍攽之子,字源深,号戒亭,陕西三原人。刘壬从小受其父刘绍攽熏陶,少能赋诗,有《戒亭诗草》存世。刘壬曾拜入吴镇门下学诗,后来又奉王鸣盛为师。该序写于乾隆三十八年,此时的吴镇五十三岁,正任山东陵县知县,而王鸣盛五十一岁,已经辞官居家十余年,但两人一直没有建立交往关系。
吴镇和王鸣盛之间开始书信往来,正是由于刘壬的介绍。乾隆五十五年(1790),刘壬邮寄吴镇诗集给王鸣盛,但王鸣盛因正患目疾,未读也未作回应。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鸣盛目疾痊愈,得通读吴镇诗集,为其诗所惊服。王鸣盛自己说:“年六十八,两目皆瞽,三原刘壬邮其师吴松厓诗,不能读矣。年七十,瞽得闻,发圅读之,大惊叹,以为异乎人人之为之者”[4]。随后,王鸣盛写信给吴镇,该书信被吴镇节录,存于《松厓文稿三编》中,信曰:
久耳芳名,未由接晤。幸从三原刘戒亭处,得读佳章,惊才风逸,壮志烟高。祗觉咳唾九天,皆成珠玉,足以藐后凌前,洵推才子之最也。拙作卷帙繁多,先寄诗笺十幅,以博一粲。老先生汲古有素,想不止长于诗,即以诗论,拔出辈流,奚翅霄壤。特寄此札,以致相慕之诚。弟字凤喈,号礼堂,别号西庄,现届七十,复改西沚。沚者,止水,取其不动也。弟王鸣盛顿首。辛亥腊月。[5]
从信中可看出,王鸣盛对吴镇诗作的惊叹是发自肺腑的,建交的愿望是诚恳的。他还以弟自称,并“寄诗笺十幅”,有与吴镇论诗的愿望。面对乾嘉著名学者、格调派代表诗人王鸣盛的来信,吴镇大喜过望,很快回信给王鸣盛,信中说:
四十年前,即读老先生之制义,虽以分隔云泥,未获把晤,然仰止之心,未尝忘也。昨蒙惠示手书,真如五色朵云,从天而降。再读诗笺,清新婉丽,足媲唐贤。惟晚岁失珠,为之怃然不乐,未知跨灶文孙,尚有几人,兼能慰晚景否也?所喜文昌之目,暗而复明,天殆佑获,老先生以留为东南之灵光乎?仆于诗道亦颇留心,祗缘僻处边方,未与海内高人,时相倡和。今蒙老先生印正提撕,觉衰气为之一振,或能晚进,亦未可知。拙刻数种,在敝省虽争刷印,但甘肃窎远,终不若南方书贾,便于风行也。老先生闻望甲于东南,足以嘘张才俊,今寄来二张(自注:康侯、牧公)诗三册,许铁堂诗二册,此系仆为刊刻者,并祈鉴定。倘笔墨之暇,与仆诗录中赐以华序,则更叨荣多矣。[5]
吴镇在信中一抒早闻大名而不得结交的遗憾,附信还寄了自己的《松厓诗录》和所刊刻的张晋、张谦、许珌的诗集,并请王鸣盛写诗序,王鸣盛欣然给吴镇诗集作序,序曰:
予于诗无专功,而四方士谬使序其诗者众矣,诗或凡猥带俗调,虽勉应之,未必惬鄙怀也。年六十八,两目皆瞽,三原刘壬邮其师吴松厓诗,不能读矣。年七十,瞽得闻,发圅读之,大惊叹,以为异乎人人之为之者。越明年,松厓复寄自选诗录,且属余序,予其何可无言以自托于知音哉。松厓甘肃狄道人也,陕西甘肃,元始各置行中书省,然溯而上之,则唐以分关内陇右山南诸道,宋已分永兴秦凤诸路矣,明乃通为一布政司,今分二司,仍古也。盖自潼华以西达于塞外,山有西倾、朱圉、鸟鼠,水有河、洮、汧、渭、沮、漆,其风土高厚而峻拔,畸人逸叟产乎其间,如王符、周生烈、皇甫谧、刘昞之徒,著述流传,至今彬彬盛矣。若诗歌一道,亦多作者,季札称秦风谓之夏声,能夏则大者矣,杜工部、岑嘉州盛唐大家,而得诸秦陇及西徼者,居半胜国,则庆阳李空同梦阳、巩昌胡可泉缵宗、平凉赵浚谷时春相继出,予皆购其遗集藏之,不敢忽也。今松厓复崛起西陲,骨骼才情,直欲上薄汉魏,下规盛唐,不特比肩空同,而可泉、浚谷并超乘过之矣。松厓由乙科起家,官兴国州牧,进沅州守。盖不但钟情秦陇之灵毓,西倾诸山、河汧诸水之秀,得其高厚峻拔之气,以振厉豪楮抑,且纵览三湘七泽,挹沣兰沅芷之芳馨,取楚骚之壮烈以为助,故诗益摆脱羁束,酣嬉淋漓,如有芒角光怪,歕射纸上,而不可逼视焉,吁亦奇矣。自解组归,用古学倡导西州后进,而我东南人亦闻风景慕,虽名位稍逊胡、赵,要其进退优闲,正复过彼,夫又奚憾耶。予与松厓年相差,二老翁数千里神交,良觌则虽期矣,籍序代晤言也可。令弟握之,犹子洵可,诗皆有兴趣,予未暇遍序也,序松厓牵连及之。乾隆壬子仲冬月长至日,吴郡西沚王鸣盛拜譔,维时行年七十有一。[4]
王鸣盛从秦陇地域历史文化论及秦陇地域文学代表作家,并指出吴镇诗文得南北文化和自然山水之助,评论非常到位。王鸣盛认为,吴镇的成就比得上李梦阳,超过明朝关陇著名作家胡缵宗和赵时春,定位是很高的。
王鸣盛的诗序写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按时间推算,吴镇收到诗序的时间应该在第二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春。此时,吴镇仍然在兰州担任兰山书院山长,应该写有感谢信给王鸣盛,但两人文集皆不载。该年秋天,吴镇因“脚气复作,兼患风痰,遂归里调养”[6]。至此,两人交往中断。三年后的嘉庆二年(1797),两位惺惺相惜的老人同年相继去世。
二、王鸣盛与吴镇的诗学渊源相近论
从两人交往始末可知,作为乾嘉著名学者以及诗坛名家的王鸣盛,主动交好偏居西北边地的诗人吴镇,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引为知音,主要原因是吴镇的诗作格律工整,而论诗又主张风雅格调,诗学宗尚近于格调诗学。
吴镇一生积极致力于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尤其精研格律,是当时关陇诗学的领袖人物。关于吴镇的诗学宗尚,其师牛运震说得非常清楚:“镇为诗不自从余始,而自从余,诗益工,其所以论诗者日益进。镇之言曰:‘古期汉魏,近体期盛唐,合而衷诸三百篇,师其意不师其体,唐以后蔑如也。’”[7]吴镇诗学宗尚主要体现在其《声调谱》、《八病说》和《松花庵诗话》三部诗学理论著作以及大量诗集序跋中。《声调谱》和《八病说》是专门讨论诗歌格律的两部著作,《声调谱》受到赵执信的《声调谱》影响而作,专门讨论律诗声调,“赵秋谷先生有《声调谱》,然乃古诗之声调,非律诗之声调也。律诗声调最宜知,而初学多茫然,则此《谱》不得不作矣。东阳八病,初亦论古诗耳,今专以绳律,使之声调和谐,讵不妙哉!至于宛陵所注,洵为后学之指南,而其说尚简略,予引而伸之,兼忝以臆见,是耶?非耶?安得起休文圣俞而细论之。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吴镇自序。”[8]《八病说》是对梅尧臣《续金针诗格》的阐释,两书是吴镇一生律诗研究的总结,其声律理论在前人基础上颇多创见,李华春说:“其中议论,多前人所未发,衣被骚坛,功不在宛陵之下也”[9]。
《松花庵诗话》论诗以格调为主,特别重视格律是否工整,如“宁夏一幕客有‘九秋蓬上下,三户杵高低’之句,人多称之。予谓‘上下’即‘高低’也,若易为‘蓬断续’,则其语顿工”[10]。评孟津王子陶“作诗好为古险奇谲之体,而实不能工。”[11]吴镇写作了大量的诗集序跋,这些序跋也都侧重从风雅格调入论,强调格律工整,如《杨山夫诗序》:“山夫之诗清刻而坚瘦,荆圃之诗爽朗而高华,其格调不同,而其近风雅则同。”[3]《王芍坡先生吟鞭胜稿序》:“先生独开生面,至新疆回部之诗,则古所未有者,而今忽有之,以采民风,以宣圣化是,非徒雨雪杨柳,感行道之迟迟也”[3];《陆杏村诗草跋》:“古体格高,近体韵胜,而足迹所经,凡怀人吊古之作,下笔如云蒸泉涌哉!”[3];《李坦庵诗集序》:“诗无尽境,而久则愈工,故古人晚年论定,辄自悔其少作”[3]。即使吴镇晚年在受到袁枚性灵诗学影响后,论诗主张从风雅格调逐渐倾向性灵,但也并未放弃对格律的追求。如,吴镇晚年所作的《牵丝草序》指出:“游览多,则诗之境界宽;推敲久,则诗之格律细;别择严,则诗之门户真,其流传必远矣”[3],在《晚翠轩诗序》中,吴镇认为:“官不必大,惟其称;诗不必多,惟其工”[3]。
事实上,吴镇与王鸣盛的诗学理论同出明“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诗学渊源是一致的。吴镇的诗学观源于其师牛运震,而牛运震的诗学又曾受到李梦阳的深刻影响。牛运震既是乾隆前期著名的儒家学者,又喜欢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其论诗主汉魏盛唐,重格调,与李梦阳的诗学观比较接近。“乾隆朝西陲能诗者,以狄道吴松厓镇为最。尝从牛真谷运震游,真谷诗得派于北地,北地为松厓乡先辈。”[12]北地即指李梦阳。牛运震讲学兰山书院时,常提及李梦阳,吴镇《奉慰真谷夫子》一诗就提到其老师牛运震为“空同门下客”[13]。吴镇对乡贤李梦阳极为尊敬,受李梦阳的影响也很深。吴镇有集句诗《咏李空同》:“弱冠参多士,思为北地雄。郗超初入幕,荀息本怀忠。汎览周王传,多逢鲍氏骢。流连披雅韵,松桂比真风。”[14]信阳指何景明,尤展成即尤侗之字,吴镇对尤侗的评价是认同的。王士禛写作《论诗绝句》时在康熙二年(1663),时年30岁,认为:“中州何李并登坛,弘治文流竞比肩”[15]236,对李梦阳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后来因诗学观变化,对李梦阳转为批评,《精华录》遂删去。吴镇对王士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可见其对李梦阳的回护之意。吴镇对李梦阳的诗作评价很高,如卷三引李梦阳的《登啸台》诗:“阳翟看山二月回,莲池登啸九天开。晚立长风摇海色,东西日月照孤台。”并评曰:“笔阵莽苍,足空千古”[16]。
王鸣盛是沈德潜的亲传弟子,而沈德潜的格调诗学也与李梦阳有很大关系。沈德潜虽出自叶燮门下,但其格调诗学对前后七子的格调论继承颇多。“沈德潜诗歌复古理论与明七子一脉相承。”[17]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最推崇七子,认为七子是“古风未坠”,“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18]1表明继承之意。李梦阳为七子之首,沈德潜对李梦阳评价甚高:“弘正之间,献吉、仲默,力追雅音。”[18]1“有明之初,承宋元遗习,自李献吉以唐诗振,天下靡然从风,前后七子,互相羽翼,彬彬称盛。”[19]1“空同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及自然;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藐焉寡俦。”[18]89选诗也能看出倾向,《明诗别裁集》选李梦阳诗47首,居明人诗歌第二。
吴镇与王鸣盛的诗学渊源相同,还表现在吴镇曾直接受到沈德潜的影响。吴镇早年主要生活在关陇地区,远离诗学中心,对执掌乾隆前期诗坛的沈德潜非常仰慕,受其影响颇深。《松花庵诗话》多处提及沈德潜及其论诗观点,如《松花庵诗话》卷一评沈青厓《咏杨花》《咏向日葵》两诗,直接引沈德潜话语代替评语:“沈归愚宗伯谓其工于用意,犹江潭之屈子也。”卷二再次提到沈德潜为沈青崖诗集作的序,“沈归愚先生序沈寓舟诗云:‘诗家之患在乎读诗成诗而不探其源,此犹铸钱者,凭仗废铜而不探铜于山,亦见泉流之立涸而已。’此诚不刊之论。”[11]
由此可见,吴镇和王鸣盛的诗学渊源同一,理论相近,是两人能成为知音,建立万里神交的关键所在。由此,王鸣盛在格调诗学走向衰落,性灵思潮席卷全国之时,突然看见远在西北的吴镇还秉承格调诗学写诗论诗,知音之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也展示出格调诗学在乾嘉之际的生存状态。
三、乾嘉之际格调诗学的生存状态
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去世以后,已经退居随园的袁枚接过乾嘉文坛盟主的大旗。袁枚以性灵诗学理论为号召,广交南北各地诗人,一时天下诗人纷纷学习他的诗学理论,性灵诗潮风行全国,形成“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20]的局面。各地诗人以能够拜访袁枚和诗作能被选入《随园诗话》为幸事,“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21]清中期的诗学思潮由此从格调转向性灵,孙原湘曾在《籁鸣诗草序》中指出:“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诗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才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者为胜,风格一变。”[22]152蒋湘南也曾总结乾隆诗坛局面:“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23]
事实上,乾隆后期的诗坛并非性灵诗学一统天下,格调诗学理论也并未销声匿迹,以王昶为代表的“吴中七子”仍然坚守格调派阵地,格调诗学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此处仅举出“吴中七子”卒年即可见出格调诗人在沈德潜去世以后的存在状态。赵文哲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黄文莲卒年不知,其担任河北唐县知县在乾隆二十五年前后,后任河南泌阳知县,卒于任,去世时间应该在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吴泰来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曹仁虎卒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鸣盛卒于嘉庆二年(1797);钱大昕卒于嘉庆九年(1804);王昶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黄文莲和赵文哲去世较早,吴泰来、曹仁虎去世于乾隆后期,而名声最大的王鸣盛、钱大昕和王昶三人均卒于嘉庆年间。虽然王鸣盛和钱大昕主要成就在史学,但并未废诗,影响仍在。继沈德潜之后成为格调派中坚力量的王昶卒年最晚,影响也最大。王昶在沈德潜去世以后,主动扛起了格调派大旗,极力宣传格调诗学理论,与性灵诗学分庭抗礼。王昶的学生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藩从先生游垂三十年,论学谈艺,多蒙鉴许。后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乃痛诋简斋,隐然树敌,比之清魔。提倡风雅,以三唐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黏者,皆在门下。”[24]王昶“痛诋简斋”,除了批评其性灵诗学甚至指责其放浪行为外,还广收弟子,提携才学士子,“所至朋旧文宴,提倡风雅,后进才学之士执经请业,舟车错互,履满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显者甚众。”[25]著名作家黄景仁、汪中、毕沅、阮元等皆曾从其学,与袁枚争立诗学门户。王昶还有针对性的编选了《湖海诗传》,该书收录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嘉庆八年(1803)之间诗人诗作,选诗四十六卷,诗人六百余人,选诗论诗以格调风雅为主。袁枚在嘉庆二年(1797)去世,而王昶活到嘉庆十一年(1806),其影响力在袁枚去世以后继续扩大。王昶实际上是沈德潜之后格调派领袖,王豫《群雅集》说:“豫谓自文悫后,以大臣在籍持海内文章之柄,为群伦表率者,司寇一人而已。”[26]在他的努力之下,格调诗学仍然还有大量的拥护者。
相对于乾隆后期,嘉庆时期的诗人对袁枚的批评变得更加激烈,为弥补风雅之道丢失和诗风浅率的弊病,格调诗学有所复兴。姚门四杰之一、桐城派代表方东树把风雅之道的丢失归结到袁枚的性灵诗学,他说:“如近人某某,随口率意,荡灭典则,风行流传,使风雅之道几于断绝。”[27]此论在当时比较有代表性。嘉道之际著名诗人、诗学家潘德舆批评袁枚,并对“性情”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在《诵芬堂诗序》中说:“古之所谓性情者,吾于周诗得一言焉,曰‘柔惠且直’。美矣哉!此性情之圭臬也。晚近之诗,于己矜而偏,非柔惠也;于人伪而谈,非直也。夫柔惠,仁也;直,义也。二者参和而时发,韩子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者也。”[28]潘德舆把性情归到仁义的范畴之下,强调性情必须是合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实际上是对格调诗学的复归。
诗学思潮的演进是渐进式的,这一特点在地域文学身上体现的更加清楚。由于信息交通以及地域文学本身传统等因素,地域文学具有相对的保守性,各地域文学受到诗学思潮影响时间是不一致的,影响的力度也不一样。格调诗学曾盛极一时,沈德潜去世以后,其在各地的影响也仍然存在,民国学者钱基博论乾嘉诗坛时,已有这样的认识:“其时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潜。德潜少从吴县叶燮受诗法,其论诗最崇格律。……踵其后而以诗名者,大兴有舒位,秀水有王昙,昭文有孙原湘,世称三君。四川有张问陶,常州有黄景仁、洪亮吉,江西有曾燠、乐钧,浙中有王又曾、吴锡祺、许宗彦、郭麐,岭南则有冯敏昌、胡亦常、张锦芳三子,而锦芳又与黄丹书、黎简、吕坚为岭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学,未尝及德潜门,而实受其影响者。其中以舒位、孙原湘、黎简三家,尤为特出。”[22]40同样,在诗学中心地带之外的西北诗坛,也仍然活跃着一群受到格调诗学影响的诗人。西北的格调诗学理论首先源于牛运震的传播,牛运震回到山东以后,吴镇成为主要传播者。特别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吴镇罢官回乡,五年后主讲兰山书院,在他周围,以他的诗友和学生为主,逐渐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这个作家群以吴镇为中心,本地作家以张翙为代表,旅居作家以杨芳灿为代表,他们以吴镇担任山长的兰山书院为主要场所,往来赠答,相互评点诗文,西北文坛一时称盛。在吴镇的影响下,西北兴起了一股格调诗学之风,至乾嘉之际仍然不衰。此处仅以核心作家张翙和杨芳灿为代表略作叙述。
张翙(1748年—?),字风飏,号桐圃,甘肃武威县(今武威市)人。张翙卒于何年暂且不知,据江苏无锡人秦瀛于嘉庆六年(1801)为张翙《念初堂诗集》写序一事可知,嘉庆六年前后,张翙仍健在。张翙颇有诗名,袁枚采其《过商州》和《晚自四安开行,深夜小泊》两首诗作入《随园诗话补遗》,有《念初堂诗集》四卷,存诗三百余首。吴镇比张翙大二十八岁,两人为忘年之交,张翙曾师从于吴镇的武威同学孙俌,故两人相识应该很早。乾隆三十六年(1771),吴镇进京赴试,曾与张翙日夕饮酒论诗,此年吴镇五十一岁,张翙二十三岁。直到吴镇去世,他们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两人诗集中均载有多首相互往来赠答诗作。张翙对吴镇极为尊敬,以师相称,《赠沅州吴信辰使君》:“李杜传衣在,于今复几人。高才见夫子,腾步蹑芳尘。赊遍泪庭月,吟残湘渚春。风骚流政化,芳草亦精神。”[30]事实上,张翙诗宗盛唐,好杜甫,格律工整,确实深受吴镇影响。吴镇《雪舫诗钞序》评其诗作特点为:“情挚而景真,格高而韵胜,摘其合作,虽古人奚让焉。”[31]秦瀛在《念初堂诗集序》中评其诗:“各体皆胜,而五言尤工。其峻杰雄特,沉涵淳滀,大略根柢李杜,而兼取高、岑、王、孟诸家之长,渊渊乎盛唐之正声也。”[32]潘挹奎《武威耆旧传》评其诗:“为诗力追盛唐,五言尤工,沉挚于子美为近。”[33]
杨芳灿(1753—1815年),字才叔,号蓉裳,江苏金匮(今无锡)人。杨芳灿是乾嘉时期著名作家,又是袁枚的学生,他的诗学观变化更有代表性。杨芳灿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担任伏羌知县,后长期在甘肃做官,与吴镇交往时间长达二十年。两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论诗品文,相互影响非常明显。杨芳灿说:“余自辛丑岁,识吴松厓先生于兰山,定忘年交,每过从,必论诗。”[34]421吴镇《杨蓉裳荔裳合刻诗序》也说:“盖蓉裳久官甘省,与予论诗,尝有水乳之合。”[3]作为袁枚的学生,杨芳灿论诗主性灵,到甘肃后受吴镇的影响,诗学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重视格律。《张春溪诗序》:“感触由于境遇也,境之真者,语必工;情之真者,传自选。”[35]188《药林诗钞序》:“情至者,语自真;志和者,声自雅。”[35]193其诗论虽然继承了性灵诗学关于诗歌写真性情的要求,但已经开始要求诗歌格调和格律工整了。
四、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杨芳灿的诗学观变化其实也展现出了格调诗学在当时的发展趋势,那就是逐渐走向与性灵诗学的合流。杨芳灿论诗本来主性情,在受到西北文化环境和吴镇的影响后,转向性情与格律并重。吴镇晚年在杨芳灿和袁枚的影响下,也走向性灵与格律结合的诗学道路,如《雪舫诗钞序》:“《雪舫诗》情挚而景真,格高而韵胜,摘其合作,虽古人奚让焉。”[31]《马让洲诗序》:“盖让洲古诗坚卓,近体清研,骨以格高,情缘韵胜,今摘其合作,足追古人,余稍涉流易者,直汰之可矣。”[31]《李坦庵诗序》:“吾州李实之孝廉,以高才逸气,枕藉风骚,尝出其《坦庵诗稿》就正于予。予受而读之,则和平安雅,如其为人,写景摅情,悉脱凡近。”[3]格调诗学和性灵诗学各领诗坛三十余年,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格调诗学主风雅格调,强调温柔敦厚和格律工整,失之性情自我;而性灵诗学主性情,强调诗歌生趣和自然,失之浅率流俗。吴镇和杨芳灿主张格调诗学和性灵诗学的融合,正可补各自的弊端。吴镇从格调诗学出发,吸收了性灵诗学的主张,而杨芳灿从性灵诗学出发,吸收了格调诗学的主张。两人的诗学转向是自发的有意识的选择,虽未提出鲜明的理论主张,但却较早彰显了嘉道诗学发展方向。
嘉道时期,受时局变化和汉宋学术思想融合的影响,诗人们关心国家和社会,面向现实,主张经世致用,视野都比较通达,逐渐形成了融通的诗学思潮。“嘉道学术汉宋兼宗的开放格局和创新精神造成了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也使士人人格走向独立,因而这是一个共融的时代,一个自由思考、独立创造的时代。兼长相济的开放思维使嘉道士人形成了融通的诗学观,诗界普遍主张跨越唐宋畛域,融汇各家,广师开新。”[36]31在融通的诗学思潮之下,嘉道时期主张性灵诗学的诗人们在吸收格调诗学理论的同时,承传格调诗学理论的诗人也吸收了性灵诗学的合理成分,格调和性灵逐渐走向融合。
被称为性灵派后劲的诗人如张问陶、宋湘、舒位等人,也在反思性灵诗学的弊端中吸收一些格调诗学的主张。“嘉庆时期,性灵后劲在一片批判声中诗思已经有所变异。如张问陶实非雅音的诗,宋湘揭示民情民隐的诗,还有彭兆荪的‘清深’、舒位的‘郁怒’和王昙的‘奇纵’,都显示出性灵诗的内涵开始走向深警。”[36]45另外,对袁枚执弟子礼的孙原湘也受到格调诗学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温柔敦厚谓之性情。”[37]评价他人诗作时甚至以儒家诗教为标准:“读君诗者,以和平温厚工于语言,谓有得于风雅之遗。”[22]322其《翁紫书诗集序》则直接提出“政教”一词:“集中如《喜雨》、《甲子河》诸作,悉有关于政教,其植乎诗之本者深矣。”[22]322徐世昌《晚晴籍诗汇》曾记载:“吴兰雪访羽可于黄树斋所,因论两人诗工拙云:‘羽可之诗,乐府特佳,余皆酝酿深醇,粗枝大叶,不假修饰。其拙处往往不工对仗,然不疑其可传。己诗如一匹天孙锦,五色斑斓,无瑕可指,然真气亦坐此雕损。’树斋以为确论。”[1]5505此段话中提到的三人均是嘉道时期著名诗人:吴篙梁(1766—1834年),字兰雪,(江西)东乡人,历官黔西州知州,著有《香苏山馆诗集》二十四卷等。郭仪霄(1775—1846年),字羽可,江西永丰人,官内阁中书,著有《诵芬堂诗钞》四卷等。黄爵滋(1793—1853年),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官礼部侍郎,著《仙屏书屋诗集》十六卷。吴篙梁曾师从于性灵派主将蒋士铨,但论诗却批评郭仪霄“不工对仗”。格律工整是格调诗学的要求,而求真是性灵诗学的要求,吴篙梁的要求以及黄爵滋的认同正体现出当时诗人融合格调和性灵的趋势。
另一方面,面对日渐衰落的社会局面,格调诗人纷纷关心现实,走向经世致用,他们在振兴诗教的同时,也主动吸收性灵诗学的一些优秀理论。作为格调派传人,曾师从王昶的嘉道时期著名学者、诗人阮元即持论通达。阮元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后逐渐登上诗坛,成为嘉道诗坛重要人物。阮元主持风雅,论诗以格调为正宗,《群雅集序》认为:“近今诗家辈出,选录亦繁,终以宗伯(沈德潜)去淫滥以归雅正为正宗”[38]但其也能折衷诸说,接受性灵诗学,其《灵芬馆二集序》评价郭麐的诗:“其为诗也,自抒其情与事,而灵气满天,奇香扑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深于骚者乎?”[39]被阮元评论的郭麐(1767—1831年),是嘉道时期著名诗人,曾师从姚鼐,又问学于王昶,其持论亦融合格调与性灵:“文之无情者,固不足以传,有其情而才与学不足以达之,则情虽至而文不至,鄙陋阘茸,岂足行远?譬如诗言格律,固不足以尽之,然废是则无以为诗。”[40]郭麐在《灵芬馆诗话》卷八中讨论了乾隆时期三家诗人后指出:“要皆各有心胸,各有诣力,善学者去其皮毛,而取其神髓可矣。”[41]这种观念代表了嘉道时期所有诗人的认识,嘉道诗人正是客观地面对乾隆以来各家诗学,学其神髓,调和格调与性情,形成融通的时代诗学思潮。
总的说来,从乾隆后期到道光年间,诗学理论从格调、性灵甚至肌理几股诗潮的并立演进和论争,逐渐走向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重视格调的诗人在关心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主张抒发性情,而重视抒发性情的诗人也开始关心时局,吸收格调诗学的诗教观,共同走向诗歌的经世致用,最终引导了晚清诗学的潮流。在这股诗学观的融合潮流之下,格调诗学产生了较大的作用。乾嘉著名学者、诗人王鸣盛和西北著名诗人吴镇的的交往,正好反映出格调诗学在乾嘉之际的生存状态。而受到格调诗学影响的吴镇、杨芳灿等在乾嘉之际走向格律与性灵的结合,为嘉道诗学融合走向指出了方向。
[1]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刘壬.戒亭诗草:卷首[M].刻本.乾隆年间.国家图书馆藏.
[3] 吴镇.松厓文稿[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1820(嘉庆二十五年).甘肃省图书馆藏.
[4] 王鸣盛.松花庵诗集序[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5] 吴镇.松厓文稿三编[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1820(嘉庆二十五年).
[6] 杨芳灿.皇清诰授朝仪大夫湖南沅州府知府松厓府君行略[M].刻本.1797(嘉庆二年).
[7] 牛运震.松花庵诗序[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1820(嘉庆二十五年).
[8] 吴镇.松花庵声调谱及八病说序[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1820(嘉庆二十五年).
[9] 李华春.八病说跋[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1820(嘉庆二十五年).
[10] 吴镇.松花庵诗话[M]∥吴镇.松花庵全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
[11] 吴镇.松花庵诗话[M]∥吴镇.松花庵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
[12]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M].续修四库全书:1707册.
[13] 吴镇.玉芝亭诗草[M].刻本.1749(乾隆十四年).
[14] 吴镇.律古续稿[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1820(嘉庆二十五年).
[15] 郭绍虞,钱仲联.万首论诗绝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6] 吴镇.松花庵诗话[M]∥吴镇.松花庵全集:卷三.刻本.
[17] 王玉媛,王英志.论沈德潜诗歌复古论对明七子复古论的修正与完善[J].江苏社会科学,2009(4):137.
[18] 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卷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9]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96:1.
[20]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1] 姚鼐.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十三[M].续修四库全书:14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3.
[22]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一[M].续修四库全书:1488册.上海:上海古指出版社,2002.
[23] 蒋湘南.游艺录:卷下[M].刻本.1852(咸丰二年).
[24]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 阮元.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M]∥佚名.揅经室二集:卷三.刻本.1823(道光三年).
[26] 王豫.群雅集:卷三[M].刻本.1807(嘉庆十二年).
[27] 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7.
[28] 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一十八[M].刻本.1849(道光二十九年).
[29] 钱基博.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0] 张翙.念初堂诗集:卷二[M].刻本,1801(嘉庆六年).
[31] 吴镇.松厓文稿续编[M]∥吴镇.松花庵全集.刻本.1820(嘉庆二十五年).
[32] 张翙.念初堂诗集:卷首[M].刻本.1801(嘉庆六年).
[33] 潘挹奎.武威耆旧传[M].杨州:广陵书社,2007:447.
[34] 杨芳灿.胡静庵诗文集序[M]∥郭汉儒.陇右文献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421.
[35] 杨芳灿.芙蓉山馆文钞:卷三[M].续修四库全书:14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6] 于慧.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诗歌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37]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二[M].续修四库全书:14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8.
[38] 王豫.群雅集:卷首.[M].刻本.1807(嘉庆十二年).
[39] 阮元.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0] 郭麐.灵芬馆杂著三编:卷七[M] .佚名.清代诗文集汇编:4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75.
[41]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M] .续修四库全书:17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0.
[责任编辑:林漫宙]
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Jiadao Poetics from the Friend-Making Communicationof Wang Mingsheng and Wu Zhen
YANG 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After Shen Deqian’s death, Yuan Mei’s poetics of natural disposition starts to very popular in the poetry circle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he taste poetics is still existing. After reading the poetry anthology of Wu Zhen, a Northwest writer who still insists on the taste, Wang Mingsheng volunteers to make communication with him. Observing the process of their whole communication can thoroughly explore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of taste poetics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Meantime Wu Zhen and his good friend Yang Fangcan’s integration of taste and natural disposition symbolizes the changes of poetic theory, manifest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Jiadao poetics.
Wang Mingsheng; WuZhen; Qian-Jia Period; poetics of taste; poetics of natural disposition
2015-12-31
I206.2
A
1004-1710(2016)06-00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