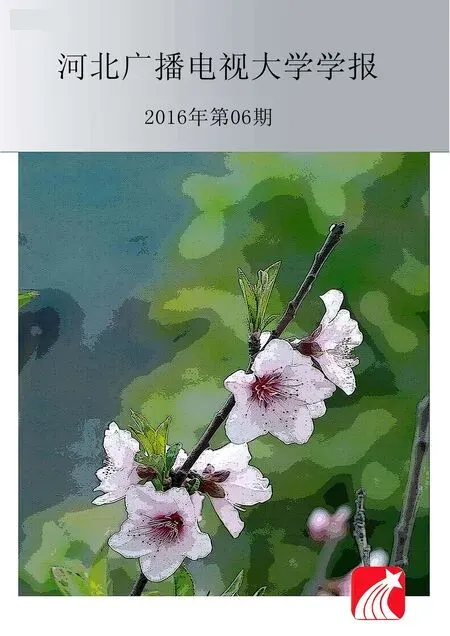卞之琳与戴望舒的同题诗《寂寞》解读
2016-03-07史新玉
史新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卞之琳与戴望舒的同题诗《寂寞》解读
史新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卞之琳和戴望舒曾在20世纪30年代各自写过一首题目同为“寂寞”的诗,虽然都是现代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且两首诗写于同一时期,但无论内容、风格还是表现形式都各具特点,在处理主客体关系上也不尽相同。卞之琳的诗主“智”,作品中很少出现直抒胸臆的语汇,在《寂寞》中,诗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讲故事,表达了一种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世界空间里处处弥漫着的寂寞气息;戴望舒的诗主“情”,且更注重形式,继承中国传统格律诗音韵特点的同时,用心灵烛照的方式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寂寞与惆怅。
《寂寞》;卞之琳;戴望舒 ;现代诗派
卞之琳与戴望舒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他们各自写过一首题目为“寂寞”的诗。虽然两位诗人的两首诗作题目和题旨相同,都为永恒的“寂寞”,但二者的具体意蕴和语言形式均有所异,表达的“寂寞”情怀也自持特点。同时,提到对诗歌主旨含义的剖析,有一点不可忽视,即诗歌的多义性,诗人承担着“社会人”与充满个性的“具体人”的双重身份,面对同一种事物,作为“具体人”的不同诗人将通过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以使诗歌产生不一样的表达效果。
一、智性的冷峻:卞之琳的“寂寞”
卞之琳作为智性诗的代表诗人,其诗冷峻多思,颇具哲学思辨色彩,他以旁观者的角度体察人事,将其尽收眼底。诗人从诗作中完全走出,或者说是消隐其间,“深刻的哲理通过小孩子与长大后、乡下与城里、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对比以及人和事的对比显示出来,诗意隐藏较深,表达也客观冷静……”[1](P243)卞之琳的《寂寞》如同本人的其他诗作一样,并没有华丽的辞藻,如同被压干的花片,脉络却清晰可见,诗的逻辑联结块被抽走,我们却可以将其重新排列组合,从而领悟到更多的含义。
在《寂寞》一诗中,诗人讲述了一个乡村孩子的一生:小孩子长大后离开乡村故土来到城市,生活节奏由慢变快,在光怪陆离中深感寂寞与迷茫。然而,城市里捉不到夜夜鸣叫的蝈蝈,“机械化”正是城市文明的象征,于是他买了一只夜明表,深夜难眠之时,看着夜明表的夜光指针不停地转动,听着夜明表滴答的声响。当他死后睡在坟墓里,夜明表并没有因为主人的死亡而停止运行,而是任凭坟前野草蔓延,蝈蝈依然悠闲地叫着,只是过去在坟墓外倾听它们歌唱的人早已在坟墓里睡去,他的灵魂将成为蝈蝈们永远的听众。针对诗中乡下小孩子的童年生活,一种观点认为孩子的童年是欢乐的,另一观点则称他从生到死都是不幸的、寂寞的。
有学者认为,小孩子的童年是在快乐的生活方式中度过的,“没有尘世的纷杂、生活的离乱,只在寂寞的沉静中寻找生活的快乐。这是一种理想之境”,在童年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痛苦,有的只是“静逸、祥和、温馨、愉悦”。[2]罗麒也认为,乡下的小孩子是天真烂漫的化身,他尚未接触人生的苦难与艰辛,不懂得寂寞的悲哀,所以即便有寂寞也是无知的寂寞、快乐的寂寞。“枕头边养一只蝈蝈”就能带给他无穷的乐趣。[3]事实上,作者写这首诗的意图是表达城市沦落者的寂寞,而乡下孩子快乐的童年生活与其日后的城市漂泊生活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学人潘庆玉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乡下孩子之所以会羡艳蝈蝈有墓草作家园,是“侧面写出了孩子的不幸和凄惶”,因为墓草是“一派荒凉凄清的景象”。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墓草在成人的眼里的确是凄凉悲伤的,然而,以一个孩子的眼眸去看世界,世界总是充满爱和美,他能够把“不好”的事物转化为美好,可见其内心是晴朗的,生活是幸福的,孩子认为墓草是蝈蝈美丽的家园完全说得过去。而且,作者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蝈蝈’写出了乡下孩子温馨的童年生活,写出了被现代文明所忽视遗忘的自然生命的存在状态。”[4]这显然前后矛盾。
乡下孩子的成年时光在城市里度过,他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追逐梦想,面对城市的繁华,感到迷茫与无助,在操劳中寂寞,于寂寞中操劳。有人说,他的寂寞是一种乡愁,也有人说,他的寂寞是对生存的困惑。笔者认为,城市中没有陪伴他的蝈蝈,也没有闲适的自然环境,有的是夜明表和灯红酒绿,于是引发了他淡淡的乡愁。然而,他为什么没有回家,而是买了夜明表?这是他对生存的困惑之后的定格,夜明表象征着机械化,象征着城市文明,他希望能够融入现代化大城市中,就算寂寞,就算操劳,他也愿意为实现这个人生目标而付出代价。这正是从侧面反映出“五四”落潮后,一大批青年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所形成的生存价值观。
诗中写道:“小时候他常常羡艳,墓草作蝈蝈的家园。如今他死了三小时,夜明表还不曾休止。”[5](P41)对于乡下孩子的死,学者们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死后灵魂归于平静,二是他至死都没有明白生命的真谛,夜明表也不曾停息。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笔者更倾向于前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把孩子乡下的童年生活与城市的成年生活理解为两种生存价值观,孩子羡艳蝈蝈以墓草为家园可以看出,他在生命的初始阶段所向往的就是平静祥和的自然生活。随着社会思想风气的演变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小孩子的生存价值观也发生巨大转变,为了能够在城市中生存而不辞辛劳,这是第二种生存价值观。直到他死后,夜明表还不停地转动,暗示着城市文明还在继续着它的脚步,这个曾经的孩子终于可以在以野草为衣的坟墓里安息,那里有他童年最亲密的玩伴——蝈蝈为他歌唱,他不用再为生计忙碌奔波,也不会再感到寂寞。当然,我们不去对第二种生存价值观批判什么,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一大批“乡下孩子”试图融入工业城市,尝试迈向时代前沿,是颇具勇气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人。一定程度上讲,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贡献,作者写此诗的意图也不在于对这两种价值观进行评价,而是为了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人所面对的生存困境,同时抒发诗人自己的寂寞之情。卞之琳的《寂寞》残忍地告诉人们,人在时间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夜明表还不曾休止”[5](P41)是因为时光不可止,更不可逆,它不会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死亡或任何一件事的发生而停滞不前,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思想、生活,甚至命运,而生命与死亡的距离,虽然仅仅表现在墓草下的坟墓里与坟墓外,却是最遥远的。
卞之琳借鉴了西方的“非个人化”理论,诗中捕捉不到诗人的影子,而乡下的小孩子好像就是诗人自己,又可以说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类。诗人仿佛在表达诗歌思想时放弃了自己“具体人”的身份,仅把自己定格为“社会人”,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但他并没有完全采用西方“主客二分”的观念,不可置否,寂寞情思其实还是来自于诗人身处于那个时代的真实体验,这恰恰体现了诗人在处理自己与诗歌的距离时,把握了文学创造主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将诗歌中的情思主体化,又将自己客体化,在诗中无一表现自己的存在,实现了真正的主客体的统一。
二、心灵的烛照:戴望舒的“寂寞”
施蛰存在《又关于本刊的诗》中宣称:“《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6]这里的“现代的辞藻”和“现代的诗形”指的就是诗体和语言。戴望舒与卞之琳同为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诗歌在语言和形式上却大相径庭。
戴诗中,“托根于我旧时的脚印”[7](P127)可以看出“我”之前来过这里,“渐离离”则表明“我”距上一次来已有一段时间。“星下的盘桓从兹消隐”,“盘桓”指的是“我”的脚印,曹植在《洛神赋》中写道“怅盘桓而不能去”,正有无限踌躇之意。在《寂寞》这首诗里,诗人将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反映了“我”当时寂寞徘徊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我”留下的脚印才曲折回绕。“从兹消隐”则是因为脚印被野草覆盖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园中人迹荒芜,野草已经长得和“我”一样高,“寂寞已如我一般高”则反映出,上次“我”在园中徘徊之后,野草与寂寞共同生长,野草愈绿,寂寞之情愈强烈。
首先,与卞之琳的智性诗不同,戴望舒的诗主情,以《寂寞》来讲,戴望舒的诗在抒发情感时更加直白,他将“寂寞永存”四字直接缀于诗中,题旨十分明了。 “渐离离”“可怜的”“旧时的”“星下的”等修饰词的运用,使诗歌变得绵长,将寂寞的情绪更加诗意化。在处理主客体关系的时候,卞之琳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而戴望舒则在诗中凸显“我”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说,戴望舒的诗歌是“个人化”的,“诗人强调对主体个人内在世界的自我审视与表现,将个我的生命意志、情感、欲望、本能等当作诗歌关照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的主视角”[8],《寂寞》这首十二行的诗中一共出现了5个“我”字,“园中野草渐离离, 托根于我旧时的脚印”[7](P127),如果把这句诗中的“我”去掉,变成“园中野草渐离离, 托根于旧时的脚印”并没有大影响,诗人却将“我”写入其中,并且不是“你”或“他”,这正是诗人在诗歌中强调“个人化”的体现。
并且,戴望舒继承了后期新月派诗人的风格,更加重视诗歌的格律化。《寂寞》一诗,第一小节的“离”“印”“衣”“隐”隔行合“一七”辙与“人辰”辙;第二小节的“存”“草”“魂”“高”隔行合“人辰”辙与“遥条”辙;第三小节的“去”“高”“雨”“老”隔行合“一七”与“遥条”辙。整首诗合辙押韵,三辙相间,隔行换韵,格律十分严整。并且,这首诗采用了闻一多提出的“音尺”概念,非常富有节奏感:
园中/野草/渐离离, 托根于/我/旧时的/脚印。 给他们/披/青春的/彩衣; 星下的/盘桓/从兹/消隐。 日子/过去,寂寞/永存, 寄魂于/离离的/野草。 像那些/可怜的/灵魂, 长得/和我/一般高。[7](P127)
这样就形成:
2/2/3 3/1/3/2 3/1/3/2 3/2/2/2 2/2, 2/2 3/3/2 3/3/2 2/2/3
这两小节的中间两行的音尺各自相同,分别为“3/1/3/2”和“3/3/2”,读起来颇有节奏感,这正符合了后期新月派主张的“建筑美”和“音乐美”。
此外,前面我们提到,卞之琳在处理主客体关系时,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而戴望舒的《寂寞》则是完全的“物我合一”。立普斯认为,人们在对周围世界进行审美观照时,不是主观地被动感受,而是自我意识、自我情感以至整个的人格的主动移入;通过“移入”使对象人格化达到物我同一,于是,非我的对象成为“自我”的象征,自我从对象中看到自己,[9]在《寂寞》中,“野草”扎根于“我”的脚印,寂寞又寄魂于野草,这里采用了“心情外射”的创作理念,即让对象有了自己的情感,间接反映出“我”的脚印是寂寞的,“我”走的路也是寂寞的;野草“和我一般高”,寂寞“已如我一般高”则说明“野草”“寂寞”与“我”共同生长。其实在这里,作者已经将主客体完全地融为一体,我们可以理解为,“我”就是“寂寞”,“寂寞”就是“我”,“我”的灵魂像野草一般孤独无依。这正是“物我合一”的具体表现。
三、不同的“寂寞”,同样的情怀
戴望舒的诗主“情”,且更注重形式,一方面,作为现代派诗人,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表达手法进行了“偏移”,同时又寻求与中国古典诗歌特点如传统格律诗歌的合辙押韵的音韵特点的融合,用心灵烛照的方式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寂寞与惆怅,以及身处浮华的现代都市所带来的孤独,他以野草作为自己灵魂的客观对应物抒发情感,使“寂寞”的代入感很强烈,整首诗氤氲着忧郁感伤的气息。卞之琳诗歌中的寂寞情绪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人体验,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讲故事,将这种寂寞的情绪上升到哲学层面,所以站得更高,他的《寂寞》表达的不只是乡下小孩子的寂寞,而是一种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世界空间里处处弥漫着的气息,这种气息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夜明表”的转动,永远地弥漫下去,这不仅是人类的寂寞,也是社会永恒的寂寞。
寂寞与寂寞是不同的,永恒与永恒也有所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卞之琳与戴望舒的两首《寂寞》尽管内容与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其精神内核却是一致的,也即表达了以诗人自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步履蹒跚的众生所体悟到的“寂寞”情怀。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10]当时的中国处于转型阶段,试图由农业文明向工业现代化进行转换,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增,在这样一种情境下,“现代派的诗人其实是被政治边缘化的一群人,现代派的领袖人物戴望舒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从时代的巅峰跌落下来的曾经的‘弄潮儿’,而卞之琳则是那些刚走出校园的诗人的代表,踟蹰在寂寞的荒街,或流连于唯美的艺术之宫。”[1](P235)卞之琳的《寂寞》写于1935年,戴望舒的《寂寞》写于1937年,两首诗均写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同一种现代情绪,也是现代派诗人共同的主体情思。正如高尔基所说:“诗人不应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他还是时代的回声。”[11]事实上,戴望舒创作《寂寞》的1937年,“京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废名写下《街头》一诗,发表在《新诗》上,这首诗同样表达了寂寞情思:“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7](P23)短短的几行诗中出现了5个“寂寞”,且最后四行诗句的谓语连用“寂寞”来进行语义上的聚合,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表达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与擦肩而过的叹惋,天地万物都被寂寞笼罩。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同一流派的卞之琳和戴望舒两位诗人写出表达时代情绪的同题诗绝非偶然。
卞之琳是寂寞的,戴望舒是寂寞的,现代派的诗人们也是寂寞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是寂寞的,整个时代也是寂寞的,但这两种寂寞情愫不是阴冷与绝望,而是失落中又萦绕着迷惘与探询的期望,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卞之琳与戴望舒两位诗人一个主智一个主情,可以说,他们珠联璧合,相互补充,使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变得多元化,立体化,为创造“五四以来诗歌历史上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12]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之后的学者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1]王勇.现代诗派的民族性建构[M]//张俊才,等.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2]胡玉梅.卞之琳《寂寞》新解——对人类生存关照意识探析[J].传承,2009(5):68-69.
[3]罗麒.生命本质的形象测试——卞之琳《寂寞》赏析[J].语文建设,2010(4):47-50.
[4]潘庆玉.这无边的寂寞何曾休止——卞之琳《寂寞》细读[J].山东教育,2012(8):44-45.
[5]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J].现代,1933(4).
[7]张洁宇.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四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8]王琳.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论戴望舒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8.
[9]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4.
[10]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M]//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2.
[11]高尔基.给基·谢·阿胡米英[M]//文学书简(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98.
[12]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73.
Interpretation of Bian Zhilin and Dai Wangshu’s Same Heading Poem Loneliness
SHI Xin-yu
(Literature Colleg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Bian Zhi-lin and Dai Wang-shu respectively wrote a same heading poem of Loneliness in the 1930s. Although they two were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poets of modern poetry, and the two poems were written in the same period, each poem has,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style and form,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 also lies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Bian Zhi-lin’s poetry claims “reason”. In his works, there are few straight expressions of the poet’s feelings. In the poemLoneliness, the poet as a bystander calmly tells the story, expressing the lonely atmosphere filled with the world’s space everywher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Dai Wang-shu’s poetry claims “sentiment”. The poe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form and uses his soul to express the inner loneliness and melancholy while inheri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rhyme.
Loneliness; Bian Zhi-lin; Dai Wang-shu; modern poetry
2016-10-27
史新玉(1993-),女,山西阳泉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I226
A
1008-469X(2016)06-0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