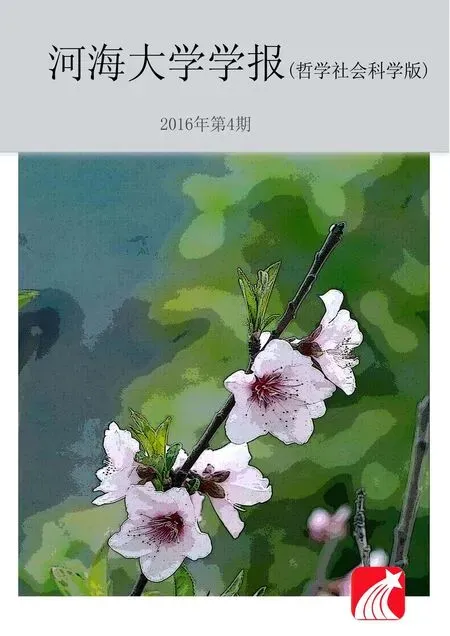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隐喻与逻辑生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解读
2016-03-06陈宗章程广丽
陈宗章,程广丽
(1.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2.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隐喻与逻辑生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解读
(1.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2.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释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以致由此形成的具体生产方式,从不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以致由此形成的市民社会,“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不断进行着空间意义的生产。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的分工和劳动,物象化的人的交往(形式)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被马克思恩格斯指认为“虚幻的共同体”。为了消灭异化的空间,无产阶级需要作为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体存在实现“个人的联合”,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从而释放人的自我解放的全部空间意义。透过这一系列隐喻性的空间话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展现了从空间生产、空间异化到空间解放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空间辩证法逻辑。
德意志意识形态;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空间;逻辑
《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系统阐述的重要文本。正是在该文本中(主要是“费尔巴哈”章),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深刻阐发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内容。当前学界针对《形态》的研究成果丰富而深刻,但大多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时间维度”的优先性为预设前提,“空间”则扮演着被压抑的维度。我们以为,透过《形态》中所揭示的诸如生产、劳动、分工、交往、世界历史、共产主义等带有空间隐喻性的关键概念,我们感受到的是其理论内部跃动着的“空间”脉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显性话语表达中,隐性地夹杂了“空间话语”[1]。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归到《形态》文本所呈现的空间语境中去,深刻把握其内置的空间问题。
一、空间生产:“现实的人”及其交往(形式)关系
马克思“从人间到天国”的致思路向是以“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已经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499这里的“人”已经被深刻地理解为体现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现实的人”,它突出强调人自身摆脱了那种以直观或思辨的方式所把握的规定和性质,进而在历史中、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呈现出本有的存在本质。“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则成为整个空间关系生成的起点,从而彻底击碎了唯心主义对纯粹精神空间的指认,也超越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抽象规定,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现实的人”并非指单纯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着具体历史活动的个人。“现实的人”基于生存的最基本需要,他所从事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经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进而生产自己的全部生活。同时,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人们还会继续产生新的需要,而对这种新的需要的再生产便成为“生产”的第二种形式。另外,为了保证生活的持续性,“现实的人”还要展开人自身生命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生命形式的延续。经由这三种形式的生产,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而根本体现“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总和”之本质规定。这种生产的多层次性(主要包括对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表征了“现实的人”所展开的“人的现实”——即在完成“空间中的生产”的同时建构起“生产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把“人”真正拉入到现实的生活和历史空间中进行“近距离”考察,既摆脱了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纠缠,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感性的直观”的弊病。由此,人的存在和本质不再作为先在的设定而存在,而是表现为一个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即感性的活动过程。
由此观之,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生产”是理解“现实的人”所展开的丰富历史实践的一把钥匙。进一步而言,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的结果对于生产者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的展开便构成了某种矛盾关系,即一定的社会阶段所展示的全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这一过程又是从“分工”开始的。简单来说,分工就是与生产存在共生关系的某种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分工最早体现为家庭内部的性的分工,而在生产劳动的意义上,真正的分工则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开始的[2]53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也正是从“分工-交换”的表层经济关系中来理解生产力的[3]。一方面,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积累,尤其是当生产和交往获得了“世界性”的空间意义,这种促进力更加普遍和强劲;另一方面,分工进一步推动了交往关系的改变,而交往的扩大又改变了阶级关系。即伴随分工和交往所推动的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结构也会发生深刻变化。换言之,在基于分工的生产活动中,“现实的人”不仅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还不断生产出现实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对于该“关系”属性的理解,马克思还着重强调,“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533因此,马克思所言说的“关系”主要指向生产性关系(即基于生产的交往关系),是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的关系,是基于人的意识的能动性作用而展开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之,社会分工的多元化意味着人的活动方式的多元化,进而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多元化的互动关系构成整体的社会力量,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力量的制约。基于这种交互力量的空间结构,社会的发展也就有了必然性(即社会规律)。
当列斐伏尔说:“社会关系作为具体化的抽象物,一旦脱离开空间便不可能真实存在。它们的支撑基础是空间性的”[4]。这就意味着,“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它不断进行着空间意义的生产。“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进而又在总体上完成对“现实的人”的交往关系的规定。换言之,“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生产了自己的历史,也生产了自己的社会空间。马克思对生产过程中人的交往关系的论述,既摆脱了唯心主义所理解的精神活动的关系,也纠正了费尔巴哈理解的类的关系,指认其为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空间性存在关系。可以说,“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历史性生成,也是空间性生成。不仅“历史”没有掩盖或消融“空间”,恰恰正是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展现。
二、空间异化:“物象化”关系与虚幻的共同体
如上所述,“现实的人”之所以成为历史的主体,因为他们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活动的。而在生产、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形式和关系,就产生了市民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540。这里所言说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关系之上的历史,不是脱离现实关系(现实社会物质关系),即脱离市民社会的抽象的历史。由此,“历史”的时间维度就有了“社会关系”的空间维度的支撑,二者是统一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市民社会就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上,基于分工以及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决定的不同所有制形式,进而由此形成的所有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的总和。基于此,也有学者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由“生产(劳动)、所有、分工、交往(交换)”四个要素构成的总体性范畴[5]。可见,市民社会就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关系体,在这一社会空间内部,由于分工、分配导致的利益的不平衡关系,从而直接导致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于是,共同利益便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536。马克思直接指认,“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2]584。然而,当我们仔细考究市民社会所容涵的生产、所有、分工、交往等具体环节时,就会发现:在私有制的阶级关系中,所谓的共同利益往往被具体的、现实的阶级斗争、利益矛盾所代替,后者才是最真实的交往关系形式。那个所谓的以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出场的国家,只能被断定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这个共同利益只是在掩饰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历史事实。由此,马克思直接断言阶级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虚伪性。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从分工到劳动到人的关系,产生了全面的异化。
在现实性上,随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种分工正日益制造出差异化的世界。分工的形成意味着一个复杂的矛盾空间的进一步展开。一方面,有分工就有分配,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分配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2]536同时,这种分工和不平等的分配关系,直接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激化,并在现实中得到真实地呈现。可见,分工带来的异化,本质上就是私有制带来的异化。因为,私有制条件下的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并非自愿形成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分工”的概念,另一方面,分工越发达,引发的空间矛盾越严重。人们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着现实的、共同的活动,它的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分工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与此同时,分工带来的异化力量使得人们并不能驾驭这个现实的力量——生产力,即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已经不是人自身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生产力积累得越多,对人的异化程度越高。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劳动)与生产力产生了某种吊诡式的关系。马克思又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532-533。因此,生产(劳动)与生产力的异化关系则直接表现为生产与交往关系的分离。于是,当现实的生产力不再作为个人的力量存在的时候,个人之间体现为一种孤立的分散关系的时候,个人就被抽空了现实的生活内容,从而成为抽象的人,他们只是在劳动,而私有制完全占有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成为私有制条件下抽象的存在形式。
进一步来说,一旦生产力本身成为私有制的强有表现力量,私有制便成为马克思所言说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它与现实的劳动相对立,甚至成为奴役和统治现实劳动的工具和手段。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财产与劳动的对立,其实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劳动范围内的对立”[6]。事实上,分工导致的空间分裂,本质上即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并最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分工越发达,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分裂越严重。当人完全屈从于这种分工,就会最终带来人自身的异化。从生产(劳动)与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分裂、资本与劳动以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裂,马克思超越了早期基于人本主义哲学视野的异化理论,深刻论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终走向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物象化”理论。著名学者广松涉在其《物象化论的构图》中曾对这一论题作了深入而系统地分析,以强调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的非人格化。吉田宪夫也明确指认,在《形态》中,晚期马克思的“物象化论”基本以完整的形式被阐发出来[7]。总之,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分工显然已经导致物的关系对人的现实统治以及偶然性对个性的统治。由此,异化的分工和劳动,异化的、非人格化的交往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市民社会(尤其是作为真正的市民社会所集中表现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成了马克思指认的“虚幻的共同体”。这种异化的资本主义的空间,在列斐伏尔那里则被指认为抽象的空间。
三、空间解放:世界历史的生成与共产主义的实现
这一抽象的空间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它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一个桎梏。因为劳动是联系个人与生产力的唯一方式,但面对异化的劳动形式,这种劳动并非是个人自主的活动,它既是个人维持自我生存的一种形式,也是资本家摧残个体生命的一种形式。他们无论在哪里都面临同样的命运——被压迫。于是,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称为“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2]567。如何超越这种对立,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解放!这是同一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发生矛盾。生产力在积累中前进,但它却建立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为了超越这种对立,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2]580-581。无产阶级在这场“占有”运动中,既要正视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让占有活动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2]581,同时也要在占有全部生产力的自主活动中释放自身全部的才能。这样“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2]581
然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尽管在生产竞争与分工合作中,关系表现得愈加复杂,但是复杂关系中的个体依然呈现诸多孤立的或地域化的特征。因此,为了消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孤立的或者地域化的无产阶级应该在最终的意义上走向联合,它必将体现最高的空间意义。换言之,实现对生产力的普遍占有,最终是通过“联合的个人”或“个人的联合”来实现的。这种联合体现最高的普遍性,它将抛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2]581,从而实现真正的没有阶级压迫的共同体,即消灭异化的空间,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性空间关系。实现这一点,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共同体中,单个的无产者才不会孤立无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才能解放出来。而这种斗争是以个人与国家的对立为前提的,必须推翻整个国家——“虚幻的共同体”,才能获得人的真正解放。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实现这种联合所需要的现实可能的历史条件。首要前提就是要实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马克思曾指认:只有实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538。由此,人——作为地域性的“现实的人”才能最终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541足以见之,世界历史的形成正是“现实的人”的交往普遍发展的产物。“交往越成为世界性的交往,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8]。“世界历史”不是所谓的思想史、观念史和哲学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和交往关系推动下的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它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体现和表征着世界发展的重大趋向[9],其实质即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事实上,对异化的超越要在“世界性”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它是以击碎物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空间)的狭隘统治为前提的。由此,马克思的空间解放诉求正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将其内置于历史自身矛盾发展之中”[10]。这是一种空间策略。可见,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和世界历史是统一的关系。没有世界历史,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世界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面对不平等的交往、分配关系,无产阶级也将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体而存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放置在最高的时空——世界历史——中才能真正实现,它体现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高度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历史性现象,共产主义则成为替代资本主义的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由此,从个体上升为整体即从一般的生产、分配到世界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从现实的个人到社会整体性关系,生成了《形态》的基本逻辑。
总之,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并要消灭以往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构建一个崭新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空间异化到空间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这种空间逻辑的实际运思,建构起完整的、科学的历史空间架构,并在此体现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空间生成性。
[1] 尤金.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隐性空间话语:空间视域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3):37-4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翁寒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新历史观的艰难蜕变: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继承谈起[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3):1-4.[4]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1991:404.
[5] 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4):40-51.
[6] 张一兵,周嘉昕.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8(4):41-47.
[7] 吉田宪夫.《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论的扬弃和物象化论的奠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5):16-18.
[8] 李金花,苗伟.需要、交往与分工理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三大基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文本学解读[J].理论界,2011(7):12-14.
[9] 聂锦芳.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思想: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研究谈起[J].江海学刊,2008(2):26-33.
[10] 孙乐强.《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J].现代哲学,2013(5):6-11.
(责任编辑:许宇鹏)
10.3876/j.issn.1671-4970.2016.04.004
2015-10-19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10008);2015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B-b/2015/01/043)
陈宗章(1979—),男,山东临沂人,副教授,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B03
A
1671-4970(2016)04-0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