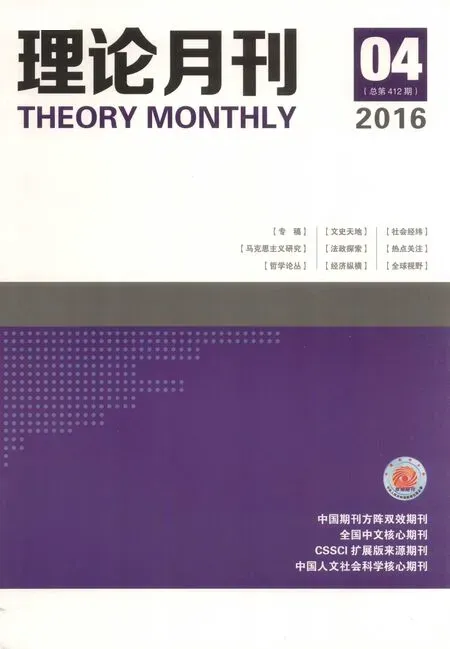抗战期间中共政权诉求路径的历史考察
2016-03-04洪富忠
□洪富忠,丁 威,陈 剑
(1.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67;2.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重庆400054;3.重庆行政学院,重庆400041)
抗战期间中共政权诉求路径的历史考察
□洪富忠1,丁威2,陈剑3
(1.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67;2.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重庆400054;3.重庆行政学院,重庆400041)
[摘要]革命以夺取政权为终极目标,实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归依。抗战期间,以国共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国共关系决定了中共政权诉求的非武力特征。中共在战时的政权诉求路径大致有三:未对中央权力分配提出明确诉求的自下而上地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要求国民党遵循自身规划的“宪政”路径以实现参政目的;以先行解决中央政府权力分配为特征的“联合政府”路径。令人遗憾的是,中共的各种政权诉求路径均因国民党坚持一党训政体制而最终流产,国共最终以疆场胜负决定政坛结局的民国逻辑实现政权鼎革。深入考察中共战时政权诉求路径的历史演进,有助于理解中共战时政策、策略的灵机变化,也有助于我们洞察中共建政思想的演变逻辑。
[关键词]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路径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4.013
①学界关于联合政府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代表性论著可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 1946年的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论文可参见占善钦《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的演变》[J],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
政权问题涉及到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以夺取政权为终极目的。抗战期间,以国共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国共关系决定了中共在战时必须放弃武力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策,但中共的政权诉求并未因奉国民政府为“正朔”而放弃。尽管作为国民政府的“独立伙伴”,[1](P284)中共有自己的地方政权,但作为一个革命政党,这并非中共的最终目的。囿于民族矛盾尖锐,国家处于存亡绝续之秋,中共的政权诉求也必须服从于这一根本大势,其诉求路径也体现出战时非武力特征。对于中共战时政权诉求,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及其演进,而对整个战时中共政权诉求路径的历史考察尚不充分,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请方家指正。
1 自下而上加入国民党各级政权
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东方型革命的突出特点是总会有一段较长的“双权对峙”时期,“革命派在此期间致力于扩大参政并扩大他们的统治体制的规模和权威,而政府则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继续进行统治”。[2](P293)其实,中共在决定同国民党合作时就必须考虑在扩大自身力量的同时如何处理和参与中央政权,即如何“参加政府”。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国共谈判中,寻求中共的合法性与公开性是其重要诉求,成为南京政府中的一员也是中共领导人曾经考虑的一个议题。对于是否参加南京政府,毛泽东在1937年2月10日致电周恩来,要求在谈判中增加“抗日时参加政府”一条。[3](P653)因此时日本尚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打消国民党方面的疑虑,加快谈判进程,2月11日,周恩来向张冲、顾祝同等表示中共代表可以以苏区和红军名义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和军委会,目前无意参加政府,抗日后再议。[4](P358-359)
如果参加政府,中共的组织思想独立能否保持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张闻天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表示,国民党如果能够发表和实行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中共在原则上可以参加这样的政府,但参加政府的党员必须要做到“为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汉奸亲日派的企图,严厉的镇压他们的反抗”,“保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之成为自己依靠的力量”,“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并受党的严厉的监督”。中共如果参加政权,其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迫使政府让步的办法“决不应该放弃。”[5](P278)显然,中共对参加政府附带了相当的要求。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认为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为积极的抗战,以致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一种可能是冀察当局让步而暂时妥协。为了争取前一种前途,中共主张全国总动员,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提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以便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5](P388)呼吁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民主化,吸收各界代表参加政府成为中共此后一直坚持的主张。尽管中共大声疾呼,但事实上却并未参加政府。
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共才会参加政府?中共认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以实际行动表示诚意;允许中共合法存在。中共还规定,“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加入中央政府之前,共产党员一般的亦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显然,国民党要达到中共的要求还有相当难度,同时也在事实上决定了中共不会轻易参加政府工作。不但如此,中共认为在没有达到条件下去参加政府“徒然模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推迟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之建立,是有害无利的”。[5](P528-529)
从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可以看出其对国民党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特别是关于两党合作形式与中共的合法地位没有完全解决,让中共不得不心存疑虑。同时,中共党内高层就是否参加政府在抗战初期还存在一定分歧。毛泽东在1937年11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改造政府”的问题,并提出了临时国民大会的方针。[6](P390)但王明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对前述中共参加政府的草案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对国民党进步认识不足的表现,并说“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关”。[7](P352-353)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政治部副部长一职在党内也有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也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认为在特殊地区(如战区)也可例外,但就总体而言,中共对成为国民党政权中的一份子并未抱积极的态度,中共也未如先前毛泽东所言“抗日时参加政府”。
中共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小心谨慎与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考量密切相关。苏联与共产国际在抗战期间的对华外交政策上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求中国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以争取抗战胜利,这是其对华政策的中心内容;二是维护中共利益防止国民党打内战。[8](P162)中共在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上自然要受这两个基本点的制约。
1938年1月2日,在武汉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致电中央,望中央“如有可能,请转告远方,国民党现在绝无请共产党参加政府之意,对于军委会下之政治部及民运工作,有请共产党方面参加之表示”。[7](P369)共产国际在收到中共请示后,表示“参加政府的问题以前我们告知[中共]中央不参加”。[9](P21)1938年1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就中共是否参加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权时指出,“远方指示我党在此时不应参加政府。参加华北政权机关,当然亦不相宜。”[10](P538-539)这说明中共不参加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一定关系。
王稼祥曾谈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不参加政府的原因。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曾指出:“中共不参加国民政府是对的,国内外有许多反对统一战线的人,我们以不参加国民政府为有利,但军事、国防部门可以参加”。[11](P140)这实际上是指国民党内不少人担心中共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名分国民党权力之实。中共如果强提参加政府工作,恐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反对,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中共均不利。为此,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强调不参加国民政府,以打消那些说“共产党企图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夺取国民党的政权”的言论。[12](P985)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的打压。5月底,斯大林鉴于与英法等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无实质进展,开始改变对德政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对其资产阶级政府由支持改为提防。这也影响到共产国际再次对中共参与国民党政权的看法,国共关系渐趋恶化。在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上,中共参加政府问题屡被提及。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事在共产国际中就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它“引起了关于国民党及其军队被共产化的议论”,常“被反动的报刊和日本的报刊所利用”,认为“中共应该放弃在政府中的职位”。[9](P221-222)鉴于此,任弼时表示他“并不反对撤销周恩来同志在政治部的工作”。[9](P171-172)
可见,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参加政府问题上要“低调”并保持克制。这与苏联当时避免英、美、日各国以苏联支持中共而影响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苏日关系有关,实质上是共产国际以苏联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来决定中共是否参加政府。此前王明对中共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批评实质上是代表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意见的反映。
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关于中国问题报告时就中共参加政权的路线,提出“似应由军事到政治,由战区到内地,由地方到中央”的途径,[9](P315)但此后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一路线无法实现。
中共此时自身实力有限,不具备向国民党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分配的条件,其所提参加政府兼有寻求中共合法性与改造国民党政权的双重意蕴。因此,在抗战期间,中共虽一再呼吁国民党革新政治,容纳各党各派人士参加政府,但并不积极强求,更多是一种宣传策略。政府作为掌握实际行政权力运行的机关,更多讲究服从、做事并承担行政责任。对于欲在国共合作中保持自身组织思想独立性的中共来说,自然不愿给自己增加一层束缚,为国民党徒增“不服从政令”的借口。同时,未能参加政府未必只有其弊而无其利,保持在政府之外,中共可以放开手脚,直言批评。唐纵就认为“共产党在野,说话批评可不负责任,而骗取人民之同情”。[13](P221-222)“骗取”一词固属不当,但在野身份确实有相当的回旋空间,可进退自如。
2 国民党设定的“宪政”路径
既然国民党无法满足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通过国民党自身所设计的政治路径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以实现中共政权诉求成为中共的另一选项,而国民大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国民大会是孙中山所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建国方略中走向宪政,还政于民的一个重要步骤。国民党1928年实施训政后即以继承国父“遗教”为名逐步实施其建国方略。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五五宪草,1937年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在此过程中,中共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共对国民大会的关注早期主要体现在其对召开国民大会重要意义的阐述,关注国民大会是否具有救亡、民主的性质。[14](P22-32)特别是国共内战基本结束,中共将有可能与昔日对手国民党和平相处,怎样在国强共弱的政治生态中保证中共的生存和发展是中共直接面临的现实问题。国民大会既然有由“训政”走向“宪政”的可能,争取召开一个有利于国家民族及中共的国民大会无疑成为中共重要的奋斗目标。藉国民大会,力图在国民党政权体系内取得话语权并争取合法讲坛成为中共在国民大会上“高调”关注的内在动因。
1937年初,伴随西安事变的解决接近尾声,中共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国共有走向和平共处的可能。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议所体现的态度表明国民党对中共问题的解决从军事途径为主转为以政治途径为主。在此形势下,中共的中心是“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4](P362)利用合法斗争,高举民主旗帜,成为中共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途径,而国民大会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国民党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共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大会可能的重要作用。“民主问题将来在我们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要成为争论的焦点”,[15](P140)“争取民主的根本问题是立宪与国民大会的问题”,而目前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与宪法,是民主运动中的基本问题,关联到每一个人的切身问题,我们必须号召群众来注意”。[16](P75)由于“通过介入选举影响国家权力的形成”,“选举也把政党作为不可替代的主体”,[17](P194)中共对于国民大会的选举较为重视,认为“国民大会的选举我们必须参加竞选(如有可能),提出竞选的候选人与纲领进行宣传”。[5](P236)中共试图通过参加国民大会选举,获得合法地位,推动国民党政权民主化,争取在国民党政权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实现参与政权的诉求。
因国民党的长期围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长期局促西北一隅,公开的合法讲坛极为缺乏,不利于扩大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因此,中共认为,只要“南京政府允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或群众选出共产党员为代表时,我们原则上应该参加进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坛与自己合法的地位,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各种有利于民族国家及民权民生的提案,号召与组织群众,推动政府走向民主化”。[18](P274)如果能参与到国民大会的选举,就意味着中共可能在国民党政权体系内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并借国民大会制宪的功能力图改造政府,果能如此,这不失为中共扩大政治影响,改造国民党政权,推动其民主化的绝佳途径之一。
为了获得这个可能的机会,中共一方面批评国大代表选举不具有代表性,提出了自己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的修改意见,但同时也意识到“蒋及国民党不会再修改其已经修改的选举法”,因而在指定代表问题上做出了妥协。中共在不放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联合各民众政治团体力争有利条件,对于蒋介石在国民大会240名指定名额中可指定中共出席代表的条件,中共在事实上也接受,其变化即在于推出240个指定名额的倍数候选人中“要求国民政府聘任(力争不用指定)”。[5](P339)
正是因为国民大会可能牵涉到各个方面,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19](P275)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国共合作宣言中,“召开国民大会”被中共称之为三大奋斗总目标之一,希望以此实现民权政治并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20](P77)
1939年初,随着国共摩擦增多,中共对国民大会的批判则集中在国大代表的有效性问题上,认为战前选举的国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包办,因此要求取消旧国大代表。[14](P22-32)同时,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有关国民大会的论争不仅是国共两党争夺民主主导权的一个工具,而且成为中共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中间党派的重要政治议题,这在抗战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中尤为突出。
1939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审查张君劢、张申府、陈绍禹等七提案,通过治本及治标两条办法,由此开启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治本办法为请政府“命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具体办法为“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黄炎培将这一办法称为“建国之根基”,“民治的起点”。[21](P11-12)国民大会在中间党派追求宪政过程中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因而格外予以关注,中共对国民大会的态度也就成为中共与中间党派关系的反映。中共虽然要求废弃或彻底修改1937年4月30日通过的选举法及1936年5月通过的宪法草案,但中共也意识到前述主张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宣传时期,国民党不会允许全部实行”,[22](P337)“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23](P234)尽管如此,中共对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运动仍然要“积极参加”,[22](P328)以此表明中共对中间党派的理解和支持。中共代表董必武在重庆多次参加宪政期成会的讨论,提出中共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五五宪草”等问题的意见。中共对大后方各地成立的宪政团体也积极参与,国民党方面认为,由中共操纵组成或共党分子积极参加其中工作的有:重庆宪政座谈会(董必武、邓初民等积极参加)、重庆各界妇女宪政座谈会(共党操纵)、成都国民宪政座谈会(共党操纵)、成都国民宪政促进会(共党操纵)、贵阳宪政座谈会(共党潜伏其中活动)、昆明妇女宪政座谈会(共党操纵)、昆明文协会(共党外围组织)、广西宪政促进会(共党从旁操纵)、昆明各界宪政座谈会(共党从旁操纵)。[24]同时,中共要求各地成立宪政促进会的群众团体,并要与国民参政会中的宪政期成会取得联络,为宪政以壮声势。
因皖南事变导致国共两党隔膜日深,中共认为按照国民党所主导的国民大会对一党训政体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结构变革。此前国民党在国民大会、宪政等方面的多次爽约,使中共对其能否达到目的并不抱多少信心,周恩来就认为开国民大会,宣布宪法,当然都是“骗局”,[4](P574)对于国民党主导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并不热心,甚至认为这一运动有可能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因此,中共最初不仅拒绝参与第二次宪政运动,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批判与抵制。[25](P819-821)但与中共不同,以中间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对此次宪政运动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国民党方面也把其十一中全会关于国民大会及宪政问题的决议作为“扩大全国对本党之政治影响”的重要步骤,使中共“民主号召无可利用其技。以防止利用参政机会为其窃取政权之阶梯”。[26]对此,中共调整此前较为冷淡的政策,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22](P678)周恩来在1944年3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参加宪政运动,表示我们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另方面也影响中间党派。[4](P585)也就是说,中共对宪政其实并不抱什么希望,参加宪政更多是表明一种态度,也借此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
国民党设定的宪政路径在战时政权民主化过程中具有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这一道路行得通,中共的政权诉求也能得到有效解决。但问题在于,国共双方对于召开什么样的国民大会,制定什么样的宪法等方面尖锐对立,无法取得共识,利用国民党的宪政路径实现中共政权诉求在事实上其实已经宣告此路不通。中共对国民大会的表态及对宪政运动的参与更多是着眼于与国民党争夺中间势力,特别是中间党派。因为,国民党如果能够按照中共的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改变国民党一党训政局面,实现中共政权诉求的目的;国民党如果拒绝,则中共在国人面前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已广为传播,中共的政治声势已大为扩张,并能吸引中间党派这样的盟友与其共进退。无论国民党接受或拒绝中共关于国民大会的建议,中共借国民大会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的目的均已达到。
3 中共的“联合政府”路径
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特别是战后有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建国,保证中共在抗战期间获得的胜利果实成为一个迫切问题。要维护中共革命成果,必须参与中央政权并能制衡国民党,中共的政权诉求思路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
中共最初的策略是通过国民大会来改造政府。周恩来认为国民大会的任务既要通过民主宪法,还要选出民主的中央政府。[27](P205-206)显然,这是希望以民主的国民大会组建民主的中央政府。毛泽东在1937年5月就中国民主改革的任务时指出,若要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应从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着手,其参与改造国民党政权的路线图为:民主的选举——民主的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选举民主的政府——施行民主的政策。[19](P256-257)
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败不但影响了大后方的各阶层的人心向背,对中共改造中央政权的思路也产生重要影响。斯大林从维护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和防止再次陷入战争泥潭的意图出发,向各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构想。[28](P572)美国也希望蒋介石能容纳中共组成联合政府,拖住日军。国际国内局势的转变使中共认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所提方案核心内容即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29](P488)经多方权衡,,中共代表林伯渠在1944年9月15日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第13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建议。这一主张“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3](P553)国共实力对比变化使中共意识到不能长期隔离在中央政权之外,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政权是中共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显然,1944年的时局为中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号召在大后方得到令中共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特别是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出现大量群众性的集会,热烈呼吁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也曾提及《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行的火热景象。汤恩伯在1945年还报告“广西大学奸党活动甚力,校方无法制止广西大学粘贴标语传单正式集会拥护建立联合政府”。[30]唐纵当时也认为,中共联合政府口号提出以后,“各党派亦和而应之,以至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国民党方面召开中央宣传会议,“发言盈庭,而结果毫无具体有效办法”。[13](P462)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可以说正中国民党党国体制的要害。
既然社会各界对联合政府充满期待,中共有必要阐明自己的具体实施方案。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双十节演讲中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六个具体步骤:各自推选代表,召开国事会议,制定切合实际的施政纲领,成立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27](P773-774)周恩来的演说向外界表明:中共的态度是严肃的,且是有认真准备的,国民党必须予以正视。
按照周恩来的这一办法,中共在参加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联合政府是其中的关键步骤。国民大会虽仍是中共参与国家政权的重要一环,但其重要性已经不如从前,即先组织联合政府再召开普选的民主的国民大会。这是中共试图掌握参与改造国民党政权话语主动权的重要尝试,改变了此前国民党大打国民大会政治牌,中共相对被动接招的状态,使中共以守为攻,国民党穷于应付。
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中共以联合政府的成立为前提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比先召开国民大会再制定宪法更具有可操作性。中共在抗战期间多次要求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改组政府,但此要求多次被国民党以抗战军兴,选举多有不便等理由而延宕。1940年9月,国民党就以各地交通受战时影响而宣布此前拟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召集。确如国民党所言,在抗战期间交通不便,人口大量迁徙流动,相当一部分国土沦陷或成为战区,要组织正式的选举本身确有难度,这种理由也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不利于中共站在舆论的制高点予以驳斥。
在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实施步骤里,首先由各党派、军队、团体自己推选代表,正式普选则以联合政府成立后再召集。换而言之,联合政府的成立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讲比实行普选召开国民大会要容易得多,国民党此前以抗战多有不便的理由便失去说服力,而且这种自己推选的代表所组织的联合政府完全有可能否定此前国大代表的合法性。在这样的基础上组成的具有实际权力的联合政府再去组织国民大会选举,使国民大会的召开、制宪都不再具有此前的决定性意义。这就使得国民党此前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政治策略大失其效,无怪乎唐纵在看到林伯渠致张治中、王世杰函件中关于承认中共军队,组织联合政府相关讯息时认为“无异于国共决裂的通牒”,“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13](P515)正如毛泽东所言,联合政府的提出“是一个原则的转变。[3](P576)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此后中共长期坚持的建政方针。1945年3 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案时指出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其中第二种可能即为独裁加若干民主。[3](P588)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最重要的会议——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的题目即为《论联合政府》。作为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文献,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中共一般纲领是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方面又认为当前的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要求是“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极具包容性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3](P1065)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和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抗战结束后的重庆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乃至新中国的建立都是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延续与坚持。
4 结语
中共的政权诉求在抗战期间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但一条有律可寻的轨迹,这就是以实力变化为归依。从最初的原则宣示到后期的具体推动,显示了中共战时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同时,中共的政权诉求又有宽广的国际背景,共产国际(苏联)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共政权诉求的变化,显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性。遗憾的是,中共的政权诉求在战时均以流产而告终,国共双方最终不得不以疆场胜负决定政坛结局。
战时中共政权诉求的流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其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开放政权。其实,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国民党曾有一定的考虑,党内对是否开放政权也有分歧。唐纵曾认为抗战期间“既不便与共党决裂,在战后与共党决裂又如此增加国家的困难”,其可行之策有开放政权与武力斗争两策,如果“开放政权,容纳共产党与各党派于政府之内,我以政治上优越之地位,掌握政治上领导权,而于无形中消灭共党的斗争”。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可使战争与抗战同时结束,使国家建设开始,得利用外国资金、机器、人才,以从事于国防民生之建设,其利有三”。[13](P379)陈诚则认为,“共产党员非经中央特许,绝对不准服务于各部队机关及军事性质之学校、交通与产业机构中,其在各地一般公私团体服务者必须开列名单,呈报中央,以免除种种流弊”。[32]最终的结果是“各机关人员加入异党查有证据者一律解除其职位”,[33]坚持一党训政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意见。蒋介石也认为,“中共不参加中央政权,中央不承认中共法律地位,保持现有实力,不使损耗,亦不与倭妥协,而政治经济,积极求进步,则俄亦无奈何我矣”。[34](P743)国民党方面担心中共参加政权会增强中共实力,扩大中共政治影响,不利于其反共。可见,在中共政权诉求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掌握着主导权。尽管美苏曾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给予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一定压力,但战争行将结束时复杂的国际局势演变及美苏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使中共的联合政府诉求无果而终。中共政权诉求的流产表面上是中共的“失败”,但实际上也是国民党的失败。国共如果能够共享国家权力,哪怕是以国民党为中心,至少国民党的“专制”色彩将大大淡化,其“民主”形象大幅跃升,战后国民党的结局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方向。
仅从结果来看,中共战时的政权诉求并未成功:直至抗战结束,国民党仍然坚持并保持一党训政体制,中共仍然被排斥与国家权力中枢之外。但在此过程中,中共也有不少收获和启示。
一是大大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中共抗战初期提出参加政府问题,要求国民党各级政权容纳各党派成为一个民主政府的努力虽未成功,但中共要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实现政府民主化的要求无疑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呼应。以国民党的宪政路径实现中共政权诉求的路径尽管未能实现,但国民大会具有代议机关的性质,在此过程中伴随着选举、宣传等活动,对扩大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因此,中共在国民大会问题上不断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便国民大会没有召开,但中共的态度与影响却已广泛传播,达到中共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在宪政运动中与中间党派的接近,也使中共在大后方获得了难得的政治盟友,对于大后方民主阵营的扩大乃至此后国共政争中的人心背向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二是注重政权的顶层设计,不图虚名。在中共政权诉求过程中,都是着眼于改变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权结构,而非枝节问题的解决。如在国民大会问题上,中共曾提议先召开临时国民大会,但临时国民大会不应只是一个咨询会议,而应当是“一个拥有实际权力的机构,它能够解决抗战的实际问题。对于抗战的实际纲领,对于改革军政机构,对于动员民众,它皆能够发挥其伟大的效力”,“它应当有类似法国革命时的国民会议”。[35](P23)国民大会应该是“一方面‘制宪’,它方面解决实际问题的,抗战建国并重的会议”。[36](P144)这显然是希望国民大会扩权,能够解决政权结构中的根本问题。同样,中共认为联合政府也“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37](P214)中共也无法接受那种“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的做法。[37](P251)对于国民党试图以允许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内阁的条件换取中共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从来就不开会,也没有任何权力”,“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并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38](P2)这种没有实际决策权力,只有虚名的“请客”式参加政府显然无法打动中共,因为其不符合中共借联合政府的方式改变国民党一党训政实质的目的。
三是为中共建政提供了启示。抗战期间中共的政权诉求仅从结果来看并未达到中共的初衷,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参政诉求却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亨廷顿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系首先有能力通过这个体系扩大参政,从而抢先进行骚乱性的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或使这些活动转向,其次能节制和引导新动员起来的集团的参政,使之不致于打乱整个体系”。[2](P444)以一党训政为特色的战时中国政治体制显然其包容性并未达到前述“强有力”的状态。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应对并不成功,特别是无法真正把社会各界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有效地纳入其政治制度框架,“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要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取代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39](P12)
训政时期的国民党“借由作为前卫政党的革命性来自我正当化”,[40](P282)以国父“遗教”强调一党训政体制拥有的正统合法性。中共通过实践,认识到国民党即便有此传统优势,但在战时内忧外患的中国也很难凝聚各界政治共识。国民党对以自己为主导,其它党派“入股”的联合政府形式参与政权都予以否决,表明要打破既得利益的政治架构之难,但国民党的统治危机又再次凸显政权必须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才能充满活力并获得支持,即必须“参政扩大化”。如果“政治体制无法为新的社会力量提供参政的渠道,无法为新的上层分子提供参加政府的渠道”,对那些只有在实现政治方面的诉求即参政愿望但却“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社会力量”无视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革命。[2](P444,101,297)基于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三三制”政权,其实质即是扩大参政基础,满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政权的愿望,这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以联合政府的形式推动国民党政权民主化的努力虽未成功,但联合政府所引起除国民党集团以外社会各界的强烈认同与支持却给中共留下了深刻印象,联合政府的精神为中共所继承和发展,大大丰富发展了中共的政权建设思想。配合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壮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而在事实上对国民党一党训政体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为此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提供了难得的借鉴与经验。
参考文献:
[1]陈永法.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郭德宏编.王明年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8]杨俊,程恩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14,(9).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0]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1]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2]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14]张太原,于宝.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态度的变化[J].抗日战争研究,2012,(2).
[15]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2]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2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4]中国共产党活动概况调查报告(1940年6月)[Z].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馆藏号:一般581/400.
[25]邹东涛主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6]奸伪最近采取三种对策之研究对策(1944年3月 6日)[Z].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馆藏号:特22/1.21.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8]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0]汤恩伯致蒋中正电(1945年6月7日),[Z].台北:“国史馆”馆藏蒋档,馆藏号:002-090300-00202-246.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2]本党对于共产党应取方针与态度初稿(1939年7 月11日)[Z].台北:“国史馆”馆藏陈诚档案,馆藏号:008-011001-00013-002.
[33]姚雪怀致蒋中正、陈布雷电(1939年5月5日)[Z].台北:“国史馆”馆藏蒋档,馆藏号:002-090300-00216-241.
[34]黄自进,潘光哲编.困勉记:下[M].台北:“国史馆”,2011.
[35]许涤新.抗战的危机与召集临时国民大会[J].群众周刊,1938,(2).
[36]张友渔.国民大会的性质和任务[J].全民抗战,1939,(98).
[3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8]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的声明[N].新华日报,1945-02-16.
[39]高华.革命年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40]〔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M].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文嵘
作者简介:洪富忠(1977-),男,四川宜宾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博士生;丁威(1980-),男,河南焦作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陈剑(1972-),男,重庆长寿人,重庆行政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重庆市2013年度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重大委托课题(2013ZDZX10)。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