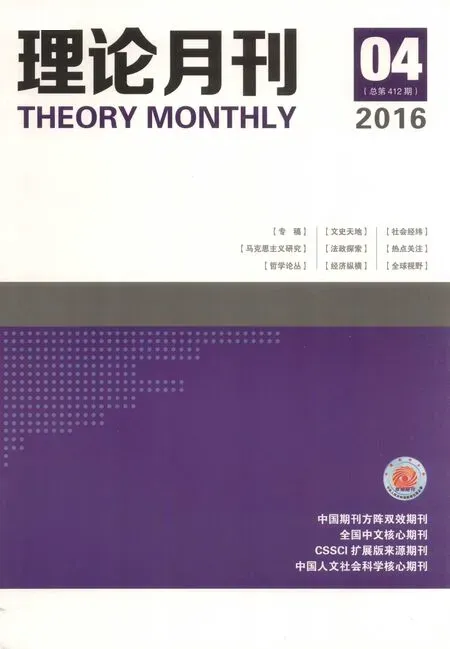大众文化非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文化学维度
2016-03-04魏艳芳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部天津300191
□魏艳芳(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部,天津300191)
大众文化非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文化学维度
□魏艳芳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部,天津300191)
[摘要]从文化的本质特征的角度批判大众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核心。他们从艺术风格、审美、观众心理等诸多方面,揭示了大众文化的非文化特征。正是通过这种文化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文化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当中,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和批判当代西方文化的独特视角,同时也对当今如何处理大众文化通俗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非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4.008
高雅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标尺。洛文塔尔的艺术性文学、阿多诺的现代艺术、马尔库塞的高等文化以及哈贝马斯合理化交往背景的文化系统是他们各自具体的参照。通过将大众文化与他们心目中真正的文化做对比,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1 大众文化是标准化、保守、虚伪的文化[1]
在洛尔塔尔心目中,艺术性文学是高雅文化的代表,而通俗文学则是大众文化的代表。他对大众文化的文化学批判是以艺术性文学为标准的。
1.1艺术性文学是洛文塔尔大众文化文化学批判的参照
洛文塔尔详细指明了这种艺术性文学的特征。首先,这种艺术性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洛文塔尔指出,“作为艺术的文学……它是个体的创造,并且被个体——个体本身——所体验。”[2]文学创作者把自己的独特的思想意图贯注在作品中,因此,艺术性文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其次,艺术性文学具有高雅的趣味。由于传统的艺术家极少受到市场和受众的影响,他们的支持者也大部分来自上层精英,艺术家就有更多自立标准的空间和可能,而且他们的标准不可能和他们的精英支持者和观众相差太远。这意味着艺术家更关心自己作品的个性表达和美学价值,而不是受众反映和市场收益,这决定了他们作品高雅的艺术趣味。最后,艺术性文学还是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正是艺术家描绘出了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东西。”[3]有关社会和个体的最生动的真理都包含在文学之中,因此,艺术性文学是个性的特色创造,它趣味高雅,真实地反映人类和社会状况,并由于其内容的真实和超越而指向自由。
而大众文化是与艺术相对的。洛文塔尔指出,与艺术性文学的自发、自由创作的特征相比较,通俗文学表现为一种人工的复制生产,不再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而且这种通俗文学越来越普遍。于是,艺术是真正的体验和个体满足,而大众文化则否定了个体的满足。“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进程中,个体衰落式微,使得大众文化出现,取代了民间艺术或‘高雅’艺术。大众文化产品没有一点真正的艺术特色,但在大众文化的所有媒介中,它具有真正的自我特色:标准化,俗套,保守,虚伪……”。[4]
1.2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保守和虚伪性
洛文塔尔研究通俗文化的特点主要是从通俗文学入手的。他选取了美国20世纪两份流行杂志①美国1901- 1941年间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煤矿工人报》。中的通俗人物传记作为研究的典型个案,明确分析了通俗文化的特点及成因。洛文塔尔发现传记作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描写传记主人公:主人公与他人的关系;主人公的心理;主人公的历史以及传记作者对语言的选择。通过对流行传记小说这四个方面描写的分析,洛文塔尔揭示了大众文化生产和制作的策略和诡计。
从主人公与他人的关系方面来看,洛文塔尔发现主人公丰富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两种基本的套路:主人公与父母及主人公与朋友的关系。我们的主人公总是处于这两类关系的帮助和提携中,俨然是“祖先和友谊的产物”,这让读者觉得这些偶像主要不是奋斗的产物,而是遗传得来的成功的结晶。当主人公的社会关系被如此简化并被模式化之后,关系的丰富性就被传记小说抛弃了,甚至爱情、性与婚姻这类本该是通俗文学最大卖点的关系都被简单地一带而过,因为爱与激情所需要的力量既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也不能被遗传与忠告所框定。于是,洛文塔尔就捕捉到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标准化和重复,因为大众文化需要的不是复杂化而是简单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容易使之投入批量生产。
传记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心理和成长的历史也都被描写成标准化的。洛文塔尔称主人公的个性结构为“没有历史的灵魂”,因为在传记作品中,赛马赌之王菲尔在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赌博生涯;未来的电影明星格尔森在她刚会走路的时候就想当一名演员等等。这种描写使得偶像的童年时代看起来只不过是对一个人专业与职业的提前出版,他来到这个世界就占据了某个位置,顺理成章地获得成功,因此,他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人类生活、智慧、精神、情感创造。而在对主人公的历史遭遇的描写中,就算是辛苦和突破也均被书写成了标准化的。
“从语言的角度切入然后去分析大众文化生产中所使用的修辞学诡计,是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抓得最准、分析最到位的部分之一。”[5]洛文塔尔指出,从语言方面来看,流行传记的策略表现为大量使用标准化的最高级语言和跟读者套近乎的语言。在洛文塔尔看来,最高级语言的普遍使用,强化了传记小说的商品化和标准化特征,经过语言的包装之后,流行传记不仅在形式上,在内在结构上也被大大地商品化和标准化了。这些看起来非常个性化的最高级语言和套近乎的语言,由于使用的普遍性,不仅没能将传记主人公描绘成一个个有鲜明个性的英雄人物,反而将他们一个个地塑造成了和蔼可亲的形象,仿佛他们就在读者身边,不再需要对他们顶礼膜拜。
2 大众文化是肯定的、压抑的、单面的文化
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是以他的高雅文化观为标尺和准绳的,正是在与作为高雅文化的艺术之否定、超越的双重性特征的对照中,马尔库塞指出了大众文化对社会现实的肯定性、对大众的压抑性,以致丧失了超越性、否定性特征的单面文化特征。
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对现实的这种超越性来源于文化的双重性质:肯定性和否定性。马尔库塞所推崇的高等文化一方面具有一种保守作用,即作为既定文化的一部分,维护着现存的文化;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否定性,即作为与既定现实的疏远,否定着现存社会秩序。如果艺术失去了它与现实的疏隔或间距,那么它就意味着它与现实达成了妥协,变成了对现存状态的肯定与维护力量。
2.1大众文化是肯定的文化
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从批判肯定文化开始的。“肯定文化”一词并不是由马尔库塞首次提出的,它首次出现在霍克海默的《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一文。霍克海默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性质。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详尽的解释与展开,并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当初,肯定的文化是为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的概念指示出超越生存既存的现实的方向,在封建末世的恶劣环境中,它表达了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它在当时是进步的、革命的。当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稳固之后,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在利益上的对立。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又必须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共同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资产阶级想到了肯定文化。于是,肯定文化就走向了它原初进步性的反面,开始“愈发效力于压抑不满之大众,愈发效力于纯为自我安慰式的满足。”[6]铺天盖地的文化产品告诉大众,只要奋斗就能成功,琳琅满目的商品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个人应该因此感到满足。因此,尽管在发达工业社会肯定文化的形式或口号发生了改变,但它的功能依然如故,即为生存的陈旧形式提供一种崭新的辩护。
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肯定文化所带来的幸福只是幻想中的幸福。但这种幻想中的幸福却有着真实的效果,因为不管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否幸福,它都给了人们幸福的感觉。这是一种被改变了意义的幸福,因为人们在这种虚幻的幸福意识中不会再意识到他的现实是需要被改变的,这种幸福因而成为了现实的奴婢。人的现实生活是穷苦的和不幸福的,但是,“若在不幸福中注入文化的幸福进而让感性精神化,就可能把这种生活中的痛苦和厌倦减缓为一种‘健康的’工作能力,这正是肯定文化的真正奇迹。”[7]
2.2大众文化是压抑性文化
1955年,马尔库塞发表了《爱欲与文明》一书。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出发点,把“压抑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雏形来加以批判。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人的不断压抑是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马尔库塞改造了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把压抑分为“基本的压抑”和“额外的压抑”。在马尔库塞看来,所谓“基本的压抑”就是为了维持文明的发展所必须加诸于本能的压抑,这种压抑具有合理性;所谓“额外的压抑”就是不合理的压抑,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消除了匮乏,却为了发展文明仍然不断地加诸于人的本能之上的压抑。正是通过“额外的压抑”,社会得以对个人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压抑。
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就是“额外的压抑”的产物,在这里被称为“压抑性文化”。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强调指出,压抑文化是由感性冲动(爱欲)和形式冲动(理性冲动)的结合和相互作用造成的。但是,压抑文化却并不致力于使理性感性化和感性理性化,从而调和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反,它使感性屈从于理性,理性的暴戾使得感性变得枯竭和繁杂。而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本质与人的感性冲动即爱欲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解放就是人的爱欲的解放。因此,压抑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就在于使人的爱欲这种主要的感性冲动变得枯竭和繁琐,因而也就阻碍了人的本质的解放。
2.3大众文化是单向度文化
在马尔库塞看来,高等文化本来是双向度文化,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超越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大拒绝,是对现存的东西的抗议。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高等文化的这种否定和超越功能却丧失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借助于文化工业之手来完成的。由于文化工业的作用,高等文化被大规模的复制和传播,成了生活中的文化用品,完全融入现实秩序。如此一来,文化就失去了与社会现实的“疏隔”,丧失了反思、批判现存秩序所必需的空间。于是,文化中与现实对抗的维度被消除了,只剩下肯定现实的一面,于是,文化就成了单向度的文化。
总的来看,单向度的文化属于单向度社会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发达工业社会,由于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融合,社会的对立面被消除,整个社会都是高度一体化的。而这种一体化又必然地表现在它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文化是单向度的文化,思想是单向度的思想,而人则在这种单向度的控制中成了单向度的人。如果说过去的时代对人的控制从未能够完全消灭人的否定性思想和反抗的意识的话,那么今天的发达工业社会则在这种控制的新形式——单向度文化的控制下,完全挫败了那些争取把人类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抗议和行动。
3 大众文化是被经济和权力侵蚀的文化
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是在与前辈们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场中进行的,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一方面又对前人的批判提出批判。哈贝马斯认为他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缺乏规范,为了改变这一点,哈贝马斯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这一生活世界中,文化应该是合理化交往的知识背景。但随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经济和权力侵入了文化领域,致使文化由人们合理化交往的背景退化为合理化交往的阻碍,它本身也不再是私人性经验的反映。
3.1文化是合理化交往的知识背景
如前所述,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理想中的文化应该是生活世界中合理化交往的背景。生活世界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最有意义的阐述,但是最先阐述生活世界的却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为了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解决科技理性的畸形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胡塞尔分析了生活世界的意识结构。哈贝马斯看到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价值,把它引入了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以期转换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法上的意识哲学的范式。
哈贝马斯把社会看作一个由系统和生活世界组成的双重结构。系统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又可再分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而生活世界旨在解决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主要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构成。正是在生活世界中,交往行动者形成了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意义在于培养公众的认同感,造就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哈贝马斯说:“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8]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文化,有意义的文化,应该是人们合理化交往的背景和知识资料,人们通过对这一文化的理解和获得、交流和讨论,从而获取某种一致性,形成一种持续的、稳定的交往网络。
3.2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经济和权力侵蚀文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系统和生活世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维护着社会的运行。随着社会的发展,系统独立性不断增强,独立化的系统反过来干预和破坏生活世界的文化机制,社会的权力和制度越来越多地干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得生活世界从属于物质再生产的体系,哈贝马斯把这种情形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大众文化是文化领域被经济和权力系统侵蚀的结果。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作为生活世界组成部分的文化也难以幸免,被金钱和权力媒介操纵的程度不断加大。这些系统媒介以单纯的报酬与惩罚为旨趣,造成了“文化的贫瘠”。在哈贝马斯看来,被金钱和权力侵蚀的大众文化的特征首先表现为文化创作的商品化,文化创作成了文化生产,为了经济动机而放弃了对文化本身意义的追求。“过去,文学样式从素材中产生,现今,则作为具有专利的文化工业公开的生产秘密而得以传播”。[9]
3.3大众文化倒转了私人性经验
哈贝马斯认为,过去的文化创作是私人经验的反映。“18世纪,市民阶级阅读公众在私人信件交往过程中,在阅读从中发展出来的心理长篇和中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能够培植一种具备文学能力,并且与公共性相关的主体性。私人正是用这样一种形态,来阐释自己建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关系之上的新的存在形式。”[10[11]因此,大众文化经由大众传媒在消费者的意识中制造的不过是“市民私人性的表象”,它所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也“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
可见,哈贝马斯与他的前辈们一样,都认为大众文化已从根本上丧失了文化的本性。但是,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是缺乏规范的,只是一种哲学逻辑上的演绎。为了把大众文化理论建立在经验和规范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借鉴了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对之进行了进一步改造,并把它引进自己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之中。
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是意义生产系统、合理化交往的背景,正是在文化的传承和积淀中,一个社会形成了自身达成共识和共同理解的知识储存,从而保证了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然而,随着金钱和权力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文化也被金钱和权力侵蚀了,从而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这样的文化阻碍了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样看来,哈贝马斯不是从所谓高雅文化的自由创造性、批判超越性来批判大众文化的非文化特征,相较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他的确开辟了一条批判大众文化的崭新思路。
4 结论:大众文化走向非文化?
应该承认,从洛文塔尔到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从文化学角度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具有开创性。如前所述,这种文化学批判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得以进入文化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单纯激进政治批判的嫌疑,也为后来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他们的这一批判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作为一种现代工业条件下的文化形式,不管是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还是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的确存在着该学派理论家所批判的缺点。在商业动机的驱使下,一旦某个文化产品获得了成功,对它的模仿就铺天盖地,大量重复的内容和形式,毫无新意地充斥大众的日常生活。一些大众文化的语言被到处使用,一些大众文化的风格被到处模仿,大众及其思维方式也在这种重复的消费中被标准化了、固定化了,所谓的个性、风格不过是无个性、无风格的伪装。在这样的文化潮流中,文化本身作为自由、个性创造的本质被遗忘。在此基础上,它更没有把反映这个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生存状况和诉求作为它的内涵和追求,因此不再能胜任人们之间关于社会和人本身生存状态的交流讨论的背景和桥梁。在此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对高等文化的推崇和对大众文化的鄙视,是我们认识当今大众文化现象并合理规范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文化学批判完美无缺。我们承认他们的理论对后来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同时更应该对他们理论上的误区保持清醒的认识,以免直接用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来裁剪我们的理论和现实。他们推崇高等文化并没有错,但他们因为对高等文化的推崇而把大众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就过犹不及了,显示出了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悲观主义态度。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存在着标准化、伪个性化、世俗化等非文化、反文化的非理性现象,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全部大众文化产品都是工业生产线上下来的标准化商品,毫无文化性可言。即使是在文化工业高度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也不至于完全雷同和陈腐。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彻底否定大众文化产品的艺术性和文化学特征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相较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对文化工业的标准化、伪个性化的彻底批判,本雅明倒是对大众文化的艺术性充分肯定和乐观。如果把二者的观点结合起来,既看到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伪个性化、世俗化导致的文化的艺术性的衰落,又充分正视文化发展的历史现实,看到新兴文化形式的进步意义,将会有助于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文化性、艺术性问题有一个公正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魏艳芳.辩护中的批判: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观及其启示[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3]张萍.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导言[J].文化与诗学,2009,(2).
[4]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 , New Brunswick (USA),Transaction Books,1984.14.
[5]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0.
[6][7][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0,33-34.
[8][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89.
[9][10][1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88,197.
责任编辑刘宏兰
作者简介:魏艳芳(1978-),女,河南商丘人,哲学博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部讲师。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