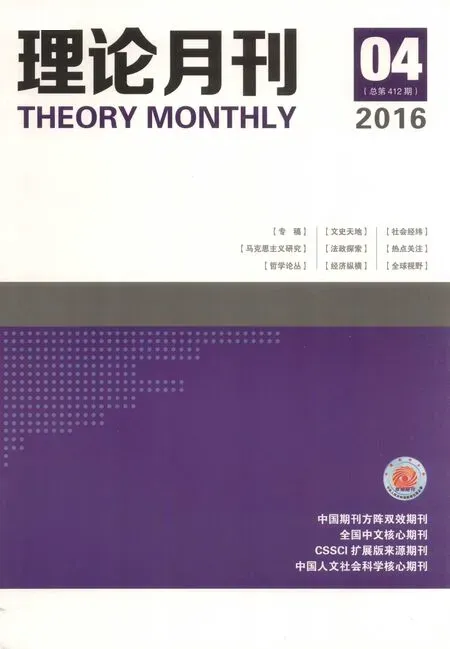孔子“天人观”与耶稣“神人观”之比较
2016-03-04靳浩辉
□靳浩辉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100091)
孔子“天人观”与耶稣“神人观”之比较
□靳浩辉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100091)
[摘要]孔子与耶稣作为儒家与基督教的奠基者,其思想根植于天人观与神人观。孔子的天人观主要体现在人本于天、天人合一、天命与人三个维度上,而耶稣的神人观则凸显在创造者与被创造者、救赎者与被救赎者、父与子三个方面中。孔子的天人观与耶稣的神人观具有鲜明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对孔子“天人观”与耶稣“神人观”进行管窥蠡测和鞭辟入里的比较,势必能深入到孔子与耶稣思想深层内核,从而对儒家与基督教思想的分野与契合有更加深刻的洞见。
[关键词]孔子;耶稣;天人观;神人观;分野与契合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4.007
纵观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面对“君子固穷”不失初心,惨遭“累累若丧家之犬”泰然自若,其“究天人之际”的沉思始终在孔子的思想视阈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耶稣短暂却辉煌的一生,淡然面对犹大的背叛,在十字架上淋漓尽致地彰显神的爱,其对神与人关系的体悟在其思想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孔子“天人观”与耶稣“神人观”进行管窥蠡测和鞭辟入里的比较,势必能深入到孔子与耶稣思想深层内核,从而对儒家与基督教思想的分野与契合有更加深刻的洞见。
1 孔子的天人观
孔子的天人观根植于殷周两代,并对其进行损益与扬弃,主要体现在人本于天、天人合一与天命与人三个维度上。
1.1人本于天
学界普遍认为,殷商以上帝为最高信仰,上帝具有至上神的崇高地位,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只能通过占卜来窥探上帝的意志,诚惶诚恐地屈从它。到了周代,出现了以天代替上帝的思想转换,萌发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观念,赋予了天以伦理性,并给予天生养万物的始祖性质,“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周书·泰誓上》),“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荡之什》)。
孔子直接继承了周人对天的论述,“就宗教信仰而言,孔子也接受周代对‘天’的信仰,相信天是至高而关心人间的主宰。”[1](P89)在《论语》中,孔子对天的论述有12处之多,可见天在其心中的崇高地位。如若对这些论述抽丝剥茧,可以窥见其天的意蕴具有多面性。首先是主宰之天。在孔子看来,天不仅主宰人的思想行为,更决定人的生死祸福。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在《论语·雍也》中还说:“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其次是自然之天。孔子从天体运行、四时交替、百物生长等现象中看到默默无言的自然界有不为人所见,更不为人所左右的必然性存在,所以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可见,自然之天化生出自然万物,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同样,孔子在《易传》中所论述的天也具有自然之天的涵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传·乾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易传·坤卦·彖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传·序卦传》)。最后是义理之天。在孔子看来,天是宇宙的法则,是人的道德的源泉。孔子去陈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认为自己存而不丧是天意,因为他承载了天赋之德,具有传承“斯文”的崇高使命。所以他的弟子子贡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认为孔子超人之道德与才能是天赋的,而仪封人也子贡不谋而合,称赞孔子“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子罕》),承认天挑选了孔子作为宣扬天道的象征。总之,孔子之“天”具有多重蕴义,就外在性而言,既是弥漫浓厚宗教色彩的主宰之天,又是顺乎自然规律无声无息的自然之天,就内在性而言,是带有浓厚价值意蕴的道德义理之天。但无论如何,天生养万物,人本于天。
1.2天人合一
孔子的天人合一不仅是追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泛爱众而亲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更是致力于“天人合德”、“天道与人道合一”的至高境界。
1.2.1天人合德。孔子继承了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展,落实到个人的精神修养上,致力于人德与天德的合一。《周易·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大人的道德像天地一样负载万物,他的圣明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他的施政像四时一样井然有序,他示人吉凶像鬼神一样奥妙莫测。[2](P14)在孔子看来,人德通过自身的修养,致力于与天德相契合,相互贯通,从而达致天人合德的至高境界。孔子一生的身体力行就是致力于“天人合德”的光辉典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将其“下学而上达”的修德历程寄托于天德的召唤,其“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精神修养历程也正是与天德相遥契的自然展现。因此在牟宗三看来,“孔子在他与天遥契的精神境界中,不但没有把天拉下来,而且把天推远一点。虽在自己生命中可与天遥契,但是天仍然保持它的超越性,高高在上而为人所敬畏。”[3](P36)
1.2.2人道与天道合一。孔子曰:“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礼记·哀公问》)。将“事亲”与“事天”相沟通,从而达致人道与天道的境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强调治理国家,应遵循天时与天道,这样国家方能长治久安,所以《礼记·中庸》称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上遵循天时的运行规律,下遵循水土的自然之理。另外,孔子在《易传》推天理以明人事,致力于人道与天道合一的思想更是比比皆是,“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易传·谦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传·观卦·彖传》)。在《系辞传》中突出强调天道、人道、地道相合一的“三才之道”。
1.3天命与人
孔子的天人观也体现在对天命与人之关系的沉思与拷问上,而顺命安命、畏命知命、尽人事以待天命正是孔子对待天命与人之关系的三种态度。
1.3.1顺命安命。在孔子看来,天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人无法左右,难以违抗,应以顺命安命的态度对待之。深为孔子所赞赏的弟子颜渊“不幸短命死矣”,令孔子悲痛不已,感叹天命的无常。有德行的伯牛竟然患了不治之症,孔子持其手,喟然叹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抱怨命运的不公,但又无可奈何,其弟子子夏所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谓契合了孔子当时的心情。孔子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公伯寮向季孙氏诽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却认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如果能够得到推行,那是命运决定的,如果无法实现,那也是命运决定的,公伯寮能把命运怎么样呢?《史记》也记载了孔子顺命安命的态度,“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在卫国不受重用的孔子计划西游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听闻晋国两位有才德的大夫被杀,感叹自己无法渡过黄河是因为命运的安排。
1.3.2畏命知命。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人生有三大敬畏的对象,首先应该敬畏的就是天命。不过对天命的敬畏不可盲目,应建构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因此孔子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认为知天命是成为君子的必备修养。孔子在自述其人生历程时,把“五十而知天命”视为一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五十而知天命”,中间需要漫长的人生历练,可见知天命之难能可贵,并且只有经过“知天命”的沉淀与修炼,方能臻至“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更高境界。正因为孔子达至“知天命”,从而区别于不知命的芸芸众生,其“会当凌绝顶”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不由地感叹“莫我知也夫”。当弟子询问原因时,孔子回答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将天当作人生寄托,视为知己。
1.3.3尽人事以待天命。孔子在顺命安命、畏命知命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屈从于天命的安排,而是努力与天命博弈,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谓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这鲜明地体现在孔子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孔子青少年时期先后丧父丧母,家境衰落,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因此孔子参见季氏飨士的聚会,被阳货嘲笑“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史记·孔子世家》)。种种困难没有让孔子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反而激发了其“志于学”的抱负,最终孔子精炼地掌握了“礼乐射御书术”六种技能,并以此为基础招收学生,创办了私学。中年孔子面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与“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自知这种局面难以扭转,依然挺身而出,“学而优则仕”,为此他拒绝阳货的拉拢,积极开展逐家臣、隳三都、强公室的行动。虽然其施政理念在鲁国受挫,孔子被迫开始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的漫长岁月,其中历经磨难,当到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但不改其信念与理想,没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去过隐逸的生活,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希望恢复周代的礼乐文明,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另外,晚年孔子深知在其生前无法实现周代的礼乐文明,从而将其理想寄托于著作上。为此孔子作《春秋》,以褒贬、曲笔的方式抒发“尊君”之微言大义。自称为王的吴楚两国国君被孔子贬为“子”,周天子被晋文公召唤过来参加践土会盟,孔子曲笔称之为“狩于河阳”。因此,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2 耶稣的神人观
在对神人观的探究上,耶稣既有继承《旧约》思想的一面,将神人关系视为创造者与被创造者、救赎者与被救赎者,也有创造性转化的一面,将《旧约》严肃庄重的神人关系转化为温情脉脉的父与子关系。
2.1创造者与被创造者
《旧约》开篇《创世纪》描述了神创造人的情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6-27)。旧约中的神在创造人的同时,赋予了人与神形象相似的特性,从而给予人管理世间万物的权力,神与人构成了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耶稣继承了旧约的神人关系,认为人由神所造,“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马可福音10:6)。“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马可福音13:19)。由此可见,在耶稣眼中,神与人的关系是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
2.2救赎者与被救赎者
耶稣强调“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路加福音1:68)。神不仅是人的创造者,更是人的救赎者。背负罪恶的人如果希望得到神的恩典,得到救赎,进入美轮美奂的天国,就应当积极遵行神的旨意。“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耶稣认为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门徒就询问耶稣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3-26)。可见,至善至真的神展现的天国蓝图为人们开拓出一条摆脱苦难、享受永生的救赎之道,引领人前行,神与人构成了救赎者与被救赎者的关系。
2.3父与子
耶稣在福音书中经常将神人关系比作亲密的父子关系。神在耶稣口中被称为“父”,在福音书中不下于170次。比较鲜明的例子是“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马太福音6:1)。“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路加福音11:2)。《旧约》中的耶和华是一位严厉、冷酷、妒忌且好施惩罚的神,使人畏惧害怕,甚至敬而远之。而在《新约》中,耶稣眼中的神则是慈爱的天父形象,神人关系显得温情脉脉,这一转变消解了神与人之间的龃龉和对立,使得人与神重归于好。神对待众人毫无偏袒,如同阳光普照,不仅照好人,也照歹人,如同雨露,既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在耶稣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5:11-32)中更能充分地彰显神“父爱”的无私与广博,人的得救并不在于那意味着解放和反抗的出走,而在于回到父亲的家中——不过,应当承认的是,父亲是不会羞辱他的孩子的,而是恢复他做儿子的地位和权利。[4](P226)由此,神化身为慈爱众人、抚慰人心的天父,神人关系构成了亲密的父子关系。
3 孔子的“天人观”与耶稣的“神人观”之比较
作为儒家与基督教的奠基者,孔子与耶稣所建构的天人观与神人观究竟有何相通与差异,下文将试图拨开迷雾。
3.1孔子的“天人观”与耶稣的“神人观”之通
3.1.1“天”和“神”都是孕育人生命与道德的源泉。孔子认为天是孕育人的源泉,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传·系辞传》)。另外,天也是人伦理道德的承载者,孔子在遇到司马桓魋追杀时,毫不恐惧,毅然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当孔子被围匡地时,同样说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他承载了天赋之德,具有传承“斯文”的崇高使命,所以天意使其存而不丧。总之,在孔子看来,天是人精神生命与道德的源泉与终极根据。
在《旧约》看来,神在起初创造了世间万物,给予人以生命与管理自然世界的权力。不仅如此,神在创造人以生命的同时,赋予人以精神生活,并主宰了人的伦理道德。“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6:5),从而兴起洪水,洗刷人的罪恶,并因挪亚的义而赐予他以方舟,使其得以存活,教训人类遵守神的诫命。后来神同样由于亚伯拉罕的义而拣选他,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始祖,让他的后代得以不断繁衍。最能彰显神主宰人精神生活的是其赐予摩西的“摩西十诫”,作为以色列人伦理道德精髓的典范,“摩西十诫”具有绝对权威和崇高的地位,指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于耶稣来说,他继承了《旧约》的思想,也将伦理道德建构在信仰神的基础之上。神就是公正与慈爱的完美化身,他的神圣性集中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人类可以自由地接受上帝的道德诫命,并完全为自身的行为负责,所以说“神提出的日常行为的伦理规范和宗教规范要义,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人的面前,赋予人选择的自由。”[5](P45)
3.1.2“天”与“神”相对人都具有至上的地位。天在孔子心中享有至上的地位。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对于王孙贾的观点,孔子不甚同意,在他看来,如果犯了滔天大罪,向任何神祈祷也是徒劳,因为天的地位最为至上。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弟子子路认为孔子去见荒淫的南子,十分不屑,孔子以其最高信仰“天”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情合理。颜渊早亡,孔子悲然痛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而无可奈何,无法违背天的意志。另外,孔子还主张天的意志和命令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应当“知天命”和“畏天命”,孔子认为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并提倡人生有三畏,其中重要一项就是“畏天命”。“知天命”与“畏天命”是相互印证的关系,“知天命”是对上天意志的把握;“畏天命”是由于天命难违,对其产生的敬畏与重视之情。根据以上的论述可知,在孔子的内心深处,天的至上地位可见一斑。而在耶稣眼中,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赋予人以生命和道德,具有绝对的权威与至上的地位。当门徒就询问人如何得救时,耶稣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3-26)。强调神享有人所不具备的权柄。当一个信徒赞美耶稣是良善的人时,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10:18)。认为神相对于人而言,是至善全善的。可见,在耶稣眼中,神的至上地位不言而喻。
3.1.3都肯定了人在“天”与“神”面前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在上文“尽人事以待天命”一节中,本人已经从孔子人生的历程中充分阐述了孔子没有完全屈从于天命的安排,努力与天命博弈,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思想,这些已经肯定了人在“天”面前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在此本人不再赘述。与孔子不谋而合,耶稣同样肯定人在“神”面前具有一定的能动性。耶稣继承了《旧约》中对人的看法,认为由于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违背神的诫命而丧失了善性。当有一个人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时,耶稣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路加福音18:18-19)。耶稣认为世间之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法承受“善良”的称号,只有神名正言顺地可享受这一称号。为此,耶稣对众人宣称他来到世界的使命,就是“召罪人”(马太福音9:13),罪人就是指偷窃的、抢劫的、奸淫的、违反律法的犹太人及异邦人。所以耶稣宣教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在耶稣看来,丧失善性的罪人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通过思想与行动上的悔改来恢复善性,重新回到神的怀抱,最终进入神的国。由此可见,耶稣肯定了人在“神”面前具有一定的能动性。
3.2孔子的“天人观”与耶稣的“神人观”之异
3.2.1多元信仰与独一虔诚。孔子在信仰天的同时,也保持对鬼神与祖先的信仰。“子疾病,子路请祷。《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在自己生病的情况下,孔子也同样向神祈祷。孔子重视人事,悬置鬼神的存在,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但同样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而“敬而远之”的态度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所以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因此,陈来教授认为,“春秋时代鬼神观念和文化中不断渗入道德因素,把崇德和事神联结在一起,成为春秋贤大夫们的共同信念。”[6](P14)另外,孔子继承了殷周以来的祖先崇拜思想,强调应以严谨缜密的礼仪制度来祭祀祖先,“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提倡严格遵守“三年之丧”。而耶稣的神人观认为人对神应该保持独一虔诚的信仰,其继承了“摩西十诫”中“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2)的诫命,认为敬拜其他偶像就是对神的最大亵渎,笃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也常常以神的独生子自居。当一个文士向耶稣询问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的时候,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可福音:29-30)。强调要全身心地去爱独一的神。当门徒请教耶稣如何能永生时,耶稣回答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认为认识独一的真神是获得永生的重要前提。
3.2.2自然而然与有意而为。在孔子看来,天创生自然与人类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传·系辞传》)。天无声无言,没有刻意为之之感,其中难以窥见上天的意志与情感。与孔子相比,耶稣之神作为造物主则迥然不同。神在创世的前五天创造自然万物,而在第六天创造了人,“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马可福音10:6)。并赋予人以“万物之灵长”的地位,给予其管理世间万物的权柄。可见,神创造人是有意识且有目的的。因此法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认为,“基督徒的上帝是高谈阔论、发布命令和提出要求的会起干涉作用的神,它主动地创造世界,赋予每个人灵魂,在人生的长河中始终都要表现出来。而中国人的“天”则相反,它不会讲话,仅以间接方式起作用,它的活动是沉默的、无意识的和持续不断的。”[7](P16)其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3.2.3天人合一与神人相分。在孔子的“天人关系”中,“天为价值提供者、社会正当治理的保障者,并不妨碍他对人的爱人、知其不可而为之、乃至杀身成仁的申述,因为天意非通过人显现不可。”[8](P121)人先天的向善性使人孕育了乐观而积极的态度,坚守“人能弘道”的价值理念,相信人可以通过充分的道德实践来彰显自身的潜质,超越天人之间的界限而不必凭借外界的力量,来臻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至高境界。而在耶稣的神人关系中,由于人类祖先的犯罪使得人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在完美纯粹的神面前,人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与神之间具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只能匍匐在上帝面前,凭借上帝之子耶稣的中保身份,来与神沟通,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也就注定人无法企及“神人合一”、“神人合德”的境界。正因为人先天的罪恶感,人与神至始至终保持着“神人相分”的关系,人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必须受到外界神的力量以及制度的约束与制约,人必须保持谦卑与虚心的态度,不能逾越“神人之间”的界限,妄图替代神的至高地位。
通过剖析孔子天人观与耶稣神人观的逻辑脉络,并对两者抽丝剥茧,进行细致入微的比较,能够更加深刻地体味到孔子与耶稣乃至儒家与基督教思想的分野与契合,启迪我们应本着“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儒家与基督教的深层对话构建精神底蕴的平台。
参考文献:
[1]傅佩荣.儒道天论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德]卡斯培.耶稣基督的上帝[M].罗选民译.香港:道风书社,2005.
[5]黄陵渝.当代犹太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6]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02.
[7][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耿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任剑涛.伦理王国的构造:现代性视野中的儒家伦理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刘宏兰
作者简介:靳浩辉(1987-),男,山西运城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0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