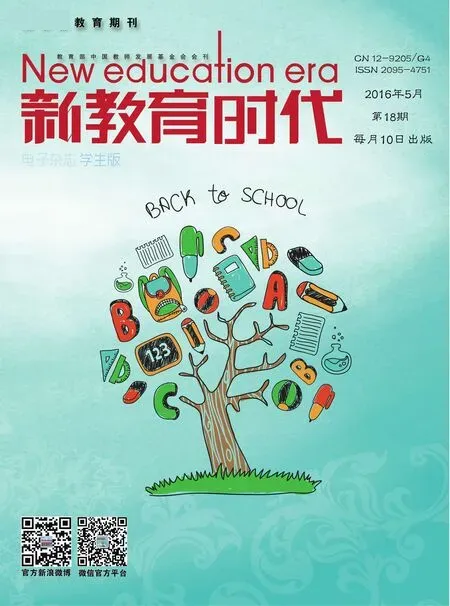从解构主义视角分析《青黄》的不确定性
2016-03-04陈倩
陈 倩
(湖北大学文学院中文国家基地班 湖北武汉 430062)
从解构主义视角分析《青黄》的不确定性
陈 倩
(湖北大学文学院中文国家基地班 湖北武汉 430062)
《青黄》是先锋作家格非的代表作品,它以寻找词语“青黄”意义为发端到消解“青黄”意义为结束,以其设置大量空缺以及与文本中心不相关的情节为人们热议。整个文本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意义的流动。本文试图从人物对话]、空缺、隐喻三个方面通过解构的视角来分析小说的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脱胎于结构主义内部的矛盾,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为代表,受尼采哲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欧洲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总的来说,解构就是“每每专执于哲学和文学文本中似乎是无足轻重,或者明显是居于“边缘地带”的片段发隐索微,以此形成突破口,进而扩张之,证明文本没有恒定的解构和确定的意义”。[1]
而小说《青黄》就是从“寻找意义”的传统结构开始,通过人物语言、空缺以及隐喻的设置,最终证明了“青黄”没有确定意义。由此看来,《青黄》是适合放在解构视角下去阅读的。
一、人物语言的不确定
小说的主要章节描述了作为研究员的“我”对于麦村几个人物的采访。在寻访交谈中,采访对象反映给“我”的话语都是不确定的,他们或含糊其辞、或言他物、或抛出新的谜团。总之,本事解开“青黄”意义的语言却将意义本身解构了。在本节中,主要例举“我”第一个访问的老人以及老人李贵的语言。
在寻访“青黄”意义的过程中,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老人,作为第一个采访的人,老人的作用很重要。他特别提到张姓男子和他女儿的到来。然而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在叙述中承认他的不知情并且提出了疑问:”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女儿好像叫小青”;“以后的事我也不怎样清楚”;“中年人……也许是对村子里的水土不太习惯”;“他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父亲”。[2]老人的陈述显示出了一种不确定性。并且老人叙述难以捉摸的原因也是无法确定的。老人在描述回忆时非常吃力,然而他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关键印象“他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2]
老人李贵是从语言上消解“青黄”意义的关键人物。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老人李贵用一封信将“我”叫去了横塘,当我提到九年前的雨夜发生的事时,老人突然“一阵猛咳”,以“梦游”将这件事敷衍了过去。最后老人李贵突然说:青黄是一条良种狗。“青黄”在不是麦村的地方被一个不是麦村的人赋予了确定的意义,但作为一条狗的名字,显然这个意义完全偏离了小说预设的前提,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麦村人对于个体记忆的描述构成了“我”的采访。采访中语言的不确定性有其本身的主观性以及客观性。“格非将往事和历史交给记忆来呈现, 其结果是作品只提供了故事和历史的片断而没有提供故事和历史的整体, 因为人的记忆的特性使其只保留了自己感兴趣和印象强烈的部分 ,每个当事人或见证人由于自己眼光的局限也只能提供局部的真实 ,更何况时过境迁之后, 时空距离和主观利害的介入常使他们所陈述的历史片断有可能扭曲历史和往事的原始形态。”[3]由于当事人的对记忆的主观无意识的选择以及时空距离的客观影响,麦村人对于个体记忆叙述的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因此让历史充满漏洞和困惑。
二、大量空缺的设置
空缺已经成为格非小说的一个标志,《青黄》也不例外的设置了空缺,让故事的统一性被消解,故事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侦探小说中解谜的结局不同,《青黄》以一个疑问的开放的文本结束,谜面永远存在,真正的意义却无处探寻。
1.“青黄”本源性缺失
小说之始通过谭维年教授的研究将“青黄”与九姓渔户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研究员却评价“一旦他所论述的对象和麦村、九姓渔户这些字眼连接在一起,就会连续不断地出现错误”。这暗示了“青黄”这一词语真正的意义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
文本内容中共9次提及”青黄“一词,并由不同阐释者作出以下6项解释:
(1)一个漂亮少妇的名字;(2)春夏之交季节的代称;(3)一部记载九姓渔户妓女生活的编年史;(4)外科郎中认为是年轻妓女(青)和年老妓女(黄)的称呼; (5)老人李贵说:青黄是一条良种狗;(6)几年之后,“我”在市立图书馆的二楼偶然看到了“青黄”这个词条。「青黄」多年生玄参科草本植物。全株密被灰色柔毛和腺毛。根状茎黄色。夏季开花。
“文本中穿插的李贵的故事本身就是对外乡人故事发展的消解,而他给出的“青黄”的解释也是对先前“青黄”所有含义的消解。而结尾处“青黄”的词典意义又将整个故事都颠覆了。”[4]寻找 “青黄”意义的过程实际上成为了拷问“青黄”意义是否存在的过程。“青黄”作为故事的本源,它的缺失让写作成为了一场对于“不在之物”的寻找,随着叙事的进展“青黄”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不断被一些和它历史有关的事物给遮掩。
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所说“叙事进行中出现的空缺与空缺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网络,空缺对空缺的补充有可能使故事重新组合,也可能使故事陷入迷宫。”[5]很明显,《青黄》里所设置的空缺就使其陷入了叙事的迷宫。
2. 老人李贵身份缺失
九年前"我"在通往麦村的大道上 遇见了老人李贵,“我”和他一同借宿在外科郎中的家里。但是到了深夜,李贵却默默地离开了借宿的厢房,回来时“拎着一双破布鞋,赤着脚出现在门口,他的裤管挽过膝盖,露出一截和他年龄和身份都极不相称的白皙小腿”[2]。为了解开心结“我”还在九年后向李贵询问当年的事情,李贵却只是神色紧张地以梦游这一原因来回答。在这样诡秘的描述下,李贵的真实身份成为了一个谜团。
3. 张姓人生死的空缺
外科郎中小时候和母亲去看死人“张姓人”时,只看到了钉好的棺材。而多年之后作为研究员的“我”在接触年轻人康康时,知道了“张姓人棺材里什么都没有”的秘密。张姓人的生死,以及其尸骨在什么地方也成为一个神秘的空缺。
4. 小青儿子死因的空缺
“我”在向小青探访“青黄”意义时,小青说,她惟一的儿子在见过一个酷似自己父亲的老人后便在门前的池塘淹死了。小青儿子充满神秘色彩,不明的死因也形成了一个空缺。
5. 张姓人对小青的感情的空缺
张姓人和小青本是父女的关系。但当小青开始叙述她的回忆时,她说道“她(母亲)或许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她。我父亲也可能不是亲生的——村里人都这么看”[2]。“我现在还是非常想他。有一次,我正在洗澡……”[2]小说又一次对话在最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张姓人对于自己女儿的情感成为一个惊人的留白。
基于这种种与“青黄”关系或近或远的空缺、悬念,小说交给读者去完成的部分大大增加了。开放性的文本引导读者主动去填补文本的空缺。这样一来《青黄》很自然地成为了一种可以让读者主动参与进去的“可写性”作品。
小说的叙事空缺是一场“不在”与“在”的博弈。“不在”的话语在种种不确定中却显得比"在场"的话语更加突出,它可以使“在场”的话语失去其失解释的权威性。"在场"话语对于回忆的描述一直被“不在”的话语给推翻。
叙述空缺的设置增强了文本的可塑性和历史真实的不确定性,是对历史的否定。
三、文本的两大隐喻
1. 历史与真实的隐喻
保罗·德·曼认为:“任何语言都必须依靠修辞特性来发挥功能。具体说来即它们都必须依靠转义和形象来发生作用,因此,它们都是隐喻性的。”[2]小说对“青黄”意义寻找的过程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作者通过各种情节的设置,各种空缺的遗留,将这种“虚妄的追寻”变成全文最大的隐喻指向了生活的真实。
格非在《青黄》中表达了他对可知历史的怀疑和否定。麦村村民的个体回忆构成了与“青黄”有关的琐碎历史,也就是“在场”的话语建构了历史,存在中的事物是历史的一部分,它无法否定历史,但换一个角度看,历史却可能被“不在”的话语推翻。由于小说人物叙述的不确定性以及大量空缺的存在,那些隐没在村民叙述之下的声音永远都可以推翻已知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在格非的小说中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因此作者借整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是值得怀疑的。“《青黄》的思想内涵与格非本人的世界观构成了一种换喻关系,或者说《青黄》就是作家内心思想状态的物质化展现。”[6]寻找《青黄》的过程正是对于人们质疑历史与真实的隐喻。正如陈晓明在《众妙之门》中所说:“格非的小说就这样表达对真相的怀疑,它总以探究真相为始,以迷失真相告终。”[7]
2. 孤独的隐喻
下船——烧船——定居麦村——娶妻——死亡,“我”通过麦村人零碎的描述大致的捕捉到了张姓人这一条简单的在麦村的生命线。
张姓人和他的女儿向麦村走来时,大风把他们吹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避门不见。终于有老艄公愿意收留他们,但后来才知道老艄公这样做是为了占有张姓人年幼的女儿。此后老艄公的船就翻了,老艄公也死了。小说中并未言明老艄公船翻的理由,但不难猜到这都源自于一个父亲的愤怒。[9]
过了几年张姓人要在麦村结婚了。可惜的是他的房事在年轻的看林人的窥视下暴露无遗,外乡人漂亮的妻子身体有缺陷,无法进行性事,也无法传宗接代。外乡人的脸色变得可怕起来,他明白他永远无法被麦村真正接受了。[10]
麦村对张姓人一开始就是拒绝的,冷漠的,婚姻让麦村短暂地给过外乡人温暖,但立刻就让外乡人更加孤独。[11]
张姓人对麦村也是躲避的,拒绝的。村民印象中的张姓人都是“不大说话,很少笑,好像有什么心事”的形象。外乡人总是带着女儿在水边玩耍,在村中祠堂的老倌提出要他在祠堂里结婚时,张姓人拒绝了,并拉着他的妻子“来到了苏子河边,对着宽阔的水面跑了下来,吻了一下河边的烂泥”。[5]外乡人在麦村生活多年,但他的心却始终和水紧紧地契合着,无法真真地安定于麦村。
四十年前的张姓人在麦村感受到深刻的持久的孤独感同四十年后的“我”的孤独也交织在了一起。[12]
“我”来到麦村,这里的人包括这里的狗都“对我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麦村对于四十年后来采访的研究员”我”是毫无兴趣的,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的来意,”我”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这个村子里。而”我”眼里的麦村也是凝重的沉寂的,”悲伤的阴影”笼罩着村民,“我”认为“这是一个缺乏热情和好奇心的村子,不仅是那个可怜的姓张的人,任何一个来这里的外乡人都会感到孤独”。[5]
麦村的那份冷漠和孤独早已穿越时间经由外乡人来和"我"相遇了。麦村的冷漠并非只是从村民身上体现出来的,它来自于村子本身。在整篇小说中我们都感受不到一个村子应有的烟火气息。相反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村子的哀伤,毫无生气的。这个村子也是孤独的,这份孤独感并非以姓氏、血缘、地域为界限。它是根植于每个个体身上是人和人之间天生的永恒的隔膜,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
无论是村民们对于张姓人碎片化的描述,还是“我”两次探寻麦村琐碎的感受,它们都是文本指向人生孤独的隐喻。诚如解构主义所说“隐喻本身就是无根据的、任意的和虚构的,所以,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最终完成的只是一种符号的相互替代:它可以言此而意他,由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符号(即隐喻)”。[8]关于张姓人的描述和我的感受看似和“寻找青黄”的中心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明确的意义,但正是描写“两个外乡人人和麦村关系”的语言符号在文本中代替了“孤独”这一话题,成为了“孤独”的隐喻。
结语
寻找是目的,消解却是结果。格非在《青黄》中利用语 言打造叙事的迷宫,将小说内的人物和小说外的读者都置身于怀疑和不确定之中。这种不确定不仅限于文本中“青黄”一词的意义,更多的通过读者的阅读来质疑现实生活中所谓历史和真实的存在。可以说,格非的《青黄》通过文本不确定性的营造激发了读者对现实意义的思考。[13]
[1]陆扬. 《德里达:解构之维》[M].第一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
[2]格非.青黄[M].第一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3]王爱松.格非:存在的眺望与沉思[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任雪.流动的碎片与消解的是非.[J].北方文学旬刊,2013(13):14-14.
[5]陈晓明.无边的挑战[M].第一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张宇宁.无望的追寻——解读格非小说《青黄》的思想内涵[J].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
[7]陈晓明.众妙之门[M].第一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马新国 主编.西方文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15页.
[9]高群.《青黄》元话语分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0]非云华.叙事的魅力——谈格非作品《青黄》的叙事艺术[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11]常健男.论格非小说中的孤独生存意识[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2]张宇宁.论格非小说《青黄》的反形而上学思想特征[J].学术交流,2011年第3期.
[13]黎小燕.从《青黄》看先锋小说的叙述技巧[J].电影评介,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