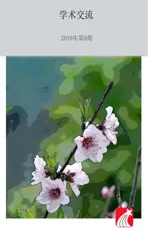在思与行之间——汉娜·阿伦特对政治哲学的批判
2016-02-27王晓蓓
王晓蓓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基础部, 哈尔滨15008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思与行之间
——汉娜·阿伦特对政治哲学的批判
王晓蓓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基础部, 哈尔滨150080)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源于思与行之间的断裂,二者之间的鸿沟肇始于苏格拉底之死,他的死让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所坚持的哲学原则产生了疑问并形成了真理与意见对立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阿伦特批判这个传统并斥其为“非本真”的政治哲学,她认为政治哲学应该是以人类事物为对象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她试图用“判断”来构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以希望能够弥合传统政治哲学中思与行的分裂,恢复公共领域这一世界意识,这是一种在实践上恢复公共世界的努力。
思;行;判断;阿伦特;调和
如何弥合政治与哲学之间的裂痕一直是哲学家们的隐秘渴望,在哲学史上各种对于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竞相呈现,在二者关系的背后实际上是思与行问题的纠缠。
汉娜·阿伦特,作为一个对现代性问题有着独特见解的哲学家突破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政治哲学,她认为政治哲学应当回答的是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应该回到哲学与政治争论的源头来考察它。现代政治危机得以形成和肆虐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看待哲学与政治所采用的方式与古人不同,方式的改变揭示了“政治”在哲学中自主地位的丧失,人作为一个思与行合一的主体,被迫把思想和行动当作两种对立的存在来思考。哲学与政治之间复杂、矛盾的关系使阿伦特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哲学与政治真的无法相容吗?她认为我们应该回到最初产生政治哲学传统的生活形态即古希腊城邦生活中去考察,回到“政治之初”,从重新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
一、前政治哲学——哲学与政治的统一
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城邦时期,公民过着言行合一,即思想与行动统一的生活。这点可以从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词“因为在行动之前我们有无与伦比的思考力和行动力,可是其他人却处于无知而鲁莽,耽于反思而犹豫”中看到人作为思想和行为统一的存在,也可以从毕达哥拉斯的寓言“生活……就像一场节日盛会;有的人参加它为了竞赛,但是最优秀的人作为旁观者前来,因为在生活中盲从的人追名逐利,而哲学家求真理”中找到古希腊人把理论和实践作为两种生活方式来思考的证据。而最能体现思想与行动统一的则是Logos,它的原初之义既包含思想又包含言说,代表着思与行的统一,证明了哲学与政治曾经的和谐关系。在早期的希腊城邦生活中人们过着思与行统一的生活,他们在言说、对话中展示自己独特的身份并证明他人的存在。这个Logos支配着整个前柏拉图时期的希腊城邦政治,在城邦中人们通过言说对话这样的行动从不同角度展示自己的所想所见,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思与行统一的政治,苏格拉底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
在阿里斯多芬、柏拉图、拉尔修和斯诺芬等人的描述中苏格拉底呈现出多种形象,有时他是一位善于诡辩的智者,有时他又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人。我们可以在这些描述中看到苏格拉底的两种形象:一个是 “哲学的苏格拉底”,一个是 “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之所以会有“两个苏格拉底”的形象存在,是因为哲学家在哲学与政治对立的基础上对苏格拉底进行了描述:“哲人的苏格拉底”希望通过哲学来改变城邦;“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希望建立一种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两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正说明了哲学与政治的第一道裂痕藏于苏格拉底自身之中。
苏格拉底是城邦的友爱者,他利用大量闲暇时间在广场跟人们讨论有关正义、勇敢、善良等问题,却经常没有任何结果,这种助产士的对话方式经常发生在城邦的各个角落。苏格拉底的对话让意见在现实城邦的生活世界中得以展现而不是在真空中孤独地思考,哲学在城邦中从来不致力于提供真理,它是要唤起和帮助公民去思考。苏格拉底的这种思考具有一种解构的力量,它吹过城邦时唤醒的不是人们的思想,而是击碎了人对日常生活的信念、摧毁了各种既定伦理标准,它是那些威胁城邦统治行为的来源。这种摧毁的力量来自苏格拉底“助产术”中的定义,因为当他用定义专注于伦理和美德的实践理性领域时,思辨所产生的方法都必然会带着一种经验之内的狭隘视野,这种“经验上有条件的理性以排他的方式想要独自提供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僭妄”[1],这种僭妄的具体表现是定义,我们经常把来自经验归纳的定义不假思索地认为是理性内使用的产物,而当它执着于实践理性领域的概念时就开始僭妄了。
当苏格拉底“把‘德行’的概念从经验中得出,并且把最多只能用在一种不完善的阐述中用作例子的东西变为知识的一种典范(如许多人曾在实际上所作的那样),谁就会把‘德行’变为随着时间与环境而变迁的东西,一种不容许有任何规则形成且意义不明的怪物”[2],他肯定深刻体会到了对实践理性进行定义后所产生的无效性,因为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还是斯诺芬的记述中他都没有真正给出任何关于伦理和道德的明确定义。但是,苏格拉底在谨慎地反复检验定义后发现幻想仍然存在,最终他认识到这个定义的过程是消极和无效的。所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所导致的定义无效性犹如飓风一般摧毁了原有希腊城邦的传统、伦理、道德基石,却无法为人们重建新的理论信仰,这才是苏格拉底为什么成为城邦政治中的最大威胁的原因,也是他自身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最终,希腊城邦对苏格拉底进行了审判和定罪,他的死使政治与哲学的冲突达到了顶点。
二、政治哲学传统的确立——哲学与政治的分裂
在这次事件后,苏格拉底之死让柏拉图对政治感到了绝望,他为了哲学和哲学家的安全对城邦和政治进行了“反叛”,提出了与“意见”相对的“真理”之路。真理与意见对立的提出是柏拉图哲学中最反苏格拉底的存在,他把真理置于意见之上也就是把政治置于了哲学之下,从此,政治被哲学统治的时代来临了。
柏拉图是第一位把思考什么和做什么当作两个完全不同事件的哲学家,他把真理置于意见之上的等级二元论变为一种非外在的“暴政”,“真理”的标准性直接宣布了思考的无意义,而后果则是城邦中的政治从多元的互动变成了一种单一的统治,思与行从此断裂,这些我们都可以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喻说中看到。
在柏拉图的洞喻说中包含两次重要的转折,这两个转折直接影响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形成。首先是从洞穴内走到洞穴外的第一次转折,洞穴中生活的人们常年观看墙上的投影,终于有人(哲学家)为了看到洞外的阳光而挣脱锁链离开洞穴,当挣脱锁链的哲学家从幽暗的洞穴来到洞外阳光之下,他本身不是为了洞穴内的人而是好奇什么东西如此光明,这种“惊奇”促使他来到洞穴外去寻求光明的存在。其次,返回洞穴是第二次转折,哲学家必然受到城邦使命感的召唤而返回城邦,在他感受到真理的光芒后哲学家才明白洞外真理与洞内真理的不同,当在哲学家返回洞穴后与众人的矛盾形成了城邦冲突时,柏拉图的“真理”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归来的哲学家无法把洞外所见告诉众人,因为对没有洞外体验的众人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哲学家所说的“真理”是什么,所以真理在面对洞内标准时它转变成了意见,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当哲学家在向众人讲述洞外“真理”时其意义状态也发生了转变,他们试图将真理与多数人分享,真理自身以“对我来说”的方式显现在众人面前,在分享时它的本真状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以强迫的姿态与其他观点相处,它变成了一种标准(来自洞外),“真理”从事物无遮蔽的状态降低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降低不是一种说理类型向另一种说理类型的转变,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向另一种存在方式的转变。而洞穴中的众人由于出生就生活在洞穴中,洞穴是所有人的生存结构,这是洞穴和众人的存在前提(包括走出去的哲学家),当众人被洞穴赋予观念时,洞穴是一面认知的镜子,在镜子的背后人类有了最原始的认识并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被洞穴给予的观念长时间就形成了洞内的标准,当洞外的“标准”和洞内的“标准”相遇时就产生了冲突。柏拉图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哲学家的“真理”标准应该凌驾于众人的“标准”,而其实众人的“标准”已经被转化为了意见,他把真理作为一种正确性的标准对后来产生的哲学和科学深意存焉。
从柏拉图的洞喻说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意见是把世界理解为向我敞开其自身的过程,它向每个人展示它不同的面貌。人们提出意见的过程就是从各种角度揭示世界的过程,这种真实性被称之为“除蔽”。真理自身的敞开需要各个方面都被光所照亮,意见是真理的一个方面,只有意见存在,事物的真理性才能得以显现。而柏拉图在确定真理的标准性时,却把意见作为了它的对立面。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那里人们是依靠意见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理的,而在柏拉图那里却正好相反,柏拉图为了不再让其他哲学家遭受苏格拉底式的审判,直接把哲学家的真理当作城邦中的标准。至此,希腊哲学的本真状态开始扭曲,logos由言说变为了理性和原则,而“真理”从明敞、无弊的状态走入一种被“相”主宰的被遮蔽的存在物。其次,城邦生活是一种政治生活,是人所必须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人是不可能脱离城邦被定义的,即使是走出洞穴的哲学家最终也会必然受到使命感的召唤回到洞穴中,因为他感到了自身对城邦的责任。但是,哲学家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在城邦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无法让所有人都认同哲学家的真理统治。为此,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结尾处阐述了最终审判的观念,来用这个他自己都不一定相信的神话来确保哲学至上的地位。
自政治哲学形成以来它始终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用城邦中的生活经验来解释哲学,要么承认哲学地位的优先性并用它来评断政治,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分别是这两种选择的代表。柏拉图用哲学家的真理标准来统治城邦,显然是用哲学的先验性来判断政治生活,要求人们用无意识的思来进行活动,这贬低和扭曲了政治的本真面貌。柏拉图是一个为了哲学而拒斥政治的哲学家,他把丰富的政治生活、思与行统一的言说都还原为统治与服从的单一关系。由此,从古希腊发展出来的政治哲学的本真理解,在柏拉图这里完全消失了。
三、阿伦特对政治哲学的批判——回归政治的本真状态
“一个传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传统中的观念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人类心志的控制。相反,一旦一个传统丧失了活力,对于起源的回忆日益淡漠,那些陈腐的观念以及范畴有时候会变得更加专横;只有在传统的末日来临人们甚至不再反抗它的时候,它才可能暴露出它的所有强制性力量”[3],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中就一直存在着用看待自然的方式来看待人类世界的现象,而由此发展出来的政治哲学传统也是扭曲的,它对待政治的方式是“对(about)”而不是“作为(as)”。阿伦特带着对政治哲学求真的态度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政治应当是以人类世界中的各种政治现象为对象,以追寻人和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答所有人类世界的问题。阿伦特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区别于以往的批判,她不是将以前的传统进行简单的颠覆,而是在哲学与政治之间进行一种思想的转换,提出一种新的认识的可能性,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提供了思考方向。虽然她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勾勒存在着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是其中提出的哲学对于政治的误解却有着深刻的普遍意义。
阿伦特基于对思与行、政治与哲学关系的考量开始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行了重新审视。苏格拉底在阿伦特那里是一个处理思与行问题的典范,他不是简单地运用思考的力量或为行动树立标准,而是能够熟练地游走于两个领域来去自如同时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一类人。一般来说,哲学家都认为苏格拉底带来的破坏在于他抛给我们的不是可以依持的观念和真理,而是一无所有,而阿伦特则认为正是苏格拉底式的如“牛虻”“电鳐”“助产士”一样的不断追问才让人们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思考的自由”,这是一种最古老的“活动自由”,是所有自由活动的基础,当人的一切被剥夺的时,这是他们体验自由的唯一方式。苏格拉底的思考的意义就在于“思”这个活动本身,因为它总是不断地重新开始,正如“我思犹如珀涅罗珀之织物,在每个清晨拆解昨晚之所成”一样,这是对思考本质的一种素描。 “思”不是哲学家所独有的心灵活动,真正的“思”属于世俗世界,虽然苏格拉底式的思考最终只得从积极的思考出发得到了一个消极的结果,虚无貌似成为了思考活动永恒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并不来自于思考本身,而是来自人对于“求一”“求真”的着迷,来自于对无意识规则的接受并直接将其应用在人类事务上,而这一危险的来源我们可以继续追溯到柏拉图那里。
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由于受到苏格拉底审判和最终处死的打击,他力图找到一种可以应用于人类世界的永恒标准来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政治悲剧。这种永恒的准则从单一的前提出发来揭示一切事物和发生的事情,贬低意见存在的意义。在城邦生活(洞穴)中,真理要求人们不加思考地按照它提出的准则行动,求真就像是永不停顿的运动,最终导致了一个无人的世界的产生,人们感觉不再有思考的必要性,思考成了一种为了内在一致性而做的活动,个体交出了内在自由,就像他们屈服于外在的专制交出了肉体自由一样。当思不再具有其活动本身的特性时,当它以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取代意见与复多时,柏拉图式的思就脱离本身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人生来就是要追寻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因为一个活的生命无法接受一切都是以死亡为告终,人活着就是为了给自身一个满意的阐释。阿伦特对这种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在本质上就是想知道如何判断各种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值得的。由于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寻是无法通过任何经验事实和逻辑推理来确证的,所以它只能通过不断地思考及由此而来的判断来缓和这种不断地追寻的苦恼。她说,人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任何经历和生活方式只有把它放置在一个相应的框架和背景下才可以确定,人只有在这样的空间层面和时间维度下才可以追问自身。
阿伦特对于思性质的探究,对恢复本真的政治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真理”并不是“意义”,哲学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接受真理,他们是要用一种积极的讨论引起对方的思考从而深化人对自身生存的理解,人选择思考是因为发现了自己在世界中可以自由活动的另一个形式,柏拉图把真理的必然性等同于存在的意义,求真的思考的必然性和强制性给意义的追寻带来了无以复加的灾难,它抹杀了人发现自我意义的价值,这样的政治哲学总是带着暴力和专制,而这也是阿伦特批判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根源所在。
那么阿伦特心中本真的政治哲学是如何的呢?她认为,本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是一项思考的事业,但是使得思考具有政治意义是一种心灵的基本能力——判断。判断不同于思考能力却是通过思考而来,它在思考所提供的空间中进行自我释放。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思考并不产生判断而是使判断得以可能,思考只是为判断转化为行动提供了一个空间。为了实现思考与行动、哲学与政治之间调和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一种媒介,思考与行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协调需要一个既与思考有关又与行动相关联的第三者,我们可以通过对判断来解决思与行之间的困惑,恢复政治哲学的本真面貌。
判断是阿伦特构建新政治哲学思想中的灵魂概念,在她那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判断模式,一种是以行动者为中心构建判断概念,在这里表现为再现性思考。对政治思考的再现性思考就是通过不同角度来考量一个给定问题从而形成意见,“再现”即把不在场人的观点呈现,这种呈现不是简单直接的采用而是从不同角度观察世界,当在思考问题时心灵所关注的立场越多、接受的观点越多,它的再现能力就越强,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意见也就越有效。而另一种是以旁观者为中心的判断概念,意思是只有旁观者而不是行动者才能理解把自身作为一种景象来提供,即在面对一个景象时行动者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必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旁观者可以不在其中,从而观察到整个全局,所以他可以更好地理解整个景象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旁观者的“身在其中”而不是“隐退世界”,一种来自旁观者的带有回顾性特质的“注视”,也就是旁观者回顾性判断概念。在这两种看似不同的判断模式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其相关性和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其实,每一个行动者身旁都预设性地安排了一个旁观者,所以,这两种判断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相互转换,不论是行动者还是旁观者都提出自身对已然发生事件的理解,通过这种理解过程让自身与现实相和解,从而让我们有存在感和家园感。
判断从未离开行动者、从未离开现象世界。判断是人用心灵关怀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手段,它是个体思与行两者的结合,它是与行动者相联而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是与旁观者相涉而与心灵生活相接的一种人类灵魂深处隐藏的技艺,它是解决政治与哲学之间僵局的最为可能的出路。判断,最关键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力图通过自身有效性确立了世界意识的存在。当然,不是所有的判断都得以让人理解和承认,判断的有效性需要范例来保证,就像在康德的认识论中图示所起到的作用一样,提到勇敢我们就会想到阿基利斯,提到善良我们想起圣方济,范例确保了判断的有效性和可交流性,但是它也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保证,判断的有效性一定是发生在一定公共领域的历史经验和时间维度之下的,不管其如何扩展自身它都会使个体意识到自我的局限性以及更为广阔的他人及其关系的存在,意识到我不过是众人中的一个,占据的只是世界中的一隅,判断者在不同立场之间转换和漫游之际,就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由此世界意识得以确立。人在判断中实现了与他人共享世界,判断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自我是否与他人得到最终一致性的共识,而是通过判断使得公共领域这一世界意识得到确认,这是一种在实践上重建公共世界的努力。在政治中,世界才是问题所在,而阿伦特所坚持的世界意识正是对政治世界多元论立场的坚持及反对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政治唯有在尊重人们之间相互差异的基础上才是本真的存在。
政治哲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政治对哲学既有传统的怀疑又有传统的依赖。一直以来,阿伦特所作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想深刻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和关联,提出一种新政治哲学的可能性。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受哲学影响,对政治的关注并非来自政治现象。在哲学家看来,人类世界的现象是意见领域,他们只关心“哲学如何保护自身并从人类事物中解放出来”[4]。政治哲学也如哲学一样起源于惊异,政治哲学建立在对人类事物领域的惊异的基础上,它把政治现象的起源作为思考的对象。当代的哲学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些哲学家那样,只关注“理念的天空”,人类世界中的纷纭现象让他们惊异地发现了政治领域中的哲学意义,政治哲学对人类世界有如此多样的显现表现出的惊异,根源在于对人类多数性的承认,它认识到人类事物形成了最终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放弃了自己超越的位置,不再用自身拥有的真理来裁判所有问题,这个态度的转变可以说是对整个政治哲学领域进行批判后得到的最重要的结果,它意味着政治哲学受哲学影响形成的对人类世界现象贬斥的传统彻底消亡,这也是阿伦特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批判的意义所在。实际上,阿伦特是一位一生都在追求人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政治哲学家,她思考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理论性的答案,而是为了激励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丰富性,即思考人类责任的意义和判断的力量。借助判断,我们可以和已经发生却不能挽回的事情达成和解;借助判断,我们也许能在这样一个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上获得一点家园感;借助判断,我们可以感到自己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阿伦特才呼吁:“即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5]即用判断来使公共领域得以恢复,使政治得以恢复其本真状态,保证人们多样性的显现空间,让世界成为一个适合任何人居住的场所。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
[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24.
[3]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G].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406.
[4]Hannah Arendt.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M]//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Jerome Kohn,edi.New York:Harcourt Brace&Co.,1994:428.
[5][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M].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
〔责任编辑:杜娟〕
2016-02-26
王晓蓓(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从事实践哲学研究。
D09
A
1000-8284(2016)09-0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