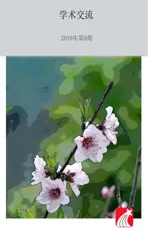现代性视域下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费赫尔关于审判和处死路易十六事件的理论分析
2016-02-27曹丽新
曹丽新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现代性视域下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
——费赫尔关于审判和处死路易十六事件的理论分析
曹丽新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法国大革命被公认是现代社会的开端。革命进程中,审判和处死国王路易十六被看作是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原则的象征性行为,其正义性问题很少受到质疑。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费赫尔却在现代性反思的视域下重新审视这一典型事件,指出在法律上、道德和政治三方面不可解决的困境使其不具备任何正义基础,因而破坏了大革命的正义性。事件遗留下来的隐患也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不断滋生和变异,引发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
费赫尔;法国大革命;正义性
对法国大革命正义性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革命的起源、革命中的政策和民主政体以及革命的命运,使革命呈现出一个完整形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费赫尔在《被冻结的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国几乎没有关于革命正义基础的认真可靠的讨论,也没有至关重要的决议来确立革命正义的原则和程序。”[1]138大革命的正义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们就这一问题已经达成一致,争论和分歧仍然存在。
一、典型事件及其正义性的争议
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典型代表。普遍的观点认为,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平民的反抗。因此,对于当时的革命参与者以及后继的研究者来说,审判和处死国王是一种打破君主专制传统的象征性行为,也是共和国的创始性行动。
熟知法律和司法程序的人不难发现,从审判到执行死刑这一过程中存疑的问题很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国王的辩护律师德赛兹首先质疑了国民公会审判的合法性,即作为原告,人民的代表们不能担任审判官。其次,他援引1791年宪法规定的国王神圣不可侵犯质疑审判的违宪性,即作为国王,路易十六不能被审判。最后,他强调即使路易十六有罪,最高刑罚不过是放弃王位,依然保有普通公民的权利,即罪不至死的路易十六不能被剥夺生存权。但是,国民公会并没有接受这些辩护,正如日本史学家横山纪夫描写的:“当时的法官们像聋子一样,对于辩护听而不闻。”判决的基调在国民公会中早已确定,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羽翼未丰,需要这次流血来确保王朝复辟的幻想化为泡影。圣鞠斯特直接把这一司法审判问题置于道德领域来加以评判:“统治,就不能是无辜的。任何国王都是背叛者和篡夺者……必须以国王之死为人民被杀复仇。……如果他是纯洁的,那么人民就是罪恶的。”雅各宾派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也认为应该由国民公会宣布以革命的名义判处路易十六死刑,他说:“路易不是被告人,你们不是法官;你们是政治家,是国民的代表,你们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人。你们的任务不是对某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是采取拯救社会的措施,起到国民先知的作用……人民审判不同于法庭审判:他们不作判决,他们像闪电一样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为乌有。这种审判比法庭审判毫不逊色……当国王被革命推翻而革命还远远没有由正义的法律巩固起来的时候,监狱也好,放逐也罢,都不能使国王的存在成为对公共福利毫无威胁的事情。审判上所承认的这种普通法律的残酷的例外,只可能由国王的犯罪本质来解释。我以悲痛的心情说出这一重大的真理: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法国需要生。”*本段中,以上三处引文均转引自林海《为路易十六辩护的人》,《检察日报》,2015年4月21日第3版。最终,路易十六在微乎其微的多数通过的判决下被送上断头台。
就审判和处死国王这一典型事件,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们态度不一。以保皇党人和右派为代表的研究者们持谴责态度,他们把对国王的审判和处死看作是一种犯罪,是对传统的神圣权威的残忍背叛。埃德蒙·柏克在其著作《法国革命论》中以英国议会向国王所作的声明为依据,强调臣民对于国王世代忠诚和顺从的义务,以此证明法国人民没有反对国王和进行革命的权利,严厉谴责法国人民在革命中处死了一位温良合法的君主。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对审判国王大加谴责。在他看来,从法律上对国王过去的统治进行定罪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而,这是最严重的犯罪。在君主作为专制国王而进行统治终结之后,又同意由最高的执政者进行统治,这是更不合逻辑的,是更为恐怖的犯罪。康德在道德和政治之间搭建了桥梁,特别强调政治参与者的道德。他批判政治道德家,主张道德政治家使道德(即康德的实践理性和正义)成为政治准则。他也看到道德准则与既定的政治任务的紧急状况很难协调,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政治家可能会蜕变成专制的道德家。但是,康德强调,在捍卫失常状态时尊重善的准则而不选择恶的准则。因此,康德捍卫路易十六的权利而反对国民议会,把处死路易十六谴责为一种比谋杀还严重的罪,但他也庆幸处死路易十六这一行动得以实施的革命原则,这向我们表明了革命的力量。[2]252另外,利奥塔也把判国王死刑称为犯罪,为现代法国奠定了一个非常成问题的基础。
相反,也有许多研究者对处死国王的行为大加赞扬。美国思想家潘恩在批驳柏克的保皇思想时指出,法国人民反对的不是路易十六,而是反对政府的专制原则。法国的专制主义历史悠久,已经深入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巴士底狱,对于法国这种通过层层官僚机构而加以实行的专制主义,其根源难以觉察,也是无法加以纠正的。路易十六的温良秉性丝毫不能改变君主专制的传统,历代专制王朝的一切苛政在继承者手中仍会不断地重演。在潘恩看来,法国革命不是由私人仇恨而激起的,而是从对人权的合理思考中产生的。这正是法国革命的伟大和光荣之处。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基于反对君主政体、赞成共和国原则的立场肯定了案件的价值,从历史、政治和法律三方面,分析了路易的定罪和死刑是一个必要的行为,但也指出了它在形式上的欠缺。沃尔泽的结论是:“公众弑君是一个完全绝对性的方式,结束了旧政体的神话,因为这个原因,它也是新政体的建构行为。”*转引自[匈]费伦茨·费赫尔《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刘振怡、曹丽新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阿伦特在《论革命》中也指出,“当一切政治发展都被路易十六倒霉的阴谋诡计所笼罩之后,专制统治才接踵而来”[3]89。大革命戳穿了宫廷的阴谋,撕开国王伪善的面具。处决的并不只是一位特定的国王,不管他是不是叛国者,这是在宣布君权本身是一种罪行。
而自由主义者对这一问题却漠不关心。例如,傅勒只是指出国王被审判是因为他被卷入到外国势力和流亡者的阴谋之中,却没有论及审判的重要意义。自由主义经典作家伯克也只是对路易十六的无能表示蔑视,没有给予过多关注。洛德·阿克顿也指出,免除路易的罪行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给其统治下的人们带来浩劫,并且密谋恢复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威。他以蔑视的口吻写道:“路易十六带着内心的满足,对罪行的无意识,对他浪费的机会和他带来的痛苦熟视无睹而赴死,作为一个悔过的基督徒但又是一个无悔的国王而死去。”[1]124
二、费赫尔对典型事件正义性的质疑
就审判和处死国王,费赫尔明确地站在反对立场上。在费赫尔看来,就这一典型事件而言,“在政治上它是多余的甚至不相关的行为,没有为共和国解决任何问题。正如历史证明的,在死刑之后并不缺少王位将来的继承人,君主政体原则也没有随着路易而葬身于断头台上。审判和死刑甚至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119。费赫尔指出,审判和弑君是一个多面的矛盾综合体,在法律、道德和政治三方面都面临不可解决的困境。
(一)法律困境:程序合法性的缺失
虽然在审判过程中,吉伦特派曾主张:审判越是符合程序正义,裁决和判决越公正,作为共和国基础的正义观念就越稳固。所以,他们希望对暴君的审判应该是形式上合法的审判,至少具有形式合法的外表。但是,在费赫尔看来,实际的审判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对国王的审判和处以死刑,虽然符合正义原则,但由于其缺乏合法程序和形式,反而损坏了法国革命的正义性。首先,国民公会并没有得到人民的书面法律授权,未经授权就进行审判,其审判资格本身就值得质疑。其次,路易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暴君,其罪行是其敌人事后分析出来的,并没有合法的证明。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对暴君的残暴行径进行的猛烈抨击中,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国民公会指控的罪行基本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叛国罪。国王作为国家的首脑和神圣权威的代表,叛国就等于背叛自己,背叛自己的国家。其三,革命者们把处决君主作为废除至高世袭权威的象征,但这一行为本身缺乏合法性。审判和处死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原则的象征,这么做毫无正义可言,这一没有合法性的审判也不可能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因为国王是假想的君主原则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个实际的个体。即使国王可以因其犯罪行为而被控告,但死刑的执行不仅剥夺了路易国王身份所象征的权威和权力,同时也剥夺了他作为普通公民的权力。共和国没有向国王给予应有的宪法保证和豁免,甚至没有上诉及复审的机会。最后,对国王的审判不是正当的审判,因为它不能以宣告无罪结束。费赫尔特别强调公众处决君主作为废除至高世袭权威的需要和合法性之前提的必要性和有用性。路易的死不是因为其犯罪的行为本身,而是革命的现实需要,是防止君主政体复辟的发生。正如圣鞠斯特所说的:不存在牺牲一个人或者反对一个人的判决,只有为共和国的安全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一种为了国家执行的预防行为。只有在君主制原则的法律来源和个人化身被消除之后,共和国的合法性才能得以确立,路易必须被判定有罪,否则共和国就没有扫清罪恶。[1]129-130因此,在费赫尔看来,审判缺少合法仪式,甚至完全没有正义的外表,是“对所有政权虚伪审判历史的讽刺和极端歪曲”[1]137。
(二)道德困境:暴力合法化的自我矛盾
在道德上,当我们为了惩罚哲学意义上的罪行而成为胜利者时,弑君是一种集体怯懦的行为表现。路易十六并非传说中的暴戾成性、横征暴敛的封建专制君王,而是一位温和而又矛盾的统治者。他在革命前试图进行改革,希望通过民众的力量迫使贵族让出一些特权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使积弊深重的国家走出困境。正如辩护律师德赛兹所说:路易十六身居王位,但没有罪行、没有渎职,他简朴友善、从善如流。阿克顿对路易十六的分析肯定了其进行的改革:“正是他(路易),迈出了与法国人同心协力建立一个稳固政体的第一步;正是他,取消了专断的权力,取消了税收方面的特权,不再根据功劳之外的标准提拔官员,也不再实行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涅也指出路易十六既不是革新家,也不是专横暴戾的君王。他缺乏坚强的意志,没能完成国家的重大变革。因此,路易十六虽治国无能,却并无必死的罪行。可是,国民公会却以人民之名让他做了牺牲品。公众弑君破坏了道德传统和神圣权威,却没能为所谓美德共和国构建出新的道德基础。相反,它是专制的基础,而不是自由共和国的建构性行为。卢梭的观点是弑君的哲学基础:“以绞杀或废除暴君统治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是合法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都是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与不幸。”[5]圣鞠斯特强调的是消灭国王的哲学基础,而不是合法判决。在他看来,国王置于社会契约之外,因此,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以正义精神来对其进行判决。
费赫尔指出,圣鞠斯特忽略了神圣性问题。正如帕特里斯·海格奈特指出的,在1789-1790年间,在君主立宪制度备受推崇的情况下,路易十六可能比法国以往的任何君主都更受欢迎。在革命之前,国王是圣神权威的象征,在法律上是法律和正义的来源。路易以其君主角色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被看作是合法的,没有人有权利由于其之前的施政而惩罚他。君主被看作是法律的来源,也不能做不公正的行为。弑君仅仅是因为革命者的恐惧,因为如果路易还活着,他可能重新得到其权力,并且给革命者以报复性惩罚。因此,在费赫尔看来,这种行为不是带有道德基础的正义行为,而只是一种懦弱的自卫。君主的死刑,给灵魂、人类正义观念意识注入了恐惧,因此,革命者不得不使用暴力,并赋予暴力行为以一种惩罚行为、司法过程的伪装,同时又厚颜无耻地赋予暴力行为以神圣权利和正义基础。[1]132所以,在德性共和国的建构中,反革命分子没有人权,因其“不道德”而受到惩罚,引发的就是大规模迫害和屠杀。以死刑的方式净化没有道德的恶人,这正是雅各宾政体之下恐怖行动的特征。
所以,费赫尔肯定弑君是谋杀,是一次犯罪,不能通过法律使其合法化。如果把谋杀敌人当作正当的实践活动,正义的希望将永久地被封闭。因为“一旦一种谋杀行为被作为最高的正义而公开地和自豪地展示出来之时,人民就已经选择了罪恶的准则”[2]239。
(三)政治困境:革命正义性的背叛
在政治上,哲学理想的血腥实践是通过斩除一个人而结束一个政治系统的象征,这是一次整体的失败。费赫尔指出,对于革命领袖来说,国民公会启动的过程不是一次合法的审判,而是一个政治决断。审判依据的不是共和国的正义原则,而是合法原则混乱的大杂烩,而且,由于缺少形式而找不到合法基础。以政治决断代替法律,说明革命参与者在制定革命法律时,制定政治的法律,实践违法的政治。安全是自由共和国的最高权威,这就意味着在危急时刻和紧急状态之下,一切政治决断都具有合法性,包括剥夺人权。一旦革命领导者残暴专断的决断付诸行动,其原意是摧毁君主专制原则,但却无意中加强了任意专断的权威原则。政治决断行为的专断表现为“正义的即时行政”,恐怖应运而生。
费赫尔认为,雅各宾派一方面希望通过弑君行为见证君主政体原则象征性葬礼,以此作为一种实现哲学承诺的行为;另一方面,割断与旧制度之间的脐带,以此作为新共和国和旧制度之间的分界点。君主制度的终结以个人的斩首这一象征性行为来破坏传统,其实质是用一种新的神话取代旧的神话。为了结束旧神话而执行的象征性死刑,同样是一个宣告新神话象征性的、不合法的行为。
三、革命正义的隐患与现代性病症
(一)超出法律正义的政治权威
在革命参与者看来,公众弑君惩罚了犯罪的政治权威,有利于共和国政治平等的实现。然而,正如费赫尔说的:“审判国王事实上将政治正义引入后启蒙政治之中”[1]133。弑君的意图是破坏君主专制原则,摧毁神圣的政治权威,但由于缺乏法律正义和合法程序,使其违背了共和国的初衷而形成了新的政治权威。审判和死刑的执行是紧急状态下的一次政治决断。此时,决断者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受法律限制。革命者计划从他们的新世界中清除暴力,结束疯狂和非理性,甚至认为暴乱状态是回归自然状态。但是,决断者超出法律之上的任意专断,不可避免地引起残暴。同时,在政治革命的狂热浪潮中,新的最高统治者不断自我膨胀,在政治形而上学中得以神化,在政治世俗化之后形成新的最高崇拜。最高主宰在道德上的完美,像正义之神一样,能够把美德注入人们的心中。对最高主宰的绝对崇拜,意味着“美德共和国”的建立指日可待。而敌人不只要因为其威胁共和国的安全而受到审判,而且要因为其“不道德”而受到惩罚。由此演化而来的观念是,社会的文明、政治的发展必须净化这些道德恶人。这种惩罚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政治决断,也是基于敌人的本性而作出的决定。政治权威成为道德典范,成为评判道德上善恶的标准和依据,最终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集权的恐怖主义系统。种族中心主义和排犹主义正是在这种观念之下催生而成的。
在恐怖统治之下,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加以崇高化,断头台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政治权威的神圣化,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宗教”,这也是政治原教旨主义的一种雏形,而这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崇拜正是现代性之下克里斯玛式统治的前奏。
(二)违背革命正义的政治清算
审判和处死国王是紧急情况下的非常措施,而在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下紧急状况不确定地延长,非常措施就具有了合法性,并且发展成为实施“革命正义”的行为。国王没有加入社会契约,因此法律认可和法律保护都不能运用在他身上,这种观念延伸到整个社会群体,就会发展成一个大规模剥夺人权的机制。审判之后,《嫌疑人法案》的颁布和执行,使无数嫌疑犯被送上断头台。一旦被怀疑,任何人都可以被宣判有罪,而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的审理程序。正如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克劳德·勒弗所说的:革命政府的法律“取消了罪行的判定标准,诛意之广,无人可以脱逃革命大义之法网”[6]。革命政府取消了一切法律的判断和审理程序,在紧急状态下无所限制,而其出发点和目标却被标榜为对祖国的热爱、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以及摧毁敌人。所以,革命的正义逐渐演化为迫害、整肃、清算和诛除,任意的专断和残酷的暴力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恐惧之下。
卡尔·施米特对现代政治概念的总结正是这种革命正义的极端化。在施米特看来,政治的概念就是敌友的划分,而最具政治性的时刻,就是在紧急状态下作出敌友的判断,进而联合盟友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这也是施米特因其与纳粹的关系而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观念正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真实写照,而革命正义口号之下的政治清算在近现代的历史中不乏实例。
(三)对抗民主正义的合法暴力
处死国王是正义的行动,因为它是群众基于革命的合法性和人民的正义而对敌人进行的公正惩罚。这一行为也象征着人民主权取代君主主权,宣告人民作为新的统治者的民主政治时代的到来。这正是卢梭人民主权哲学承诺的政治实践。但是,这种集体统治蕴含着潜在的政治风暴,甚至可能陷入集体政治歇斯底里症之中。原本以国王为核心构成的政治社会统一体,随着其头颅被砍断,整个社会就缺乏了得以凝聚的载体。人民的自我同一性就取而代之,成为所有正当性、真理与共和国美德的根源,而人民永远不能被推上断头台。在革命背景下,只有敌人才能给予革命以同一性,而敌人无处不在,这种普遍怀疑的心态强化了革命想象,造成恐怖统治。公意并不是清楚确定的,只能通过个体意志的集合而简单地体现。人民在选举其代理人时很容易作出错误判断,同时也不能保证人民代表不会作为暴君而进行统治。政治的神化或‘救赎政治’的计划天然地就蕴含在人民主权的二元结构中。正如阿伦特指出的:“政治领域的绝对性问题无一例外,都归因于不幸的历史遗产,归因于绝对君主制的荒诞不经,它将绝对性,将君主这个法人,放入到政治体中,然后革命走入了歧途,徒劳地试图为这种绝对性寻找一个替代品。……时至今日,被置于绝对统治权地位的那种新的绝对性,究竟是法国大革命伊始西耶斯的民族,抑或它已经在革命史最后四年,伴随着罗伯斯庇尔而变成了革命本身,这些都已经无关宏旨了。因为,最终燃烧世界的正是两者的结合:是民族革命或革命的民族主义,是说着革命语言的民族主义或以民族主义口号发动群众的革命。”[3]142-143
作为一场民主革命,大革命使每个人都挣脱了政治特权所代表的权威,可以依据其个人意志而行动,以正义与理性原则作为判断其行为的唯一准则。这是启蒙政治的主旨。但由于大革命违背了正义性,其法律、道德和政治上困境的隐患,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滋生和变异,表现出多种现代性病症:大屠杀、集权主义、绝对性、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崇拜、种族中心主义等。因此,在现代性境遇中,人们享受着美好,也历经着不确定性的磨难。正是基于此,费赫尔才疾呼,雅各宾主义革命应该被冻结,不能使暴力神话作为革命内在的必要性而残存下来,以非正义手段实现正义目的,这一行为本身也是非正义的。
[1][匈]费伦茨·费赫尔.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M].刘振怡,曹丽新,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匈牙利]费伦茨·费赫尔.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性的诞生[M].罗跃军,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4][英]洛德·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M].姚中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47.
[5][法]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5.
[6]Lefort Claude.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M].Macey David,trans. 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81.
〔责任编辑:曹金钟〕
2016-07-04
曹丽新(1978-),女,黑龙江穆棱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
B505;K565.41
A
1000-8284(2016)09-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