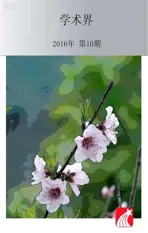制宪权起于决断还是协商:民主制宪与共和制宪
2016-02-26○赵强
○赵 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191)
制宪权起于决断还是协商:民主制宪与共和制宪
○赵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北京100191)
在制宪权理论中,施密特沿着西耶斯民族制宪权的路径发展出了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而阿伦特则通过对西耶斯民族制宪权的反思提出了制宪权与制宪权威相分离的制宪理论。施密特的决断论完全排除了制宪过程中不同政治主体间协商与妥协的可能,而阿伦特则将制宪权建立在“约束和承诺、联合和立约”的基础上,但其过于强调制宪权威与制宪权力相分离的理论则限制了其对制宪合法性的理论解释力。通过将制宪分为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两个逐步达成的进程,进而区分出民主制宪与共和制宪的不同,仍然将制宪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行使制宪权的基础之上,但制宪权的基础不是制宪权主体做出的政治决断,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不同政治主体间的协商与妥协。
制宪权;决断;协商;民主制宪;共和制宪
制宪权是现代宪法学,尤其是欧陆宪法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成文的宪法典成为主要的宪法模式之后,追问宪法创制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在理论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制宪权的概念正是应此而诞生的。“制宪权的概念提出后,宪法是否正当的问题就转化为是否享有制宪权的问题。”〔1〕但是自法国思想家西耶斯提出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制宪权概念之后,后世也是众说纷纭,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形成一个学界公认的理论通说。
一、施密特的决断论
在关于制宪权的理论学说中,德国宪法学者卡尔·施密特的决断论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施密特看来,“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凭借其权力或是权威,制宪权主体能够对自身政治存在的类型和形式作出具体的总决断。”〔2〕在施密特的理论中,制宪权体现为制宪权主体在宪法时刻做出的政治决断,这里的制宪权主体或者是君主,或者是人民,而且“制宪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3〕
施密特在其理论的一开始,并没有完全否定协定宪法也是宪法的重要起源,“宪法要么通过制宪权主体单方面的政治决断产生出来,要么就通过若干制宪主体相互间的商议产生出来。”〔4〕但是,在施密特的理论框架中,协定宪法只能是用来分析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前的封建等级制的国家中的宪法发展史,他将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以及1688年的《权利法案》都视为这一类型的协定宪法,在协定宪法中,宪法的作用并不是要“建构统一体,而是预设了统一体”〔5〕。与后来的民族国家时代相比,这是英格兰封建等级制的岛国政治的独特性,“从历史上看,在欧洲大陆,这些关于政治统一性和民族一体性的基本概念产生于专制君主制的政治一体性,而在英国,中世纪国家之所以能够朝着民族统一体的方向不断演进,是因为‘岛屿位置顶替了宪法的功用’”〔6〕,它并不需要一个宪法时刻来创生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因此也就不需要宪法来承担建构民族共同体的功能,其宪法主要是解决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
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国家成为政治共同体存在的主要形式,与英格兰的协定宪法相比,宪法不仅要承担起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的问题,更要承担起民族国家的建构任务。因此,人民将自己建构成为制宪主体,“人民意识到自己作为拥有政治行动能力的主体的身份,必欲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7〕,人民通过制定宪法这一活动,对自身存在的特殊类型和形式作出了决断,将自身构建为一个民族。
在施密特看来,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的宪法理论中,虽然也存在着君主制原则,但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封建等级制中的君主了,而是可以“采取单方面行动作出根本政治决断”的制宪权主体了,在这里“宪法不是什么协议,而是国王钦定的法律。”〔8〕在君主立宪制中,在国王与人民代议机关的“二元制”的体制下,君主制原则和民主制原则之间的妥协“绝不是真正的实质性妥协,而只是延迟性的形式妥协”〔9〕,虽然施密特也承认“就历史和政治现实而言,只要国内和国外政治形势保持平衡,这种延迟决断的状态就是完全可能的”〔10〕,但施密特从没有把这种协商妥协的状态看作是一种稳定均衡的状态。在以民族国家原则为主导的政治共同体的宪法创制过程中,施密特完全否定了宪法协议成为宪法的可能性,因为“真正的宪法协议至少预设了两个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缔约方,每一方都拥有一个制宪权主体,因而都是一个政治统一体。”〔11〕“如果宪法在现有政治统一体内部是通过协定或协议制定出来的,这样一种协议在冲突情况下对制宪权主体就没有任何约束力。”〔12〕取消了协定宪法的可能性,也就将制宪过程中的协商与妥协排除在了制宪进程之外。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施密特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将作为个体的公民间的,以及公民团体间的协商与妥协排除在了制宪进程之外,其理论在追求制宪权主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也为个人或是政治团体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将自己单方面的政治意志上升为人民的意志打开了通道,为专制开启了绿灯。但是在考察英美的制宪史的进程时,我们就会发现,宪法并不是诞生于“民族整体的政治决断”,其宪法制定和稳定运行的基础正是施密特所要否定的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妥协。
二、阿伦特制宪权威与制宪权相分离的制宪理论
汉娜·阿伦特并不是一位专门的宪法学家,但是她通过对美国革命的分析和解读,发现一套不同于施密特决断论的制宪理论。阿伦特的理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施密特的,但是她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决断论的制宪论,乃至以民族国家为整体的制宪理论都构成了批评和挑战。
阿伦特的制宪理论是从批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通过对“革命意义”反本溯源的分析,阿伦特指出,现代革命中所具有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含义“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13〕,并不是革命的本意,社会之所以会发生革命,并不是人民追求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共同体的结果,其目的是要恢复在封建等级制的政治结构中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利,虽然在新的政体原则之下人民自由与封建体制下人民的自由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政体”的诉求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构建自由”是革命唯一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这也是立宪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从这里开始,阿伦特的制宪理论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耶斯和施密特民族制宪权的路径。在阿伦特看来,革命并不是像西耶斯论述的那样,革命将一个政治社会推进了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民只有行使制宪权力才能为自身的存在和合法性给予全新的定义。对于西耶斯和施密特在宪法理论中所极力强调的民族共同体意志的建构问题,阿伦特指出“群众意志的定义变化无常,以之为基础和作为其立国形式的结构,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14〕她对于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是嗤之以鼻的,她讽刺道“将民族国家从瞬间崩溃和毁灭中拯救出来,非常轻而易举。任何时候只要有谁愿意背负专政的重负和荣耀,民族意志就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强加于民。”〔15〕在阿伦特看来,构建民族国家并不是制宪的首要目的,西耶斯民族国家的制宪权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王国’(哈林顿)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用民主制置换了君主制,用多数统治取代了一人统治。”〔16〕这与追求自由立国的共和国是背道而驰的。
阿伦特的制宪理论是建立在制宪权威与制宪权力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阿伦特首先将权力与力量区别开来,“权力不同于力量,力量是每个人与一切他人相隔绝的状态下都拥有的天赋和财产,而权力只有在人们为了行动而聚集在一起时才会形成,而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一哄而散、互相疏远时,权力就将烟消云散。”〔17〕因此,权力的基础是约束和承诺、联合和立约,而不是赤裸裸的暴力。当法国革命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人们回到前政治状态时所获得的不是权力,只是混乱和不受约束的暴力,“这种乌合产生不了权力,前政治状态中的力量和暴力是会夭折的。法国革命者不懂得如何区分暴力与权力,相信一切权力必须来自于人民,他们向群众这一前政治的自然力量打开了政治领域的大门,却被这种力量扫荡一空,重蹈了国王和旧权力的覆辙。”〔18〕通过区分权力与力量的差别,阿伦特就避免了宪法由何种初始性的权力创造的难题,由于在前政治状态中存在的只是暴力,而不是权力,人民需要重新立宪来创造新的国家权力。
既然宪法不是由权力产生的,那么宪法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呢?阿伦特在这里就提出了权威的概念,她认为权力与法律的来源是不同的,“权力的根源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来自于‘基层’人民,法律源泉是‘在上’的,在某个更高的和超验的地方。”〔19〕法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试图将权力与法律的权威同一化,都赋给了神化的人民,这才导致其堕入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法国大革命致命的大不幸在于,没有一个制宪会议拥有足够的权威来制定国内法……反观美国革命之大幸就是,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对抗之前,已经以自治体形式组织起来了。用18世纪的话来说,革命并未将他们推入一种自然状态”。〔20〕因此,美国的制宪会议的合法性并不是来自于人民的制宪权,而是“完全从次级权威中”汲取的“总权威”。“如果联邦会议不去创造和构建新的联邦权力,而是选择削弱或是废除州权,立国者将立刻遭遇法国同行们的困惑:他们将丧失其制宪权力。……联邦体系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原则唯一的替代选择,它还是避免陷入制宪权权力与宪制权力恶性循环的唯一道路。”〔21〕
阿伦特将制宪权力与制宪权威相分离的理论避免了制宪进入恶性循环的恶果,“阿伦特的理论尽管带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而法学感稍嫌不足,但却给打破恶性循环带来了重大契机”。〔22〕但是权威与权力本身就是相伴相生的概念,即使在美国制宪的过程中,美国宪法的权威也不仅仅是来自制宪会议从下级权威中汲取的总权威,其宪法还需要人民的批准才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因此人民的制宪权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制宪进程之外,相反是宪法合法性的根本性来源。但是阿伦特“权力的基础是约束和承诺、联合和立约,而不是暴力”的观点为我们认识制宪权提供了新的可能的思路。
三、基于协商与妥协的制宪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施密特沿着西耶斯民族制宪权的路径发展出了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而阿伦特则通过对西耶斯民族制宪权的反思提出了制宪权与制宪权威相分离的制宪理论。阿伦特的理论对我们理解英美的革命与制宪权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她的制宪理论并没有在宪法理论上解决在制宪的过程中自由政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她并没有将制宪过程中自由政体所赖以存在和建立的政治基础深刻的揭示出来。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继续沿着阿伦特的思路,通过对施密特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的反思,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和认识制宪权和制宪过程,那就是基于协商与妥协的制宪权理论。我们将制宪过程中一部宪法所需合法性分为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制宪的实质合法性是指在制宪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既有的政治权威纳入到制宪进程中来,通过制宪将不同政治团体间的协商与妥协转化为宪法制度的设计,而制宪的形式合法性则是指将在实质合法性阶段完成的宪法草案交由人民讨论、批准,通过人民批准的宪法草案才能成为正式的宪法规范。
(一)英格兰宪制史中的协商与妥协
在施密特的制宪理论中,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人民主权原则产生之后的制宪活动,而将英格兰自中世纪以来的宪制发展史排除在了其理论解释之外,他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下,不同阶级之间的“宪法协定”并不能称之为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因为协议本身就预设了不同的政治主体,这与近代宪法的主题——完成政治统一体的构建——是相悖的,“协议并没有为政治统一体奠定基础,也并不包含对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23〕但是,在笔者看来,在英格兰的宪政史中,不同等级间的协商与妥协恰恰是英格兰宪政精神的核心之所在。
从大宪章以来的英格兰宪政史,不仅完成了英格兰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也完成了对君主绝对主义的驯化。在宪政的危机时刻,之所以要协商与妥协,是因为不同等级共处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因此公权力并不是君主的私有之物,君主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任意侵占、剥夺其他等级的利益。在签订《大宪章》和1688年革命的过程中也许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各等级坐下来和平的协商、立约,其背后也夹杂着反叛、强迫以及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这在任何一个宪政危机时刻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在立宪过程中是协商与妥协,而不是“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才是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关键,“敌友论”的思维模式只能是不断强化团体内部的凝聚力,而将政治共同体置于分裂的境地,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一方以人民的名义做出的单方面的政治决断,而不是“政治共同体的共同意志”。这与通过立宪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本意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基于协商和妥协的立宪才是构建政治统一体共同认知的基础和关键。
对君主权力的驯化也是在协商与妥协中完成的。对君主权力限制不可能来自于君主自上而下颁布的“主权决断”式的宪法,其最根本的是来自于贵族和平民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并不是要推翻君主制的统治,而是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保障自身的权利。当1640年代的英国内战,克伦威尔推翻了君主制之后,英国人民发现自己的权利面临着一个更为强大的专断权力的威胁,比自己先前反抗的国王的权力更加专横、野蛮和不受限制。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英国又重新请回了君主,经过反复的斗争与妥协,最终在1688年通过与新君主签订《权利法案》形式完成了对君主权力的驯化。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对君主权力的驯化并不仅仅是将双方妥协的内容以成文条约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协定宪法中除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威能够保障双方能够履行契约,因此更为有效的办法是将立约时双方的力量对比转化为制度化的设计,将任意专断的权力放入制度化的笼子之中。在《大宪章》中就设定了一个抵抗委员会,以防国王不遵守其中的条款。而在《权利法案》中更是将国王与议会的权力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划分,将国王的权力置于议会的权力之中,将君权与议会的权力共同熔铸于“王在议会”(King in Parliament)主权结构之中。〔24〕
在英格兰宪制发展的过程中,直至1688年《权利法案》的签订,人民主权原则还未成为政治秩序的主要构成性理论,即使有人民主权因素的影响,英国的宪制通过议会主权的原则很好地吸收了人民主权的理论诉求,从而避免了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人民必须出场制宪的理论难题。因此我们可以说英格兰的宪法完成了实质合法性的制宪,而并没有完成形式合法性的制宪,但在人民主权原则成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之前,制宪的形式合法性的缺失对于宪法的合法性来说并不构成挑战。
(二)美国制宪中的协商与妥协
美国的制宪是建立在推翻英国君主统治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君主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支撑,建国者们必须将国家权力建立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之上,那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是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最终依归。但是,在美国制宪之前,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政治共同体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直接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美国的建国者来说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美国的建国模式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在施密特那里,美国的制宪被划为了联邦制国家的制宪,而联邦制原则的制宪与民主制原则的制宪是相悖的,因为在民主制原则的制宪中,“制宪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这一民主概念取消了国家的联盟基础,从而也就取消了国家的联盟性质”〔25〕,因此在联邦制国家的制宪中,“联邦没有自己的制宪权,而是建立在协议的基础上。联邦有可能对联邦章程行使修改权,但这种权力不是制宪权。”〔26〕施密特对联邦制宪法的分析很有洞察力,但其理论可能更适用于对欧洲历史中联邦制国家的解释,但对于新世界中联邦制的美国施密特则并没有抓住其核心。虽然施密特在分析联邦国家宪法的制宪会议的特点时也注意到了宪法是要交由各成员邦人民表决同意的〔27〕,但是他并没有给予这一程序以实质性的意义。而在阿伦特的理论中,在美国的制宪过程中,制宪权威与制宪权是相分离的,在制宪过程中主要是制宪权威在发挥作用,人民的制宪权只是在宪法草案制定完成后交由人民批准时才出场,而宪法批准完成之后,人民的制宪权也即隐退,这样就能够避免人民不断出场的恶性循环。阿伦特的理论前文已经深入分析,这里就不再深入展开。
笔者认为,美国的制宪经典地为我们展现了制宪的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合二而一的过程。美国1787年的制宪会议起源于革命胜利后《邦联条例》治下的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联邦层面的政府权威不足的问题。《邦联条例》治下的美国是制宪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制宪会议得以召开的基础。制宪会议要考虑的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而只是协商在现有的州政府之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全国政府的问题,在《邦联条例》下经过初步政治整合的美国已经有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并不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只是这个经过初步整合的政治秩序不足以应对当时出现的各种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在邦联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全国政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像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制宪过程与其说是人民制宪权的出场,不如说是制宪权威的凝聚,美国的制宪会议是建立在现有各州现有权威的基础之上的。
再从制宪会议的组成上来看,制宪会议是由州议会向制宪会议选派代表的形式组成的,每个州2-6名代表不等〔28〕,但是制宪会议中采用每州一票的表决规则。制宪代表们来到制宪会议代表着自己州的利益,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要与其他州之间达成一个州与州之间的宪法协议,而是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一部新的宪法,虽然在制宪过程中有人倾向于更多的保留州的权力,有人期望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但是这与施密特所说的联邦国家的宪法起源于邦与邦之间的宪法协议有着本质的不同。
制宪会议的召开过程,就是代表各州的制宪权威之间的协商与妥协的过程,也就是制宪的实质合法性达成的过程。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与妥协,制宪代表们将制宪的实质合法性贯注于新的国家政体的设计上,倾注于宪法条文的讨论上,最终形成了一部大多数制宪代表都能够接受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的批准过程则可以看作是制宪的形式合法性达成的过程。制宪代表们也深深地认识到,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只有经过人民的批准才能成为真正的宪法,“参加的成员,都是取得人民信任的人物,很多人是在考验人们的意志和情感的时刻以爱国精神、品德和智慧而出名……他们除了对国家的热爱,没有受到任何权力的威胁或任何感情的影响,最后把他们共同努力和全体一致同意而产生的方案提供给人民,并向人民推荐。”但“这个方案只是推荐,不是强加于人。”〔29〕
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并不是交由既有的十三个州的议会表决的,而是由每个州分别重新选举产生的宪法批准会议进行表决。这是在制宪会议中制宪代表们有意设计的结果,他们要把联邦政府的权威直接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不是在各州政府的权力基础之上,因此在宪法草案的批准过程中人民的直接出场就成为宪法获得足够权威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不是像在之后的欧洲大陆的制宪过程中,制宪会议就直接代表了人民,其通过的宪法草案就成了正式的宪法。宪法草案获得形式合法性的过程,即人民制宪权出场的过程,将制宪的实质合法性阶段各制宪权威经过协商与妥协达成的宪法草案批准成为正式的宪法,赋予宪法以正式的效力。
四、民主制宪与共和制宪
提出制宪过程中制宪的实质合法性与制宪的形式合法性的理论,其基础在于笔者认同阿伦特的分析起点,即革命之后并不是将一切权威都扫除了,人们回到了人与人没有任何联结的自然状态,需要人民以整体的状态重新出场,通过制宪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这种革命扫除一切既有权威的理论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在理论上也存在着悖论。
从历史上说,人类的革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美式的政治革命,另一类法国式的社会革命。就英美式的政治革命来说,其革命只停留在政治层面,其制定宪法的目的仅仅在于建立新的政治权力结构,即解决政体问题。而法国式的社会革命波及面更大一些,其追求的不仅是在政治层面,更主要的是要在社会结构层面完成对政治共同体的重构。但即使是在法国的大革命中,革命之后的法国民众也不是被打入了原子化的个人状态,其依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权威,法国的制宪就是在不同的政治权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斗争中进行的。从理论上说,如果说革命将原有的政治共同体推翻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回前政治状态中的原子化的个人,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权威,人民之间如何联合以完成制宪权出场就成为制宪权理论无法解开的难题。在理论上无法解开的难题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获胜的一方以人民的名义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共同体意志的说辞,这也就是施密特所说的主权者做出政治决断的真实的历史处境。
我们承认革命并没有将政治共同体推入自然状态,革命之后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权威,但是由于革命的性质以及暴烈程度不同,革命之后政治权威的碎裂程度也不同,这也给制宪过程中制宪权威的凝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难题。在英国和美国的革命中,革命之后依然存在着各种建制化的权威,制宪的实质合法性在既有的政治权威之间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即可。我们将这种制宪称之为共和制宪。而在法国大革命,由于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君主一力建设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政府,打破了原有社会架构及政治结构的组织构成方式,“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与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经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30〕当革命推翻了法国的君主制之后,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权威以非建制化的形式涌现出来,加入到角逐权力的游戏中去,并将其他政治权威排除在制宪的过程之外,将制宪看作是将自己阶级,自己的小团体的意志上升为民族共同体意志的过程,就像西耶斯“第三等级就是一切,就是整个国家”〔31〕的口号所宣称的一样。我们将这种制宪称之为民主制宪。
与共和制制宪追求在各种政治团体、政治权威间通过协商达成妥协不同,民主制宪追求制宪主体的同质化,而完成同质化构建的主要手段就是将非同质化的群体排除在制宪进程之外,在极端化的情况中可以将其视为敌人予以驱逐或是消灭,这与通过制宪完成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的宪法价值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制宪过程中,只有通过共和制的原则达成制宪实质合法性的宪法才可能是一部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宪法。否则,即使通过民主制的原则完成了制宪实质合法性的构建,并且也通过人民的批准,完成了形式合法性的达成,也不可能成为一部限权宪法,因为其建立在敌我决断论基础上的政治基础是不牢固的,是缺乏协商与妥协精神的。而基于协商与妥协的共和制宪则是尽可能的容纳不同制宪权威的诉求,其主导精神是宽容,而不是排除,将制宪团体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控制在大家都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将不同团体之间的协商与妥协转化为宪法草案的设计。正是在这一协商与妥协的制宪过程中,原来分裂的政治权威才能熔铸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
注释:
〔1〕〔22〕王锴:《制宪权的理论难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
〔2〕〔3〕〔4〕〔5〕〔6〕〔7〕〔8〕〔9〕〔10〕〔11〕〔12〕〔23〕〔25〕〔26〕〔27〕〔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6、118、77、81、84、85、87、88、89、99、106、78、498、486、129页。
〔13〕〔14〕〔15〕〔16〕〔17〕〔18〕〔19〕〔20〕〔21〕〔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第17、147、147、148、160、167、168、149、149-150页。
〔24〕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15,p.xviii.
〔28〕各州派往制宪会议以及能够代表本邦投票的代表人数各不相同,详见〔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页注释10。
〔29〕〔美〕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第2篇),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页。
〔30〕〔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9页。
〔31〕〔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
赵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