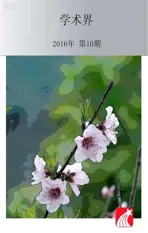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文明政体论”——从孟德斯鸠到休谟的政体论申说
2016-02-26高全喜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上海 200240)
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文明政体论”
——从孟德斯鸠到休谟的政体论申说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上海200240)
通过对孟德斯鸠和休谟“文明政体论”的分析,为当今中国学界有关宪制转型与政治文明的各种论说,提供一个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理论借鉴。孟德斯鸠提出了有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三种政体的性质及其动力原则的观点,区分了文明政体与野蛮政体,在他看来,专制政体就是野蛮的政体,专制等同于绝对专制,因此等同于野蛮。休谟则把孟德斯鸠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通过把法治作为衡量专制程度的客观标准,为政体类型的划分开辟了一个新路径,提出了一个两阶的实质性政体理论:一阶是野蛮政体与文明政体的划分,它以是否存在绝对专制为衡量标准,关键在于法治之有无;在二阶层面的文明政体中,政体的优劣则在于法治之多少,以此来衡量相对专制的程度。休谟的政体论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范畴,法治政府和宪法体制的构建与演进在其政体论中举足轻重。他将现代政府的权威和正当性建立在从强权向文明政体的转型之路上,这种历史规范主义的政治文明观对当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最具启发意义。
政治文明;文明政体;法治;历史规范主义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革时代,由于历史过程的内部累积和与外部世界的冲撞交汇,滋生的社会政治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举其大端,仍然是一个制度转型问题。对此,固然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审视分析,但宪法学的思考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值得注意的是,主流的政治理论在这些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文明”的问题,并试图从文明的高度对于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给予某种合法性的证成,为此,各派学者纷纷就政治之组织结构、权力形态与文明历史给予相关的理论叙事。〔1〕
在笔者看来,“政治文明”之政治维度,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其实就是一种政体结构或一种国家的组织建构。考诸历史,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政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西方的古代社会与中国的古代社会,都必然存在着自己的“政体”或政治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种政治组织形式随着历史的演进,需要经过古今之变,从古典文明进入现代文明。因此,探索当今中国的“政治文明”,显然不能固守传统的政体与文明,必须面对现代的政体与文明,与时俱进,这是人类历史政治文明演进的基本态势。就西方政治历史的理论思考来看,15世纪以来,它们的思想家们也都在构造现代国家的理论原理,就中国政治历史的理论思考来看,自鸦片战争以降,我们也面临古今中西问题,有晚清立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的演变。在今天,当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制度变革之后,如何基于现行的中国宪法(八二宪法以及四个修正案),从政治文明的高度探讨新常态下的制度演进问题,无疑是十分迫切的和十分必要的。
本文试图从一个二百年前的思想史个案——从孟德斯鸠到大卫·休谟的“文明政体论”,着力检点一下休谟是如何面对18世纪英国的社会政治变革而从文明的视角予以回应的。特别是休谟将现代立宪政府的正当性权威,建立在从强权向文明政体的历史性转型之上,这可以为当今中国学术界关于政治文明的各种论说,提供一个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理论借鉴。
一、孟德斯鸠的文明政体论视角及其局限
我们知道,与古代的城邦政治相比,近代民族国家是伴随着神权政治的解体而出现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新兴城市共和国的产生,商业与贸易的发展,公民权利的兴起以及人性的世俗开放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迫切要求对于一个市民社会或民族国家治理有新的制度安排。17、18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思想处于一个所谓的启蒙时期,思想家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但有启蒙的眼界,还有历史的眼界,冲破神学束缚,开启民智,审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史,为本国的社会变革输入新的资源,这是当时思想家们的共识。这一历史潮流在法国,体现为对各个民族的风俗、礼仪、文化与制度的考察,体现为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大批著述的涌现。这一历史潮流在苏格兰,体现为考察一个社会或民族内部在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的动力因素和法律制度的机制作用,体现为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说苏格兰历史学派。
在孟德斯鸠和休谟之前,维科的《新科学》曾经考察过历史政制的演变,但其中神学的色彩浓厚,他有关从神权向民政制度演变的考察虽然重视历史,但忽视了经济与法律的重要作用。而传统的自然法理论,如格老修斯、普芬道夫等人的国际法学说,虽然考察了法律对于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与交往的作用与影响,但那是一种国际的公法原则,显然不同于一个经济和法律共同塑造一种文明社会的机制。至于当时的各种社会契约理论,它们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形成机制,只描述了一层单向度的历史演变,即从自然状态向国家状态演变的历史的理性逻辑,它们与其说是历史的演进逻辑不如说是理性的演绎逻辑。
我们知道,政体学说到底是处理两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即由谁统治与如何统治,传统的古典政治学中区分政体类型的一个主要标准是有关统治者的人数问题,亚里士多德就是以统治者是一个人、几个人或多数人为标准而把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平民政体)等三种基本的类型。这种传统的分类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被忽视了,那就是如何统治即是否依据法律进行统治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上述政体划分中并没有突出地显示其应有的重要地位。例如,同样是一个人统治,但根据是否实行法治,在何等程度上实行法治,便使得它们的性质具有了根本性的差别。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如东方的君主制乃至僭主政体就属于野蛮的政体,而有限的君主专制,如法国的君主制则属于文明的政体。我们看到,正是看到古代传统的政体理论由于依据统治者人数作为划分标准所带来的问题,孟德斯鸠才对法治问题十分强调,他的三种类型的政体分类便不是单纯依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来区分的,而是兼顾考虑统治是否依据法治并实现自由来区分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有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三种政体的性质及其动力原则的观点,其特色是区分了文明政体与野蛮政体。孟德斯鸠的君主政体指的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政体一起属于文明政体,而专制政体是野蛮政体。文明政体与野蛮政体的区分,在孟德斯鸠这里体现为根本的质的差别。从思想史渊源来看,这未始不是西方政体论从一开始就有的正宗与变态的区分的体现。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就有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分类,他按照正义的标准,依次划分了如下六种从好到坏的政体序列: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宗的意味着符合正义的,变态的是不符合正义的,前者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与共和政体,后者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
亚里士多德的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划分,主要关注的是道德正义问题而虚化了政体的专制与自由与否的关键问题。自由政体问题不是古代的古典政治学考虑的核心问题,它是近代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首要的政治学问题。孟德斯鸠三种政体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这个根本性问题突显出来,他通过对于专制政体本质的揭示而把自由问题放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加以统治,其唯一的动力原则是恐惧,专制统治者用恐惧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窒息一切野心。〔2〕相比之下,君主政体的动力原则是荣誉,而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各种各样的美德——共和政体有很多类型,每个不同类型的共和政体追求不同的美德。孟德斯鸠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英格兰的政体,而英格兰政体是一种混合政体,这一混合政体的动力原则是自由。
但是,应该看到,孟德斯鸠把专制问题简单化了。在他那里专制就是专制,就是以恐惧为唯一原则的个人专横意志的统治,而专制程度的区分是次要的,意义不大,因此他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按照他的推论,专制政体就是野蛮的政体,专制等同于绝对专制,因此等同于野蛮。这样一来虽然是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但却并不符合历史的现实状况,因为欧洲近代以来的很多君主政体都或多或少具有着专制的色彩,即便是法国的专制君主制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种野蛮政体,固然像路易十四的那种“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是一种个人的独断专行,但并不能否认即便是在这种政体之下,法国社会依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是当时欧洲文明的中心。
二、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文明观:经济与法治的历史演变
英国17、18世纪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的本性。“英国思想家们尽管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文明社会的演进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于文明历史的考察,如对于政府、财产的起源、对于知识、文字的起源,甚至对于审美、情感的起源等文明多个领域的历史考察,试图找出文明演变的内在机制。英格兰思想家洛克已经表现出了对于历史的特殊兴趣,他通过追溯财产权的起源从而建立起一种私人财产权的理论。”〔3〕苏格兰启蒙学派对于人类历史形态的演变的考察不像法国思想家们那样偏重于风俗与文化,而是偏重于经济动力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塑造文明社会的作用。例如,斯密在《论法律》的演讲中就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演变过程中的法律制度,考察了不同社会形态之下的政府体制与法律规则。
休谟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政体的看法渗透着启蒙时代的文明精神。但毕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精神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不同,休谟有关文明与野蛮政体的观点,对于政府的起源与本性的看法,尽管与法国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仍然呈现出了其理论的独创性。休谟并不像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人们可以事先通过理性的计算而主动地建立起一种政治契约,由此组成一个国家或政府,在他看来,政府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一步步地演化出来。“休谟的政府理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的进化论,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秩序论,在其中通过人为的正义德性的制度转换和历史演变,而逐渐建立起一个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政体模式。”〔4〕
休谟在当时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而闻名的,他的煌煌六卷的《英国史》是历史学的经典著作,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休谟的政治理论是有一个历史维度的,在史观上他并不赞同法国乃至英格兰前辈思想家的理性色彩较浓的历史观,他的历史理论是经验主义的,是建立在他的政治哲学和政体论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他的历史观服务于他有关人类政治事物的理论。“应该看到,休谟的英国史首先与有关文明研究的十分广阔的主题相关,与商业的繁荣、政府形式的转变,以及它们与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休谟的关切点在于欧洲业已存在的现行体制的起源与本性,相比之下,经济领域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系统的一个部分。”〔5〕休谟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诸多政体类型,指出这些文明程度不同的政体的共同基础在于人性与法治。
通过对于人类历史状态的考察,休谟隐含地认为人类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四种基本的社会形态,米勒分析道:“休谟从没有试图创造出一个系统的社会形态理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有关四种社会类型的粗略的描述。”〔6〕第一种是野蛮的极少文明的社会,在那里还没有出现主权之类的事物,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如此。第二种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虽然存在少许的贸易,但工业并不发达。政制形态有多种形式,公民平等,共和精神和民主意识都很强烈。第三种是封建社会,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封建等级普遍存在,但国家有统一的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产技艺落后,生活简陋,无高雅兴趣。第四种社会是近代以来的商业社会,有关这个社会的经济、政制与文明的内容是休谟论述的中心,他的一系列著作都是围绕着这个近代社会展开的。总的来说,休谟实际上已为我们大致勾勒了一个从原始渔猎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封建农业社会到近代以来的商业社会的文明演变史。
“这个演变史尽管受到了格老修斯等自然法学派的影响,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如此明确地描绘出这条线索,休谟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对于斯密、弗格森的社会历史理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同构成了18世纪苏格兰历史学派的一个主要理论内容。”〔7〕斯密有关人类历史演变的观点采取的便是休谟的基本观点,他遵循着休谟有关社会发展阶段的路径,着重考察了不同社会形态的法律制度的演变,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从游牧民族到当时欧洲社会的各种政治体制的法律演变的进程——“1.野蛮民族政府的由来;2.游牧民族政府的由来;3.小部落酋长政府;贵族政治发生的方式;侵略性小共和国和防御性小共和国的崩溃,以及专制政治瓦解以后欧洲所发生的各种政体。”〔8〕
休谟不赞同他那个时代各种社会契约论有关假想的原初自然状态的存在,但他并不否认人类文明前的游牧、渔猎社会的存在,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从上述社会到文明社会转变的机制。从前文明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转变机制只能是商业社会的逐步发展与法治的逐渐进步。休谟强调经济动力与法律制度对于文明社会的机制性推动作用,在18世纪的欧洲思想领域是相当深刻的。休谟认为,“人类的理性,在通过实践,以及通过至少在像商业和制造业这类较为庸俗的行业方面的应用,而获得提高和进步以前,要想改进法律、秩序、治安和纪律,并使之臻于完善,是绝对不可能的。”〔9〕
关于文明,休谟认为文明首先是一种制度,这一观点与他的政体论是密切相关的,是构成他的野蛮与文明之别的关键之所在。关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固然体现在生活状态、生产技艺、思想意识、知识文化等多个方面。对此当时的博物学家、旅游学家以及传教士都曾有过大量的描述,他们为当时的欧洲人提供了一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方社会、非洲大陆和美洲印第安民族蒙昧生活状态的景观描述。“对于那些描述虽然休谟并不持疑义,也认为它们是一些基本的内容,但他并没有重复他们的观点,而是注重更为重要的方面,即文明与野蛮在制度方面的根本区别。”〔10〕佛波斯指出:“对于休谟来说,‘文明’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或法律的概念:‘文明’的进步是‘法律与自由’的发展,是‘有益的法律约束与正义’的发展(没有法律自由仅仅意味着无所顾忌),也是在休谟的政治哲学中作为政府职责的‘正义’在历史中的实现。”〔11〕
在休谟那里,制度表现为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野蛮社会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与商业行为,也没有以追求财富为主要动力的经贸往来,在那里只是简单地依靠天然的自然环境而一次性地满足基本生存的欲望。而在文明社会中,人们是可以克服自然环境的匮乏,并通过劳动特别是分工来进行经济交换和商品往来的,并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了知识,积累了财富,创造了文明,从而建立起一个文明的社会。“就政治方面来说,野蛮社会的制度受丛林原则支配,人们之间不是相互为敌,就是受制于一个野蛮君主的专横统治,而在文明社会人们却可以通过正义的规则而建立起一个政府,并在权威政府的法律统治之下产生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维护与保障的政治社会。特别是近代的立宪制度,则在更高的制度层面上塑造了一个自由、富足与繁荣的文明社会。”〔12〕总之,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制度的不同,或者说文明社会正是有了制度的保障才使人从蒙昧状态走出来,享受经济繁荣与政治昌明的果实。佛波斯指出:“休谟提出了一个新型的自由史:自由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即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成果的历史。”〔13〕
正是在制度文明的基础之上,人类文明的其他要素,如文学艺术、科学技艺、审美感受乃至奢侈品的享受等等才成为可能。休谟在一系列论文中分别考察了文明社会的各种良好品态,谈审美,谈趣味,谈雄辩,谈写作的简洁与修饰,谈鉴赏力的细致与情感的微妙,谈艺术与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谈技艺的日新月异,谈人性的高贵,这些都是他所写文章的著名的篇名。列维斯顿指出:“休谟把一整套历史地演进中的发明,诸如语言、法律、艺术、宗教等,称之为道德世界。当人们对于道德世界的演进过程达到有所意识,并进而采取一些手段予以控制时,他们就进入了文明化的程度,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遵循一定的原则行动的事情;……对于休谟来说,真正的哲学家与真正文明化的人是一致的,在此我准备进一步探讨休谟的文明概念,并揭示传统与自由这两个概念是如何与它本质相关的。”〔14〕
三、休谟的二阶政体论
休谟虽然没有建立斯密那样的法学系统理论,但他的一系列政治与经济论文,同样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政体形态与法律制度的变迁。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和《论政府的首要原则》《论政府的起源》等文章集中处理了政府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政府论与霍布斯、卢梭等理论家不同,他并不关注所谓国家或政府的主权问题,休谟认为那是一些抽象的唯实论在政治理论上的空洞议论,此外,他也反对各种契约论的政府理论,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些有关政府问题的理性推论,与真实的政府问题相去甚远。”〔15〕休谟对政府的形成与本性的考察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更关注政府在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演变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制度性的机制功能,这些机制的制度性演化就构成了他“文明政体”的概念。
在休谟的思想体系中,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有关政体的理论首先是一个有关文明与否的政制问题。“尽管休谟考察了一系列不同形态的政体,在他的论文中涉及到专制政体、自由政体、共和政体、混合政体、民主政体、绝对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君主专制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东方专制政体、温和政体、野蛮政体、僭主政体等等,但是在我看来,休谟理论中的这些政体形式并不是平行排列的,如果仔细研究休谟的政体理论,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内在的政治逻辑,即隐含着一个有关人类政治体制的二阶划分。”〔16〕休谟政体论的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政体形态的二阶划分中,用野蛮与文明作为一阶划分的标准,而以文明的程度作为二阶划分的标准,从而对孟德斯鸠的比较简单的文明政体论有了实质性的深化。在对上述大量的政体形式的考察之后,休谟做了二阶的层次划分:首先,野蛮政体与文明政体的划分是一阶逻辑;在一阶的基础上,才有所谓二阶形态的政体区分。
虽然,有关野蛮与文明的一阶划分在休谟的政体理论中是隐含的,不是休谟所要考察、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它的基础性意义,否则就不能准确地理解休谟的政体理论。这一点,要联系到休谟和孟德斯鸠对专制的不同看法才能获得理解。休谟与孟德斯鸠一样对于专制问题格外重视,不过休谟的思想要更为复杂和深刻。在他看来,对于专制应该有程度上的衡量标准,而这也正是休谟的文明政体论超出孟德斯鸠的文明政体论的地方。
休谟认为文明政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但是野蛮政体本质上只有一种,即追求绝对无限暴力的专制政体,在他那里这种野蛮政体主要是指东方社会诸如波斯、土耳其的君主专制政体。但是,“休谟实际上并不关心波斯之类的野蛮政体究竟如何,他也没有就此专门讨论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挖掘其背后的涵义,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野蛮政体在休谟的心目中还有另外几个版本,他是以东方的绝对专制政体为野蛮政体的正版,并以此为参照而评论欧洲社会的政体类型。在这一点上休谟采取的是皮里春秋的笔法,影射当时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些绝对专制的政体,例如僭主政体在他眼中就是如此,克伦威尔的独裁也是如此。”〔17〕休谟的政体思想虽然在政体形态上吸收了孟德斯鸠的分类理论,但他有关政体区分的实质标准却与孟德斯鸠的文明与野蛮简单二分的标准大不相同,他更关注于自由政体的历史性发生和演变,更关注不同程度的文明政体的衡量标准。在休谟的政体论中,这个文明政体的衡量标准就是,各种文明政体中的相对专制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文明政体的衡量就转换为对专制程度的衡量。
正是因为看到了专制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休谟并不像孟德斯鸠那样对于政体采取简单化的一概而论,他感到专制程度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他隐含地把专制的程度作了绝对的与相对的划分,认为只有绝对专制的政体才是野蛮政体,而一些相对专制的政体仍不失为一种文明政体。“我认为,休谟这一基于历史经验与观察的发现,在政体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把有关政体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有关政体的二阶划分便是以此建立起来的。这个有关专制程度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如何划分专制的程度,以什么标准区别什么是绝对的无限的专制,什么是相对的有限的专制。显然,正是在此我们看到了休谟政体理论的独创性及其蕴涵的审慎的政治智慧。”〔18〕
在他看来,区别专制程度的标准不是随意的,也非孟德斯鸠的恐惧原则所能解决,因为恐惧正像专制一样也是一个在量上无法加以衡量的东西,是一种心理感受。作为科学的政治学应该给出一种客观的衡量标准。在此,针对这个问题休谟开辟了一个新的政体论的路径,他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把法治原则纳入到划分野蛮政体与文明政体之专制程度的区分上。“在休谟看来,区别绝对专制与相对专制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存在着法治,而不是在于是否由一个人、多个人或全体人民成为统治者这样一个传统政体论的划分标准;而对相对专制的衡量,则以法治的实现程度为衡量的标准和依据。也就是说,通过法治这一实质性的制度转换,有关专制程度的量的区分而变成在客观上可以衡量。”〔19〕
我们已经指出,孟德斯鸠在有关专制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在何等程度上决定了政体的本质,但他相对有些处理的不足,只是提出了一种专制政体,认为它是不依据法律的独断统治,而没有看到专制有一个程度的问题。“休谟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把孟德斯鸠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通过把法治这一根本性因素作为衡量专制程度的客观标准并放到一个首要位置,因此,对于政体类型的划分就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与传统的古典政体论的一般划分有了很大的不同。”〔20〕虽然他也同时接受了传统政治学按照统治者人数划分政体类型的分类标准,但对他来说,它们只是二阶政体形态层面上的政体分类。休谟所关注的问题在于通过把法治导入政体理论,从而提出了一个两阶的实质性政体理论,即一阶是有关野蛮政体与文明政体的划分,它以是否存在绝对的专制为衡量标准,至于如何衡量专制的程度,则取决于法治这一根本性尺度。在野蛮与文明的一阶层面上,关键在于法治之有无,在文明政体的二阶层面上,政体的优劣则在于法治之多少。这样,关于专制问题,就克服了孟德斯鸠的简单化之不足,我们根据休谟隐含的政体理论,可以分析、考察不同的专制政体,这些专制政体并不都是平行排列的,并不都只是形态的不同,可以有本质性的差别,绝对的专制政体与有限的专制政体是大不相同的,前者属于法治之无,后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法治,绝对的专制政体是一种野蛮政体或准野蛮政体,而相对专制的政体则大多属于文明政体。
这样一来,休谟有关政体类型的二阶理论,就使得政体分类不再是单纯形式上的区分,而且具有着实质性的内容。例如,同样是专制政体,在传统的分类标准之下只是一种类型,而对于休谟来说,就具有如下几个性质不同的形态:一个是绝对的专制政体,如东方的专制君主制,以及欧洲的某些暴政统治,它们属于野蛮政体;另一个是仅有君主专制形式的法治政体,它们以英国的混合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为典型,这种政体属于纯粹文明的政体,它的专制色彩是极其少的,为此休谟称之为自由政体;此外,还有程度不等的有限的专制政体,是一种介于绝对的野蛮专制与英国的自由政体之间的君主政体,如法国的君主制,它们也属于文明政体。
四、立宪政府的权威——从强权向文明政体的历史转型
在笔者看来,休谟的政体论属于一种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范畴,因为他考察与划分政治形态的基本原则是基于法治与自由的有无与多寡,因此宪法体制(不分成文与未成文宪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他强调的三个基本的元规则(财产权的确立、财富转让的同意和个人承诺的履行)为核心内容,它们作为基本规则构成了现代政治之构建与演进的基础,也是政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21〕
在休谟看来,文明政体下的政府权威问题的关键,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转型机制。休谟在多篇论文中多次指出了野蛮政体是一种绝对专制的政体,并把它与东方社会的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这种野蛮政体并不直接等同于游牧、渔猎社会,因为在那里尚没有出现成熟的政制,而是从那个社会演变过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演变并没有像欧洲的政治社会那样走向一种文明化的道路,而是走向一种绝对专制的道路。“东方社会大多就是如此,它们不同于游牧、渔猎社会,已经具备了十分完善的政制,但并不是欧洲那样的文明政制,而是野蛮政制,其野蛮性质并不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等方面,而在于政制方面。尽管东方的野蛮社会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原始社会的贫乏和低下,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制作技艺和物质财富方面有时优于欧洲一些国家,但因为它们的政治制度的绝对暴力和专横性质,因此仍然可以称之为野蛮社会。”〔22〕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主要是走上了一条文明政体的道路,建立起了不同于东方社会的政治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文明社会、向政治文明的现代宪制的转型机制只能是商业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最终到立宪政府的达成。
休谟重视有关政府起源的考察,而正是在这个起源问题上,休谟与契约论的理论家们拉开了距离。契约论总是义正词严地寻找政府的正当起源。“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政府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同意的理性契约之上的,随便考察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政府形态,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几乎没有一个政府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它们无不是通过政治上的强权,通过征服、掠夺而建立起来的。”〔23〕因此,休谟指出,契约论的那种“同意甚至在很长时期内仍然很不完备,不能成为正规的行政管理的基础。……几乎所有现存的政府,或所有在历史上留有一些记录的政府,开始总是通过篡夺或征伐建立起来的,或者二者同时并用,它们并不自称是经过公平的同意或人民的自愿服从。”〔24〕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理论家们从理性的假设出发认为政府应该起源于人民的同意,是经过契约而建立的,但是现实的历史状况却又告诉我们那只是理论家们的一厢情愿,政府在其起源上从来就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25〕如果按照契约论的观点,未经同意的政府应该推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的存在是正当的。
“休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认同理论家们的那套美好的谎言,而是力图在现实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在他看来,一味纠缠于政府起源上的是否合理是无意义的,只会导致人们对于政治的离心离德,甚至无政府主义,其结果只会带来新的暴政。”〔26〕休谟并未像洛克那样用契约论去论证政府的文明起源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威,他宁愿采取另一种方式论证政府的权威;休谟的现实主义道路意味着,没有什么政府在起源上是没有原罪的,但是起源上的肮脏和野蛮并不影响后来走向文明和向善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帝系或共和国政府最初不是建立在篡夺和反叛上的,而且其权利在最初还是极其可疑而不定的。只有时间使他们的权利趋于巩固,时间在人们心灵上逐渐地起了作用,使它顺从任何权威,并使那个权威显得正当和合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习惯、使任何情绪对我们有一种更大的影响,或使我们的想像更为强烈地转向任何对象。”〔27〕休谟认为尽管政府在起源上无法排除强权和野蛮,但是政府毕竟是一件有益于公民的共同利益的事物,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而实际上任何政府一旦产生之后,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就不再基于人民的原初同意与否,政府的权威随着统治时间的持续而自然地形成。
休谟指出,一个政府是否合法与正当,关键看它在统治过程中是否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并且满足人民的共同利益,看它最终能否走向法律规则之治,而不是依据统治者个人的独断意志进行统治和治理。所以,政府的权威及其正当性依据并非来自起源上的神圣或者文明,而是在政府的持久延续,特别是在政府稳固地实施法治并走向立宪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这个法治化和立宪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人民的认可和同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在历史进程中最终能否走向政治文明范畴下的法治和立宪主义。休谟的这种经过历史演化而逐步达成法治政府和立宪政府的道路,是一种历史规范主义的道路。
到此为止,笔者大致梳理了休谟的二阶划分的“文明政体论”的概观:他以法治作为衡量政治文明的量化程度,从而对孟德斯鸠的单纯质的判断的文明政体论形成超越,进而把法治的逐步生成作为文明政体的历史演化线索,最终走向现代的法治政府和立宪政府。当然,休谟的法政思想基于18世纪英国政治社会的语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制度转型问题,显然不能照搬休谟的理论。但是,休谟的很多看法依然具有原理性的价值与意义,诸如政治文明与法治政府的关系、文明政体与野蛮政体的划分,等等。尤其是将现代政府的权威和正当性建立在从强权向文明政体的历史规范主义转型之路上,都非常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个现代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明与国家建设、宪法维护与制度变迁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
注释:
〔1〕相关论述,参见许章润:《政体与文明》,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年;高全喜:《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年;甘阳:《通三统》,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26页。
〔3〕〔4〕〔7〕〔10〕〔12〕〔15〕〔16〕〔17〕〔18〕〔19〕〔20〕〔22〕〔23〕〔25〕〔26〕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244、233、236、237、243、235、239、241、241、242、239、245、245、245页。
〔5〕A.S.Skinn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230.
〔6〕Divid Miller,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in Hume’s Political Thou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22.
〔8〕〔英〕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页。
〔9〕〔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22页。
〔11〕〔13〕Forbes, 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296,298.
〔14〕D.W.Livingston, Philosophical Melancholy and Delirium,Hume’s Pathology of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190.
〔21〕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24〕〔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2页。
〔27〕〔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97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
高全喜,1962年生,江苏省徐州人,《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吉林大学哲学系,1988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教授和北航高研院创始院长。2016 年转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任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中西立宪史、法理学( 法哲学) 与政治哲学。30 年来在国内外出版的学术专著: 《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与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现代政制五论》《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政治宪法学纲要《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 The Road to 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 (Spinger Heidelberg New York Dordrecht London 2015)等十余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的专业论文:《“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论共和政体》《格老秀斯与他的时代:自然法、海洋法权与国际法秩序》《现代政府政体论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变法图强保守的现代性》《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论宪法的权威》《论公民》《论国家利益》《政治宪法学的政治观、On Rule of Law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China;Revolution, Reform & Constitutionalism: The Evolution 0f China’s 1982 Constitution 等数十篇。此外,还主编:《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法政思想文丛》《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六卷集、《大》与《大观》学术丛刊、《北航高研院法政文丛》《北航高研院通识教育文论》等近十种,一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