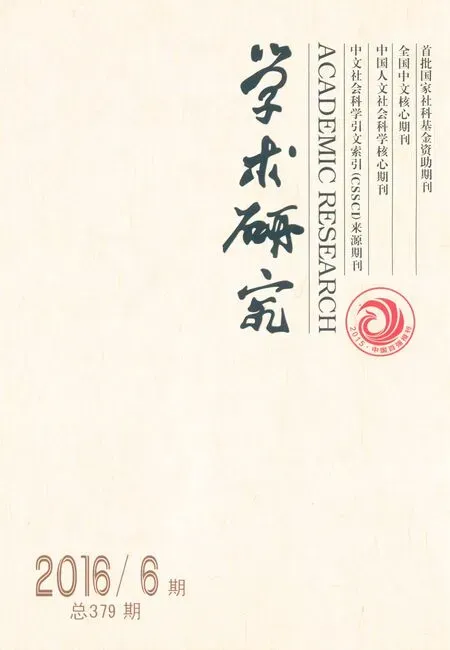章门师友的文体理论研究*
2016-02-26吴承学刘春现
吴承学 刘春现
章门师友的文体理论研究*
吴承学刘春现
[摘要]章门师友的文体理论,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学术转关、西方科学兴盛的学术思潮与学校分科教育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从本土文论中汲取资源,立足于对传统经、史、子、集学术的辨析,在整理旧有文章学、文体学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总体上表现出浓厚的复古色彩。重小学、明训诂、辨体裁是其文体学研究的特色。他们强调经、子在文体溯源中的重要影响,致力于对魏晋六朝文体学经典的研究,在文体阐释、著述方式、文体体系构建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元素,是使《文心雕龙》成为20世纪显学的主要功臣。他们从桐城派的文宗唐宋,转变为激赏秦汉魏晋文章。章门师友以其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在近现代的传统文学与文体学研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晚清民国章门师友魏晋文体体系学术影响
清末民初,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波谲云诡、新变迭出。其中,章太炎(1869—1936)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学术界关于章太炎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文以章门师友为讨论对象,探讨他们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文体学的贡献。所谓章门师友,除了章太炎及其弟子之外,还加上刘师培。刘师培(1884—1919)非章太炎弟子,但彼此交往较多。刘师培稍长黄侃(1886—1935),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①钱玄同(1887—1939)也视刘师培为朋友。②1938年钱玄同在致郑裕孚的信中说:“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见《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章门师友之间虽然存在不少差异,但大致有类似的学术背景和旨趣。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氛围中成长,于经史考证之学浸淫极深,经学与音韵、文字、训诂等小学是其兴趣所在。章太炎、刘师培等受章学诚的影响显而易见。他们的思想源于朴学却又超越了繁琐的考据学风。与桐城派文宗唐宋不同,他们激赏魏晋文章。章门师友非常重视文体之学,他们从传统文论汲取资源,构建新的文章体系。他们强调经、子在文体溯源中的重要影响,致力于对汉魏六朝的文学与文体论经典的整理研究。章门师友在中国文体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一、“文”之内涵
所谓文体,首先是文。章门师友多从文字、训诂入手,阐释“文”之概念。不过,入手路径虽同,而所得似乎大相径庭。章太炎与刘师培的不同阐释,典型地反映出对于“文”的广义与狭义的理解。
侯外庐说,章太炎的文字学“建立由文字孳乳以明历史发展的根据”,“又建立由文字起源以明思维发展的理论”。章太炎融合文字学和东西名学成为一种“以分析名相始”[1]的朴学,其泛文学观正是建立在朴学基础之上的。他在《文学说例》中说:“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2]他从训诂入手,考察文章的本源与差异。《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说:“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彣,也。'‘彰,文彰也。'”[3]章氏在《文学总略》中从训诂、文笔之辨、文辞与学说、集部与文学等角度,辨析“文”的含义与范围。他所说的“文学”是指广义的文字之学,是相对于《文选》以降局限于集部的文学观而言的,而且是基于应用的。“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4]在文字基础上谈文学,“既知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语言)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5]把无句读文纳入文学的范畴,是章氏的创举。
刘师培与章太炎之学术渊源及根柢有一定差异。钱基博曾评论刘师培:“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章学诚者也。阮氏之学,本衍《文选》。章氏蕲向,乃在《史通》。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观会通;此其秪也。”[6]刘师培《文章源始》说:“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7]其论文亦以文字训诂解释文的含义,征引《易大传》、《说文解字》、《释名》等典籍,认为偶词俪语乃得称文。《论文杂记》卷十:“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8]笔与文相对,“盖笔从‘聿'声,古名‘不聿',‘聿'‘述'谊同。故其为体,惟以直质为工,据事直书,弗尚藻彩”。[9]由此他认定“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之训相符。故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10]刘师培虽然与章太炎一样从文字训诂入手,但从阮元之说,重《文选》,主骈文,认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11]萧统《文选序》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文,不取六艺、史传、诸子文章。阮元延续六朝文笔之辨,以韵偶为文,散体为笔,以沉思翰藻为文,单行质言为笔,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纪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12]刘师培亦曰:“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13]强调文、笔之辨:“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14]刘氏说本于昭明、阮元,从集部角度而言,刘师培分析了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书志目录中文集之源流,认为有韵之文实有别于他体,而唐宋之后文集名实淆乱,后人承之而不察,只有阮元之说贴合古义,因此总结说:“昭明此序,别篇章于经、史、子书而外,所以明文学别为一部,乃后世选文家之准的也。”[15]集部正是刘师培文学观的核心范畴。
章太炎与刘师培皆从文字训诂入手,引经据典。二人在“文”的观念上的差异,还引发了讨论。①刘师培曾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论文杂记》、《文说》等文章,提出骈文是文章正宗的说法,而章太炎随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章针对这一说法展开了批评。章太炎以“包举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之”为文,认为其涵义宽泛,凡文理、文字、文辞都可称为文。而刘师培则认为偶词俪语乃得称文,并以骈文为正宗。他认为形式上韵偶,文采灿然,能动人感情的才算作“文学”。他把经史诸子之文列入“文章”,以之和“文”相对应。朱希祖(1879—1944)也有此论:“文章为一切学术之公器,文学则与一切学术互相对待,绝非一物,不可误认。”[16]学说、杂文、历史、公牍、典章、韵文、小说等均称之为“文章”,而文学专指诗赋、词曲、小说、杂文而已。虽然章门师友之间对于“文学”的理解不同,但站在文章学的角度,其实只是广义与狭义之区分。正如黄侃所言,广义上来说,“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而狭义上“则文实有专美”。[17]从这个角度看,章门师友之间关于文的观点看似不同,其实并不矛盾。而他们所推荐的理想文章,则是相同的。相较桐城派古文“上攀秦汉,下法唐宋,中间不取魏晋六朝”[18]的做法,刘师培以骈文为正宗,自然以魏晋文为榜样。章太炎虽然对“文”的理解非常宽泛,但也以魏晋文章为至美。章氏经历了从学唐宋文到学魏晋文的变化,他自言:“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犹是体裁初变。”[19]从文宗唐宋到文宗魏晋,这正是章门师友与桐城派在审美理想上的差别。
二、文体之分类与谱系
文体分类学是文体学的核心内容。章太炎非常重视文体分类体例。早在1897年,他在《文例杂论》中就提出“类例”之说:“古之作述,非闳览博观,无以得其条例。惟杜预之《善文》、挚虞之《文章流别》,今各散亡,秏矣!矩则同异,或时时见于群籍。凌杂取之,故不能成类例,亦庶几捃摭秘逸之道也。”[20]在确定了广义的文章范畴之后,章氏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经书不再是儒家经典的名称,“诸教令符号谓之经”,“兵书为经”,“法律为经”,“教令为经”,“经之名广矣”。[21]经部与史部密切相关,不仅“六经皆史”,且说“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22]诸子内涵尤其广泛,“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争议最大的乃是集部,章氏认为集部内容丛杂,体例不一。经、史、子、集的命名与界限并不十分合理,四部之中的文体也时相混杂:“经部之中,不乏类史之书(如《尚书》、《春秋》则类史),子部之文,岂无名经之作(如《老子》、《庄子》、《离骚》,皆名经之类),此中封域,原不可截然分也。章实斋谓:宋人笔记及近人考订诸书,可入集部,其说甚是。近人书由本人撰者为子,由后人编辑者为集,其说亦不尽然。如《管子》及《晏子春秋》,皆为后人所纂,何以不名为集?盖子、集之名,亦无一定标准。”[23]可见,章氏讨论文学与文体,立足于对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分类的形成与辨析上。章氏首先将文分为无句读文、有句读文两种。又分为十六科:图画、表谱、簿录、算草、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24]科之下又设类,以此建构了独特的文体谱系,如下所示:
无句读文:图画、表谱、簿录、算草
有句读文:
有韵文: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
无韵文:
学说:诸子、疏证、平议
历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国别史、地志、姓氏书、行状、别传、杂事、款识、目录、学案
公牍:诏诰、奏议、文移、批判、告示、诉状、录供、履历、契约
典章:书志、官礼、律例、公法、仪注
杂文:符命、论说、对策、杂记、述序、书札
小说
他在广义的文章范畴之中,重新排列、整合了四部中的文体,重构文体分类体系。经书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诗》者,赋颂科也。如《尚书》,历史科之纪传类、纪事本末类,公牍之诏诰类、奏议类、告示类也。如《周礼》者,典章科之官礼类。如《仪礼》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也。如《礼记》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书志类,学说科之诸子类、疏证类,历史科之纪传类也。《春秋》者,历史科之编年类;《世本》,则表谱科;《国语》,则历史科之国别史类;二《传》,则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论语》、《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25]诸子中,文体类目较多,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之外,“其他散入历史、公牍、典章、小说、疏证等类中”。史部“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人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集部纳入杂文科中,以与学问、历史、典章等区分:“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26]如此,完成了对四部典籍中文体的重新划分归类。
1922年章氏在上海讲国学,其中《文学之派别》以《文选》以来的集部文学为界,将无韵之文分为“集内文”与“集外文”:集内文,指偏于沉思翰藻的文章,包括记事文(传、状、行述、事略、书事、记、碑、墓志、碣、表)、议论文(论、说、辨、奏议、封事、序、跋、书);集外文,包括子、史、经、数典文(官制、仪注、刑法、乐律、书目)、习艺文(算数、工程、农事、医书、地志)。[27]分类显得随意,记事文、议论文、习艺文之分,也不同于此前的说法。1935年以后在苏州讲学时讲稿《文学略说》中,以陆机《文赋》中的十类之分为基础,略述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祭文、传状、序录、游记等文体,且说“姚鼐《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大旨不谬”。[28]这是对传统集部分类的肯定了。
自古以来有两种不同的文体谱系,一种是纯理论建构,一种是集部编选的具体操作。纯理论建构与文章总集编选不同,不必考虑具体操作的可行性,所以其谱系更为自由,甚至巨细无遗。《文心雕龙》与《文选》正反映出二者的差异。章太炎对四部典籍文体重新划分的文体谱系,是一种超出集部的纯理论建构,因此可以包罗万象。如章氏的文体谱系中,学说、历史、典章数科,是集部所不收的学术分类与文体。
对疏证文的关注,显现了章氏朴学家的兴趣所在。经学家以训诂为文,以笺疏为文,认为文莫重于注经,极其重视注疏、笺证之文。章氏曰:“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籍,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并称“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证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29]这极大地抬高了书志、疏证文的位置,与推崇情感美的文学观形成鲜明对比。对此,刘师培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批评说:“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30]认为考据与著作不同科,不能算作文。注、疏实乃经学术语,自清代朴学、考据之风盛行,注疏的运用扩展至经、史、子、集著作,逐渐演变成将文字校勘、资料笺证、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新式研究方法。民国大学教育中一些课程也以注、疏的形式讲授,①如黄侃《诗品讲疏》、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庄子·天下篇〉讲疏》等。前人文体论中亦关注到此类文体,但并未重点论述。②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中“序跋类”下有传、注、笺、疏等体。自章氏之后,注疏文体渐受重视,高步瀛在《文章源流》中将注疏文独立为一类。注疏文虽不合于纯文学的性质,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重要文体,章氏在文体谱系中标出学说科疏证类,正是对清以来训诂考据学风下新的文体发展趋向的总结。此外,对于典章、疏证的强调,亦可以看出章氏非常重视实用文体,甚至指出这两种文体的写作手法可为一切文辞所借鉴。他说:“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与无句读文最为临近。”“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31]总体来说,章氏的文体谱系之构建,实乃在新的学科观念下,对传统文体的又一次重新整合,既有对传统文体体类观念的沿袭,又有所创辟。
刘师培的学术分类思想受外来影响较大。他在《周末学术史序》中运用西方学术体系分类来阐述先秦学术,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学科。他的文体学观念也从西方文学得到启发。对于中国古代文体由韵至散的发展趋势,刘师培从国外文学发展中找到同类的证据,曰:“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32]以时兴的进化论对待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刘氏《论文杂记》第一条即借印度佛书分类阐述对中国文章分类的观念:“印度佛书,区分三类,一曰经,二曰论,三曰律。而中国古代书籍,亦大抵分此三类。一曰文言,藻绘成文,复杂以骈语韵文,以便记诵,如《易经》六十四卦及《书》、《诗》两经是也;是即佛书之经类。一曰语,或为记事之文,或为论难之文,用单行之语,而不杂以骈俪之词,如《春秋》、《论语》及诸子之书是也;是即佛书之论类。一曰例,明法布令,语简事赅,以便民庶之遵行,如《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是即佛书之律类。后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经类也;单行之文,皆论类也;会典、律例诸书,皆律类也。”[33]他借用佛经的分类,认为“经、论、律三类,可以该古今文体之全”。具体而言,刘氏分别“文学”与“文章”为两种。形式上韵偶,文采灿然,能动人感情的才算作“文学”,而单行无文的经史诸子之文,则称之为“文章”。《论文杂记》第七条说论辩、书说、奏议、敕令、传、记、箴、铭诸体源出六艺、诸子,曰:“是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若诗赋诸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别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以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34]既分诗赋与其他文体为两类,那么有韵文中又如何分类呢?《汉书·艺文志》叙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体以作家、作品分为四类,刘氏认为“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其余可分三类:“有写怀之赋(即所谓言深思远,以达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骋辞之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有阐理之赋(即所谓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35]可见,他是从赋的思想内容进行分类的,大致相当于抒情、描写、析理三类。整体来看,《论文杂记》显然是针对他所说的“文学”而言,论述诗、赋、乐府、词、小说、戏曲、谣谚等文体。而对于诗赋之外的“文章”,刘师培则从功用上来说:“文章之用有三:一在辩理,一在论事,一在叙事。文章之体亦有三:一为诗赋以外之韵文,碑铭、箴颂、赞诔是也;一为析理议事之文,论说、辨议是也;一为据事直书之文,记传、行状是也。”[36]《论文杂记》中直接提出了三分法:“近世以来,正名之义久湮。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合记事、析理、抒情三体,咸目为‘古文辞'。”[37]并以此区别南北文学之差异,认为北方文学“不外记事、析理二端”,南方文学“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8]
三、文体史源学与辨体
文体史源学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文本于经”之说,影响深远。如明代黄佐编《六艺流别》即以六经为各体文章之渊源,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于每类文体之中特标明经书为源。此外,先秦诸子、史传文章也被作为后世文章渊薮。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溯文体之源流,也直接将文体之源归于子、史、经书,如曰:“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传状类者,虽源于史氏”[39]云云。相较于“文本于经”的传统观念,章太炎更加重视王官、诸子对于文体发生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许多经书就是王官之书,而诸子与王官之学关系相当密切。他说:“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40]《国故论衡·论式》中说:“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原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大氐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其当官奋笔一也,而风流所自有殊。”[41]将早期的官书文体风格溯源于名家、纵横家。
对于文体之源,刘师培提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认为很多文体出于古代巫祝之官,在“文本于经”的传统说法之外别开生面。他运用训诂,辨析“巫”与“祝”的原始意义,认为“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祀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42]认为早期韵语之文,大多由祭祀之礼产生:“试观《周礼》太祝掌六词以司鬼神,即后世祭文之祖也。殷史辛甲作虞箴以箴王阙,即后世官箴之祖也。又太祝所掌六祠,命居其次,诔殿其终也者,后世哀册之祖也。诔也者后世行状、诔文之祖也。颂列六义之一,‘以成功告于神明',屈平《九歌》其遗制也;铭为勒器之词,以称扬先祖功烈,汉、魏墓铭,其变体也。且古重卜筮,咸有繇词,遂启《易林》、《太玄》之体。古重盟诅,咸有誓诰,遂开《绝秦》、《诅楚》之先。况古代祝宗之官,类能辨姓氏之源,以率遵旧典,由是后世有传志、叙记之文;德刑礼义记于史官,由是后世有典志之文。文章流别,夫岂无征?”[43]巫史祝卜中使用的六祝六祈,是后世祭文、箴、诔文、哀册、行状、墓铭、誓诰、传志叙记、典志等文体之源头。由此进一步延伸,刘师培认为墨家、纵横家乃后世文章之渊薮。《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毛传有“君子九能”之说,刘师培引用后加案语曰:“毛公此说,必周、秦以前古说,即此语观之,足证文章各体出于墨家、纵横家两派矣。”[44]“君子九能”涉及当时占卜、田猎、外交、军事、丧礼、地理、祭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精神在于强调大夫应该具有多方面修养与能力,能在不同场合适应不同的需求。刘氏说:“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工于祷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则工于辞令。”“若阴阳、儒、道、名、法,其学术咸出史官,与墨家同归殊途,虽文体各自成家,然悉奉史官为矩矱。后世文章之士,亦取法各殊,然溯文体之起源,则皆墨家、纵横家之派别也。”[45]虽然刘氏将文体之源归于墨家与纵横家的说法未必准确,但是,他从宗教与制度角度考察文体的发生,确为特见。
刘师培与章太炎一样,其文体溯源之学是以诸子出于王官为理论基础的。张舜徽说:“清儒如章学诚、汪中、龚自珍,近代若章炳麟、刘师培,皆推阐刘《略》班《志》之意而引申说明之。以为古者学在官府,私门无著述文字。自官学既衰,散在四方,而后有诸子之学。”[46]刘师培很重视经学、子学的学术思想与文章的关系。他在《论文杂记》中说:“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于《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47]刘氏将经学作为一种学说看待,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流行之学说,而流行之学说影响于文学者至巨”。经、子之学对文学影响最大,因此“欲撢各家文学之渊源,仍须推本于经。汉人之文,能融化经书以为己用”、“研究各家不独应推本于经,亦应穷源于子……战国之时,诸子争鸣,九流歧出,蔚为极盛。周秦以后,各家互为消长,而文运之升降系焉。”[48]子学流为集部,因此刘师培更注重将文体之渊源上溯至经书、诸子。从文体角度而言,他认为论说之体“实出于儒家”,书说之体“实出于纵横家”、“奏议之体,《汉志》附列于《六经》;敕令之体,《汉志》附列于儒家。又如传记箴铭,亦文章之一体,然据班《志》观之,则传体近于《春秋》,记体近于古礼,箴体近于儒家,铭体附于道家”,由此观之,刘氏曰:“是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49]
中国文体发展至何时而齐备,历来有各种说法。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50]受到这种影响,章太炎提出“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说:“概而论之,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若其细碎,则在六朝。”[51]章太炎认为战国是中国古代文体形成的关键时段。古代文体在战国已基本完备,但六朝之后,又出现“细碎”的文体,也出现一些新体。刘师培则提出“文备东汉”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52]此前,包世臣认为“文体莫备于汉”,[53]胡朴安曾说“文之缘起当溯源于两汉”,[54]又说“文章体裁至西京备矣”。[55]刘师培提出“文备东汉”说,较近于文体史实际。在范晔《后汉书》列传中,有48篇传记著录了传主的著述情况,共著录了诗、赋、碑、诔、颂、铭等44种文体。[56]可以看出,后世的常用文体,到东汉确已大体具备。章太炎“文章大体备于七国”与刘师培“文备东汉”两种说法看起来差异较大,但未必有很大的矛盾。因为两人的角度和内涵并不一样。章太炎所说的文体是指具有后代的文体之用,而不是具体的文体之名。刘师培所说的文体比较具体,大致是后代集部中的文体。
刘师培秉持《文心雕龙》的辨体观念,曰:“文章既立各体之名,即各有其界说,各有其范围,句法可以变化,而文体不能迁讹,倘若逾其界畔,以采他体,犹之于一字本义及引申以外曲为之解,其免于穿凿附会者几稀矣。”又曰:“至于文章之体裁,本有公式,不能变化。如叙记本以叙述事实为主,若加空论即为失体。《水经注》及《洛阳伽蓝记》华彩虽多,而与词赋之体不同。议论之文与叙记相差尤远,盖论说以发明己意为主,或驳时人,或辨古说,与叙记就事直书之体迥异。”[57]认为汉魏六朝文学大多合体,鲜有出辙,批评唐以后文章讹变失体:“杜牧《阿房宫赋》,及苏轼之前、后《赤壁赋》是也。此二篇非骚非赋,非论非记,全乖文体,难资楷模。”唐宋之际,涌现出众多新文体,旧文体亦有新的衍变。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大家往往任笔直书,不拘束于传统文体的格式。刘师培对此表示非议,比如针对诔文的变化说:“唐以后之作诔者,尽弃事实,专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铭,亦但叙自己之友谊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违例之甚,彦和将谓之何也?”[58]如韩愈以传体作墓铭,甚至参杂小说笔法,虽然较具文学性,但不合墓志铭之传统体例。基于对文体早期形态的判断,刘氏认为应主要取法两汉魏晋六朝之文,曰:“大抵析理议礼之文应以魏、晋以迄齐、梁为法……论事之文应以两汉之敷畅为法,而魏晋之局面廓张,亦堪楷式。叙事之文(包括纪传、行状而言)应以《史》、《汉》为宗;范晔、沈约盖其次选。诸史而外,则《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之类固可旁及;即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废。”[59]总体而言,刘氏辨体大致以汉魏六朝文为经典,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则从摹拟对象降为借鉴对象。
四、文体学之学术史
清末民初时期,魏晋南北朝之际的文论经典受到了新的关注,学者们纷纷以朴学的治经方法整理、阐释《诗品》、《文赋》、《文心雕龙》、《文选》等著作。魏晋六朝的文学与文论,成为应对西潮冲击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工具。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表现出对魏晋六朝时期文体理论的强烈兴趣,并取得代表性的成就。
章太炎的文体学受魏晋六朝文学理论影响甚大。其泛文学观显然得力于《文心雕龙》论文序笔的理论构架。朱希祖曰:“章先生之论文学,大抵宗法刘氏。刘氏之论文体,靡所不包,凡有文字著于竹帛者,皆论之矣。”[60]在文体分类上,章太炎认为“士衡《文赋》,区分十类,虽有不足,然语语确切,可作准绳”。[61]就陆机所论的十类文体,略述文体之源流正变,并对同类文体加以辨析。大体来说,对诗、赋、碑、诔、铭、箴颂等体论述较简略,论、奏、说则较详细。他注重补充文体在东汉、六朝的发展演变,指明韩文得力之所在,对后世效法唐宋之作导致的文体讹变正本清源。如曰:“作碑文者,东汉始盛……魏晋不许立碑;北朝碑文,体制近于汉碑;中唐以前之碑,体制亦未变也。独孤及、梁肃始为散文,然犹不直叙也。韩昌黎作《南海神庙碑》,纯依汉碑之体;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则可,作传即不可。桐城诸贤不知此,以昌黎之碑为独创,不知本袭旧例也(昌黎犹知文体,宋以后渐不然)。”[62]十类之外,章氏补充了《文赋》中没有的家传、行状、游记、序录等体。比如:“游记一项,古人视同小说,不以入文苑。东汉初,马第伯作《封禅仪记》,偶然乘兴之笔。后则游记渐孳,士衡时尚无是也。序录一项,古人皆自著书而自为序。刘向为各家之书作序,此乃在官之作;后世为私家著述作序者,古人无是也。”[63]皆有创见。
除了对《文赋》的研究之外,章太炎亦曾讲授《文心雕龙》。①章氏在日本时讲《文心雕龙》,1909年3月11日开讲,至4月8日讲完。听讲者有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沈尹默、张卓身等,见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页。章氏在苏州的国学讲习会亦讲《文心雕龙》,见童岭《章太炎先生〈文心雕龙〉讲录两种》,《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页。据诸祖耿所作《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流别》,开首第一句便说:“向来论文,有《文心雕龙》一类的书,今天,可以不必依照他们去讲。”[64]章氏其实是在刘勰的基础上有所辨正。如:
铭箴第十一:“夫箴诵于官(述己之官守,所以戒其主也),铭题于器”是也,铭、碑、颂三者实同。汉碑多有称颂、称铭者。唯铭、碑必题于器,颂则可不必。
诔碑第十二:“诔与碑实异,如秦世所勒之碑盖称扬己之功德”、“‘叙事如传’为诔之正体。古言诔,今言行状,唯有韵与无韵之分耳”、“‘若夫殷臣诔汤’至‘盖诗人之则也’皆颂体,非诔也”、“碑据彦和所言,正与后世之家传相似,唯碑则兼称扬,有异于家传耳”。
史传第十六:传,即专,即六寸篰,所以记事者也。即《孟子》“于传有之”之传。《史记》列传,传之正体也。若《左传》、《毛诗故训传》皆注疏类,传之变体也。[65]
可知,章氏较重视文体之间的辨析,根据文体的内容、形式、功用、载体等辨析异同,并关注到文体在后世的衍变。对刘勰的文体论加以辨正,如碑体,刘勰曰:“其本则传,其文则铭。”章氏认为碑兼颂扬,与家传不同。又如论体:“论说以明晰事理为贵,故文字不厌其繁。彦和务简之说,非也。”[66]此外,章氏从文字训诂中,溯源文体的本来面目,如刘勰合“赞”、“颂”而论,章氏从文字学角度,认为赞之本义“与相谊,同为助”,但“颂有褒无贬,赞则兼有之”。以之考察汉代赞、颂文,更符合二体的实际情况。
刘师培最推崇汉魏晋六朝的文体学。他说:“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晋代名贤于文章各体研核至精,固非后世所能及也。”[67]刘师培特别标举《文心雕龙》:“《雕龙》一书,溯各体之起源,命立言之有当,体各为篇,聚必以类,诚文学之津筏也。”[68]同时,对刘勰所说也有所辨正。如《文心雕龙·杂文》分七、对问、设论、连珠四体,刘师培将之归纳为三种:“答问,始于宋玉(《答楚王问》),盖纵横家之流亚也”;“七发,始于枚乘,盖《楚词》、《九歌》、《九辩》之流亚也”;“连珠,始于汉、魏,盖荀子演《成相》之流亚也。首用喻言,近于诗人之比兴;继陈往事,类于史传之赞辞,而俪语韵文,不沿奇语,亦俪体中之别成一派者也。”“三者而外,新体实繁。有所谓上梁文者矣(出于《诗·斯干篇》)。有所谓祝寿文者矣(始于华封人之《祝尧》)。”[69]注意文体的起源,兼及文体的体式内容。又论赋体,从功用上分为三类:“写怀之赋”、“骋辞之赋”、“阐理之赋”,分别源出于《诗经》,纵横家,儒、道两家。[70]在随文注解中继承刘勰“选文定篇”的体例,分别列举每类的代表之作。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全面拓展《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全书重心由注疏、训诂,转向文学理论的探讨,融章句训诂、考证订误的文献研究与文学批评、文论阐释于一体。该书大量征引前人之说,或佐证己说,或加以辨正、补充。如《辨骚》篇简述赋的渊源,辨析骚、赋体制之同异。《诠赋》篇则是历代赋论。《乐府》篇以学术考辨的写法论证歌诗合一至歌诗分离的过程,较早提出词乃乐府之流变,准确把握了词的音乐性特征。《书记》篇认为古代凡箸简策者,皆书之类,包括札、尺牍、笺记、列、票、签、弔、谚、掌珠等体。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解释书、记,并从古代典籍中书体之应用,归纳其内涵。《颂赞》篇曰:“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收以简驭繁之功。”[71]文体是随着社会发展和需求而不断新生、衍变的。新的文体产生,或另立新名,或在旧名基础上有所变化。其中不乏同一文体而名称不同,以及使用不同文体却沿用旧名的现象。黄侃主张在文体溯源、辨析的基础上,分辨名实之异同,以简驭繁把握古代文体。陆宗达说:“季刚先生扩大了训诂研究的范围,不但在经学的基础上发展小学,而且在文学的基础上充实小学。”[72]《札记》将文字校勘、笺证、理论阐释结合,在疏证基础上的分体研究与理论总结,充实了《文心雕龙》的文体理论内涵,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一种典范。黄侃亦非常重视《文选》研究,其所著《文选平点》虽属注疏而非理论研究,但他所提倡将《文选》与《文心雕龙》互相参照的研究思路影响较大,曰:“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73]可谓治批评史学术之金针。
黄侃的弟子延续其治学思路,专研《文心雕龙》、《文选》诸书。骆鸿凯(1892—1955)是黄侃弟子,也曾向章太炎与刘师培问学。其《文选学》认定《文选》与《文心雕龙》在文体分类大体上的一致性。《文选学·体式第四》开篇曰:“《文选》分体凡三十八,七代文体,甄录略备,而持校《文心》,篇目虽小有出入,大体实适相符合。”[74]此书体例上,从文史、文体、文述等方面为研读《文选》者导之津梁。其所附录的“分体研究之示范”,从文体定义、性质、学术流变、问题诸方面作考察,是文体学入门之径。以书笺为例,首先释名义与作法,引《文心雕龙·书记篇》之释义;分别作者与时代;辨别文章体性(如壮丽、雄健、繁缛、优柔等风格,又分阴柔阳刚);统观众篇之粹美;析观各篇作法(笔法、章法、修辞、造句);《文选》书笺类诸篇比观;《文选》书笺类所遗之篇(与《文心雕龙》相比)。[75]骆鸿凯的这种研究方法为古代文体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范文澜(1893—1969)曾师从刘师培、黄侃,其《文心雕龙注》就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基础上,体例更为系统化,注疏更为细致详实,并加以理论阐释。如《原道》篇注中将《文心雕龙》所述文体归纳为文类、笔类与文笔杂类三种,对刘勰所论各文体的详细疏证,以及列出篇目的体例,为《文心雕龙》文体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章门师友的文体学史研究,比较集中在魏晋六朝,而其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是《文心雕龙》研究。①章门《文心雕龙》研究的影响甚至远及海外,如黄侃弟子李曰刚在台湾讲授《文心雕龙》,著有《文心雕龙斠诠》等。
五、章门师友文体学的意义与命运
章门师友的文体学研究,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学术转关,西方科学兴盛的学术思潮与学校分科教育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整理国故的运动中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新的探索。早在1919年,刘师培、黄侃就协助学生在北大成立国故社,并创办《国故》月刊,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76]的宗旨。《北大整理国学计划书》(1920年)明确说:“吾国固有之学术,率有混沌紊乱之景象……自乾嘉诸老出,而后古之学术略有条理系统之可得……当时谓之朴学。其整理之法,颇有近于近世科学之方法……今日科学昌明之际,使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则吾国固有之学术,必能阐扬而有所发明。”②《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国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9日。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0-171页。章太炎及其弟子如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等都投入了这场学术运动。毛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中明确说:“近时出版的讲国故学的书籍,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检论》和《国故论衡》……朱逷先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皆是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的结果。”[77]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研究国故,实际是将清代朴学方法,与近世输入的西学中的科学方法结合,分门别类整理中国旧学,以为当时及其后的学校分科教育奠定基础。③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章氏所著《国故论衡》正是整理国故的代表性成果。黄侃也曾讲过“科学”和“证据”,曰:“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78]其所著《文心雕龙札记》正是这种方法的精妙呈现。
章太炎是传统泛文学观的坚守者,对偏执于主情的美文学观嗤之以鼻。在西方文学观念传入而迅速流行并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章太炎的文体思想往往被认为是复古和保守而被否定。这需要略加辨证。当时的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是以被动的姿态接受西方文化的,章太炎的目的是为了“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他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并顽强地从本土文化自身事实,去寻找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所不同的独特性。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章太炎之意在突破中国古代文章学文体体系,自创为文体形态谱系,成为中国文体学包涵最广的一种独特体系。透过复古的外表,这种体系是有其合理性与深度内涵的。首先,章太炎的文体学研究从文字训诂入手,这是合乎学理的。中国文体是建立在中国文字基础之上,以文字为存在方式。中国文体乃至中国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字的特殊性密切相关。研究文体与文体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有必要从文字溯源开始。其次,章太炎把“无句读文”列入文体谱系之中,似乎使“文”的内涵显得漫无边际。但他的“文”不是一般的文章与文学,其目的并不是建立文章或文学的文体体系,而是建立以文字为存在方式的中国著述文体形态体系。其中如“图书”指的是河图洛书、图谶、图画等。这类“图书”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特殊部分,确可以拓展文学研究。把图像纳入“文”之研究中,是21世纪的学术新潮,而章太炎所提出的谱系,早就把图像包括在研究对象之中了。又如表谱、谱录,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孔颖达《诗谱序》疏:“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郑玄《诗谱序》:“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79]谱牒之学与古代文学批评方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如《文章缘起》之类的大量书籍其实就是谱录类。谱录类诗文评形式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减省掉文字的论证过程,只展示最简要、形象、直观、明确的结论。它的内在精神是重视渊源流变、嫡庶远近、正宗旁门,有中国宗族文化的影子。总之,章太炎所建构的以文字为存在方式的中国著述文体形态体系是超越一般文章学体系的,应该放到文化学层次去深入理解和体会,不宜轻易以复古或保守视之并加以否定。
相较章太炎,刘师培更多地吸收西方学术。但他的立足点与学术理想与章太炎一样,也是为了“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与章太炎广义的“文”相对,刘师培认为偶词俪语乃得称文,并以骈文为正宗。刘氏严格区分文、笔,这种复古观念恰与当时受东西方主情与美的纯文学思想暗合,表现出复古而又趋新的有趣现象。在新式的文学史教学中,刘氏选择回归中古早期的文章学研究范式中去,其所著《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明确道出这一思路:“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宜仿挚氏之例,编撰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80]他所著《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文杂记》、《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章原始》等论著中对汉魏六朝文体,乃至后世剧曲、小说都有论及。作家与文体是刘师培文章学研究的关键,在文各有体的基础上,阐述文体之起源、文体与时代、文体与作家、文体写作等各个层面,是在传统文体论基础上的一次升华。
在文学的观念上,章太炎顽强地坚持本土的文化资源与立场,采取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泛文学观念。刘师培为了缓解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文学”与欧美等外来“文学”观念之偏差,提出用“文章”一词作为传统文学的概念,以示区分。此后,在西方纯文学思潮的冲击之下,中国本土学者也纷纷趋附,以有情感的韵文为文学,而小说、戏曲、诗歌等成为中国文学的代表性文体。章门弟子也概莫能外。以朱希祖为例,在其早期所著《中国文学史要略》中,“文学”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经史、辞赋、古今体诗等。朱氏早期讲义中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来源于章太炎、黄侃等人。《朱希祖年谱》引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先生)授中国文学史,撰《总论》二十首,每一首成,必以呈章先生,盖不经章先生点定,则不即付油印。”[81]又据朱祖延记载:“季刚与朱希祖同门友善。希祖勤于记诵,然拙于为文。尝撰《中国文学史要略》未就,季刚为厘定而足成之。书出,洛阳纸贵,朱氏之名噪甚,殊不知季刚实捉刀者也。”[82]可见朱希祖早期的文学思想之渊源所在。1920年重印文学史时,朱希祖转而提倡纯文学。他深入研究英国学者培根、日本学者太田善男的文学理论,试图以外来的眼光重新审视本土文学和文体:“日本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亦以诗为主情之文,以历史哲学为主知之文,惟称主情文为纯文学,主知文为杂文学,其弊与吾国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相同,兹所不取……今世之所谓文学,即Bacon所谓文学,太田善男所谓纯文学,吾国所谓诗赋、词曲、小说、杂文而已。”[83]朱希祖此说在当时较具代表性。相较于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对传统文学、文体思想的坚守,朱希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转而提倡作为美术的纯文学观,①1908年周氏兄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论文章、美术、纯文学的概念与范畴。如鲁迅《摩罗诗力说》(第2-3期)、《文化偏至论》(第7期),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第4-5期)等。转向诗歌、小说、杂文等纯文学文体的创作与研究。②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诸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转变思想,积极趋新,参见周作人《我的复古经验》、朱希祖《非“折中”的文学》、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大趋势。
在文章定义上,周作人认为西人文论中“非以文章为一切学问通名,即为专主娱乐之事”,只有美国宏德(Hunt)《文章论》得其折衷,曰:“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他认为:“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故如历史一物,不称文章。传记(亦有入文者。此第指纪叠事实者言)编年亦然。他如一切教本,以及表解、统计、方术图谱之属亦不言文,以过于专业,偏而不漙也。又如泛言科学范围,其中本亦容文章,第及科学实地,又便非是。”[84]从这种艺术性的文学观来看,传统文论以文章为经世之业,倡征圣宗经之说自然显得陈旧落伍,他指出刘勰《文心雕龙》“正吾国论文之最盛者。特终沉溺前说,发端原道,次以征圣宗经,终以大易之数”。[85]鲁迅的观点与之相仿,《摩罗诗力说》曰:“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86]在西方纯文学思想影响之下,美术成为文学艺术的重要标志,诗赋、词曲、小说、杂文等文体成为此后文体创作与研究的主流,而早期产生于社会礼仪制度下的文体与后世生活中衍生的实用文体,逐渐淡出此时期多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放到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来看,章门师友的选择去取正是在立足本土文化与接受西学的矛盾与潮流中一个典型个案。在西学冲击下,新的知识、技术、学术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新潮流。面对传统辞章教育的衰落,部分学人转而提倡本土文化,以之为抗衡西学的一种资源。陶曾佑《中国文学之概观》(1900年)分论战国以讫明清的文学样式,提倡中国传统文学,以对抗西学。他告诫同胞说:“慎毋数典忘祖,徒迎皙种之唾余,舍己芸人,尽捐弃神州之特质……凡吾同胞,其有哀文学之流亡,斯文之隳堕者乎,请速竞争文界,排击文魔,拔剑啸天而起舞。”[87]文体学是传统文学的一大枢纽,在提倡国学、国故或国粹思潮中,对传统文体理论的阐释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如1906年《国粹学报》载王闿运《湘绮楼论诗文体法》对陆机《文赋》八体加以阐释。王葆心《古文辞通义》(1906年)认为文章本质乃附体制以达诸群用,“其三门十五类,本曾氏《序目》而少增变之,间采姚氏之说以归完备”。[88]吴曾祺《涵芬楼文谈》(1910年)基本沿袭姚鼐的文类划分,并且效仿黎庶昌、王先谦等细分文体子目的做法,共分二百余子目。仿照《文心雕龙》的阐释方式,从释名、选文、原始、敷理几个方面论述文体。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4年),凡例仿之《文心雕龙》,门类结合曾氏《经史百家杂钞》,阐述姚鼐十三类的分法。从纯粹的文体理论阐述与选本中的文体分类实践两个层面来看,《文心雕龙》的文体理论与姚、曾的选本成为当时主要的资源与方法。章门师友则主要集中于对六朝文论的阐发,尤其着力于《文心雕龙》。
随着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的文体理论不免也受到影响。蒋祖怡《文体综合的研究》谈到近代文体之分类说:“自欧洲的学说,传入我国以后,我国的文章分类方面,也很受它底影响。骈散文的分类法既不合时宜,而以用途来分之,项目名词,亦颇有可议之处。于是文体分类之方法,一换以前的面目。”[89]较早的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乃仿日本人的《中国文学史》撰成,文体上分治事文、纪事文、论事文三类。1905年汤振常编《修词学教科书》,取之于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较早将文体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四种。清末龙伯纯的《文字发凡》(1905)取法于日本,③龙伯纯论文体基本源于日本人所著《文法独案内》的“体制”和“文体要解”等节。参见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于“体制”一节中将文体分为叙事体、议论体、辞令体和诗赋体四大类。又基于思想之性质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四类。蒋祖怡批评说:“欲博而失之繁碎,欲面面俱到而失之不伦,前面依近代之说分类,后来又以旧说来分类。”[90]其实是混合旧说而加以改变,是新旧两说的过渡产物。来裕恂《汉文典》(1906年)则有感于日本人所作中国文典浅近且不合于中国文法实际,欲合泰东西各国文典之体,“以此保存国粹”。提出“文当本经”,“文当本史”,“文当本子”,“文当本集”。论“文体”分叙记篇、议论篇、辞令篇。篇、类、体下均有题解,简要叙述文类、文体含义,文体源始,体裁衍变,创作要领等。此书仍以古文为中心,文体溯源的主线基本是在《文章流别》、《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论著的基础上稍加调整的,其体系则基本承袭《文心雕龙》。
外来的四分法与本土的文体分类法结合,是这一时期文体分类学的一种尝试。早在叶燮《原诗》中已提出天地万物发为文章,“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91]王葆心则进一步发挥此说,用述情、记事、说理三者统筹文体。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将文章分为说理、述情、叙事等三类十六种文体。可见,刘师培《论文杂记》所说记事、析理、抒情三分法,在当时颇有代表性。章太炎晚年亦用记事文、议论文、数典文、习艺文的名称,表现出对于外来文学分类法的吸收。总体而言,“文章”与“文学”逐渐成为杂文学与纯文学的代名词。周作人说:“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书记论状诸属,自别为一类,皆杂文章耳。”[92]将纯文学与杂文学明确区别开来。章太炎以文字为基础的文章体系虽然不合时宜,但其不分骈散,诗、文、词曲、小说兼收的文体观影响较大。刘云孙《文体之分类》在文章界说上,折衷于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论与《文选》狭义文学观:“既不能并图表、谱谍、科条、簿录、兼容并包;亦不能拘泥于均文偶语”,“言文章者,当综四部骈散,兼收并蓄”。[93]从功用上分纪事(包括典章、历史、杂记)、抒情(词章、公牍、书札)、言理(学说、疏证、评议)三类。将章太炎的科类谱系转换成事、理、情的三分范畴。
总体来说,在清末民初,西学大举进入中国之际,从坚守本土文化资源与文化立场到逐渐接受西学,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和趋势。其中,章门师友的文体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个案。
[参考文献]
[1]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第813-819页。
[2]章太炎:《文学说例》,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03页。
[3][4][21][22][41]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48、269、276-277、313、405-410页。
[5][24][25][26][29][31]章太炎:《文学论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21、21-22、22-23、24-35、25-27页。
[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
[7][11][13][32]刘师培:《文章原始》,《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45、1646、1646、1646页。
[8][10][33][34][35][37][44][47][49][69][70]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第715、715、711、713、713、722、719、713、713、713、714页。
[9][14][15][52][67]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申叔遗书》,第2366、2365、2406、2372、2372-2392页。
[12]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9页。
[16][60][83]朱希祖:《文学论》,朱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48、50页。
[17][7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8、62页。
[18][51][61][62][63]章太炎:《文学略说》,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记录:《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7、291、298、299、298页。
[19]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20]章太炎:《文例杂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23]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1-142页。
[27][28][40]章太炎:《章太炎讲国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05、353、212页。
[30]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刘申叔遗书》,第1646页。
[36][48][57][58][59]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1517、1534-1535、1541、1541、1517页。
[38]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刘申叔遗书》,第560页。
[39]姚鼐选纂,宋晶如、章荣注释:《古文辞类纂》,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14页。
[42]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刘申叔遗书》,第1283页。
[43][45]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刘申叔遗书》,第526、526页。
[46]周国林编:《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00-101页。
[50]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21页。
[53]包世臣:《复李迈堂祖陶书》,《艺舟双楫》,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54页。
[54]胡朴安:《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15页。
[55]胡朴安:《读汉文纪》,《历代文话》第9册,第9077页。
[56]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64]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43页。
[65][66]童岭:《章太炎〈文心雕龙〉讲录两种》,《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2-133、134页。
[68]刘师培:《文说序》,《刘申叔遗书》,第700页。
[72]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15页。
[73]黄侃:《文选平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74][75]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4、487-512页。
[76]《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号。
[77]《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
[78]黄侃著,黄焯编:《蕲春黄氏文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7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诗谱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页。
[80]刘师培:《左盦外集·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刘申叔遗书》,第1655页。
[8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5599页。
[82]朱祖延:《朱祖延集》,武汉:崇文书局,2011年,第592页。
[84][85][92]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1908年),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3集第13卷,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第774-775、783、327页。
[86]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87]陶曾佑:《著作林》,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45页。
[88]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历代文话》第8册,第7705页。
[89][90]蒋祖怡:《文体综合的研究》,上海:世界书局,第41、42页。
[91]叶燮:《原诗·内篇》,王夫之等:《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79页。
[93]刘云孙:《文体之分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法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6-0145-1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春现,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