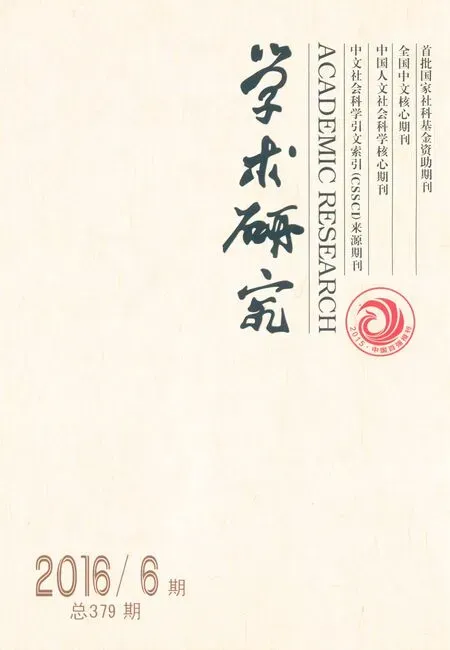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离合”
2016-02-26夏蓉
夏蓉
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离合”
夏蓉
[摘要]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滞留香港不归,治病虽然为事实,但更主要的是因宋美龄器重妇指会的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是宋美龄主持的全国妇女团体总机构,吸收了各党各派各方面的妇女人才,工作成效卓著。然而,由于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等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在其中工作,甚至占了主导地位,引起何应钦、陈立夫、张继等国民党高层的不满,妇指会的工作受到压制,宋美龄与蒋介石也发生了冲突,最后妇指会被迫改组,1940年10月宋美龄借治病之由赴香港且迟迟不归。蒋宋的嫌隙和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是国民党内部对中共态度分歧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宋美龄蒋介石妇指会蒋宋关系国共关系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全面抗战时期宋美龄共赴香港四次。第一次,1938 年1月13日出发,①“Mme. Chiang in Hong Kong”,New York Times,January 14,1938,p.2.关于宋美龄第一次赴香港的时间,《蒋介石日记》没有记录,不过《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有相关报道。2月19日,“妻由香港回武昌”;[1]第二次,1939年3月17日,“送妻登飞机赴香港”,[2]4月17日,“妻已安抵重庆”;[3]第三次,1940年2月12日,“送妻到珊瑚坝飞机场飞港休养也”,[4]3月31日,“妻与孙夫人来渝”;[5]第四次,1940年10月6日,“妻赴港医病”,[6]1941年2月12日,“妻由港回渝”。[7]值得注意的是,宋美龄前三次留港时间均为一个月左右,而最后一次却逾四月。此间,国共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蒋介石内外受困,一直危难相助的宋美龄究竟为何滞留香港长期不归?对此,学界缺乏充分的关注。②仅杨天石从情感生活的角度探讨了宋美龄留港不归的原因,认为蒋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机”,既和宋美龄怀疑蒋介石的“私德”,又和怀疑蒋纬国的来历有关。详见杨天石:《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9-508页。2010年1月,两岸学者在台北举行以“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为主题的研讨会。在讨论过程中,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说:“我想问罗敏博士,稗官野史谈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的关系非常糟糕,不晓得这部分您的解读如何?”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回应:“刚刚还有提到蒋纬国与宋美龄的关系,我想是看了杨天石教授的文章。不过,我看了也没有被老师说服。我想等我有答案再跟您联系(参见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3、200页)。这恰恰说明宋美龄留港不归另有原因。本文拟借助中外各方人士的日记、回忆录以及报刊等资料,对此事内情及缘由进行论证分析,以增进对蒋宋关系及国共关系的认识。
一、妇指会的工作受到压制
全面抗战爆发后,宋美龄顺应时代大势,赞成国共合作,[8]注意团结各党各派各方面的力量。她反复强调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我国现在最大的需要,是各党派以及社会各部门的团结合作,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论有什么党派的偏见,为顾全国家的利益,都应该祛除净尽。”[9]
为了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战,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妇女界领袖及各界知名女性代表在江西庐山举行谈话会。会议决定以宋美龄担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为全国妇女团体的总机构。7月1日,妇指会在汉口改组扩大。指导长宋美龄之下设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0人,委员36人,她们是国民党、共产党、救国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方面的人士以及党政军官员的夫人、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等,例如李德全、吴贻芳、曾宝荪为常务委员,救国会的曹孟君(中共秘密党员)和代表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为委员。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分别任联络委员会主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和训练组组长;无党派人士俞庆棠、谢兰郁分别为生产事业组组长、总务组组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钮珉华为儿童保育组代理组长;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陈逸云、黄佩兰分别任慰劳组组长、战地服务组组长和生活指导组组长。从领导层来看,左派人士和中间势力占了优势。
通过组织改造和革新,妇指会实现了各党各派各方面妇女的大联合,也标志着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史良认为,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是一个“从来所没有的崭新而充实的领导全国妇女团体的总机构”,“全国妇女,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不分宗教的在蒋夫人贤明的领导下,紧紧团结起来了,这个团结已成为全民抗日联合阵线中的最优良的模范”。[10]在妇指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界妇女积极开展了文化宣传、儿童保育、慰劳救护、战地服务、乡村服务、生活指导、生产事业等各种工作,成为安定鼓舞后方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共对妇指会的工作很重视,选派大批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活跃其中,宣传、动员、组织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工作,促进了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而且,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出色的才干赢得宋美龄的器重。①请参阅拙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同时,她们也对宋美龄抱有好感。1941年1月10日,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登载了《论今年的妇女运动》一文,总结道:“全国二百多个妇女团体,大多数都能团结在蒋夫人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周围同心协力的开展工作”,“工作逐渐深入工厂和农村”。[11]沈兹九称赞,“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各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斐然成绩,好像一颗巨大的彗星,带着万道光芒,在黑暗的天空出现。”[12]
宋美龄对妇指会工作很投入,甚至积劳成疾。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之以背疼、牙病数症并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他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忍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13]宋美龄的这种工作态度,与人们所想象的高高在上、雍容华贵的贵夫人形象不太一致,或许这也是许多优秀的女性共产党员聚集在妇指会中的原因。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相对融洽,在军事方面配合作战,共同抗日。但随着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两党间的摩擦冲突愈演愈烈实难避免。②参见杨奎松:《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1939年至1940年的下半年,随着华北前方国共两党间的军事摩擦日趋尖锐化,大后方因国民党要“消灭异党分子”而引起的人事冲突也逐渐加剧,即使妇女团体亦未能幸免。由于妇指会及其附属单位均有左派人士和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甚至占了主导地位,国民党方面逐渐着手干预。
1940年8月,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孟庆树在《“促进”妇运抑是加紧压迫妇运》中揭露:许多国民党部和地方政府“专门从事压迫妇女运动,破坏妇女团结,捕杀妇女干部的危害行动”,“连蒋夫人亲自批准的河南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和陕西妇女慰劳分会亦被少数顽固分子拒抗上级命令违反群众要求而强迫改组了”。[14]宋庆龄也观察到,在1940年夏天,妇女又开始遭到战前的那种歧视了。例如,邮政局突然宣布不再雇用已婚妇女。在妇指会的主持下,首都所有妇女团体曾举行会议,讨论自卫的步骤。但妇指会“本身就立刻引起了特务和行施压力的政客们的注意”。[15]沈兹九在《回忆妇女大团结》一文中指出:关于妇指会的谣言,“如雪片似地飞来,它堆积在蒋夫人的身边,大约不下于喜马拉雅山的积雪”。沈兹九见到宋美龄时,发现她“不是往常那样满面笑容,而且是忧形于色”。显然,宋美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过,与一般的国民党人不同,她更倾向于从工作本身考虑问题:“什么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共产党,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能够做得这样好,即使是真的共产党,我也愿意将工作交给她做。”[16]
宋美龄看重属下工作人员的能力,而不是其党派身份。训练组股长郭见恩①后改名郭建。湖南株州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训练组的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撤到香港,转苏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等。参见高魁祥、申建国编:《中华古今女杰谱》,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第125-126页。是中共秘密党员,能干活跃,而且吃苦耐劳,她带领的战时乡村服务队深受群众欢迎,也获得了宋美龄的信任和重视。1938 年9月中旬,郭见恩向总干事张蔼真辞职,说要出国深造,张蔼真将报告转请宋美龄批示。不料,宋美龄竟然亲自到黄陂服务队队部挽留郭见恩,强调妇指会的工作需要她。后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断向宋美龄告状说郭见恩是共产党首要分子,宋美龄也没有动摇对郭见恩的器重。
不过,尽管宋美龄对妇指会的一些人士是否为共产党不予以深究,但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夫人领导下的妇女组织,竟然查出许多“异党”活动,并且倍受压迫或干涉。当时,宋美龄面临的尴尬是不言而喻的。
二、宋美龄与蒋介石发生冲突
宋美龄自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后,即成为其得力助手。抗战时期,宋美龄与蒋介石共患国难,夫唱妇随,蒋对宋的感情愈发深厚,时常在日记中感叹:“心神忧急之象未除,幸妻能解愁耐烦也。”[17]“上和下睦,夫唱妇随,此精神安乐胜于克敌千万矣。”[18]“夫妻融融,苦中甚乐也。”[19]
对于宋美龄的工作,蒋介石更是赞赏有加,“开战以来余妻对伤病官兵、难民、难童之爱护工作,此种赤忱与热心非任何人所能有,而于近月为尤甚。”[20]“妻往衡阳、邵阳亲自分别代余慰问伤病官兵,已可感激,而其对伤兵之诚心,所赏给之食、衣皆必由其亲自料理,丝毫不苟,更为佩感也。”[21]1940 年2月,他还公开称赞妇指会的成绩:“抗战以来,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策动之下,我们女界同胞参加战地服务,已经显著的功效,他如保育儿童,已经成立了四十八个保育院,保育了几万名的难童,设立纺织实验区,蚕桑实验区,组织新运妇女工艺社,设立抗战家属工厂,对于增进生产,也有很伟大的贡献,这实在是最可欣喜的现象。”[22]并且,他一直乐于参与宋美龄开展的活动。1939年3月5日,在日记中写道:“回渝参加妇女献金运动,妻之奋兴提倡,一日竟得六十三万六千余元之数,此为妇女界破天荒之佳象,足以自诩于世界矣。”[23]同年12月24日,日记云:“今晚由妻约妇女指导会各组长同宴,谈笑自如。”[24]可知,蒋介石对宋美龄领导的妇指会工作是非常支持的。
患难时的相助,工作的彼此欣赏,使蒋宋的感情历久弥笃。蒋介石自感“余俩之爱情,因彼此爱国之故,而更成知己之爱与同志之爱也。”[25]即使起初不看好蒋宋婚姻的宋庆龄也改变了观感,认为二人已真心相爱。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初次与宋庆龄见面时,被告知蒋宋婚姻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但是,1940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斯诺说:“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但是,现在我认为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26]
然而,随着“国共关系一天一天恶化”,[27]蒋、宋对妇指会工作逐渐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表现在妇女干部训练班的教员聘请、讲课内容等方面。
黄薇是从新加坡归国投身抗战进而加入中共的女记者。1939年春,宋美龄在重庆各界妇女领袖座谈会上听过黄薇的发言,觉得她很会做宣传工作,便邀请她到第三期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讲课。该期学员举行结业式时,蒋介石也来参加,他看见黄薇坐在主席台上极为不悦,显然他从其他渠道知道了黄薇的情况。几天之后,刘清扬告诉黄薇:“前几天蒋委员长批评了蒋夫人,问她为什么把你请到训练班去宣传共产党,并且叫她以后不能再让你去讲课。”[28]由于蒋介石的反对,黄薇自动解职了。
刘清扬曾因积极参加“一二·九”救亡运动,以爱国罪被捕入狱。[29]出狱后,还是继续不懈地努力于救亡工作。宋美龄欣赏她的才干,极力邀请她担任妇指会训练组组长,刘清扬表示:“我要训练的是真能为群众服务、为祖国赴汤蹈火的干部,那样一来,会有人说我刘清扬是共产党,专门训练出一些共产党。那样,夫人你就不好办了。”但宋美龄依然说:“只要训练出能为抗日工作的干部就行,陈立夫他们管不了我的事,你做你的好了。”[30]不过,1940年5月1日新运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关于再办下一班的消息却没有了。刘清扬忍不住去问宋美龄还办不办训练班。宋回答,“委员长说训练班不能再请以前的教员办了,有人汇报,说训练班宣传共产主义”,“委员长说,今后要训练干部的话,要让浮图关上的中央训练团的教员来训练了”。刘清扬听了气愤地说:“夫人,你可知道,群众是这样议论中央训练团的:浮图关训练糊涂官,越训练越糊涂。我们能让他们去训练青年吗?”宋美龄显然也对此不满,淡淡地说:“好在目前我们的服务队已不少了,够用了。刘组长,你就经常到各地去视察视察、督导督导吧。”[31]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宋美龄暂停开办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虽然1940年9月宋美龄曾发表告女青年书,号召女青年参加第五期干训班,但却迟迟未见招生。①该班直到1941年11月15日才正式开办。参见《历届干部训练班一览表(1938年7月—1943年1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1-920。而正是之后不久,宋美龄第四次赴港“医病”。
1939年3月,蒋介石夫妇聘请了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②文幼章(James G.Endicott),1898年出生于四川乐山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1947年回到加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幼章7次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会见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希望定期听到他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所见所闻和种种想法。此外,宋美龄还要求文幼章协助妇指会的工作,说她的各级工作人员中共产党人、基督徒和其他党派人士各占1/3,要文幼章协助解决这些工作班子中出现的难题。自此,文幼章常常“陪同蒋夫人四处奔波,看到她那么辛勤操劳”,“对她的尊敬与日俱增”。③[加拿大]文忠志:《文幼章传——出自中国的叛逆者》,李国林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文忠志(Stephen L. Endicott)为文幼章的儿子,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历史教授,亚洲问题专家。但是,1940年春,文幼章与宋美龄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问题的核心是,在宋美龄亲自督导下培训的新生活女青年队与三青团合并了,文幼章抗议这种草率从事的做法。不过,“蒋夫人的懊恼使文幼章感到高兴和宽慰。因为他觉得,这表明她脑子里的确在进行思想斗争”。[32]文幼章写信给宋美龄说:把新生活运动纳入国民党的轨道是一个错误。新生活运动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应该对国民党和它的行动提出有益的、正确的批评。[33]宋美龄请文幼章直接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想法。显然,宋美龄的内心是矛盾的,她既不能抗拒蒋介石的命令,又不满国民党对新生活运动的干涉,她早就说过,“新生活运动的本身,不含政治作用,对于任何党派活动,不感兴趣,而且也不应该发生兴趣”。[34]
文幼章与蒋见面时开诚布公地批评,“国民党力图完全控制新生活运动;下一期妇女干事训练班(指新运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引者)中,国民党员占80%,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实行联合战线的三三制”,结果谈话不欢而散。文幼章感到他这个顾问没有价值了,决定辞职。但是,宋美龄不允许,并给教会写了一封信,请求留他再为新生活运动工作一年。这时,文幼章发现,缘于对“联合战线”的处理,蒋介石夫妇之间有了裂痕,“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个裂痕可能会逐渐扩大到无法弥合的地步。看来蒋介石不是更民主了,而是在转向它的反面。他可能会对一个女人企图向他施加压力并进行控制感到愤怒”。文幼章觉得自己必须从这个运动中退出,“以避免造成战时中国的这两个最卓越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决裂”。[35]1940年夏,他又重新回到教会工作。
文幼章的自我定位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冲突则是显而易见的。受过10年西方教育的宋美龄在政治上难免有一些自由主义倾向,处理事情也往往有自己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特别是表现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的国共关系问题上,显然她比蒋介石更开明大度。
1940年7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恢复设置妇女部以利妇女运动案。[36]蒋介石希望宋美龄负责国民党的妇女工作,但宋美龄表示“对政治没有兴趣”,“不愿参加党的妇女工作”。[37]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集各省市妇运干部在重庆举行全国妇运干部工作讨论会,代表们一致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五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案,早日成立中央妇女部,并恳请宋美龄出任部长。不过,宋美龄发表讲话,谢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38]而只愿集中精力主持妇指会,故中央妇女部终未恢复设立。作为党派最高领袖的夫人,宋美龄却表示对任何党派活动不感兴趣,并拒绝出任党职,可见宋美龄与蒋介石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
三、宋美龄“赴港医病”与妇指会改组
1940年10月6日,宋美龄“赴港医病”。[39]第二天,中共《新华日报》刊登了题为《妇指委会局部改组(谢冰心胡惇五分任组长)》的消息,称:“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组组长与儿童保育会总干事,原由指导会副总干事陈纪彝兼任,兹陈以指导会工作日繁,不暇兼理保育事宜,已辞去兼职,闻该组组长与该会总干事,改由胡惇五女士继任,又指导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现聘定谢冰心女士担任。”[40]在宋美龄赴港的同时,中共方面立即披露了妇指会改组的消息,颇耐人寻味。
关于妇指会改组,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有所记载。1940年11月20日,王子壮去四川教育学院拜访朋友,朋友介绍同乡李昆源(中共秘密党员)来谈。在当天的日记中,王子壮写道:“彼原在妇女指导会随蒋夫人工作,近来此,担任女生指导员。余询及妇女会情形,彼云蒋夫人信仰教会中人,以其于事务理财方面较有办法。其次国民党员之唐国桢等能力太差,故偏重他人。闻何部长(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引者)曾以该会左倾告诸蒋先生,近日该会改组,蒋夫人,似亦在香港等语。”[41]这里提示了一种合乎情理的逻辑:蒋得知妇指会左倾,令其改组,宋赴香港。
事实上,宋美龄也曾配合蒋介石试图改变妇指会的“左倾”。她曾动员史良、沈兹九等参加国民党,声称要吸收她们作特别党员。[42]关于此事,史良回忆,“有一次,宋美龄请我吃饭,蒋介石也在座,她对我说:国民党需要增强新的血液,你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一道把它进行一番改革呢?”[43]史良委婉地拒绝了。郭见恩也记得,为了动员她加入国民党,宋美龄亲自与她谈了三次。[44]由此可见,为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宋美龄也号召鼓动妇指会工作人员参加国民党,但毕竟还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并未采取强迫的方式。她似乎属于国民党内比较开明的一派。
对此,接触到宋美龄的人都有类似的看法。1940年,周恩来在苏联莫斯科写了一份题为《有关蒋介石最信任的人》的札记,称赞“蒋夫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蒋相比,她更民主化,而且强烈支持对日抗战和维持中国统一”,“她和陈诚很接近,不过她与何应钦及陈立夫不睦”。[45]周恩来所观察到的宋美龄与蒋介石的不同,以及所谓“更民主化”,显然是指对中共的态度而言的。此外,周恩来认为,宋美龄与何应钦、陈立夫关系差,而与陈诚颇接近。担任过宋美龄顾问的文幼章也注意到,宋美龄“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和国防部长何应钦这类人物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些人担心她的民主思想会影响委员长和国民党的一些活动,从而危及那些人和国民党极右派的专制统治”。[46]
何应钦、陈立夫、陈诚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他们对中共的态度并不一致。何应钦、陈立夫一直坚持反共态度,而陈诚对中共的态度微妙而复杂。著名的国民党左派、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是陈诚的好朋友,陈诚与周恩来的私交也不错。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力邀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还邀请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知名人士到政治部工作。此外,蒋介石的心腹张群也是统一战线的支持者,他认为“若将政府的精力用来对付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那将是致命的错误”。[47]1941至1942年,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时,与国共双方人士有许多接触,他描述在重庆看到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蒋介石的特工机构,像戴笠和陈氏兄弟,他们正在迫害和跟踪左派人士,另一方面又有相当数量的左派受到国民政府内高层人士的保护。”[48]这无疑反映了国民党上层对中共态度的分歧。
不过,蒋介石作为最高领袖自然是要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希望的国共合作也只是限制在抗日的范围。如果认识到中共势力的膨胀,那就是他不能容忍的了。但宋美龄显然并未完全照蒋的要求改变妇指会的“左倾”形象,面对其中的国共之争,她似乎还保持中立。史良曾说:“国民党里的人虽然和我们争得很厉害,但宋美龄本人却从不表示态度。”[49]对于妇指会的“左倾”,既然宋美龄自己不能改变,蒋介石在别人的鼓动下出面干预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此次妇指会改组中,辞去保育组组长与儿童保育会总干事的陈纪彝,即与“左倾”有关。她曾留学美国,是思想开明的基督教徒,早在担任汉口女青年会总干事时,已与邓颖超和左翼人士交往。[50]她政治上希望超然于党派之争,特别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共产党人报以同情态度。邓颖超不仅与她建立了良好关系,还指示中共党员和左翼青年尽力支持她的工作。比如,中共党员徐镜平担任儿童保育组副组长,与陈纪彝配合默契,深得陈的信任。[51]并且,在儿童保育组及战时儿童保育会中,活跃着大批中共党员。在基层保育院,一大批中共秘密党员担任保育院院长。[52]蒋介石的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曾一再提到儿童保育会及儿童保育院被中共把握,引起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层不满。①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195、251、256页。显然,受宋美龄器重的陈纪彝辞职,与国民党的干预有关。
此次改组中,另一个重要变动是文化事业组组长。这一职务原由文化界知名人士沈兹九(中共秘密党员)担任。当时,沈兹九吸收了一批中共党员和左翼青年在文化事业组工作,比如,中共党员夏英喆、徐培影分别编辑《妇女新运通讯》半月刊、壁报资料;左翼青年郑还因编辑妇指会会刊《妇女新运》月刊,魏郁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53]郑还因回忆,有一天,沈兹九说,形势日益恶化,她只得辞去组长的职务,并说:“我走后将由李昆源来担任代组长,李是可信的,你们要和她合作。”[54]沈兹九所说的“日益恶化”显然指国共关系。为躲避风头或免于迫害,她先行退出了,其中必有中共组织的安排。
王子壮和沈兹九都提到的李昆源,亦是中共秘密党员,曾担任汉口临时保育院院长,而她最终也离开了。事后,由于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推荐,[55]宋美龄邀请著名作家谢冰心接任文化事业组组长。
1941年7月,沈兹九在《抗战四年来的妇女运动》一文中谈到:从武汉、广州沦陷到1940年底,突飞猛进的妇女运动及妇女工作,遭受到猜忌和打击,“幸喜蒋夫人坚持团结合作,因此一切造谣中伤,不能发生多大的效力”。[56]若干年后,邓颖超仍然记得,儿童保育会的“一些成员和保育会内部事务,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破坏。这一点我们是得到宋美龄和战时保育会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终于没有受到极大破坏。”②《邓颖超致函郭建——谈战时儿童保育会问题》(1985年8月3日),《保育生通讯》1998年第1期。引自古为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可见,宋美龄对国民党的干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她自感对属下有一份责任,但在一些国民党人看来,这可能有纵容共产党活动之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陈逸云、唐国桢两位国民党员组长也辞职离开了妇指会,或许因宋美龄不满她们的工作能力,以及她们与妇指会中的工作人员难以合作共事。总的来看,1940年10月宋美龄赴港前后,妇指会的人事更迭异常频繁,沈兹九、郭见恩、刘清扬、史良等中共党员及左派人士先后辞职,宋美龄新聘任的各部门主管人谢冰心、胡惇五、李曼瑰、熊芷、黄翠峰,均为毕业于教会大学或留学美国的专家、学者及社会活动家,似乎更体现了非党派色彩。应该看到,这是在国共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宋美龄个人的言行,自然要服从国民党的大局。而由此产生的情绪却很难不流露给作为家人的蒋介石。所以,在妇指会改组之时,宋离家出走,并在其工作因“异党”问题受到严重干扰之时,滞留不回,便成为合乎情理之事。
四、蒋宋恢复“和爱团圆”
蒋宋结婚后,虽偶有闹意见,宋美龄负气出走,但逾四月不归的事情从未曾有过。长期以来蒋介石对于宋美龄形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依赖关系,考之于他在此前后十几年的日记便能清楚地发现这一点,宋美龄在港期间他也不止一次有感于此。
1940年12月24日圣诞节,他写道:“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惟一之苦痛。”[57]到了旧历除夕,他在日记中悲叹:“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58]春节期间,蒋介石更感寂寞孤苦,日记云:“近日寂寞异甚,时感孤苦自怜。”[59]2月8日日记又云:“心神比较沉闷抑郁”,“手制寂寞凄怆歌”。[60]可见,没有宋美龄在身边,蒋介石度日如年。
宋美龄自己曾解释过滞留香港的原因。1941年2月26日,她在致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信中说:“在香港经过医生四个月的治疗后,两个星期前我返回了重庆。”[61]当然,这也是事实。宋美龄一直体弱多病,抗战期间工作过度紧张,加之1937年10月前往淞沪前线慰问时遭遇车祸留下的创伤,使她饱受头痛、失眠、荨麻疹等各种病痛的折磨。然而,这些病并不一定非要在香港治疗。就在宋美龄出走的前两周即9月21日,蒋介石还在日记中感叹妻之牺牲精神,“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62]为何仅仅两周之后,宋就改变了这一切呢?妇指会改组与宋美龄“赴港医病”绝不是一种巧合。
宋美龄赴港后,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工作考核委员会主任的国民党元老张继扬言要对“异党活动”予以“制裁”。1940年11月18日至1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载:张继“以为现在竟有以政府公款办理团体,而其中培植异党力量者(指孔之工业合作协会及蒋夫人之妇女指导会)更有种种非法行动”,“张先生为异党活动,尤以要人为掩护之活动,深恶痛绝,迭在监察委员会研究制裁之法,今日乃公布于大家”。王子壮议论:“在党主政之形势下竟有此等现象,妇女指导会亦大致相同。其所以致此,足证明党之无力。急应予以救正者也”。[63]这种看法反映了一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心态。不过,尽管蒋介石对妇指会内的中共活动表示不满,但是面对他人的攻击却立即进行了维护。11月20日,在日记中称,“对溥泉之狂言”“应有制裁”。[64]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濒临全面破裂以致发生大规模内战的边缘。防共反共的气氛同样反映到妇女工作上,即使宋美龄担任指导长的妇指会及其附属机构也受到严重的打击。比如,儿童保育会被进一步改组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处于半冻结状态中。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中,能力强的,能够做事的,也大多数被认为是“异党”。[65]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妇女工作最高领导的宋美龄又怎能回来呢?即使她不怕“制裁”,也无法面对众多被作为“异党”的下属。
事实上,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66]他在日记中写道:“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为中共与家事,忧不成寐”。[67]他还批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产党,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与十年前毫无进步,可叹!”[68]他坚持“对中共应消灭其组织为主,而对其武力次之”。[69]可见,在团结御侮的大环境下,蒋介石不赞成通过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也不想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关系。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面临困境,试图改善国共关系,正是在此情形下,2月12日宋美龄回到了重庆。据妇指会《会务大事记》,1941年2月1日,“张总干事蔼真因公飞港”;2月12日,“张总干事蔼真公毕返渝”。[70]张蔼真是宋美龄最信赖的教会派人士,所谓“因公”,显然是她向宋美龄请示和讨论妇指会的事务,亦或是执行蒋介石交付的任务。张在香港待了十余天,提示“公”事并不顺利。但是,宋美龄最终与张同日回到重庆。先前因工作而去,如今还是因工作而回。她在致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信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没有完全康复,医生们不同意我离开,但是我的工作需要我回来”。[71]
2月15日,宋美龄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私人谈话时,特别提到自己面临的困境:既被指控为左派,又被指控为右派。宋美龄用了“困境”一词,可以说是她长期不归的最好解释。她进而向居里说,之所以病情还未恢复就回来,目的在于澄清居里提出的青年人被指控为左派的事。①“Currie,Lauchlin 1stTrip to China”,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No. 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原文如下:Madame Chiang talked with me a few minutes after we went upstairs. She told of her own difficulties in being accused of being both leftist and rightist. She said she had come back,though not yet well,to get certain things straightened out on which I inferred with younger personnel accused of being leftist.比如,她随即出面保释被国民党特务怀疑为“异党分子”的周健即是一例。[72]看来,经过张蔼真总干事在港期间的汇报和劝说,宋美龄改变了想法,由原来的退却、逃避,开始变为利用自己的影响进行积极应对,以保护下属和推动工作的开展。自然,这离不开蒋介石的认可和支持。
宋美龄回来不久,2月27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与妻郊外车游,晚谈中共事。”[73]晚上夫妻俩讨论中共问题,这是别有趣味的。从当时的情景看,谈的无非是妇指会内的中共活动和对皖南事变的处理,两人似在对中共的方针与态度方面达成了共识。稍后,蒋介石日记称,“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74]为了缓和皖南事变造成的国民党与中共的紧张关系,3月13日蒋介石日记:“预定:约周恩来谈。”[75]但是,此时国民党高层并没有放松对妇指会的侦查。同一天,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记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何总长(军政部长何应钦兼参谋总长——引者)报告女共党在重庆之集中所,一为儿童保育院,一为妇女指导委员会。其后讨论宣传问题,陈立夫表示,委座对共党态度不得不持宽大,吾人则应力求严正,苟无准备将有后悔。”[76]也是同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称:“下午特种会报,何敬之报告李德全、刘清扬、史良等早加入共党,并担任为共党作掩护工作等。”[77]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蒋介石与夫人刚刚达成的共识即对中共的缓和策略。第二天,蒋介石如约与周恩来谈话,当时宋美龄也在座。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再见面,宋美龄提出还要请周恩来吃饭。[78]15日,蒋介石在预定工作课目中写道:“对中共之策略,约恩来夫妻聚餐。”[79]17日仍“预定:约恩来夫妻聚餐”。[80]此举可能是宋美龄的建议,因为邓颖超是妇指会的委员,二人相熟,《妇女生活》杂志曾记载,蒋夫人“特别器重她,邓颖超当选为参政员,夫人是提名人之一”。[81]25日,即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席间周恩来同蒋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82]同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委座请周恩来夫妇午饭,无非想缓和中共的决裂。谋国之心,亦良苦矣。”[83]其中宋美龄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似乎还有意利用宋先前与中共的融洽关系来改善紧张关系。而时局的确从此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不过,国民党内追究妇指会“容纳”共党问题的声浪仍然在升温。3月29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谈话会,蒋介石亲临主持。王子壮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谈话会中有一足记者,溥泉先生(张继——引者)与蒋先生之冲突。溥泉先生似不满蒋先生于共党问题之处理,日常闻彼谈不满蒋夫人于妇女会容纳共党及孔氏主持之工业合作协会亦然,今以谈话会可以自由发言,乃提出共党问题,叙其如何猖獗,最痛心为本党同志中有为之张目者,即总裁身边亦未能免彼等之包围。蒋先生在座闻言甚气,当场责训其非……。”[84]
张继所以敢当面直言,颇代表了国民党内的一种看法,即总裁已被共产党人包围。当天,蒋介石日记称:“心神愉快之时较多,尤以母子亲爱、夫妻和睦为最。家有贤妇与孝子,人生之乐,无过于此。惟在会中对溥泉发愤失态,不觉自我暴弃至此,可痛矣乎!”①《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母子亲爱”,指宋美龄与蒋纬国之间的关系。蒋纬国一直由养母姚冶诚抚养,从未见过宋美龄。1936年赴德留学,后又留美。1940年10月底,蒋纬国自美返国,途经香港时拜见了宋美龄。宋之前对蒋纬国的存在和身世不可能不知晓,但毕竟这是第一次见面,难免会有生疏感,而并非蒋纬国的到来引发了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矛盾。1941年2月12日宋美龄返回重庆后,随着与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达成共识,两人和解,3月27日蒋介石令蒋纬国正式叩拜母亲宋美龄,实现了母子亲爱、夫妻和睦。虽然蒋介石未必认识到“夫妻和睦”与对攻击宋美龄的张继发怒之间的关系,即使从维护自己的权威出发,张继的态度也是需要讨伐的。3月31日,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再次写道:“家庭间夫妇、母子之和爱团圆,此为一生幸福之开始。”[85]无论如何,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和爱团圆”,与他们形成的对中共态度的一致是同步的,也是与蒋介石压制和批评国民党内对宋美龄“容纳共党”的指责发生在同一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皖南事变前后,蒋宋因中共问题而离,最终又因中共问题而合。
五、结语
综上所述,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赴港并长期滞留,固然有医病因素。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显然是她的工作问题。妇指会作为宋美龄主持的全国妇女团体总机构,吸收了各党各派各方面的妇女工作人才,工作成效卓著,在国内外享有很高荣誉,无疑增加了她的光环。然而,由于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等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在其中工作,甚至占了主导地位,引起何应钦、陈立夫、张继等国民党高层的不满,接连进行干涉或发出制裁之声,妇指会的工作受到压制,宋美龄与蒋介石也发生了冲突,最后妇指会被迫改组。这使宋美龄的工作遭遇严重的挫折,她虽然在公开言行上不能不支持蒋介石,而私下里则难免会有情绪,滞留香港,迟迟不归,即是一种表现。对于整个共产党,她未必认同,但是个别共产党人的才干和工作,她是欣赏的。人与人只要接触就有感情,在宋美龄领导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大都对她有好感,甚至把她当作一顶保护伞,即使周恩来对她也格外的赞赏。
无论如何,当时蒋宋之间的“离合”明显地受到了国共关系的影响。他们之间的不和谐,是国民党上层对中共态度分歧的一种反映。而他们最终和好如初,又与取得的对中共态度的一致相关。蒋介石的家事与国事如此相连,大概是人们以前所不曾想到的。
[参考文献]
[1][2][3][4][5][6][7][13][17][18][19][20][21][23][24][25][39][57][58][59][60][62][64][67][68][69][73][74][75][79][80][85]《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9日,1938年3月17日,1938年4月17日,1940年2月12日,1940年3月31日,1940年10 月6日,1941年2月12日,1940年9月21日,1937年9月27日,1938年12月4日,1939年2月25日,1939年10月31日,1939年11月3日,1939年3月5日,1939年12月24日,1939年10月31日,1940年10月6日,1940 年12月24日,1941年1月26日,1941年1月30日,1941年2月8日,1940年9月21日,1940年11月20日,1941年1月13日,1941年1月13日,1941年1月14日,1941年2月27日,1941年3月9日,1941年3月13日,1941年3月15日,1941年3月17日,1941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8]莫蓝:《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访问记》,《周恩来邓颖超最近言论集》,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第67页。
[9]《(庐山全国妇女界空前盛会)蒋夫人呼吁大团结》,《新华日报》1938年5月25日第2版。
[10]史良:《妇女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妇女生活》第6卷第11期,1939年1月1日。
[11]《论今年的妇女运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19期,1941年1月10日第4版。
[12][16]兹九:《回忆妇女大团结》,《大众生活》新5号,1941年6月14日。
[14]孟庆树:《“促进”妇运抑是加紧压迫妇运》,《中国妇女》第2卷第3期,1940年8月10日。
[15]宋庆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1942年7月),《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9页。
[22]《新运六周年纪念前夕蒋会长广播演词(历举五要点为今年主要工作),《中央日报》1940年2月19日第2版。
[26][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宋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00-101页。
[27][76][83]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131、195、198页。
[28]黄薇:《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54-255页。
[29]季洪:《记刘清扬先生三十年来的奋斗》,《妇女生活》第5卷第6期,1938年1月5日。
[30][31]刘清扬:《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196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52、66-67页。
[32][33][35][46][加拿大]文忠志:《文幼章传——出自中国的叛逆者》,李国林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9、210、211-213、202页。
[34]蒋宋美龄:《妇女谈话会演讲辞》,《妇女生活》第6卷第3期,1938年6月5日。
[3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653-654页。
[37]辜严倬云:《蒋夫人与近代妇女工作》,童淑纯整理:《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行谊演讲会记录》,台北《近代中国》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
[38]《蒋夫人训词》(1941年4月21日),《妇运干部工作讨论会纪要》,重庆:中央组织部1941年编印,第4-5页。
[40]《妇指委会局部改组(谢冰心胡惇五分任组长)》,《新华日报》1940年10月7日第2版。
[41][63]《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25、323-324页。
[42][53]《南方局通过新运妇指会开展的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第5册《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494、485-486页。
[43][49]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0、48-49页。
[44]郭建:《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百年潮》1998年第5期。
[45]潘佐夫、高念甫:《俄罗斯档案馆中的宋美龄女士文件》,秦孝仪主编:《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3年,第374-375页。
[47][48][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1、140页。
[50]《青春颂》,北京: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1993年,第2页。
[5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433页。
[52]古为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54]郑还因:《沈大姐在妇指会》,董边主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55]钱用和:《钱用和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56][65]沈兹九:《抗战四年来的妇女运动》(1941年7月25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577、577-578页。
[61][71]“Chiang,Kai-shek,Mme”,Lauchlin Currie Papers,Box No.3,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
[66]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0]《会务大事记》,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工作八年》,南京:南京印书馆,1946年,第266页。
[72]邹韬奋:《经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96页。
[7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60页。
[78][82]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上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第178-179、179页。
[81]文纶:《来来往往》,《妇女生活》第8卷第1期,1939年9月16日。
[84]《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7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88-89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文学语言学
·中国文体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6-0135-10
作者简介夏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