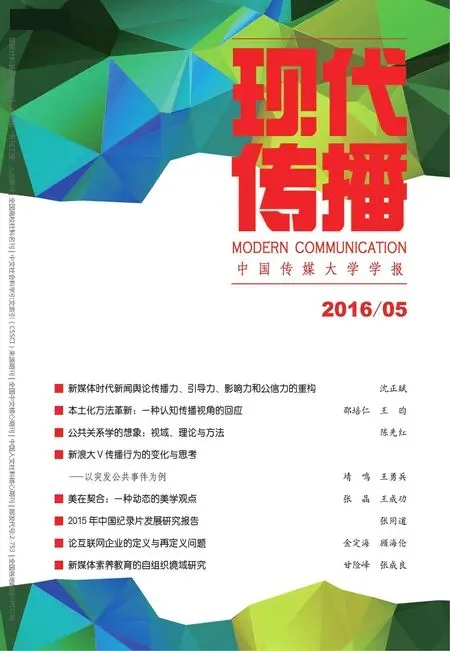技术哲学进路审视现代设计之于人才培养的启示
2016-02-19詹鹏超
■ 卢 渊 詹鹏超
技术哲学进路审视现代设计之于人才培养的启示
■ 卢渊詹鹏超
【内容摘要】在机器生产时代,设计成为人与技术的博弈,然而在现代设计发展的很多情景中,人正在受到技术的限制,沦为技术进化的工具。现代设计作为技术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包涵着人的主观能动行为,体现着人对“美”的认知,是人的知性和想象力二者互动,并自由活动的结果。以技术哲学进路审视并解析现代设计的发展历史,提出设计的本质和意义不应仅在技术基础上改良,而应该发现人性的真正需求,并满足这种需求,唤醒人内心对“美”的追求。这是现代设计教育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也是探讨当代中国设计走向需要关注的维度。
【关键词】现代设计;设计艺术;技术哲学;设计教育;人才培养
当人类陶醉于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时,应该要看到今日的设计大繁荣表象下,在人文、经济、生态等范畴内,作为人类高级情感特征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过度包装、设计贵族化、抄袭仿造现象、盲目消费、生态危机等问题日益显现。不断进步着的技术已全面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创造技术的人类也并不能完全确定这些新技术最终会将世界引向何方。在这一背景下,以哲学进路对设计的本质和意义进行思考变得必要和更加紧迫。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和创造未来,因而梳理人、设计、技术纠葛的历史,从中寻找对今天和未来有借鉴意义的启迪成为可能。
一、工匠阶层的异化与设计者的反思
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工业革命爆发之前,经验认知是喜欢实践的文艺复兴学者内生的认知类型,他们强调经验在知识基础中的重要作用,对杰出工匠实用知识的重要性有很强的意识。这种对工匠实用知识和技能的青睐,使得人们对机械、原料和大自然的兴趣提升。萨顿曾说:“文艺复兴如果只是简单地回到古代,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远不止此,文艺复兴是回到自然。”①在这种探索自然的思潮中,劳动被视作价值的来源,人们寻找自然的规律,并热衷于以此进行创造,工匠和手工艺人因对自然的细微观察和确切了解而获得尊重。艺术家并不排斥兼具优秀工匠的身份,他们投身于各种实用产品的设计中,并亲自制造这些产品。莱昂纳多·达·芬奇即是例证,他的笔记中包涵了大量的设计图纸,他本人不仅是一位建筑师、雕刻家、画家,而且作为一名工程师、军事工程建造技师和战争武器专家,为米兰城统治者拉多瓦·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服务。②与此同时,工艺技能也出现了向学问领域合并的趋势。例如,1235年出现了第一部由工匠撰写的专著,它由法国建筑师维拉尔·德·奥内库尔(Villard deHonnecourt)按照当时的技能和技术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写成,它既是识字的工匠所写成的技能方法总结,也是当时建筑领域的系统专著。③在这一阶段,设计和制作是融合的,艺术家也是优秀的工匠,工匠也具备设计的技艺。
但这种因“知识分子伏下身去亲近自然”④而带来的艺术家、学者、工匠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快便中断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机器的强大力量逐渐显现。由于机器的生产效率远高于手工操作,工匠阶层渐渐被排挤,工人成为他们可选择的新职业。英国1831年的人口报告称“苏格兰的家庭织工渐渐变成不是为本身即棉纱生产者这种消费者,而是为城市中的生产组织者做件工的工人”⑤。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统计过,这一时期制作一枚针的工序可达18道,每天可制4.8万根针。这正是机器化大生产带来的愈加细致和专业的劳动分工。这使得生产过程被分解成极简单的动作,劳动从而具有连续性、秩序性、规范性和单调性的特征。工匠们的劳动对象由自然换成冰冷的机器,交流因不被允许而不复存在,劳动中的欢愉为追逐效率的紧张工作所取代。脑体劳动分离,从事简单机械操作的工匠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在梳羊、精纺呢绒、缎带织造及金属制作等行业,手工艺人成为“自身属于别人的、并且只是作为工作机而使别人感兴趣的工人”。⑥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潘评价受雇于纺织厂的纺织手工艺人说“从商业观点上看,这些人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并且除去作为过去几代中一度人数很多的一个团体的残余之外,不能再唤起人的任何兴趣了”⑦。这一时期,工匠沦为机器生产的“人形工具”,他们既无能力也无兴趣关注产品的设计。
在这种技术变革的新社会,变革浪潮给人们观念带来巨变,体力劳动成为获取商业利润的工具,与自然、愉悦的劳作再无关系。资本成为生产的主宰,盈利才是当务之急。英国艺术家、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对此哀叹“一切全都牺牲了:工人在劳动中的快乐,他的最起码的安适和必不可少的健康,他的衣、食、住、闲暇、娱乐、教育——总而言之,他的全部生活——和商品的‘廉价生产'的可怕必要性比较起来是一文不值的,而事实上生产出来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完全不值得生产的”⑧。
这催生出一系列棘手问题——追求商业利润使富足后的人们消费欲望被夸大和极端化。资产阶级新贵为炫耀身份,鄙弃工业产品、追逐手工制作产品,将其视为贵族气息的象征,市民阶层因生活的富足,也产生了提升身份的诉求,然而高尚审美情趣的缺失致使设计艺术作品充斥浓重的虚饰奢华之风。在这种追求宫廷豪华风格的消费趋向的引导下,生产商开始利用低廉的材料冒充贵重材料,并在产品上刻意装饰繁琐花纹。市场上充斥着粗制滥造、毫无美感的批量化产品,生产商为增加销售量获取利润而无意义、无节制的装饰产品。威廉·莫里斯评论说:“最好的商品是一些普通的下等货,最坏的商品简直就是冒充货,……商品是做出来卖的,而不是做出来用的。”⑨
在建筑业、珠宝业等保留了独立手艺人形式的行业,优秀的工匠成为社会审美混乱时期硕果仅存的设计者,他们为了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排除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的不适感,开始奋力反抗技术洪流。威廉·莫里斯便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他不满于工业革命的批量生产带来的设计水平下降的趋势,推进了英国作家约翰·拉斯金于1888年提出的重新提高设计的品位,恢复英国传统设计的想法。威廉·莫里斯成立了“工艺美术运动展览协会”(The 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形成了包括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等在内的声势浩大的工艺美术运动,其特点可以总结为:强调手工艺生产,反对机械化生产;在装饰上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其他各种古典、传统的复兴风格;提倡哥特风格和其他中世纪风格,讲究简单、朴实、风格良好;主张设计诚实,反对风格上华而不实;提倡自然主义风格和东方风格。⑩
分析其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威廉·莫里斯对当时社会中新兴的机械化生产是排斥的,他的设计理念中渗透着反技术的观点。尽管威廉·莫里斯试图改善当下设计水平的初衷没有问题,他试图修复设计与制造之间断裂的链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他企图理想化的退回中世纪的想法却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逆,而他对当时的技术现状——机械化生产的拒斥,更使得他所谓的“艺术为大众服务”的理想成为泡影——手工生产的昂贵代价并非普通人所能负担,而这正限制了工艺美术运动所生产产品的推广,最终沦为有钱人享受的奢侈品,在提高社会的审美观上毫无作为。刘易斯·芒福德对此评价说:“工艺美术运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生代技术已经大大拓展了机器体系的功能,也改变了手工生产的全部关系。机械生产的过程未必就一定要与手工生产和精细的手工艺技术对立起来。”⑪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的形式下,手工艺生产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发挥作用了,即使是在纯手工艺生产中,也必须融入那种原本仅属于机械生产的经济和简洁。
二、重构—崇拜—回避:人与技术在设计中博弈
1.重构:工艺、技术与艺术和谐统一
现代主义设计诞生在20世纪初的欧洲,此时中世纪的深刻影响已然消褪,民主思潮涌起。如果说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对技术的态度是无视和回避,那么现代主义设计则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理念的缺憾。人们尝试接受技术、理解机器,并试图重构这种关系。
以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两大内核的“机械美学”观念即是这种重构的成果。“机械美学”的奠基人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如此诠释这种理念:“在当代社会中,一件新设计出来为现代人服务的产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机器。如住宅是供人们居住的机器,书是供人们阅读的机器……它们的美学原则是独特的,并不跟随古典艺术的美学原则,只有面对这种新的社会状况,才能掌握新的美学立场和美学原则,那就是代表二十世纪新时代的机械美学。”⑫从中不难看出,“机械美学”已经意识到,在技术时代回归自然的设计观已然于事无补,必须要重新建立既符合机械化大生产,又确立人性自主的美学观念,而这种美学观就是形式服从功能和理性设计的。
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设计者理解机器的尝试显然是有益的,对此,刘易斯·芒福德曾有着精辟论断。他认为,理解机器不仅是使我们的文明重新定向的第一步,而且也是我们了解社会和了解我们自己所必须的。机器体系所作出的永远不变的贡献在于它创造和促进了合作的精神和行动,在于机器形式在美学上达到的完美程度,以及对材料和力量的精妙逻辑的揭示。机器体系所创造的艺术有着自身的确切标准,也能够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⑬
从“机械美学”开始,设计者对于机器排斥的观念逐渐改变了,人们尝试着调整自己在技术社会中的地位,并将技术社会的哲学思考结合到设计行为的具象实践维度。这一点从现代主义设计的三个典型代表德意志工业同盟、乌尔姆学院和包豪斯的实践中即可看出。德意志工业同盟的设计原则是经济原则——设计必须讲究目的、实用功能和制作成本,如果不能为整体效果起到有益的作用,那就毫不犹豫地去除。乌尔姆的根本理念是“设计不是一种表现,而是一种服务”,以这种理念为核心的乌尔姆设计学院运用了理性而抽象的数学形式,促进了德国重理性、重功能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模式的形成。⑭这三者之中,包豪斯在重建设计与制造之联结方面做得尤为成功,包豪斯的奠基人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主张建立艺术家、工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合作关系,格罗皮乌斯曾在《包豪斯宣言》中指出:“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们,我们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艺术不是一门专门职业,艺术家与工艺技术人员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不存在使得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竖起很大障碍的职业阶级观念。”由此可见,格罗皮乌斯的核心思想是打破艺术种类的界限,将手工艺人的地位提高为艺术家的高度,强调工艺、技术与艺术的和谐统一。这种理念改善了大工业的非人格化,提高了设计水平,真正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统一,从而改善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尼古拉斯·福克斯·韦伯对此有很高评价,他说“包豪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生命在这里受到礼赞,视觉形象在这里被赋予极为重要的意义,无论来自什么世界的人们在这里都有机会探究和享受生命与艺术的奇妙。它的遗产不是某种具体样式的不朽,而是那些更普遍的价值向全世界的扩展”⑮。
2.崇拜:资本诱导下的工业非人格化
就现代设计的诞生而言,毋庸置疑,重新思索人与技术的关系是“机械美学”理念的重要出发点,也是形式服从功能和理性设计的基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是德意志工业同盟、乌尔姆学院或者包豪斯,他们创造性活动的旨趣和重心是设计新产品,他们所关心的重点是应用技术发明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新的智识或哲学体系的创造性发现或者发明,并不是他们必然的责任。因而,当技术在美国受到狂热追捧时,人们对设计的思索便偏离了理性的轨道,在机器狂潮和资本的引诱下,开始了对技术的崇拜,进而在设计中滥用技术,人性之光却在这里退缩了。
美国设计的目标似乎更加明确——更关注设计产业及其产能的覆盖率、可用性以及通用性。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了销售积压的产品获取利润,设计成为企业避免淘汰的制胜武器。
1880年间,一位叫泰勒的美国工程师热衷于研究工作流程优化和科学化管理。他认为企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少非必要的环节,将每一环节所需的操作时间控制在最小值,统一劳动姿势与操作方法,实现人与机器的最大程度整合。⑯然而,工业生产的流水线虽然创造了劳动效率的奇迹,但却侵犯了人性。现代有研究证明,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作业作为典型的单调静力作业主要依靠肌肉的等长性收缩以施力或维持一定体位,很容易产生隔离感、疲劳感,如头痛、头晕,肌肉酸痛,当工人感受到极大工作压力时,机体处于较低的生理健康水平,两者交互作用导致工人自我灵活性降低、自我刻板性增强,引发工人对自我现状的不满、偏执和躯体化极易产生⑰。在资本驱使下,原本就晦涩不明的艺术之光在设计中更加萎靡,技术如脱缰的野马,它凌驾于人之上,包豪斯致力于弥合的设计与制造的缝隙,再度被割裂,一度得到改善了的工业非人格化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再次退化,人连获得等同于机器的“地位”都不再可能。
风靡一时的“流线型”设计则体现了人们对技术的疯狂崇拜。美国著名工业设计师雷蒙德·罗维(RaymondLoewy,1893—1986)于1948年设计了流线型的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此后,流线型被人们使用在各种各样的产品上。那时,设计师们以流线型为设计宗旨,因而出现很多罔顾使用功能的流线型产品——流线型的冰箱顶盖,甚至有棺材商要求设计师为他设计流线型的棺材。然而,这种以形式代替功能的观点,实则是对功能和审美相结合原则的否定,“机械美学”所倡导的形式和功能的和谐统一,又一次被打破。对于流线型的冰箱顶盖,就有妇女诉苦说:“流线型的冰箱上面,什么东西也不能放。”
另外一方面,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日新月异的技术成为推陈出新的理由,不断更换产品以追求时尚成为最大卖点,“计划废止制”将其推向最高峰。
“计划废止制”起源于美国福特和通用两大汽车巨头的竞争。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流水线将汽车这种奢侈品从手工技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通用汽车公司为了改变福特垄断市场的局面,有意识地推行“计划废止制”——在设计新车时,有计划地考虑以后几年不断更换部分设计,使汽车最少每2年有一次小的变化,每3至4年有一次大的变化,造成有计划的“式样”老化过程。“计划废止制”从功能、款式和质量三个方面以人为方式有计划地迫使商品在短期内失效,造成消费者心理老化,并促使消费者不断更新、购买新的产品。⑱
3.回避:一切皆游戏的精英立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对技术开始倾向于怀疑、失落。这时候涌现出了大量的激进派非暴力团体,他们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反对核能、反对美国在欧洲设立导弹发射架。这种技术悲观思潮对设计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意大利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设计师,把设计当作表达意识形态、弘扬个性和直击社会的手段,他们以刺激、新奇的设计来表达他们的设计观点,非正统的风格反对正统的国际主义设计、反对现代主义风格。在这种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兴起的具有强烈反叛意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乌托邦运动,被笼统称为“反设计运动”。
与现代主义设计所倡导的理解机器之美,反对装饰以节省额外开支,让大众都享有设计产品的理念不同,后现代主义则恢复装饰性,无论建筑设计师或者产品设计师,都高度强调装饰性。娱乐是其典型的特征,一切都可以是后现代主义戏谑、调侃的对象,人们力图解构现代主义的理性,主张以“游戏的心态”来处理作品,强调设计对感性精神价值的追求多于对理性价值的追求。“机械美学”为“高科技”风格所取代,设计师采用最新的材料,以夸张、暴露的手法塑造产品的形象,以图达到娱乐和戏谑的效果,产品内部的部件、机械组织被充分暴露,以表现高科技时代的“机械美”“时代美”“精确美”。⑲现代主义设计试图创造高质量的、大众能够买得起的产品的理念被嘲笑和反对,后现代主义设计故意采取了一种精英化的立场:批量产品是不真诚的,要由少数人来生产个性化、手工制造的昂贵产品,卖给有钱的艺术鉴赏家群体。这种对现代大批量化生产技术的强烈反感与19世纪的工艺美术运动如出一辙。
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虽然在20世纪下半叶的设计界盛行,但却仍然距离大众生活很远。生活中“现代主义”的产品更加普及,这说明功能主义的确具有很高的民主性,恰当利用技术,会带来的物质生活提高,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尽管后现代主义设计在大众中的影响并不深远,但因其娱乐至上的理念在设计界被奉为时尚,因而对人与技术关系的严肃讨论在设计界无法进行。
三、启示:以主观能动行为融合智识和想象力
纵观现代设计的发展史,近代科学注重实践,而实践维度的实验技能、实验工具和实验理念都从回归自然的劳作和技能中产生,亲近自然可谓是近代科学的源泉。早期的设计者脱胎于建筑、珠宝设计等具有美学素养和艺术追求的工匠阶层。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亲近自然”之风的洗礼,面对机械化时代人地位的降低,自发的进行理性思索,这也是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原因,也启发欧洲出现了“机械之美”这种设计上的哲学思考成果。然而,当科学飞速前进,并带来了技术革命时,尽管现代设计曾试图理解机器,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但这种尝试却为技术狂潮所淹没。随着技术的愈发强大,人已无法通过设计来驾驭这种“力量的科学”,反而是技术以设计来驱动人。及至后现代时期,娱乐和戏谑让设计的理性思索无法继续。毋庸置疑,不管是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时期还是后现代主义设计时期,人们都意识到了技术的负面影响。但是,他们的旨趣和重心却是回避技术,这并不能阻止现代设计一步步沦为技术自主性发展的工具,对于使人把握技术的物性功能,发展和完善人与技术的新制度并无裨益。在这场博弈中,回避技术的艺术作品只能是少数人的“玩物”,而缺少艺术的技术成果则沦为趋利的工具。
然而,技术与艺术并非天然分离,它们曾同源而混沌一体,这二者在希腊时期共用一个词——techne便是例证之一。只是随着历史的更迭演进,“艺”从形而下的“技术”涵义,逐步增添了精神内容与高度,走向形而上的心灵体验与审美。⑳探索出物之为美,便在于它即纯粹和本身,而不是其所附带的功利性的精神内涵。可以说,现代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包涵着人的主观能动行为,体现着人对“美”的认知,是人的智识和想象力二者互动并自由活动的结果。
现代设计将原本混沌一体,而后又各自独立认同的技术与艺术再次纳入同一视域。如何在经历了技术的张扬独立、个性爆棚之后,使这二者重归更高级的理性,进入另一个新阶段的开放与融合状态,是现代设计本质所属的范畴。设计人才在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糅合人类智识的成果与自身的想象力时,能否对技术既不崇拜也不回避,同时以艺术所增添的精神与心灵的“净化”功用将对审美趣味的建构等功能卷入其中,从而使现代设计满足人本性中对“非常态”超越性的渴求和对纯粹之美的向往,这是设计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
观古思今,近年来,我国设计产品在功能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上都取得了进步,却在审美价值上出现倒退。这种局面与工艺美术运动之前的局面颇有几分相似,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文化差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民族完整的自我审美素养。正因如此,设计更应发挥其唤醒人们对美的意识的作用,让艺术所具有的“使得人们突然跳出日常生活与世俗现实,陌生化的关照日复一日、习以为常的经验,发现现实的崇高或丑陋,壮美或荒诞,伟大或卑微。当人们从停顿于艺术的那一刻走出再回到现实中时,现实在人们心中已经得到升华,人们便也可以从更高的视野,以更从容的心态来观照现实”㉑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显现,而唯有融入日常生活,技术社会的民主性才能在设计中成为显性因素。从而完成社会成员整体心智的开启、审美的提升、人格的完整。面对技术社会的诸多问题,若不想设计产品最终沦为技术奴役人类的工具,设计人才的培养便应该攫取艺术的上行之道,在理念建设构建上探求纯粹和本身,并使得设计人才自觉将这种探求融入到日常生活产品的设计理念中去。
注释:
①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8-69页。
② [美]M.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26页。
③ Proctor.R.N.Value-Free Science Is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3.
④ 韩彩英:《亲近自然:工匠实践的知识分子与实验主义的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5期。
⑤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9页。
⑥⑦ [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早期铁路时代1820-1850年(第一分册)》,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2页。
⑧⑨ [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225、121页。
⑩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⑪⑬ Lewis Mumford.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Boston: Mariner Books,p.298,pp.283-284.
⑫ [瑞士]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陈志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⑭ 滕晓铂:《伦理VS.审美:基于功能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设计批评》,《装饰》,2012年第2期。
⑮ [美]尼古拉斯·福克斯·韦伯:《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郑炘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⑯ 李砚祖、张黎:《实用与民主的技术崇拜: 20世纪美国设计的风格化与国家身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⑰ 林秋红、周静东、范远玉:《某蓄电池生产流水线作业工人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的调查》,《职业与健康》,2008年第23期。
⑱ [美]大卫·瑞兹曼:《现代设计史》,王栩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7页。
⑲ 彭澎:《设计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⑳ 刘俊:《论传媒艺术的科技性》,《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
㉑ 刘俊:《论传媒艺术的媒介性》,《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作者卢渊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詹鹏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