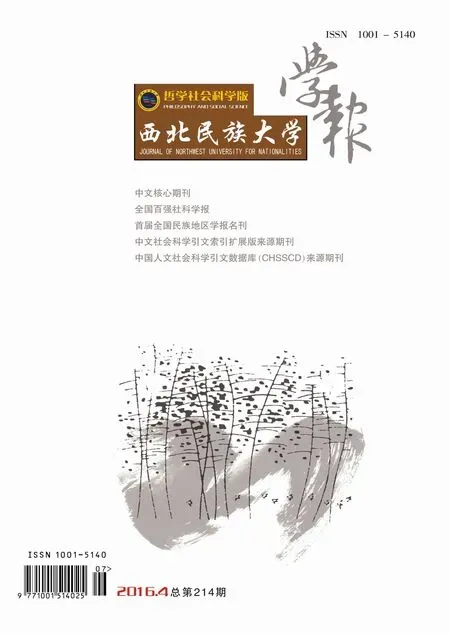代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2016-02-19胡岩涛
胡岩涛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0069)
代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胡岩涛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0069)
[摘要]唐代宗时期,唐廷在对待吐蕃入侵的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遂使吐蕃开始大规模进攻唐朝。广德、永泰年间,吐蕃数次进犯关陇地区,规模巨大,来势凶猛,让唐军难以招架,京都长安曾经一度沦陷。大历年间,吐蕃在关陇地区的攻势依然十分猛烈,而唐军在长期的战争中抗击能力也逐渐增强。纵观代宗朝的唐蕃关陇战争,可以说总体势态是吐蕃进攻,唐朝防御。为捍卫社稷,保卫京都,唐朝在与吐蕃交战中不仅重新组建西北边兵,继续实行防秋制度,而且还加强京都西北部军事要地的防御,同时又针对吐蕃骑兵特点采取闭城拒战、以守为攻的办法,逐渐在长安西北部构建起新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吐蕃进攻长安的步伐。
[关键词]代宗朝;唐蕃战争;关陇地区;京都长安;军事防御体系
唐朝与吐蕃是东亚地区两个强大的政权,相接壤的领土包括安西、河西、陇右、剑南四道。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为戡平内乱,迫不得已“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1],遂导致西北边防守备薄弱。吐蕃趁唐危机乘虚而入,于是唐蕃关系发生了强弱易位的历史性颠倒。至德元载(756年)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2];至德二载(757年)吐蕃陷西平;乾元元年(758年)吐蕃陷河源军;上元元年(760年)吐蕃陷廓州……唐朝为集中力量对付叛乱,以牺牲金帛赋税和被迫承认吐蕃占领土地的事实为代价,曾让吐蕃一度暂时停止东侵。彼时,吐蕃正值乞黎苏笼猎赞执政,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志在开疆拓土,随着唐朝西北防御体系全线崩溃,吐蕃继续东扩实为历史之必然。
目前,对唐蕃关系的研究具体涉及到关陇战争的,学术界一般集中在防秋制度的实施、德宗朝的御边措施以及京西北诸藩镇等方面,关于代宗朝关陇战争情况则很少详细涉及。故此,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关陇战争系统研究,重点对大历年间京畿关内道战况和唐朝构建京都防御体系的措施进行论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广德、永泰年间唐蕃关陇战况与京都危殆
唐代宗即位后,安史叛军已是强弩之末,故唐廷开始严肃对待吐蕃入侵问题。代宗为人“宇量弘深,宽则能断”[3],他始终把李氏家族的社稷同唐朝的领疆、臣民统一联系在一起[4],对吐蕃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史载“冬末,唐廷皇帝崩,新君立,不愿再输帛绢,割土地,唐、蕃社稷失和。”*《吐蕃大事纪年》,虎年,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21页。吐蕃以占领的陇右为基地挥师东进,对唐朝发动全面进攻。
宝应元年(762年)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5]因兵力薄弱,唐朝在河湟的军事防线瞬间崩溃。
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寇陷泾州,刺史高晖叛附于吐蕃,充当向导[6]。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末,寇奉天、武功,京师戒严[7]。代宗急忙“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8]。“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9],“蕃军自司竹园渡渭,循南山而东”[10],唐军拒战失利,节节败退。丙子,代宗逃出长安;郭子仪收合散卒,退趋商州[11]戊寅,吐蕃攻入长安,高晖和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12],企图“扶立一个亲蕃政权,以合法地满足其割土、输绢帛的政治、经济要求”[13]。而后,吐蕃又“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萧然一空。”[14]
吐蕃这次入侵到长安沦陷的两年间,尽管关陇西部有贺兰山、屈吴山、陇山等高山大川,是唐朝京都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但在吐蕃大军面前因防守空虚,最后竟如摆设一般。从整体战局来看,吐蕃猛烈攻势,如同进入不设防之地,唐朝在强敌西来之际几乎毫无抵抗的能力。当此之时,安史之乱基本平定,渡尽劫波的唐廷如释重负,应该继续实行肃宗朝对吐蕃忍让和好的政策,想办法延缓吐蕃入侵,韬光养晦,恢复实力。虽然代宗朝君臣坚持不妥协的政治原则,全力组织抵抗的态度值得肯定,但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贸然与敌国恶化关系,不得不说是唐廷国防战略上的极大失误。李唐开国百年来长安首度被异族武装攻下,这不仅意味着唐廷完全丧失对周边部族的优势,更有可能导致中央权威下降,国家凝聚力松懈。
由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力据守长安,加之听闻唐朝大军集结准备收复长安,若在唐朝腹地坚守,吐蕃自知困难,遂逐渐退兵。这时射生将王甫又秘密纠结百名少年,夜里在朱雀街击鼓呐喊,让吐蕃更加惶恐不安,于庚寅全部退去[15]。需要指出的是,吐蕃并非退回国内,而是退到原、会、城、渭诸州安营扎寨[16]。经历这次进攻,“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17],正如白居易《西凉伎》中所描述,“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唐蕃双方军事对峙由安史之乱前河西、陇右、河湟一带推进到关中长安、泾州、邠州、凤翔一带。吐蕃在陇山徘徊,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动进攻,京都长安依然受到严重威胁。
广德二年(764年)八月,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将入寇,京师震骇[18]。唐廷急诏“子仪帅诸将出镇奉天”[19]。癸巳,吐蕃寇邠州,邠宁节度使白孝德败之于宜禄[20]。九月,辛亥,唐廷又“以郭子仪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以……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21]所谓“通和吐蕃使”,在名称上带有明显的和平色彩,可见唐朝似乎无力与吐蕃作正面抗争[22]。以故“冬十月丙寅,仆固怀恩引吐蕃二万寇邠州,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京师戒严。……子仪屯泾阳,蕃军挑战,子仪不出”[23]。白孝德统领安西、北庭行营,郭子仪统领朔方步骑,皆乃唐军精锐,尚且不敢阵战,一方面足证吐蕃锐不可挡[24];另一方面也说明唐朝在军事布防上准备不足,仓皇应战,且缺乏整体的战略指挥,只能被动挨打。幸亏此时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命令监军柏文达发兵五千,攻克了摧砂堡、灵武,又进攻灵州,以牺牲自身兵力而力保京师,迫使仆固怀恩调两千精锐相救[25]。*《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载“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怀恩闻之,自永寿遽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苏晋仁编、李加东知译《通鉴吐蕃史料全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48页;然《新唐书》卷6《代宗本纪》所载有所不同,“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及仆固怀恩战于灵州,败绩”。仆固既移师,二国兵也必随之转移[26],因之史书复载,“十一月乙未,吐蕃军溃,京师解严”[27]。
永泰元年三月(765年),吐蕃遣使请和,双方与盟于唐兴寺。唐将杨志烈主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以来很有一番作为,吐蕃于此年初请和,很有可能是抽出兵力对付河西唐军的指征,同时又是一种麻痹唐廷的手段[28]。果不其然,到了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项师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29]吐蕃这次进攻声势浩大,连营而进,又皆骑兵,京都防御形势又一次极其严峻。甲辰,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师震恐[30]。为了保卫长安,代宗甚至令高僧大德置百尺高做讲《仁王佛经》,祈祷上苍拯救大唐江山社稷,可见,当时唐廷面对入侵是多么的紧张。当然,唐廷也紧急调兵遣将,组织抵抗。“己酉,郭子仪自河中至,进屯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31]代宗亲自率领六军屯苑内,“庚戌,下诏亲征”[32]。丁巳,吐蕃已经在京畿道大肆抢掠[33],京都形势破不容缓。恰在此时,仆固怀恩暴病死于军中,而上苍似乎也在帮助唐朝,史载自丙午至甲寅,关中地区“平地水流”[34],“大雨不止,故虏不能进”[35]。此时郭子仪又“遣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会军”[36],*《旧唐书》卷120列传70《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52页载:是时,急召子仪自河中至,屯于泾阳,而虏骑已合。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虏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高昇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虏见而问:“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年远涉万里,翦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忽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谓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虏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虏初疑,持满注矢以待之。子仪以数十骑徐出,免胄而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罗锦,欢言如初。子仪说回纥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国,无负而至,是无亲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马满野,长数百里,是谓天赐,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举,与我继好而凯旋,不亦善乎!”准备联合进攻吐蕃。吐蕃知其谋,是夜奔退。回纥与元光追之,子仪大军继其后,大破吐蕃十余万于灵武台西原[37],十月辛巳,京师解严[38],长安才转危为安。
二、大历年间的唐蕃关陇战况与长安防御战
大历二年(767年)九月,甲寅,吐蕃寇灵州,进寇邠州,郭子仪率兵三万,自河中镇泾州,长安再次戒严[39]。冬,十月,戊寅,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破吐蕃于灵州城下,斩首两千余级;吐蕃引去[40]。(《旧唐书》载:“灵州奏破吐蕃两万,京师解严。”[41])唐军虽守住长安,却在明年招来吐蕃更大规模的进攻。
大历三年(768年)八月,“壬戌,吐蕃十万寇灵武”[42],刚刚平静的关中又一次紧张起来。丁卯,吐蕃寇邠州,京师戒严[43]。尽管在“戊辰,邠宁节度使马璘破吐蕃二万于邠州”[44],但长安的军事压力依然巨大。九月壬申,郭子仪自河中移奉天[45]。奉天在长安西北,是通往京都道冲要处,奉天陷落,吐蕃便会进攻咸阳,顺着渭水可发起对长安的攻击,郭子仪以五万兵力[46]屯居于此,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壬辰,灵州将白元光破吐蕃二万于灵武。戊戌,灵武奏破吐蕃六万。”[47]此时,属于凤翔节度使的唐将李晟又率千人,“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48],迫使吐蕃“释灵州之围而去”[49]。吐蕃撤退后,唐廷“百僚称贺,京师解严”[50]。为了更有效的防止吐蕃对长安再一次冲击,宰相元载认为,“吐蕃连年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51],遂与郭子仪商议,让马璘镇守泾州,但仍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由此,安西、北庭行营移镇泾州。郭子仪以朔方军镇守邠州,以都虞侯段秀实知邠州留后[52]。这样就使得邠宁为朔方军的主力阵地。邠州“泾水北绕,邠岩南峙,依山为城,地势雄壮……以遏寇冲,盖厚泾原之形援,固畿辅之藩冲,州实南北襟要也”[53],是守护长安的军事战略要地。十二月,代宗“以吐蕃岁犯西疆,增修镇守”[54]为名,将御蕃防线由邠州移到泾州,可见泾、邠二州是遏制吐蕃进攻长安的重要据点。
大历四年(769年)九月,吐蕃寇灵州,被朔方留后常谦光击退[55];十月,吐蕃寇鸣沙,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浑瑊帅五千精兵救灵州,自己亲自扎驻庆州,吐蕃退却[56]。灵州本为唐军精锐朔方军大本营,若被攻陷,唐军不仅损失惨重,在战略上也会处在更加被动的局面。吐蕃以此可兵临泾州,直接威胁长安。
从大历二年至四年,吐蕃两度逼近长安均被唐军击退。唐朝面对吐蕃的进攻不再像广德、永泰年间那般狼狈不堪,甚至还能够做到主动出击或是有针对性的防御。经过安史之乱创伤的唐朝虽元气大伤,但依然有实力同西蕃抗衡。同时也可看出唐军在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抗击能力是逐渐增强的。
大历六年(771年)二月,唐将李抱玉进言朝廷:“凡所掌之兵,当自训练。今自河、陇达于扶、文,绵亘二千余里,扶御至难。若吐蕃道岷、陇俱下,臣保固汧、陇则不救梁、岷,进兵扶、文则寇逼关辅,首尾不赡,进退无从。愿更择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专备陇坻。”[57]代宗同意李抱玉的请求,让他在河、陇御敌,这样又增强了长安防御吐蕃的力量。可以说,唐廷已经在认真构建京都防御体系,虽然这个过程不时有吐蕃的破坏,但成效还是显而易见的,今后吐蕃的进攻将会证明这一断论。
大历七年(772年)四月,吐蕃五千骑至灵州,寻退[58]。这似乎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吐蕃的军事意图是想南上剪除唐军在灵武的军事力量,为进攻泾、邠二州做准备。
大历八年(773年)八月,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践秋稼而去[59]。十月,吐蕃众十万寇泾、邠二州[60]。郭子仪遣朔方兵马使浑瑊将骑步五千拒之[61],与泾原节度使马璘前后接应,形成犄角之势[62]。甲申,双方战于宜禄,浑瑊登黄萯原远眺吐蕃阵势,命令部队占据险要地形,采取守势战术,行布列拒马枪,防备战马奔突[63]。宿将史抗、温儒雅刚愎自用,不服从浑瑊指挥,尽撤拒马,列骑阵战,却被吐蕃军反扑,唐军大败,士卒死者七八,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64]。甲子,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又遭惨败。马璘被吐蕃拦隔,逮暮未还,泾原兵马使焦令谌等与败卒争门而入[65]。有人劝行军司马段秀实登城拒守,段秀实回答道:“大帅未知所在,当前击虏,岂得苟自全乎!”[66]于是找见焦令谌等,训斥“军法,失大将,麾下皆死。诸君忘其死邪!”[67]焦令谌等惶惧拜请命。段秀实于是将城中未战者全部出阵,陈于东原,并且搜罗散兵游勇,做出拼死准备作战的姿态[68]。“吐蕃畏之,稍却。”[69]都知马使李晟率领部下与吐蕃全力交战,“既夜,璘乃得还。”[70]战后,郭子仪召集诸将商议破敌之法,要派浑瑊驻守朝那(甘肃平凉西北)。盐州刺史李国臣认为,“虏乘胜必犯郊畿,我掎其后,虏必返顾。”[71]郭子仪采纳其意见,李国臣带领军队奔赴秦原,鸣鼓而西[72]。吐蕃听闻后,到达百城的军队开始往回撤[73]。浑瑊在关隘要地阻击他们,解救了大批被俘民众,马璘也在潘原袭击吐蕃,迫使吐蕃再次退却[74]。浑瑊、马璘、郭子仪等竭尽全力才勉强遏制住吐蕃攻势,由此也暴露出唐军正面作战不敌吐蕃,这其中的原因便是河西、陇右等牧马产地尽被吐蕃所占而导致战马不足。是岁十一月,唐廷一次向回纥购马六千匹[75]。
大历十年(775年)九月壬子,吐蕃寇临泾,癸丑,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76]。丙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于义宁[77]。吐蕃又寇泾州,但被马璘在百里城击退[78]。
大历十一年(776年)九月,吐蕃寇石门,入长泽川[79]。马璘组织兵力抵抗,吐蕃不久撤退。
大历十二年(777年)九月,吐蕃将八万兵马驻扎在原州北长泽监一带,己巳时攻取方渠,又进攻拔谷[80];郭子仪派副将李怀光前去驰援,吐蕃不敌而退,但在庚午时转攻坊州。十月,吐蕃进犯盐州、夏州,又南下进犯长武城(宜禄县内);郭子仪派李怀光前去抵抗,拒却之[81]。看来吐蕃的军事意图很明确,先占领关内道北部重镇,然后迅速南下进攻长安。唐军在防御上拆东补西十分被动。
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己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夺填汉、御史、尚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82]。夏,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七月,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朔方都虞侯李怀光击却之;八月,已亥,吐蕃二万众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诏郭子仪、朱与段秀实共却之[83]。虽然唐军作战英勇,但是战争的主动权仍掌握在吐蕃手中。
从大历十年至十三年,吐蕃分别进攻唐朝剑南道和关内道(包括京畿道),但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剑南道的挫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关陇地区的进攻。不能否认的是从战争整体势态看,吐蕃在关陇地区的进攻远不如以前那样凌厉,但依然处在攻势而唐朝处在守势,京都长安防御形势还是十分严峻。唐朝在战争中似乎逐渐摸清吐蕃的进攻策略,防御体系不断强化。当然,这与吐蕃在西南战场屡次失利和国内政治斗争分散精力以及唐朝实行防秋制度等有关。代宗朝君臣齐心协力,面对吐蕃的威胁积极应对。由于在和平谈判中坚定地维护不割土、不弃民、不输帛的政治原则,在战备上全力组织抵抗,吐蕃势力基本上被遏制在泾、原以西[84]。
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重点进攻巴蜀地区,同时也派出使臣请和,但往往“玉帛才至于上国,烽燧已及于近郊”[85],唐蕃双方依然处在战争状态。
三、吐蕃进攻特点和唐朝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纵观代宗朝吐蕃进攻唐之腹地势态可以发现,吐蕃在作战过程中目的性十分明确,机动性极强,行兵布阵迅速,为唐朝前所未有之劲敌。
通过关陇战争不难总结出吐蕃进攻特点,第一,吐蕃作战时善于运用唐人向导。广德年间,吐蕃之所以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速攻陷长安,除了唐朝因安史之乱而西北守备空虚之外,使用大量降将充当向导也是关键因素。“吐蕃陷泾州,虏刺史高晖,晖遂与蕃军为乡导,引贼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济渭而南,缘山而东。”[86]这说明吐蕃取胜与降将引狼入室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唐朝虽然饱受内讧重创,但极盛而衰的迹象不可能在几年内显现出来,况且安史之乱已近尾声,唐廷对吐蕃的态度逐渐强硬也表明唐朝定在不久的将来会集中力量对付吐蕃,而降将因熟悉唐朝交通情况,遂使吐蕃轻易取得胜利。此外,还有仆固怀恩曾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奴剌等部总共数十万人来犯,迫使京都几次戒严。史载,“怀恩逆命三年,再犯顺,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87]。第二,吐蕃善于集中兵力聚众专攻一地。这种作战特点可以在数量上取得优势,以多胜少,以强胜弱。如广德元年,吐蕃联合吐谷浑、党项兵20万寇武功、盩厔等地。永泰元年,吐蕃10万众寇奉天、醴泉等县。大历三年,吐蕃10万寇灵武等,大量兵马浩浩荡荡,让唐军难以招架。第三,吐蕃攻城略地以骑兵为主,战速如闪电一般。骑兵在冷兵器时代机动性迅速,攻击力极强,适合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作战。史载吐蕃骑兵“人马俱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所能伤也”[88]。可见,这为重骑兵装束是以步兵为主的农耕王朝远不能相及的。如大历二年,吐蕃游骑至潘园、宜禄,迫使郭子仪三万兵马镇守泾阳,京师戒严[89]。第四,吐蕃季节性军事行动明显,破坏性十分强烈。“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90],故吐蕃在关陇进攻多集中在夏末至冬初这段时间。吐蕃大军的活动对关中社会经济的破坏性是非常巨大的。如永泰元年,吐蕃军队所到之地,“大掠居人,男女数万计,焚庐舍而去”[91],“禾稼殆尽”[92],“其所掠之财不可胜载,马牛杂畜,长数百里,弥漫在野。”[93]大历八年秋,“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蹂践我禾稼而去”[94],“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95],关陇一片狼藉。
唐朝在与吐蕃长期的交战中必然会逐渐摸清吐蕃的进攻特点,因此在关陇西北要地有针对性的进行军事防御。这个过程不时受到吐蕃的袭击而前功尽弃,只能在连续的战斗中逐步完成,所以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极为艰难。
(一)重建西北边兵,实行防秋制度
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防御吐蕃、解决西患成为唐廷国防的头等大事。唐朝边防形势已极为严峻,吐蕃在陇山以西虎视眈眈,随时都有进攻的可能,故决定了代宗朝边兵的重建防御属性与备御地位即遏制吐蕃东拓关内,保卫京都长安。唐廷重建的边兵包括边镇兵、神策军和关东戍卒[96]。需要指出的是,唐朝防御吐蕃的策略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既要能够抵挡得住吐蕃对京都的冲击,又要借此时机削弱关东割据的藩镇,以此重新树立中央权威。
代宗将对付安史叛军的河西、陇右、安西、北庭、朔方等精锐陆续调回,驻扎在京西北军事要地。如河西、陇右兵屯凤翔,安西、北庭兵屯泾州,朔方兵屯邠州等地,并选用郭子仪、马璘、李怀光等得力将帅坐镇指挥。唐军在西起陇州,北至灵州、盐州、银州,南到坊州、邠州等地布有重兵,以拱卫京师[97]。神策禁军因在安史之乱时护驾有功而被皇帝信任,内乱结束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禁军镇之,皆有屯营。”[98]神策禁军是防御吐蕃的重要力量,唐廷也用其节制其他诸军,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吐蕃屡次大规模进犯,几乎都能长驱直入,从侧面也说明唐朝边防戍兵存在不足的缺陷。以朔方精锐为例,“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99];“臣(郭子仪)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100]唐廷限制朔方军固然有戒备之心,但吐蕃威胁严重,只能征调关东戍卒轮番到京西北防秋,补充兵员不足之问题。大历九年,代宗下诏:“四海之内,方协大宁,西戎无厌,独阻王命,不可忘战,尚劳边事。……每道岁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其岭南、浙东、浙西,亦合准例。”[101]关东戍卒实行三年轮番更替,衣粮由当道提供,显然暴露出唐廷财政窘状,亦有唐廷分割和抑制关东藩镇之意图。边镇兵、神策军和关东戍卒各成系统,指挥混乱,因此作战时“递相推倚,无敢谁何”,*《陆宣公奏议》卷3。导致多次抵抗失利。
(二)加强京都西北部军事要地防御
吐蕃关陇进攻的目标就是直取长安,志在使唐易君,以实现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关陇西北部是吐蕃攻唐之入口,要占领长安,必须要占据通往长安道路上的重要城镇、关隘。从广德到大历年间吐蕃在关陇地区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泾州、邠州、奉天、凤翔、宜禄、灵武、灵州等地是吐蕃经常攻掠之地,而这些要地正是拱卫长安的重要门户。因此,代宗期间重新组建盐灵、邠宁、凤翔、泾原等藩镇是唐朝建立京都防御体系的重中之重。
凤翔是西部防御吐蕃的中心,“当关中之心膂,为长安之右辅”[102],战略位置显赫,“陇关西阻,益门南扼”[103],素有“国之西门”之称。永泰元年正月,(唐廷)以李抱玉兼凤翔、陇右节度使,凤翔从此成为京西北重镇[104]。史载:“抱玉移镇凤翔,以汧阳被边,署奏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广二百余步,上连峻山,山与吐蕃相直,虏每入寇,皆出于此。燧乃按行险易,立石种树以塞之,下置二门,设篱橹,八日而功毕。”[105]凤翔镇兵始终保持在3万人以上[106],是抵抗吐蕃的精锐之一。泾原镇始建于大历三年十二月,建成后即“以犬戎浸,岁犯郊境,泾州最邻戎虏,乃诏璘移镇泾州,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泾原节度、泾州刺史。”[107]“泾原镇实际只辖泾州,它与吐蕃军队对峙于原州。虽然泾州在地形上不利于防守,但它与后面朔方主力所在的邠宁镇组成了向西的双层防御。……泾原镇的建立,直接堵住了吐蕃常用的入侵道路。”[108]泾原镇边防建设包括原州、连云堡、平凉、良原、临泾等地,北与盐灵相连,南与凤翔相结,大历年间有兵3万余人[109];邠宁镇是防御吐蕃,保卫京都的头号大镇,为朔方军主力驻扎地,主体为邠、宁、庆三州,“其南与京畿相连,是京西北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西北与吐蕃对峙于原州、庆州。西面是泾原镇的后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10]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邠宁镇兵力不足,唐朝调安西军四镇行营节度马璘的军队进驻邠宁,兵力达一万人,邠宁镇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111]。大历年间,邠宁防御的重点是在邠、宁交界的宜禄县[112]。史载:“(周)智光平,诏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军,郭子仪领之;子仪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便于宜禄县防秋。”[113]邠宁镇在重要关隘设有重兵,全镇兵力常年保持在3至5万[114]。邠宁镇的驻军不仅是镇兵,还有关东戍卒和神策军,在指挥上各成系统,颇有特色;盐灵是京西北藩镇中资历最老的镇[115],是京都北部阻挡吐蕃南下的重要军事基地。盐灵镇中的灵州素有“国之北门”之称,与其旁的灵武互为犄角,“西御犬戎,北虞猃狁”[116]。永泰元年闰十月,“子仪以灵武初复,百姓凋敝,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117]戊申,代宗任命户部侍郎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路嗣恭披荆斩棘,设立节度使军府,严厉贯彻军令。灵州、灵武的得失关系到泾州、邠州的安危,也直接影响长安,如大历二年、三年,因吐蕃围攻灵州、灵武,迫使长安两次戒严。盐州是盐灵镇防御吐蕃的要地之一,“地当要冲,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捍王畿”[118],是唐蕃争夺的重要对象,受到双方重视。此外,还有鄜坊、振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援其他军镇的作用。
(三)闭城拒战以守为攻
吐蕃在关陇数次凌厉进攻,唐朝虽然全力组织抵抗,但只能算是勉强挡住吐蕃攻下长安,这其中与吐蕃善于使用骑兵有莫大的关系。众所周知,骑兵在古代军队的种类中相当于现代军事装备中的重型武器,它的局限性是只能在开阔的地方作战才能增加胜算的筹码,而关中平原城镇密集,攻打具有城墙的城市却不占太多优势。如果骑兵非要攻城不可,那么也只好离开战马,像步兵那样在弓矢和投掷机械的掩护下攀登城墙、挖掘地道,将城堡攻陷[119]。广德元年,吐蕃攻下长安,但面对长安犹如棋盘,密密麻麻的巷道,骑兵的作用发挥甚少,当听闻唐朝大军将至,自知无力拒守,只能仓皇撤退。“十一月,吐蕃还至凤翔,节度使孙志直闭城拒守,吐蕃围之数日。镇西节度使马璘闻车驾幸陕,将精骑千余自河西赴难;转斗至凤翔,值吐蕃围城,璘帅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战,单骑先士卒奋击,俘斩千计而归。”[120]可见,此时吐蕃骑兵优势在攻城时发挥不出来,只能围之数日。同样,广德二年,吐蕃10万入寇至邠州,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至泾阳,副元帅郭子仪紧闭城门,任凭吐蕃挑战就是不出。唐廷自知经受安史之乱重创之后,实力今非昔比,在城镇采取拒战的方式,实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121]的方针,闭城拒战,以守为攻,拖延吐蕃消耗自身力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实为明智之举。
代宗朝唐蕃关陇战争总体势态是吐蕃进攻、唐朝防御,双方在京都长安西北部展开将近17年的拉锯战,长安曾经几度告急,可见防御形势极其严峻。吐蕃的行动迹象表明,志在攻入长安另立新君,满足其合法的割土地、输绢帛、弃子民的政治经济要求[122]。广德元年到大历九年,吐蕃的进攻让唐朝一时难以招架,而九年之后吐蕃对唐朝的进攻远不如之前那般凌厉,唐朝的抵抗力有所加强。在长期的战争中,唐军基本掌握了吐蕃的进攻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重建西北边兵,实行防秋制度,不仅弥补了关中兵员不足之问题,也加强了唐廷对军队的控制;在京都西北部军事要地构建京都防御体系是唐军作战的重中之重,有效阻挡了吐蕃对长安的冲击,巩固了唐朝社稷;闭城拒战、以守为攻则针对吐蕃骑兵之优势,适合长期的军事对抗。吐蕃自身实力有所消耗,无功而返,唐军再抓住战机从背后偷袭,打击吐蕃嚣张气焰。代宗朝君臣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郭子仪、李怀光、马璘、浑瑊、段秀实等将领的坚决抵抗,基本上将吐蕃遏制在泾、原以西。
参考文献:
[1][3][5][10][11][17][23][31][32][33][34][36][37][38][39][41][42][43][44][45][47][50][54][85][86][87][94][99][100][101][105][107][113][116][118][121]刘昫.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2000.3562-3563,181,185,185,185,3563,187,189,189,189,189,3252,3252,190,194,195,196,196,196,197,197,197,3567,3583,2347,2371,3567,2353,2353,206,2510,2764,2519,2353,2665,2353.
[2][8][9][12][14][15][16][18][19][21][25][29][30][35][40][46][48][49][51][52][55][56][57][58][59][60][61][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6][77][78][79][80][81][82][83][89][92][93][95][117][120]苏晋仁.李加东知译.通鉴吐蕃史料全 译[Z].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44,44,44,45,45,46,47,47,47,48,48,49-50,50,51,53,54,54,54,54,54,54,55,55,55,55,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7-58,58,58,58,58,58,59,59,53,51,52,56,52,47.
[4][13][22][24][26][28][75][84][122]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114,117,118,118,118,119,123,125,117.
[6][7][20][27][90][9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169,169,170,171,6098,1334.
[53][102][10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2][97][111]邵明华.安史之乱后唐朝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与巩固[D].山东大学,2005.23,15,15.
[88]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1]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6]曾超.试论唐代中期边兵的重建、命名及影响[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1.
[104][106][108][109][110][112][115]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6):74,74,75,75-76,77,77,80.
[114]吕学良.唐代邠宁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29.
[119]卢林.战争史纲要[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44.
(责任编辑贺卫光责任校对肇英杰)
[收稿日期]2016-05-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军事考古学研究”(13ZD102);“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14ZDB031)
[作者简介]胡岩涛(1990—),男,山东蓬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民族关系史、中国考古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4-00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