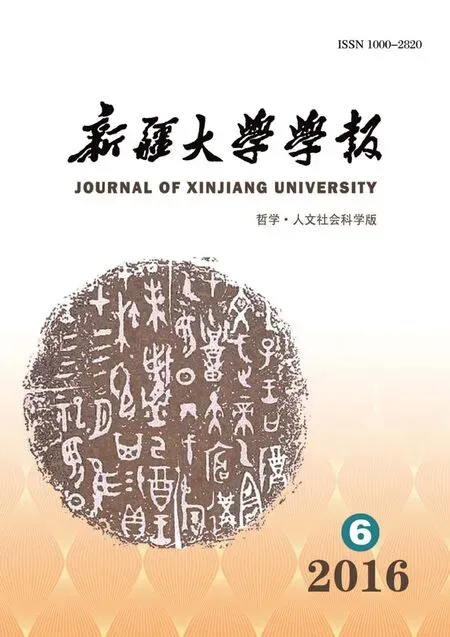论地域文学中《庄子》的镜像书写
——以明初文学为例*
2016-02-18白宪娟
白宪娟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明初文学,着重指的是明代洪武、永乐年间的文学。此期文学虽时间短暂,但异彩纷呈,并对明代中后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元明之际的战乱割据阻隔了文化的交流融合,却加强了文化的地域色彩。元末文坛遂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群落,此种特点一直延续到明朝建立初年。在明初最有影响力的地域文学流派是越诗派、吴诗派、江右诗派和闽诗派。除闽诗派随后逐渐消息,其余三者对明代文学均产生重要影响。江右诗派变身为台阁文学,左右明代文坛百余年。明初吴中四杰之后有吴中四才子、王世贞等人。越派则出现了徐渭等在明代文学上力能扛鼎的非凡人物。在明初,四个诗派特色鲜明。越派、江右诗派文人在为人、为文、事功方面崇尚儒学。吴派、闽派则看重个体生命,文学创作多有私人性话语。虽然四者大体上可分为两大派,但其间仍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庄子》在其中的呈现,有着不同特色。文章意图借明初这一特定时空中的,对之后明代文坛有重要影响的四大文学流派与《庄子》关系的考察,以便在一种共时态中览观《庄子》的历时性存在状态,并预览明代文学中的《庄子》存在状况,进一步深刻体味《庄子》生命哲学和《庄子》文本的永恒魅力。同时,在明初士人对《庄子》的态度中把握明初士人的真实心态。
一、越派文人与《庄子》
明代越地文人所秉承的是起自南宋的浙东事功之学,相较于朱熹理学、陆王心学,其特点是事功文学兼重。故而越地文人在投身政治的同时还享有文坛盛名。刘基、宋濂、章溢、叶琛、方孝孺、王祎、苏伯衡等人是此地文人的杰出代表,所以便有了“国初闻人,率由越产”[1]的说法。在事功之学的影响下,越地文人大多主张经世致用,坚持儒家诗教观。因此,在对《庄子》的认识上呈现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标准:保留性地认可《庄子》思想,充分肯定《庄子》的艺术成就。越地文人的《庄子》接受主要呈现以下特色:
首先,越地文人立足儒家立场去审视庄子思想。其表现有三:其一,激烈反对庄子诋侮圣人的言论。如宋濂在其《诸子辩》中把庄子定性为“古之狂者”(《诸子辩》,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因为庄子对孔子“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诸子辩》,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把庄子学说定性为惑乱世人的离经叛道之说,终将导致“礼义陵迟,彝伦斁败”,“踣人之家国”(《诸子辩》,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其二,越地文人以其事功观念批判庄子无用自适的思想。如在《庄子》中作为精神逍遥的象征物——无用大樗,在凌云翰(钱塘人)的笔下成了空老山中,可堪嘲笑的对象。其《画(七首)》其五言“长松落落千丈,大厦渠渠万间。应笑樗材拥肿,等闲空老深山。”(《画》其五,卷一,四库全书本)其三,从儒学观点去解读庄子其人。如宋濂在《七儒解》中认为儒有多种形态,“有游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旷达之儒,有智数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七儒解》,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庄周、列御寇属于旷达之儒。在诸儒种,只有道德之儒孔子方为万世之宗,其他儒者均以缺陷“不可以入道”(《七儒解》,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从宋濂试图将庄子纳入儒者圈子的努力来看,宋濂对庄子思想有某种程度的认可。
其次,在文学层面对《庄子》的高度评价及对《庄子》文学营养的汲取化用。一者,对《庄子》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如宋濂在《诸子辨》中,一方面有保留地评价《庄子》的思想,一方面对《庄子》的文辞做出高度认可,其言:“其文辞汪洋凌厉,若乘日月骑风云,下上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诸子辩》,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再如被人誉为醇儒的方孝孺,对《庄子》文章推崇备至。他认为《庄子》是“神于文者”(《苏太史文集序》,卷十二,四库全书本),“以文学高天下”(《畸亭记》,卷十五,四库全书本),具有“宏博而放肆”(《张彦辉文集序》,卷十二,四库全书本)、“放荡纵恣”(《苏太史文集序》,卷十二,四库全书本)的特点。并探讨了《庄子》文章之所以呈现宏肆风格的原因:“求道而不得,从而以言穷之。虽欲简而不可致耳。”(《送平元亮赵士贤归省序》,卷十四,四库全书本)方孝孺是完全将庄子放在一个成功文学家而非思想家的位置上加以审视的,庄子、李白、苏轼的诗文风格:纵横捭阖、自热而然,成为方孝孺艺术追求的准的。二者,创作实践中对《庄子》典故、字词、语句、文风、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吸收、借鉴。如王炜《心迹双清亭记》中有一段话:“谓吾果有心乎?吾心泊然其犹太虚耳,止水耳。日月之明不能烛其微,鬼神之灵不能测其倪,虽吾亦不自知其主宰我者,此也。是可谓之有心乎?无心乎?谓吾果有迹乎?吾虽不能不与物接,而固未尝物于物也。当吾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物之始,而无所穷止,虽吾亦不自知所当止而止矣。是可谓之有迹乎?无迹乎?心与迹俱无矣。”(《心迹双清亭记》,卷八,四库全书本)这段文字化用了《庄子》中的《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逍遥游》等篇章的字词、语句,甚至思维方式。再如宋濂《萝山杂言(二十首)》之“君子之道与天地并运”“子不见婴儿乎”“至虚至灵者心视之无形”三则,对“道”“原”的探讨,以及贝琼《宇定轩记》对“天光”的描述都套用了《庄子》的用词和句式。越派文人还擅于寓言创作,出现了一批寓言作品集如刘基的《郁离子》,宋濂的《龙门子》、《燕书》、《寓言》,叶子奇的《草木子》等。刘基的寓言创作对《庄子》的借鉴、改造最具代表性。《庄子》中“狙公赋芋”“涸辙之鲋”等寓言被刘基编撰成《郁离子》中《瞽聩·术使》《玄豹·石羊先生》等寓言。在全书的结构布局上,《郁离子》借书末的《九难》一篇卒章明志的手法,极为类似《庄子》书末安排《天下》篇的结构用意。不过,一重政治理想的表达,一重学术思想的盘点而已。
二、吴中文人与《庄子》
吴中大致涵盖了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是李唐以来的人文之薮。唐代便有吴中四士,到了明代,吴中人文更是繁盛。前有袁凯、高启、张羽、杨基、徐贲,后有吴门四才子以及作为后七子首领之一的王世贞。明初吴中文人对《庄子》表现出极大认可,主要体现在吴中文人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自娱自适的个体生存态度和纯艺术化的文学观。
其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使吴人倾向隐居,耽于烟霞,视功名富贵如天际浮云,并以生死同一的达观态度消解了死亡带给生命的精神威胁。吴人的隐逸情怀颇为浓重,袁凯说“一听野人言,复起沧州愿”(《偕友人早出郊》,卷二,四库全书本);徐贲称“谢事返丘壑,退耕理田园。兹心获遂初,稍得洒中悁”(《闲居》,卷二,四库全书本);张羽言“寄谢沧洲人,予亦堪同调”(《立秋日早泛舟入郭》,卷一,四库全书本);杨基写道“此中真小隐,予亦久忘机”(《句曲秋日郊居杂兴》其十,卷七,四库全书本);高启的隐居情怀最为强烈,在《出郊抵东屯五首》其二、《东园种蔬》《练圻老人农隐》《晓睡》《喜家人至京》《京师苦寒》《陪客登陶丘》《倦寻芳·晓鸡》《摸鱼儿·自适》等诗词中屡屡表达归隐的愿望,并将隐居生活描绘得无比美好。隐而不出或渴望归隐,是中国士人的常见行为模式和心理追求。在隐逸的行为和心理中,传达的是中国士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以及精神上的洁身自好和精神自我提升的努力。士人隐逸在行为上源自上古隐士传统,在理论上则奠基于老庄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庄子与现实的对抗、不与当政者合作的行为和注重精神的净化提升的理论,坚挺了士人追求隐逸的腰杆。在古人那里,隐居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自然的亲近,乐于隐居的吴人的山水情怀也颇为浓重。如袁凯说“白鹭晴烟满平野,老夫于此最关情”(《沙边》,卷三,四库全书本);徐贲自傲于“泉石应同我有缘”(《三月廿三日重到蜀山》,卷六,四库全书本);杨基则愿意“归去匡山中,云松可娱老”(《送汇东宋处士》,卷一,四库全书本);高启则干脆说“夙负云水债”[2]207。吴人归隐田园山林,给肉体寻找到一个惬意的安身之地。在吴中文人归隐山林田园的集体性话语中,流露着庄子乐于隐居,与天地同乐、与万物为春的精神惬意。这样的精神惬意不造作,不逼仄,明快真实而又自然和美,没有吴人对《庄子》灵魂的彻悟是难以达到此种圆满地步的。
吴人在安放肉体的同时,也注意将精神从困境解脱出来,主要表现在对功名富贵和死亡困缚的超越。张羽说“世上浮名都莫爱”(《立春吴黄二友皆有作率尔同赋》,卷三,四库全书本),杨基是吴地文人中对功名富贵看得最透的人,他的诗歌中处处可见其对功名富贵转头空的述说,如“人生富贵等浮云”(《巢云为周孟基赋》,卷二,四库全书本)、“人生富贵等泡幻”(《赠许白云》,卷二,四库全书本)、“世上功名贱如土”(《渔樵问话图》,卷五,四库全书本)、“世上虚名一杯酒”(《舟抵南康望庐山》,卷五,四库全书本)。杨基对生死的达观在吴人中同样颇具代表性,如其言“生死固常理,勿为达士嗤”(《白门答高二聘君》,卷一,四库全书本)、“生死俱两忘”(《午窗坐睡甚适觉而有赋》,卷一,四库全书本)。杨基的话语集中代表了吴人旷达超越的生命情怀。对富贵功名和生死的参悟,是对生命困境的超脱和生命境界的升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庄子坐忘、外物等理念和生死常然、死生一体思想的承递。
其二,重视一己生命的自娱、自适。吴人看重个体生命,不复受家族荣誉、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之类外在义务的捆束,在读书、作诗、交游的个体生命的小天地中,吴人自得其乐。吴人以其生命观念的转变,带给其人生一份轻松自如,也为明初诗坛添上一抹飘逸洒脱之笔。如杨基乐于“携书坐深竹,自读自卷舒”(《秀野轩》,卷一,四库全书本);袁凯读书不为稻粱谋,甚至只是“读书不闻道,聊复自娱嬉”(《题东斋壁》,卷二,四库全书本);徐贲作诗自娱自乐,其言“夜静谁能到,诗成只自哦”(《夜坐池上有咏》,卷四,四库全书本);高启的自适自娱心态更为鲜明,其在《娄江吟稿序》中言“衡门茅屋之下,酒熟豕肥,从田夫野老相饮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适其适矣!”[2]893再如《青丘子歌》言“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2]434。在《昼睡甚适觉而有作》重,高启为其大白天睡懒觉大张名目称“我意在有适,宁顾朽木嗤”[2]272。在自娱、自适的生命态度中,吴中文人的生命个性得到高度张扬,这也是吴人彻底回归自我生命的高度表现。在吴人的自娱、自适观念中,庄子自适其适的思想及庄子哲学对个体审美化存在的强调起到了极大的涵养之功。
其三,痴迷于文学创作,并将诗歌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吴人对诗、对文学的痴迷与高度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实属不多见。吴人之所以能够专注于文学创作,并将文学作为生命寄托,将之从功利的诗教怪圈中解脱出来,除与诗人的癖好有关外,与吴地经济的发达,吴人观念的通脱开放不无关系。吴人爱诗,徐贲言“自喜吟身得自由,长寻酒伴与诗俦”(《将往吴兴徐行正以诗见送奉酬二首》,卷六,四库全书本);杨基说“浮名薄俗看俱幻,独有耽诗癖未除”(《春日白门写怀用高季迪韵》,卷八,四库全书本);最爱诗的,还要数高启,高启为自己是一名文人而自豪,《赠钱文则序》便是这种情感的流露。高启懒散不拘,但不辞“心苦为寻诗”[2]528。在进行诗歌创作时,高启殚精竭虑,喜怒哀乐都为诗歌所左右,甚至称即便遭遇极端困境也不放弃诗歌,其言“一事于此而不他,疲殚心神,搜刮物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有所得意,则歌吟蹈舞,举世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笃好,虽以之取祸,身罹困逐而不忍废”[2]906。在《青丘子歌》中,高启再次书写了对诗歌的痴迷:一切不挂心上,眼中唯有诗歌。其言“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2]434。对文学创作的痴狂,对诗歌地位、价值的高度重视,集中代表了吴人非功利的纯文学观,此种纯文学观延续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一派的艺术观念。而在艺术创作的痴狂之举和全身心的投入中,我们看到了庄子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的生命情调。
吴人诗文中不乏对《庄子》典故的运用,如高启有六十余首涉及《庄子》典故的诗歌,“畸人”“达生”“虚”“静”“灵府”等《庄子》语汇在高启的诗文中屡屡出现。其他诗人也不乏对《庄子》典故的借用,如杨基《皂角滩》称“牛刀惯熟中肯綮,郢斧神捷回锋棱”(《皂角滩》,卷三,四库全书本);袁凯《邹园十咏·钓矶》言“既寡羡鱼情,还闻濯缨唱”(《邹园十咏·钓矶》,卷二,四库全书本);徐贲《题葛仙翁移家图》说“暂将劲翮戢鷦鷃,蹑景追风岂能已”(《题葛仙翁移家图》,卷三,四库全书本);张羽在《寄吴隐君》中写道“颐性得天和,齐物同化先”(《寄吴隐君》,卷一,四库全书本)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吴人在生命气质上对庄子最高生命境界的逼近:飘逸洒脱,旷达超越;在美学精神上对庄子一派诗学观念的继承:摆脱功利,专注艺术,使诗歌获得独立发展。
三、闽中文人与《庄子》
洪武至永乐时期,福建出现了以尊唐相号召的地域性文人集团,其代表人物即所谓的闽中十子:王偁、林鸿、高棅、陈亮、王恭、王褒、郑定、周玄、唐泰、黄玄。相对于占据明初文坛大半江山的吴越文人而言,闽中诗派显得力量薄弱。但闽中诗派尊唐的主张却开启了之后明代诗歌的走向。永乐之后,随着闽中文人逐渐进入馆阁,福建文人偕同江西文人共同支撑起明代的台阁文学,闽中诗派也随之解体。闽派文人大多崇尚隐逸,适性逍遥,其诗歌关注的多是个体生活,诸如宴饮、山水、私人倡和之类的内容,其诗歌境界清雅飘逸。如林鸿生性倜傥潇洒,乐好山水泉石,不喜入仕,年仅40岁便自请致仕。倪桓评价其诗歌曰:“皆新奇俊逸。驰骋若骐骥,浩荡若波涛,清绝若雪山冰崖,皎洁若琼琚玉佩。择其优者,置之韦、柳、王、孟间,未易区别。”(倪桓《〈鸣盛集〉序》,四库全书本)再如陈亮、王恭、王偁等,或“不欲与世接”(林环《〈白云樵唱集〉序》,四库全书本),或累征不就。闽中文人隐逸恬淡的文化人格,使其易于在精神层面接近庄子。这一地区文人普遍关注的是《庄子》的全生哲学和精神自由的理念。在闽中诗派中,王偁与《庄子》的关系最为紧密。
王偁《虚舟集》明显带着《庄子》色彩的作品为《咏史》其一、其七,《感寓》其九、二十五、二十八,《习静山房》其一、二、三、四,《题畦乐处士成趣园》其一、二,《草堂成题已见志》其二、五,《拙斋》《虚舟》《远游曲》等。其中有借用《庄子》典故者,如庖丁解牛(《感寓》其二十八),赤水玄珠(《感寓》其九)、庄子却楚王聘(《咏史》其一),沌凿七窍、汉阴叟灌园(《拙斋》)等;借用《庄子》术语者,如“无为”“ 真 人 ”“ 外 物 ”“ 至 道 ”“ 陆 沉 ”“ 宇 泰 ”“ 自 然 ”“ 一 死生”“游心”“忘是非”等;以诗歌形式再现《庄子》思想者,如《感寓》其二十五、二十八等。
王偁视庄子为神交千载之上的知音。解缙评价王偁说其“为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视功名泊如,每有抗浮云之志,期在息机,与世无竞”(谢缙《〈虚舟集〉序》,四库全书本)。可见王偁是一个孤傲高洁,不同流俗的人。他对世俗似乎也刻意保持着警惕,“遁喧俗”“绝垢氛”(《习静山房》其三,卷二,四库全书本)、忘尘虑。对自己的这份孤傲,王偁如山鸡临镜,颇为自赏,他穿越千年历史尘埃而上友庄子,其言:“岂徒漆园傲,百世同高情”《(感寓》其四十七,卷一,四库全书本)。既然将傲视为高情,其自我推崇与对庄子的崇仰之情便显然可见。在为王偁的《虚舟集》作序时,解缙称王偁为标榜自己的泊如超拔之志,特意以“虚舟”名集。“虚舟”作为固定的文化意象,最早见于《庄子·山木》,原文是这样的:“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3]虚舟”这一意象中容纳了《庄子》泯除是非之念,消除成心,虚己游世,不与世争的思想。这与“期在息机,与世无竞”(谢缙《〈虚舟集〉序》,四库全书本)的王偁颇能形成共鸣。王偁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吟咏山水、悠然自得的生活,全身而逍遥,心灵宁静、自由、真朴,并在诗歌如《长歌行》,《感寓》其二十五、三十三,《习静山房》其二,《题畦乐处士成趣园》其一等中,诉说着这样的精神诉求。与此相关,《庄子》无为、外物、齐物的思想也成为王偁认同庄子的重要层面①提倡无为者,如:《拙斋》、《感寓》其九;外物全身者,如《题畦乐处士成趣园》;齐物者,如《草堂成题以见志》其五。。退隐不争,逍遥自乐,自矜自傲的隐士之高情,是闽人王偁与庄子的精神契合点,并以此而成为闽地文人认可《庄子》的典范代表。
闽地负山临海,与中原地区往来不便,地域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这一方面对闽地经济文化发展造成障碍,一方面又成为躲避战乱与权力斗争的世外桃源,渐渐形成闽地崇尚隐逸的文化风气。淡泊寡欲、与世无争,注重精神追求的隐士最易与《庄子》形成精神共鸣,其共鸣的基点在于人格的独立自尊和精神的净化提升。
四、江右诗派与《庄子》
洪武年间,相比于吴越文学的多姿多彩,江西的江右诗派显得黯淡了许多。而永乐年间,台阁文学大半成员均来自江西,就此现象,钱谦益曾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杨士奇)。”[4](甲集“刘崧”条)江西文人之所以能称雄于永乐年间,与吴越文人遭政治的血腥洗礼而凋零的现实有关,同时,更重要的是与江西的地域文化特性有关。从宋代开始,江西文化便开始发迹。在哲学上,江西理学独具特点,注重自我修养,强调道德至上。在文学上,出现了引领宋代文风的一代宗师欧阳修。在科举教育上,江西人普遍重视教育,专注仕途,出现了吉州、饶州、抚州等著名的进士之乡。由此形成了江西人重修养、尚文学、亲政治的文化传统。在明代,江西士人的诸多优点及其在明王朝建立过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使江西士子成为朝廷所青睐的对象。故而,江西文人成了百花凋零,惟台阁独放时期文坛的主宰者。
江西文人中与《庄子》关系密切者,以同为江西泰和人的刘崧和杨士奇为代表。二人均推重道德砥砺,为人隐忍敦厚谦慎,忠于王朝政权。在文学上尊奉儒家的政教观,文风畅达雅正。二人均可谓典型的儒者。儒者的身份并未影响其对《庄子》的认可。杨士奇屡屡在诗中表达对《庄子》的挚爱,其言:“半酣高咏漆园书”(《夜雨次韵寄蔡用严杨仲举》其二,《续集》卷六十,四库全书本),“窗中《南华》篇,流玩以澄心”(《题山水图》,《续集》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案有庄生论,门临孺子坊。游心邈千载,尘虑已都忘”(《次韵答胡若思宾客》其一,《续集》卷五十八,四库全书本);刘崧也不拒斥《庄子》,闲时不妨“来听先生诵《秋水》”(《奉题钟隐君东皋幽居图》,卷三,四库全书本)。因为江西文人注重道德内修,故而《庄子》中某些理念也成为江西文人达此目标的手段。如杨士奇的《题髑髅图》:“漆园傲世者,放言出糟粕。大观天地间,玩化以嘲谑。昼夜自恒理,生死等酬酢。存顺而殁宁,焉往非吾乐。”(《题髑髅图》,卷一,四库全书本)《庄子》中的齐物、安命、任化、生死一体的思想都被江西文人拿来消解烦忧,超越世俗,实现精神的平和安宁。但在江西文人眼中,《庄子》始终属于小道,其基本对《庄子》持以玩赏的态度,如杨士奇诗中称借《庄子》“流玩以澄心”(《题山水图》,《续集)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流玩”二字很可以见出杨士奇对待《庄子》的立场。再如杨士奇的《题髑髅图》虽准确把握到了《庄子》任化、齐生死的思想,但诗中却用“糟粕”二字形容《庄子》学说,透出杨士奇骨子里对庄子思想的排斥。对于江西文人而言,《庄子》永远只是用,绝不会成为体。
江西文人以忠臣自我约束,自我期许,并将这样的心理期待带入对《庄子》的接受中,使之带上儒家忠君报国、念君恋君的话语色彩。如刘崧在其《西馆积雨》中以大樗自比,明显沿用了《庄子·逍遥游》无用逍遥的路径,但在诗的结尾,作者又感慨“君亲恩未报”(《西馆积雨》,卷四,四库全书本),一下子便冲淡了逍遥自由、自在的意味。再如杨士奇的《自题东皋小像》《画牛》《次韵答胡若思宾客》等均是此种情况。于此便可进一步见出江右文人以儒自居,亲近王朝政治,又注重内圣之学的特点。
五、小 结
《庄子》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既体现于历朝历代的庄学著作中,又鲜活地存在于文人的文学创作和生命践履中。后者使《庄子》在庄学低迷期以潜流的形式绵延下来,又使《庄子》在庄学辉煌时期异彩纷呈。而正是《庄子》在文人的创作和生命历程中扎实深远的存在,才真正彰显出《庄子》中生命哲学、美学的恒久魅力,也是《庄子》能够穿越时空的真正生命力的体现。《庄子》对士人生命的渗透是庄学发达,中国艺术独立发展,以及个体生命意识兴发的重要动力。明初文坛四派:越派、吴派、闽派、江右派,在短暂时间里,以空间性存在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历史上的《庄子》境遇。越派文人代表了崇儒重功利的士人对《庄子》的认识。从儒学角度认识改造《庄子》,甚至干脆否定《庄子》思想,艺术上则给予《庄子》充分认可。此点体现了宋代以来逐渐成型的《庄子》接受风尚,以及历史上大多数士人对待《庄子》的态度。江右文人则体现了儒者对待《庄子》的另一种态度。在重事功、道德,端正严谨的儒者面目下,私底下不乏对《庄子》精神境界、生命理念的倾心向往。儒以修身立功,道以治心炼神,儒道互补,锻造出屈伸自如、刚柔并济的君子形象。吴派、闽派则体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士人对《庄子》的认可与接纳,重视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是两派共同得益于《庄子》的所在。而两派又存在差异。闽派对待《庄子》走了传统隐者对《庄子》的态度,带着一种对抗政治、对抗世俗的刻意、严正与孤傲。而吴派对《庄子》生命精神的领会与践履,似乎要轻松许多,有着气质贴合的内在亲近感。在闽派所推重的《庄子》的隐逸之高情外,吴派文人更好地演绎了《庄子》追求审美化生存的思想,是对《庄子》精神更高层次的靠近。
在朱明王朝刚建立的初始阶段,对士人而言,政治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迫于王朝的高压,大多士人都会表达对明王朝的感恩戴德和热烈拥护。这其中有发自肺腑的诉忠诚,也有言不由衷的口是心非。在这一片驳杂中,如何才能辨得清士人心灵的真正状态,实属一件不易之事。而士人在私我空间里独自面对千古之上,且向来与士人心灵密切相关的庄子时,士人们的心扉便彻底打开了。从明初文人对待《庄子》的态度中,我们便可窥晓明初士人是怎样对待朱明王朝的,从而认清士人的真面目。这对我们了解明代士人心态的发展和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