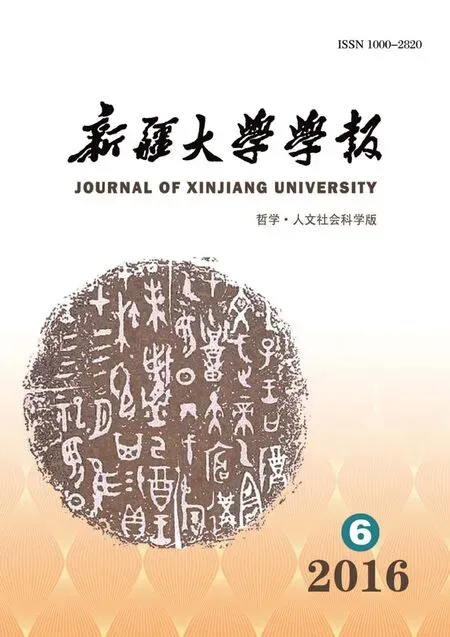国族、国族建设与中华现代国家*
2016-02-18刘永刚
刘永刚
(1.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2.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这个世界由民族国家组成”[1]。起源于西欧激烈传播于国家转型期的“民族”(nation)概念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对于内忧外患蹒跚走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中国社会,其既助推中国模仿并参照西方样式以民族(nation)为主体建立现代主权国家,也使得中华现代国家的国族、国族建设与国家政治发展体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这种模仿性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使得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建设既是中华现代国家建立的政治基石,也是现代中国实现疆域治理的基础性政治保障。
一、从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看“民族”(nation)的现代特征与意涵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要件,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政治合法性与稳定”、“公民身份与一般性政治认同的建立”以及“经济发展”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要件[2]264。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由“领土”、“人口”、“主权”三要素或再加上“政府”四要素[3]构成。另有中国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市民阶级、市场经济、理性主义传统、宗教改革运动”[4]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
无论学界对现代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认识有何种分歧,但对于培育一套共同信仰作为立国之基则是基本共识。在国家转型之际传统制度体系与权威体系分崩离析,如何实施社会整合完成政治动员以获得足够的国家转型动力,通过内争外战的方式建立主权独立、领土完成的民族国家是各国转型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作为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理论”[5]1-2的民族主义无疑具备打造共同信仰最为廉价但卓有成效的价值工具理性。运用民族主义对国家传统疆域社会人的整合过程,实质就是“确定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认同,以整合变动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并确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6]的过程。因此现代国家产生之初民族(nation)原则与国家原则相结合的过程,也被称为“民族统一构设”(nation building),其实质就是“国族建构(或建设)”或“国家建构”,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7]527。
民族主义大师盖尔纳(Ernest Gellner)、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曾反复强调,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性(nationality)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诞生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社会巨变的近代欧洲。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不仅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步,也是从分散、以族群(ethnic group)为基础的地方社会走向统一的民族(nation)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过程。也即将分散的地方性族类群体统一于主权整体的国族化的过程。所以,吉登斯认为“‘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所以,“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民族才得以存在在此。”[8]141-147
较之于“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8]4,现代民族国家是以民族共同体(国家民族)为组织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其次,作为民族国家范畴的国家要素,“是一种自立于其它制度之外的、独特的、集权的社会制度,并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7]490因此,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区别于王朝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其核心构成要素。再次,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国家认同形成并走向一体的前提,当国家和民族熔为一体时现代民族国家方能建立。最后,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包含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与专业化的组织取向,使得民族国家体现出显著的现代性特征。
由此反观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民族性”才是现代国家的本质属性,各要素无不体现着“民族性”。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组织形态的国家与民族,在现代政治理性之下呈现的排斥外延合法属性,使得国家疆域内的人从来不是一个个体概念,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概念。在国家转型之际的国族建构与建设中,无论“领土”、“人口”、“主权”、“政府”都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民族”特征与时代意涵。这种民族性的获得是国族与国家双重建构的直接根源。
现代国家对于传统王朝国家的否定与超越正在于“民族”(nation)成为特定区域(领土)社会成员最为直接且有效的链接方式。在《欧美图解百科全书》中将“民族”指称为“统辖于统一政府之下的,一国人民的集称”[9]。民族(nation)的政治涵义直指民族国家,nation就是拥有线性边界、具有排他性的民族国家领土上的人的集群称谓。可以这样认为,基于主权原则建立“民族”(nation)的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10]虽然民族国家经历了从“一族一国”模式向多民族国家的转变,但这里的民族(nation)从来就是国家民族,也即“国族”。
质言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国族(nation)构建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政治发展过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也即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7]527。在以领土为基准形成的可识别且为他国认可的特定地域范围就是民族国家的疆域,而其人口共同凝聚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国族。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包含着国族建构的目标与诉求,而国族建构则又巩固并推动着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
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构建与中华现代国家的展开
如上所述,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实质就是要解决由“谁”和“如何”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nation)成为这个社会改造运动的主体也成为这个运动的被塑造的对象。盖尔纳认为:“民族是人的信仰、忠诚和团结的产物。”[5]9在亚洲和非洲,“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现代民族的形成是相伴相生的。”[11]传统疆域治理范式的规约与对欧美全新国家形式的模仿是中国启动国家转型以及新型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基本前提。当然,由于“民族”(nation)的现代属性,使得作为现代中国国族的“中华民族”及其建设(nation building)只能是现代概念与现代政治实践。
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强势袭来的西方文明,让中国社会蒙受前所未有之屈辱的同时,也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形成共同命运感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中华民族主义”兴起的外部参照与催生力量。由于列强的侵夺所带来的屈辱感使得中西文化、人种的差异迅速转化为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对自身特殊性的认知。曾经仅为西欧地方性知识的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经日本传入中国后,为处于矛盾境地的国人认识世界与自我提供了全新视角与理论武器。当然,西方的民族理论传入并未立刻给中国的国家转型带来曙光。由于国人矛盾的心态以及西方知识传入的殖民色彩,国人对于民族(nation)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并启动了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与地方性的族类群体“民族化”的共同建构历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多次边疆危机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地方族类群体“民族化”的身影。而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也主要呈现为压迫与反压迫、分裂与反分裂的中华民族主义运动。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予以交代。在中国近代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由“谁”来承担构建新国家的任务。最早由梁启超将日本学者借用汉字“民族”对应英文的“nation”概念将现代国家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之后“民族”与“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改造、社会整合的工具与武器。这个过程可分成两个阶段进行观察,即种族革命国家观统领时期和民族革命国家观统领时期。前者是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目标便是建立种族国家,“反满兴汉”是近代革命党人奉行的最基本信条,其出发点就是以生物学为基准划“我群”与“他群”。从“排满兴汉”到“五族共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从“种族革命国家观”向“民族革命国家观”转变的完成。期间,杨度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五为一”[12]的主张与辛亥前后的“五族共和”观的张扬对维护各民族团结、领土完整的努力都极大的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族体意识。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将“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等同起来,指出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向。期间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作为国族(nation)的“中华民族”概念也经历了从“种族观念下的‘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民族统一’”、“汉族中心的‘共冶一炉’”、“汉人社会的‘宗族民族主义’”、到“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不断深入的认识阶段[13]。中华民族概念的构建与发展也依据时代特征呈现为中华民国建立、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及之后现代国家建设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属中华现代国家建构时期,第四个阶段则属于中华现代国家建设时期。
“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主义”兴起的中国特色在于激荡的“民族”(nation)话语与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大一统”思想的有机结合,国人为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展开的民族救亡运动使得“中华民族主义”明显区别于西方范式。带有鲜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建设主体与凝聚中心。以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为指向的模仿性民族国家建构,注定凝聚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主义”的现实行动方案就是爱国主义。伴随着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愈益强化并自觉融入其中,汹涌澎湃的“中华民族主义”运动(也即民族解放运动)通过内争外战的方式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中华现代国家。
当然,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与社会整合,作为近代国人共同建构国族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与“华夷之辨”相独立的“大一统”思想,“包括版图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要素,其首要途径就是实现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14]。与“大一统”相伴随的“有教无类”式的文化认同对于增加各种文化融入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威系统大有裨益。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中华大地上的各族民众“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5]。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直接归因于以儒家文化为轴心的中华文明对于边疆社会的有效辐射与吸附,以及中华大地上各族农牧互补的依存关系[16]。
以上,历史记忆、文化观念、时代背景均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过程中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建构与凝聚中华儿女共建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客观基础。
三、“中华民族”国族机制下的政党、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体化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建构既是一个宏大的政治整合工程,更是一个细致入微的社会一体化进程。在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新式知识阶层对于家国命运的感知与现代政治理性的传播,运用现代政党的新型社会动员与整合形式,完成了在中国传统疆域上各族民众认同并自觉融入中华民族以构建新型的主权国家。可以这样认为,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一致的体认以及共同理想凝聚的新兴知识阶层组织政党、运用“中华民族主义”来动员和整合各族各群各地力量,通过曲折革命的途径展开的现代国家的转型是中华现代国家政治起步的基本特征。
(一)现代政党的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
在现代政制中,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运动整合进共同、持续的政治活动与组织框架之中,同时将“包罗万象而又散乱的目标转化为有关具体的政治目标、问题和困境的实际术语”,是“由某些政党或政党一类的组织和活动表现出来而获得”[17]。尤其是在中国急迫且艰巨的现代主权国家构建中,现代政党既是中国国家转型中社会整合的组织保障,也是“中华民族”国族机制得以发挥的核心动力。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民族主义成为近代中国“凝聚人心、动员社会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符号,谁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18]。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众多政党或政党性质的组织均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现代政党的活跃反显出传统国家政治的僵硬与顽固。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能够承担起横向融合与纵向同化功能的只能是具有强大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能力的现代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之后民族国家建构中作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融合与同化的社会组织能力上,也即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吸纳与嵌入。“通过吸纳与嵌入机制,政党对少数民族进行组织和动员,从而将民族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19]
现代政党用“中华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尤其是边疆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社会改造与政治动员,“由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主导的政治意识与国家蓝图,在价值观上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与正当性”[20]74,使得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政治力量得以有效克服渗透性与分配性危机,完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与政治整合,才造就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得以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凝聚的中心除却历史文化等因素外,由政党主导的族际政治整合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最重要与最根本的组织保障。
(二)新式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与救国方案
20世纪研究国家建设的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20世纪的知识分子所要表达的思想“居首要地位的是民族独立与统一”,民族主义也通过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得以表达[2]278。作为传统社会主体成员的农民群体是新式知识精英启蒙动员的主要对象。通过知识阶层以民粹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启蒙与组织动员,以农民为主体觉醒起来的民众,“就有可能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2]282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正是新式知识分子鼓吹“中华民族主义”推动国族与民族国家相互构建的一体两面过程。中国社会借此摆脱传统的、衰弱的统治形式,而建立起主权独立、领土清晰的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
对于残酷现实的深刻体认与安邦救国的社会责任感,留洋、新学成为知识分子拯救衰败中国的理论来源与思想武器。然而“中国社会潜在的爆炸性根源在于感觉到的可能性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21],新式知识阶层向国内介绍、传播西方政教文明、探索救亡图存的建国道路上认识与方案呈多元甚至芜杂状态。从“天演论”的提出、“中华民族”性质的讨论、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建国实践等等,莫不以新式知识阶层为主导。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种族救国论到民族救国论下的“五族共和”、从“一族一国”的单一民族国家建国模式向共同打造一个多元共存的多民族国家模式的转变,体现了中国新式知识阶层不断成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的艰辛。
当然,无论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新式知识阶层的主张多么芜杂甚至矛盾,但由新式知识阶层引领、组织、动员形成强大的“中华民族”以建立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中华现代国家的路径与方向是清晰、明确的。同时,由新式知识阶层主导、推动的“广泛的政治动员与理性价值观的传播、文化与情感上激发的个人和国家的共同命运感使革命的目标在边疆社会被广泛认可”[20]73-74,极大地增强了边疆社会系统与中央政府系统间的有机协作与互动支撑。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尤其是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并自觉融入,是中华现代国家成功建立的政治基石。
(三)国家整合与反分裂
中国社会转型之际,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感召力与西欧成功建国的示范效应,再加之西方殖民者企图分裂中国的各种努力,使得各色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在中国具有了广泛的政治舞台。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之时正值亚非拉地区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运动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力量,之后的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内争外战均是以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形式展开的。
然而,中国传统王朝国家体系的衰败与解体、国家权威体系的混乱与无序的直接后果是国家的边疆面临空前的危机。如上文所述,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与地方性族类群体“民族化”同时展开。“清末和民国时期企图分裂中国的英、日、俄等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地用‘民族’(nation)来称呼中国境内的蒙古、新疆、西藏各部落,混淆视听,并直接煽动各部落追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为此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9年曾专门撰文《中华民族是一个》予以批驳”[22]。这种分裂主义的民族运动在中国主要表现在“蒙”、“回”、“藏”等地区,一系列的边疆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整合、领土主权完整必须克服的现实问题。
在内忧外患的险恶处境下,“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及觉醒的中国人,都自觉地推进民族国家构建。”[23]正是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华大地上各族民众逐步凝聚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直接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张扬与有效的国家整合。中华现代国家建构时“大一统”天下观的承继以及对传统社会国家认同想象素材的整合、征引与现代想象、加工甚至再发明均是基于国家整合主义展开的。同时,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再次证明民族主义既可以是国家统一依据,也可以成为瓦解国家的工具。重述“民族”并更新、重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中华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源性要求。
四、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国族建设
有学者认为“民族结构并不是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构成民族国家本质内容的,是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文化的同质性,是国民对主权国家在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24]。在民族国家时代,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家成员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而作为民族国家发展重要制约因素的国家认同状况,既受到国家制度、政策、文化等的多重制约,也深受国家民族结构的影响。中华现代国家的认同政治在民族国家建设与疆域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培养并更新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则是中国认同政治的轴心与疆域治理的基石。
(一)“中华民族”的性质与国族认同
如上文所述,“中华民族”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凝聚中华儿女并承载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建立主权国家的过程中,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与取向。纵观百年来对“中华民族是怎样民族”的三次大争论①三次争论分别是20世纪初关于汉族与“中华民族”关系、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中国存在多个民族、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下中华民族是实体民族还是复合民族的讨论。,其核心问题或争论焦点是“中华民族”的性质问题。其直接表现在关于现代中国疆域内各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之形成的所谓“问题”的称谓上。持“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观的学者以我国的政治生活与国家制度上各族类群体统一赋予的“民族”的政治称谓与权益事实为依据;而持“族际关系”论的学者则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与“民族”(nation)的现代政治属性认为,组成我国国族——中华民族的各族类群体为文化意涵的族群(ethnic group)而非政治意涵的民族(nation)②前者观点在我国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民族”即指“少数民族”,往往也与“民族地区”相关联。如郝时远的《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中国民族报》2012年2月3日)、王希恩的《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点》(《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金炳镐的《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熊坤新的《当前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应坚持的路径和方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徐杰舜的《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等。持后者观点的学者如马戎、周平、胡鞍钢、胡联合等学者在《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中华民族的结构与性质》(《学术界》2015年第4期)、《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中认为我国习惯上称谓并由政治权力确认的56个“民族”实则是56个族群(ethnic group),在我国唯一能够被称为“民族”并已获得相应地位的是“中华民族”。。
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形成、演变与中国国家转型的历程来看,在中华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由中华大地上各族各群自觉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才是真正民族国家意义上具备完整政治属性的“民族”(nation)。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各群均是有机构成中华民族的次级文化群体。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5]。周平教授认为费老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判断依托的是对历史上的各个民族群体相互关系的分析,侧重于或强调的是各个民族群体的‘多元’凝聚为‘一体’的事实”,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的实质在于“一族多群”[26]。“一族”指的是与政治国家结合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多群”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族类群体。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民族发展的实质在于“多元一统”的历史格局[27]。“多元”既指族类群体,也指次文化体系;“一统”既指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也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各族类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深刻存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在内忧外患的国家转型之际孕育了“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主义”,现代中国就是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认同并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建立的主权国家。各族人民交流、交往、交融而呈现的族际关系的本质属性在于国家内部人民间的关系,其根本利益既是一致的、也是可调和的。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均是在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nationstate)框架内被确认和实现的。
(二)国家疆域治理与中华民族建设
“由于国家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与整合的长期性,使得国族的整体性与凝聚度直接体现为民族国家内各构成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28]克服国家认同问题,推进中华民族建设则是中华现代国家实现有效疆域治理与政治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国家疆域治理是一个完整性框架与系统性体系,在中华现代国家全面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国家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体现在疆域观下的治理理念,也表现为具体社会治理上的信度与效度。从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来看,其既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最终凝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因中华民族对于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础性与根源性意义,在国家疆域治理过程中,须完善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述与文化建设,夯实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情感归属;平衡国家区域差异,加快边疆社会发展、保障边民的合法权益,构筑各族人民稳固的共同利益与价值;以“法治”为中心推动国家疆域治理体系的革新,强化各族人民的中华国家意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搭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的政治空间。
质言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现代国家治理,在疆域治理理念上须突破具有悠久传统的以稳定为取向的差异治理观、树立以发展为取向的平等治理观;在国家疆域治理能力上,须有效协调地区、族际间的利益与发展,推进各族各群各地的交往交流交融,以现代国民身份与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尊严与民族自豪感。所有这些均取决于国家的制度构建与政策影响各族人民社会生活而呈现的国家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同时,因“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固定的和永远不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29]。在推进国家疆域治理时,须清醒认识民族主义的负面意义、辨识民族主义的各色表征,通过国家制度与中华民族国族机制有效规制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更新与重构的应有议题。
猜你喜欢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