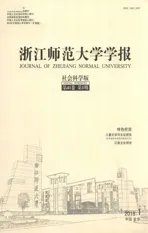论《艰难时世》《功利主义》《论边沁》中共同的情感结构*
2016-02-16闵晓萌
闵晓萌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876)
论《艰难时世》《功利主义》《论边沁》中共同的情感结构*
闵晓萌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876)
摘要:狄更斯和穆勒分别在《艰难时世》《功利主义》和《论边沁》三部著作中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做出回应。两人看似立场殊异,实则殊途同归。他们倡导个体权利、反对机械化的情感计算方式、坚持精神至上的价值判断,试图从对象、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层面对功利主义学说进行全面弥合,表现出了共同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彼时文化界对边沁学说的接受和反拨,为深入探析功利主义哲学影响下的文化模式和意识结构提供了管中窥豹的一个片段。
关键词:狄更斯;穆勒;功利主义;情感结构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名著《艰难时世》( Hard Times,1854)虽与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哲学伦理学论著《论边沁》( On Bentham,1838)、《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1863)有着共同的话题,都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作出回应,却鲜有学者将上述名作并置,进行比较研究和相关性分析。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从两人的生平经历来看,狄更斯虽与维多利亚社会批判家们关系密切,不仅曾借鉴和效仿卡莱尔( Thomas Carlyle)的观点,[1]也颇得阿诺德( Matthew Arnold)、罗斯金( John Ruskin)嘉许;但他与穆勒却并无交集。有历史记载称,穆勒在阅读完狄更斯的《荒凉山庄》( Bleak House,1853)后,曾愤愤然说道:“狄更斯那家伙!”[2]显得两人还颇有些嫌隙。其二,从两人作品中折射出的观点来看,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功利主义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猛烈抨击。而穆勒一方面受其父詹姆斯·穆勒( James Mill)的教诲,笃信功利主义的“快乐动因”学说,捍卫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受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人的影响,对功利主义的冷酷和缺乏同情心加以驳斥。两人不仅写作文体和风格大相径庭,基本立场和态度也迥然相异。然而,如果借用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范畴——“情感结构”( structures of feeling)对上述作品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两人南辕北辙的阐述中隐藏着深刻的一致性,表现出共同的情感结构。本文拟在这一范畴的关照下研读上述作品,打破文学与哲学的学科边界,发掘差异性背后隐藏的一致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构作品生成的文化语境,还原和发掘作品的思想真貌;也使得我们得以管窥19世纪中叶前后,文化界围绕边沁功利主义思潮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意识结构。
“情感结构”的概念最早见于《电影序言》( Preface to Film,1954)一书,后经由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1961)、《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中做了进一步阐发。在上述著作中,威廉斯将情感结构界定为处在特定时期中的一代人对所处世界的一种回应。有别于“世界观”“意识形态”等体系完整、官方认可、制度确认的价值观念,“情感结构”表现为人们真实体验和亲身感知的一种文化模式。[3]它既可能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趋同,也可能与其相悖;既具有“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又具有“情感”的细腻和难以捕捉性;[4]既表现出与前代人情感结构的连续性,又表现出特定时期内人们感知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是一种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有机文化模式。[5]从这个意义上说,狄穆两人的著述正是对19世纪中叶前后、边沁学说影响和作用下情感结构的一种书写。它从功利主义学说的缺陷中衍生而来,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彼时文化界对边沁学说的接受和反拨。
功利主义学说是边沁( Jeremy Bentham)于1789年提出的一套哲学思想,最早应用于立法和道德领域,认为追求快乐和回避痛苦是人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因此政府与社会应倡导个人合理利益的最大化,以实现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为将这一原则细化为一套可操作的伦理规范,边沁提出了一系列指标,主张通过先量化计算个体的快乐值和痛苦值,再运用数学公式加减求和,测算共同体的快乐倾向和痛苦倾向,以评估一项决策或一种行为对社会产生的整体影响。[6]虽然这一学说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司法、道德领域的社会生活向更为民主和人道的方向发展,其积极作用不可小觑;但其局限性同样不容讳言。从对象来看,功利主义虽然试图兼顾个人与集体,但在对共同体利益进行评估时,个人只作为集体中无差别的砝码和单元存在。“最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使得与集体利益相左的个人处在被牺牲的危险边缘,可能导致伯克( Edmund Burke)等保守派思想家所忧虑的“多数人专政”的局面出现。[7]8从方法论来看,苦乐这样复杂的情感该如何分类、量化和计算,同样是个不小的技术难题。穆勒就曾在《论边沁》一文中批评边沁缺乏必要的人生历练,对人性不够了解;这种个人缺陷直接导致功利主义哲学“忽视了人类具有的大约一半的内心情感的存在”。[8]33从价值导向层面来说,功利主义偏重物质层面的快乐,对精神之乐则强调不足;“能使社会制定赖以保护其物质利益的规则”,但却“无助于社会的精神利益”。[8]34在一个卡莱尔眼中被金钱关系主导和异化的社会里,这样的学说确有助长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之虞。
穆勒和狄更斯对边沁学说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予以回应。穆勒以慎思的哲学精神,以拓宽内涵、澄清误解、纠正偏颇的方式修正学说的种种不足。而狄更斯则凭借小说家的生花妙笔,在特定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中倾注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二人关注个体合理权利、反对机械化的情感计算方式、坚持精神至上的价值判断,试图从对象、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层面对功利主义学说进行全面弥合。下文将逐层分析这一共同的情感结构,以期在哲学、文学、文化三位一体的参照系统中领悟作品精髓,拓宽和加深对作品的认识。
一、重现多数人专政下的个体声音
功利主义将学说捍卫的对象界定为“最大多数人”,从而赋予了大多数人将其意志凌驾于少数人意志之上的特权。[7]61面对岌岌可危的少数派权利,穆勒和狄更斯力图凸显多数人专政体制下的个体声音,以化解功利主义带来的逻辑困境。早在1838年问世的《论边沁》一文中,穆勒就曾探讨过多数人专政体制的局限性。他承认功利主义学说竭力保障多数人权利,甚至穷尽一切手段和资源,试图用大众舆论钳制政府官员的言行。然而,学说在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上强调不够、论证力度不足。社会仍然需要建立一种平衡机制,为少数人保留一定的话语权,“以此来矫正片面的观点,保护思想自由和人的个性”。否则,个人正当权利极有可能会“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8]47-48这种观点在时隔25年后面世的《功利主义》一文中发展为对功利主义学说的一种拓展和修正,强调功利主义并不要求人们只专注于“世界或社会整体这样宽泛的一般对象”;在不损害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最有道德的人也只需考虑有关的个人”。[9]18-19这一再诠释虽然在沃洛克( Mary Warnock)看来“已经偏离了严格意义上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10]但其用意与25年前并无二致,都是为多数人专政体制下的少数派个体代言发声。
多数人专政下的少数人困境不仅是穆勒在《论边沁》和《功利主义》中着重讨论的议题,也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第九章关注的焦点。小说家在写作小说时虽不像哲学家那样直抒胸臆,但特定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词汇选择和句法修辞常常成为传递隐含作者观点的表意方式。在上述章节中,驯马师之女西丝接受了功利主义教育者麦却孔掐孩先生的思维训练,并向露意莎转述了这次经历。依照热奈特( Gérard Genette)在《叙事话语》( Narrative Discourse,1983)中的提法,该片段包含多重叙事层次,其中隐含作者写作小说这一事件属于故事外层( extradiegetic),西丝与露易莎之间的交谈为故事内事件( diegetic or intradiegetic),西丝转述的课堂教学内容为元故事( metadiegetic)。[11]狄更斯反对多数人专政、维护个体权利的基本态度,即镶嵌在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中。
在元故事层面,麦却孔掐孩与西丝在看待几个命题的态度上发生了分歧: 1.假设课堂是个拥有5 000万英镑的国家,可否称之为繁荣? 2.如果课堂是一个有100万居民的大都市,在一年之中,只有25个居民饿死在街上。这个比例怎样? 3.如果10万人在海上作长途航行,有500人淹死或被火烧死,这个百分比是多少?按照功利主义原则,这三个例子均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的实例。然而在西丝看来,第一个例子中的国家富裕并不能等同于国家繁荣,因为财富的去向及个人所占份额并不明了;第二个例子中有100万居民存活也不是幸福的表征,因为毕竟有25个人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在第三个例子中,虽然有10万人得以安然度过海难,但对于亲友在海难中丧生的人来说,每一个生命的离去都让人难以承受。[12]66-67西丝的看法没有得到麦却孔掐孩的认同。然而,这些判断建立在对公平的追求、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对他人伤痛的同情之上,符合公平、人道、博爱等普世价值观。麦却孔掐孩将其否定的同时,也就在元故事层面构建了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公正、人道、博爱等普世价值观的对立。隐含作者通过将多数人专政可能引发的道德困境实例化,使原本枯燥概念化的伦理问题真实可感,也促使读者采用更为情感化的视角审视多数人专政下的少数人困境。
而到了故事内事件层面,西丝在长期无法取得“进步”的压抑情绪作用下,向露易莎倾吐了自己的苦闷,转述了这次经历。由于西丝个性温良、见识不广,服从麦却孔掐孩在元故事层的教导;因此在这一叙事层次中完全否认了自己之前的判断,认为自己犯下了“天大错误”。而露易莎从小深受功利主义教育浸淫,早已将功利主义哲学内化,所以也不假思索地附和了西丝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你的一桩大错”。[12]66-67结合上文相关情节来看,两人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呈现了功利主义教育与西丝原本秉持的公正、人道、博爱原则在故事层面的对立。
由此可见,狄更斯层层构建了多数人权利——个体合理权利以及功利主义教育——西丝原本正确的信念这两组矛盾的双重对立,融维护个体权利、反对多数人专政、质疑功利主义教育的价值判断于多层次叙事结构中。这与穆勒对同一命题的论述相比,虽形式不同,但立场无异。正是得益于两人历时多年、不拘体裁、富于层次的反复论证和呼吁,“维护个体权利”这一主题才得以在19世纪中叶以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敦促人们在各个阶段、从不同渠道对功利主义的多数人原则进行反思。
二、质疑情感的数字化考量方式
功利主义学说以确立明晰有序的立法原则为出发点,因而必须改变以往立法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和草率立论的局面。为实现这一目标,边沁采用了一套量化的计算方式。他不仅对快乐和痛苦做了32种分类,在陈述计算方法时也追求数学般的严密精确。这些做法“使法学从莫名其妙之物变成为科学”[13](麦考利语)。穆勒在《论边沁》一文中重申了麦考利(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结论,对边沁在法学领域的建树予以充分肯定,[8]11-12但他同时也指出:边沁本人人生经历太过单纯,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足够了解,对苦乐的分类又完全建立在主观经验之上,这些局限性不仅使得他的计算方式只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具有适用性,而且对于人性中复杂深邃和难以估算的部分,他的学说更是较少涉及。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功利主义计算体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他对人类情感知之甚少,对情感形成的影响知之更少,思想自身以及外在事物对思想更加细微的运作被他遗忘。”[8]26
事实上,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使得苦乐这样的情感生成机制极为复杂,不可捉摸、难以测算,唯有以情感的方式才能理解情感。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穆勒将想象力与同情心并置,并将这两种特质视作弥补功利主义缺陷的不二法门。早在1838年写作的《论边沁》一文中,穆勒就毫不讳言地宣称,边沁对人性中许多最自然、最强烈的感情没有同情心,这是他作为哲学家的一大缺陷。[8]2425年后,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又再次强调,许多功利主义者“培养了自己的道德感情,却没有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和审美鉴赏力”,因此“在看待行为的道德性时考虑过分单一”。[9]20而要获得“共情”的能力,必要的想象力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想象力是一个人可以了解另一个人的想法和境遇的能力”,它“帮助人们通过自发的努力来将不在场的事物感受为好像在场,并且让人们将想象的事物感受为好像是现实中的事物”。[8]24在穆勒看来,想象力激发同情心,而唯有同情心才能使人们设身处地、心灵相通,从而体悟他人情感,而非僵化测算、漠然无视他人内心的情感诉求。
穆勒笔下不通人情的边沁成为《艰难时世》中葛擂硬的人物原型;他对功利主义计算体系危害性的预估,在小说中经由一桩荒唐的婚事得到了证实;而他所看重的同情心、想象力等特质,被狄更斯赋予了一位扭转不利情势、改善人物关系的理想化人物——西丝。葛擂硬与边沁同为功利主义教育家,他看重事实,对情感和想象力有着难以言喻的鄙夷,惯于用数学方法测算复杂难解的情感问题。即便是女儿露意莎和好友庞得贝的婚事,他也要通过代数计算予以定夺。一番测算下来,他发现,在所有婚姻中,有相当比例的夫妻双方年龄相差悬殊,且3/4以上为男方年长。这一结论一方面经英格兰和威尔士搜集来的婚姻数据验证无误,另一方面由旅行家在印度、中国、鞑靼等地,以最好的估算方法予以证明;因而可以被认作是大多数婚姻的存在状态,符合“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原则”。依照这一推论,庞得贝和露意莎虽然年龄相差30岁,两人结合仍完全合理,婚后幸福理应可以预期。[12]110-111葛擂硬的计算过程虽然精准,但他却忽略了婚姻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忽略了女儿自身的意愿。而这种情感上的体谅只有通过共情心理才能获得。葛擂硬正和缺少必要人生经历的边沁一样,不具备这种能力,因而看不到这桩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带给露意莎的伤害。对此狄更斯不无讽刺地评论到:“要是他看到这一点,他一定会一跃跳过那些人为的障碍,这些障碍全是他多年来在他自己与那些微妙的人性本质之间树立起来的。那些本质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是极巧妙代数学所能捉摸的,而到那时候,就是代数学也要与世界同归于尽了。这些障碍是太多了,也太高了,他跳不过去。”[12]112
狄更斯的措辞与穆勒对边沁个性的剖析十分契合,两人都意在批评边沁、葛擂硬一派的功利主义教育家对人性的不了解,以及以代数公式处理情感问题的不恰当。而这段婚姻的后续发展轨迹则充分诠释了上述处理问题模式的可能性后果。露意莎与庞得贝婚前毫无感情基础,婚后两人生活并不和睦融洽。露意莎长年压抑的情感找不到出口,几乎沦为花花公子詹姆斯·赫德豪士的玩物,险些和他私奔。虽然露意莎迷途知返,折返至娘家与父亲一起生活,但她与庞得贝的关系也因此完全破裂,两人终身分居,婚姻实际上已经消亡。一桩以精准数据为依据的婚姻,最终以婚姻破裂作结;狄更斯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在将穆勒的观点实例化的同时,也传达了对功利主义体系的辛辣嘲讽。
而西丝的出现既成为葛擂硬一家扭转不利情势、改善相互关系的契机,也从侧面印证了穆勒的观点——为缓和功利主义的僵化教条,同情心和想象力至关重要。史里克( Paul Schlicke)指出,西丝长年生活的史里锐马戏团是全书想象力( fancy)和手足之情( fellow-feeling)等人本价值的寄存地,[14]与代表着功利主义的葛擂硬学校以及象征着大工业生产的焦炭镇形成相抗衡的态势。西丝本人很明显继承了马戏团象征的这两种特质,她温柔感性、善解人意,在缓解葛擂硬家庭危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露意莎刚刚宣布订婚,西丝就敏感地察觉到露意莎的痛苦,预见到这桩婚姻前景堪忧。[12]80而当露意莎婚姻破裂、身心俱疲地回归家庭时,首先也是向西丝发出求救的呼声:“原谅我,可怜我,帮助我!现在我极其需要人帮助,你要怜悯我,让我把头放在你那友爱的心坎儿上吧!”[12]252
这时的西丝则如同圣徒一般,“发出一种美丽的光辉照亮对方心中的黑暗”,[12]251用同情和爱心抚慰露意莎的伤痛。在她的帮助照顾下,露意莎过上了虽不甜蜜却还安宁的日子;葛擂硬也从女儿的婚姻失败中汲取教训,开始认识到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家中僵硬冷漠的气氛有所和缓。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葛擂硬家族的小女儿珍虽然仍然接受功利主义教育,但由于自幼与西丝感情甚笃,受其影响颇深,长大后成为了一个“容光焕发”的孩子。狄更斯借露意莎之口,称两派力量的中和使得珍“年轻的心弦已被拨出和谐的音符”,[12]248-249显然是在暗示用同情心和想象力中和功利主义僵化教条的可能性。
这不禁又让我们联想到,穆勒在1840年面世的《论柯勒律治》( On Coleridge)一文中,将边沁哲学和柯勒律治的学说视作对立的两个学派,认为这两个人的哲学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柯勒律治对情感和想象力的强调人所共知。从这一主张中,不难发现穆勒和狄更斯殊途同归,都试图从浪漫主义传统中寻求到医治功利主义机械理性的良方。这种努力也许如威廉斯所说,是一种“机械的整合方式”。[7]54但是,两人如何分别以哲学论述和文学创作的方式阐发这种立场,各自独立又共同建构了英国文化传统,仍然是一个值得后世读者反复回味的命题。
三、坚持精神至上的价值判断
将追求快乐、回避痛苦奉为圭臬的哲学伦理学说常常难以摆脱耽于感官享受、沉溺物质诱惑的指责;亚里斯提卜( Aristippos)的享乐主义学说、伊壁鸠鲁( Epicurus)的快乐伦理学说和爱尔维修(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的唯物主义伦理思想皆是如此。功利主义学说问世不久,同样因为以“快乐”为基准的论调而被德、法、英等国的抨击者们将之与伊氏的快乐伦理学说相提并论。反对派认为两派学说都因追求感官享受而将人类与牲畜等同起来,落入了物质主义的樊篱。[9]8不可否认,边沁确将追求“快乐”视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但若不加辨析地认为功利主义只强调物质层面的快乐,则是对学说的一种误读。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边沁既列举了虔诚之乐、仁慈之乐、想像之乐等精神层面的快乐,也列举了感官之乐、财富之乐等依托物质、诉诸感官的快乐。[6]42可以说,学说创立的本意非但没有排斥精神之乐,反而将物质之乐和精神之乐并置,视二者为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元素。
穆勒一方面承认精神之乐在功利主义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不吝指出,相较物质之乐而言,精神之乐并没有得到强调和重视。功利主义忽略了约半数人类精神上可能产生的情感,即使是硕果仅存的那些,它们的存在也并没有引导出什么实质性的结论。[8]33但即便如此,如果认为功利主义意在鼓动人们追求感官享受,仍然是对学说宗旨的一种误解。在《功利主义》一书的第二章中,穆勒首先驳斥了反对派的观点。他指出,以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者们虽然信奉快乐动因学说,但并没有将人和牲畜等同起来。反对派们如果认定学说中的快乐等同于感官之乐,恰恰说明他们自己否认人类拥有高于感官的精神愉悦,认为人类之乐与动物之乐是无差别的。在随后的论述中,穆勒又对感官之乐和精神之乐的高下做了辨析。在他看来,只有对物质之乐和精神之乐皆有体验的人,才能体会到两者之间的差别。而但凡经历过灵与肉两重愉悦的人,都会更为偏好更高级官能的快乐,即精神之乐。如果从这一经验引申开来,那么精神之乐较物质之乐不仅程度上更为强烈,而且境界更为高远,理应更为功利主义信奉者们所推崇。
穆勒借助个体经验,以说明精神之乐和物质之乐的高下优劣之分,这与狄更斯借助小说情节设置,凸显物质主义导致的精神荒芜和婚姻不幸,具有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我们不妨看看《艰难时世》中,功利主义者葛擂硬和资本家庞得贝的一次正面交锋。露意莎婚姻的不顺遂促使葛擂硬认真反省了自己的教育模式,从而调整了对待女儿的态度。为化解女儿的婚姻危机、缓和她和丈夫的关系,葛擂硬试图劝说庞得贝更为体贴地对待露意莎的情感诉求。正是在这次交谈中,功利主义者笃信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和商业资本家执持的“物质至上”原则发生了激烈的冲撞。葛擂硬承认自己对女儿性格的不了解,意在从精神层面做出补救。为此他与庞得贝交涉道:“我想露意莎的性格有许多部分是——是被我们粗心地忽略了,因此——因此她性格中的这些部分也就从坏的方面去发展而使她走入歧途。我——我要向你建议的是——要是你肯帮我设法,任凭她自由地发展她的好天性,温柔体贴地鼓励她让她去发展——这样做对我们都有好处。”[12]267
然而,庞得贝的答复中却充斥着将婚姻物质化的粗鄙观念:“只要一个人告诉我什么富于想象力的本能,不管是谁,我就知道他用意何在。他的意思是想用金调羹吃甲鱼汤和鹿肉,想坐六匹马的马车。这就是你女儿想的东西。”[12]268
在这场婚姻精神性和物质性的交锋中,葛擂硬的立场和态度较之前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他虽然仍以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为立足点,以“对我们都有好处”为行事的目标;但当他认识到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只能招致不幸时,也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改变了先前执持的观点——“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12]315并开始关注女儿的情感需求。他的改变印证了穆勒的申辩之辞,证实了功利主义学说与精神之乐的兼容性。然而,庞得贝惯于以商业视角考量问题,以物质利益衡量得失。在他眼中,所谓的情感需要只不过是攫取物质利益的托词,婚姻的实质不过是“用金调羹吃甲鱼汤和鹿肉”,夫妻琴瑟相调比不上“坐六匹马的马车”的舒服惬意。正是这种立场的殊异决定了翁婿两人的决裂,而他们的决裂也正代表着功利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从这桩婚姻的走向上来看,庞得贝固守物质主义立场,使得他与露意莎的婚姻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最终因为难以为继而破碎,这种结局无疑是对所有相关方伤害最大的一种情节设置;在极其重视家庭完整性的维多利亚社会里,这一情节更是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传递了小说家批驳“物质至上”,追求情感和谐、人性关怀的基本态度。在这一情节设计上,狄更斯走向了穆勒:两人都在为功利主义原则与物质主义原则划清界线的同时,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性。而葛擂硬的转变也正契合了穆勒的判断:功利主义者最终要在精神之乐中才能真正寻求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 Culture and Society,1958)一书中,将穆勒的立场界定为“拓展了的、人性化的功利主义”[7]71;而将狄更斯的态度概括为,小说家在秉持善良、同情心、包容等人本价值的基础之上,对以葛擂硬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加以抨击。[7]101-102然而上述分析却为我们揭示了两人看似殊异立场下的内在一致性。阿尔图赛( Louis Althusser)认为,科学让我们获得关于对象状况的概念知识,使我们认识到意识形态;艺术让我们获得关于对象状况的经验知识,“看到”和“感觉到”意识形态。[15]穆勒和狄更斯在《论边沁》《功利主义》和《艰难时世》中,分别以哲学论证和艺术再现的形式建构了共同的情感结构,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予以回应、反拨和修正。穆勒以一名功利主义信徒的身份,试图拓宽功利主义学说的内涵,弥合其缺陷;而狄更斯通过叙事结构、人物刻画、情节安排等艺术手法,巧妙地传达了一个具有反哲学倾向的文学家对功利主义哲学的反思。二者一为哲学思辨,明晰而严谨;一为文学建构,具体且感性。在形式上各有特色,在根本立场和根本目的上却殊途同归。从跨越文学和哲学两界的共同情感结构中,我们不难读解到功利主义思潮下,维多利亚知识分子辗转寻求出路的困顿、艰辛、睿智和洞见,以及这些思想的火花如何汇聚到一处,转变为同一个强劲而有力的声音。
参考文献:
[1]FORD G H.Dickens and His Readers[M].New Jersey: Princeton UP,1955: 88-92.
[2]BOWEN J.Dickens and the Force of Writing[M]/ /BOWEN J,PATTEN R I.Palgrave Advances in Charles Dickens Studies.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259.
[3]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M].New York: Oxford UP,1977: 132.
[4]WILLIAMS R.The Long Revolution[M].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1961: 64.
[5]阎嘉.情感结构[J].国外理论动态,2006( 3) : 60-61.
[6]边沁.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M].程立显,宇文利,译.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25-26.
[7]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New York: Doubleday&Company,1960.
[8]穆勒.论边沁与柯勒律治[M].白利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WARNOCK M.Introduction by Mary Warnock[M]/ / WARNOCK M.Utilitarianism and On Liberty.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 9-10.
[11]GENETTE G.Narrative Discourse[M].LEWIN J E,trans.Ithaca: Cornell UP,1983: 228.
[12]狄更斯.艰难时世[M].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3]哈特.导言[M]/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14]SCHLICKE P.Hard Times[M]/ /SCHLICKE P.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New York: Oxford UP,1999: 269.
[15]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41.
(责任编辑周芷汀)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Hard Times,Utilitarianism and On Bentham
MIN Xiaomeng
( School of Humanities,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Beijing 100876,China)
Abstract:In Hard Times,Utilitarianism and On Bentham,Charles Dickens and John Stuart Mill responded separately to Utilitarianism put forward by Jeremy Bentham.Their seemingly opposing arguments actually share some common ground.Both of them attempted to modify utilitarian doctrines by advocating individual rights,objecting to the mechanical method of calculation and emphasizing spiritual happiness as against sensual pleasures.Their arguments manifest the same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their response to Utilitar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bjects,methodology and judgment of value.To some extent these structures of feeling reflect how Utilitarianism was received and responded in the literary circle,hence provide a sample study on cultural pattern and ideological form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Key words:Dickens; Mill; Utilitarianism; structures of feeling
作者简介:闵晓萌( 1983-),女,湖北孝感人,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5-01-04
中图分类号:I109.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 2016) 01-002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