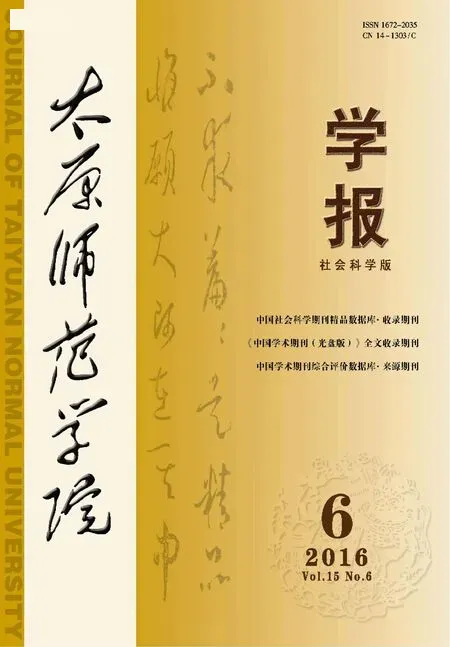论《光荣》结构对主题的烛照
2016-02-13李思
李 思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文学】
论《光荣》结构对主题的烛照
李 思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长期以来,《光荣》被研究者认为结构简单、平淡无奇而遭到忽略。其实,纳博科夫为了完美地呈现主题,而设置了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外部结构明晰匀称,为小说的主题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外部框架;内部结构复杂而精致,通过反复出现的主题意象、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以及起伏的情感律动将内外结构勾连在一起,而小说的主题就在这种完整性中得以呈现。从中可以一窥纳博科夫在处理内容与形式、主题和结构之间关系上的匠心独运和美学成就。
纳博科夫;光荣;结构;主题
《光荣》是纳博科夫第五部俄语小说,1933年出版于巴黎,后经其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翻译成英文,由纳博科夫修改、校订,最终于1972年出版于纽约和伦敦。而在我国则至2012年才由石国雄以《荣耀》为名翻译出版。
不管是俄语本还是英语本抑或是中译本,《光荣》在纳博科夫小说中似乎都没有如其名所示那般耀眼。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反应也异常地冷淡,纳博科夫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安德鲁·费尔德就指出,这本书并没有“带着精微的意义的多重性挑战读者”[1]118。尽管纳博科夫在英文本序言里赞叹这部小说“提升到了一种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艺术境地”[2]2,但依然无法阻止一些评论家相信“《光荣》只是一部苍白而易碎的作品”[3]224。在英语界,对《光荣》的研究远不如对《洛丽塔》、《微暗的火》的研究那样如火如荼,甚至没有像纳博科夫的其他俄语小说那样为人所提及;在国内,截至2016年6月,收录进知网的专门研究《光荣》的论文竟无一篇。
这部小说是否真如看上去那样不值一提?一些研究者敏锐地发现,《光荣》与纳博科夫的其他小说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伊迪斯·哈伯(Edythe C.Haber)从俄国民间故事入手,通过对《光荣》中人物的名字、意象等与民间故事的联系,从而发现小说里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立,而这一对立也反复出现在纳博科夫俄语和英语的作品中。哈伯最后总结道:“对《光荣》中童话故事的花样的探查,显示出这部小说在纳博科夫所有小说中不可分割的位置,并且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审视小说内在连贯性的视角。”[4]222佩卡·塔米(Pekka Tammi)同样认为:“注意到《光荣》是如何紧密地融合进纳博科夫的经典小说之列以及它如何在作者的其他作品里发展了主题和结构上的可能性是更加有意思的事。”[5]170塔米继而从主题、结构以及形而上层面对《光荣》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指出它与纳博科夫其他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布赖恩·博伊德从对主人公所处时空的来回转换的分析发现了小说结构上的和谐,指出“这部小说的结构就在于前后的切换”[6]460。
由此可以看出,论者大多已涉及对小说结构方面的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光荣》所体现出的最重要的主题,继而分析小说复杂的结构艺术以及这一结构与主题呈现之间的紧密关系,以期对小说的艺术价值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作为主题的“光荣”
纳博科夫曾说:“我很反对将内容与形式区分对待,把传统的情节结构同主题倾向混为一体。”[7]27言外之意则是,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抑或主题与结构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小说的主题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情节结构才能为读者所理解,而在优秀的小说里这两者是一个完美的契合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恩·布斯指出:“不管我们怎样给艺术或艺术性下定义,写作一个故事的概念,似乎就已有寻找使作品最可能被接受的表达技巧的想法包含在自身之中了。”[8]115《光荣》的主题之光正是在结构的玻璃网上折射出耀眼的色彩的。那么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
像纳博科夫的其他小说一样,《光荣》的故事除了带点异国情调外并不复杂。小说主要讲了一个青年俄乔马丁·埃德尔韦斯从俄国辗转至西欧的生活,以及他基于自己的冒险精神所做的一个壮举——非法穿越苏俄边境,小说以马丁的好友达尔文将这一消息告诉马丁的母亲结束。达尔文对这一明显的送死行为大惑不解,而除非有什么实际的目的,否则此举看起来显得毫无意义。此外,马丁还有一系列看似无意义的行为让人困惑。他深爱索尼娅,明知没有结果还追求到底。他千辛万苦赶到莫里尼亚克寻找记忆中的灯火,最后却并不能确定那个镇子是否就是莫里尼亚克。难道作者只是将马丁视为一个盲目而无知的反讽对象?作者在序言里明确指出:“这是我唯一一部带有意图的小说,着重揭示了我那年轻的流亡者在最平凡的乐事和看似无意义的孤独冒险经历中发现的激情与魅力。”[2]2但这似乎仍不能解释马丁无意义的行为与赋予这种行为以“光荣”之名有何联系。这一联系需要到纳博科夫对英译本书名的选择上去寻找。纳博科夫说,对俄语词“英勇行为”(podvig)的最明显和通常的翻译是“功绩”(exploit),但是后者所含有的“功利”的意思将会破坏俄文词所具有的“无用的行为”这个含义,因此他选择了“间接的‘光荣’一词,虽然它离原意较远,但是更丰富地表达了俄语书名的意思”[9]ⅹ。可以看出,纳博科夫之所以认为马丁的行为是可赞颂的光荣的行为,正是因为它剥除了功利和实际的目的,而纯然是一种听从内心召唤,对神秘事物充满好奇并因此不断探索的行为。马丁冒死穿越苏俄边境,并不如达尔文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传递情报、会见要人,而只是为了亲眼看见那片充满神秘意义的国土。正如佩卡·塔米注意到的,这一无功利的光荣行为即可看作小说的主题之一,而笔者以为这正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而这一主题通过小说清晰的外部结构和复杂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来并与其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
二、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间的张力
相比于《洛丽塔》、《微暗的火》等纳博科夫成熟时期的作品,《光荣》的结构乍一看显得平直而显明,似乎正如费尔德所说的没有带给读者很大的惊喜。但是细查之下就会发现,在规整而匀称的外部结构的框架里含有纳博科夫式的细密而交错的内部结构。而小说的主题就在这二者间的张力中熠熠闪光。
较之于纳博科夫其他俄罗斯时期的小说,《光荣》的时间跨度较长,从马丁的童年写起直到22岁,中间可以轻易地划分出几个生活阶段,文章脉络很清楚。这就给整部小说搭建起一个非常稳固的外部框架,虽然小说的结局是开放的,即纳博科夫并没有明确指出马丁的最后命运,但消失在文本最后的那条神秘的林中小路与小说开头提及的那幅画有蜿蜒小径的水彩画融为一体,从结构上讲是很规整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外部结构其实提供了理解主题的诸多线索。具体来说,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叙写了马丁离开俄国之前的生活,包括主要家庭成员的介绍以及马丁性格的形成。“小径”、“火车”、“灯火”等主题意象几乎全部出现,这些意象与马丁无功利的探索精神的联系后文会提到。而马丁对神秘的未知事物充满好奇这一性格特点也被一再渲染:“马丁感悟到的那份激情,那份以各种形式混合表现出来的激情,从此开始伴随他的一生”[2]7。第七章到第十章,马丁和母亲离开俄国前往瑞士,途中他和一个粗俗而蹩脚的已婚女诗人发生了一段罗曼史。后面对爱情的寻找和接近自虐式的坚持都是对这次激动人心的经历的回应。而“爱情”作为《光荣》的一个线索对理解主题有重要的作用。第十一章到第二十九章,讲述马丁在剑桥的生活以及他与达尔文和索尼娅之间的三角关系。在这一部分里,达尔文还是一个与马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桀骜不驯而充满探险精神的青年,这就与后面那个中规中矩的达尔文形成了对比,也使得马丁不改初衷的探索精神更令人动容。第三十章到第四十八章,马丁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并没有像达尔文那样被生活所驯服,而是将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穿越边境的探险计划付诸实践。
这样,外部结构就为主题的呈现设置了一个明晰的轮廓,但从注意到马丁无功利的光荣行为到理解纳博科夫赋予这一行为的价值,也即从主题的呈现到主题的生长、深化,还需要借助细密复杂的内部结构。纳博科夫利用重复出现的主题意象、相互交叉的三条线索和悲歌式的情感律动这三个手段将小说的内外结构嵌套在一起,不仅留下了可辨识的编织轨迹,还展现了一如波斯挂毯上华美精致的图案。
三、结构对主题的烛照
“林中小路”、“灯火”和“火车”是散落在小说各处并反复出现的三个主题意象,这三者在文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林中小路”首次出现在童年马丁婴儿房的一幅水彩画里,“画中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和一条消失在树林深处的蜿蜒小径”[2]6。这条虚幻的小路激起了马丁对神秘莫测事物的最初的好奇,并幻化为雅尔塔大海中诱人的尾波,延伸至通往禁地的行程中马丁想象中的“一片茂密的森林,一条蜿蜒的小径”[2]177,最终汇合于达尔文脚下那条逐渐淡出的“在树干间蜿蜒,景致如画,神秘莫测”[2]229的小径。“灯火”首先闪耀在雅尔塔的夜空里,这使马丁回忆起儿时在南方快车车窗外看到的那一把散落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的灯火。十三年过去了,他对记忆中的灯火仍痴迷不已,在从柏林去往斯特拉斯堡的旅程中马丁恰好经过了同儿时那个南方快车之旅相同的路线,在车窗外再一次看见了那些灯火,这次马丁跳下火车追踪着灯火来到莫里尼亚克镇。小镇平静而美好的务农生活让马丁探索了灯火神秘而宁静的本质,他最终决定要实施他的偷越边境的计划了。在离开农场前他与心爱的灯火告别,此后这一意象再没有出现。“火车”这个意象首次以火车模型的形式出现在涅瓦大街的商品橱窗里。那一天天气阴沉寒冷,呼应着成年马丁告别母亲通向禁地那天的细雨蒙蒙,而后与马丁的各种旅行联系在一起,“他回想起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奇怪,就好像他从未走出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不过是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罢了”[2]177。从童年起马丁就坐着火车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那未知的远方似乎在召唤马丁,让他一刻不停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在前往禁地的途中,马丁提醒达尔文不要忘了自己的临别请求,而最后一句话正是落在了火车这个意象上“我是说:我的火车。对,对,火车……”[2]225
由此可见,“小路”、“灯火”、“火车”这三个主题意象都具备一种神秘的特质,这与马丁探索未知的精神相通。而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小路和火车两个意象贯穿全书,都始于第二章终于第四十八章,而灯火这个意象却突然中止于马丁离开莫里尼亚克镇之后。纳博科夫为何会做这样的安排呢?火车让人联想到旅行,是一个不安分的从一个目的地通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过程。马丁一直想计划一次非法的远征,正是火车把他送往命运的终点。他在火车里不止一次地看见迷人的灯火,这时的灯火对于他来讲是一种神秘的召唤。而当他终于听从内心的召唤跳下火车,探索了灯火那宁静的本质后,灯火神秘的色彩褪去了,马丁并没有安于农场的安静生活,而是选择继续乘火车越过危险的边界,探寻那禁地深处的小路。这样的安排正与纳博科夫所赞颂的无功利的光荣行为相一致:看似无意义却有着超越一般世俗理解的对于发现生命激情的虔诚向往。
如果说,这些主题意象如珍珠一般散落在小说的外结构里还不足以构成凸显马丁前往禁地探寻未知这一行为的价值的话,那么纳博科夫又用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时间线索、死亡阴影和劳而无功的爱情把这些意象串起来,让马丁的越境计划从萌发经过中间的犹疑到最后的实施这一过程清晰可见。博伊德在论及《光荣》时仔细分析了情节发展中时间的前后切换,认为“时间”本身就是通过人事的变化为人所感知的,而《光荣》的时间线索又使达尔文对生活的看法的变化与马丁不变的初衷形成了对比,从而凸显了马丁行为无用却光荣的性质。达尔文由一个崇尚自由、桀骜不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讲求实际的城市中产阶级,他“过着坚实可靠的生活,很少激动(甚至在表白爱情时也是这样)”[2]224。达尔文并不能理解马丁的越境行为有什么意义,甚至只把它当作无理取闹的傻事。而马丁依然在时间的流逝中将水彩画里的森林小路变为现实,追寻着记忆中的璀璨灯火,不断地乘着火车探索未知的神秘,义无反顾地实现很早就勾画好的通往禁地的旅程。马丁对理想的坚守与达尔文对生活的功利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让人们看到马丁的探索就是“崇高冒险与无私成就的光荣,是这个尘世与不完整的天堂的光荣,是个人勇气的光荣,也是光辉灿烂的殉道者的光荣”[9]ⅹ。
细心的读者不难察觉,整部小说都笼罩在一层无法确指的死亡预感里。小说第一章就提到了马丁祖父和父亲的死,之后写到马丁夜不能寐在黑暗中等待父亲灵魂的回应。如果这些还都是想象性的,那么在散步途中意外滑落到悬崖边上的经历则让“死亡”更具实在性,当马丁俯瞰深渊时他一下想到了死亡“我要掉下去了,要死了”[2]97。马丁暑期归来在拜访济拉诺夫家后得知索尼娅的姐姐奈丽和她的丈夫双亡,晚上他刚好住在奈丽以前住过的房间,他又一次想到了死亡,甚至想象了自己死亡的场景。为了不让索尼娅的影子阻碍自己实现心中那庄严的梦想,马丁决定离开柏林前往斯特拉斯堡,途中在与一个法国人谈话中马丁说道:“我的路要穿过荒凉而危险的地方,谁知道呢?也许我回不来了”[2]175。马丁其实已经隐约感到他的冒险的危险性,但无论死亡的阴影之后变得多么浓厚,他都坚持听从内心的召唤。从第四十三章开始,马丁真正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死亡气息也渐趋浓烈。离开瑞士木屋的早晨,一切都蒙上了不安的色彩,细雨蒙蒙的天气,母亲一再的不舍与挽留。早餐期间,马丁强烈地感觉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母亲。在通往禁地的火车上“他想到了死,想到自己也许随便什么时候就会死去”[2]204。奇怪的是,马丁的母亲索菲亚是作品里隐秘的死亡预言者,父母离异后马丁会在周末去看望父亲,回来稍晚一点索菲亚就会担心马丁不会回到她身边了,马丁长大之后索菲亚又时常害怕儿子一声不响地去参加白军。马丁向母亲谎称去柏林后会回来,“你不会回来的”[2]188此话竟一语成谶。马丁无疑是畏惧死亡的,可他还是作出了选择。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越境不是为了传递情报,不是为了当白军战士,不是为了科学考察,也不是为了破纪录,而是为了寻找“光荣,爱,对大地的温情和千万种相当神秘的感觉”[9]127。巨大的死亡的威胁和看似无意义的行为之间的反差,足以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此外,爱情也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实际上马丁对索尼娅的爱情是与前往禁地的行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索尼娅点燃了马丁去往禁地的激情,与他一起想象了边境那一边的生活,并给那片想象中的土地命名为佐尔兰德。是索尼娅首先问马丁是否愿意参加北方的白军军队,这无疑在马丁的意识里留下了一个印象,后来这个印象将以一种探险的形式融进他的禁地之旅。马丁对索尼娅有一种近乎白日梦的期盼,他希望自己在经历了众多冒险后,回到索尼娅身边,赢得她的爱慕。如此看来,马丁无功利性的行为里不是也夹杂了一种目的性?其实,这条爱情线索的设置对主题的凸显有着巨大意义,爱情本来就是马丁在生活中发现的激动人心的经历。马丁不顾已婚女诗人艾拉事实上的过分俗气,硬是用自己的幻想重新复活“那份神秘的魅力”[2]47,其实他与艾拉的浪漫史,与对索尼娅无望的爱情都是和他孤身冒险的激情和他内心对神秘事物的好奇融为一体的。
如果说三条线索将主题意象串联起来,那么纳博科夫又以一种悲歌式的情感律动充盈着整部小说。这里的“律动”其实是指叙事节奏上的变化,这一变化复杂化了小说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到,小说的主题在第二章就以一段舒缓的旋律奏出了——索菲亚发现了幼年马丁身上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激情,此后一直到第十章,小说都是在一种明媚的抒情小调中进行的。从第十一章开始小说情绪稍稍有了些变化,明媚的抒情小调中夹杂了太多不协和和弦,营造出一种紧张感。马丁对索尼娅的爱情从朦胧到异常纠结,他对俄国的想念逐渐增强,他去往禁地探险也从雏形发展到细致的计划,中间不时有死亡意识的闪现。在计划终于开始实施之际,死亡的阴影聚拢起来,情绪也开始爆发。第四十三章之后原本缓慢的节奏开始加快,情绪成一个渐强的趋势。大家都屏住呼吸凝视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听从内心的召唤孤身一人奔赴“禁地”。年轻人的未来模糊不清,这时读者恐惧的心情已经达到极点,我们迎来了小说的高潮。而纳博科夫偏偏在这段旋律旁加上了附点,这就是马丁原计划去柏林要见的人——他的挚友达尔文的缺席。由于达尔文的不在场,马丁的计划变了,他那将要脱口而出的全部计划得到了一个延缓。马丁开始在柏林城里一个一个拜访昔日的熟人,本来紧凑的节奏重又开始变慢。即使在最后一章达尔文终于出现,马丁原本充满期待的心情也变得沮丧,他没料到自己最好的朋友居然也不明白他为何闯入禁地。马丁就这样离开了柏林,从此杳无音讯。当达尔文沿着马丁曾走过的小径告诉索菲亚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之前激起人们的恐惧慢慢归于一种温柔的感伤。这样的安排具有一种结构意义,高潮前后的平缓反而让高潮部分更加突出,让人们大脑中最深的印象停留在马丁克服一切使他放弃前行的因素以及在火车上的恐惧与克服恐惧的那一段时间,而小说的主题由此得到凸显。
四、结语
作为一部久已被评论界忽略的作品,《光荣》至多被简单地当成自传式的作品来解读,但是,正如纳博科夫所说“《光荣》的乐趣在于别的地方”[9]。也许,《光荣》确实没有纳博科夫成熟时期的小说那样结构完美、诱人深入,但是,谁又能以作家成熟期的技巧来苛责他前期作品的构思呢?像许多研究者指出的,《光荣》体现出了纳博科夫作品主题和结构艺术的连贯性。而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在处理结构对主题的呈现关系上已经做到了足够的精致,是其令人叹服的美学成就的又一明证。
乍一看,《光荣》的故事发展稳定、均衡,无非是从马丁的童年写起直到他去往禁地,生死未卜。其实,这只是一个明晰的外部结构,马丁非法越境的计划从酝酿到实施都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中慢慢展开的。如果纳博科夫只搭建这样一个简单的框架而把主题按部就班地呈现出来,那么人们确实有理由对这部小说不以为然。但纳博科夫从来不会满足于这种均衡感,他将“森林小路”、“灯火”和“火车”这三个重要的主题意象分散在外部框架的各处,然后以暗示变化的时间、死亡阴影以及与禁地相连的爱情这三条线索将这些意象串联起来,最后辅以起伏的情感律动,从而使读者在前后切换、纵横交错中体会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嵌套在一起的契合感,而作者赋予马丁的光荣就在这整体和谐中散发出夺人眼目的光彩。
[1]Andrew Field.Nabokov:His Life in Art[M].Boston:Little,Brown,1967.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荣耀[M].石国雄,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
[3] Norman Page.Vladimir Nabokov:The Critical Heritage[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2.
[4] Edythe C.Haber.Nabokov’s Glory and the Fairy Tale[J].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1997(2).
[5]Vladimir E.Alexandrov.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C].New York: Routledge,1995.
[6] 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M].刘佳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8]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9] Vladimir Nabokov.Glory[M].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6.
【责任编辑 冯自变】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Theme in Nabokov’s “Glory”
LI Si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Glory”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imple and plain novel and therefore ignored by researchers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Nabokov created an external structur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to completely express the novel’s theme. External structure, clear and symmetrical, provided a steady frame to the theme while internal structure, complicated and subtle, connected with the external structure by means of the repeated images, three interwoven clues and the fluctuant rhythm. Therefore, the theme was glittering in this organic whole. And it can be perceived Nabokov’s extraordinary skills on the aesthetics of novel.
Nabokov; Glory; structure; theme
2016-06-06
李 思(1988-),女,河北唐山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6)06-0082-05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