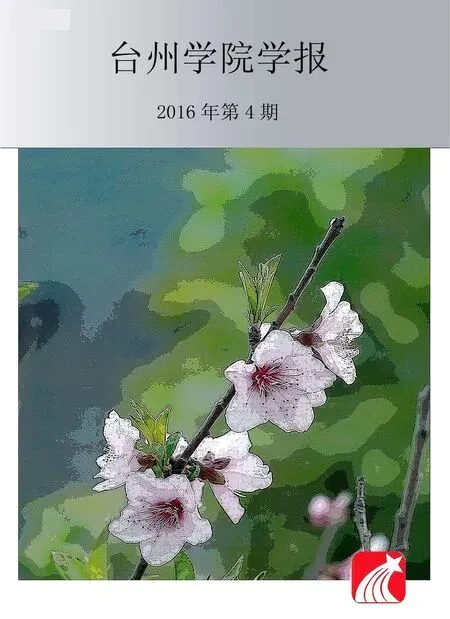诗体文学中的视觉节奏与翻译
2016-02-13毛静林董伟娟
毛静林,董伟娟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诗体文学中的视觉节奏与翻译
毛静林,董伟娟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文本节奏在中国长期以来被等同于格律,被视为语音领域的装饰性材料,这是对节奏的误解。文本节奏是动态言语的组织手段,表现在文本的音、形、义等各个领域。这些手段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参与文本意义、价值的生成,其中视觉表现是文本价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近现代诗体文学中尤其明显。译者必须系统解读文本方方面面的节奏表现,才有可能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重现其价值。
诗体文学;视觉节奏;翻译;节奏;格律
一、新旧节奏观
节奏是中国译界一个富于争议的重要话题,近百年来出现过三次大的讨论。首次讨论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初,是闻一多、郭沫若之间的内外部节奏之争。当时的主要参与者闻氏在诗论中提到“节奏”、“音节”、“格律”三个概念,并将三者等同混用,还提到格律表现在听觉、视觉两个领域。另一位热议者郭沫若提出,听觉表现不过是“诗歌的外在韵律”[1]337,其精神重在“内在韵律”(即情绪的自然消涨)[1]337。闻氏或许没有想到,他此番的“格律节奏说”被学界默认,在随后20年代中后期、50年代及之后的多次讨论热潮中,学者始终在其规约下研究节奏,如第二轮热议探讨节奏模式,学者们分别提出了从语音轻重角度出发的“轻重节奏说”和从语音单位的时值角度出发的“音顿节奏说”;第三轮有关诗歌形式的讨论主要围绕“格律”展开,如何其芳、卞之琳认为“顿”是新诗的基本节奏单位,林庚提出“半逗律”的概念,王力构建汉语诗律学等;八十年代后,出现了一些零星散论,也未能突破前人理论成果。
不可否认,近百年的节奏热论取得了一定成就:基本构建了学界比较认同的理论框架,对“格律”进行了较为全面且有一定深度的分析,这些都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些论断在揭示规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惑:其一,“节奏”与“格律”是否能够等同?后世将闻的“格律节奏说”坐实为规则,把节奏视为格律,对节奏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对格律的研究。那么文本节奏与诗歌的格律是否能够划等号?两者的性质、功能、意义是否完全一致?这一论断能否有效地解释文本中的一切节奏现象?其二,基于传统节奏观,学界历来对于诉诸语音领域的节奏表现关注较多,对其他领域的节奏表现关注较少。那么文本节奏表现是否仅仅限于语音领域?其他领域是否能够承载节奏?闻提到的“语形”与郭的“内在韵律”是否是节奏?如果是,具体模式又有哪些?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的节奏承载方式?
真正把这些困惑摆在人们眼前的,是近现代相继在东西方推广的新诗。这类诗歌不论语句铺排方式还是韵式都较旧体诗有了很大突破,“旧诗大体遵格律,拘音韵,讲雕琢,尚典雅。新诗反之,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2]。由于长期被格律束缚,国内传统节奏观在解读这类不拘字数、不拘格律的新诗时尤其显得捉襟现肘。
相比之下,西方诗学中的节奏观倒是较早挣脱了格律的桎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英美“新批评”等各派开始质疑传统节奏观,对其性质、意义等提出了新的观点。根据新型节奏观,节奏是“对言语活动——指索绪尔意义上的言语——的组织,它同时体现了话语的特殊性、主体性、历史性,和它的系统性”[3],而非“格律诗的特有属性”[4]51,一种外在的装饰性手法。曹红丹梳理了西方诗学视野下的新型节奏观后如是总结道:
“节奏是文本的组织形式,这就意味着翻译节奏不仅仅是对音调、音步等格律因素的再现,而是对文本中将形式和内容融于一体的言语组织方式的再现”[4]54;“由于节奏代表的是文本的特殊性,也就是文本的诗性及其价值,因此对节奏进行忠实再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令文本的诗性和文学价值在译语环境中获得重生的过程。”[4]55
如此一来,文本中的节奏就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方诗学中的新型节奏观:第一,节奏并非静态语言的装饰材料,而是动态言语的组织手段,因此,它的表现不仅仅限于听觉领域,而是表现在文本的听觉、视觉、涵义等各个领域;第二,节奏作为动态言语的一种组织手段,必然会系统地参与文本意义、价值的生成。因此,要忠实地传递源文本的诗性与价值,就需要从听觉、视觉、涵义等领域全面解析其节奏表现,并尽可能再现出来。可以看出,这种新型节奏观为解读音、形、义之于文本的价值,为解读诗体文学、乃至所有文学体裁的言语组织手段,为在译文中实现价值重现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试以这一观点为切入点,结合几首小诗,简要探析各领域中较少为人关注的视觉节奏表现,以及再现文本价值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二、文本视觉节奏与翻译
文本,尤其是诗体文学文本的视觉节奏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被几种模式所囊括,本文仅选取几种常见模式略作讨论,勉强充做前人相关研究的“续貂”之作罢。
(一)视觉重复与翻译。重复是文本的一种组织手段,适当地运用这种手段,可以收到美化语言、强化语气、渲染气氛、深化主题等艺术效果。重复可表现为韵式等听觉领域的复现,表现为字词句等涵义领域的复现,也可表现为语句排列方式等视觉领域的复现。最后这一点在诗体文学,尤其是在主要诉诸视觉效果的具象诗中表现尤为突出,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代表作A Red Wheel Barrel(《红色手推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诗共四节,每节一长一短顶格排列,这一偏离常规的排列方式自然不是信笔之作,而是匠心独运——特殊的诗形既隐约传递了载物时的负重感,又临摹了“手推车”这一实物,本诗的主旋律也在特殊版式中得以强化。某些译者由于没有深刻把握视觉价值,使译作偏离了原作之形,削弱了原作的艺术感染力。本文且以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经典之作Oh Captain!My Captain!(《船长,哦,我的船长!》)与江枫译本为例,简要探讨“重复型”视觉节奏在诗体文学中的运用以及对传递原作精神的一点启示(篇幅所限,仅选取第一节)。
O Captain!my Captain!our fearful trip is done;The ship has weather'd every rack,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
The port is near,the bells I hear,the people all exulting,
Whilefolloweyesthesteadykeel,thevessel grim and daring:
But O heart!heart!heart!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tain lies,
Fallen cold and dead.
江枫译: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目迎着我们的船从容返航,我们的船威严而且勇敢。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5]
19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林肯领导联邦政府军经过四年奋战后击溃南方军,废除了奴隶制,然而却在举国欢庆之际遇袭身亡。消息一出,全国震惊。惠特曼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创作了数篇诗作以悼念这位伟大的英雄,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
本诗一改传统律诗的规则与格调,在律式、修辞、语句铺设方面都做了大胆的突破,其中律式与修辞引起了广泛重视,而语句铺设这方面则鲜有论述。事实上,惠特曼创造性地运用了灵活的诗形,不拘泥诗行和诗节长短,甚至以诗形临摹实物,这种独特的铺设形式在构建文本价值、深化主题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同样值得学界关注。
熊沐清指出:“图形象似性指文本呈现某种可见的物理形式,与意义、意图、情感、效果之间有着摹写性的关联,或者形式与意义、情感、美学效果之间有着某种隐喻性或转喻性的关系。”[6]图形象似可以表现在语篇层面,如具象诗,从诗形来看,本诗就是一首具象诗。首先,诗歌主题与“轮船”有关,诗歌每节都由四长四短组成,长句部分长短不一,短句部分每行缩进一格,整体视觉效果就犹如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轮。以形拟神,此关联一也。船长是巨轮的最高指挥者、领导者,在人们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本文悼念颂扬的核心,而诗歌每节都把“船长”一词放在了最吸引人眼球的首行。以形喻神,此关联二也。长句部分呈现的意象为“奖赏”、“钟声”、“欢呼”、“旌旗”等等,内容蓬勃向上,让人感到激昂振奋,视觉上铺排不规整的四长句犹如迎风飘扬的风帆,风帆的联想意义也是积极向上、令人振奋的;后四句描写遇袭的船长,措辞有“倒下”、“死去”、“冷却”、“梦”等,给人沉痛悲怆之感,而逐行缩进的短句有似船舱,船舱是冰冷坚硬之物,同样容易引发沉重、悲哀的联想感受。以形应神,此关联三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创作者浓烈的情感不仅诉诸文字,更诉诸于形式,反过来,形式对内容的呼应又增强了文字的表意功能。本诗共三节,其意义、情感与形式之间的映射关系始终贯彻如一,主旋律也在不断重复的视觉节奏中得到强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抒情效果。
既然形式之于文本有如此意义,那么传递原作精神时就不能不小心对待了。可以看出,江枫的译本除内容的精心雕饰外,视觉节奏也基本上是亦步亦趋地复写了原文的模式,原因正如他所说,“译诗,形似而后神似。”[7]383
(二)视觉递进与翻译。递进是将语言按一定的逻辑次序层层推进的一种言语组织手段,适当运用此手段可使读者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印象。递进作为文本一种润色词句、装饰文采的手段,可以存在于语义、听觉、视觉等各个领域。情感的浓淡、音响的高低、语句的展缩,都可见递进。本文关注的是容易被忽视的视觉递进,以美国诗人克雷普西(Adelaide Crapsey,1878—1914)独创的无韵五行诗为例,此类诗体诗行依次加长,末行骤然缩短,如下面的这首November Night:
Listen……
With faint dry sound,
Like steps of passing ghosts,
The leaves,frost-crisp'd,break from the trees
And fall.
译一(译者不详):
听……
伴随干涩微弱的声响
幽灵般脚步
枯叶和着严寒,一同折断在树上
然后坠落
译二(辜正坤):
听啊……
卷脆霜叶
宛如幽魂脚步,
发着枯声悄然离树
而下。[8]
这首小诗分五行排列,音步数分别为1-2-3-4-1,视觉层递一目了然。翻译此类小诗自然应当遵循原作的形式,再现其创作特色。此外细读之下,我们还会发现独特的视觉模式并非脱离文字的刻意装饰,它与诗歌的内涵相连,与人类的认知相合,与人类的情绪相谐。本诗的主题是秋日的夜晚,诗歌氛围神秘而幽晦,随语句的渐次伸展,随意象与内涵的逐渐丰富,读者的潜意识慢慢被激活。顺次变化的诗行与诗歌内涵交织在一起,引领着读者感受缓缓展开的画卷,推动着读者的情绪一起脉脉流淌。叙述内容由少而多、由浅而深、欣赏者随之渐入佳境,整个欣赏过程平静、自然、和谐。从这一角度来看,诗形用意可谓深矣,译作非存其形而不能达意。
以上两个译本有诸多可评析之处,且不说其他方面与原作的吻合度如何,语句的铺排方式就颇不相同。译一完全抛开了原创渐次展开的诗形,以自由的散句翻译全文,文本的思绪情感完全被重置,读来感觉与原文意境出入很大。译二以顿代步,两字一顿,诗行逐层展开,引导着读者的思绪逐渐深入,且停顿模式为1-2-3-4-1,与原作的音步模式完全相符,因此相较之下明显强于译一。
(三)视觉参差与翻译。有一类诗每节行数多寡不均,每行字数长短不一,结构自由、诗形随义而转,其视觉节奏可归为参差式。这类诗视觉上能带给人一种错落有致的美感,表意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张力,能自如地传达更丰富、更细腻的情感,比起形式上有严格限制的格律诗,似乎更易于讨好广大读者。陈望道先生提及“变化”的艺术效果时,也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人类心理却爱好富于变化的刺激,大抵唤起意识须变化,保持意识的觉醒状态也是须要变化的。若刺激过于齐一无变化,意识便将有了滞钝、停息的倾向。”[9]新文化运动以来,此类诗歌就逐步取代旧体格律诗,占领了诗体文学的主流地位,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戴望舒的《雨巷》等;而西方主要出现于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和《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等。诗形如是,那么翻译时应当如何把握呢?本文且以英国诗人Mathew Arnold(马修·阿诺德,1822—1888)的名作Dover Beach(《多佛海滩》)与郭沫若、辜正坤译本为例(篇幅所限,仅选取首节)。
The sea is calm to-night.
The tide is full,the moon lies fair
Upon the straits;on the French coast the light
Gleams and is gone;the cliffs of England stand;
Glimmering and vast,out in the tranquil bay.
Come to the window,sweet is the night-air!
Only,from the long line of spray
Where the sea meets the moon-blanched land,
Listen!you hear the grating roar
Of pebbles which the waves draw back,and fling,
At their return,up the high strand,
Begin,and cease,and then again begin,
With tremulous cadence slow,and bring
The eternal note of sadness in.
郭译:
今夕海波平,潮满月如镜,海峡之上空,流光照遥境。彼岸法兰西,灯光时明灭,英伦森峭壁,闪烁而阢臬。请来窗边坐,夜气何清和!只见月光下,遥岸滚银波,请听细石音,随潮去复来,打上高岸头,方退又再回。万古恒如斯,音调徐而悲。[10]
辜译:
苍海静入夜。
正潮满,长峡托孤月;
看法兰西岸,灯火明灭。
英伦峭壁森森,光熠熠,
崖下风烟一时绝。
凭窗立,觉夜气清和透心冽!
远望,月洗平沙千万里,
排浪一线翻霜雪。
听!涛吼如咽,
潮卷砾石声威烈,
又回首,怒掷高滩侧。
才至也,又消歇,
慢调如泣轻吟处,
愁音万古声声切![11]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诗人,一生留下的诗作并不多,但他的诗篇比同时代人的作品更敏锐地揭示了工业繁荣景象之下的社会危机,《多佛海滩》就是这样一篇经典之作。该诗以多佛海滩象征看似繁华实则危机四伏的维多利亚时代,海滩远望潮满月圆,光华熠熠,一切都那么宁静美好,走到近处才发现海浪在咆哮、砾石被卷起又抛下,大海呜咽不已,远不似那般平静和谐。
全诗共四节,每节语句长短不一,如此排列的诗形自然有其深意:一方面,本诗的主题是暗流汹涌、象征着岌岌可危的社会的大海,而参差不齐的诗句恰好有似于汹涌澎湃的海浪;第二,创作者的思维与作品形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思维的规整严密可表现为形式上的规整严密,同样地,思维的萌动奔流也可表现为形式上的萌动与奔流。诗人对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于日益沦丧的古文明,对于无数人沉醉于迅速繁荣的工业,而对繁华背后的罪恶毫无知觉感到忧虑彷徨,眼前澎湃的海滩景象恰好触动了诗人的敏感神经,令他不吐不快。在这种激烈冲突的心理状态之下,挣脱了形式束缚的散句确实更能承载诗人那种奔泻愤懑不能自已的情绪。
郭译以工整的五言律诗译之,虽然看似内容未做太大改变,但意境情趣改变太大,读来更像是峨冠博带的老夫子在摇头吟咏,原诗英伦才子凭海吟叹、收放自如的意境情趣完全感受不到了。相比之下,辜译要折中得多。它以散曲体译之,保留了原诗参差的诗形,如此一来,诗形对主题的呼应、诗形承载的情绪也就都保留了下来。因此,不论“形”还是“神”,辜译都更接近原作。通过译本对比可以看出,在重现自由诗意象和艺术效果方面,选择散句有其必然性,在民族化的过程中“强求莎士比亚或拜伦、雪莱全都穿上长袍马褂”不讨好[7]382,也没有必要。
三、结 语
数十年来,学界把节奏等同于“格律”,把它视为“语音领域的装饰性材料”,这是对节奏的误解。事实上,它在自由诗面前的苍白无力也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如西方诗学所论,节奏应当是一种动态言语的组织手段,有其主体性、特殊性、系统性、历史性,表现在具体文本的音、形、义等各个领域,这些组织方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参与文本意义、价值的生成,而视觉表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并不只是内容的外衣、信息的载体,在多数情况下,形式就是内容,载体就是信息,这一点在现当代诗歌中表现得尤其明显”[7]381。作为译者,必须尽可能参透原作方方面面的节奏表现,以期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重现文本价值。
[1]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诗三札[M]//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康白情.新诗底我见[J].少年中国,1920(3):1-14.
[3]Meschonnic,Henri.Poétique du traduire[M].Lagrasse:Verdi⁃er,1999:29.
[4]曹丹红.西方诗学视野中的节奏与翻译[J].中国翻译,2010(4). [5]江枫.美国现代诗抄[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7-8.
[6]熊沐清.试论诗学象似性的涵义与形式[J].外国语文,2012(6):11.
[7]江枫,许钧.形神兼备:诗歌翻译的一种追求[A].海岸.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9]陈望道.陈望道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5:42.
[10]郭沫若.英诗译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1.
[11]辜正坤.世界名诗鉴赏词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83-385.
Visual Rhythm of Verse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Mao Jinglin,Dong Wei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Taizhou University,Linhai,Zhejiang 317000)
It has been long in China since textual rhythm was identified with meter or was taken as ornamental material in voice.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it.Textual rhythm,actually,is an organiz⁃ing device of dynamic parole which can find its expression in voice,form and meaning of text.All those devices are organically combined to construct text value.Among them the form constitute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it,which is even more distinct in the verse literature of modern times.Consequently,translators cannot reproduce value of source texts to the utmost before the analying it comprehensively.
verse literature;visual rhythm;translation;rhyme;meter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6.04.011
2016-04-28
本文为台州学院2015年校立培育基金研究课题“文学作品中的视觉节奏与译文价值重构初探(2015PY005)”研究成果之一;台州学院2016年校立培育基金课题“熟语的概念隐喻研究——以台州方言中饮食类熟语为例(2016PY012)”研究成果之一。
毛静林(1977-),女,湖北十堰人,讲师。董伟娟(1979-),女,浙江临海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