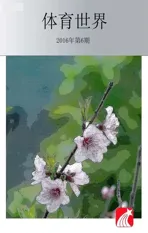从怒族的源流与分布审视其民族传统体育
2016-02-13杨晨飞张帆
杨晨飞 张帆
从怒族的源流与分布审视其民族传统体育
杨晨飞 张帆
本文从地域性自然选择与非自然选择过程中伴随的适应与斗争双向矛盾入手,证实人类迁徙过程中所产生的融合与斗争现象为人类再次从自然获取生存价值提供依据,这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自然矛盾与独特文化之间的互为存在关系。利用此关系,从怒族迁徙源流中爬梳其肢体活动的地域性适应,最终得出怒族的肢体活动是极具地域性特征,并依地域特点而出现独特且又具有共性的肢体活动。由此,本文最终论据所证实怒族肢体活动具有不稳定性,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对怒族肢体活动的限制是矛盾地,并且是不客观地。
怒族;迁徙;融合;民族传统体育
10.16730/j.cnki.61-1019/g8.2016.06.023
1.引言
人类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矛盾与适应。矛盾的膨胀,让人类自身开始反思生存的意义,反思的结果是私欲的产生与高涨,血腥残酷的斗争油然而生,成为矛盾膨胀的显性表现形式。显性的表现形式促使矛盾的本体剥离处于弱势的一部分人类,迫使这部分人类开始背离起初所生长的地域,迁徙于另一种地域中。在迁徙过程中,所到地域已有类似于迁徙类人类聚集群体或是依地域早期发源的人类聚集群体。被迫迁徙的人类聚集群体将会同此地域已存在的人类聚集群体产生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一部分会适应其地域融入其中,另一部分又将会踏上迁徙的路途。还有少部分虽然会适应新地域存留下来,但不与原住人类聚集群体发生融合,而是独立在原住地域人类聚集群体周边,产生同地域的不同人类聚集群体。若将此行为归结于自然,那就印证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自然选择留下与遗弃是按人类发展规律不断进行的,通俗地说是为人类从猿走向智人或更高层次提供的一剂良药。
考察怒族的民族源流,须对云南整体民族分布、源流及迁徙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对“迁徙”与“融合”得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与模式构架。“融合”的基本形式为A+B=C或A+B=A、A+B=B。融合形式有自然融合和非自然融合两种。自然融合的基础是自愿、团结、互助、共生、共荣,通过杂居、通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的互相和渗透,其中一个或几个民族丧失自己的特征,而变为另一个民族。也有经过相互对抗、冲突,而实现的非自然融合。[5]融合与迁徙的构架体现了迁徙对于融合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融合又反作用于迁徙,并使人类聚集体向更高层次发展,逐而出现人类聚集群体发展快慢的不稳定状态。
2.怒族现分布状况及源流研究对其民族传统体育多元内核的分析
2.1怒族现分布状况及源流研究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始对境内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在识别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地域分布不同,但语族、语系相同的怒族。从而构成了依地域划分的4个怒族支系与按语族、语系划分的2个语群部。
据何林在《“怒人”是谁?——文化视野中的怒族源流》一文中所考查的结果:怒族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辖的贡山、福贡、泸水、兰坪四个县:1.“阿怒”,也称“贡山怒族”,……。此外,居住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察隅县察瓦龙乡所辖松塔、龙普两村的门浪人大部分自认与贡山“阿奴”和独龙为同族,使用同种语言,……。2.“阿侬”,主要居住在福贡县的上帕镇、鹿马登、架底等乡镇,……。3.“怒苏”,主要聚居于今福贡县匹河、子里甲乡等地,原属碧江县,称“碧江怒族”,……。4.“若若”,也称“兰坪怒族”,居住在兰坪县兔莪乡和泸水县鲁掌镇,……。此外,在维西县还散居少数怒族,约200人。[6]从上述怒族分布情况看,怒族在早期可能有过多次的迁徙。
高志英在《唐代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一文中说:“聚居于怒江、澜沧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怒族为远古氐羌系统民族,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后演变而来的,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7]同时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出现了羌、髳、濮、劳浸、靡莫、滇、嶲、昆明等众多的族群部落。[8]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氐羌系统民族在夏时期以前就已迁徙入云南,并逐渐与古云南土著融合构成更为庞大的人类聚集群体。
战国时期与怒族族源及地域较为相近的方国是昆明国。昆明国主要民族是昆明族,昆明族源是氐羌系的游牧民族,昆明国范围在今洱海附近,昆明国历史沿革至西汉初。三国时期所载昆人和叟人是今天中国西南一些藏缅语族民族的先民。[15]唐代前期,洱海地区诸部分为“乌蛮”与“白蛮”,乌蛮包括昆明蛮、哀牢蛮、磨些蛮,同汉代及三国时期的分布与名称极为相似,只是人口数量不及先前,主要原因与汉族的迁入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做造成的。乌蛮主要从事游牧业,他们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具有游牧民族尚战死,恶病亡的剽悍之风[16]。南诏时期,汉代的昆人称为叶榆蛮,主要有施蛮、顺蛮组成。南诏破剑浪后迁长裈蛮与施、顺蛮杂居,后一起迁到云南东北诸川,后又被牵至铁桥节度的剑羌(今永胜一带)。[17]元代时期,怒族与傈僳族先民被称之为“卢蛮”,并与彝族先民统称为“卢鹿蛮”(也写做“卢蛮”、“潞蛮”)[18]。据《元一统志》记载‘元代“卢蛮”族称,与丽江路(元代行政区划)其他蛮类族称并列。明代,居住于金沙江流域的“卢蛮”后裔“傈僳蛮”再次迁徙,此次迁徙如同唐朝时的迁移一样属于非自然迁徙,是由于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吐蕃的战争问题。在这次迁徙中的“傈僳蛮”与元代迁徙的“卢鹿”蛮相融于澜沧江一带。通过对怒族民族源流历史考察,可以认定怒族是在民族交融与迁徙之间矛盾的徘徊,为了生存不断在地域问题中适应与徘徊,这也造成民族缓慢行走在人类进化里程中的早期阶段。
2.2民族传统体育多元内核的分析
从对怒族本源的考察发现,其早期是存在于一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中,在这个民族共同体中,有诸多原因塑造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就现在的怒族而言,在早期随时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民族中的一员,但这不妨碍其为适应特定地域而形成特定的体格与肢体运动。因生存所迫,使只要在此地域生活的人都要从事适应此地域的体格变异与肢体运动。例如在汉代的怒族先民共同体之一的昆人,据史料记载曾阻挡过汉武帝通往身毒,迫使汉武帝在长安城修筑仿洱海的巨大人工湖泊来训练水军。从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昆人此时应已适应的了此地的环境,从而能从事水中的作业。又从怒族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也可以看到关于水事的项目,譬如竹筏、猪槽船、竹管水枪等,这足以说明有关水或借用水产生的肢体活动。
从碧江怒族普遍行父子连名制[19],可以看出其早期曾与彝族同属一源。因为南诏国是彝族早期人类聚集共同体所创造的,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的融合逐渐分成乌、白蛮之分,南诏国上层王室基本属乌蛮,而乌蛮使用的也是父子连名制。再从历史考察中也可看到相符的记载,如上述南诏时期迁施、顺二蛮驻今永胜县等。考察的资料能清楚地说明,怒族先民曾与南诏政权发生过融合与斗争,如果有斗争必将有军事的训练,曾经的军事训练较为残酷,以杀死对方或制服对方为目的。这使在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难以充分且直白的展示,但还是有一些具有攻击性的体育项目,如踢脚、摔跤等项目,也有诸多可推测为辅助军事训练的项目,如爬绳、爬竹竿、跳竹等。怒族在非自然的选择过程中也不只是经历过一场战争,而是始终伴随着怒族的人类进程,例如贡山怒族的“库噜羌”舞蹈,是受藏文化的熏陶,据历史记载曾受察瓦龙藏族土司的管辖。两种选择的对抗,终其根本是为了人类的进步,但进步是要付出相等的代价,这种相等的代价也体现在了怒族现居地域的生活方式上。怒族现居地域基本上属高山峡谷。为了适应地域,一代一代的怒族先民付出着沉重的代价,族群的独立与存活是怒族先民沉重代价所换取的慰藉,逃离强势民族的管辖与融合是惟一的途径。在恶劣地域环境的适应过程里,怒族先民总结着存活经验也开发着所积累的经验。怒族在适应地域条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培养体系:怒族男孩在四五岁后,开始利用长辈所赠的弩弓射猎一些小型禽类;六七岁后,陪伴父辈狩猎,并熟悉动物的习性、脚印及粪便;八岁后,开始任务性的捕获攻击性较小的猎物;十岁后,开始学习设置陷阱及练习性的提高弓箭及弩箭的使用方法;十三岁后,开始与父辈们进行围猎活动;十四岁后,开始捕获喜独行的大型猎物;十六岁后,便属于成人,开始参加氏族内的一切活动,并着手培养下一代。[20]但在怒族内部,依地域也产生了民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就若若怒族现居地外,其余三个怒族分支看,生活地域均是高山峡谷,并与傈僳族、独龙族杂居。这种分布使有些肢体运动是属于此地域所共有的,并不是独有的项目,如过溜索、爬绳梯等地域条件限制必须从事的肢体运动。而若若怒族较其余三个怒族所居地平坦、宽阔,这种地域所提供的基础需求远远高于山地所赋予,对外的交通也相对便利,就促使若若怒族对外交流远比身处山林之中的同族怒族频繁,但这也造成了内部文化多元与混杂,肢体运动的模式也多是附庸于宗教祭祀或是外来民族文化支配下,使若若怒族具有了类似怒球、打陀螺、秋千及多种舞蹈形式的肢体运动。
利用历史学、人类学角度对怒族分布状况及族源的深入考察,逐步发现了怒族内部自然与非自然选择造成的族支分布不均导致的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样性问题。也充分说明了怒族因于地域不同构成的生产经济方式、对外交流元素的不同。高山峡谷交流的限制让生活在这里的怒族、独龙族、傈僳族具有文化的共通性及肢体运动的相似性,但又因分布的不同产生一定的差异,不可排出的是此三个民族又有氐羌族性的共性。兰坪县居住的若若怒族,地理环境较平坦,从现居民族考察可充分说明若若怒族的多元文化的产生。若若怒族族性本质中虽存在与高山峡谷怒族共同的氐羌族性,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优势,藏族、汉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彝族均有聚集居住,导致怒族或多或少的吸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内核,以致若若怒族的文化多元性,同时也造成肢体运动的多元化。
3.结论
人类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融合与迁徙,此二者较容易在人类聚集群体庞杂的地域中出现。云南地域中为何出现较多人类聚集群体的汇聚,除了自然与非自然的选择,更多的也许与云南元谋人出现有很大的关系。自然选择让生存在不同地域的人类进行融合,构成新的群体,进而使人类大脑及肢体不断进化,因进化产生对地域与自身关系的认识,逐渐出现了民族文化。非自然的选择在自然选择的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出现,人类对于精神需求的渴望促使生存基础需求的不足状况出现,为了满足基础寻求,矛盾产生,迫使进一步的迁徙出现。在开篇引言中曾说过非自然选择的自然选择性,即人类对于地域生存条件的不适应,也是促进迁徙的一条途径。云南因是人类鼻祖—元谋直立人出现的地域,人类自然与非自然选择的必经区域,所以造就了不同的人类聚集群体,即现在的民族。从上述方面的研究,可以充分说明某一个民族的肢体运动项目,并不是固有和不变的,而是充斥着多元性及不固定性,肢体运动更多是源于地域的适应、文化的交流。诸多历史资料里,我们也能看到许多详细的记述说大多数少数民族生存条件是极其恶劣的,每天都在与自然界的对抗中艰难存活。设想这样艰苦的生存,何能再去从事现所谓的“民族传统体育”?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民族传统体育”是否有违背人类进化的嫌疑?据人类现发展状况看,全球化促使民族文化的大交融,且又将带来更进一步的人类进化,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否是对“民族传统体育”词条的一种莫大的讽刺?
[1]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3—164.
[2][4][5][8]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0,21,29,301
[3]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21.
[6][9]何林.“怒族”是谁?—文化视野中的怒族源流[J].昆明学院学报,2012(4):70—71.
[7]高志英.唐代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J].学术探索,2004(8):102—106.
[10]李方桂.中国语言和方言[J].民族译丛.1980(1):3—9.
[11]西天龙雄.藏缅语群藏语族概况[G].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83.
[12]孙宏开.怒族柔弱语概况[J].民族语文.1985(4):65—80.
[13]谢飞.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G].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汉藏语言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32.
[14]博爱兰.怒语(怒苏)系属研究[J].语言研究,1989(1):133—151.
[15]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195.
[16][17]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11.116-145
[18]高志英,李珊娜.中缅怒族与傈僳族的分化与交融[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7):018版.
[19]刘达成.怒族[J].思想战线,1980(2):69
[20]赵静冬.云南省特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189.
杨晨飞(1989-),男,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助教,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