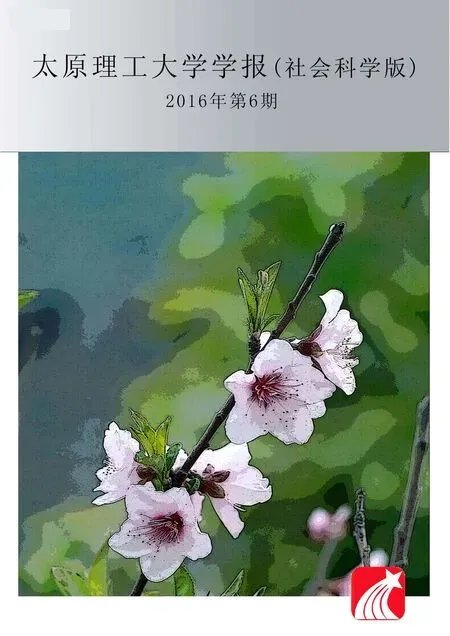论晚明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与形式意味
2016-02-10吴衍发
吴衍发
(安徽财经大学 文艺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论晚明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与形式意味
吴衍发
(安徽财经大学 文艺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基于一般艺术学的理论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考察晚明绘画、戏曲、音乐、舞蹈、工艺美术、园林等门类艺术的本性观念和感性形态,揭示其共通的情感本性和形式意味。晚明各门类艺术都把情作为艺术的本质,把情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性,致使晚明艺术主体的情感意味更加浓厚,艺术形式的审美意味愈益强化,从而拓展和丰富了中国艺术的情感本体论研究,真正建立起中国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影响深远。
晚明;情感本性;形式意味;感性形态;艺术观念
晚明艺术在本性上是以“情”为内核,以感性形态为外在表现形式,是内在情感与外在感性形式的统一。晚明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人文主义思潮,与建筑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市民文艺相结合,形成了晚明艺术在继承宋元传统中重在衍变、力创新风的趋势,带来了市民文艺的蓬勃发展和狂放激情的浪漫主义艺术思潮,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晚明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
受广泛传播的心学之影响,晚明文人对情感的认同成为艺术的一大特征。在世人对程朱理学的抵制与反对中伴生着对情的欣赏和接受。理学的解体,为晚明带来了一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本主义思想解放潮流。这场思想解放潮流为晚明文艺创作开启了思想先河,打下了理论基础,把市民情趣、日常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来描写,对晚明艺术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和推动。
谈到文人画,董其昌提出“文人画”概念和“南北宗”论,奠定了文人画的崇高地位,而其与其他绘画流派相异的最本质特征即在于它的抒情言志。中国画向来重视生命,视生命为画的最高纲领,而这种对生命感的追求,是看重画中生机、生趣、天趣、意趣、生意的表现。谢肇淛说:“今人画以意趣为宗。”[1]高濂提出“天趣、人趣、物趣”三者,以得“天趣”为高,并谓“求神似于形似之外,取生意于形似之中”[2]48。李日华指出:“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2]50唐志契也强调:“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2]51凡此等等,无不充分体现出晚明文人艺术家对生命精神的追求,也与文人画在当时的发达有密切关系。文人画家游心于画,以绘画形式来显现生命情感,正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3]170。徐渭的水墨大写意画,酣畅淋漓,墨色滋蔓,尽显氤氲流荡之态,可谓“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充分表现出淋漓的宇宙生命和艺术家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徐渭题《雪竹图》诗曰:“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题《四季花卉图》卷云:“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杂四时。莫怪画图差两笔,近来天道壳差池”。正是由于董其昌的主盟和“南北分宗”的提倡,文人画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与诗文、书法进一步融合,带来了晚明文人画的发达与繁荣,而其所特有的自娱性和抒情性特征,使艺术的情感属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晚明以戏剧为主流的表演艺术,其情感性亦非常突出。在人类艺术史上,“戏剧是一种表现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艺术。可以这样说,戏剧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一种生命意识的高扬”[4]。因此,从本质上说,戏剧艺术是“一种重在抒情也长于抒情的戏剧”[5]。戏剧艺术的情感本性经过元曲的繁荣发展和元人的实践探索,已经为晚明文人艺术家所熟悉和了解。明人何良俊指出:“《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2]404。潘之恒在《鸾啸小品·曲余》中认为,那些最著名的中国古典戏剧皆出自于情。他说:“推本所自,《琵琶》之为思也,《拜月》之为错也,《荆钗》之为亡也,《西厢》之为梦也,皆生于情。”曲论家王骥德在《曲论·杂论》中强调戏曲的情感性特征:“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6]160。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词和曲各文体之间的抒情性有其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最终曲能取代诗和词,就在于曲具有诗和词不可同时而语的“近人情”之艺术魅力。明人黄龙山在《新刊发明琴谱》序曰:“夫琴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则吾心之所出也。”[7]367-368曲论家张琦在《衡曲塵谭》中亦提出“曲之道”乃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他说:“子亦知夫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灵窍隐深,忽忽欲动,名曰心曲。曲也者,达其心而为言者也。”“曲之为义也,缘于心曲之微,荡漾盘折,而幽情跃然,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8]晚明传奇多以才子佳人为传统题材,擅长言情,正因为此,晚明人张萱所辑《西园闻见录》宣称:“诗言志,今俗乐词曲,各陈其情,乃其遗法也”[9]。著名戏曲大师汤显祖极力标举“情至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可以说是其“情至说”的纲领。而他的千古绝唱《牡丹亭》即是一首“至情”的颂歌,剧中女主人公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为爱情死生以之,终成为爱情浪漫主义的宣言书。《牡丹亭》的情感内核,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时人王思任即谓:“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消肌栗。”王思任还认为《牡丹亭》的“立言神指”即在“情也”,“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2]448。再者,孟称舜的《桃花人面》也是一首歌唱爱情的颂歌,其《娇红记》演绎了以身殉情的大悲剧;周朝俊的《红梅记》是一首争取爱情与反对暴政的悲歌。凡此等等,这些戏曲均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醒意识,洋溢着不受羁绊的浪漫主义激情。
然而,若对晚明艺术的描述仅仅局限于绘画和戏剧,当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说清晚明艺术的情感本性,虽然它们代表了晚明艺术的主体,但毕竟晚明艺术种类繁多,且呈全面复兴之势。事实上,若考察晚明其他诸种艺术形式,同样也能很容易发现情感本性是其共同的属性。中国传统艺术中,音乐、舞蹈与戏剧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它们都是抒情、表现情感的艺术形式,其中音乐是最心灵化、最浓于抒情的一门艺术。李梦阳指出:“音”乃“发之情而生之心者”,天下“无非情之音”(《结肠操谱序》)。艾浚《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引》认为,曲乐在价值功用上与《诗经》相通。他指出:“乐府古有之,亦皆本乎诗也。《诗》三百十一篇,皆古人歌者;世降时异,变而为词为曲,咸以乐府目之。盖诗与乐府,名虽不同,而其感发惩创,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则一耳。……情由外感,乐自中出,言真理到,和而不流,诚为治世安乐之音也。依腔按歌,使人名利之心都尽,拟诸古之乐府,语虽深浅,其乐天知止之妙,岂相矛盾哉!”[7]361艾浚对曲乐的认识,以及从“情”出发对音乐价值的探讨,自然代表了明中期以来大多数文人的共识。晚明人张萱所辑《西园闻见录》还指出:“诗言志,今俗乐词曲,各陈其情,乃其遗法也。”[9]被卓珂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赞为“我明一绝”的民歌俗曲;冯梦龙在《山歌·序言》中则为之下一断语曰:“皆私情谱耳”。另有明末琴学家徐上瀛所谓“琴即心、乐即情”之观念,以及李贽所谓“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焚书·读律肤说》)。凡此等等,足以说明音乐的情感本性。既然音乐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因而它必然与人的性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本质上必然是人的情感的表现。舞蹈艺术方面,王世贞认为戏曲舞蹈能深入到人物之内心,情感表现具体而又细致,即其所谓“体贴人情,委屈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2]411。朱载堉《律吕精义外篇》卷之九《论舞学不可废》亦指出舞蹈的起源及其缘情本质:“盖乐心内发,感物而动,不觉手足自运,欢之至也。”[10]晚明文人写意园林更离不开“情”与“趣”二字。文人园林艺术源于艺术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追求味象畅神,抒写情志,以景写情,随兴适趣,体现了艺术创作主体的人品和人格。园林艺术讲究意境的构造,文人“构园”立足心性,充分运用写意手法,“一拳代山,一勺代水”,心物相应,情景交融,这种诗情画意的意境之美,正是艺术创作主体心灵和情趣的反映,所谓“文之极也”、“从于心者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晚明书画及戏剧,抑或是音乐、舞蹈和园林等艺术形式,“情”都构成了它们的基本内核。所有这些都表现为晚明狂放激情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二)晚明艺术的感性形态和形式意味
从晚明艺术作品构成来看,无论是造型艺术,书法、绘画、工艺美术、雕塑和园林等,还是表演艺术,戏剧、音乐、舞蹈等,当然还包括语言艺术,诗歌、散文、民歌和小说等,它们往往都是文人艺术家情感与生命的灌注,皆有着相当完整的审美形式,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感性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因此,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也就是说,“艺术家创作的是一种符号——主要用来捕捉和掌握自己经过组织的情感想象、生命节奏、感情形式的符号”[11]。这些以感性形态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是晚明文人内在情感生命和丰富个性的真正显现,能最大限度地传达并表现出晚明的艺术本性和时代精神。
中国书画艺术主要由线条、色彩和笔墨构成,它们不仅是中国书画艺术的基本造型语言,也是构成中国书画艺术“有意味的形式”的核心要素。中国书画艺术的基本样式及书画艺术观念的确立,基本上都与此三者相关联。清人盛大士说:“画以墨为主,以色为辅。色之不可夺墨,犹宾不可溷主也。”[12]也正因此,笔墨成为中国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和媒介材料,也是中国水墨画的基本语汇。在用笔与象形的关系上,唐人张彦远作了经典性的总结和说明:“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2]19。董其昌几乎把笔墨视为山水画中的最高表现。他在比较笔墨与造型的关系上指出:“以蹊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5]217董氏对笔墨大为提倡,并在山水画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但一股强大的复古潮流,把重笔墨、轻造型演为重古人笔墨、轻师法造化,并进一步演为对自然和人生世界的忽视。被千百次重复而非活用的笔墨,也就失去了它曾具有的描绘与表现世界的活力[13]。
“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他说:“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地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14]“有意味的形式”用以阐释造型艺术或视觉艺术的本性,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它能让人感受和体验到由审美情感所激起的那种深层意蕴、情致、趣味和精微绝妙的艺术个性。中国书画艺术是由线条、色彩和笔墨等形式因素按照某种特殊关系组合成的抽象形式,能够唤起欣赏者无穷的审美情感,真正称得上是“有意味的形式”。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式化的、规格化的,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但“有意味的形式”却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于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中国书法艺术,这些净化了的线条,行云流水一般,犹若音乐旋律,疏密起伏,曲直波澜,有柔有刚,方圆适度,表现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而中国绘画艺术的笔墨更加耐人寻味。“毛笔、水墨依照一定程式在纸、绢、壁上作画时产生的点、线、面、团、叠加、渗透、摩擦、转折,行笔疾徐、轻重、粗细,用墨运水多少所产生的光涩、枯润、曲直、方圆、厚薄、齐乱种种效果,这些效果引出的刚柔、遒媚、老嫩、苍秀、生熟、巧拙、雅俗种种感受,画家内在世界、外在操作与这些效果、感受的诸种关联,以及人们在创作、欣赏过程中形成的对它们的感知方式与习惯,都凝结在笔墨话语之中。”[15]“中国画之美就美在笔墨。”它凝聚着中国文化独有的意味与气质,气韵生动、生机盎然,活泼的生命力荡乎其间,不仅彰显了艺术家丰富的内在情感和独特的人生体验,同时还唤起了欣赏者的审美体验与情感。
戏曲方面,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顾曲塵谈》[16],论及填词度曲之道,既详且尽。戏曲主要由宫调、音韵、生旦净丑角色、动作及服装、道具、灯光、布景、音响等组成,在多种乐器的伴奏中,通过角色在舞台上的唱、念、做、打等具有装扮性与程式化的表演,以代言体的方式,诉之于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以真实、生动的形象传达社会生活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人类发明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借以对自身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环境进行一次直觉的、形象的再体验,从而娱乐自己、欣赏自己、认识自己、批判自己、升华自己,优化和扩大生存的空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体现着人类‘自由狂欢’的精神并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17]。戏剧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宫调、声韵、曲牌(曲谱+曲词)、词调、曲律及虚拟性和程式化动作等诸多方面。戏曲中的唱段,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抒情性最强。王骥德《曲律》曾从丰富多彩的发音效果入手,以“美听”为尺度,对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十九韵目”进行了多层次划分。王氏说:“东钟之洪,江阳、皆来、萧豪之响,歌戈、家麻之和,韵之最美听者。”[9]153王氏用“洪”“响”“和”等概念,来描述“东钟”“江阳”“皆来”“萧豪”“歌戈”“家麻”等韵目,其中的审美“意味”不言而喻。王氏还评述“支思”韵“萎而不振,听之令人不爽”,更体现了有“有意味的形式”之谓的声韵作为一种鲜活生命的运行状态,也说明和强调了声韵的选择要与表现情感相适应的选韵原则。再譬如戏曲宫调,“宫调者,所以限定乐器管色之高低也”[16]7,所谓“宫调声情”,即是对宫调所具有的特殊“意味”之概括。“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诸如“仙吕调清新缠绵,南吕宫感叹伤悲,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道宫飘逸清幽,大石风流蕴藉,小石旖旎妩媚,高平條物湟漾,般涉拾掇坑堑,歇指急併虚歇,商角悲伤婉转,双调徤捷激袅,商调凄怆怨慕,角调呜咽悠扬,宫调典雅沉重,越调陶写冷笑”[18]云云,说明戏曲的宫调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抽象形式,而是一种具有情感意义的“有意味的形式”。曲牌因关联到不同之宫调(情调)与节奏,因而要求曲作家填曲时要使曲词之情与曲调之情融合无间,相得益彰。故此,吴梅先生再三强调:“先将所填曲中情节,悲欢喜怒之异,辨析清楚,然后择定用某宫某套(如仙吕宫之[忒忒令]一套,宜清新绵邈,越调之[小桃红]一套,宜陶写冷笑,皆详《南曲谱》中),再将《南词定律》检出所用各曲,依谱填之,则自无位置舛错之病矣”[16]30-31。吴梅先生之说,再次强调了宫调、曲牌、词调皆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另外,戏曲中有“做”与“打”的动作。舞蹈动作显然是对表演动作的美化,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无不经过了艺术的加工提炼。譬如“上楼下楼、开门关门、赶路行走、坐船驾车等,从形式上看,一个动作过程就是一段舞蹈,即连写字睡眠、绣花喂鸡等等,都带有浓郁的舞蹈感和舞蹈姿相,甚至角色的上下场,也是上场有上场舞,下场有下场舞”[19]13-14。这些虚拟化和程式化的动作,是主体审美意识对现实生活动作的超越,是自由地抒发主体精神的表现,当然它们同样亦能体现出戏曲表演艺术的形式“意味”。正因此,蓝凡先生指出,“中国戏曲的一切表现形式(手法、手段等),如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演员的演唱、唱腔的安置、色彩的设计等等,不仅是为了抒发感情,而是整个儿地‘情化‘了,更确切地说,它们本身就是感情的‘化形’或‘物化’”[19]40。所以说,音韵、宫调也好,曲牌、词调和舞蹈动作也好,一方面,它们皆是所谓纯粹的抽象形式;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相应的情感载体,皆因应着某一情感,而情感则将这些形式与音韵、曲牌等统领谐和起来,构成一种融合无间的“有意味的形式”,可以让观众尽情享受悦耳之美、娱目之妙。
(三)结语
中国古代艺术本性观念,“往往是从情感的表现和艺术对情感的作用出发进行观察和探讨的,因而,艺术的情感本性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本性观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本质特征。中国古代艺术史上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艺术本性观念,主要表现为儒道禅对艺术与情感二者关系的体认上。儒道禅皆把艺术的本性与情感相连,强调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艺术的功用和使命在于表现情感。儒道禅对中国古代艺术情感本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同样,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
晚明艺术秉承和丰富了中国艺术传统中以“情”为内核的艺术本性,而且晚明戏曲、文人画、小说等艺术理论成果亦很丰硕。丰富的情感论为艺术与理论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晚明文人艺术家多是任情适性之辈,他们在阐述自己的艺术本性观念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情”,将其视为艺术的内核与本性,成为一种本体性存在。于是,艺术的情感本性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成为晚明文人艺术家群体相当普遍的艺术观念。尽管“情”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之内核而贯穿始终,但把“情”提到创化万物的本体论高度而又如此普遍一致的艺术本性观念,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正是到了晚明时才真正形成和建立起来。在晚明艺术活动中,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深度转型,导致人们审美观念的大变迁,传统审美的主流地位逐渐被大众审美所取代,世俗大众的现实生活和世俗情感成为文人们关注的重点,艺术活动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晚明文人对艺术情感本性的探讨,加深了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拓展和丰富了中国艺术的情感本体论研究。
[1] (明)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35.
[2] 周积寅,陈世宁.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辑注[G].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M].屠友祥,校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 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3.
[5] 付瑾.中国戏剧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113.
[6] (明)王骥德.曲律[G]//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7] (明)黄龙山.新刊发明琴谱·序[G]//易存国.乐府神韵(文献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67-368.
[8] (明)张琦.吴骚合编小序[M]//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3.
[9]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五十《礼部》九《乐律前》[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10] (明)朱载堉.律吕精义[G]//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11]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29,455.
[12] (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G]//俞剑华.画论类编.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262.
[13] 郎绍君.论现代中国美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137-138.
[14]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周金环,马仲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
[15] 郎绍君.笔墨论稿[J].文艺研究,1999(3):222.
[16] 吴梅.顾曲塵谈中国戏曲概论:第一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7] 俞为民.曲体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3.
[18]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G]//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31.
[19] 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20] 吴衍发.中国古代艺术情感本性观念发微[J].齐鲁艺苑,2014,138(3):106-109.
(编辑:陈凤林)
第34卷卷终
On the Concept of Emotional Nature and Form Meaning of the Late Ming Art
WU Yan-fa
(SchoolofLiteratureandArt,Anhu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ngbuAnhui233030,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eneral art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concept and emotional form of such art categories as painting, opera, music, dance, arts and crafts, gard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reveals their common emotional nature and form meaning. All art categories regarded emotion as the nature of art, promoted it to the ontological height, and endowed it with a new era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ich brought about stronger emotional meaning of the artistic subjec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which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the aesthetic meaning of the art forms. As a result, the emotional ontology study of Chinese art was further expanded and enriched, its concept of emotional nature was set up in the real sense. And thus all these have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
the late Ming Dynasty; emotional nature; form meaning; emotional form; artistic idea
2016-10-14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晚明书画消费与文人生活”(16BA008)
吴衍发(1974- ),男,安徽金寨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
J0
:A
:1009-5837(2016)06-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