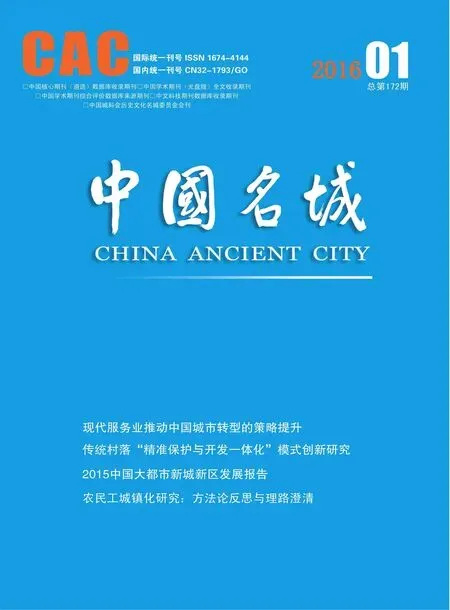连片特困地区城市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理论发展回眸*
2016-02-05王志章丛丹丹
王志章 丛丹丹
连片特困地区城市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理论发展回眸*
王志章 丛丹丹
当前,连片特困地区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关系着我国能否在2020年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空间生产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阐释,对山地城市、城市空间、空间生产以及城乡一体化等概念进行研究,通过梳理连片特困地区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探讨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和现有的模式,指出了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研究的不足,从而针对山地城市空间生产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策略,希望对山地城市未来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连片特困地区;城市空间;空间生产;城乡一体化
我国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一项重大的扶贫工程,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战略举措。除西藏、四省藏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外,新划定的六盘山、秦巴山、武陵山、乌蒙山、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大兴安岭南麓、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大别山、罗霄山等11个片区包括505个县,其中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382个、革命老区县170个、少数民族县196个、边境县28个,国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0亿(其中乡村人口约1.90亿)。[1]连片特困地区范围之广,面积之大,地位之重要,能否在2020年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托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十年来备受学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关切,并产生出一批优秀成果。回眸在扶贫开发实践中诞生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观点,对做好新常态下连片特困地区城市空间生产和城乡一体化这篇大文章,赢得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1 关于相关概念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约650万平方公里,我国划定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多处在山地范围内。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突飞猛进,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规模的迅速扩张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空间发展带来良好机遇和全面挑战,山地城市空间在探索新的空间结构形态和功能有效组合的过程中面临更多新局面和新问题。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全球不同学科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近年来也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
众所周知,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交通运输条件、经济技术水平、社会文化习俗、政治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664座城市中,山地城市和连片特困地区内的城市仍处于社会经济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城市化水平落后的处境,城市空间发展的外在条件、空间环境、内在功能、结构形态都面临众多复杂的问题。首先,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在区域空间内极化和辐射作用不明显,城镇等级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缺位,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另外,城市内部建设密度和开发强度不断增大,城市内部绿化空间和公共空间日益减少;再者,城市生态系统负荷加大,资源危机严重;最后,人居环境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的规津性以及规划、建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但目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往往忽视地域特色、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照搬套用平原地区城市空间模式严重。因此科学研究我国这一特定区域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和规律,认真探索城市空间结构和内部地域组合的优化具有重大意义。学者首先从概念入手,以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理论视角,对山地和连片特困地区的城市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城市发展理论。
1.1 关于山地城市
城市是人类的灵魂。城市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作为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聚集中心,城市成为时代烙印最深刻和最生动的写照和纪实。当前,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得各个领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动力的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以爆炸性、连续性、矛盾性和革命性为特征的现代城市化影响着我们的城市社会,巨大数量人口的物理和社会流动给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如果说城市是一个复杂开放且适应性强的系统,空间就是城市的基础依托和发展动力,城市空间的创造、扩展和优化成为当今时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明智选择。根据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理论[2],城市空间的创造和扩展可以表述为其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城市化的肇始和目标(王志章,2009)。[3]
对于山地城市的概念,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界定尚不统一。工程学建立在地理地貌特征基础上界定,城市形态学以不同形态特征将城市界定为山地—城市二元概念。苏联学者克罗·基乌斯在《地市与地形》一书中从城市与地形的关系人手,认为在多山或丘陵地形区域内的城市,由于其复杂的地形影响了城市的建设,因此将城市规划范围内从50%以上以及25一50%的复杂地貌城市定义为建在复杂地形条件上的城市,即山地城市。[4]同样欧美国家认为山地城市即指城市选址修建在倾斜的山坡地面上(邹徳慈,2002)。我国“山地城市学”的创始人黄光宇先生倡导广义的山地城市,即包括两种类型:一是选址修建在倾斜的山坡地面上的城市,如香港、重庆、兰州、延安、拉萨等;二是有些城市虽然选址和修建在平坦的地区,但由于其周围处于复杂的地貌条件,从而对城市的布局结构、交通组织、气候、环境及其空间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类城市也应纳入山地城市的研究范畴,比如昆明、贵州、杭州、南京等。[5][6]后来,山地城市学的追随者还按照“区域规划范围中对地理地貌特征的限定+城市规划范围内对地形地貌特征的限定+“城市”的逻辑将城市划分为四类:高海拔山地城市、高海拔平原城市、低海拔山地城市、低海拔平原城市,除第四类城市外,其他三类都是广义的山地城市(陶石,2001)。[7]山地城市人居环境研究在世界人居环境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是人居环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以吴良镛先生为首的学者,提出了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张,主要借鉴了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从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出发,认识城市和乡村建设中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探索和建设符合人类聚居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环境。陈炜(2001)等从人居环境的意义上对山地城市的本质特征从地理位置,社会文化和空间特征做了归纳,从城市学角度看,他认为在讨论山地城市概念时,不应当忽略作为山地城市的主体—人的意义,研究山地城市目的是通过改善城市面貌,给予山地城市居民以更好的生活,工作,休闲环境,是以山地环境中人的生存条件作为研究对象。[8]
1.2 关于连片特困地区的城市研究
2011年12月6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以2007-2009年的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公布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些特困地区的城市都具有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差等特点(黄承伟,2013)。[9]贫困的成因不同,类型不同。张立群(2012)将连片特困地区分为资源性贫困、生产性贫困、主体性贫困和政策性贫困,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10]由于武陵山率先被国务院扶贫办确立为“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示范区”,因此成为研究领域的首选和热门地区;大部分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研究方法采用定性描述的方法,侧重分析连片特困地区致贫因素、反贫困战略、突破治理困境、完善脱贫政策建议等(李佳,2013)。[11]当前,为了更好的实施扶贫攻坚,学者从生计资本(张大维,2011)、[12]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黄承伟,2013)、[13]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高峰,2010)[14]等不同的视角下研究连片特困地区的城市发展路径,为区域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1.3 关于城市空间
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一切场所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是人类生产的场所,也是人类改造的对象。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空间与环境利用为基础,以聚集经济效益为特点,以人类社会进步为目的的集约人口、经济、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城市空间则是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载体和容器。列斐伏尔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对城市空间进行建构。[15]富利(L·D·Foley)认为,城市空间具有三个结构层面,分别是物质环境、功能活动和文化价值,对城市空间应从“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去理解,形式即空间分布模式与格局,过程即空间的作用模式,形式与过程体现了空间与行为的相互依存性。城市空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空间化,城市空间的形态和结构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政治经济背景,然而,城市空间商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空间公平”和“空间冲突”凸显,成为社会热点(马学广,2010)。[16]城市空间的塑造,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公民作为城市的主体,公民道德提升与城市空间优化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我国学者夏祖华、黄伟康认为:“城市空间是实体与空间构成的时空的连续体。”由此可见,城市空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它不仅包括由建筑、街道等人工环境和城市山水等自然环境所构成的物质空间,即实体空间,还包括由人们的交往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所组成的非物质形态的社会空间,即虚体空间。另外城市空间还有城市内部空间(城市建成区内)和城市外部空间(城市腹地及周边环境)之分。近年来,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空间扩展、城市空间规划都成为城市学者的研究范畴。
1.4 关于空间生产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J·厄里( John Urry,1946-)宣称:“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福柯(Michel Focault,1926-1984)也说:“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沉疴弊病逐渐暴露,危机日益严重,触发了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哈维等一批学者对城市化、空间—社会关系、空间—资本关系等问题的关注(魏开、许学强,2009)。[17]秉承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等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的空间学说贡献,自1970年以来,空间开始逐步进入社会理论的论域,新城市社会学开始了空间转向的研究。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1901-1991)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提出了“空间的生产”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历史性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模式。社会生产的主导实践方式决定着空间生产的方式。[18]卡斯特尔和罗西分别从集体消费和城市记忆的视角论述了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另一位著名空间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则要求放弃“空间是什么”的问题,代之以研究特定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并使用特定的空间的问题,即空间生产的问题。[19]后现代城市社会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1941-)利用“社会空间辩证法",得出结论:人口城市化意味着国家要建新城,复兴旧城,连接城市带,即经营城市空间;扩大城市吸纳劳动力的容量,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增值城市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在西方学者的理论基础上,我国城市学者大多做的是理论结合实践的案例研究。张京祥(2011)等认为区域空间生产关系导致了新区域合作治理关系的形成,并使原先区域合作治理关系解体。[20]庄友刚(2012)通过审视空间生产理论及其发展认为不仅要宏观阐明空间生产的发展规律,也要阐明与社会生活辩证作用的具体内容。[21]郭文(2015)从资本、权力和利益三方面构建生产空间的逻辑体系,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提供指导。[22]就中国语境而言,城市空间生产具体应该指的是城市空间的创造、扩展或优化。
1.5 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上个世纪已经存在,国内外相关领域也有相关的研究。早期恩格斯经典的“城乡融合”理论,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等,对城乡结构及融合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城乡一体化思想出现,80年代末受到重视,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纵向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重心的转移,城乡一体化问题作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概念的理解,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合理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深化社会分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城乡一体化更加侧重人与人的全面发展,打破城乡之间相互分割的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以及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生态学、环境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环境畅通有序,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从规划学的角度则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对城乡边缘区作出统一的规划,对其具有一定关联的城乡物质和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23]由此可见,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城乡一体化作出不同的概念界定。无论侧重哪个角度,都有共同的特点,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城乡综合的社会、经济和空间发展过程,又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2 关于山地城市与连片特困地区城市空间生产
依据对上述山地城市空间生产概念的理解,它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极为广泛的系统。各个要素的相互交织、协调配合才能促使整个系统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交织的集合体,因此空间生产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它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都离不开多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有关山地城市的山地学、城市学、社会学、生态学、景观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美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已经开始出现相互渗透甚至融合的趋势,尤其以山地城市学、山地景观学等学科的成就最为突出。各种有关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的空间布局拓展模式、规划设计实践更是层出不穷。
2.1 理论研究
重庆大学的黄光宇教授,作为我国山地城市学的奠基人和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的开拓者,他站在生态学的理论视角上,采用“自然生态因子分析法”为核心的山地城市学理论研究方法,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对山地生态环境、自然空间形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4]莫文静提出在设计中应重视人对城市空间的情感需求,践行“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才能创造出具有活力和人情味的城市空间。[25]而山地城市景观学,从景观学、山地学和城市设计原理出发,综合相关学科,通过山地城市景观的视觉审美和理性认识,探求其景观的本质、内涵、规律、价值以及景观创造的科学。其意义在于揭示山地城市的景观美学价值,调节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促进生存环境的持续进化发展,协调保护山地城市文化的特性创建优美的山地城市景观风貌,完善和拓展山地城市学、景观学理论。
然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案例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难以适应实际建设的需要。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赵万民教授提出对国外山地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理论和案例研究,以空间形态为切入点,寄希望形成一个涵盖了美洲、欧洲、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区域,关于国外山地城市发展与建设基本认识和基础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拓展山地城市发展建设相关理论与案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指导我国山地城市建设(王澜凯,2014)。[26]
2.2 关于城市空间和连片特困地区城市发展的实践探索
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典型山地城市及山地资源型城市整个城市空间形态、拓展模式及策略研究和构成城市空间系统的具体要素的规划设计。
2.2.1 城市空间形态研究
克罗基乌斯(1982)总结了五种山地城市空间形态模式:紧凑型、放射型、线型、枝型和组群型。在我国,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呈现视角多元化的特征。首先,从历史学(徐熠辉,2000)、地理学(陈炜,2001)、社会学(陶松龄,2001)、政治学(张鹏举,1999)、经济发展(钱小玲,2001)的角度对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要素进行研究;其次,是对城市形态演变机制的研究(熊国平,2005)以及对城市形态方法论上的探索(相秉军,2000);最后,是对特定对象的城市空间形态的解读,包括对国内城市的研究(姜世国,周一星,2006)和国外城市形态理论的研究(段进,丘泽潮,2008)。
2.2.2 城市空间拓展模式及策略研究
黄光宇(1983)指出,在特定的自然地形和自然环境下重庆发展成了以分片集中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地区分散布点的星座式分布形态,严格控制中心城市的发展,按总体规划逐步调整中心城市七个片区的功能。他在《丽江古城的保护与开发》中从六个方面建议采取措施对丽江进行可持续性保护和开发。[27]姚士谋(2002)认为,香港在有限生存发展空间、世界资本技术高度集聚、市场经济规律、政府诱导资本扩散的政策、现代都市生活环境等机制的引导下采取的发展新城镇,促进郊区城市化的新模式是利于香港的空间发展的。[28]汪昭兵在《探析城市规划引导下山地城市空间拓展的主导模式》(2008)中发现山地城市空间拓展在城市规划引导下呈现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采取跳跃式的空间拓展模式,工业空间拓展和新城 (区)规划建设成为该类城市空间拓展的主导模式。[29]钟纪刚以攀枝花为例,提出空间形式应是未来型和节约型的,应按照现代宜居城市的空间概念来重新规划,充分利用坡地,实现空间的紧凑发展,合理开发地下空间,塑造具有特色的城市空间形象,注意吸纳和反映多元文化和文明,实现自然、科学、人文和生命的有机融合。[30]
2.2.3 城市具体要素的规划设计
对山地城市地表空间的设计,学者选取不同空间结合实际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如广场的设计(姚捷,2008)、街道(黄光宇,2005)、城中村(王添翼,2009)、道路交通(,2009)、轨道(游婷,2009)、住宅(陈俊,2005)、旧城(彭寰,2005)等等的规划设计以及地下空间如(何飞,2008)等,都是研究的范例。上述文章从组成山地城市系统的不同要素出发,指出应结合山地城市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环境等进行规划设计。一些有益的结论丰富了山地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
3 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概念的提出与探索阶段;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城乡边缘区的研究阶段;第三个时期还90年代至今,是城乡一体化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开始建立,研究内容日臻完善时期。
3.1 新型城镇化
2015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当前,中国已进入城镇化的战略转型期。加快推进城镇化转型,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为此,要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各具特点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强调以城带乡,是一种城市支持农村的城镇化;强调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四化”同步的城镇化。[31]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乡关系问题,而是城市平等发展权的问题,有了平等发展权,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要素,才能按照市场的方式来促进发展,才能更多的形成城市发展的活力。[32]地理空间是城市化不可忽视的因素,李铭等认为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动力,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新时期中国城镇化道路是渐进式、集约式、多样化、可持续、智慧型城镇化之路。李克强总理在中欧城镇化论坛的致辞中讲到,中国和欧洲的城镇化要“结伴而行”。所谓结伴而行就是在互补的基础上,更好的学习欧洲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整洁的城市形象、便利的城市交通网络设计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保护等经验。
3.2 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对于中国城乡一体化推进路径的探讨有以下几种代表观点:黄明坤(2009)在《民本自发与政治自觉:城乡一体化在嘉兴的实践》中认为中国城乡一体化既是政府自觉推进的结果,也是民本力量自发推进结果,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33]李伟(2010)在《关于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综述》中指出,要真正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就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由城市单方面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格局,城市偏向决策机制形成的背后是我国农民权利的弱化[35];厉以宁(2010)则从要素流转的角度提出城乡双向一体化,即除了农民进城市民化之外,城市的人员、技术和资本也要流向农村,这样才有利于农村的发展[36]。
3.3 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城乡一体化发展因各国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目前,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主要有,欧洲模式: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美国模式:完全以市场为主导:拉美模式:过度扩张式。宋刚(2015)通过对国外城乡一体化模式的研究中指出,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合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道路。[37]
4 以往研究的不足
综观迄今有关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不够规范,研究内容不成体系,研究范围还很狭窄。目前研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不足:
(1)概念界定不明确。明确的概念界定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但到目前为止,对山地城市各个学科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对空间生产的外延和内涵缺乏深入透彻的理解。
(2)学科融合研究趋势不强。研究过程中未引起相关学科和学者的重视,缺乏理论指导,研究结果没有形成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3)研究方法不科学。典型对象的描述性文章较多,缺乏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等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难以进行评估。
(4)研究内容不成体系。主要集中在典型山地城市整个城市的拓展模式和策略研究以及构成城市系统各个要素的规划设计。然而,山地城市空间生产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而是一个系统。
(5)研究范围狭窄。迄今的研究只针对我国西南地区典型的山地城市,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我国山地城市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多,这些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我国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的整个研究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基于上述不足之处,建议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应着力于以下几点:
第一,要明确山地城市及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依笔者看来,可以组织研讨会,邀请相关学者和专家共同商量讨论最终确定山地城市及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的概念、内涵及外延。明确之后以恰当的方法公之于众,以便在以后的研究中遵守、执行和采用。
第二,加强理论创新,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整合与山地、城市、山地城市、山地城市空间生产有关的学科知识,开拓交叉学科,拓宽理论视野,为后继研究拥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全新视角打下基础。
第三,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实地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对全国山地城市的数量、分布以及各自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困境等做详细的了解和翔实的记载,科学制定和不断完善山地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研究的指标体系。
第四,组织力量对山地城市空间生产研究的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入研究,这是能否成功开展下一步研究的先决条件。山地城市是特殊的城市形态,这说明一般城市城市化所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发展机遇和困境、前景趋势也是山地城市发展的题中之义。正如陈为智(2008)所说“城市的空间生产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利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生、交织、博奕、冲突过程,并受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因素的支配。”因此今后应将研究置于整个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视角弄清山地城市空间生产面临的现状、发展困境,预测其发展前景,提供建设性意见。
第五,努力拓展研究范围。针对我国山地城市数量多、分布广且各具特色的现状,在对其大体情况了解的基础上,开展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为全国山地城市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城市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城市化是城市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是近9亿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在物理和社会空间中完成向城市的转移,是空间扩张和资本积累增殖的过程,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所有权流转中的矛盾冲突,是居住正义、进城农民工、城市改造、征地等等问题的集合,研究山地城市空间生产问题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许多学者专家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一课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它只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正是如此才给后续研究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我们要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国际化视野,加强学科融合,拓展研究范围,运用科学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研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任重而道远。
[1]王思铁.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及其特征[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a3d490100xx3d.html,2015-09-07.
[2]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J].社会学研究 ,2009,(1):27-33.
[3]张引,王志章.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与城市化路径[J].规划空间站,2009.
[4][苏]克罗基乌斯著,钱治国常连贵钟继光译.城市与地形[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5]黄光宇.山地城市学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6]黄光宇.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学思考[O].重庆市首届工程师大会论文集,2003.
[7]陶石.中国城镇空间形态类型的二元界定与八极划分——兼论“山地城市学”中“山地城市”概念的界定[J].规划师,2002,(11):83-86.
[8]陈玮.对我国山地城市概念的辨析[J].华中建筑,2001,(19):58-59.
[9]黄承伟.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战略研究 [J].社会主义研究 ,2013,(01):32-36.
[10]张立群.连片特困地区的类型及对策[J].红旗文稿 ,2012,(22):18-20.
[11]李佳.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研究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 ,2013,(12):88-91.
[12]张大维.生计资本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的现状与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1,(04):16-22.
[13]黄承伟.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战略研究 [J].社会主义研究 ,2013,(01):32-36.
[14]高峰.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 [J].学习与探索 ,2010,(01):9-13.
[15]George C.S.Lin: Chinese urbanization in question:state,society,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s,Urban Geography,2007.
[16]马学广.“单位制”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研究[J].经济地理 ,2010,(09):1456-1460.
[17]魏开,许学强.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范式述评 [J].城市问题 ,2009,(04):83-87.
[18]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学 ,2008,(05):133-135.
[19]张佳.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探析[J].北京大学学报 ,2015,(01):82-89.
[20]张京祥.基于区域空间生产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1,(01):5-9.
[21]庄友刚.何为空间生产?——关于空间生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J].南京社会科学 ,2012,(05):36-42.
[22]郭文.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J].地理科学 ,2015,(06):708-716.
[23]江郭涛.山东半岛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D].山东:中国海洋大学,2011.
[24]黄光宇.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学思考[J].城市规划 ,2005,(01):57-63.
[25]莫文静.城市空间情感的表达[J].城市与建筑,2013,(12):23-26.
[26]王澜凯.国外山地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日本地区探析[D].重庆:重庆大学,2014.
[27]黄光宇.丽江古城的保护与开发[J].城市规划,1986,(01):53-57.
[28]姚士谋.香港城市空间扩展的新模式[J].现代城市研究 ,2002,(02):61-64.
[29]汪昭兵.探析城市规划引导下山地城市空间拓展的主导模式 [J].山地学报 ,2008,(06):652—664.
[30]钟纪刚.山地资源型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关于攀枝花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思考 [J].规划师 ,2006,(04):15—16.
[31]魏后凯.新时期中国城镇化转型方向[J].中国发展观察 ,2014,(07):04-06.
[32]李铁.城镇化关键在于城市城市平等发展权[J].西部大开发 ,2013,(06):44-45.
[33]黄明坤.民本自发与政府自觉:城乡一体化在嘉兴的实践[J].中国发展 ,2009,(01):76-83.
[35]李伟.关于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 ,2010,(42):39-45.
[36]厉以宁.论城乡一体化[J].中国流通经济,2010,(11):7-10.
[37]宋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2015,(01):23-26.
责任编辑:王凌宇
So far, production of the urban space and ruralurban integration are critical to whether we can meeting anti-poverty and building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the contiguous poverty stricken areas by 2020.On the basis of the seniors’ research,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theories such as urban space theory, dual economic theory,regional economic. It also explores the concept including mountain city,urban space, rural-urban integr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e discuss the route and spatial patterns in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y conclud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bout production of the urban space in the contiguous poverty stricken areas. We also point out som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s well as suggestions about production of the urban space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at will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city in the future.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 ; urban space ;production of space ; rural-urban integration
C912
:A
1674-4144(2016)-01-27(7)
王志章,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丛丹丹,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 (编号:12ASH00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部乡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编号:14CSH009) 和中央高校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路径研究》(编号:SWU15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