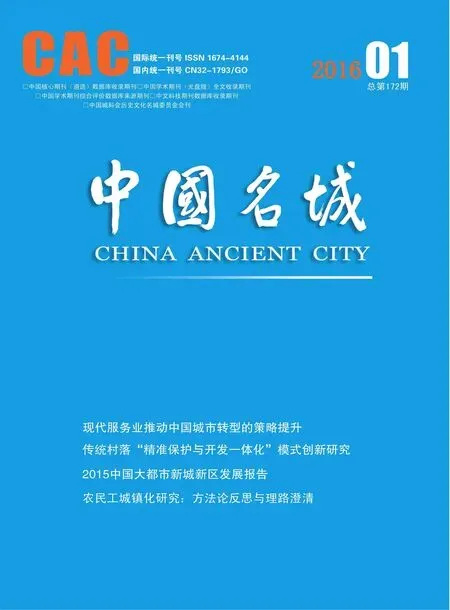2015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报告*
2016-08-02刘士林刘新静周继洋
刘士林 刘新静 孔 铎 周继洋
2015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报告*
刘士林 刘新静 孔 铎 周继洋
以符合国家最新城市层级划分中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标准的我国12座大都市规划和建设的130余座新城新区为研究对象,对规划与建设的总体情况、基本特点、最新进展与突出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大都市新城新区面积大、数量多、在功能上以综合型为主、由单一型升级而来,并具有级别较高和区城共生等特点,同时呈现出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网络化、追求“宜居”、“生态”和注重产城融合的新趋势,但仍存在着体制僵化、创新意识淡薄、集聚效应冷热不均、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建议从七方面提升层次和质量:一是区别对待大都市新城新区的审批;二是从顶层设计角度重新考虑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三是走文化型城市发展路径十分必要;四是深入研究新城新区的比较性优势;五是要理性客观看待新城新区;六是提升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度;七是充分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在规划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新城新区;城市化;都市化
2000年以来,我国城市人口以年均超过1.3%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而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我国这种大规模、高速度、集中化的城市化特点,必然要以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为载体,建设新城新区完全符合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城市“爆炸式扩张”的特殊国情,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设置了包括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科技园区等在内的2957个新城新区,且其面积高达107288.69平方公里的现实背景。无需否认,我国新城新区规划建设中存在着违规、违法及盲目开发等突出问题,这是2010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新城新区建设”、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珍惜每一寸国土,控制开发强度”、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继续强调“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的主要原因。
对新城新区的规范和治理,始于2006年国家发改委等对全国开发区的集中整治。经过此轮规范和治理,全国开发区在数量上从6866个减少到1568个,规划面积也从3.86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949平方公里。2011年,为遏制新城新区的“粗放发展”,国家发改委停止了新城新区的审批。2014年1月,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范新城新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签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形成的《新区设立审核办法》,在送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林业局、法制办等16个部门征求意见后报送国务院并经国务院领导审定,成为国家审批新区的正式文件。为理性观察和评估我国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成长,继2012年底发布国内首个《全国新城新区研究报告》[1](P.21-34),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从2015年开始发布《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年度报告》,关注和跟踪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进程,同时为中小城市的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提供示范。
1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的研究背景
作为本报告核心概念的“大都市”,在内涵上包括国家最新城市层级划分中的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①。在“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这些大都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和增长极,不仅对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也是观察和衡量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风向标。大都市新城新区则成为了是全国新城新区“核心中的核心”,这是本报告选择大都市新城新区开展深入调查研究的主要原因。
1.1 新城新区建设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建国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时长各三十年左右。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阶段尽管城市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从1949年的79个增长为1980年的223个,但我国的城市化率一直在低位徘徊,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1949年为10.64%,1980年为19.39%,30年的时间仅提升了8.75%;第二个阶段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加速度发展,城市数量和城市化率都有了大幅提升,城市数量从1980年223个增长为2013年的658个,城市化率从19.39%跃升为53.72%。从图1可以发现,城市数量与城市化率在大趋势上相吻合,都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的时间段并不完全吻合。如第一个阶段三十年城市数量增长了182%,但城市化率仅增长了8.75%;第二个阶段的前二十年城市数量增长了197%,但城市化率却增长了16.83%;最后十年尽管城市数量出现了负增长,但城市化率却增长了17.5%。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解放前我国城市数量少,城市化率低,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快速发展,无论城市数量还是城市人口必然都呈现增长趋势,但其之所以不是完全对应,主要是新中国前三十年主要是“政治型城市化”,城市数量在某些阶段不升反降,而单体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进程还在继续(图1)。

图1 新中国的城市数量与城市化率趋势图(1949-2013年)
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新城新区建设主要建于2000年以后,这和中国城市化步入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2]在时间上高度吻合,是中华民族在城市时代亟需拓展生产生活空间的集中体现。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新城新区设置存在着不断调整、合并等原因),截至2011年底,全国31个省市共计拥有新城新区545个,面积达68671.52平方公里。其中,20世纪80年代建设面积为0.9%,20世纪90年代建设面积为14.4%,新世纪以来建设面积为84.7%。[1](P.30-31)而据另一项调查显示,我国12个省会城市中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其中沈阳最多,共规划建设了13个新城新区,武汉次之规划了11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城市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比为92.4%,平均每个地级市规划建设1.5个新城新区。在161个县级城市中,也有67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比为41.6%。[3]
从城市史的角度看,和西方19世纪下半叶开始大规模建设新城建设一样,新世纪以来,在我国城市数量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由于城市化率的快速和持续攀升,原有的城市空间已无法容纳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和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我国大规模的新城新区规划和建设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和现实需要而兴起的。
1.2 所谓“鬼城”现象让新城新区面临颇多质疑与批评
新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新城新区规划和建设,为诸多罹患人口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为更加有序地安排各种资源和要素、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提供了保障。但由于政绩考评、土地财政、盲目追求规模、相互攀比、崇洋媚外等原因,一些城市在缺乏科学研究和论证基础上上马的新城新区项目,也造成了“鬼城”、人气不足、产城分离等现象的出现。这些发育不良的“新城新区”浪费了大量资金和土地,加重了一些城市在空间规模上的无序野蛮增长,因此受到了颇多质疑和批评。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质疑新城新区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其主要体现了政府和官员的意志,是“行政的手”取代了“市场的手”,而非出于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并大幅度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二是质疑新城新区建设的规模和数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12个省会城市平均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市规划建设200个新城新区为对象,认为我国新城新区数量过多、建设标准设置较高,超出了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当地财政的承受能力。三是质疑新城新区建设的目的和意义。认为政绩工程和土地财政是主要推手或动机,前者包括一些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等,主要功能是为地方官员晋升“铺路”,后者主要是拉动地价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益,与城市民生关系不大,在拆迁、征地中存在着损害普通百姓权益的情况。四是全盘否定新城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以一些“鬼城”、“空城”和产业不成功的新城为口实,把人气不旺、空置率高、公共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滞后、产业集聚程度不高或经济发展乏力,也包括违规占地、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群体性事件等完全归罪于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4]这些批评和否定意见具有某种片面的深刻性和局部的合理性,但从总体和本质上看并不全面和客观。以具有准新城新区的开发区为例,从1984年开始设立到2014年,437家国家级开发区、1600余家省级开发区及逾2万家各类主题产业园,30年来这些开发区贡献了全国GDP的68%、外贸出口的近九成。[5]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城市就会更美好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1.3 理性思考和客观评价新城新区
在我国新城新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鬼城”现象,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政绩工程、贪大求洋等问题的集中反映。但如果因此就全盘否定新城新区,认为其一无是处或主流是错误的,则明显是在片面调查研究上做出的以偏概全的错误判断。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些质疑和批评的主要问题在于三方面:一是缺乏对新城新区的理论研究,不理解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我国新城新区建设的必要性。我们不能泛泛地谈新城新区多还是少,也不能与人口总量有限、城市化速度较为均衡的西方国家机械地比较。相对于空间狭隘、基础设施落后的老城区,新城新区在大规模解决人口居住和就业、在整体上带动和引领城市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和关键作用,已成为我国城乡人口就业、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功能区;二是缺乏对新城新区的历史研究,不了解历史就容易跟着感觉走,也不能对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做出科学的认识和评价。从新城新区的发展历程看,不存在从一开始就规划得很完美、高质量的新城新区。英国从规划功能单一的卫星城到相对独立的新城市中心,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科技园区、居住小区等,但在遭遇到通勤成本上扬、公共服务短缺、人气不足等现实问题之后,近年来已纷纷启动向综合性城市中心的升级和改造。相关专家和媒体把新城在某些区域、某些阶段必然存在的空置率高、公共服务滞后、产业集聚程度不高等,误判为我国新城新区的整体和本质属性,甚至称为“鬼城”,有悖于新城新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中国经验;三是缺乏全面的数据和科学的经验研究,在现状的概括上比较随意和不严谨,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新城新区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实质。我国新城新区应重点整治的问题是未批先建、少批多占、越权审批、以租代征、借壳建设、人均面积超标等。这些问题既是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存在的主要病症,也是在当下急需应对和处理的具体对象。把精力和思考更多地放到这些具体层面,不仅有助于找到真正的患者和深层的病因,探索、寻求规范和治理新城新区的策略与技术,同时也有助于端正思想和摆平心态,使城市研究和传播在客观基础上发挥出建设性的正能量。[4]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新城新区也是如此。从发达国家建设新城新区的经验看,新城新区建设往往不是十年八年就能完成的。如美国的里斯顿新城,从1961年买地、1962年规划、1963年开工、1964年开盘直至2005年才竣工,其建设过程长达44年。而建于1971年的加州尔湾新城,其规划面积为88平方公里,但迄今也只有17.5万的居住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新城新区都能成功,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不仅没有达到疏散东京人口的目的,还因为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健康发展。[6]这些世界新城建设经验,对我们科学理性看待中国新城新区建设可以提供重要的借鉴。“宁欺白须翁,莫欺少年穷”。我国绝大多数的新城新区,在规划建设时都属于情势所迫,同时它们目前主要处于生长变化的幼儿期,对其未来不宜过早盖棺论定或一棍子打死。以2010年还被称为中国最大鬼城的郑东新区为例,现在已是车水马龙、人流如梭,甚至到处堵车。这符合世界各国新城新区的发展规律,即在新城初建时,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口和资源的集聚度不够,所以新城总是不如旧城热闹,但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的完善,很多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城市化基本国情,新城新区发展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进程,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也会超过西方和拉美,对此我们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对其发展进程的艰难不易做到“知人论世”,宽容探索其中的失败并承担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也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储备和蓄积了足够的物质条件与经验智慧,有能力解决我国城市化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7]
1.4 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和建设具有典型意义
人口与空间是城市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也是人类在城市化进程中永恒的矛盾。正如芒福德把城市比喻为“容器”[8]一样,当容器内的东西过满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不是小打小闹地挖掘内部潜力,而是为装不下的东西找一个新容器。在通常情况下,人口和空间是一种正比关系,对于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而言,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须的。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我国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 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9]按照这个新的城市层级体系,对处于不同城市环境的新城新区开展实证研究,可以有效避免不分青红皂白、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新城新区研究,同时把真正符合中国城市化需要的新城新区与各种徒有虚名的“伪新城新区”区别开。
根据国务院最新的城市划定标准,截至到2013年年底,我国超大城市有3座,分别是北京、上海、重庆,其市区常住人口分别是1245.2万、1364.1万和1787万;②特大城市为9座,分别是天津、西安、广州、沈阳、郑州、武汉、成都、南京和汕头,其市区常住人口分别是821.7万、580.6万、686.6万、524.6万、517.7万、512.6万、564.9万、643.1万、532.5万。③在本报告中,为了语言简洁并和世界对接,我们将将其统称为“大都市”,其新城新区即作为本报告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需要说明的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向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迅速集聚,大都市在范围上将是变动不居的,随着各个城市城区人口的增减,纳入《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发展年度报告》的名单也会不断变化。尽管这些城市的级别不同,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地区级城市,但人口众多这一共同特点决定了其城市空间需求相对较大(图2)。从图2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这12座大都市的人口大幅增长,建成区面积也相应地不断扩大,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吻合,这说明我国大都市在新世纪以来已基本实现了空间扩展与人口集聚的同步性,而土地资源浪费或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在宏观上表现得并不明显。

图2 中国大都市人口、建成区面积趋势图
与大都市人口主要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不同,建成区面积的增长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老城区的扩张,二是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这是我们客观掌握新城新区发展进程的主要依据。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尽管大多数都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但无论在体量还是面积方面,后者和大都市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同时,从落实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出发,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的建设、发展及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我国新城新区的价值和意义,也可以为其他城市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提供样板和示范。
2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与建设的总体情况与基本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12座大都市共规划和建设新城新区为130座左右④,其中新区13座,新城117座(包括自贸区1个),总建设面积达14900多平方公里。依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为国家《新区设立审核办法》提供主要支撑的《新城新区认定方法及统计标准》,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自主建设了《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与建设的现状、特点与趋势进行分析研究。
2.1 中国新城新区的界定及阐释
“新城新区”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是结合我国城市发展实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同时也和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很多新事物一样,具有先建设、次规划、后研究的鲜明时代特征。从渊源上看,“新城新区”与英美等国的“新城”概念最接近,一直以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管理部门,我国对“新城新区”一直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及统计标准。根据我国新城新区发展的历程和现实情况,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全国新城新区研究报告》课题组在系统梳理西方新城理论源流、形态演化、主要模式等基础上,从研究并设定了符合中国城市化和新城新区建设实际的广义和狭义概念。其中广义的“新城新区”定义为:“1979年(蛇口工业区)以来我国各省市在原来的农村地区设立的、具有一种或多种功能的、具有行政管理机构的区域”。狭义的“新城新区”定义为:“1992年(浦东新区设立)以来我国各大城市新建的独立于母城之外的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具有自主性的现代城市区域”。[1](P.27-28)这两种概念较好地适应我国区域与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为分类指导我国不同层级的新城新区规划和建设提供了依据。
在本报告中,我们对新城新区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凝练和深化,将其界定为:“中国各个建制市在政府部门审批通过的各种规划中提及的、名称中带有‘新城’、‘新区’字样的或被规划明确指定为‘新城新区’的、独立于老城区之外的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具有自主性的现代城市区域”。原因在于:
第一,新城新区的规划主体是各个建制市。尽管有明文发布的国家级新城新区,但由于国家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是审批、指导和监督,所以具体的规划主体仍是新城新区所在城市。
第二,行政区划调整后未命名为“新城新区”的暂不列入本报告的数据库及调研范围。改革开放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各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如北京东城区、西城区的调整,上海黄浦区、浦东新区的调整,广州黄埔区、萝岗区的调整等。尽管一些行政区的合并、升级事实上涉及城市区域的建设扩张,但与新城新区的本质——农业环境与资源的城市化相背离,所以同样不列入研究范围。
第三,以政府部门的规划和文件为准。各种房地产开发商出于商业炒作的目的将其很多楼盘命名为“××新城”,其中有些楼盘的规模也颇似新城,但实际上和国家及地方政府主导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并无关系,这些商业楼盘同样被我们排除在新城新区的统计与研究范围之外。在当下的一些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中,常常将商业楼盘混同于新城新区,这种不负责任的张冠李戴,是出现全盘否定新城新区舆情的主要温床。
第四,在内涵上沿用新城新区的狭义概念,即空间上独立于母城之外,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兴建的,在功能上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自给自足,各种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比较完善。但不包括单一功能的大学城、高新园区、工业园区等,同时与母城的关系主要是行政上的管理与隶属关系。
这种概念内涵的变化和调整原因在于,2010年以来,中国新城新区规划和建设本身发生了主要的变迁,即新城和新区逐渐有了各自的内涵并开始走向独立。具体说来,新区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出现的新的行政区域,往往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政府部门的设立,如上海的浦东新区、西安的西咸新区、重庆的两江新区、成都的天府新区、郑州的郑东新区及沈阳的浑南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其特点在于成立了新区就相应设立了新区政府管理部门。而新城是就土地使用性质和城市景观而言,是指在原来的老城区之外建设的城市区域,其中可能涉及新设一些管理部门,如新城管委会等,但却不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从层级上看,新区在面积、体量和级别方面明显高于新城,如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都属于副省级单位,同时新区也可以包括几个新城,如成都天府新区包括华阳新城、龙泉新城和东升新城,天津滨海新区包括大港新城、汉沽新城等,沈阳沈北新区包括蒲河新城和沈北新城等。此外,也存在着特殊案例,如西安的泾渭新区,原是西咸新区的一部分,尽管名称为“新区”,但实质上属于新城类别。新城新区的快速发展和建设,是造成这种“名”与“实”相错乱的主要原因。“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些问题也是深化研究及制定政策时需要加以重视和关注的。
2.2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建设的总体情况
本报告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都市化进程”和“新城新区认定方法及统计标准”为基础理论和方法,以我国现有的3个超大城市和9个特大城市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并以这12个中国大都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及相关部门关于新城新区的批复文件为统计来源,对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明确了规划和建设的数量、名称、规划/建设时间、规划人口和规划面积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统计,为开展本报告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和权威的数据与资料。
对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统计仍为不完全统计,主要原因在于各新城新区规划本身的不一致。如各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和面积均以远期目标为统计口径,但它们各自的远期目标截止时间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是到2015年,有的是到2020年,还有的是到2030年,因此统计结果会有一定偏差。但就总体而言,本统计已是目前所可能获取的最详实和最新的数据资料,从中也可以判断出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与建设的整体面貌和总体趋势。

图3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情况图
从数量和面积看,据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12座大都市共规划和建设新城新区130座左右,其中新区17座,新城117座(包括自贸区1个),总建设面积为14900多平方公里。⑤其中以沈阳的数量最多,共计为19座新城新区(其中2座新区,17座新城)(图3)。此后依次是成都(新区1座,新城17座)、广州(新区4座,新城11座)、上海(新区2座,新城10座)、天津(新区1座,新城11座)、北京(新城11座)、南京(新区1座,新城10座)、武汉(新城11座)、西安(新区3座,新城6座)、郑州(新区1座,新城6座)、重庆(新区1座,新城4座)、汕头(新区1座,新城3座)。
从规划和建设面积上看,广州的面积最大,其1座新区和13座新城共计面积为2529.42平方公里。位居第二到第十二的,其新城新区的面积依次为天津2124.2平方公里、上海1978.32平方公里、南京1738.66平方公里、北京1693.45平方公里、成都1156.75平方公里、沈阳947.18平方公里、重庆880平方公里、郑州599平方公里、汕头480平方公里、武汉412平方公里、西安362平方公里。
从建设时间看,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的建设,除了极少数(如上海浦东新区和广州珠港新城)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规划建设之外,其他均为2000年以后规划建设的。同时,即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规划的,其正式的大规模的建设也是在2000年以后。其中最典型的是广州珠港新城,尽管从1992年就开始规划建设,但直到2000年这里仍是一个空壳,不仅没有一家商务办公建筑建成,很多已出让的地块也在闲置着。2003年1月,随着《珠江新城规划检讨》正式发布实施,并在开发强度、开发模式、交通系统、“城中村”改造等方面做了较大调整之后,珠江新城的建设才走上快车道,先后建成广州新电视塔、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广州歌剧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图书馆、西塔等地标性建筑,2010年,随着珠江新城花城广场的建成开放⑥,珠江新城这场“马拉松”式的建设终于暂告一个段落。这说明,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的集中化、大规模和爆炸式增长,与中国在1999年彻底改变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城市政策,与中国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并由此融入当今世界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息息相关。正是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经济等城市发展要素在大都市的高度和快速集聚,才为我国新城新区、特别是大都市新城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并促进了它们的跨越式发展。
2.3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与建设的基本特点
截至2013年底,我国正式建制城市总数为654个,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在规划和建设新城新区。由于城市层级、城市化率、资源环境条件、经济实力、社会建设水平及建设新城新区的需求存在差异,我国大都市在新城新区规划建设上与其他城市也有着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3.1 面积大、数量多的突出特征
截至2013年底,中国12座大都市共规划与建设了130个新城新区,每座城市平均为10.8座,规划与建设总面积超过了14900平方公里,每座城市平均为1241.75平方公里。从城市数量上看,如图4所示,这12个大都市仅占我国全部城市总数的1.8%,但其规划与建设的新城新区数量占到全国新城新区总数的27.7%,在面积上占到全国新城新区总面积的33.92%,也就是说,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在数量和面积分别接近或超过了全国的1/3。具体说来,在中国大都市的130个新城新区中,如图5所示,规划与建设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个,即天津滨海新区。规划与建筑面积在1000-50平方公里的为74个,50-10平方公里的为52个,10平方公里以下的仅有3个。与之相比,全国新城新区目前为470座,建设面积为43924.38平方公里,平均每座城市建设数量为0.72座,平均建设面积为66.2平方公里,而大量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市的新城新区,其规划建设面积基本上在50平方公里以下。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呈现出的面积大、数量多特点,既与大都市人口多、经济发达以及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亟待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发展现状与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表明大都市新城新区本身就是中国新城新区规划和建设的主平台,而它们的规范和治理、导向和模式,也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研究和重视。

图4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与全国新城新区对比图

图5 中国大都市新城市新区规划建设面积图(单位:平方公里)
2.3.2 是以综合型为主体形态
从规划类型看,不同于以工业区、高新区、大学城、开发区等功能单一的城市化区域,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基本上都定位于综合型的综合性城市中心。从我国新城新区发展的历程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生产、居住、学习、商业贸易等为中心的城市功能单一型新城新区,如各种工业园区、居住小区、大学城、高新技术园区、创意产业园区等,这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新城新区;二是融合了产业、商业、居住、休闲等各种城市功能的综合型新城新区,如《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中的提到的嘉定新城、松江新城、临港新城等。如《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指出:“高起点建设两江新区,强化交通、金融、商贸、物流等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⑦这些城市功能规划设计全面、甚至具有发展先锋意义的新城新区,可称为中国“第二代”新城新区。在这个整体背景下,中国12座大都市新城新区以2005年为界碑分为两大阵营,在此前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多为第一代新城新区,而此后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均为第二代综合型新城新区。这从冠名上也可以见出端倪,在2005年之前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多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命名;而2005年之后则直接冠以“新区”或“新城”。从数量对比上看,2005年之前,我国批准设立的新城新区为12个,主要是上海的1座新区和10座新城;2005年以后为118个,占比高达90.8%。可见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的主流是第二代综合型新城新区。大都市新城新区对其他新城新区的转型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实际上,尽管我国新城新区最初主要是工业区、开发区、高新园区、大学城等功能单一型新城,但在面临产业与人气不足、通勤成本上扬、公共服务短缺等压力后,它们大都开始主动探讨并推动新城新区建设走上综合发展之路。而作为我国新城新区体系中层级最高、规划更加科学的大都市新城新区,就是它们学习和模仿的直接对象。
2.3.3 第一代新城新区的升级版
对每座城市而言,无论大小空间都是有限的,而且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还要保留一定的农业空间,所以其空间不可能100%地开发为城市功能区。在这种政策和资源环境的约束下,我国2005年后规划建设的第二代新城新区,有很多都是从第一代新城新区升级发展而来,而不完全是另起炉灶。如北京的亦庄新城的前身即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开发区始建于1992年,并于1994年由国务院批准为北京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了200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复《亦庄新城规划(2005-2020年)》, 将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功能区的亦庄新城明确定位为北京东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和重点发展的新城之一。又如广州萝岗区,其前身是成立于1984年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也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2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和广州出口加工区实行合署办公,总规划面积达到78.92平方公里,并形成了全国国家级开发区独一无二的“四区合一”新型管理模式;2005年,依托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了萝岗区,面积进一步扩展到393.22平方公里。⑧其他还有上海的闵行新城、宝山新城、金山新城,天津的武清新城,郑州的郑东新区等,都是由第一代新城新区“脱胎”而来。这完全是符合城市发展和新城新区建设的一般规律。城市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即城市各种产业、资源和功能郊区化的进程,一般而言首先实现郊区化的是工业,然后是人口、商业、服务业等郊区化,第一代新城新区升级发展为第二代新城新区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加强现有开发区城市功能改造,推动单一生产功能向城市综合功能转型”,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我国的第一代新城新区向第二代转型发展将是大势所趋。
2.3.4 级别较高的天赋优势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新区12个,其中6个隶属于12个大都市,分别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西安西咸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和成都天府新区。其中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副省级,在行政层级上明显高于一般的新城新区。其他国家级新城新区由于级别不能高于或者等于所属城市,所以依托于所属城市,但因为拥有国家级新区批复,因而在实际管理权限上也与普通新城新区不同。由于成为国家级新区,就可以在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得到更多的优惠,既可为区域发展起到孵化、辐射、示范、开放和集聚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和功能,因此,在12个大都市中,郑州郑东新区⑨、南京江北新区、汕头海湾新区、沈阳沈北新区及武汉的高新区,都已提出并申报了国家级新区。而其他省市有实力的新城新区也不甘示弱,都在为尽快入围“国家队”而努力奋斗。但从总体上看,12个大都市因其先天的优势和优越条件,如人口高度集聚、城市级别高、经济贡献大等,使其新城新区规划建设一枝独秀,占据了国家级新城新区的半壁江山。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也很难在短期内被打破。
2.3.5 区城共生的发展模式
经过三十多年的规划、建设、冲突和磨合,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逐渐走出了“区是区、城是城”的初级阶段,在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框架下,日益呈现出区城共生和一体化发展的新特点即以行政职能为主体的新区,在其区域规划中往往包含了多个新城,由此形成了区中建城的新型城镇空间体系。这不仅与2005年之前的大都市新城新区,也和当下众多中小城市的新城新区规划判然有别。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新城新区基本上没有城镇体系的概念,“区就是城,城就是区”,即使像浦东新区这样面积广阔的新城新区,也是“有区无城”。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新区,最初主要是以开发区建设为导向,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园区、金桥进出口加工区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为建设节点,而对城市的综合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和设计,这不仅使新区服务设施单一、分散、滞后,且由于在区和街道两级政府中增加了开发区环节,同时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并不同程度地制约和影响了浦东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与之相比,2005年以后的新城新区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在规划环节就明确了综合型的新城为新区建设的城市区域,注重“区中有城”的总体安排和发展新城新区的综合功能。这既中国大都市新城西区走过的一段弯路,同时也为我国中小城市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但相比较而言,在我国众多中小城市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中,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区城分离或城市总体规划与新城新区规划缺乏统筹安排问题,是当下需要深思和关注的。
3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与建设的最新进展与突出问题
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中,新城新区被赋予了深切的希望和重要的职责,特别是大都市的新城新区,既是实施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试验区中的试验区,也是推进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建设目标的排头兵中的排头兵。也可以说,新城新区强则城市强,新城新区弱则城市弱。同时,由于新城新区在区域与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也会间接影响到城市群甚至整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3.1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的最新进展与趋势
3.1.1 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圈层模式向多中心网络模式转化
大都市规划建设多个新城新区的地理表现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这些城市原来的空间结构多为单中心圈层模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和资源涌向各大都市,原来的城市空间结构不能适应高度集聚的人口的需求,在旧城之外规划新城的举措是为了拓展城市空间,容纳仍在向大都市集聚的人口和经济,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沈阳、广州、成都、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规划了10多个新城新区的城市,在客观上将为市民提供多个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和环境,城市的公平性、多样性和选择性也会随之得到较大改善。《成都城乡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以城市中轴线为发展主轴,以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为双核,走廊展开、组团发展,构建‘一轴双核六走廊’的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城镇发展格局”;[10]武汉提出“严格控制主城用地,积极促进新城发展,形成主城为核心,新城为重点,中心镇和一般镇为基础,辐射到农村广大地区的多层次、网络状城镇体系”;[11]南京提出“以长江为主轴,以主城为核心,结构多元,间隔分布,多中心,开敞式的都市发展区空间格局”。[12](图6)可以预见,多中心网络式空间结构,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空间拓展的趋势。

图6 成都、武汉、南京、重庆四市城市空间结构图
3.1.2 宜居、生态、低碳成为大都市新城新区的共同追求
尽管130个新城新区在面积、人口、产业等方面差别很大,但宜居、生态、低碳理念却是它们共同的追求。这种现象既是各大都市深陷“城市病”困境的精神觉醒,也是城市发展新理念、新潮流和新战略的具体体现。如浦东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规划中,就结合城市的交通规划网络,合理安排了若干个城市综合分区,在各分区之间用大型的城市公园及公共绿地加以分隔,同时,各分区内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关系,浦东新区规划这一开放式城市布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浦东新区的城市生态环境;[13]天津滨海新区规划中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示范区”;其他如《南京市龙袍新城总体规划(2012-2030年)》提出“生态优先战略”;《南京市板桥新城总体规划(2010-2030年)》提出“低碳新城战略”等。可以充分肯定的是,对宜居、生态和低碳的追求,在今后将成为各级新城新区规划建设不能绕过的目标和方向。
3.1.3 产城融合是大都市新城新区下一阶段规划建设的重点工作
一些新城新区人口集聚度或产业集聚度不高,是在一些地方出现所谓“鬼城”和“卧城”的主要原因。我国大都市的人口基本都在500万甚至1000万以上,其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基本上不需要担心人口不足。但仅仅有足够的人口并不能称之为城市,换言之,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规划等固然重要,其发展的动力机制才是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在规划建设较早的浦东新区,筹建伊始就设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以及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大型开发区,就是基于产业引导的思路和策略。而中国2000年以来大都市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大多数也依托着一个或多个产业园区,或者是由它们升级而来。这些新城新区出现了有产业无城市或有城市无产业等突出问题。2015年7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主旨即在于要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大都市新城新区在这方面已有了较多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为加快促进产城融合提供经验和示范。此外,还要推进单一的居住型新城新区向综合型城市中心转型,以解决大都市职住分离带来的大规模通勤行为,为解决老城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房价居高不下等创造积极条件,真正实现新城新区疏散老城区过度集聚的人口和资源的目标。
3.2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面临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不可能遗世而独立。受全球都市化进程带来的“大城市病”和中国新城新区一段时期以来粗放式建设的不良影响,这12个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在表层与深层、功能与结构、模式与路径等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些瓶颈性的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着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大、城市经济反复震荡、人口都市化不断提速、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的现实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想的巨大反差中,这些固有矛盾和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减弱,反而深陷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悖论中。
3.2.1 创新口号越来越响亮,但创新精神却越来越淡薄
以“闯”和“创”的“浦东精神”[14]为象征,新城新区的精髓在于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及创新型城市的大背景下,集聚了高新产业、先进科技、优秀人才的新城新区,本应成为转变和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先锋队,但与数量上不断增多的现实相反,新城新区特有的创新精神却越来越淡薄和空泛,一些新城新区成为政府跑马圈地、开发商造楼卖房的代名词,新城新区的名不副实现象日趋严重。与深圳比较一下就可知晓,尽管其不属于本报告研究统计的对象,但深圳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新城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深圳精神、深圳速度及知识产权城市等发展目标,成为了深圳区域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城市气质与风骨。以浦东新区为例,尽管其以经济开发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不无弊端,但在“敢为天下先、善于集大成”的创新精神驱动下,其在管理制度方面的尝试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学习和参照。继浦东新区之后,国家相继批准建设11座国家级新城新区,此外还包括更多的省级新城新区、地市级新城新区,它们在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复制多而创新少,既没有触及要害,也没有什么新思路,“创新”一词异化为一种应对媒体的话语狂欢。这不仅与新城新区的本质相违背,也导致了新城新区规划的“雷同化”和建设的“同质化”。其最大的问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
3.2.2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文山会海,但管理体制本身却越来越僵化
目前,中国新城新区的管理体制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建立管委会。国家级新区普遍都建立有管委会作为其行政管理部门,但事实上管委会与原来的政府架构基本一致,只是名称不同,在组织、构架上并无突破;二是沿用原有的政府管理部门,所谓“新城新区”只不过是再多盖点楼,多修些路,即城市区域在地理意义上的扩张,其行政职能等与原来并无本质区别。许多地方政府热捧新城新区,除了它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有就是可以因此带来更多的行政资源和岗位。无论是新设管委会,还是原有县、乡、镇政府升格为新城新区政府,都意味着权利和行政资源的扩张,以及安置更多需要工作的人员。在这种背景下,新城新区体制机制的设立和改革创新,无非是已有行政部门的兼并、升级与重组,并没有真正引入和建立符合新城新区性质和需要的行政体制机制,这是我国多数新城新区在管理体制越来越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创新力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新城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亟待从制度和体制上加以研究和解决。
3.2.3 体量和规模高速扩张,集聚效应冷热不均
与乡村的分散和孤立相比,集聚和集中是城市的本质特征。新城新区作为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引擎,一般而言比老城区具有更高的集聚效应,这在建设历史较长的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从1994年开始,这两个国家级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差不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如图7所示,浦东新区的最高增速为28.6%,滨海新区的最高增速也达到28.3%。但也应该注意到,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新城新区的引擎驱动效应也会进入衰减期。如浦东新区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9.7%,比起最高峰值几乎回落了2/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在2013年9月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实施范围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其主要原因即以自贸区重新整合已有的四大开发区,减低、延缓和扭转浦东新区的发展颓势,从而带动上海、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图7)。但并非所有的新城新区都有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优势,举例而言,南方某个城市曾提出“建设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的新区”,但在20多年的时间里,投入一千多个亿,实际开发面积约三百多平方公里;再如一个西部省会城市,在该城和另一个城市之间规划了一个500平方公里的新城,但其全省前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支撑这500平方公里的发展”。[15]出现这些问题有其必然性,既符合“中国城市在空间、人口与经济规模上的迅速扩张,只是获得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物质躯壳”[16]的普遍规律,也与我国新城新区处于青少年时期、在城市性格、心态、发展观等方面尚不稳定、不成熟的现实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12个大都市新城新区中,规划建设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超过了30座,在有了足够的体量和规模之后,如何形成符合自身实际和需要的特色发展模式,不再做看上去很美但实质上只是政府沉重的债务包袱,真正成为驱动城市创新转型发展的增长极和引擎,同时为全国600多座城市的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是中国新城新区这个“金凤凰”最应该思考和谋划的头等战略议题。

图7 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经济增速趋势图(1994-2013年)
3.2.4 贪大求洋问题依然如故,精明增长和紧凑发展停留纸上
尽管学界、舆论界和多地政府都提出要遵循精明增长和紧凑型城市的发展模式,但在新城新区规划建设中并未实施或效果并不明显,粗放增长的问题普遍存在。从规模和面积角度看,与老城区改造相比,新城新区的土地资源相对廉价,因此地方政府建设新城新区往往贪大求洋,中国12个大都市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其人均面积大多数都在国家规定的100平米/人以上。从财政收入角度看,多数新城新区仍主要是靠卖地过日子,在各城市普遍存在的土地财政问题在新城新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空间模式看,尽管“摊大饼”式的城市化的弊端和问题早已人所共知,但在现阶段仍是我国新城新区规划建设的主要空间模式。与人口相对少的其他城市新城新区不同,对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北京、上海和重庆,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天津、广州、南京、西安、郑州、沈阳、成都、武汉、汕头,由于人口的高度集聚和总量偏大,其新城新区无论是人均建设面积、还是空间拓展模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都更应该走精明增长、质量增长和内涵增长之路。
3.2.5城市规划调整频繁且幅度大,被规划折腾现象比较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划意识、理念、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匮乏,规划缺乏曾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新时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但受中国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往往从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极端,在过分求新求奇的畸形心态诱导下,不顾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和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使被规划折腾成为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遗憾的是,新城新区也未能幸免。由于规划的滞后或超前以及发展定位、战略变化较多等原因,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的规划修编和调整异常频繁。有的是规划面积扩大,如上海松江新城,原来规划面积为60平方公里,调整后为160平方公里;[17]有的是面积缩小,如上海金山新城的规划经过第三轮修编后,城镇布局和功能发生变化,规划面积由原来80平方公里缩减为41平方公里[18];还有的是土地利用性质发生变化,如广州白云新城规划自2009年出台以来多次修改,2014年的最近一次修改住宅用地减少了23.6万平方米,商业用地增加了127.4万平方米,同时规划人口也相应减少了4.7万。[19]尽管这些规划调整不乏理由,有些也的确是由于原有规划滞后于现实发展,如人口的集聚速度和规模超过或未达到预期等,但有些调整也明显存在着要人手不要人口,以及向土地要GDP等问题。其中最常见和突出的是通过减少住宅用地和规划人口增加商业用地等。这不仅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相违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城新区人均占地面积过大、城市人气不足的重要原因。
4 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4.77%,但与70%的中高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由此可以推知,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升,在未来还会不断有大城市迈入大都市的行列,同时,这些未来的大都市必定要规划和建设越来越多的新城新区,以吸纳迅速增加的人口和承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于中国大都市的新城新区而言,它们不仅指数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同时也是其他中小城市规划建设新城新区竞相模仿的对象。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大都市和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和城市群弱则国家弱”这一新的游戏规则,作为中国大都市核心平台的新城新区建设的成败,也势必直接影响到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中的地位和形象。就此而言,科学合理地规划建设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应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和战略中的战略进行布局和实施。
4.1 在国家层面上,对大都市新城新区的审批应区别对待
目前,中国12个大都市已有6个国家级新城新区,上海、天津和重庆因其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当仁不让地各占一席,而广州、成都和西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也各占一席,这些先赋资源得天独厚的城市的一般发展规律是强者更强,在此大势之下的新城新区建设也无须过多担心。但对另外一些先赋资源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大,在审批国家级新城新区时则应予谨慎处理。但是对于像汕头这样的级别不高却集聚大量人口的城市应该给予足够重视,重点研究其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产业规模是否匹配,从而在新城新区规划建设和审批方面要积极引导。人口是资源,也是矛盾集中发生的源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4.2 在规划主体层面上,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重新反思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
城市研究者提出了三种城市空间拓展理论,即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和多核心理论。与之相应,城市空间拓展也存在三种模式:一是原有城市空间的再开发,即所谓的旧城更新;二是城市空间的连续开发,即所谓的“摊大饼”模式;三是城市空间的跳跃式开发,即建设新城新区。近年来,对“摊大饼”模式的批评与否定十分流行,并成为建立多中心、组团式空间结构及大力发展新城新区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摊大饼”模式在现阶段也有明显优势:一是在一定的规模以下,土地开发的成本会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减少;二是城市边缘带的交通可达性高,可以最小的代价将城市居民与城市就业机会连接起来;三是“摊大饼”模式可提供多样化城市住宅,满足城市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多样化需求。[20]同时,由于远离旧城造新城的“多核心”模式成本高昂,所以中国城市空间拓展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把农村变成城市就没有退路,所以城市规划部门不应彻底抛弃“摊大饼”模式,而是要根据不同城市的需要去选择最优方案。
4.3 在建设主体层面上,各个新城新区走文化型城市发展道路十分必要
当今城市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一是传统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为主要要素的经济型城市化,二是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文化型城市化。[21]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都表明,经济型城市化的风险很大,无论是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还是主要依赖房地产业,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2013年底美国城市底特律的破产就是典型案例。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苏州的发展史是最好的案例,其深厚的江南文化底蕴成为苏州城市历2500年变迁而不衰的源泉。新城新区规划建设伊始,就应自觉地选择文化型城市发展之路,以人为本,重视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摈弃“唯GDP”主义,就会从源头杜绝新城新区“鬼城”、产城分离等后遗症。
4.4 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应深入研究新城新区究竟“新”在哪里
目前,我国关于新城新区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利于指导和指引众多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新城新区不仅仅意味着新房子、新建筑,而是包含了更深刻和更丰富的内涵。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看,是低碳、节能和环保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是高效、创新的管理体制和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从精神文化上看,是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和国际化因素的新城市精神。这三方面应该是既相互独立又互为有机整体,超越目前的千城一面和文化雷同,使新城新区真正成为都市人的精神家园。
4.5 在舆论传播上,是要理性对待和客观评价新城新区
不可否认,在我国新城新区的快速发展中,已经出现并将继续面临很多问题,即使是发育较好的中国12个大都市新城新区,其在发展过程中也走了许多弯路。但决不能因此就彻底否定新城新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未来的城市还要容纳8亿左右的人口,对此不可能依靠既有的城市区域,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是大势所趋,不能因噎废食。同时还要明白,一座新城新区的生长过程,可能需要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理性而有耐心地对待新城新区,在当下是亟需启蒙和确立的城市意识。
4.6 在管理制度建设上,要努力提升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度
城市是市民的城市。早在20世纪,英、德、美、日等国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制度,并通过听证会、有效公告等确保公众切实享有参与权。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情况相对滞后。2008年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初步规定了在城乡规划中公民的参与权利。但公众参与程度仍然较低。与此同时,公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错位往往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如2007年厦门PX 项目事件,2008年甘肃陇南拆迁事件,2011年的广东乌坎事件,2012 年的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及 2012 年 10 月的宁波 PX 事件等。尽管它们“并非相关主体的心血来潮或是突发奇想,往往都有城市规划作为依据”,但由于公众并不知晓或并不认可,[22]遂导致了此类事件的一再重演。在中国的大都市,由于人口高度集聚,市民的维权意识更加强烈以及新城新区规划建设往往牵涉多方利益群体,因此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十分必要。
4.7 在新信息技术的层面上,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为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提供了新平台
对于新城新区规划的编制来说,计算机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的手绘规划图被CAD制图所取代,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给城市规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支持城市设计的三维景观建模,支持城镇化的城市生长模拟,支持相关政策决策的人口空间分析、公共设施布局、土地利用变化的分析等。[23]此外,新技术还可以用于新城新区规划的全过程,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目前普遍采用的在互联网上公示规划成果和问卷调查等已经滞后,而利用微博、WebGIS和微信等平台,可以搭建一种基于社交网络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模式。其中,微博主要用于传播和推广,微信在传播的同时还有帮助公众生成空间信息的功能,而WebGIS平台则主要用于收集和展现在空间信息。[24]由于大都市新城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与智慧城市建设水平都比较高,因而可望实现更好和更充分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并有力地促进和提升大都市新城新区的建设水平。
在总体上看,中国大都市已有新城新区,不仅在数量和体量上稳居全国城市的前茅,而且在形态和功能上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它们不仅以全新的城市空间、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直接体现了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瓶颈性矛盾,也是我国新城新区建设的通病。我们希望通过本报告的梳理、分析、研究和诊断,为中国新城新区在整体上提高规划建设水平,走出一条低成本、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正确的思路和正面的指引。
注释:
①本报告以“大都市”统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和国际学术界的通用概念衔接;二是避免语义上过于繁琐。
②本报告的人口数据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统计人口数量为市区常住人口,非全市人口。
③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据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发现,该统计年鉴在统计标准上并不一致,所以实际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大都市还会多一些。
④受城市化速度快、体量大、政策多、变化性强等因素影响,中国新城新区的设置和规划经常发生各种变更,有时是合并,有时是增加,同时由于往往来得很突然,所以在数量、人口和面积上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
⑤本统计涉及的新城新区面积均为规划建设面积,而非规划面积,例如上海浦东新区规划面积为1210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为831平方公里;北京顺义新城规划面积为1021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369平方公里,本统计均采用后一数据。因为规划建设面积是城区面积,统计规划面积即把新城新区中的非城市建设用地也统计进来,造成结果人为夸大,故采用规划建设面积,这与时下其他关于新城新区面积的统计存在差异。
⑥来源于2002年6月17日南方网发布的《〈珠江新城规划检讨〉公众展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唯一以“检讨”命名的城市规划调整文件,尽管可以解读为“‘检讨’不是否定,而是回顾、总结、重新筹划,是通过‘回头看’以更好地把握未来”。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无疑表明了1993年的珠江新城规划是很不成功的,是中国大都市新城新区规划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的一个缩影。
⑦来源于2012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文件、规划与方案汇编(2010-2011年)》(内部资料)第389页。
⑧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调整广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同意撤销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设立新的广州市黄埔区,以原黄埔区、萝岗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黄埔区的行政区域。因此本报告并未将原广州市萝岗区列入新城新区名单,但是其发展历程是新城新区升级发展的典型案例。
⑨郑东新区实际上已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新身份跻身于新城新区的“国家队”,但由于其发展规划尚未正式发布,本报告暂存而不论。
[1]刘士林,刘新静.全国新城新区研究报告[M]//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J].学术月刊,2006,(12).
[3]张琰.新城新区进行时[J].瞭望东方周刊,2014,(17).
[4]刘士林.中国的新城新区建设的正确认识和评价[J].学术界 ,2014,(2).
[5]沈文敏.2014中国开发区创新发展年会举行 30年为全国GDP贡献68%[N].人民日报,2015-01-17.
[6]张书成.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人文转型[J].中国名城,2014,(12).
[7]刘士林.对新城新区建设要有耐心和信心[N].文汇报,2014-03-01.
[8][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3.
[9]新华网.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 通 知 》[EB/OL].[ 2014-11-20].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1/20/c_1113330964.htm.
[10]成都市规划管理局网.成都城乡总体规划[EB/OL].[2013-03-05] http://www.cdgh.gov.cn/wsggg/lbgg/99.htm.
[11]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网.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EB/OL].[ 2011-11-30] http://www.wpl.gov.cn/pc-35849-69-0.html.
[12]南京市规划局网.南京城市总体规划[EB/OL].[2006-04-21] http://www.njghj.gov.cn/ngweb/Page/Detail.aspx??CategoryID=dd8b3d29-1b2a-4d65-8275-496d16e6e7b6&InfoGuid=228fcddd-825c-4287-8ba9-7781953a23a5.
[13]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 上海市浦东新区总体规 划 [EB/OL].[ 2008-12-8] http://www.fzzx.sh.gov.cn/LT/KDUCO1466.html.
[14]洪浣宁.浦东精神:中国梦的时代元素[N].浦东时报,2013-04-18.
[15]李铁.新城新区建设的六大问题[N].城市中国网,2014-04-20.
[16]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病象研究与文化阐释[J].学术研究,2011,(12).
[17]余梦.松江新城面积将扩容近两倍[N].东方早报,2012-04-23.
[18]邹娟.金山新城面积减半让它尽可能凭海临风[N].东方早报,2012-04-27.
[19]田桂丹.白云新城规划将进行调整[N].信息时报,2014-08-18.
[20][美]丁成日.城市“摊大饼”式空间扩张的经济学动力机制[J].城市规划,2005,(4).
[21]刘士林.中国城市化的文化挑战与回应[J].天津社会科学,2014,(5).
[22]付健.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权研究[D].吉林大学,2013.
[23]马妍,沈振江,高晓路,等.城乡规划支持服务资源的聚合发展现状及趋势[J].地理科学进展,2013,(11).
[24]李苗裔,王鹏.数据驱动的城市规划新技术:从GIS到大数据[J].国际城市规划,2014,(6).
责任编辑:于向凤
The object of this report are more than 130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of 12 Chinese metropolis whose population is above 5 million. The report examines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basic features and issues of these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holding the opinion that the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of Chinese metropolis are characteristic of vast area and huge numbers. They usually have comprehensive functions and are upgraded from those with a single function. They are of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and are coexisting in the region. The urban spatial layout is multi-nodes. They are subjective to living-friendly, ecological living and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industries. However, the mechanism is rigid.The innovation is weak. The clustering effect is unbalanced. The growth model is to be refined. Basing on this current situation, the feasible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hat dealing with each planning of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on its merits; the second is that reconsider the planning of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with Top-level Design; the third is that take the path of cultural city; the fourth is that take research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the fifth is that view the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objectively; the sixth is that enhanc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the seventh is that take full adoption of big data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new towns and districts ; urbanization ;metropolitanization
C912
:A
1674-4144(2016)-01-34(15)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刘新静,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
孔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生。
周继洋,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生。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编号:10JBG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