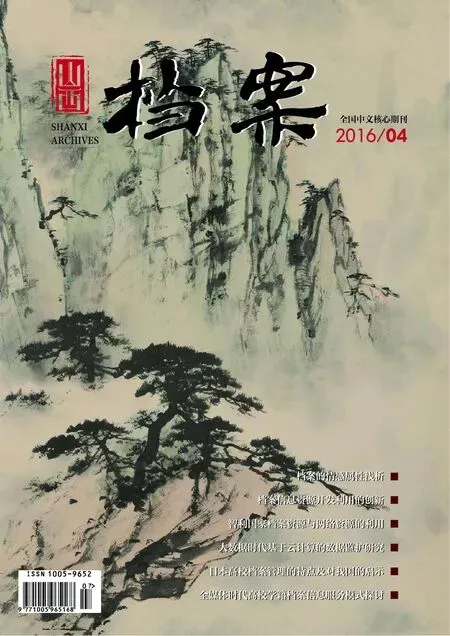儒家民本思想作用刍议
——以明代地方官员的考课政策为中心
2016-02-03张祥明ZhangXiangming
文/张祥明 Zhang Xiang-ming
儒家民本思想作用刍议
——以明代地方官员的考课政策为中心
文/张祥明 Zhang Xiang-ming
The Role of Confucian Notion Regarding the People as the Basis of State
有人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明朝廷在不同时期出台的针对地方官员的考课政策以及地方官员的行政举措昭示:民本思想难以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产生影响。因此,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民本思想;明朝;考课
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民本思想的讨论甚多。儒家民本思想的称赞者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一些皇帝,使一些有见识的皇帝敬畏民众的力量,迫使他们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改善。这是民本思想的积极作用。上述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假如符合,儒家的民本思想一定会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历代王朝的各项政策就会以便民和利民为出发点。有鉴于此,本人尝试以对明代地方官员考课政策的解读为切入点,变换一个角度对儒家民本思想的作用做一番考察。
一、明初对地方官员的考课政策
为了加强地方治理,朱元璋特别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考课。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下令府、州、县官员三年考课一次。[1](第一册p238)
凡各处府、州、县官员,任内以户口增、田野辟为尚。所行事迹,从监察御史、按察司考课明白,开坐实迹申闻,以凭黜陟。[2](p4)
从《大明令》的规定看,发展农业生产是明初地方官员的最重要职责,但是,这一政策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洪武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再次强调把教育和农业发展的业绩作为对地方官员考课的重点内容。[1](第一册p378)这一考课政策的确在朱元璋的亲自关注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比如,洪武九年六月,山东日照知县马亮考满进京朝觐。在进京前,知州将马良的考课等级定为优等,给他的考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见到马良的考语后说,地方官员的要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兴办教育,而不是巧于敛财以完成国家的赋税。因此,他敕令将马亮黜降。[1](第一册p476)关于朱元璋对地方官员的考课举措,清朝官修《明史》卷281记载如下:
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府州县吏来朝,陛辞,谕曰:“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已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尔等戒之。”洪武五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日照知县马亮善督运,无课农兴士效,立命黜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对照《明实录》,我们不难发现《明史》的记载存在诸多错误,其中之一,日照知县马亮进京朝觐是在洪武九年,而不是在洪武五年。另外,张廷玉等人对朱元璋的考课政策评价甚高,认为朱元璋的考课政策对地方官员起到了威慑和引导作用,官场风气因之一变,民众受益,成就了明前半期的清廉政治。其实,清朝官修《明史》的这种说法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洪武九年(1376),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在奏疏中批评府州县官“以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3](p56)这说明,在洪武前期,完成赋税征收是地方官员最迫切的任务。洪武前期的地方官员把赋税征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洪武后期也是这样。洪武二十一年,解缙在奏疏中抨击地方官员征税太重、贪婪苟且,民众被逼得无法生存。[4](p4115)这说明,清朝官修《明史》所谓的明朝前期官员守法爱民、民众安乐、吏治澄清的论断,不过是修史者的臆断而已。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王朝的前期多是民众生存条件较好的时期。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亲眼目睹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强调“为政以得民心为本”[1](第二册p125)。为了得到民心,他强调要“爱民”[1](第二册p317),要不违农时,薄赋敛,节徭役[1](第二册p132),藏富于民[1](第二册p130)。由于朱元璋提倡爱民和安民,明朝初期应该是国泰民安的时期。但是,民众在洪武年间仍然被沉重的赋税逼得弃家逃亡,聚众反抗。永乐年间,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山东和河南等地的受灾民众,明朝廷不仅不加以赈济,反而征敛不息。从明朝前期民众的处境看,儒家的民本思想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明朝后期对地方官员的考课政策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明朝前期的国家政治不能发挥作用,对明朝后期国家政治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因为明朝中后期,政府的开支比前期增多,民众的负担比前期更重。与此相对应,在明朝中后期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和施政行为上更难找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
明朝后期,军饷开支大增,为了督促地方官员按期完成赋税征收,至迟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明朝廷就针对赋税的征收,对地方官员实行考成制度,“凡本年银两欠一分者,州县印粮官住俸督催;欠二分、三分者,降俸二级;欠四分、五分者,降职二级;俱戴罪督催;欠六分、七分者,降职二级,起送吏部调用;欠八分、九分者,革职为民。”[5](第二十四册p471)天启七年十月,明朝廷又规定:地方官员更调、考满或请求封赠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先由户部核实他们是否完成了任期内的赋税征收任务。[6](第二十三册p351)
崇祯元年(1628)六月,明朝廷又规定:各布政司及两直隶府每年额定的赋税钱粮必须按期上缴,否则,朝廷根据缺欠钱粮的数额对各级地方官员予以惩罚。[6](第二十五册p479)八月,明朝廷又出台政策:将州县官员每年完成的当年的税粮数额,以及催征的往年欠税数额和其他杂项税额,计入考成册内,根据州县官员一年上缴的各项赋税的数额对他们进行考课。[6](第二十五册p500)十月,明朝廷进一步决定根据地方官员完成工料银和柴夫银征收完成的份数对地方官员实行处罚。[6](第二十五册p538)
由于“上官以催征为考课”,善于搜刮财富的地方官员被看作“徇良”,考课制度罢黜不职和惩罚赃私的目的完全丧失。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考成任务,赋税新旧并催,广大民众被迫卖儿鬻妻,所有的财富被搜刮殆尽。
崇祯四年十二月,明朝廷又对加派的辽饷征收实行考成之法,除了继续推行地方官员完成征收七分免于惩罚的政策外,①从崇祯五年对地方官员的奖惩情况看,地方官员赋税征收完成六成以上者就可免于惩罚,见下文。明朝廷还规定,完成全额辽饷征收的官员,只要实心任事,地处繁巨,由督饷御史记录,报请朝廷升职。这一政策在随后的崇祯五年得以贯彻。该年十二月,明思宗就核准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请,根据辽饷征收的完成情况对全国地方官员进行奖惩,少数官员因按时完成辽饷征收任务获得“优叙”,多数官员因未能完成辽饷征收任务受到不同形式的惩罚。[7](p17-46)
由于地方官员的待遇和前途取决于他们完成国家税额的多寡,“长吏考课惟问钱粮”[6](第二十六册p537),因而,地方官员“迫于功令,惟知催征如额,速图升迁,鲜知以民生为念”[6](第二十六册p511),甚至借机中饱私囊,导致民穷盗起。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不论明朝前期还是后期,赋税征收始终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任务,上缴赋税始终是普通民众最重要的义务,沉重的赋税始终是普通民众难以应付的负担,经常使普通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沉重的历史事实昭示:儒家的民本思想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很难发挥作用,民本思想无法使普通民众得到实惠。
其实,所谓的民本思想,在许多明代人的政治思维中,绝对不是国家以民为本,而是把民众看作赋税之源。比如,朱元璋早在称帝以前就表示,农民是国家赋税之源。为了确保税收,各级官员必须劝农耕作,无夺农时。[1](第一册p77)洪武二年,朱元璋又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1](第一册p225)因此,他要求百官“裕民”[1](第二册p382)。可见,朱元璋的爱民之举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源和朱氏王朝的稳定。明代士大夫的政治逻辑也和朱元璋的政治思维相似。比如,崇祯四年二月,刑科给事中吴执御批评粮饷加派,他的理由是:“财之源在于民,而理财必先治民,不先为蹙民之事,以竭其源流耳。”[6](第二十六册p306)他又说:“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故自古帝王必以民为重。诚以军国之经费,兵食之大计,悉于此系焉。”[6](第二十六册p471)这说明,统治者宣扬民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赋税,民众绝对不是国家的“本”。①李宪堂认为,“民本”强调的并不是“民”自在自足的价值,而是它对于国家社稷,归根结底是对于君主的意义。参见李宪堂:《试论儒家民本思想的专制主义实质》,《历史教学》2003年第5期。从明朝君臣对民本思想的论述看,李说甚是。
明代地方官员考课制度昭示我们: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历史发展的历程中不过是一种口号而已,它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任何政权的存在必须以获得足够的税收为前提,民众必须纳税,即使以保障民权为目的民主社会也不例外,更何况明王朝是一个以维护名分等级为特征的政权。由于明王朝(历代王朝也类似)的政权性质不是为了保障民权,而是为了维护特权,因而,奢望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中发挥大的作用,无疑是缘木求鱼。
(责任编辑:杨秋梅)
[1] (明)姚广孝等.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M].北京:线装书局,2005.
[2] 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大明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明)朱纯臣等.钞本明实录·明熹宗实录[M].北京:线装书局,2005.
[6] (清)汪楫.钞本明实录·崇祯长编[M].北京:线装书局,2005.
[7]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国立北京大学文史研究院文史丛刊第一种:崇祯存实疏钞[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K248
A
1005-9652(2016)04-0165-03
张祥明(1967—),男,山东济宁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