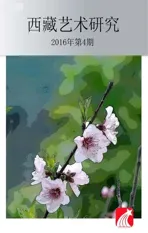浅析藏戏的剧场化进程
2016-02-03刘才华
刘才华
浅析藏戏的剧场化进程
刘才华
纵观全世界各地的戏剧,从古希腊到中国,从衍生初期到逐渐成熟,都必然经历剧场化这一过程。诞生距今已有600多年的藏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剧种之一,虽然与汉族戏曲一样同属于中国戏曲这一体系,但由于受到地域、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其剧场化进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渐起步,十分缓慢。本文从现有的剧场版藏戏入手,结合笔者参与的剧场化藏戏创作经验,试分析藏戏的剧场化进程。
藏戏;广场;剧场化;诺桑王子;进程
藏戏,作为藏族民间传统艺术,从诞生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剧种之一。它由藏族文化发源而来,积淀了深厚的藏文化底蕴,是盛开在雪域高原上的一朵艺术奇葩。藏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艺术形式独特,其剧目多出自于佛经故事,故而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藏戏分支众多,流派纷呈。藏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受广大藏族同胞的喜爱,也吸引了不少内地观众的目光,特别是很多藏戏传统剧目改编成剧场版之后,增加了各地交流演出的机会,提高了藏戏的知名度,也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藏、汉戏曲同属于中国戏曲体系,藏戏虽然表现出与内地戏曲极大的差异,但它毕竟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生根而来,二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自然拥有很多相似之处。①刘志群《中国藏戏史》,第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汉族戏曲起源有多种说法,民间歌舞、百戏、傩戏、宗教祭祀等等。藏戏除了上述起源之外,由于受西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宗教对藏戏的影响更加深远,从故事情节、演员表演、人物设置到服饰造型等,都可以看出浓厚的宗教色彩。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汉族戏曲已经具有高度剧场化的特点,而藏戏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宗教的影响,加上高原的天然屏障,剧场化进程似乎慢了一步。缓慢的剧场化进程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原生态的内容,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让人可以窥探藏戏甚至是中国戏曲几百年前的样子,但是戏剧要发展,剧场化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之后,古老的藏戏踏上了剧场化的进程,吸收了内地戏曲的经验,增加了实践性的探索,特别是近年来藏戏的剧场化进程越来越快,成效越来越明显,剧场版的藏戏摘得了不少戏剧奖项,古老的藏戏与现代剧场相融合正在迸发别样的生命力。
一、广场藏戏
广场藏戏顾名思义是在广场上演出的藏戏,也是现在藏戏演出的主要形式,在专业藏戏院团成立之前,藏戏演出没有固定的舞台,在乡间、草原、寺院、广场,搭个帐篷就可以连演好几天藏戏。直至今日,广场还是藏戏的主要演出场所,宗教祭祀、大型庆典都能在广场上看到藏戏演出的影子,藏民们带着糌粑、奶渣、酥油茶围坐在广场,跟着戏剧的节奏起伏,为遭受厄运的主人公叹息。演员们也能在每场演出中的休息时间,与观众一起吃食物、聊天,在这里,大家不仅是来看戏,也是一种社交活动,是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谢真元《藏、汉艺术表演特征之比较》,《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与广场演出的随意性相比,高度剧场化的演出对于观众的要求也更多,人们在剧场正襟危坐、屏息以待、不苟言笑、更不能随意交谈,唯一的躁动就是每一场结束或是演到精彩之处的掌声与叫好声。
广场戏剧未经太多雕饰,现在还能在广场藏戏中看到很多戏曲形成初期的影子。拿藏戏演出来说,演出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温巴开场、甲鲁赐福,这是开场戏,作为序幕并不承载太多的戏剧功能,主要目的在于祈神赐福,聚集观众为正戏做准备。“温巴”就是猎人或者渔夫,带着蓝面具,手持五彩箭,跳着祈神驱邪的舞蹈,然后类似于宋元南戏的副末开场,蓝面具会开始说“雄”把一出戏的剧情从头至尾说一遍,过去的说“雄”中甚至还会出现整出戏所有人物的戏词,所以仅仅是一个开场,演上一天都毫无问题。
紧接着是正戏演出,跟着剧情的发展分场次演出,由于藏戏大多取自于佛经的故事,加上没有演出剧本,只有文学本,所以各地演出并没有什么规范性,戏也不像我们现代剧场戏剧那么紧凑,两个小时左右能说完一个故事。八大藏戏的故事剧情庞杂、故事冗长、支线众多。最后是“扎西雪巴”,也是演出尾声,全体演员出场,同开场一样,载歌载舞,为在场观众祈福,并接受观众献来的哈达。如此下来,一出戏在广场上演上几天轻而易举。观众可以随时观看演出,并且知道剧情发展到哪个地步。
藏戏中的面具也可谓是一大特色,也与广场演出有着极大的关系,带面具演出,不仅可以更好地塑造剧中人物形象,增强感染力,也便于坐在广场周围的群众识别人物,对人物有直观的了解,这和汉族的戏曲乃至欧洲的戏剧都有相似的地方,虽然藏戏发展过程中,男女主人公逐渐不带面具,取之以淡雅的化妆,并且有些反派人物所戴的面具很小,斜于额头的一角,富有象征性。②刘志群《中国藏戏史》,第12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尽管面具有些改变,但是大多数的人物角色还有动物都是带面具进行表演的,加上穿插进藏戏的民间艺术表演和宗教表演都有许多的面具,并且面具的表演技巧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且沉淀了藏族的审美趣味,所以带面具表演仍然是藏戏表演中的特殊形式,也彰显了藏戏的艺术特色。
二、剧场化的藏戏
汉族戏曲高度成熟是建立在高度剧场化的基础之上的,汉族戏曲作为剧场艺术,拥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的瓦舍勾栏,到了元代,已经建成了大量戏台,直到今天,这些戏台在山西还有不少遗迹,明代戏曲的表演场所更为多元,上层社会有堂会,民间有庙台、戏台。到了清初更是出现了营业性质的戏曲演出场所——戏园。剧场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催生出汉族戏曲的高度成熟。
然而几百年来,藏戏都在乡间、草原、广场上演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藏戏演出才逐渐往剧场化发展。八大藏戏作为最广为人知的藏戏剧目,其中《诺桑王子》《卓娃桑姆》《白玛文巴》《文成公主》《朗萨雯蚌》已经整理改编成剧场版,并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苏吉尼玛》《智美更登》建国初期打磨过,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向剧场化走进。八大藏戏中唯一没有经过任何改编创作过的就是《顿月顿珠》,这是唯一一个目前还保持着广场特色的戏。八大藏戏作为藏戏最有名的剧目,尚且有三个没有进行过剧场化的重新创作,可见藏戏的剧场化进程是比较缓慢的。
将广场藏戏变为综合的舞台艺术,前辈们做了很多调整和改编,吸收了内地戏曲的经验,将民歌融入藏戏唱腔,以便更好的塑造人物;借鉴现代剧作技巧,重新整理剧本,让戏剧性更突出;同时还借鉴了现代舞台技术,包括舞台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等等,一改以前一鼓一钹两种打击乐伴奏下得清唱和大段唱诵,传统藏戏慢的特点有极大的改善,下面笔者将一一进行阐述。
表演上:过去藏戏是唱时不舞,舞时不唱;说时不舞,舞时极少说。①谢真元《藏、汉艺术表演特征之比较》,《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剧场化之后要兼顾人物的唱念安排于是说唱相间,散韵结合。并且藏族民间舞蹈,往往是唱一段,再舞一阵,唱和舞交错进行,即唱和舞是相分离的。现在也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歌、舞、唱的有机统一。并且吸收了不少内地戏曲的表演经验,《诺桑王子》中,为了突出剧种咒师的心肠狠毒和诡计多端,单纯的藏戏面具已经不能满足表现人物多面性的要求,于是让演员赴四川学习变脸的技艺,从而更好的表演人物心理的变化,并且进入剧场之后变脸也很有看头,成为演出中的小小亮点。藏戏演出善歌舞场面,但是技巧性的动作不多,而汉族的戏曲经过多年剧场化的演变,有很高的技巧性,比如人物上马、行军、开门、饮酒等等,这些表现人物心理、行动等等技巧非常之多,藏戏演出中吸收这些小技巧,使人物更加丰满,表演也更加生动,极大的丰富了藏戏的表演。
文本上,广场戏经常连演几天,观众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此时广场不仅仅是表演场所,更具有一些社交功能。但是剧场戏剧不同,由于时间的限制,一旦戏剧演出时间过长,观众坐在剧场会逐渐焦躁不安,失去耐心,所以纵观剧场的戏曲演出,很少有戏特别冗长,都是尽量在两个小时左右完成整个戏剧故事。这样广场戏和剧场演出从文本上就有天然的矛盾在里面,一个连演七天的戏要变成两个小时,剧本上必然需要调整,修剪一些旁支末节,使戏更加紧凑,戏剧性更强,戏剧冲突更强烈。以《诺桑王子》为例,《诺》剧中支线众多,有咒师作法勾结恶妃迫害云卓拉姆的线,还有猎人救龙王对云卓拉姆起色心的线等等,戏剧性很不强,剧场演出中大胆地删掉了猎人换宝物,对云卓拉姆起色心等线索,变成猎人主动想把云卓拉姆献给诺桑王子,这样既使故事紧凑又突出了猎人这个人物。并且由于甲鲁开场中大量的敬神祈福的内容,严重耽误了剧情的发展,大胆又包括开场甲鲁的敬神之讼,扎西雪巴中的东西都省略了,这样戏看起来更加紧凑,也更适合剧场演出。
创作形式上,内地的导演、编剧介入使得藏戏进入剧场的步伐更快。由于地域的天然屏障,国内外一些新鲜的戏剧信息不能那么及时的传入藏戏,内地导演和编剧的介入可以带入很多新鲜的戏剧元素和戏剧观念,笔者有幸作为编剧参与藏戏《朵雄春天》的创作,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藏族的导演和汉族的导演一起,藏族的编剧和汉族编剧一起,不仅能融合一些戏剧创作上的新观念,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并且有本民族的人一起创作,一起把关,在整个剧作的把握上都能保持民族特色的东西,不至于和汉族的戏曲一样趋同。举个例子,创作当初我们想在剧中安插一个类似于说书人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藏戏,怎么安排说书人都觉得不合适,后来大家思考了很久发现藏戏中的老两口角色特别契合我们剧本中的说书人,而且老两口原本也是对剧情有一定介绍作用的,于是老两口在融入我们这个现代题材的戏当中,老两口串进串出,与剧中人物隔空对话,在藏戏剧场的舞台上这是首次运用,大家也觉得很新颖。藏戏有很强的歌舞性,但是藏戏中穿插的舞蹈很多与剧情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舞蹈动作不是为剧情发展、人物塑造服务而创作的,而是为烘托气氛,塑造歌舞场面,在剧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作为间奏出现。我们不想阉割藏戏原本的艺术特色,但是尾声的扎西雪巴如果不与剧情结合,并不能凸显本剧的独特之处,于是我们想到此剧是以一把六弦琴为主线,如果把六弦琴的歌舞场面融入到尾声的扎西雪巴之中,会不会独具特色呢?这么尝试之后发现确实很独特,也很有民族特色,跳出来特别好看,也特别符合藏戏的特点。
虽然藏戏在向剧场化进军,但是藏族观众不一定能这么快的接受剧场化的藏戏,笔者在剧场中亲眼见到,观众如同广场演出一样,带着食物,边聊天边看剧场化的藏戏,剧场演出的神圣感荡然无存。这并不是观众素质的问题,而是藏民在长期的广场演出中形成的观剧习惯,这些已经深入骨髓的习惯并不会因为演出场所的改变就改变,所以培养观众对于剧场与广场不同的认知也是极为必要的。
三、展望
藏戏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从它的发端开始一直存在于广场、草原、乡野之中,现在它正往剧场里面走,希望它能保持自己的艺术魅力,开出别样的艺术之花。
戏剧艺术在剧场中演出,走进剧场的过程中很容易逐渐趋同,纵观我们现在的剧场戏曲演出,有些演出在走入剧场的同时,可以说丢失了自己本剧种的艺术特色,这点要为藏戏剧场化所警醒。藏戏或者说整个藏族文化都是和宗教艺术息息相关,所以创作上一定要尊重此民族特点,在原有的艺术基础之上再进行拔高。藏戏进剧场一定要保持原有的民族特色、艺术特色,宗教的、文化的,包括面具都不应该因为进剧场而有所放弃,反应该更加通过这些独特手段,借剧场化之力增强自己的艺术魅力。同时要合理利用交通、网络带来的便利,加强对外交流,参加国内外的戏剧演出,多吸取一些先进的理念,融入传统演出中。
虽说剧场化是戏剧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藏戏广场演出这一古老的传统,千万不能因剧场化的演出而破坏。剧场化是有选择性的,该保留的传统广场戏演出依然保留,保持这个鲜明的特性,不能所有演出全部剧场化,应该有所分开,广场演出还是要保持原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一批剧场的艺术精品,要满足不同层次的演出需要。舞台技术上要多吸取一些声光电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演出服务,也更能吸引观众。并且由于常年的广场演出,观众对于剧场藏戏的接受程度并不太高,走入剧场的观众很少,要培养观众在剧场内的观剧习惯,鼓励大家多进剧场看戏,让大家逐渐接受这种改变。
中国的戏曲从宋时的勾栏瓦舍到现在已经有多年的剧场演出经验,表演也趋于完善、精致。但是藏戏带着他从高原上来的原始的原汁原味的表演,他的剧场化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吸收汉族、国外的剧场演出经验,保持住自己原来的民族特色,古老的藏戏就一定会迸发出别样的生命力。
1.刘志群《中国藏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刘志群《藏戏与藏俗》,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李云、周全根《藏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索次《藏族说唱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彭隆兴《中国戏曲史话》,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
6.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7.朱文相《中国戏曲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年版。
8.谢真元《藏、汉艺术表演特征之比较》,《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
9.谢后芳《佛经故事在藏族文学作品中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刘才化,中国戏曲学院在职研究生】
(责编:褚丽)
;J825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
; A<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
;ISSN1004-6860(2016)04-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