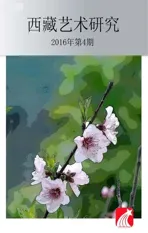西藏音乐的历史书写
——评更堆培杰及其《西藏音乐史》
2016-02-03次仁朗杰
次仁朗杰
西藏音乐的历史书写
——评更堆培杰及其《西藏音乐史》
次仁朗杰
【论文摘要】更堆培杰的《西藏音乐史》是一部兼顾历史顺向研究方法和逆向研究方法研究藏民族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文化,以音乐人类学视域双向关照下撰写的西藏音乐史学专著。本文以音乐人类学视角评述更堆培杰及其著作《西藏音乐史》。
更堆培杰;西藏音乐史;音乐人类学
藏民族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享誉世界,研究藏族文化的藏学已成为一门当代国际性显学。藏学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历算、艺术、民俗、历史等广泛领域,国内外研究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而举世公认。音乐作为一门藏族文化的分支学科,近半个世纪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藏族音乐历史方面的人文社科研究还处在藏学研究里尚未完全开发的边缘学科,所以,西藏音乐史写学在藏学研究中属于刚刚开始和起步。在近几十年里,随有少数学者踏足音乐史学的领地,但有关西藏音乐史学的著作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
人类从事音乐活动的历史是一部客观存在的音乐史,而音乐史家写的音乐史著作则是一部主观的音乐史;因此,前者是音乐史本体,后者是音乐史学对音乐历史的史学研究。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历史学;二者不可混淆。历史学与历史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历史学不仅仅去追寻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各种现象,而且还要去探寻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的科学。音乐史学与音乐史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音乐史学不能代替音乐史,音乐史学同样不仅仅去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各种音乐现象,还要去探寻音乐发生和发展的规律①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而西藏音乐史学的研究与撰述,必然也是探寻这一发展规律的过程。
一、历史成因:西藏音乐研究
(一)西藏音乐研究
上世纪较早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学者出生背景、意识形态和研究视域不同等原因,对西藏音乐的研究范畴自然形成了两种不同趋势:国外学者大部分更多关注宗教音乐研究和《格萨尔》史诗音乐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大多关注点基本限于民族民间音乐居多,由此研究对象和成果呈现出两级化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国内改革开放和新的文化思潮冲击,以及几大集成的编纂工作起始,国内音乐研究领域趋于单一化形态研究局面逐步有所改观。以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以本土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和研究,先后完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西藏卷》《中国曲艺志·西藏卷》《中国戏曲志·西藏卷》等几部集成的编撰工作,在历史源流等方面都涉及音乐史学。
随之,国内众多学者在国内各类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音乐学术论文,西藏音乐研究的范围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成果丰硕,先后出版发行了多部涉及西藏音乐史料的专著和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雪康·索南达杰《西藏歌舞概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藏文版)、边多《当代西藏乐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西藏音乐史话》(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米加参《雪域热巴》(民族出版社,1998)、《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索朗次仁《藏族说唱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嘉雍群培《雪域乐学新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冯光钰、袁炳昌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京华出版社,2007)、更堆培杰《西藏宗教音乐》(民族出版社,2009)、觉嘎《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田联韬《走向边疆-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西藏音乐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王华《西藏热巴音乐文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藏族传统乐器——扎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强巴曲杰、次仁朗杰《西藏传统戏剧——阿吉拉姆戏剧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格桑平措《西藏乐器概论》(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藏文版)、米玛洛桑《西藏当代音乐史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张伯瑜等《环喜马拉雅山音乐文化研究》、田联韬《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格桑曲杰《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藏族传统乐器——哔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等;此外,还有涉及音乐史学的硕士学位论文格桑《论西藏音乐中的西藏历史》(西藏大学,2008)、加拉《论藏戏——阿吉拉姆的起源及其艺术特征》(西藏大学,2008)、次旦卓玛《西藏传统歌舞‘卓’久(鼓舞)研究》(西藏大学,2008)、次仁朗杰《西藏传统戏剧阿吉拉姆音乐研究》(西藏大学,2009)等,博士论文有嘉雍群培《藏传佛教密宗“死亡修行”仪式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07)、次仁朗杰《西藏卫藏地区阿吉拉姆音乐文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6)等。
纵观近几十年涉足西藏音乐史学专著和学位论文,我们可清晰地观察到,西藏音乐史学从无到有,从专题研究到通史的撰写,逐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西藏音乐的通史写作方面,更堆培杰的《西藏音乐史》(2011,以下简称《藏音史》)从西藏音乐史学的系统研究和完整程度以及出世时间(2000——2003年)而言,这是一部填补西藏音乐史空白的学术研究成果,以研究的深度和全新的视角得以脱颖而出,是目前西藏音乐史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而独占鳌头。
(二)更堆培杰及其西藏音乐研究与历史书写
更堆配杰,1953年出生于西藏拉萨,1982年毕业于西藏师范学院音体美系,曾在天津音乐学院进修作曲。现任西藏大学艺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西藏音乐家协会理事。在30年的教学工作中,培养了大批音乐专业学生,特别是自2000年始,教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藏族音乐硕士研究生,所授专业方向涉及藏族音乐史(古代史、现当代史)、藏传佛教音乐研究、藏族戏剧音乐研究等课程。多年教学工作之余还创作有歌舞曲《欢庆》、歌曲《雪域青年》、《温暖的太阳》、《幸福泉》、《迷恋的草原》,合成器配乐曲《天葬冥音》、《高原风景》,歌曲《鹰》等。收集整理了以堆谐、朗玛为主的大量民间音乐乐谱,录音制作了《西藏古典音乐》盒式录音带和CD。先后发表《西藏宫廷音乐概述》、《试论藏传佛教音乐的审美》、《西藏宗教音乐史概述》、《略谈藏戏阿吉拉姆音乐》、《声律文字与藏传佛教诵经音乐》《藏传佛教音乐审美》《西藏雄色寺佛乐“绝”“及其”研究》等二十多篇专业论文,出版著作更堆培杰《藏族音乐简史》(西藏大学校内教材,2000藏文版)、《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西藏宗教音乐》(2009)、《西藏古乐谱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西藏音乐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藏文版)、《西藏音乐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等。在更堆培杰的藏族音乐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涉猎藏族音乐文化的多个领域,而且在近十年内三次编著西藏音乐史,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多产的学者,也是一个具有当代学术思想,撰写高品质《藏音史》的理想人选。
对于他的《藏音史》,先后由国内专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藏族音乐研究资深专家田联韬教授对《藏音史》的评价中写道:本人在阅读书稿之后,认为《西藏音乐史略》是一部有学术深度和创新意义的著作。他还具体评价道:
1.史论研究首先重在掌握翔实可靠的资料。本书作者从西藏古代文献、考古发现、先存音乐生活等诸多方面,收集占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这为此项特殊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比较扎实、比较可信的基础。
2.各民族音乐历史发展的分期,属于基础性的学术判断,十分重要。本书对西藏音乐史的分歧,是西藏独特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发展的特点而确定的。本人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合理的。
3.本书脉络清晰,观点明确,论据合理,分析比较细致,内容也比较丰富。其中本教音乐、谐钦、吐蕃古尔鲁歌、藏传佛教音乐及乐谱等许多章节的内容,都是言而有物,言之有据的。创新意义表现在书中有不少内容是首次正式提出的。①更堆培杰著:《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认为,这是一部我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有关该课题的研究专著,对推进西藏文化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②同上。。但是,2006年新华网西藏频道4月29日报道:“中国首部系统介绍西藏音乐历史的著作《西藏音乐史话》近日有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错误信息,这只是由于记者不了解西藏音乐史学前沿动态所导致,并不影响更堆培杰《藏音史》在学术领域的领军地位。
二、历史书写:《西藏音乐史》
更堆培杰的《藏音史》主要有四章正文构成:第一章、远古时期的音乐;第二章、吐蕃时期的音乐;第三章、藏传佛教后宏期以来的音乐;第四章、噶丹颇章地方政府时期的西藏音乐。作为通史性的音乐史,历史时期的时间划分,作者沿用了国内外藏学研究领域较为通用而粗线的划分方法。这是因为作者考虑到,《藏音史》撰写是历史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历史时间划分既要符合西藏历史的整体发展的时间节点,同时重点考虑音乐史料能够提供音乐历史信息的实际作为出发点的结果。作者认为:《藏音史》历史时期划的过细,而没有相应的音乐史料来支撑,可能某些历史时期就成为没有音乐有关的“音乐史”。 由此可见,作者《藏音史》的研究是立足于西藏音乐史学的实际,采取是音乐史料为先,以音乐史料的把握确定既符合西藏历史整体时间段的划分,又能够有依据地阐述其相应历史阶段音乐史的比较科学的时间划分方法。
更堆培杰在《藏音史》第一章中论述的关于音乐的起源,是学术界认为比较复杂或避而不谈的命题。但是,作者在有关音乐起源上,首先分析人类对此认识的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各种不同说法,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音乐起源认识加以比较,把有关音乐起源的共性和个性揭示出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进一步阐述,劳动创造人的前提下,音乐起源是多元的学术观点。作者通过包括民间传说、神话等大量史料,梳理了西藏远古时期音乐的形成发展线路,呈现了一幅美丽的原始音乐文化图卷,从原始的宗教信仰直至苯教宗教文化的形成,并通过早期文献和考古、乐器等实证藏族乐舞远古时期的存在;第二章,根据大量吐蕃历史记载论证吐蕃时期的民间歌舞音乐、吐蕃古尔鲁歌、谐钦、果孜”嬉武、吐蕃时期的乐论、吐蕃乐器、吐蕃佛教音乐等各类歌舞音乐品种的多样性。其中以起源于吐蕃时期的谐钦为例,作者以历史的联系比较解释方法与音乐人类学的比较阐释模式描述的方法,把同一个历史时期舞台上出现的吐蕃“谐钦”(即大歌)和唐朝大曲加以比较阐述,从而使《藏音史》始终保持即尊重藏民族音乐发展的独立性,也注重其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普遍性的音乐人类学音乐史观;第三章,藏传佛教后宏期以来的民间歌舞音乐、藏传佛教音乐及乐谱、藏传佛教乐器、噶举派与古尔鲁歌、萨班乐论、藏戏阿吉拉姆音乐、格萨尔说唱音乐等七个领域,阐述这一时期音乐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脉络;第四章,论述噶丹颇章地方政府时期的西藏音乐宫廷卡尔音乐、乐谱与音乐理论、仓央嘉措及其古尔鲁歌、“堆谐”“囊玛”歌舞音乐、职业和业余歌舞音乐组织及其活动、乐器、歌舞音乐艺人及有关人物等展示了西藏音乐文化繁荣的景象。全程地展现了一个完整的西藏噶丹颇章地方政府时期音乐文化的历史画卷。其中最精彩,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有关西藏“卡尔”宫廷古乐谱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超越时间和空间,把300年前的“卡尔”古乐谱破解并展现在我们当代世人面前。
就西藏音乐历史而言,作者认为“西藏音乐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而我们所表述的西藏音乐史则是这以几千年客观历史的部分主观反映”①更堆培杰著:《西藏音乐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通过作者在前言自叙,我们可以体会作者撰写《藏音史》的初衷:“藏族音乐史是一本通过史学、人类文化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尽可能揭示藏族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各种音乐体裁的形成和积累;乐论及其音乐技法和作曲理论的产生和内涵;中原音乐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同藏族音乐文化的交流及相互影响;周边邻国和地区音乐文化对西藏音乐的影响;职业和业余歌舞音乐组织及其音乐活动;诸音乐艺人的生平及其社会影响;音乐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关系等问题,并系统地叙述藏族音乐历史发展基本轨迹的史书”①更堆培杰著:《西藏音乐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三、历史视角:音乐人类学
在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不管是“宏观”研究还是“个案”的研究,任何研究都回避不了对历史的书写。当代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领域,受人类学影响,国内外音乐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突显出了新的方法和运用,尤其以欧美国家的音乐学者更具代表性。在书写音乐民族志的方法上形成两类态势,而不拘泥于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的收集材料的“坐在轮椅上的研究”原始阶段。因此,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指出:“在民族音乐学(广义)学科范畴内,较基础及核心的部分是音乐民族志,其外沿则与当代种种学术理论,包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时期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相联系。同时,在广义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内部,则存在两种对课题研究范围的基本选择方式:一种是较注重课题的抽象性和理论性特点,并且立足于文化行为的考察目的和历史性解释的考察方法;另一种则是较注重课题的具体性和整体性特点,其研究目的、方法和过程均建立在田野考察和实践性基础之上,文本的撰写方式中兼顾描写性和解释性。前者是一般性的音乐人类学课题,后者则是音乐民族志课题。从研究视野或范围上看,前者往往较注重并立足于宏观层面的探索与比较,后者则立足(或起始)于微观个案的考察与描写,继而才考虑跨文化比较和理论性探讨。前一类学者更似于人类学界的文化哲学家和美学理论家,后者则是一批重行为实践的行动家。前者的主要作业场地是以书斋为主,田野为辅。后者则是以田野为主,兼涉书斋”②杨明康著:《中国传统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页。。更堆培杰《藏音史》正是在当代学术思潮影响下,改变传统音乐史书撰写的书写方式,以全新的音乐人类学视角和理念书写而成。我们可在后记中看到作者这一研究的方法和目的:“这次重新修改编写的《西藏音乐史》教材,注重教学目的,以音乐人类学的音乐史观重点描述和解释西藏重要各音乐历史时期及其各个时期中的重要音乐事象等内容”。《藏音史》的撰写,印证了民族音乐学家涅特尔所指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为我们展示了重大而广阔的历史性价值和贡献”③杨民康著:《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音乐人类学视角的研究理念决定了作者研究的方法。作者在编著新版《藏音史》期间,同时承担《西藏宗教研究》和《西藏古乐谱研究》的课题。在文献梳理的期间,翻阅了大量藏文古籍,反复推敲古籍文献中深奥难懂的词汇,以及不断地自我提出新的问题。为了实证文献与现实的活态音乐文化,不顾艰辛,深入田野,花费大量的课余时间,多次前往各地实地考察,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并时刻关注音乐人类学科发展的前沿,促使《藏音史》的撰写有了新的突破和研究视角。作者以兼具“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不仅从”宏观”-“客位”研究视角的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又以“中观-互补”的思辨研究思维梳理了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再以“微观”-“主位”的田野考察阐释了各时期、各音乐种类的音乐的形态和风格特征,结合音乐图像学说,配上大量的音乐图片文献,以“历时”与”共时”的叙述,以全新面目(音乐人类学方法),给读者呈现了一部生动而鲜活的西藏音乐史。
结 语
美国音乐学者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曾在《音乐民族志的风格》一文里所说:“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历史”①杨明康著:《中国传统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页。。西藏音乐史学从无到有,从早期史话到完整的通史,经历了其历史发展的必然归路;《藏音史》以清晰的历史脉络,详实的古代文献资料,多次的田野实地考察,丰富的音乐案例分析,大量的图片的展示,试图以全新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理念,完成了其西藏音乐历史的写作航程,开端了西藏音乐史学一个新的道路,也对西藏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该书的书写范式是否具有严格意义的音乐人类学学科范式有待商榷。另该书美中不足之处还在于作者尽可能详尽地勾勒西藏音乐文化全面的论述,但还是遗漏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文化现象,从全面性和整体性而言无疑是一个缺憾;同时,在书写规范方面,有些文献出处标明不够详细,书中几乎没有必要的注释,这也许是由于《藏音史》的撰写一开始就是以教材的需要而写作的缘故吧?
总之,更堆培杰的《藏音史》是一部了解西藏音乐文化的视窗,也是西藏音乐史学的一座丰碑,它让我们翱翔于横跨千年的西藏音乐史话中,期待《藏音史》在今后修订中更加详尽、丰富,至臻至美。
1.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2.更堆培杰著:《藏族音乐简史》,西藏大学藏文铅印版校内(藏文版)教材,2000年版。
3.更堆培杰著:《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更堆培杰著:《西藏音乐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杨明康著:《中国传统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6.杨民康著:《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次仁朗杰,西藏大学音乐学院讲师,博士。】
(责编:褚丽)
;J60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
; A<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
;ISSN1004-6860(2016)04-0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