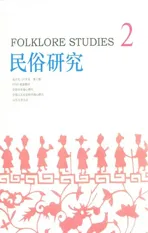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2016-02-03周大鸣
周大鸣 黄 锋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
——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周大鸣黄锋
摘要:以民俗活动“游神赛会”为切入点,对比凤凰村与周围4个村庄民间信仰活动的现状,厘清民间信仰活动在构建村庄内部认同与维持外部边界中的意义。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以游神赛会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填补了村庄集体行动的空缺,通过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表现对村落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游神赛会活动也体现了村庄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游神活动协调村落关系、构建村庄边界。
关键词:民间信仰;村庄边界;祭祀圈;游神赛会
一、研究缘起
华南研究经历了从“宗族范式”到“祭祀圈范式”的转换过程。祭祀圈范式是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组织的一种理论。①周大鸣:《祭祀圈理论与思考——关于中国乡村研究范式的讨论》,《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祭祀圈”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②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62期。,后众多华人学者将其应用到汉人社会的信仰体系研究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解释祭祀圈,通过主祭神与庙宇组织和宗教活动来分析地域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互关系、宗教活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整合之间的关系。其中王斯福避开了研究华南汉人乡村社会常用的“宗族范式”,讨论民间宗教组织如何将分散开来的个人组织在一起。王斯福认为,在古代中国,宗教活动通过隐喻式的模仿,将帝国运作的逻辑加诸民间信仰活动中,以获得民间的认可并发生变化。地域社会的“迎神赛会”实质上是一种对地域边界的巡查,以祈求这一地域的和平与安全。③[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73页。本文即将“游神赛会”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活动进行分析。④本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调查:笔者于1994-1996年在凤凰村调查,黄雪亮于2005年以凤凰村为调查点完成其硕士论文,2014年黄锋继续在凤凰村调查完成其硕士论文。
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具有其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与经济边界。⑤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9-40页。本文将位于广东潮州的凤凰村与其周围4个村落的“游神赛会”活动进行比较,讨论民间信仰活动与其社会边界之间的关系,即通过信仰活动表达出来的村落间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子。笔者认为,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
二、游神赛会与村庄关系
仪式在信仰活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众多人类学家对仪式过程进行过研究。特纳认为,仪式是指“人们在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页。涂尔干指出,“仪式是人们赖以与神圣事物发生联系的一组实践,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布朗通过对安达曼岛的调查,强调仪式在维持社会团结与凝聚方面的作用,他认为“仪式习俗是社会借以影响其个人成员,将某种情感体系在他们思想中保持活跃的手段。没有仪式,那些情感就不会存在;没有那些情感,社会组织就不能以其目前的形式存在。”*[英]拉德克里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马凌诺夫斯基从功能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仪式具有增强个人安全感以及凝聚社会群体的功能。”*[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3-81页。这些研究表明仪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心理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年节中或多或少包含着仪式,如游神赛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性的仪式展演。下文将以凤凰村以及周围4个村落的年节仪式“游神赛会”为切入点,分析仪式活动在凝聚群体、增强认同感方面的意义。
“狮峰的孥仔,神前的走仔,仙洋的猪仔,塘埔屎桶盖饭锅,潭头北风吹,溪口剥麻皮,沙洲(金舟村)吃沙粥……”。在凤凰村,这样的歌仔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仍然存在,只是已经无法很清晰地记录下来。*在潮州方言中,“孥仔”意为“孩子”,“走仔”意为“女儿”,“歌仔”意为民间歌谣。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村落之间表面看来相对独立,但相互间非常熟悉,能概括出对方的自然地理、人文区位特征。人们认为,狮峰村的孩子最坏,神前村的女儿最勤快,仙洋的猪仔没有圈养,因此比较野。塘埔村的农田离村庄非常远,所以村民早上出门耕种的时候要带上午饭,如果恰好需要施肥则只能把饭放在屎桶之上挑到田地里。潭头村的北风一吹,代表冬天到了,溪口村*本文采用溪口村的学名“凤凰村”。(凤凰村)种的麻就可以收了。同时,处在江中的金舟村就要尘土飞扬,稍不注意,碗中的白粥就变成沙粥了。这些歌仔反映了村落间彼此的印象和相互关系。
从更具体的方面看,则是游神赛会。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各村陆续恢复了正月里的游神赛会活动。村庄发展至今,虽有镇政府作为他们统一的上级领导,但由于村庄距离较远,加上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代表人为村民选举的村主任与村书记,因此国家对村庄的控制力比较有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大年初一,各村锣鼓队都要给镇政府拜年,目前只有位于镇区的归湖锣鼓队维持不变。其中的原因包括上级政府对安全的考虑、对民间祭祀活动的态度变化,以及各村的锣鼓队衰落等。2015春节的游神活动前夕,镇政府要求举办游神的村庄向派出所打报告,详细说明活动的时间、地点、规模、责任人,以及就安保问题与派出所协商,当天派出所会派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凤凰村也组织了12人的保安队协助维持秩序。
以往人们通过游神赛会表达了村落间的关系,在集体时代通过村际公共事务实现合作。现在只能通过保存其传统的要素——游神赛会表达村落间的关系。实际上游神是一种象征的秩序的表达,体现了村落间、姓氏间在政治、经济、婚姻、娱乐、信仰方面的联系,从其活动中也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乡土意识和姓氏合作。目前,游神活动在有些村庄已经消失,而在另外一些村庄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隆重。因此,从游神活动及其现阶段的发展可以窥视村庄内部各群体间的关系。
(一)凤凰村的游神赛会
凤凰村人口总数为1238人,常住人口700余人,有戴、林、黄、陈四姓,其中戴姓占多数。该村土地总面积289亩,实际人均耕地一分左右。凤凰村目前最值得村民称道的节日便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日的游神赛会,村中平时人比较少,甚至过年的时候也较少人回来,反而是“劳热”*“劳热”,潮州民俗庆典活动。(游神赛会)的时候在外工作的人纷纷返乡。村里的“老人组”*凤凰村“老人组”为村民自发成立的非正式组织。每年正月初一前后会将“题钱”*意为捐款拜神。告示贴在村口大路上,得知此消息的村民会前往老人组捐资拜神。老人组收款后开具收据,并以一对大桔相赠。如,陈XH是目前凤凰村仅有的1户陈姓人家,在村里还有老房子,但平时并不在村中居住。他在潮州市办工厂,每年村里游神赛会的时候都会“题钱”拜神,2015年春节他“题”了8000元,并且答应为凤凰村修建老人活动中心捐资20万元。此外,还有众多热心的村民积极踊跃参与捐资。此外,“老人组”还到镇上的电信局、水利所、超市等单位“拜年”,对方也要捐资拜神。
农历正月十一日晚,村民饭后开始在家里祭拜“天公”。人们已将村庙中的“老爷炉”“请”到祠堂里供村民祭拜。按就近原则,村民选择到祠堂或村庙祭拜“老爷”(即各神灵,主祭神是感天大帝)。晚八九点钟开始,祭拜的人陆续增加,村民按照次序排队拜神,晚上11点是高峰期。祭拜过程中,村里的鞭炮声一直持续到午夜。同时祖祠门口还搭建一个小型戏台做木偶戏,戏班来自汕头澄海区。
正月十二日清晨,祠堂门口旗杆夹悬挂两面“天地父母”黑底旗子。清早七点钟锣鼓队、仪仗队的孩子们来到祠堂门口集合,穿上定制的服装,如旗袍、马褂等,演奏笛子、唢呐、琵琶、二胡等乐器。这些孩子在寒暑假里由老人组组织培训。游神队伍由约100人组成,配备一支由12名本村人临时组建的保安队。其中抬神的主要是当年结婚的年轻男性,人数不够则由年长的人补上。村民津津乐道,去年抬神的人中一共生下了12个男童。锣鼓队大多是青少年,衙役则由小童扮演。游神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契机,通过该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播给下一代。
游神队伍中前排为8个灯笼,分别为“感天大帝,合社平安”(2个),“九牧世家”(林姓,2个),“乡贤世家”(戴姓,2个),“江夏世家”(黄姓,2个),分别代表村庙(福灵古庙),以及3个大姓的祠堂。两面大旗分别写有“潮安县归湖镇溪口村”“合境平安”,八面小旗分别写有“迎祥接福”“出入平安”“合乡平安”“一帆风顺”“同庆升平”“福星高照”“财通四海”“财星拱照”,扛旗者均为少女。2015年部分旗帜重新定制,一面旗造价约为1000元。
伴随着一阵阵鞭炮声,早晨八点游神队伍从戴氏祠堂出发,鞭炮开道,前往村庙将感天大帝、伯爷公、花公花妈、关帝等诸神“请”出。请出的诸神按照规定的路线分别到各个祠堂“巡视”,供人们祭拜。每到一处祠堂,房头的人出来迎接,将诸神安放好后人们纷纷上前祭拜上香。人们相信诸神可以保佑健康平安,并认为上香后摸一摸神像可以给来年带来好运,例如添丁。祭拜过程大约持续20分钟,期间锣鼓队在统一指挥下奏乐,敲响锣鼓,吹响唢呐。同时,人们认为在“老爷”路过时放鞭炮可以驱走邪恶,带来好运。因此在“老爷”路过沿街商铺时,主人纷纷将买好的鞭炮点燃,马路弥漫在一片鞭炮声中。“老爷”每隔一段距离便会“歇脚”,许多村民向队伍走去,将准备好的香火插到神像前,并给“老爷”挂上红包祈福。“老爷”脖子上满满一串红包犹如长须,村民也戏称挂红包是给老爷“捋须”。尽管林姓和戴姓曾经有过矛盾,但在游神之日,双方都抛去恩怨,一心为村落的安宁和子孙家族的平安祈福。游神结束后“老爷”被安放在戴氏祠堂中,待到元宵夜再将神像请出祖祠,按照规定好的路线送回福灵古庙,整个过程大约持续四个小时,至此游神活动结束。不仅在乡村地区,潮州市区的游神活动同样盛行。2014年2月24日潮州青龙庙会在市区进行盛大的游神仪式,13个锣鼓班,500多名年轻人一同抬神,多名海内外著名潮商赶赴现场观看。这些文化展演活动一来是弘扬传统文化之举,二来也极大地凝聚海内外潮人,增强族群意识,为共同建设家乡出力。
相比其他乡村,凤凰村在游神中是做得比较“好”的。从上世纪80年代陆续恢复游神赛包括会活动,整个镇从正月初一到十八每天都有游神活动。到了2014年全镇仅剩6个村仍然在进行,包括凤凰村、金光村、金舟村、石陂村以及远离镇区的仙洋村和神前村。正月十二凤凰村的游神活动自然吸引附近乡村的人们前来观看,尤其是有亲戚在凤凰村者多数到此“做客”。游神活动在村中受到重视,从平日的练习到组织族人捐款到当天的游神过程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历史上凤凰村和金光村的关系较好,据说解放前狮峰村和金光村闹矛盾打官司时,凤凰村曾出面帮助金光村。上世纪90年代在凤凰村老人组没有经费的时候,金光村老人组送去了3万元的资金赞助。现在金光村没有自己的锣鼓班,其游神也会请凤凰村的锣鼓队帮忙,并付给一定的报酬。与此不同的是,狮峰村和凤凰村解放前经常闹矛盾,打架斗殴非常多。凤凰村人对狮峰村人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们村里有“黑社会”,烂仔比较多。在清代两村曾经因为游神赛会中的冲突而发生过械斗,村民戴MY的爷爷的头颅被砍下,另外一位也成重伤。因为矛盾众多,两村之间极少通婚,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所缓解。
游神是村落之间、村民之间展开互动的契机。当天可以看到附近村的青年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四处游荡,返乡的人开着小车互相走访。这一天,主人要留在家里准备好午餐招待客人,亲戚好友应邀前来,以女方家的亲戚居多。通过游神赛会人们相互走访,增强彼此的联系。与夏天相比,正月十二日的凤凰村要热闹得多,在很大程度上这天村里比过年还要热闹,路上满是小汽车,村里熙熙攘攘。游神期间也是附近的青年人集会并发生冲突的高发时期,解放前有几次械斗都是发生在游神期间,近年来有所缓解,但摩擦仍然难以避免。
例如,2012年游神赛会期间,狮峰村几名青年男子在凤凰村戴氏祠堂门口开赌档,进行名为“鱼虾蟹”的赌博游戏。凤凰村的书记听闻后领着长辈去“清场”,不料这几名青年和他们起了冲突,他们首先动手打了村书记,引起众人围观,后逃走。事情过后不久,凤凰村人查出这几名青年是狮峰村人。他们事后知道当日打的是村书记,自知无法隐瞒。于是,这几名青年人通过其好友的妹妹——嫁到凤凰村的李姓妇女找到凤凰村的长辈,约定时间赔礼道歉。凤凰村人认为老人组和村书记是本村人的代表,他们动手打了书记等于是打了全村人,在村里游神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非常恶劣的。最终商议的结果是,这几名青年当众承认错误,并在戴氏祠堂门口下跪,向祖祠进献一对金花,买200元鞭炮到祠堂门口放,再向村里每户人送一对大桔。平日里仗着人多、地大,向来嚣张的狮峰村人这一次被狠狠地惩罚。人们表示,若不是他们有亲戚在凤凰村,惩罚还要更严厉,在过去要他们出钱请戏唱三天三夜才能解恨。
(二) 斑驳记忆——各村的“锣鼓日”
1.潭头村:消失的“游神”
潭头村位于凤凰村西北,自1997年后该村停止“游神”,该村是镇内两个贫困村之一,平时村中剩余的多为老人及孩子。户籍人口1080人,实际常住人口不及总人口一半。随着物价的上涨,村民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市场,仅靠务农难以支撑生活开支。一个五口之家能分到的田地仅有两亩左右,而务农只能提供稻米、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土地大量抛荒,村民只能将份田让给亲戚耕种。由于外出务工人数较多,经济条件差,难以筹集经费,加上难以组织村民学习锣鼓等游神必备的乐器等,目前该村无法组织起大型的游神活动。
潭头村主要有戴姓、林姓、吴姓、江姓、陈姓以及蔡姓。其中戴姓、江姓、陈姓和蔡姓信仰感天大帝,林姓和吴姓信仰三山国王。潭头戴姓是凤凰村戴姓之分支,目前约有20户戴姓人住在该村。潭头村戴姓、江姓、陈姓和蔡姓的游神日为每年农历正月初十。尽管目前村里已不再游神,但参与过的村民依然清晰记得游神路线图。
2.金舟村:“营锣鼓”取代“游神赛会”
金舟村地处凤凰村西南面,位于仙洲岛上,人口约700余人,土地面积相对较大。全村共有山林2500亩,耕地600余亩,其中水田500亩,旱园竹林数百亩。目前仍然种植水稻的人家极少,大多外出务工或在村内从事手工业。该村信仰玄天上帝,农历正月十三日是该村的“锣鼓日”,金舟村每年都请归湖镇的锣鼓队协助“营锣鼓”,但已没有游神活动。“营锣鼓”当天,该村大姓“李氏”将村庙(武当行台)中的老爷香炉“请”到李氏祠堂祭拜,小姓则将香火“请”回自家祠堂祭拜,更小的姓氏人家(没有祠堂的)直接到村庙中祭拜。其锣鼓队行走的路线以李姓和陈姓两个大姓为中心,没有涉及其他小姓祠堂。可见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地位,描画着大姓村民的认同边界。尽管目前没有了游神活动,但是村民对于此类大型集体活动依然十分支持,2014年游锣鼓活动中,金舟村共筹得捐款47386.92元。
3.狮峰村:“游神”引发的冲突
狮峰村位于凤凰村东北面,该村有耕地1562亩,户籍人口2627人。该村主要由蔡、李、吴三大姓,其中蔡姓、吴姓和李姓一个分支信仰“三山国王”,占人口较多的李姓信仰“玄天上帝”。农历正月初六是狮峰村的“老爷日”(游神赛会)。狮峰村创乡之初聚落分散,各个角落的人随意组织自己的游神活动。往往小姓在进行游神的时候常有“大姓”过来“闹”,秩序非常混乱。后来附近几个聚落的人统一起来,定下统一的日子进行游神活动。“文革”中游神活动中止,改革开放后曾举行过“游神赛会”,1993年最后一次游神后不再举行。目前在正月初六“游神日”当天,各祠堂长辈到古庙中给神灵上香,再将祭拜过的香火“请”回自己的祠堂中供人们祭拜,同宗人士当天也会返乡祭拜。
1993年正月初六,村中如往年一样举行“游神赛会”,按照前人定下的游神路线为:公厅(李氏总祠堂)——净湖古庙——岭前——下吴——蔡厝——顶吴——五家李——三家李——公厅(李氏总祠堂)。锣鼓队途经“刺蕴内”李氏祠堂时,按照原先的规划本不应在该祠堂停留。但是这房的李姓人从途中拦截,用大量烟花爆竹将游行队伍围住,不断放鞭炮使得游行队伍无法前行,双方僵持不下。经过商讨,当日的解决措施是,该房人将“老爷”香炉“请”进祠堂进行祭拜,锣鼓队的唢呐和锣鼓等在原地面朝该祠堂演奏。因此,本该下午三点结束的游神活动延迟了不少。这次游神后狮峰村再没有举办游神活动,原因是路线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此后,村里老人和领导等多次催促老人组组织游神活动,但是老人组表示路线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如果再进行同样可能遭到拦截。
人们认为狮峰村“游神赛会”中止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大量外流和村庄经济基础较弱,无法组织锣鼓队。因此各姓只能到村庙中将神灵请回自家祠堂进行祭拜。但游神的中止并不仅源自上述原因。更深层的是该村各房支、各姓氏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游神中的冲突实际上是内部冲突的外在表现。
4.龙溪村:一个村庄,四个游神日
龙溪村位于凤凰村南面,有刘、陈、王三姓,总人口564人,其中王姓约80人,陈姓约120人,其余为刘姓。陈姓来自凤凰村菜园尾;王姓来自金光村,与其王姓一同尊王大宝为始祖;刘姓于明弘治年间(1496年)迁自饶平,分为东厝与北厝两支。传说创乡的兄弟两人不和,各自的祠堂朝向不同方位,北厝为兄,东厝为弟。
村庙(龙溪古庙)属于刘姓,庙中供奉玄天上帝。王姓随金光村王姓,正月十八进行游神活动,陈姓随凤凰村正月十二进行游神活动。刘姓分北厝和东厝,农历正月初一东厝游神,初二北厝进行游神。因此,在龙溪村,春节期间一个村庄有四个“游神”日。
相传某一年凤凰村游神队伍不愿意到龙溪村陈姓祠堂。原因一是该村离镇政府太近,二是到龙溪村游神也会耽误许多时间。正当人们决定不去龙溪村时,队伍出发前的“掷杯”总是没有得到“胜杯”(掷出“胜杯”才是好兆头,没有得到意味着队伍不宜出发)。迫于无奈,人们才决定维持原路线到龙溪村去,这才有了“胜杯”。后来回忆起来,凤凰村人只能认为游神可能有利于两村的和睦,“乡里乡亲的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多走几步过去游神我们还是乐意做,为了和谐嘛”。从那年起,凤凰村每年的游神活动都会到龙溪村的陈姓祠堂去,以此表示各姓间的相互尊重与和睦相处。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游神的中止并不仅仅因为表面上客观存在的理由,若是仅看这些理由,凤凰村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好的,其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等远不及狮峰村,其村民收入远不及金舟村。在村委选举的时候狮峰村经常闹矛盾,而凤凰村的选举几乎毫无悬念总是戴姓人当选。凤凰村的游神赛会不仅没有中止,反而在强有力的组织下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为村民津津乐道,每逢游神总是吸引附近村的村民前来围观。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狮峰村人口众多,土地面积大,各方人口竞争激烈,纠纷不断,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同样的例子,金舟村的经济状况远胜于凤凰村,但是其游神活动也中止,仅有“营锣鼓”,且锣鼓队是从镇里借用的。因此,游神活动的进行与否与客观经济条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一百年前葛学溥*[美]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周大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调查的年代凤凰村作为一个贫穷的乡村,其游神活动照常进行。而到了百年后的今天,沧海桑田,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和经济社会变迁,其传统要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由此不得不思考其游神背后的逻辑,游神与否实际上表达的是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他们来说,返乡祭祖、拜神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归属感的获得,但不仅限于此。人们并不单纯从这些信仰活动中获得心理慰藉,或是求助、依赖神灵。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传统要素被加以改造并重新阐释,以建立村民的自我认同机制和排他机制。
三、结论与讨论
(一)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以山神作为社神是原始社会氏族宗教的重要特点,从调查中发现每个村都有其信仰的主神,主祭神甚至成为同一个村庄内部区分不同姓氏的标志。各村的神灵正是其神圣空间的象征,村庙成为透视神圣空间的主要载体。在普通人的意识中,村庙是村庄的象征,并且区分彼此之差异。村庙管辖的地界正是村民认同的社会边界,凤凰村的村庙辐射到龙溪村的陈姓,金光村的村庙辐射到龙溪村的王姓。村庄的认同边界与行政边界并不重合,甚至与行政边界相互冲突的情况也不鲜见。可见,以村庙神灵为载体的民间信仰活动实际上是划定认同边界的方式。另一方面,在村庄内部,主祭神灵的不同又再次区分不同的姓氏、房支。可见,神灵信仰不仅仅是村民精神的慰藉,还是建立自我认同,区分不同群体的重要象征。
(二)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既非有严格教义和组织的制度性宗教,同时它的内部又有明显的地域性,自然神、山神、英雄等都可以成为信仰的主体。村民通过庙祭、年度祭祀、节日庆典等活动表达对社区守护神灵的敬畏。对于本庙社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其他庙社的排斥,以庙社为中心的信仰活动不仅建立了村民认同的社会边界,而且构筑了内部认同机制。
明清时期官方的里社祭祀制度派生出里社组织,明中叶里社祭祀活动逐渐为迎神赛会所取代,里社演变为神庙。清中叶后,随着“分社”“分祭”的日益盛行,里社制度逐渐趋于家族化、社区化和社团化。*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5-353页。从里社制度的演变中可以看到国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往往需要借助民间信仰作为其文化机制,民间信仰“嵌入”到政治经济过程中以便获得实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通过对凤凰村和周围村庄的情况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各村的主祭神灵虽然不同,但角色一致,都是村庄的保护神,并且以姓氏为单位。在当前,民间信仰已不仅仅是社区中人们满足愿望的手段,仪式的复兴不仅满足了群众的心理需求,更是加强了村落之间的联系,成为维系认同的符号。
总之,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以游神为代表的祭祀活动填补了村庄集体行动的空缺,通过意义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表现对村落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游神活动体现了村庄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游神活动表达村庄的外部边界,协调村落关系。
[责任编辑 刁统菊]
Folk Belief and Village Boundary: A Study Centered on Fenghuang Village, Chaozhou, Guangdong Province
ZHOU Daming and HUANG Feng
This paper is a comparison of the folk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Fenghuang Village and other 4 nearby villages by taking the God Games as an example, to throw ligh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folk religion in constructing internal identity as well as outer boundary for a village. Folk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nternal identity, which makes sens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a village. Also,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oundary of a village. The otherwise vacancy of group activities has been filled by the folk religious activities during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dividual, families and villages are reunited by such folk religious activities at which expressions of care for the fortune of the village can be readily found. In add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can also find its expression at the games which is an opportunity to coordinate village relations and construct boundaries.
Key Words:folk religion; village boundaries; sacrificial offering circle; God Games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际潮学研究会第七届“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博士、硕士论文资助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黄锋,中山大学旅游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广东珠海 519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