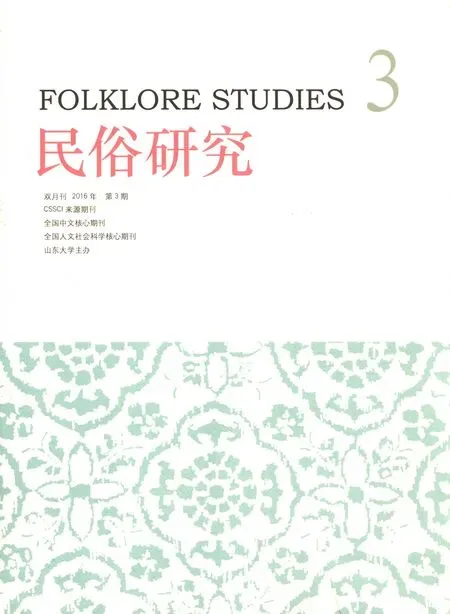西方传说学视野下的谣言研究
2016-02-02张静
张 静
西方传说学视野下的谣言研究
张静
摘要: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网络谣言的泛滥,中国学界对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展开了多学科的学术探究,其中既有社会学、传播学的视角,也有民俗学的视角。民俗学视角的最大特色,是将谣言的传播和变异视作一种人类固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民俗学界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关注谣言,将之视作传说,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取得了众多成果,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谣言的类型、语境、传播和变异展开研究,不仅推动了谣言的研究,也促进了传说学的发展。
关键词:谣言;流言;都市传说;传说学
一、谣言研究在民俗学领域的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研究逐渐兴起,既有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角度①王琼、刘建明:《谣言研究的方法论述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4期。,也有传播学、伦理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的方法。西方学界对谣言同样也是多角度切入的,民俗学家自1970年代起,已经将谣言纳入研究视野。民俗学家关注谣言文本本身,视其为人类生活、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为谣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西方民俗学对谣言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开始的民俗学转型。民俗学家们将目光由乡村转向城镇、由农业生活转向都市的工业化生活、由口头传统转向大众传媒,开始关注当代都市民俗。他们抛弃民俗是文化遗留物的观点,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当代,对“民”和“俗”,以及“民俗”重新进行定义,学术取向上由文学向人类学转向,在民间文学领域内主要表现在研究重心由文本转向过程(process)和语境(context),将更多的人群和体裁纳入研究领域,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对都市传说的关注。
具体到传说学领域,罗布特·乔治斯*Robert A. Georges,“The General Concept of Legend:Some Assumptions to be reexamined and Reassessed”, in Wayland D. Hand(eds.),AmericanFolkLegend:ASymposiu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1-20.、吉莲·本耐特*Gillian Bennett,“Are Legends Narratives?”,TalkingFolklore,no.6(1989),pp.1-13.、琳达·德格*Linda Dégh,LegendandBelief:DialecticsofaFolkloreGenr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pp.83-85.对统治民俗学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格林兄弟的传说定义提出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传说是不是故事或叙事,是不是被设定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是不是讲述者和听众都认为是真实的。在持续的讨论中,传说的定义也在不断发展,大体来说不再将是不是叙事或故事作为区分传说的根据,同时将定义的核心由“事实(truth)”转向“信仰(belief)”,因此原本因为没有完整叙事情节而不被纳入传说范畴的体裁,因与信仰密切相关而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如元传说(memorate)、谣言(rumor)、流言(gossip)、个人叙事(personal experience)等,这些体裁关注个体和当代,往往涉及某些社会问题,也是其他学科关注的对象。当时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作的吉莲·本耐特和保罗·史密斯自1982年开始举办都市传说研讨会,并于1988年成立了世界都市传说研究会(ISCLR,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Legend Research),协会杂志《都市传说》(Contemporary Legend)成为都市传说及相关体裁研究的平台*Carl Lindahl,“Series Editor’s Preface”,in Jillian Bennett and Paul Smith(eds.),ContemporaryLegend:AReader.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6,pp.xi-xviii.,聚集了来自众多学科的学者。
民俗学家原本往往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对叙事文本的内容、形式和结构进行研究,受到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影响之后引入了语境化 (contextualize)的方法,将文本与情境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欧美民俗学家将都市传说、谣言、流言等视为民间文学,并运用学科独有的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以下的研究成果:(一)从体裁学的角度进行界定,探讨谣言的特征和其他相关体裁的关系;(二)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包括文本、文学影视作品、相关民俗志资料;(三)运用一系列民俗学成熟的方法和理论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二、谣言作为民俗事象的文类属性
如果我们抛开对于谣言这一文类的价值评判,单从文本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那么,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都是当代的民间叙事,更准确的说,属于“传说”这一体裁。曾经担任美国民俗学会主席的布鲁范德在《北美民俗研究》中,将谣言(rumor)、流言(gossip)、都市传说(contemporary legend)、轶闻(anecdote)、个人叙事(personal experience)等都归入传说一类。由于谣言和传说在生产、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些社会谣言理论可以被运用于传说研究,反之,民间传说的研究方法也可应用于社会谣言的研究。这些体裁具有传说的共有规律:至少包含一个事件(event),内容上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形式上较为自由,有地方化和合理化的特征。*[美]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谣言与传说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布鲁范德在对谣言和传说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说:“传说、谣言、轶闻、都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据说发生了的、不寻常的、甚至奇异的事件有关。人们谈论叙述这些事件,解释这些莫辨真伪的奇闻异事,以通知和警示他人。其结构是松散的,每个版本的复述,都是讲述者利用传统因素再创造的故事。对于讲述者和听众而言,传说似乎是可信的,因为它们包含了两个‘现实的因素’:某一可证的事实与‘通常信以为真的错觉’。”*[美]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谣言和传说,往往都有“确认的惯用语”,如“这是我邻居的故事”“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他认识当事人”“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件事”,诸如此类,谣言和传说一样,都与即时新闻同属一类,因此在当代民俗中,大众传媒通常也会起到谣言(传说)媒介的作用。
盖尔·德·沃斯进一步梳理了都市传说、谣言和流言的定义、特征、分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从语言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界定。都市传说,“是在当代社会口耳相传,被当作事实讲述和展现的传统变异的故事。它们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内广泛流传”。流言,“是无意义的闲谈、没有根据的谣言、闲聊、有关个人或社会事件的难以控制的谈话或书写。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琐碎的。流言传达与人有关的信息,可以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意图”。谣言是“一般的谈话,传闻或道听途说。一般来说是简短的、揣摩的信息,缺乏明确的叙事元素。主要是涉及个人的事件,也可以涉及很有声望或很重要的地区或事件”。*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21.
谣言、流言与传说这三种体裁之间有相似性甚至重叠之处,都是人们用于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信息交换的工具。讲述者和读者可以借此搜集信息、表达观点、增加或者替换某些信息。沃斯归纳出三种体裁的相似性:运用明确的细节和对话加强可信性;包含非正常的经验或实践的内容;根据当代的情况发生变化,但是会从传统和流行的民间信仰中吸取素材;具有传递信息和探究缘由的功能。
不过,三者也能够从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加以区分。从文学的角度看,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完整的故事,有细节和戏剧化的行为。流言一般通过既有的交流渠道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内传播,谣言则创建自己的流通渠道和群体;流言反映了一个群体的道德规范,而谣言则表达了一个公共的道德规范,流言比谣言更为无意识或自发;流言是未经证实的有关个人的讯息,谣言是未经证实的有关某事的讯息。举个例子,“哦,另一个晚上,我老板从内曼·马库斯买了一个配方,他差点气爆了”,是流言;“内曼·马库斯一个烘烤配方要250刀”,则是谣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时很难将三者严格区分开来,而且讲述者本人并不会加以区分。*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p.21-25.
不仅如此,民俗学家用动态的眼光看待这些活跃在人们口头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学,关注它们自身的产生和消亡、发展和演变,关注它们随着时代、地点、语境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考察它们在民间文学传统中的生命史以及与传统的关系。在口头传统中,三种体裁共存,而且可相互转化。如果某一谣言或传言只是即时性的,或者出现了极端的地方化,有可能很快就会从口头传统中消失,不过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暂时的,当外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它们会再次活跃起来,从而在传统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Timothy R.Tangherlini,InterpretingLegend:DanishStorytellersandtheirRepertoires.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1994,p.17.
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谣言虽然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地域内流传,一旦具备了生长机制,如反映了某一公共的观念和兴趣,就会进入口头传统,彼此融合,成为传说。民俗学家对谣言和流言的研究及关注更多是为了考察传说这一体裁的起源和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真正能转化为传说的谣言和流言是非常有限的,只有那些带有某些能够固化为传说情节的主题才具备这种可能性。*Linda Dégh,LegendandBelief:DialecticsofaFolkloreGenr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84.而且关于同一内容的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往往是共存的,大众传媒则是谣言和流言转变为传说和其他文学体裁的温床。在1980年代,美国涌现了大量关于食品安全的传说,如麦当劳汉堡中的虫,肯德基里的油炸鼠、花生酱里的蜘蛛卵和可口可乐中的老鼠。在连锁快餐急剧发展的年代,类似的谣言大量涌现,通过口头和大众媒介等多种渠道流传。比如中餐馆的油炸鼠反映了对大众快餐或者异文化食物的担忧和恐惧、内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对女性走出家庭和远离家务劳动的惩罚。*Gary Alan Fine,“The Kentucky Fried Rat:Legends and Modern Society”,JournaloftheFolkloreInstitute,vol.17,no.2/3(May-December 1980),pp.222-243.在大众媒介这个温床上,简单陈述事件的谣言最终发展成了有固定情节的传说,并与口头流传的文本相互印证,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谣言、流言、都市传说和其他民间文学体裁,如歌谣、寓言、笑话、恐怖小说、神秘故事、闲谈、UFO传说,以及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内容、功能或者流传方式上存在相似性,某种程度上前者以后者的形式存在和流传。*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2006,pp.84-96.UFO传说的传播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星际迷航》《星球大战》《X档案》等科幻影视的影响。青少年对各类的神秘事物和人类所不了解的时空充满了好奇,受到影视作品影响后对这类事物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也产生了相关的谣言和传说,反过来又影响了通俗文化。
三、传统叙事母题在谣言研究中的运用
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传说就和谣言一样,反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各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动物伤人的传闻)、人与人的关系(如盗窃传说、社会治安事件)、人与物的关系(如关于新科技的谣言、食品安全的谣言),以及人与鬼神、信仰的关系(如邪灵传说、恐怖传说),涉及到了人们在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民众当代生活中普遍关切的问题,伴随着对未知事物的焦虑和恐惧。比如汽车传说的流行始于1930年代的欧洲,以汽车的广泛运用为背景;现代科技谣言的产生和流行是基于微波炉、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食品安全传说的产生是以食品工业的发展为背景的;邪灵传说随着西方社会信仰的削弱而兴起;谣言和传说中的受害者往往是女性,危险往往来自异文化,这反映了北美社会的性别和种族歧视。
布鲁范德认为,不管一个传言或故事听起来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奇异怪诞,但一经寻根究底,其真正的民间特质就会显露出来,与失踪的宝藏、地下的财富、预言、幽灵、罗宾汉式的江湖英雄等古老传说相似:“即使是‘消失的搭车客’这样的鬼故事,其发生背景也由19世纪的马车上转到了当今的汽车里,从而继续散发着故事的引人魅力。”*[美]布鲁范德:《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李杨、王珏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布鲁范德认为现代都市传闻具有与古老传说相似的传播形式,其叙事结构、内在逻辑,以及我们称之为‘母题’的这类传统核心因素仍然保持不变。但在这些现代都市传闻中,都市人的情绪已经逐渐丧失了那些积极向上的力量,剩下的只是焦灼与不安。都市传闻事实上已经成了人们排泄都市情绪的下水道。”*施爱东:《都市情绪的下水道》,《新世纪周刊》2007年第5期。
部分欧美民俗学者借助在高校教学的机会,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对当代流行的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搜集的范围涉及家人、邻里、朋友的口头讲述,以及报刊、杂志等书面材料,还有广播、新闻、电视等影视媒介。搜集往往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展开的,在材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俗学家会对较为流行的谣言、流言和传说进行分类。布鲁范德将都市传说分为六个类别:经典的汽车传说、“钩子”和其他少年恐怖传说、可怕的污染、尸盗、令人难堪的裸体、购物的噩梦。*[美]布鲁范德:《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李杨、王珏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沃斯借用了布鲁范德的分类并根据研究对象做了相应调整,分为七大类:科技产品传说、食品安全传说、盗窃传说、动物传说、对青少年的威胁的传说、邪灵传说、恐怖传说。*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这些谣言看起来虽然简短,却拥有丰富的种类和多样的组合。“传统的谣言形态结合当代社会生活,不断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新谣言。虽然谣言内容各不相同,但是,无论新谣言还是旧谣言,同类谣言的形态和结构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甚至还可能拥有相同的表述方式。”*施爱东:“谣言研究专栏”主持人语,《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人们花时间讲述和聆听传说,不仅仅是因为其奇异有趣的情节,更深层的原因是它传达了真实的、有价值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信息”,“都市传说与电视台等媒体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关注死亡、伤害、绑架、悲剧、丑闻等。”*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p.12-14.相比较而言,民俗学家关注的谣言和都市传说的范围更为广泛,涉及到了人类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社会影响面大,有的只在部分群体内流传,有的恐怖,有的幽默,有的训诫,有的只是娱乐,比如兑奖谣言(集齐某种物品可以参与兑换,如瓶盖、烟头等,最后发现是假的)。民俗学家将谣言和都市传说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作为认识人和社会的镜子与窗口,这种视角本身就是独特的。
四、谣言传播的渠道及语境研究
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其传播和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以传统的口耳相传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在当代社会更是借助大众传媒、通俗文化和科学技术大范围传播,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并产生与之相关的文本形式。举个例子,随着复印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复制大量的文字和图画信息变得简单、便捷和高效,由此产生了大量相关的民俗,较为流行的传说有:贴出爱犬走失的信息,并附上属于一个无辜者的手机号码,接着,这个无辜者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科技产品作为传播媒介影响了谣言、流言和传说的流传以及相应的叙事风格。通过科技产品讲述和传播不同于面对面的交流,比如通过电话讲述无法交流非语言的信息,复印机和电脑只能通过文字和图画的形式进行讲述。电话和传真的讲述形式中,讲述者和听者之间的渠道是明确的,但是电脑和网络则不同,讲述者要面对一批庞大、模糊、未知的接受者,这些都与传统的讲述形式存在很大差别。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甚至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渠道。互联网自媒体提供了大量可阅读的文本,大大扩充了讲述者和阅读者的搜寻范围,提供了新的双向交流渠道。此外,新的传播方式对传说的叙事结构和特征产生着重要影响,如以新闻为形式的谣言和传说是书面报道式的风格,以事件为中心而不是依照时间发展顺序组织讲述,因此依照事件的重要程度降序排列来进行报道或讲述;电视和广播通过图像或声音传播,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特定的观众群体。*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p.120-122.“中餐馆的猫肉”在北美和西欧广泛流传,1991年8月10日的《埃德蒙顿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安大略伯林顿当地的一个中餐馆已经承认他们出售猫肉——汉密尔顿虎猫。为了努力澄清这一谣言,中餐馆将邀请20位虎猫足球队的队员及其家人享受一顿大餐……”。这一新闻开头利用一则广为人知的谣言作为广告宣传的开头,其实也是流言传播的一种渠道和方式。
对讲述者、听众和语境及其表演的研究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听众参与到讲述过程当中,与讲述者互为补充,形成对话,由此可能会形成新的文本。讲述者的目的和看法会影响到文本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作为职业的故事讲述家,沃斯专门探讨了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的讲述艺术,除了文本上的技巧,如简明、停顿、作者特地的说明之外,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加深听众的印象,语言的组织、声音和腔调的变化、讲述场景的选择和氛围的营造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和技巧。在讲恐怖故事的时候为了达到最佳的讲述效果,讲述者往往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一般是漆黑的夜晚,在荒芜人烟的室外或野外;讲述的过程一般以气氛的烘托开始,然后讲述者和听众共同参与故事的创作,故事和对话交织,一个一个的故事接连讲述,由一个明确的结尾来结束。*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15,p.294,pp.308-310.野营、露营等户外集体活动是讲述这类故事的最佳语境,此时的青少年远离成年人和自己熟悉的生活,处在一种紧张、刺激同时又非常自由的一种环境中,具有特殊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
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本身就是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不仅仅作为文学的形式存在,也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欧美民俗学者研究较多的是传说的“操演(ostension)”、“伪操演(pseudo-ostension)”和“传说之旅(legend trip)”。“操演”是“人们按照民间叙事中的主题和时间行事”*Gary Fine,“Redemption rumors and the power of ostension”,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vol.104,No.412(Spring 1991),pp.179-181. Linda Degh,“Does the Word ‘Dog’ Bite? Ostensive Action: A Means of Legend Telling”,JournalofFolkloreResearch,vol.20,no.2(May 1983),p.7.,传说通过操演变为事实,并通过操演不断强化其可信性;“伪操演”则是“模仿已知叙事的基本情节使恶作剧延续”*Bill Ellis,“Death by folklore:Ostension, contemporary legend and murder”,WesternFolklore,vol.48,no.3(July 1989),P.204.,如年轻人假装杀人狂魔吓唬朋友,人们模仿献祭仪式等;“传说之旅”指的是有组织(有时是自发的)前往一个偏僻地区的旅行,用于测试面对超自然现象的勇气,主要是去墓地、地道、废弃的或传说中闹鬼的屋子、偏僻的小道和桥梁,最理想的环境是漆黑、多雾的夜晚,如月圆之夜的午夜,夏季和初秋,特别是万圣节前后。*Patricia M. Meley,“Adolescent legend trips as teenage cultural response:A study of the lore in context”,Children’sFolkloreReview,no.14(1991),pp.5-24.
年轻人中较为普遍的传说操演和伪操演有:学习巫术而杀死或虐待动物;放学后贪玩失踪,为逃避家长的惩罚而谎称被绑架;万圣节施虐,将大头针、刀片等危险物品或毒药等放入送给孩子的苹果或糖果中;针头事件,用针头扎人,往往造谣声称针头携带艾滋病毒。以上这些行为总是伴随着谣言和恐怖色彩,但是,有些伪操演行为则无伤大雅,如“病危孩子的愿望”这一谣言自1987年以来在美国和英国流行了数次,每次人们都热烈积极地响应,大体内容是一个病危的孩子希望能够收到更多的明信片,打破吉尼斯纪录,后来当地邮局收到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但是因为地址错误无法投递。*Anna Elizabeth Kearney Guigne,The“DyingChild’sWish”Complex:ACase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realityandTradition. M.A. thesis form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1993.
传说之旅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参与的人员讲述相关的传说,或者预先散布一种谣言,往往声称是个人的真实经历,烘托恐怖气氛;第二阶段发生在目的地,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参与者落荒而逃;第三阶段是回顾,参与者匆忙逃离,逐渐恢复平静后回顾发生的事情,完成一个叙事。这个叙事又成为这个传说之旅的一部分,它将会在下次行为中再次被讲述。传说之旅依据谣传中的恐惧对象,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类型:冤死或惨死的灵魂,他们无法安息,常常到他们死去的地方游荡,如鬼屋、废弃的居所、偏僻的桥头等;一般死者的灵魂,他们回来惩罚那些破坏他们的墓地的人;可怕的人或生物,如巫婆、狼人、僵尸、盗尸者等,或者是疯子,潜逃的精神病人。*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p.56-63.
传说的操演、伪操演和传说之旅都可视为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这些文学的转化形式,同时也是这些文学讲述、表演的重要语境,在实际的民俗生活中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行为具备特殊的功能,是了解超自然世界的重要渠道,通过超自然的惊吓来缓解压力,作为一种反抗成年人权威的仪式,当然也具有相当的娱乐功能。
五、谣言的类型与异文研究
虽然对谣言、流言是否为叙事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这并不妨碍西方民俗学家使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对谣言展开研究。民俗学家在广泛搜集文本、科学整理的基础上,从主题、类型等角度对它们进行分类,并且运用诸如母题和情节的考察,文本生命史的追溯,类型和亚型的分类与解析等方法对其展开研究。
布鲁范德介绍的谣言或者说都市传说类型计有31个,沃斯提到的则有大约有80个,法国民俗学者维若妮卡·坎皮侬·文森在她的《都市传奇》中则详细地分析了37个广泛流传在欧洲的奇闻轶事,其中为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有《都市下水道里的鳄鱼》《拦路搭便车的鬼魂》《病危孩童的感人故事》《被偷走的祖母》《电焊工人的隐形眼镜》《被微波炉烤熟的小猫》《消失在试衣间的年轻女子》等。*[法]维若妮卡·坎皮农·文森、[法]尚布鲁诺·荷纳:《都市传奇》,杨子葆译,麦田出版,2003 年。
这些谣言或传说多以当代都市生活为背景,经过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流传,具有了较为稳定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其中,《消失的搭车客》是欧美最为流行的都市传说。现有资料显示,在北美,有夏威夷、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纳瓦霍印第安人的异文;在欧洲,有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异文;在亚洲,有以色列、日本和蒙古异文;在非洲,有南非的异文。这些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都市谣言,全面展现了这一全世界最为流行的都市传说的基本面貌。通过比较文本,同一传说的众多异文可以划分为几个有限的亚型,如《男友之死》有美洲和欧洲两大亚型,故事基干类似:一对男女的车子没油或出故障停在一个荒凉或僻静地方,男子下车寻求帮助,一去不返。女子留在车内,被奇怪的声响惊吓,第二天早上,车子被警察包围,才发现男子被人杀死,吊在车子的上方。两个亚型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美洲亚型中男女是夫妻或情侣,欧洲亚型中两者则没有明确关系;离开车子的原因一个是停在偏僻地方,一个则是没油了;美洲亚型中男子被吊死在树上,欧洲亚型中男子则被砍头。这些差异性源于文化的差异,如在美洲对人处以私刑非常普遍,但是在欧洲用刀杀人则比较常见。*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p.332-357.Mark Glaze,“The cultural adaption of a rumor legend:‘The boyfriend’s death’ in South Texas”,in Gillian Bennett,Paul Smith,and J.D.A.Widdowson. Sheffield(eds.),Perspectivesoncontemporarylegends. Englan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87,pp.93-108.
某些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往往既是大范围甚至是全球流传的,同时也具有地方性,与某一个特定的环境融合。某一类型的传说流传到一个区域,往往会实现地方化,与其他地方流传的类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美国流行一些有关种族隔离的谣言和都市传说,流传到了具有类似问题的南非,生根发芽。其中一则在南非白人中普遍流传,内容是:在某一个特定日期,黑人会武装起来反抗白人,行为包括杀死遇到的白人,给自己的白人雇主下毒,侵犯白人妇女,接下来甚至焚烧白人儿童的学校,抢劫白人店铺等。这一谣言在1961年南非警察杀害黑人的沙佩维尔惨案*1950年代末期,南非国内黑人反抗斗争高涨,杀死警察的事件时有发生。1960年3月21日,在沙佩维尔,一万多群众围住警察局,参与“反通行证法”运动。政府派军队动用催泪瓦斯、飞机均未能驱散人群,最后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此后白人当局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大肆搜捕,颁布《非法组织法令》,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1976年,联合国将3月21日定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之后首次出现,之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对南非白人和黑人的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谣言在美国则是说在特定日子,一伙英国黑帮将会在对手的学校展开撒旦的复仇。*Gary Alan Fine,“Rumors of Apartheid: The Ecotypificaiton of Contemporary Legend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JournalofFolkloreResearch,vol.29,no.1(January-April 1992),pp.53-71.同一谣言流传到南非之后,与当地的社会、历史、政治环境,特别是种族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在适宜的土壤很容易生根发芽,特别在流传渠道如此多源和高效的当代社会,因此同一谣言、传说会大范围流传,形成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文本,进而成为固定的某一亚型。
无论谣言、流言还是都市传说,它们都拥有一些固定的情节和母题,很多来自传统的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比如有关蜘蛛、蛇和短吻鳄相关的谣言和都市传说。在基督教文化中,蜘蛛吸食人血,蛇往往被视为恶魔撒旦的化身,短吻鳄则被视为龙的替身,它们都是邪恶的表现。因此,在当代美国社会的民间文学中,这三种动物仍然是恶的代表,代表那些未知的邪恶力量,给人们带来致命的伤害。当代流传的这些谣言、流言和传说不完全是当代的,它们与既有文学传统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下水道中的短吻鳄与欧洲民间文学题材“洞中的龙”非常类似,这类谣言和传说与民间故事中的“屠龙故事”存在联系。还有“窒息的杜宾犬”,故事大意是主人回家发现自己的杜宾犬被噎住了,赶紧送往诊所,后来发现家里原来有贼,杜宾犬咬掉了贼的手指所以被噎住了。这类传说明显与传统民间文学中的忠犬护主故事存在渊源关系。*Gail de Vos,Tales,RumorsandGossip:ExploringContemporaryFolkLiteratureinGrades7-12.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2006,pp.208-211.
六、小结:谣言研究是民俗学介入当代社会的一个入口
西方民俗学家的谣言研究不仅仅是多学科参与的谣言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从民俗学的学科发展来说,这些谣言研究有重要的贡献:一是拓宽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二是借鉴学习了其他学科的方法,三是推动了与其密切相关的传说学研究。从传说学发展角度来说,谣言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将传说作为动态(dynamics)和过程(process),关注传说与信仰、人、社会和生活的紧密联系;二是关注语境,除关注传说本身的含义外,更要借此认识个人、社区和社会;三是表演的研究,包括讲述者、讲述方式、风格、心理研究等;四是传说的类型研究;五是传说的体裁研究,特别是有关文本的内部研究,如形式和结构的探讨。当然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如研究范围的界限不能无限扩大,在研究中不能忽视传说的叙事特征。谣言研究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块试验田,同时也是民俗学介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切入口。
[责任编辑龙圣]
作者简介:张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湖北武汉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