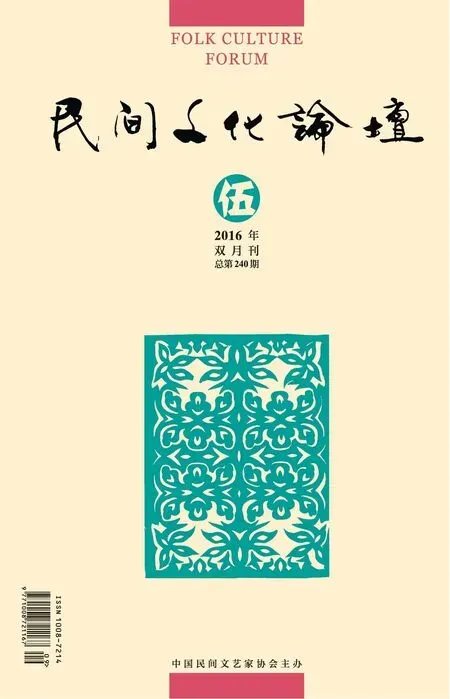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
2016-02-02程正民
程正民
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
程正民
照我理解,跨文化就是文化的对话,跨文化研究就是文化对话的研究。在这方面,巴赫金关于文化对话性的思想(文化的整体性和多元性、文化的主体性、文化的互动性、文化的边缘性和开放性、文化的创新性),关于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思想(理解、外位性),为我们开展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认真加以梳理和研究。
一
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研究涉及哲学、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符号学和文艺学、美学多个领域,具有丰富的多面性和很强的原创性,对20世纪思想文化界有巨大的震撼力。
我国对巴赫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开始是关注他的复调理论,继而关注他的狂欢化理论,最后才抓住对话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才逐渐体悟到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的背后和深处是巴赫金毕生追求并为之付出重大代价的对话精神、对话理论,认识到不理解对话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复调和狂欢。对话精神正是巴赫金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根基,是巴赫金思想最有魅力和最具震撼力的精华所在。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对话,文化的本质也是对话。
生活的本质是对话。他指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的,包括眼睛、嘴巴、双手、心灵、整个躯体、行为。他以整个身心投入话语之中,这个对话则进到人类生活的对话网络里,参与到国际的研讨中。”①[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在另一处他又谈,“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②[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8页。,“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③[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巴赫金关于生活的本质的思想是他对人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理解,是他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独
思想的本质是对话。他指出,“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把思想看作是不同意识不同声音间演出的生动条件,这样来进行观察和艺术描绘。思想、意识、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因而是与思想多少有些关联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这一艺术发现使他成为伟大的思想艺术家)”①[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为什么说思想的本质是对话?巴赫金认为思想不是主观的个人心理的产物,不是生活在个人意识之中,思想的真正生存领域是在同别人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的关系之中,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种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获得活力,才能不断生成和发展。思想如果只生活在个人的意识之中,拒绝同别人对话,把自己凝固起来,把自己树为绝对的权威,那么这种思想肯定会走向僵化,甚至走向死亡。
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巴赫金把对话思想运用到语言领域,对语言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既批判以洪堡为代表的把语言局限于个人心理范畴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语言学,也批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把语言看成是稳定不变的体系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他强调语言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社会性,认为语言属于社会活动,话语是双方的行为,它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谁说的,二是对谁说的。他明确指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艺术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②[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对话。巴赫金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提出审美活动是一种审美事件,它由作者和主人公构成,两者在审美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它们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实际上审美事件的构成除了作者和主人公,还应当包括读者,审美事件是作者、主人公和读者的对话关系。所谓审美事件所体现的对话,按巴赫金的意见,又可以有三种对话关系:作家同前辈作家的对话;作家与同时代接受者的对话;作家同后代的对话。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具有潜在的思想艺术价值的,它要“生活在长远的时间里”,真正比在自己的时代更活跃更充实。
当然,巴赫金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对话,他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整体,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文化的互动和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有成效的生活是在文化的交界处和边缘;文化对话的目的是文化的创新。
不论是哪个领域,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强调的是主体性(对话的双方都是独立的,都有自己的价值)、对话性(对话是主体展现的形式,对话的双方是互动的,是相互交锋、相互作用的)、未完成性(存在就意味着对话,对话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
为了深刻理解巴赫金的对话思想,还需要深入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了解其历史针对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实证主义在哲学中的蔓延和科技发展中机械论的影响,不少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都为哲学中失去人,美学中排除伦理、价值要求感到担忧。巴赫金正是在这时开始对人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同时,巴赫金的对话也是针对他所生存年代俄罗斯现存制度对人的压制。从他的学术著作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人与人平等关系的追求,一种对专制的无声抗议和深沉的人文关怀。
二
巴赫金把他的对话理论运用于文化领域,对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对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文化的主体性、文化的互动性、文化的开放性和边缘性以及文化的创新性,都做了深刻的、独特的、富有创新性的阐释。巴赫金文化对话性思想是独树一帜的,是20世纪文化理论重大发展,它对于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
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巴赫金在谈到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来研究文学,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他明确指出,“不把文学同文化隔离开来,而是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①[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在这里,巴赫金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区分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既是一个统一的也是多元、多样的,既是完整的也是可以分割的,它是又合又分的。只讲多元、分割,不讲统一、整体,只讲统一、整体,不讲多元、分割,都是片面的。如何辩证地认识和对待这种辩证关系,是巴赫金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巴赫金首先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是多元的。例如在中世纪有上层文化,有下层文化,有宣扬禁欲主义,宣扬世俗生活的罪恶,妄图使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的教会和官方文化,也有反对禁欲主义、反对等级制度、主张自由平等的民间文化。而不同文化的存在归根到底又是由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条件决定的。他深刻指出,正是中世纪两种生活存在产生了中世纪两种思维体系和两种文化。官方和教会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和交际形式,他们的宗教仪式,决定了官方文化冰冷僵化的严肃性;而民众广场和狂欢节中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决定了民间文化自由平等的精神和充满更新的创造精神,决定了民间文化自由、欢乐的音调。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在谈到一个时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时,也指出一个时代的各种文化所占有地位及其价值也是不同的。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多元文化中,他特别看重民间文化的地位和影响,高度重视民间文化给文学带来的重大的和深刻的影响。他说,不了解民间诙谐文化就无法理解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不了解民间狂欢文化就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到了晚年,巴赫金更是大声疾呼要人们重视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文化潮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他认为不能把一个时代的文学过程仅仅归结为文学诸流派的表面斗争,仅仅归结为报刊的喧闹,而要去揭示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只有如此,才能“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②[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
一个时代的文化不仅是有区分的,是多样多元的,而且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整体。一个时代文化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各种文化的相互联系,各种文化都有统一的时代精神和特色,往往又体现出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例,它虽然遍及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同时在多个国家中又分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但它们都体现了文艺复兴文化统一的精神风貌,统一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和反对神权的人文精神。在19世纪俄罗斯的众多作家、艺术家身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反农奴制的人道精神,感受到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在唐代文化中,也体现一种统一的“盛唐气象”,一种开阔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度,一种进取、昂扬的精神。
更难得、更重要的是巴赫金还特别关注一个时代文化整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多元性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文化研究中先是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忽视多样性、多元性,后来又是只强调多样性、多元性,又忽视整体性、统一性。实际上,任何具体文化领域都需要从文化整体性的联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显示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就文学研究而言,原苏联过去的庸俗社会等只强调文学同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忽视文学的特性,后来纠正这一弊端后又走过另一极端,是过分强调文学特性,而忽视文学同文化整体的关系,缺乏广阔的文化视野。对此,巴赫金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他主张“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①[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说到底,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精义就在于此。
文化的互动性。巴赫金所说的文化对话性主要表现在文化的互动性和开放性,这里先讲文化的互动性。它包括三个主要思想:文化互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文化互动不仅是内容层面,也是形式层面的;文化互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在研究文化互动、文化对话时,巴赫金特别关注民间文化、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往我们更多研究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巴赫金认为这种影响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民间文化为文人文化提供养分,反过来文人文化对整个民族文化,其中包括民间文化也是一个大的提升。他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同正宗文化的关系深刻证明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整整一千年积淀起来的非官方的民间诙谐文化、狂欢文化闯入了正宗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并使之充满创造力,这种作用表现在狂欢化文化对狂欢体裁形成的作用,更主要的表现在民间狂欢文化所形成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自由平等的精神、交替更新的创造精神)对文艺复兴世界观的影响。正如巴赫金所说的,“在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基础上,还逐渐形成各种复杂形式的文艺复兴世界观,透过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一时代人道主义者所理解的古希腊罗马文化。”②[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这里所指的民间狂欢式世界感受对文艺复兴世界观的影响,对文艺复兴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在于“使人回到人自身”,在于对人的尊重,在于弘扬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反过来讲,在巴赫金看来,千年积淀起来的民间文化、民间诙谐文化也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影响,本身也得到提升,也产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巴赫金认为表现在“它的全民、激进性、自由不羁、清醒和物质性已从自身近乎自发的存在阶段,转向艺术自觉和坚定性的阶段,换言之,中世纪的诙谐在其发展的文艺复兴阶段已成为新的时代的自由的、批判的历史意识的表现”①[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4—85页。,这里说的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化在文艺复兴先进人文思想光照下,逐渐由感性的自发状态上升为自觉的状态,并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表现形式。
巴赫金关于上下层文化互动的思想,应当说是揭示了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和重要规律。多种文化的互动,在我国多个时期文化和文学发展中都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我们看到了民间故事、民间说书对文学经典《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形成的作用,也可以看到这些文学经典走进民间,对整个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提升作用。谈到“五四”时期,钟敬文先生认为,“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它打击得更严厉的是上层文化。它对民族的通俗文化和下层文化,却是保护和提倡的。在他看来,“五四”时期对中层(市民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提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起促进作用的,其中包括提倡白话文;赞扬口承文学,创办《歌谣》周刊;提高俗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的地位;进行作为民族文化的民间风俗风尚的勘察等。他认为这些活动所提倡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同“五四”新文化活动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民间文化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支持一样,当年弘扬传统的中、下层文化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支持。
从巴赫金到钟敬文,他们关于文化转型期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互动的思想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面临文化转型,当代文化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有主流文化有非主流文化,有精英文化有大众文化,有雅文化有俗文化,多种文化如何在互动中发展,上层文化如何从下层文化中吸收营养,下层文化如何在上层文化影响下得到提升、特别是新文化的形成如何得到下层文化的激活和支持,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论述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文化的开放性。巴赫金在解释一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互动关系之时,特别指出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统一体。从共时的角度看,要在同别人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显示出自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双方的文化都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历时的角度看,要把文化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放在“长远时间”里,在同未来时代的对话中,揭示其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巴赫金所说的文化开放性有宏大的视野,既有横向的开放,又有纵向的开放,既指向当代,也指向未来。从历时的角度看,巴赫金提出把文化放在长远的时间里,向多个时代开放,在开放和对话中,不断揭示其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巴赫金说:“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在世世代代之中,既生活在长远的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作品则永远是)比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②[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5页。这就是说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化仿佛超越自己的时代,在自己身后的生存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意义。我们经常所说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关于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生命力和潜能问题,巴赫金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开放和文化对话来加以理解的。在他看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存在一种对话关系,都要同不同时代开放和对话,要同前代对话,同本世代对话,同时同后代对话。能够活在长久的时间里。除了它有现实的内容,还在于它有潜在的内容。前者是已经被同时代人理解和关注的内容,后者是潜藏其中后来被同时代人揭示的内容,它要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被激活,不断被揭示。
文化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主体性是文化对话的前提问题和立场问题。所谓前提就是必须承认文化对话是两个主体而不是只有一个主体,对话双方的文化都是平等的,都是有其价值的,都应当受到尊重。所谓立场就是在文化对话中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自己的主体立场。巴赫金认为,以往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中,存在一种片面的、也是错误的观念,就是为了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当融于其中。他指出,“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要忘记任何东西。”①[俄]巴赫金(М.М.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
在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在同外国文化交流中就是缺乏对话精神、缺乏主体性。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我们向原苏联“一边倒”,文化上也是倡导以其为师,在文化学术领域,在文学艺术领域,完全照搬原苏联的一套,缺乏自己独立的看法,缺乏主体意识,根本谈不上文化对话,也就不可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向西方文化开放,引进了西方有价值的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但也存在硬搬硬套,缺乏分析和辨别,缺乏与其展开对话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老一辈学者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坚持文化主体性问题上,钟敬文先生同巴赫金完全一致。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中,他多次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主体性,指出中国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别人学术的附庸。②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要在对话中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要在资料的掌握和深入研究方面下大功夫。文化对话、文化交流不等于介绍对方的文化,而是要有自己独立见解。真正的中国声音应当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自己独特的见解。钟敬文先生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民俗学家,他在狂欢文化研究问题上,并没有简单搬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而是在巴赫金的启发下,结合中国狂欢文化的实际,做出自己独特的阐释和理论概括,如他发表的论文《略谈巴赫金文学狂欢化思想》③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2—158页。。他晚年明确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国学派的旗帜就是学术自觉的旗帜,学术独立的旗帜,学术创新的旗帜,这也是跨文化对话的真正旨归。
[责任编辑:冯 莉]
G122
A
1008-7214(2016)05-0020-06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的存在,都有独立的价值,人的存在和差异应当受到尊重和关怀,有了这个前提才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