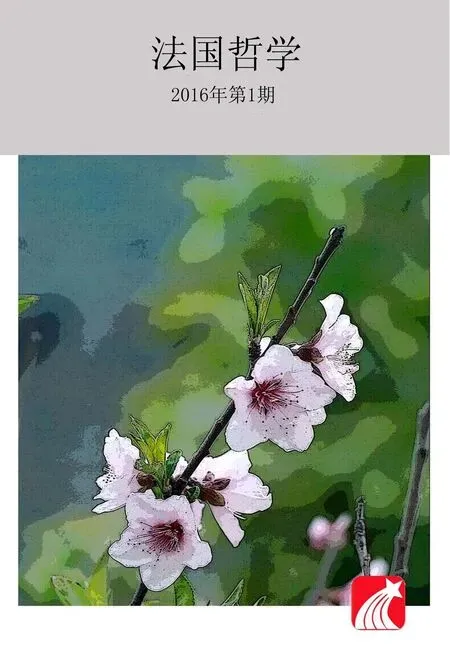“我思”之“我”何以可能?—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自我”概念
2016-02-01胡成恩
胡成恩
(温州医科大学社科部)
“我思”之“我”何以可能?—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自我”概念
胡成恩
(温州医科大学社科部)
笛卡尔经过“普遍怀疑”将整个世界,包括自己的身体,还原到作为纯粹理性的“我思”,并以此作为整个世界的源点,从这一点再回头来看(思)世界与自身,则万物莫不是“我”的“表象”,“我”成了万物的“镜子”。但这个“我”是“谁”?本质为何?从何而来?笛卡尔似乎并不能为之提供有效的证明和保证。无论其著名的循环论证是出于“高贵的谎言”还是“知性真诚”下“求证的失败”,从“我思”到“我在”都只能被看作是在形而上学奠基处对本体性意义上的裂隙及其不确定性的“信仰式跳跃”,它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行为”①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解读培根、笛卡尔与尼采》,李致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而在本文讨论的主题—精神分析这里,拉康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对这个一直被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当作基础的自明、自足、同一的“自我”作了更彻底地还原。在拉康的理论中,这个作为世界之“镜”的“我”也是“镜子”映像的产物,因为世界也是他的镜子,他是从这镜子中认出自己而进入世界的。
在名为《镜像阶段: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的文章中,拉康一开始就言明,通过对“自我”的还原及其构型中存在的误认、异化的揭示,精神分析可以反对“任何直接源自‘我思’的哲学”①Jacques Lacan,Écrits,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93.中译本参见拉康:《镜像阶段: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载吴琼:《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本文相关引用参考了这一译文。。在拉康看来,笛卡尔之后西方有关自我的现代观念就体现为“主体=自我=意识”的对等式②狄伦·伊凡斯:《拉康精神分析词汇》,刘纪蕙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年版,第42页。,而他有关“自我”构型的理论不仅将“自我”同“主体”区别开来,而且最终为认识本质上分裂的“主体”之真相奠定了理论基础。这里所谓的构型理论,就是将“自我”还原为一个从人类个体“更源初的混沌状态”,经过“想象性自恋认同/误认”而异化、绽出(ek-sistence)③“绽出”(ek-sistence),也被译作“外—在”,拉康经常使用海德格尔的这一概念,在对自我的还原和解构中,我们能从中看出海德格尔对拉康的影响。参见Jacques Lacan,Écrits,p.629, 654;亦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二十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才得以形成的东西。因而,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中,一直被当作“知觉—意识”核心的“自我”是“被构成的”,而不是“构成性的”,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想象性的功能”和“结构化的产物”。本文认为,拉康这一理论可看作是从精神分析的视角为“我思”之“我”何以可能的问题所提供的一种回答。
一、欠缺:“我”来自何处?
在以“冲动和自恋理论”从第一心理地形学向第二心理地形学过渡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自我”何以可能的问题,但他并未提供自己的解答。弗洛伊德在写于1914年的《论自恋·导论》一文中这样说道,“与自我(Ich)相提并论的整体性(unity),不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于个体之中,这是因为自我需要发展”①弗洛伊德:《论自恋:导论》,宋广文译,载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3),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拉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将其当作早期理论思考的重要问题,并最终通过对各种相关理论的参考②肖恩·霍默(Sean Homer):《导读拉康》,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结合自己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分析经验,于1936年提出了镜像阶段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答。那么,精神分析所理解的“自我”构型之前的人类个体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呢?自我以何种方式从这种状态中得以构型呢?拉康在《镜像阶段: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一文中说,他所赋予这一阶段的意义“揭开了迄今仍有疑问的力比多机制以及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的秘密”③Jacques Lacan,Écrits,p.94.。我们不妨从“力比多机制”和“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讨论。
根据精神分析有关前镜像期的各种经验总结和分析描述,作者将这一阶段总结为一个概念:“欠缺”(Le manque)。在前镜像期,它表现为“存在性欠缺”(Le manqué de l’être)和“秩序性欠缺”,前者对应“力比多机制”,后者对应“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
何谓“存在性欠缺”?它为何与力比多有关?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简要说明精神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即冲动(Trieb,又译作驱力)。冲动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区别于动物性本能的一种人类特质④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它处在心理与生理的边界上⑤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宋广文译,载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3),第27页(译文有改动)。,力比多是对其能量的量化概念,它指称人类身上存在的一种恒定量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175页。亦参见Jacques Lacan,“Du《Trieb》 de Freud et du désir du psychanalyste”,in Jacques Lacan,Écrits, p.852。。在解释其冲动理论为何不是“泛性论”的时候,弗洛伊德曾将这一“冲动”类比为柏拉图意义上的“爱欲”(Eros)。⑦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第8页。不过这个爱欲是《会饮》中诗人阿里斯托芬口中的爱欲:人在经历神对自身的原初切分而丧失完整性之时,爱欲以对这种完整性的“欠缺”体验进入生命,此后,人终其一生都为此“爱欲”所驱动,为恢复完满的自然状态去寻找他丧失的另一半。①柏拉图:《会饮》,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当然,弗洛伊德并不会相信“冲动”是由神对人的切分而产生的,但他确实将这个以“欠缺”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的爱欲,当成了其性学理论的基石,而对于人为何会具有这种爱欲冲动,弗洛伊德坦承无法回答②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173页。。
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拉康对冲动作了更深入的抽象和还原,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还原和抽象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巨大影响。同样借助于阿里斯托芬的寓言,拉康将“冲动”理解为人必然要经受某种“永生丧失”的产物③Jacques Lacan,Écrits,p.845.,这一“丧失”以“欠缺”的形式成为生命中一个“无身体的器官”。④Jacques Lacan,Le Séminaire de Jacques Lacan,Texte établi Par Jacques-Alain Miller, LivreⅪ,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64,Éditions du Seuil, 1973, p.179.在拉康的解释中,这种“永生丧失”是人作为有性繁殖的生物在其性化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丧失,它是人进入“实存”状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注定了人必死的宿命,而人对此种“永生丧失”的否认,对完满无欠缺状态的向往和追求则构成了人类一切乡愁的原型。⑤Jacques Lacan,Les complexes familiaux dans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 Autre écrits,Éditions du Seuil,2001, p.36.因而,拉康说,这种欠缺,不是缺这个或那个,而是一种本质性欠缺,拉康称其为“存在性欠缺”。⑥Jac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Ⅱ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translated by Sylvana Tomaselli, W.W.Norton & Company,1988, p.223.经过这种处理,冲动在拉康那里成了以“欠缺”的形式起着动力源泉作用的核心装置。拉康说,“存在(l’être/being)进入实存 (l’exsistence)正是以这种欠缺所具有的精确功能来实现的”⑦Ibid., p.224.,而冲动发现的每一个客体和对这种欠缺的每一次填补,都同时意味着对存在本身的遮蔽和对此欠缺的缝合。这就是“存在性欠缺”的基本内涵,因此它关系到力比多机制和弗洛伊德所说的冲动及其力比多的不同变化阶段。
“秩序性欠缺”则是人类特殊的早产所带来的结果。人是天生的早产儿,若无大人的长久照看,必定夭折。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尚未发育成熟。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他尚未进入“世界”之中,这种进入不是出生意义上的来到世间,而是只有当他能将自身同世界区别开来,世界也能“在他之中”的时候,他才作为一个“个别化”的个体而“在世界之中”。因而,对于海德格尔“在世之中”的概念,精神分析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拉康和齐泽克看来,人并非“总已”在世界之中,而且“在世之中”本身就是一种“被迫选择”(vel)的结果,这种“被迫选择”也就是拉康的“异化”概念。①Jacques Lacan,Le Séminaire de Jacques Lacan,Texte établi Par Jacques-Alain Miller, LivreⅪ,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64,p.192.对此,齐泽克说道,“与海德格尔相反,拉康则坚持认为,我们的‘在世之中’已是某种原始选择的结果:精神病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即不选择世界是完全可能的,一个精神病的主体并不在‘世界之中’,他缺乏向世界敞开的‘澄明’(Lichtung)”②Slavoj Žižek,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Verso, London, New York, 1994, p.184-185.熊伟先生将Lichtung翻译为“澄明”,也有译作“林间空地”和“疏敞地”的。关于海德格尔对Lichtung的论述,参见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 、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8页以下。。因而,前镜像期在秩序性方面的欠缺也就意味着在自我构型之前,个体尚处在混乱无序的混沌状态③Jacques Lacan,Écrits,p.96.,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身心关系”方面,新生儿欠缺能够自控的运动机能,需要大人长久的照料和哺育,而神经系统的不成熟则使其欠缺对自身身体的完整感受和把握,他对身体的感知基本上处在一种局部化的、碎片化的状态。④Ibid., p.97.这种状态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感性杂多”,个体尚无力完成对“杂多”的“联接”以获得对自身的“统觉”。其次,在“内外关系”上,新生儿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也无法将自身与外部的环境区别开来,所以,在内在世界(Innenwelt)与外在世界(Umwelt)之间,他既无法区分,也就无法建立联系。最后,在这种个体与世界混沌无序或说浑然一体的状态中,也就谈不上对“我他关系”和“时空秩序”的意识与把握了。不难看出,这种状态的诸多特点非常类似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本我”状态①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弗洛伊德曾对本我的状态作过总结,我曾在博士论文中将其归纳为六个特征:无组织性、无逻辑性、无时间性、无价值观、无生死观,以及是冲动的领域。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7—58页。。
从以上描述来看,处在“混乱聚集”(chaotic aggregate)的无序状态中,无论是力比多机制还是个体意义上本体论世界的结构,都仍处在类似于“世界之夜”的状态。②齐泽克曾将这种状态类比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之夜”,并将这一状态中个体的破碎感知发展为“前综合的想象力”(pre-synthetic imagination)概念,并以此概念来反对康德以及现象学中“先验想象力”。参见 Slavoj Žižek,The Ticklish Subject: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9, p.30f。首先是力比多机制,弗洛伊德称这一阶段为“自体性欲”(autoerotism)阶段,即婴儿的力比多都贯注在身体的局部器官上,尚无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贯注可言,也就是说,他尚不具备“整体的性趋向”(die ganze Sexualstrebung)。对此状态,拉康也曾说道,“在自恋的背后,你已经发现了自体性欲;那就是在有机体内部由力比多所投注的能量块,而它的内部关系,我会说,就像熵一样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③Jac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Ⅱ,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p.95.其次是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如果个体尚未进入世界之中,尚无身心之别、内外之分和对时空秩序的意识,也就谈不上本体论的结构了。弗洛伊德认为要实现上述过渡和秩序的建构,“在自体性欲之上一定还会有新的心理行为”。④弗洛伊德:《论自恋:导论》,第123页。中文本译文将trieb译作“本能”,作者在此改为“冲动”。拉康认为这个“新的心理行为”就是他在镜像阶段理论中所揭示的“想象性认同”。⑤Jacques Lacan,The Seminar,Book I,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edited by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lated by J.Forrester, W.W.Norton & Co., 1988, p.115.
二、想象:“自我”如何构型?
在拉康看来,新生儿虽在躯体和神经系统方面发育尚不成熟,但其视觉能力的发达却为其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婴儿在6到18个月大的时候,便可以在自己的镜像中或他人的形象(image)中获得对自身形象的辨认与完整的把握,这一镜像或形象是以“完型”(Gestalt)①完型(Gestalt)意指一个有组织的形态或整体,具有它的组成成分个别分开时所没有的特质。在心理学中,就有一个“完型心理学派”,其理论根据是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全形构想,同时强调身体呈现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拉康的镜像理论也受到了完型理论的影响。参见狄伦·伊凡斯:《拉康精神分析词汇》,第122页。的形式呈现给他的。这种基于“完型”功能的“同形认同”现象,已经为生物学和儿童心理学所证实,而在哲学上,类似观点也由来已久,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②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注18。亦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6页。。不过与动物仅仅依此来激发本能回应不同,对人类来说,这一认同还有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首先,在镜像期中,当婴儿看到外部自己的完整的“身体形象”之后,它的完整性与自身无法协调的真实状况会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反差会强化婴儿对碎裂身体(fragmented body)③Jacques Lacan,Écrits,p.97.的经验,并使其感受到肢解的威胁。因此,从一开始,这一对照就带有差异性张力。其次,为了缓解这种反差所带来的不适,婴儿会很快将这个形象当成自己,并将其内化为意象(imago,也译作心象),想象性地将其认同(同时也是一种误认)为“自我”(ego)。这一身体形象,是以一种固定或者说凝滞的形式被其内化的,即它是一种形象的固定或者说形式上的凝滞(la stagnation formelle)。拉康认为,这种凝滞带来的固定形式和形象“类似于电影放映中,胶片突然停止转动之时,在屏幕上呈现出的一张古怪陌生的演员面容”,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人的有机体和其外部世界之间引入了某个层面上的断裂和不一致”④Ibid., p.111.。因为这个“形式的凝滞”是以虚幻不实的“持久性、同一性和实体性的属性”来构成自我及其客体的。这个借由人形意象而完成的形式固定,在构建出秩序的同时,也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种区分和取舍,是一种对前镜像期个体世界的流动性和多元性充盈状态的暴力干预。之后,婴儿将这一固定下来的形象和意象认同为“自我”,这一认同形成了“理想自我”(je-ideal)①Jacques Lacan,Écrits, p.94.,拉康也称其为自我的原型(Urbild)②Jacques Lacan,The Seminar,Book I,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p.115.。这一“理想自我”之所以是理想的,就在于它成了个体可以朝向的未来综合体,是自我赖以建立的整体幻觉,“它具有应许未来完整性的作用,是透过期待来维持自我的操作”③狄伦·伊凡斯:《拉康精神分析词汇》,第122页。。在此之后,它将永远伴随自我,也是之后其他认同的源头。④Jacques Lacan,Écrits,p.94.最后,依靠想象性认同实现自我构型的时刻,对婴儿来说也是一个欣喜愉悦的时刻。因为认同使婴儿获得了一种想象的驾驭感,拉康说,“婴儿得到了快乐,因为虽然事实上他的能力还有所欠缺,却预先经验到了某种程度的机能协调,获得了想象的胜利”⑤Jacques Lacan,Some Refections on the Ego,Int.J.Psycho-Anal., Vol.34, 1953, p.15.。借助这一认同,个体进入到想象界的辖域之中。根据这一认同的特征和主要内容,作者将镜像阶段总结为一个概念:想象。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拉康赋予它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是秩序性的建构。在拉康看来,借助于“想象性认同”的作用,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在个体那里都到了基础性地建构。在身心关心上,通过想象性的异化认同,幼儿在“心”的层面上获得了一个具有“完整性、统一性”的身体形象和对它的预期与把握。在此意义上,“心”是通过对“身”的领会和辨认得以构型的。这也暗合了弗洛伊德对自我的理解,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说,“自我首要的是躯体的自我(bodily ego);它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实体,而且本身即是表面的投影”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身体形象以“完型”的形式赋予了幼儿对自身身体完整形象的预期和把握,正是这一完型“把一个碎片化的身体形象整合进了一个整容术式的整体性之中”⑦Jacques Lacan,Écrits,p.97.。也可以说,意识的自我是以自身的身体为基础才得以形成的。
通过这一身心关系的想象性建构,个体得以将自己提前把握为一个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的整体,他实现了最初的“个体化”,而这一“个体化”同时也是将自身从混沌状态中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时刻。而且,它还是个体进入世界的时刻,他通过这一构型,在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建立了区别性的联系,因此,拉康也称“镜中之像是可见世界的入口”①Jacques Lacan:Écrits,p.95.。
进入到世界之中,也就意味进入到时空之中,对时空秩序的最初意识,也就将个体抛入到对时空的区别性认知之中:空间上他开始意识到自身身体和他人身体的区隔,也开始意识到自身和周围世界的位置关系;时间上,他在自身的“欠缺”和从外在世界获得的“预期”性满足之间的差异中,陷入时间的辩证关系之中。对此,拉康说“这一发展过程可被体验为一种决定性地将个体的形成投射到历史之中的时间辩证法”②Ibid., p.97.。此后,自我将以预期(anticipation)的方式来把握当下,以回溯(retroaction)的方式来重建过去。在这一时间结构中,未来居于优先地位,而过去则退入阴影逐渐被压抑、遮蔽和篡改。
另一方面是力比多机制的变化。第一,通过“自我”的构型,个体在混乱流动的混沌中将自己的身体形象进行固定和内化,将其“执取”并“误认”为“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功能就是赋予自恋以形式”③Jacques Lacan,The Seminar,Book I,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p.115.。因而,自我构型之时就是力比多对这一“形象”的贯注之始,弗洛伊德和拉康将其称为“原发性自恋”④Jacques Lacan,Écrits,p.98.。这一自恋将赋予“自我”和“理想自我”以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因而,“原发性自恋”是自我得以可能的条件,严格来说,这种自恋会终生伴随“自我”,弗洛伊德更将一定程度的自恋,或说非病态的自恋,看作“自我保存”的必需。第二,在这一原发性自恋中,“自我”其实是被对象化的,而这种“对象化”的能力将是个体以后将他人对象化的前提条件。拉康说,“要形成对象关系,就必须已经有自我对他人的自恋关系。而这就是外部世界对象化的首要条件。”①Jac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Ⅱ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p.94.我们也可以说,这一自恋中,力比多与其说是贯注在自我身上,还不如说是贯注在他认同于自身的“理想自我”身上,而这个“理想自我”,毕竟是理想化的,想象性的,而非自身实际占有的。以后,个体及其理想自我对父母的依赖,会逐渐将这种自恋力比多引导到对他人的贯注中。在精神分析的经验中,个体在外部找到的第一个客体,一般都是“母亲”或长久呵护他的人。第三,弗洛伊德在《冲动及其变化》中,称这一时期的个体处在“快乐自我”(Lust-Ich)时期,而前镜像期或弗洛伊德的“自体性欲”期被其称为“真实自我”时期。经过这个整体性自我的产生,“借助鲜明的客观标准将内在与外在区分开来的原始的‘真实自我’(Real-Ich)便成了纯粹的‘快乐自我’(Lust-Ich),从此将快乐置于万物之上”②弗洛伊德:《冲动及其变化》,宋广文译,载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3),第156页。。这个快乐的自我,会以快乐不快乐来衡量自身的体验和外部世界中的人与事。③启蒙现代性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可被描述为西方社会及其现代性个体从“后俄狄浦斯阶段”向“前俄狄浦斯阶段”的退化,它将个体的快乐置于万物之上,“拉摩的侄儿”就是其典型形象,弗洛伊德就曾将本我类比于“拉摩的侄儿”,而科耶夫也曾说过启蒙就是“拉摩的侄儿”的普遍化。因而,也是在这个阶段,爱恨并存的矛盾情感也同时产生。
在拉康的理论中,镜像阶段是个体进入世界—在拉康那里被称作大他者的领域—的第一道关隘,它初步完成了以自我为核心的秩序性建构,也将力比多带入到自我与自身和这一世界的复杂关系之中。拉康说:“在镜像阶段趋于完成的那一刻,它通过对来自某个相似者意象(imago)的认同和原生嫉妒的戏剧(夏洛特布勒学派[Charlotte Bühler school]有关儿童互易感觉[transitivism]的案例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现象),开创了从此将我(je)与复杂的社会关系情境连在一起的辩证法。”④Jacques Lacan,Écrits, p.98.那么,这一仅仅依靠“想象”来粘合和维持的秩序,以及仍不能完全依赖“自恋”来获得欠缺满足的状态肯定不是平衡稳固的。如果此时的个体可以依赖这种想象和自恋来获得平衡和稳固,那么他和动物也就没什么区别了。因而,这个以“自我”和“世界”互为镜像的阶段的结构性僵局,将会进一步把人类个体及其“自我”推向真正属“人”的,却也是异化最深的符号世界之中。
三、僵局:自我的本质
在汉语中,“我”字的构造似乎也印证了拉康对“自我”构型之本质的揭示。①威尔汉斯:《现象学和拉康论精神分裂症:在脑研究的十年之后》,胡冰霜,王颖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从字形来看,“我”可以被理解为“两戈相背”或“手持大戌”,它与一种对抗性或侵犯性的行为与意向相关,这似乎暗示了“我”就是一种争执斗争的产物或场所,或者说“我”就是自身最终的对手;而“自我”的“自”是以身体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即“鼻子”来隐喻整体的,其引申含义有“起源和开始的地方”。②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拉康也是在上述意义上来理解“自我”构型中存在的各种对抗性关系的,因为“自我”是要靠着认同于自身之外,与自己相对立的“相似者”才得以确立的,这正是使“主体在结构上成为自己对手”的原因所在。③Jacques Lacan,Écrits,p.117.对于镜像阶段“自我”构型中存在的问题,我将其总结为一个概念:僵局(impasse)。在镜像阶段中,“自我”陷入一种“二元关系”的对抗性僵局之中。
无论是“存在性欠缺”还是“秩序性欠缺”,个体都无法自足、自主地予以填补来使其完整而获得同一性。这就意味着,要填补这个欠缺使其满足或完整,个体必须从外部世界拿来某种“相似的”东西作为对欠缺的“增补”,其方式就是认同于它,将其同化于自身。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要想获得自我的同一性,主体必须把自己认同于想象性的他人,他必须异化自己—将同一性置于身外,可以说置于他双重的意象之中”。①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但“认同”同时也就意味着“异化”。因而,通过这种“外—在”(ex-sistence)的方式获得的同一性并非是自主和自足的,在自身的真实状况与通过异化认同获得的完整性之间,在欠缺与其增补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性将时刻威胁着这一自主性和同一性的幻象。而“自我”对抗这种威胁的方式则是充分肯定那个完整而同一的理想状态,否认甚至遗忘在这一理想掩盖下的真实状况,将其以妄想症的方式强加于它并取而代之。因而,拉康也称“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类似于妄想症的认知。②Jacques Lacan,Écrits,p.94.在这种威胁与对抗中才产生了拉康所说的嫉妒的戏剧与自我的战场。
首先,在外部形象提供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与婴儿实际上对自身的碎裂体验之间存在着差异。对实际上仍处在碎片化体验状态的个体来说,看似完整的外部身体形象赋予个体的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虚构,“自我是被建立在整体性与主人性的虚幻形象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正是自我的功能在维持着这种一致性与主人性的幻象,换句话说,自我的功能即是一种误认(misrecognition)的功能,它拒绝接受破碎与异化的真相”③肖恩·霍默:《导读拉康》,第37页。。但是,即使当个体身体机能真正成熟之后,拥有了对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种最初对身体破碎的感知经验也会依然以无意识的方式存在,它会在精神分裂症、歇斯底里症状、梦境,甚至某些艺术绘画中回到“自我”面前。④Jacques Lacan, op.cit., p.97.其次,“自我”与自身(self)的差异。当个体将具有完整性和自主性的形象当成“自我”来认同的时候,“自我”就被当成了自身的全部,这个带有虚假特性的自我形象取代了自体(self)的位置。之后,与这个“自我”不相符合的,威胁着自身统一性完整性的东西,都将被它压抑、掩盖和否认。这也是拉康反对“自我心理学派”的主要理由之一,即自我并非主体的全部,更不会凌驾于无意识之上。再次,“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异。理想自我被以预期的方式为个体所把握和期待,这是在时间中朝向未来的投射和与之不断同化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不断地把自己认同、改造为一个同他人相像甚至可以互换的人。在儿童心理学对儿童间存在的“互易感觉”(也译作“传递效应”)的研究中,就已证实这一现象—看见别人被打,自己却哭起来,打了别人却说自己被打,别人要的我也要,等等。正是这种认同与异化的张力“决定了他对他人欲望的对象生发出欲望:原初的协作突然转变为侵凌性的竞争,从这一竞争中将发展出他人、自我与客体的三元组”。①Jacques Lacan,Écrits,p.113.
因而,在拉康看来,自我的构型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对自身及其起源之真相的遗忘或否认,它以偏概全,自恋自欺,其本质不过是一种“误认”,一种类似于妄想症的知识结构,它将具有持续性、一致性和自主性的固定形式和意象强加于具有间断性、匮乏性和差异性的真实状况之上,并取而代之。因而,秩序性构建的问题就在于,个体的自我构型及其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完全依赖于想象,即对一个理想形象的认同,个体要同化、占有、控制这一“理想形象”才能完成对“秩序性欠缺”的增补,但这个本质上相异的形象无法被个体完全拥有和控制,即他无法在二者间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和同一化。因此,在想象性的误认中,他对理想形象的期待和欲望必将它引入“那喀索斯式”的二元对抗性僵局之中。
同时,在力比多机制方面,僵局也同样处在欠缺和对欠缺进行完整化的对抗之间。自我构型以后,力比多实现了对自我的贯注,也即“自恋”,但由于自身需要依赖他人才能生存,婴儿一开始就活在与母亲(或长期照看他的人)的共生关系中,通过“自恋”要获得满足也必须依赖他人的帮助和爱。所以,当个体可以在外部发现客体的时候,母亲便成为他第一个力比多贯注的客体和爱的对象。因而,在这一阶段的力比多机制中,也存在着一个二元关系,力比多和它的第一个客体,精神分析也将这一关系称为“亲子关系”,而将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称为“三角关系”。但拉康在这一“二元关系”中,分离出了第三个元素,即“想象菲勒斯”,所以他也称其为“想象的三角”①Jacques Lacan,Écrits,p.554.。这个“想象菲勒斯”,其实可以被看作拉康所说的“存在性欠缺”的一种阶段性表象形式。这里的“二元关系”停留于想象层面,二元性表现为个体对母亲的依赖和独占母爱的欲望。存在性欠缺在这里被具体化为“母亲意象”,但个体不知道的真相在于,母亲也是一个有所“欠缺”的存在者,她并不能真正填补个体的本质性欠缺。这种依赖和爱会在不断出现的挫折和被人争夺的状况中演变为攻击性的倾向和负面情感。因此,镜像阶段之后,力比多机制同样陷入二元性的对抗性僵局,而其本质就在于主体误以为外部的形象和力比多客体直接就是自身欠缺的“补体”,对它们的“想象性认同”和“强制同一”,既带来了自恋中的妄自尊大,也带来了任性中的无法无天。
总之,僵局的本质就是主体自身的“非同一性”异化在想象层面上导致的结果,或者说就是主体的“欠缺”和其想象性的“增补客体”之间本质的“非同一性”之症状表象。在其中,自我的想象功能成为这种僵局的主要成因。简言之,它把“相似性”误认为“同一性”,它以为自己所欠缺的,就是它所认同的形象和欲望的他人,它力图通过对它们的占有实现同一性和整体性;而处在想象层面上的“自我”,无法认识到形象的虚幻性和他人的有限性,在本质上,它们并不具有“可交换性”,也不具有“自我”所赋予它们的上述价值。因而,通过“正反题”的“直接交换”和互补并不能实现对“欠缺”的完美填补,这种“直接交换”会像“那喀索斯困境”一样导致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也会像“俄狄浦斯悲剧”一样因为想象性的“误认”和所谓的知识而导致乱伦的罪恶。
四、结语:从想象性自我到符号性主体
拉康认为,要通过(pass)上述二元对抗性僵局(impasse),必须实现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否定,即,通过“语言符号”和“父之名”的介入将二元关系转换为三角关系,将处在想象层面的个体引入符号结构化的象征秩序之中,个体才能真正完成从自然向文化的过渡①在镜像理论中,我们也能看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对拉康的影响。参见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7页以下。齐泽克也曾多次以同样的逻辑来阐述“想象性认同”所存在的僵局及其解决方式,参见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按照张一兵先生的说法,就是要把“想象的镜像”转换成一种语言介体构成的巨镜②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第153页。。这种介入和转换也可以从“力比多机制”和“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语言符号(学会说话)的介入对应“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父亲功能的介入对应“力比多机制”。
本体论结构方面。首先,“符号”或说“能指”取代“形象”成为结构的核心要素。其次,“符号性认同”形成的“自我理想”取代想象性认同形成的“理想自我”,前者是对某一位置的认同,后者是对某一形象的认同。再次,在语言切割的效应中,“主体”得以从镜像阶段的“自我”中区分独立出来,以人称代词“我”的形式来发挥转换和指示的功能,而主体分裂的本质也将在这个作为主格的“我”这里得到呈现。拉康在文中说道:“幼儿对其镜像的欣悦认定似乎暴露了某种典型情境下的象征母体。在此,‘我’突然被抛入了某种原始的形式之中,之后,又在对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被对象化,而后又通过语言而得以复活,使其作为主体在世间发挥功能。”③Jacques Lacan,Écrits,p.94.因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在想象的二元关系中,拉康要增加一个要素,即存在于二元对立中作为根本原因的“欠缺”。这个欠缺将会在语言符号的世界中,具体化为拉康意义上的“主体”,拉康将其写为一个被打上斜杠的大写的S,即 。这个区别于“自我”的“拉康式主体”才是笛卡尔那个被还原为“纯粹消失点”的“我思”主体④Mladen Dolar,“Cogito as the Subject of the Unconscious”, inJaques Lacan, 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Vol.2,Philosophy,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6.,这个“‘我思’并非实体性实存物(substantial entity),而是纯粹的结构性功能,是一个空位(拉康所谓的 )”①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因而,也正是在“符号性主体”和“想象性自我”的差异中,才会有“普遍怀疑”的可能性空间。
力比多机制方面。“父亲功能”的介入会将儿童贯注在母亲身上的力比多分离出去,在二者间确立正常的距离。精神分析称此为“去势”或“阉割”,就是让个体在认同于父亲所象征的权威的同时(这一认同即前面所说的符号性认同),将力比多进行分离、转移和升华,拉康也称此父亲功能为“父之名”②Jacques Lacan,“Du《Trieb》de Freud et du désir du psychanalyste”, p.852.,它是拉康象征界或说符号界理论的核心概念。因而,存在于想象阶段的二元对抗性关系只有通过将其本质中隐而不显的欠缺经过符号化,主体才能从“直接交换”的对抗性僵局中解脱出来。拉康说,“通过这一认同,主体可以超越在其最初主体性与个性中所具有的最基本的侵略性。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强调过这一认同构建在确立距离的这一步中,通过这一距离和类似于尊重的情感,一个有关邻人(le prochain)富有情感的完整假设产生了”③Jacques Lacan,Écrits, p.117.,以此方式,主体才能超越与他人陷入的生死斗争和与自身陷入的那喀索斯困境。
综上所述,拉康式主体( )就是人类自身的“存在性欠缺”的符号化,它通过“镜像阶段”和“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两次异化被具体化在符号体系之中,以一个“空能指”的方式发挥“结构性功能”。而“自我”不过是对“欠缺”及其表象的否认、填补与缝合,是“缘起”构型的“假有”,只有偶在的属性而并无实体性的本质,也可以说其本性为空。不难看出,在拉康那里,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并非其理论的基本视域,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中,本体论视域不过是人类自身“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是更深层的问题与冲突所导致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