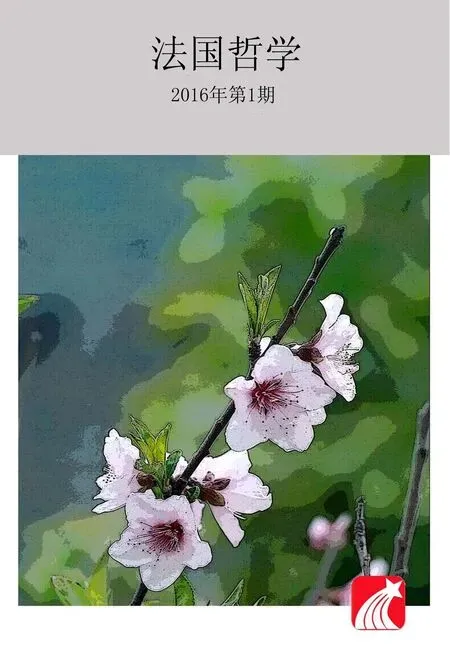现代哲学的奠基:先验现象学视域中的笛卡尔
2016-02-01李守利
李守利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
现代哲学的奠基:先验现象学视域中的笛卡尔
李守利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
一个似乎洋溢着个体特殊性的思考过程的如实记录,它以诚恳对话的方式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哲学远航旅程。在这质朴简洁的思想实录中有着怎样的充沛活力,它如何能够从事这样意义深远的奠基性行动?借助于胡塞尔近乎四十年间的反复思索,我们试图重温这段精神历程,并从中汲取思想前行的力量。
“现象学必须将他作为真正的先驱予以尊敬。正是对笛卡尔沉思的研究影响了这门成长着的现象学的新发展,赋予现象学以现有的意义形式,而且几乎可以允许人们将现象学称为一种新的笛卡尔主义,一种二十世纪的笛卡尔主义。”①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一
为了理解现代哲学奠基这件事情,需要理解现代哲学。所谓奠基的意义,似乎要有待于它的最终完成才能看得清楚。今天,现代哲学是否已经完成,甚至,哲学是否已经完成,从而可以宣布“哲学的终结”?似乎唯当我们自身处于后现代,才能谈论“现代性”,才能反思现代哲学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然而,哲学的最卓越之处即在于它能对自身予以反思,或者说它总是致力于使得自身反思成为可能,使得人可以理解自身,科学可以理解自身,一个时代也可以理解自身。
理解现代哲学的奠基,也需要理解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关系。所谓奠基,是否标志着一个断裂,建立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哲学?“春去春又回”,万物更新的春天是否标志着新的一年是一个与去年全然不同的一年?哲学精神的发展历程也是生命的历史,有萌芽成长枯萎,也有再次萌发。笛卡尔开启的现代哲学进程,是古希腊哲学精神的一次复兴,仍然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传统之中,而我们也仍然处身于这个传统之中。因此,现代哲学对主体性的认识并非对立于“理念论”,而仍然是同一个哲学精神,如先贤所言,真正的哲学只能是“理念论”(idealism)。只是古代哲学讲,唯有心灵能认识理念,而现代哲学讲,唯有心灵能成就理念。奠基指向一种统一性,精神旨趣的一贯性,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连续性,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开端,因此同时它也意味着一种撕裂,一种颠覆,它要求自身成为基础,要求依据于自身而具有运动的本原,它拒绝未经检验地将他者认作为自身的当然基础。
因此,评价笛卡尔的成就,首先是真正哲学精神的复兴,他再次发现或发明哲学,再次论证了哲学的正当性,再次显明了哲学精神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进入现代社会,古希腊罗马文化成为典范,依据于哲学的存在方式被认定是古代文化的本质,即以来自纯粹理性来自哲学的准则作为自身生活的准则,因此,“哲学作为理论不仅解放研究者,而且解放任何受过哲学教育的人”,根据自由理性根据普遍哲学的洞察,人开始在伦理方面重新塑造自己,同时重新塑造人的整个环境,人的政治和社会存在。①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18页。开启哲学之思,以哲学的态度去思考世界,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无可替代的意义。“人类的真正存在只是作为指向终极目的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如果它确实能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才能实现。”②同上书,第28页。因此,在胡塞尔看来,最重要的事情似乎就是“进入现象学”,也就是说“开始”哲学研究。“开始”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异乎寻常地艰难,不是以后的研究艰难,而是“开始”很难。难在何处?难在对熟知之事开始质疑,难在对天天之所见开始惊叹,难在目光从可感可触的世界转向不可见的世界,难在从“差不多就行”转向“绝不将就”,难在从偏执己见的虚荣转向坦诚的交流与相互理解,难在从安居乐业转向思考令人不安的死亡与令人畏惧的非人力量。
哲学之难,难在人们没有勇气面对。因此首要的哲学美德是勇敢,哲学思考首先是哲学家个人的勇敢行动,是决断,是生命的投入,是冒险,是对可能失败的承担。这首先是胡塞尔的自白,他对自己精神发展的总结,之后也是对将要成为哲学家的人的激励与劝勉,是宣告与召唤。他在邀请我们一起出发。
“当主体将自己规定为哲学的主体时,它甚至表达了一种指向其整个未来认识生活的意志决心。”③胡塞尔:《第一哲学》下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9页。
“哲学家必然需要一种一般总是最初地和原始地将他造就为哲学家的特殊决心……任何人也不能被卷入到哲学之中。”④同上书,第60页。
没有人会被卷入到哲学之中,即哲学从来不是勉强之事,他不会是一种出于善意的跟随或赞助,他一定是出于一种大的决心,也必然会有一种大的坚定。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是对同样的哲学理念的洞见,哲学的事业是真正的志同道合之事业。胡塞尔的生命与哲学是一体的,因为他的彻底精神,因为他以自己的生命将理论的哲学具体化,他可以称之为现代的苏格拉底,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刻可以自豪并且无所畏惧地对身旁的护士说,“我作为一名哲学家而生”,“我也将努力作为一名哲学家而死”①史密斯:《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前言,赵玉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在胡塞尔的著作中,哲学的自觉意识特别强烈,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得他的思想特别强劲有力,这是哲学对于时代的责任,我们作为正在生成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责任。
二
哲学的奠基也是奠基的哲学,即以开端作为对象的哲学,甚至很可能唯有以开端为对象的哲学方能成为哲学的开端。现代哲学所思之开端指向真正的知识。哲学家和科学家最初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热爱智慧的人,即追求真理的人,力求把握实在,理解现象,力求自己所做出的判断是真的,因此,具体的分支科学构成着作为科学之真正统一的哲学的分支,是作为科学整体的哲学的部分,这里的哲学是作为普遍科学或严格科学的哲学。人的本性在于求知,即热爱知识适合于人的自然,对以真实存在为对象并且具有严格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的追求是必然的和原初的。科学作为对知识的朴素追求,具有一种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性由怀疑论所发现,即怀疑论者发现在认识者、认识对象与所认识的真理三者之间并不是协调一致的。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特殊与普遍之间,在相对与绝对之间,在变易与恒常之间,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存在着持久而剧烈的冲突。
以科学形象出现的人的认识成就,总是面对各种各样怀疑论的质疑,与这些怀疑论对应的是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即所谓的客观主义。先验现象学以克服怀疑论和独断论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由此在先验哲学的伟大传统之中,并且因为同样的理由而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开创的伟大传统之中。胡塞尔以恰当的方式回顾了哲学的历史,特别是哲学在古希腊的第一次奠基,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哲学事业的最伟大开创者,同样的只还有笛卡尔。就哲学在古希腊的奠基,哲学之直接对手是智术师们的相对主义怀疑论。笛卡尔与胡塞尔踏上哲学的道路,也是出于同样的责任心,同样的批判精神,同样的战胜怀疑主义的决心。因此我们赞成史密斯的分析,正是在对柏拉图与笛卡尔的不同理解中,显示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迥然不同的思想旨趣,与胡塞尔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已经偏离了所谓的真正原初思想,而笛卡尔则使得这种偏离恶劣到无以复加。①史密斯:《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第11—12页。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想倾向不是偶然的,我们在他这里所看到的,与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之后的英国经验论那里看到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经验保守主义对于奠基性的哲学革命所做的反击。
胡塞尔所要求的知识的绝对有效性,或者康德所承认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不单是指自然科学知识,同样包括道德判断,因此关涉生命的整体,关涉人出于本性的对于善好的最终追求。如同笛卡尔对他自己的思想历程的如实呈现,苏格拉底在《菲多篇》中讲述了他的思想转折,自然哲学家们将万物如是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物质因素,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水、火或原子不能说明万物的如是存在对于它们而言是好的,苏格拉底之不越狱而接受法庭的裁决,原因不能归结为他的身体物质组成,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好的,因此对好的理解是行为乃至存在的真正原因。
哲学的理念要求知识的绝对有效性和与之相关的彻底精神,这种彻底精神不可能由于对于知识的朴素的热爱而“以自然的方式不经意地产生出来”。哲学理念出现的前提条件恰恰是一切朴素的认识价值和科学价值之破灭,即认识到迄今以来评价甚高的一切科学都有“无可救药的不完善性”,认识到它之遭受怀疑并以某种方式失效的必然性。这就是从事哲学奠基行动的哲学家所面临的独特处境,这不是偶然的。①胡塞尔:《第一哲学》下卷,第62—63页。
“对于他(笛卡尔)和每一个真正想成为哲学家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应从一种彻底的怀疑的悬搁开始,即对自己迄今所有的一切信念的整体加以怀疑,……每一个哲学家在他的生涯中必须这样做一次。”②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95页。
哲学在根本上不同于各式各样的怀疑论,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与之相对立。由此出发,可以理解胡塞尔之先验还原,以及笛卡尔之普遍怀疑,不同于怀疑论之怀疑。先验还原的最重要成果,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成果,即是对纯粹意识领域的获得,具有绝然自明性的意识领域,作为无可置疑的清楚明白的认识根基。所谓的“面对事情本身”,一切原则的原则,原初给予的正当性,所言即是如此。所谓“悬搁”,是目光朝向的改变,不再指向所谓的“外在”世界,而是仅仅以意识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这里的意识是包含一切意识内容在内的意识。对“外在世界”的研究必须以“对外在世界的意识”的研究为根据。
自然态度的生活是一种原初的生活,完全专注于世界,忘我的生活;“而非自然的生活,是一种彻底的纯粹的对自身予以思考的生活,这种对自身的思考指向纯粹的‘我在’,指向纯粹的自我—生活,指向在任何意义上作为客观之物呈现的东西在这种生活中,恰好获得作为客观之物的这种意义和这种有效性的那些方式。”③胡塞尔:《第一哲学》下卷,第183页。
用胡塞尔的例子,“我知觉到这个房屋”④同上书,第139页及以下。,在这个知觉行为中,自我的目光与兴趣是指向这个房屋的,是专注于非我的世界,但同时,这个知觉行为可以被回忆,可以被反思,例如“我刚才在观察这个房屋”,这样,同时存在着实行知觉行为的自我与对这个知觉行为予以反思予以把握的反思自我。如康德所言,“我思必然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即在一切表象行为中都有对这个表象行为予以统觉的自我,实行表象行为的自我是杂多,而对这个杂多的自我予以统觉的自我实行了综合统一的行为,因此提供了在诸多表象行为中的自我的同一性。在胡塞尔这里,“我作为反思的自我超越了我知觉这种行为”,我作为新出现的反思的自我,使得在“我知觉”这个行为中的自我得以呈现,在这个呈现中,投身于世界的自我成为了反思的自我予以理论观察的内容,不仅如此,与这个投身于世界的自我一起成为客体的,还有这个投身于世界的自我所投身的世界,即在“我知觉到这个房屋”中的房屋,然而,这个一起成为客体的世界现在成为了在知觉行为中的世界,即被我所知觉到的世界。在对世界予以知觉的行为中,包含着自我对世界的兴趣,而当知觉行为被反思自我所把握时,这个兴趣也一同被把握,而现象学的悬搁则使得反思的自我对被知觉的世界自身没有兴趣。在反思自我的把握中,实行知觉行为的自我与这个自我所知觉的世界分离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获得了纯粹的自我,然而这个纯粹的自我却不是没有内容的,它所知觉到的世界作为客观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和有效性就是它的内容。
在笛卡尔的沉思中,这个实行知觉行为的自我,即观察蜡块的自我,以及在知觉行为中的世界,即蜡块,同样被反思。在达到“我在”这个确定无疑的真命题之后,笛卡尔继续追问,“这个确实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①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在这个追问中,如上面所分析的,有两个自我处于张力中,一个是“我存在”中的我,一个是“确实知道我存在的我”。然而,笛卡尔没有将其分析为两个,他随后的问题是“我究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一个思者,所谓思,即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在想象、在感觉。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他指出,虽然我始终将某种事物作为思想的对象,但我通过思想所把握的不仅仅是事物的相似物(图像),作为思想形式的意欲或情绪,或者判断,同时被意识到。
在对知觉行为中的蜡块的分析中,笛卡尔将物体性区分为从感官得来的性质和通过理智思维得来的性质,他认为感官得来的性质是模糊的,而从理智得来的性质则是清楚分明的。在这里可以看出笛卡尔反思并非总是那么彻底,即他预设了意识内容的不同来源。现在,笛卡尔认为他的“我思”达到了对蜡块的清楚分明的认识,他再次追问,这个清楚分明地对这个蜡块予以认识的我,究竟是什么。“如果由于我看见蜡而断定有蜡,或者蜡存在,那么由于我看见蜡而因此有我,或者我存在这件事当然也就越发明显”。“一切用以认识和领会蜡的本性或别的物体的本性的理由,都更加容易、更加明显地证明我的精神的本性。”在这里,笛卡尔已经提出了意识的意向性原则,但他没有继续。
反思的自我与实行知觉行为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分离的诸多自我只能在同一个自我的反思中呈现。这里自我的统一性是直接自身呈现的。“我思”、“我在”与“我思”之思是我在思,这三者是同时给出,具有同样的明证性。这里没有无穷倒退的恶循环,没有无止境的自我反思。能设定诸多自我,能使得这些自我分离的自我,也同样能将这些自我予以综合统一。
笛卡尔的成就,首先是给出了通向哲学思考的一条途径,之后是明确了哲学的理念,即哲学研究对象与哲学研究方法的发现,从而有作为绝对主体“我思”的发现,由此重新开启了主体性哲学。如前人所指出的,在笛卡尔之前,奥古斯丁已经发现自我意识的绝对存在。然而,笛卡尔的成就是以“我思”为最终根据去论证其他一切知识,重要的不是他的论证是否有效,不是他的论证步骤,而是他对论证必要性的洞见。“我思”是认识的根据和基础,而随后以无限完满作为规定性给出的上帝存在证明则给出了“真”的必要条件,将这两者予以综合,于是有“所思”之真,即真正知识的最坚实基础。
三
在《观念》中,为了达到新的存在领域,本质直观的领域,需要从对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开始,以经验主义面貌出现的自然主义态度是对本质性存在以及对本质性存在的认识持怀疑态度的怀疑论。在自然态度的理论研究中有一个根本的预设,即所认识的世界永远作为现实存在着,这个世界永远是事实存在的世界。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使这个设定失去效用,才能达到纯粹意识的领域。在阐述现象学悬搁的意义时,胡塞尔引入了笛卡尔的方法,他将其概括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的“试图普遍怀疑”的程序,但同时指出笛卡尔的目的与现象学的完全不同,并且普遍怀疑只是一个权宜方法。①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页。
在《观念》法译本注释中,利科指出,在胡塞尔的论述中,方法论怀疑与现象学悬搁先是被谨慎地加以区别,然而随后对悬搁的说明却具有笛卡尔风格,即为了分离出意识领域,把它描述为“不可怀疑的”,通过“世界消除”,现象学的纯粹意识作为“剩余”出现,这是明显的笛卡尔式的步骤。以“加括号”“排除”作为现象学悬搁的形象化比喻是令人迷惑的,因为这样似乎只是否定的意义上讲悬搁。②同上书,第509—510页。
在《巴黎讲演》中,胡塞尔特别指出,应该拒绝因为青睐数学自然科学所产生的成见,仿佛“我思”所涉及的是一个确然的公理,可以给研究世界的科学提供一个演绎的基础,仿佛所要做的仅仅是根据“我思”将世界的其他部分推演出来。他的批评是,笛卡尔不恰当地使自我变成了思维着的实体,变成了被分离出来的人类灵魂,变成了根据因果原则推理的起点,由此,笛卡尔成为了荒谬的先验实在论之父。③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第8—9页。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全面细致地对现代社会予以诊断,目光转回到“现代人性”生成的历史之中,回溯确认现代人性的精神起源与文化基础,对现代社会的科学危机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予以剖析,发现近现代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所处身的现代,“正处于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没因而放弃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巨大危险之中”。①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5页。胡塞尔指出,欧洲人性的真正思想斗争是不同哲学之间的斗争,即在怀疑论的哲学(“毋宁说是非哲学”)和真正的哲学之间的斗争。真正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为自己的真实意义而奋斗,并以此为真正的人性的意义而奋斗”。②同上。
通过对精神历程的分析,在指出客观主义哲学与先验论哲学之搏斗之后,胡塞尔指出,笛卡尔既是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现代理念的奠基者,同时也是冲破这种理念的先验论哲学动机的创立者。“笛卡尔式的悬搁”,是一种“迄今闻所未闻的彻底主义”。一切经验,以及相关的世界,一切认识,包含科学在内,一切建立在经验之上的意义和有效性都受到质疑,都需要检验。这是“认识批判”的开端,胡塞尔特别指出,这个开端同时也是“作为对于客观认识的彻底批判的历史开端”③同上书,第95页及以下。。
在主体理性中产生的理性构成物,如何能够要求客观的真理性和有效性,这是近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理性批判哲学的核心,这在笛卡尔的沉思中有其意义的根源。因此,笛卡尔开启了全新的哲学,即在主体性中寻找最后的根据。然而笛卡尔仍然是客观主义的,即在他这里,为客观科学奠定基础的“心灵”却自相矛盾地也是客观科学(即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胡塞尔批评性地指出,笛卡尔没有发现,自我(我思)不可能成为客观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能在世界中作为研究主题而出现”,因为一切世间的东西(具有世界性,在世界之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心灵存在,都在意识(我思)的构成性功能中获得其意义。“笛卡尔没有看到,像我与你,内在与外在,所有这样的区分,只有在绝对的自我中才能构成”,因此笛卡尔没有为自己提出系统地研究纯粹自我的任务,他没有看到这样的难题,即从自我中的现象世界出发系统地回溯世界如何在自我的内在成就中获得其存在意义。④同上书,第101—103页。
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坚持主体性,而是过于匆忙地去为外在世界以及关于外在世界的科学提供正当性论证。他发现了主体,却忽视了主体的丰富内容,没有将目光停留于此。当“我思”被理解为与身体处于对立之中的“心灵”(mens)时,这种客观有效性论证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它只能借助于“上帝”之完美性而取得虚构的证明。“意识生活是成就着存在意义的生活,意识生活固然是作为感性直观的生活,但更是作为科学的生活。”“正如感性的世界,日常生活的世界,是感性思维活动的思维对象一样,科学的世界是科学的思维活动的思维对象”,胡塞尔指出,笛卡尔对此没有深入的思考。①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12页。
我们注重先验现象学对于柏拉图—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胡塞尔对此传统的批评和他的创新性贡献。然而,我们不能走向一个极端,即如兰德格雷贝和许多研究者所主张的,胡塞尔后期放弃了笛卡尔的道路或在根本上背离了笛卡尔主义。兰德格雷贝在《胡塞尔之告别笛卡尔主义》论文中分析指出,胡塞尔离开笛卡尔的道路,从个人经验出发,通过还原,达到先验自我之路,先验自我不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而是哲学思考即现象学反思的结果。兰德格雷贝的工作影响广泛,其中他的学生威尔顿继续努力论证笛卡尔纲领破产之后的“另一个”胡塞尔,他试图依据对胡塞尔手稿的研究去纠正以往研究者只重视正式出版著作的片面的所谓标准解读。②参见威尔顿:《另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视野》译者序,靳希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8页。如靳希平先生在威尔顿著作中译本序中所言,他们的研究工作值得阅读,有启发意义。针对兰德格雷贝等人的主张,也有很多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如史密斯认为,笛卡尔式道路是达到现象学的认识论道路,在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可选择的道路,例如在《危机》中所提的心理学的道路或生活世界的道路,然而,这些道路只是提供了不同于笛卡尔式道路的诸多选择,却并不是它的替代品。③史密斯:《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第63—68页。不同的主张在胡塞尔的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论据,这使得这个问题显得错综复杂。我们认为,从对哲学理念的根本理解出发,根据先验现象学的原则,胡塞尔仍然坚持着柏拉图—笛卡尔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仅是一个胡塞尔思想诠释的问题,而且是两种哲学传统的对立的问题,而经验论无法理解或接受那样一种彻底精神,即着眼于严格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哲学研究。
重思胡塞尔对哲学思考历程的把握,为什么恰恰是柏拉图与笛卡尔被非同寻常地标示出来?究竟在何处,虽千载之下,胡塞尔仍同心以求?我们注意到,首先是同样的哲学奠基的特殊时刻。越是深入于思想的搏击处越是能体会到这种奠基的意义,思想在流行的模糊混同中敏锐地看到差异性并能坚持哲学的不容妥协的真理要求。也许是格外明晰的真凸显在思想之前。在这样的时刻,所要确立的是同样的真理之路与知识领域。他们同样坚持真理与意见的区分,坚持以严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作为研究对象的择取标准。能够将研究对象清晰地分辨出来,划定研究领域,与之相应,能够把握对象的方法也自然地确定下来,由是我们才真正获得了一种知识的可能性。柏拉图与笛卡尔要求区分感性相关物与理智相关物,胡塞尔则要求某种“悬搁”,要求区分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要求从理智相关物更进一步地深入于理智自身,即具有意向性的意识自身。确实,在某种需要特别努力才能理解的意义上,他们持有的是同样的实体观,即所研究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存在,这不是我们之外的感性的物理世界,也不是我们之内的个体的内心世界,而是能够被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通过他个人的理智努力加以认识的实体世界。如是存在领域的获得是异常艰难的,而它的失去却是很轻易的,这种轻易是因为存在的真知并不直接地具有显明的作用,它需要自然哲学,即今天的自然科学作为媒介,或者说需要某种转化,才能作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每一次这个领域的获得并经过相应的自然科学运用之后,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识都出现了根本性的进展,在柏拉图哲学之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主导着对经验世界的认识,笛卡尔哲学之后,牛顿物理学主导着对经验世界的认识,其中,在康德哲学之后,现代科学获得了更可靠的方法论保障。略微让人惊奇的是,每一次自然科学取得极大成就极大声誉的时候,都伴随着经验论的兴盛,伴随着对理性哲学的贬损,从而导致了上述存在领域的失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哲学之重新需要奠定基础的必要性,由此可以理解胡塞尔重新开始在柏拉图—笛卡尔哲学路向上从事思想工作的意义。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胡塞尔:《第一哲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史密斯:《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赵玉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威尔顿:《另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视野》,靳希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