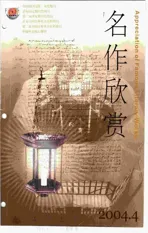学人读书自述 文心宗大雅,经典读如新——读书生涯六十年回顾
2016-01-28山西丨寓真
山西丨寓真
学人读书自述 文心宗大雅,经典读如新——读书生涯六十年回顾
山西丨寓真
在阅读中学会作文
读书可以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嗜好。健全的人生应当有一些好的习惯、良的嗜好,不能有坏的习惯、恶的嗜好。如果把人们各种好的习惯、良的嗜好开列出来,爱读书应该是排在前头的。
大凡嗜好都是青少年时候养成的,我自上中学时沉湎于课外书阅读,这种习惯从未改变,读书便成为我几十年人生的一个主要内容。
成语说“学以致用”,学是为了得到运用。但读书成为一种嗜好以后,未必就是为了使用,读书时时随其兴味,并无明确目的。如同爱好钓鱼的人不是为了吃鱼,爱好养花的人也不为卖花赚钱,读书常常像钓鱼养花一样纯属闲事。其实读书本身就是生活,常常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所以不需要为了什么。
现在回头想想走过来的读书生涯,却又可以总结出许多的好处来,于是,又觉得读书并非纯属闲事,不仅充盈了生活趣味,而且陶铸了人格情操,即使在具体事情上也让人得益匪浅。虽然当初读书并没有想到为了如何使用,但实际上它还是发挥了用处。
我想说的读书的一个直接的好处,是学会了写作。
我上学的那个年代,文学上有两个显著现象,一个是鲁迅崇拜,一个是苏俄崇拜。我读鲁迅的作品较多,又由鲁迅及于左联,左翼作家中郭沫若和茅盾的作品当年重如鼎吕。此外,我爱看的是郁达夫、蒋光慈、柔石、殷夫等人的选集,还有丁玲的小说和闻一多的诗。苏联作家中读的较多的是高尔基和肖洛霍夫,读高尔基的三部自传小说时,我很入神,书中那个在艰难环境中坚忍磨炼和刻苦读书的形象,为我的青春年华注入了精神的激励。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曾经使我痴迷过的诗人。俄国小说也看了不少,包括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巴金翻译的《父与子》。有一部小说名为《怎么办》,作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其中描写一个有志之士在钉了几百枚钉子的床上睡觉,那个情节给人印象极深。记得有个说法,是说马克思和列宁都对这部《怎么办》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教导人、鼓舞人的真正的文学。
对于世界文学有所了解之后,我也很注意阅读欧美方面的名著。我所在中学读书环境很好,图书馆藏书颇丰,阅览室陈列有多种杂志。那时有一批错划为右派的文化人士被下放到中学教书,其中不乏造诣深厚的学者,对我的读书多有指诲,他们博学雅达的君子风度使我受到了感染。但也有意外情形,一次班主任走进教室,我手里正捧着拜伦的长诗《唐璜》,他夺了我的书指责说:“这是你们学生能看懂的书吗?”他批评我不务正课,但到期终考试下来我的成绩都好,他便也无话可说。有的老师总结我的经验说,阅读多语文就好,语文好理解能力就好,其他功课因此也能学好。最支持我读书的当然是语文老师,因为我的作文好,几乎每次作文课都会讲评我的作文,我心里明白是读书帮助我学会了写作。读了那些佳作名著,不但可以拓宽知识视野,而且可以丰富语言词汇,还可以学到种种表达方式和修饰手段,以至于如何组织材料、安排文章结构,起笔如何开门见山、娓娓言之,结尾如何恰到好处、余音袅袅。这些虽然是小技,但如果读书不多便难得其三昧。
人生在世总要做一番事业,因而需要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技能,写作也是一种技能。学会写作并不就是要当作家、写著作,现代社会中写作是人的基本技能之一,许多工作都离不开写作。我长期做司法工作就深有感触,写作能力跟不上就当不了法官,因为写好法律文书才能最终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好的法律文书必须表述明晰,语言精准,不仅要正确适用法律,而且要入情入理,使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过去有一位文化名人叫樊增祥,别号樊山,清末任陕西宜川令、渭南令时,所审案件的裁决文书都是上好文章,曾经梓行于世,风靡一时,后来官至护理两江总督,慈禧太后《罪己》《变法》等诏书都出自樊山手笔。此人在民国早期属于京城的名儒巨公,诗文著作极富,而我喜爱看的还是他当法官时候的那些判牍。
诗书为伴的那些年华
我大学将要毕业那年,逢上了“文化大革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几乎所有古今名著都已不合时宜,甚至被打入了扫荡之列。古典文学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槁木死灰,教我们古汉语课的老师遭到了批斗。我那时候的阅读兴趣,已经转向古典诗文,运动一来不得不有所收敛。领袖说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运动期间“众芳摇落独暄妍”者只有鲁迅,所以,我就读《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及鲁迅辑录的《唐宋传奇集》。那时不乏印着“毛泽东选集”字样的红色塑料书封,想看旧书时套了那种红色封皮,可以掩人耳目。不过到运动后期也就宽松了,私下看看所谓封建主义的书并不会遭人检举。
1967年我被派遣往海南岛西部的黎族山区,为轻装便行起见,书籍或送友人,或卖废纸,教材只留了王力主编的四册《古代汉语》,是中华书局第一版印本,另外还有两三本诗集随身。先到广州,在招待所里认识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同学,他看见我携有《陶渊明诗选》,取来一本李长之的《诗经试译》要与我交换,他很诚挚,我便欣诺。到了琼崖荒僻之地,苦于无书可读,只能钻在王力的讲义里研究古文句法和诗词格律,兴致好时偶尔背诵几篇《风》和《雅》。
在海南漂泊了六年有余,调回山西时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报刊上大讲“儒法斗争”。以批判为由,机关和学校的图书馆半开放了,可以借阅儒家法家之类的种种旧书。时隔数年,我又重新走进图书馆里,那种感觉真的是如鱼得水一般,令人异常兴奋。原先在我父母亲那里存放的书也取来了,我的读书生活又丰赡起来。
在海南那几年研究诗词的工夫没有白费,我熟悉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和格律、声韵,加之椰风蕉雨、沧海云帆的那种特殊感受,写下了不少诗稿,写诗填词从此也成了我的嗜好。日月蹉跎,事业无甚起色,我只有在读书兼写诗中默默度过那些壮岁光阴。
在海南写的那些诗词,我后来印了一本小书,名为“飘萍集”。印前曾请教过两位专家,一位是老诗人徐放先生,一位是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他们为拙作撰写了评论。徐文发表在1991年2 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姚文发表在《火花》1992年第3期。两位先生的热忱指点和勉励,坚定了我写作诗词的信念。我那时颇有一些创新的志趣,想法未免幼稚,继续探索中才深深悟出了中华诗词的真谛。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始终居于冠首地位,两三千年中一直传承着《诗经》《楚辞》的灵魂,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从汉魏古风到唐诗宋词,格律声韵这些外在形式虽有变化,而其内涵始终不离诗骚神髓。写作诗词不仅要有生活体验,而且必须读书,这大概是古典诗词与新诗、与别的文学创作有所不同的地方。杜甫所以成为诗圣,不能只是简单地说他的诗歌如何反映了唐朝动乱年代的社会现实,要知道他的忧国忧民精神原是承接于《诗》《骚》。前人评论说杜甫作诗“无一字无出处”,“上自骚雅,下迄齐梁,加以五经三史,博综贯通,无不咀其精华”,可见做好一个诗人,不仅要行万里路,而且要读万卷书。现在写旧体诗词的人很多,而佳作殊少,究其原因,不是没有生活经历,而是没有好好读书之故。我在学习诗词中,常常感佩前贤胸度高胜而惭慨自己读书之不足。
开始学习古典文学时,我手边常置三本书:《四书白话解》,是家里老人遗物,民国年间重庆桂林新生书局印行;《唐诗三百首》,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古文观止》上下两册,也是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这三本绝版书,现在成了我的收藏品。为便于学习诗词,多年相伴身边的几本书是: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余冠英选注的《乐府诗选》,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龙榆生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陈乃乾编辑的《元人小令集》。学习诗歌文学理论,当然还要时时翻看诗品、诗话之类的书。诚如苏东坡所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工作之外开辟一个境界
进入不惑之年,我在政法机关担任了领导职务,繁忙的工作几乎耗尽了我的时间,也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欧阳修《归田录》云:“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枕上、马上、厕上。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初读此语,犹不以为然,自从被压在重任之下后,我有了自己的体会,宝贵的时间正是“三上”,读书也必须利用这种时间。枕边时刻垒着书,厕边时而放一两本,外出一定是要携书登车的。我坐小车习惯坐后排,不喜旁边有人,一路上手不离书。在省内跑各市县是常事,因公务赴京每年也有数次,大都坐汽车往返。即使到省外开会,如郑州、武汉、西安、兰州等地,我也不乘飞机,喜坐汽车。行车看书,看看停停,忽闭目静思,忽观赏一阵外面的风光,眼睛不会太累,而且有利于记忆。
我上大学读的是法律系,当年的教科书许多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教条主义观点甚多。面对的社会状态和工作实践,使我深感过去某些正统理论的空泛和脱离实际,甚至于荒谬,进而看到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思想不灭的光辉。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法理学、刑法学、诉讼法学这些学科,但相关理论大量散布在经史子集著作中,其论述极其丰富,极其深邃。我国古代的学说没有像西方那样分门析科,似乎不够科学,但传统的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崇本敬民的思想,是把自然法观念和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这才是最科学的淑世治国的理论。阅读诸子百家的书籍,让人如同走进了一座光芒四射的宝库。聆听古代思想家们的精湛讲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前人留下了“有福方读书”的箴言。
《尚书》这部古老的经典中,就有很多法律的叙述。尧都在今日山西临汾,洪洞士师村传说是法律始祖皋陶的故里,因此我读《尧典》和《皋陶谟》别有兴致。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一个极致的哲理,《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又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法令滋张,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以说,在中外法律思想史上,再没有比这些更精妙的论述了。儒家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省刑罚,薄税敛”的仁政,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重民论是我国数千年来最宝贵的思想文化传统。法家主张以法为本,《韩非子》一书中提出了“法治”这个概念,其中关于“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论述,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滥觞。儒法合流,而有荀况,“治之经,礼与刑”是他的名论,“德主刑辅”的思想由此形成而亘延了两千余年。《荀子》三十二篇,大多是文意隽永的篇什,如《性恶》《劝学》《天论》等篇,我读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
近些年出版业猛进,虽然垃圾累累,却也出了很多好书,包括一批西方思想家名著的译本,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英国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美国庞德的《法律的任务》等,都是我研习法律的必读书。至于我国先秦诸子的书,更是已有多种版本,其中不乏精制。新版本的书看来版式时尚,清晰便读,但我还是爱看旧版本,以为先前的文字更可靠一些。手边的一本《先秦诸子文选》,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繁体字竖排,选取了十家五十篇学术性较强的诸子名作,题解和注释简明扼要,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本。我国古代的法学经典,如《唐律疏议》和《名公书判清明集》,我购有新出版的点校本,也有旧刻本,阅读时便于参照。
工作任务繁重时我常常感到疲惫不堪,这时看看书不仅不会增加疲倦,反而会顿感轻松。如果说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常常是烦躁之事,那么读书便是清静;如果说工作中不免会有纷扰焦虑,那么读书便是无忧;如果说官场上难免逢场作戏,有一些世俗习气,那么读书便是高尚。总之,身为公职人员务须尽职尽责,因而身不由己,但也不能完全陷入到事务中,摆脱不出来就没有了自己,没有了个性,没有了生活。读书是一个摆脱烦务的途径,是从繁忙中挤出来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是在工作之外开辟一个空气清新的境界。
工作之外开辟一个读书境界,可以让人调整身心、冷静头脑、舒缓步履,我感到很利于适时总结经验,避免失误,稳健推进其事。我将工作体会和读书心得结合起来,经常写一些随笔小文,并出版过几个集子,其中有两本书或许算是专著,一本是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犯罪预防新论》,一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治文化丛谈》。《领导者》杂志李文子主编看到《法治文化丛谈》中关于山西近现代法治的文章很感兴趣,转载了近两万字,其中实际没有多少论述,主要是我平时阅读中积累起来的资料。
太极仙林,读书佳处
坐落在北京西郊颐和园北门外的中央党校,是一所培训干部的学府。在那里除了听课之外,可以得到充裕的阅读时间。图书馆富藏书籍,凭借书证一次可以借书五本,而且在阅览室密布的书架间可以随意浏览和取阅。党校的学员未必都爱读书,将进京学习当作攀附关系的机会,用心只在仕途而不多看书的人也是有的。而对于喜好读书的人来说,便能感受到中央党校的那种阅读条件是别的地方所罕见的。
我在省政法机关工作期间,有幸三进党校。1985年初入党校,培训半年,其时正值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那场激战之后,我很关注预防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并勠力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工作。为此,那半年中读了不少社会学、犯罪学和刑法方面的中外论著,记了不少笔记,写了一些相关论文。1994年第二次入党校进修,形势处在市场经济的空前冲击下,我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深感法律的不适应和体制的滞后,我的读书与写作集中思考着一个问题,即法律制度的改革。当时,我写的论文中有一篇发表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三次上党校的时候,我已接近退休年龄,脑子里已不多思虑工作,从图书馆随意借一些书看,三教九流的东西都有。那年从玉兰绽放的春天,到玫瑰飘香的夏日,留下了一段自由自在的读书生活的记忆。
校园中原有一片自然的湖水,湖畔立着一栋古代的牌楼,后来经过整修,牌楼到了湖心岛上。每从水边走过,牌楼上面“太极仙林”四个大字便会赫然扑入眼帘。牌楼是建校之初从故宫后面的大高元殿移过来的,“太极仙林”据说是明代严嵩所书。我没有推究过这四个字的涵义,但觉得这牌楼为党校增色不少,周边碧水清澄,林木蓊郁,花香鸟语,让人有如临仙境之感。这天我在园林中一个幽静处坐下来,轻轻打开了《楚辞集注》,曾经读过多遍的《离骚》这时似乎又产生了新的诗意。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既有“内美”,又重“修能”,披挂香草、佩戴秋兰正是他的美德和高尚的象征。“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这是屈原在呼吁抛弃腐败,改革政治制度,他愿意先乘骏马驰骋,在前面为我们引导开路啊!“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想让太阳停止下来,以便能在漫长的道路上努力去寻求和探索。他所求索的是什么呢?是举贤授能、明修法度的美政,是一个法治开明、正气张扬的人类社会。这几句诗曾经被鲁迅题在小说《彷徨》的扉页上,正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美好理想一直像神箭一般射入在国人的心中。
鲁迅将《史记》与《离骚》并论。他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我曾经通读《史记》,其中《屈原贾生列传》是我喜爱的篇章之一。尤其是读《报任安书》,司马迁身上所凝聚的屈原精神给人以很深的感触。司马迁述史和屈原赋骚都是由于“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因而追述往事,留给后人,以使他们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精神能够流布人间。如果把鲁迅的话翻过来说,《离骚》就是“诗家之绝唱,有韵之《史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们无虑于自身的灾祸,所担忧的是国家的命运,忍辱负重正是显示着他们内心的修养,他们所追求的“修名”是一个完美的灵魂,一个伟大的人格。
现代作家聂绀弩,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他写过几首歌咏屈原的诗,有句云:“牢骚肠肺谁千古,莽荡乾坤一左徒。”“奇气胸中久郁盘,汨罗江水几时干?”“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天地间。” 聂绀弩感仰屈原和《离骚》巍然雄立在莽荡天地之间,诗中表达了深情的赞颂,而同时又不禁流露出自身不遇的感叹。我读聂诗,感觉到聂绀弩的胸臆中也有奇气郁盘,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人那个千古不散的灵魂。
那时我手边正有一些聂绀弩的资料,并陆续写过多篇小文,于是产生了联缀成一本书的想法。中央党校那片湖水名之为掠燕湖,湖的西畔耸起的小山名之为千萃山,就在这燕湖萃山之间,我读着,沉思着,拟出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提纲。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在看书或是浏览报刊时,遇到好的诗词或警句,会随手记下来。但因工作忙乱之间,并没有形成整齐的笔记,有时写在纸片上,不免常常遗失。及至退休之年,解脱繁杂事务之后,安坐下来翻阅以前的笔记,发现所记的许多诗词都是历史事件的表述,足可以整理成一部史诗。为此,我又进一步展开搜集,选取了自1949年至2009年六十年内的近三百家诗词作品,计四百八十余首,按照历史顺序逐一评述,编成了《六十年史诗笔记》一书,由作家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我在《前言》中写道:“这六十年历史,犹如一台闳闳大观的多幕剧,帷幕甫落,而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栩栩然尚在眼前。”“而这个时代所留下的诗词作品,又恰似一面历史的长镜,反映着其间所发生的每个具体事件和整体历史风貌。几乎每一个年份、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次社会变化,都在诗词中得到了敏锐而深沉的表达,这大概是别的任何文学品种都未能做到的。”
在上世纪初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中,新诗应运而生,古典诗词在强大的文学革命潮水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然而,中华诗词毕竟是传统文化中的“国香”,它是不会凋谢的。对于那些坚守在千古传统的田园里默默耕耘的诗词家,我由衷钦佩,张伯驹就是其中一位崇尚旧学的文化名士。我在阅读《张伯驹词集》时,感想甚多,于是着手搜寻资料,撰写了《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
张伯驹身世经历中,涉及诸多司法问题,因而在写作过程中我又复读了关于民国时期的司法历史书籍。清朝末年曾诏令实行新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制定宪法提上日程,同时推出各项现代法律,为我国走向现代法治社会开了先河。进入民国,“主权在民”的宪政思想一时成为主流舆论,司法独立的原则也得以通行。但在后来政局的复杂变化中,民主法治的进程经历了曲折和逆转,同时引起了思想文化界观点歧异、派别纷呈、论争不休。对于民国时期的法治文化观念,我在《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略有述及。
梁启超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法律的论述,一度颇有影响。他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之唯一主义”,他还在早年撰写的《论中国宜讲究法律之学》一文中说:“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可知其学贯中西,多有深论。我记得大约是初中一年级课文中,有一篇萧三写的韶山的故事,写到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读的书中就有《饮冰室文集》,从那时我就知道了梁启超其人其书。现在我读的《饮冰室文集类编》,是在旧书市场上淘来的民国早年印本。此书中可读到《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讵子卢梭之学说》《法律平谈》等法学论著。
在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界,胡适是一个重要人物。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中,知识界在文化与政治的诸多问题上展开过激烈论争,在中西文化论争中胡适主张西化,在民主与独裁制度论争中胡适持民主论。正当蒋介石政权背离民主、走向独裁的时候,胡适的一些文章应该说是具有反专制的积极意义的。我在校学习的年代,胡适是被批判的一个反面人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见到胡适的书,陆陆续续看过他关于文学革命和政治论争的一些文篇。
张伯驹是不同于梁启超、胡适的另类学人,他没有出过国,也从来不谈西学,他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中国的读书人。他三十岁之后就不再过问政治,一生兴趣有三:一是诗词曲赋,二是京剧,三是中国书画的收藏和研究。三者以外诸事并不用心,性情淡泊常常有若世外人。张伯驹著述不多,除诗词以外,有《春游琐谈》《京剧音韵》《红毹纪梦诗注》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等。读其诗词,观其行藏,足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魅力,这也是他受到人们敬慕的原因。
其实,凡中国的卓越学人,都会具有传统文化的魅力。梁启超、胡适虽然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许多主张倾向于西化,但他们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其渊源与基础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的那些政治的、文学的理论观点逐渐被历史消磨、淡化、遗忘以后,如果还能留下些什么,那就只有他们遗魂中的那种中国文化的魅力了。
还家读尽旧藏书
爱看书必爱买书,我住太原后小河多年,书店就在附近,每星期日逛书店手不空返。当时上肖墙巷口还有一处专卖古旧书籍,后来迁至桥头街,我在那里买过一些古时的线装书。到了北京常去涵芬楼,或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看古书。家里书多了,堆放很乱,有些书买了并没有好好看过,有时想看又找不见。退休以后正在逐渐整理,看看那些没有看过的书。
古旧书籍中有些是我的珍藏,如在上肖墙店里买的“前四史”(《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是明代汲古阁版;从地摊上淘来的《红雪楼九种曲》,是学校图书馆流散出来的,清乾隆蒋氏红雪楼原刻本。1936年上海万象书店出版的《现代创作文库》,包括二十位现代作家的选集,经数年间在书摊上寻觅,终于陆续买全了,其中如王独清、张资平、庐隐等几位作家的选集都是前所未见。偶尔翻翻古旧图书,有些古色古香的感觉,颇能欣然自得。
由于逛地摊买旧书,不知不觉间又喜欢上了别的收藏,譬如书画、碑帖,以及文房中的砚台、印章之类。我买书画有自己的偏爱,侧重于那些书写有诗词名文的作品,如有山西近代学者常赞春的隶书条屏,写的是郑康成的《毛诗谱序》,既欣赏了书法,又学习了古文。市场上买到的碑帖,多是新拓,价值不大,但有些古碑拓的临摹或影印本也小有佳趣。我收的古旧印章较多,为此写了《读印随笔》一书,自序说:“平生好读书,而今目力不济,偶尔发觉读印胜似读书。”迟暮之年,读印、读帖、读字画,成了我阅读的重要内容。
进入收藏界之后,又必须阅读种种有关收藏知识的书籍,包括古籍版本、书画鉴赏等。因为研究碑帖和印章篆刻,近几年我费功夫最多的是钻研古文字和金石知识,《说文解字》和《六书通》翻来翻去,而且不得不下力学习甲骨文和金文字汇。中国文化是如何的博大精深,如果读了“四书”“五经”还体会不深的话,接触了金石学的时候便会让人发出无穷的感叹。
“还家贫不死,读尽旧藏书”是陆游的诗句,出自他晚年写的《日用四首》。陆游致仕回家之后,与高官厚禄的豪门相比,居处诚然清贫,但在衣食生活方面并不至于艰难。“还家贫不死”句中一个“贫”字,实际是他孤独心境的反映。我退休之后,社会交往渐少,基本是闭门读书,不上网,不会玩微信、博客之类,不喜欢当下的文风,大多时间钻在古旧书籍和古玩收藏中,感觉很落伍,跟不上时代潮流,却也只能自适而已,因而,陆游的这两句诗颇能引起我的共鸣。“读尽旧藏书”的退休生活其实并不寂寞,孔夫子说得好:“乐亦在其中矣!”夏日在树荫下看书,看着看着朦胧入梦了,我有小诗记之云:“把卷斟茶红药边,频飞粉蝶舞襟前。名篇诵罢蝉声静,树下颓然入睡眠。”躺在床上读《山海经》时,也曾随手写道:“窗上雨霖铃,床头山海经。梦魂何处往?造化本无形。”再如读《世说新语》及重看《文心雕龙》时,都写过这种小诗:“征尘自苦辛,书卷老吾身。灯下读名著,权当看美人。”“园静偶鸣禽,携书坐绿茵。文心宗大雅,经典读如新。”
如果从我上初中时始读现代文学作品算起,至今有了六十年的阅读生涯,看书不少,成效不多,嗜好不改,常以“书呆子”自嘲。从事几十年政法工作,国家实行《法官法》时授我为二级大法官。为此,我表白自己的身份即是:一级书呆,二级法官,三级作家。
作 者:寓真,本名李玉臻,文学批评家。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