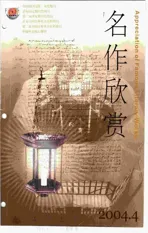潜泳者归来——评诗人郭建强和他的《昆仑书》
2016-01-28青海丨马钧
青海丨马钧
潜泳者归来——评诗人郭建强和他的《昆仑书》
青海丨马钧
摘 要: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郭建强,虽然成果不算丰富,但出手不凡。继《穿过》《植物园之诗》之后,他带着他的第三本诗集《昆仑书》不动声色地归来。诗集中所体现的文体自觉、“粗犷”与“蛮横”的语言与运思的创造,都让郭建强的诗成为了独特而不凡的文本佳构。
关键词:郭建强 《昆仑书》 颂诗
1
之前我虽说相继阅读过《穿过》《植物园之诗》,可这回读完新结集的《昆仑书》,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郭建强骑乘的所罗门飞毯,早就飞临于文学王国中那些林立的辉煌殿堂。
从郭建强握笔写诗的上世纪80年代算起,他把生命行程中的一多半时间毫不吝惜地献给了文学。这期间他也在诸如《诗刊》《花城》《上海文学》等名刊间歇性地亮出过他非同凡响的诗歌面孔,但是回馈给他的反响,还没有和他钻石般闪烁的诗歌光芒相匹配。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他更多是在扮演一个文学潜泳者的角色。如果不是2009年夏天青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星宿海丛书》让他的第一本诗集《穿过》得以面世,他肯定还会把他在文学界露面的时间推后。
现在,他是带着非同一般的身手和他的第三本诗集《昆仑书》不动声色地归来了。他锉刀般粗粝的面孔,铸铁般敦实而略显发胖的身架,大车间钳工般瓷实的腕力,“无产者”舒坦憨实的微笑,活脱脱地还保留着大工厂劳动者的范儿。可这些信息,仅可充作他的一面浅浮雕而已,他身上隐藏着更内在、更有力的东西:奇崛、峥嵘的文学棱角。
2
在郭建强的诗集《昆仑书》里,打头阵的一个作品类型是“十二颂”,像是献给一年的光阴中十二个月份的象征性颂词。颂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但流传至后世被人传颂的诗篇却少之又少。我们最久远的诗集《诗经》,早就有风、雅、颂之别,颂是“诗三百”中篇数最少的一类,周颂、鲁颂、商颂加起来,也不过四十来篇。由于它最初的功用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是“粉饰太平的庙堂乐章”(程俊英语),因此它最初的声音是国家主义或宗族主义的吟唱。而以个性主义为根底的诗歌,则与此相背而行。“颂”体诗原本用于歌功颂德的主要功用,在漫长的时光中几乎被磨损殆尽。事实上,诗歌的独特使命,就是为世界、万物、生命而歌颂,它独特的韵腔也应该是因感念着什么、热恋着什么而情不自禁发出的那种吟诵的声息。只可惜因为每况愈下的世界的沉陷、人性的沉沦、自然的衰变,全世界的诗人仿佛都变得难以直接去歌颂世界了,他们一个个目光忧郁,眼帘低垂,脑颅沉重。于是,作为诗体的颂诗,在现象上日益成为“孤品”和“绝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估郭建强的“十二颂”,我们才能准确地掂量出它们不容小觑的分量。而且我还认为,“十二颂”有着恢复诗歌久违了的质朴机能、纯真价值的特殊意味。
看看这些颂歌篇目,《雪山颂》《戈壁颂》《草地颂》《矿山颂》《蝙蝠颂》《离开颂》《神秘颂》《格萨尔颂》《探入颂》《春天颂》《寻找颂》《山野颂》,其中除了对自然、人物、动物、季节这些属于传统题材的客观物事进行歌颂外,像《离开颂》《探入颂》《寻找颂》则属于现代诗歌在题材上的一次开边拓疆——它们把赞颂的目光转向人的精神、心理、行为世界。
我必须亮明,“颂诗”在超出了文体诗学这一单纯的规范层面之外,它还有着自己来自形而上学的、审美伦理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严正依据。这也就意味着享有夜莺之誉的诗人,本质上是个世间的歌唱者。郭建强作为一个虔诚的诗歌信徒,很快就辨认出诗人身上的一种神秘力量。由于受到此一力量的加持,他向人们毫不含糊地宣告他诗学的根本宗旨:“这种力量在人流中准确地挑选着它的信徒。它不关心信徒在现时现世中的遭际命运,它只要求他歌唱,尽一切可能将世界精确为诗。”
郭建强所熔铸出来的颂体诗学,无论在成色上还是在音色上,都在努力还原着善恶悲喜交织共存的复杂世界及其真相。他摒弃了以往颂体诗里像感冒一样四处传染着的那种具有浅薄、天真、廉价、粉饰等病毒体征的乐观精神,或者换句话说,他从不会为了提高积极情感、正面价值在文学表现上的锐化效果,而把与之粘连的消极情感、负面价值粗暴地加以剥离、模糊、割除。如此,不但是他的“十二颂”,而且在更广大的范围,在他目前所创作出来的全部诗篇中,他已经把“赞颂”作为他诗歌的基因,植入到大大小小的诗篇里——尽管许多诗作不再冠以某某颂的文体标签。
3
“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因为向你流来的永远是新的河水。”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一句哲学格言。我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会晤中,诗人郭建强被他的思想深深击中,他被唤醒的同时又再一次被强化的关于“变化”的意识和理念,让他在某一天按捺不住地写下他目前最长的诗篇——二百五十行的《残片:赫拉克里特》。他表现出的沉思与思辨,他迸发的哲思与激情,是当代诗坛罕有的一次歌咏。辛波丝卡只有短短十八行的《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相形之下,仿佛只是挽着裤腿的一次涉河,而郭建强则是浮游在那哲思的洋流里。我目前还不能够准确概述出这首诗的主旨,我只是觉得它旁逸斜出的主题,就像每一段波流辉映出不同的光色一样。他如此着迷于这样一位哲学家,就像一只蜜蜂对着一朵奇美之花的叮咬,他一会儿探入内蕊,一会儿又盘旋于花朵之上,一会儿又贪玩似的飞到童年,飞到草地,飞到星空下仰望,飞到牛与苦豌豆那里,飞到掘金者那里,中间又不停地绕飞回来。漫漫三千年的时光,他搭乘了一种神奇的飞去来器,浮想联翩的脑电波在思维中脉脉闪烁。
可以肯定,变化的意识、变化的形态、变化的无所不在和无所止息,让郭建强找到了他诗歌不竭的蜜源。它们不但促成了他繁杂多样的诗歌题材,在更深层面上,在他的诗歌语言的结构和诗歌文法上,也显现出直接的征象。在这里我想就其中他特别擅用的一种语言类型做一点提示和初步的阐释,这种语言类型就是他诗歌中以虚词“而”起句的“而字句”字法。
《穿过》——
“而篝火为什么不熄呢?草木锈蚀……”(《青海湖畔沉思曲》)
“而你的呼唤使无数黑暗岁月/丧失魔力。”
(《深秋十四行(组诗)》)
“而我必须承担生活/尽管内心不屑一顾”
(《几乎》)
《植物园之诗》——
“而我的记忆烈焰熊熊……”(《忆》)
“而结局怎能优美……”(《蓦然回首(组诗)》)
“而她再也不能沉默/而她必将冲出群山的丛林/而她的使命就是将生命流布……”(《鄂拉山侧:正在解冻的冰河》)
《昆仑书》——
“而移民们坐在黄昏里摇摆歌唱/这些被鹰隼从黑海夺来的幼子……”(《草地颂》)
“而你知道鸟鸣和花香只是一划而过而你知道挣扎和呼告来自膝盖和颈骨,也是最恶的……”
(《陶匠》)
“而抽筋似的好声音一鞭一鞭抽打得满天星斗聚散不定/而绳索似的好声音牵引你们的身子前倾卧倒摇摆跳跃……”(《合唱》)
以上诗句撷取自诗人的三部诗集。这些“而字句”都是在一首诗的开头部分“突然”出现的。它们像半路猛不丁杀出的程咬金,像一队彪悍响马的突然出击,更像一个隐去了前世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们显示出语言的一个钻石棱面陡然向另一棱面的闪转。它们永远带着点不言自明的心照不宣,带着“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钱锺书语)。
故意省略上下文之间正常的语句衔接,有意制造语义的裂隙,制造不完整的语言结构或篇章结构,这是诗歌这种语言艺术在语法、修辞上所获得和享有的一项特权,一种与诗歌固有的简约风格里应外合的诗学现象。
我们不能简单地或想当然地以为以“而字句”起句的“字法”是个现代诗歌的发明,它其实有着更为久远的赓继。钱锺书先生早在他的《谈艺录》里,通过“而”(我)的用例,得出一条前后相承接的诗歌链条,大致是由陶渊明到李白,经韩愈过渡到宋代王安石以下,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只有在这么广阔的文学时空和文学传统里,我们才能更加分明地看到诗歌语言与表达的前世今生,甚至看到它的来世。
但古今诗歌省略文法的细微差别是,现代世界更加强调事物的突发性和偶然性,还有事物的转折性、读者的参与性;或者反过来说,郭建强更善于从突发性和偶然性、转折性中,把世界敞开,把意义呈现,为此我们只要细细体会他在《塔尔寺:酥油花》一诗里出现的十六个“突然”,就能心领神会他的这种字法的峻利闪转。
我想其字法修辞的来源,定与他在现代世界频频遭遇的突如其来的事情所给予内心的突兀震荡息息相关,或许也跟他曾经在电解铝车间一次次猛然惊醒的经历遥相感应。
4
作为诗人的郭建强,像威廉·布莱克一样,具有“一种臆造幻象的天赋才能”(艾略特语)。这种幻象,时而以梦境的形式出现,时而又以镜子和一切具有照见和折射事物形象功能的镜像得以体现。如同艾米莉·狄金森把“恐怖”“着迷”“欣喜”这些体验统统混融起来一样,郭建强在对镜子既拒又迎的矛盾体验中,获得了神奇的点化。从此,他就好像发现了屡试不爽的诗门秘笈一样,只要借用一下镜子的斜射、折射、反射、转移功能,整个诗歌的意象和意境马上就会显现出超人意表的陌生化效果,世界好像以崭新的形象重新来过。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一点看成是郭建强诗歌的一个修辞技法,那就和他整个的镜子诗学和诗歌认识论的深刻性和广延性失之交臂了。看看《神秘颂》里的这么一节诗句,大家一定会心悦诚服于诗人诗思的神妙、灵异和诗歌视觉的精微别致:“你在波状的风里凝视自我面孔的粼粼波动/一枝烈香杜鹃用她细长的花柱追问叹息//在一头牦牛的眼瞳站着木呆呆的你/一座侧身而过的金雕用他的眼神描摹着你。”
以曲喻法获得的波状之风映出粼粼波动的面孔,牛眼、金雕之眼反映出人的形象,反过来也是说人眼看到了牛和金雕,这种双映效果正是镜子、镜像的魅力所在。可是仅仅知道从一面玻璃镜子观照自我的人,是无法发现他周围那些无所不在的“镜子”的,他不懂得人与物之间,永在着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但他必须做到双向的互动,必须熟谙诗人移情的秘法,方能“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5
作为诗人,他十分清楚词语之于诗人、诗歌的意义。2013年他应某诗歌节之约写下《从时代挖掘出通向无限的词语矿脉》一文,他在其中明确表达了他的诗歌语言观和价值评判标准:“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参照谱系和炼铸词语的秘密……衡量一个诗人成就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词语烘焙的专注程度和技艺,端给读者的词语盛宴的质量。在此,我把纯诗视之为诗人对词语的某种至善至美的排列的追求。”“烘焙”无疑是这段文字最惹眼也最响亮的一个词语,因为它原本属于食品加工的一道工艺,现在把它用到诗人对词语的锤炼上,不仅新颖,而且让精心处理、推敲后的词语有如食物一样,更富有营养,更易于吸收,并具有良好的口感和色泽,这就把词语经过一定时间锤炼而提升了表达质量的性质,说得更加亲切、熨帖、准确。
《昆仑书》中,他把这种词语活用的修辞美学,由传统诗词体现在只言片语上的句子单位(即所谓字眼、句眼或炼句),发展到完整的篇章单位;由局部一枝独秀式的语言修辞魅力,扩展为繁花竞秀式的语言修辞魅力。《删改》和《导语》这两首诗作,是实践这一语言修辞美学的典范。以《删改》一诗为例:
你要相信所有的消息都需要删改/所有的想法也是/你要相信没有删改就没有除暴安良丰衣足食/欣欣向荣的农场恰恰来自一遍一遍的删改/你要明白你的血液每天都被空气和梦境删改/一个小小的喷嚏就会把月亮删改得面目全非//你要看清就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的工业臭气/同样是你我删改的结果//你以为你的爱的根基在于你的DNA?/删改让你的爱人变得和初春一样可爱//——何况一段导语一则消息一篇四分五裂的文章?/删改是必须的删改蹬踏最性感的高跟鞋删改抖乳摆臀/向你走来向你致敬为你臣服雌卧/看着显示屏看着桌子看看眼睛看看闪亮的门齿/看看,无所不在的顺光逆光反光到处都是真理之镜//只剩下一排排肋骨/骷髅还就着秋雨相互删改自我审定
这完全是“删改”一词演出的一幕诗剧:从原先词语属对的“从一而终”,走向一次次截然不同的“婚外情”。十七行诗句,出现“删改”一词竟多达十二处(一处使用了省略),其中只有两处沿用了“删改”的本义——对文章多余或不要紧文字的删削、改动,其余十处“删改”的面目俨然词语的川剧“变脸”和“百变金刚”,词义随着语境的不同不断翻新、变化,新意纷披:镇压,维稳,革命,改革,篡改,社会治理,意识改造,灵魂侵蚀,工业污染,爱情感化,话语阉割,精神的自我整容,对性感诱惑的驯服与压抑,秉性因受到环境、心境影响以及偶然性、非理性因素影响所发生的随即改变……仿佛诗人带着不可遏制的愠怒、讽刺的笔调,一股脑地让“删改”一词变声变调,又像多声部音乐众声混响,穷形尽相地衍生出世间百态。
不能轻忽作为结语的最末两行诗句:“只剩下一排排肋骨/骷髅还就着秋雨相互删改自我审定。”如此奇崛、幽冷的画面,显然是延续了卢奇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审视灵魂的天才们所具有的批判意识,只有这类深深遭遇过人生之恐怖、绝望、战栗、痛楚、阴鸷、恶心的作家和诗人,才可能在他们的灵视里营造出如此“异乎寻常的境遇”。诗人不仅揭示了“删改”在空间上无所不在的分布,更是透析出“删改”在时间上漫长无尽的流转。这种刻毒、尖锐、清醒、异质的审视,把“梅尼普体”式的讽刺、闹剧、怪诞引入了诗歌,更重要的是他把巴赫金所津津乐道的“杂语”“复调”引入了诗歌,如此他才会异常警醒地揭示人的精神境遇,揭示存在,揭示社会。
耐人寻味的是,“删改”和“导语”全都来自诗人所从事的编辑职业,是媒体行当口滑耳熟的常用术语。诗人将它们凝练为“诗语”,背后必是隐去了各种不愉快、压抑、隐性病症等复杂、纠结的体验,这样,他就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在词语的反抗力上,寻找到了一条以冒渎反抗冒渎的解放途径。他把词语的受伤、扭曲、瘟疫般的感染,变成了词语的侵略、词语的爆炸、词语的燎原式燃烧。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把词语的侵略变成词语的控诉,词语肆无忌惮的撒泼,浑融出生存所能容纳的全部的戏剧性和全部的荒诞性。
郭建强在词语上所获得的语言自觉带给他的那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让他诗歌中的遣词造句,他的运思,体现出罕见的“粗犷”与“蛮横”。他几乎让他笔下集结的词语,像摇滚和街舞那样恣肆地炫舞起来,像狂欢节上暂时放下礼节和教养的人们,在解除长期的拘谨对他们所形成的压抑之后,做出他们平时不敢做出的表情一样。他们在那么一个狂放和不拘礼数的时刻,忽然迸发出的生动、有趣、可爱、灵性以及崭新的、洋溢着全部生命之美的雅驯与亲和,完全盖过了此前所有被人们习以为常了的价值所能传递给人的愉悦感。郭建强就是以这种诗人的强力意志,带着狂野风暴般舒展的气势,驱散掉我们身上那惰性十足的审美疲劳,让词语一个个欢欣地受孕,也让它们经受一次次汗水淋漓的分娩阵痛。他已经习练出了一套让陈词滥调刮垢磨光的诗艺。
郭建强的语言,当然也会经过一番钉钉邦邦的敲凿。与一般偏才诗人有所不同的是,他会把男性的粗豪作风、北方人的大刀阔斧,与女性的细腻优雅、南方人的精雕细刻,结合到他对词语的熔铸里。中国古典诗艺在炼词、炼句、炼意、炼境方面所达到的那种深湛而精微的诗学境界与语言修养,与西方诗歌触探人性的锋锐不断激荡、磨砺,让词语的奔流日益声势浩大,直到磅礴的声波,震颤在我们神经末梢。
作 者: 马钧,青海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报媒,业务从事散文、随笔、评论写作。代表作有《越界的蝴蝶》《文学的郊野》等。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