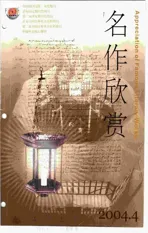重估俄苏文学(十四) 对前现代生活的不满与焦虑——论《死魂灵》(上)
2016-01-28北京丨李建军
北京丨李建军
重估俄苏文学(十四) 对前现代生活的不满与焦虑——论《死魂灵》(上)
北京丨李建军
摘 要:本文以“前现代性”为切入点,通过与俄罗斯作家的比较,说明了果戈理的独特个性。此外,本文通过对《死魂灵》文本细节的考察,揭示了果戈理对前现代俄罗斯的“庸俗”等社会现象的讽刺和嘲笑,分析了他的文学感受力的成因和特点,阐释了他的主观而直接的介入方式和感伤而温暖的抒情方式。
关键词:作家 庸俗 笑 感受力 介入 抒情
唯独你,诗人,掌握飞翔的音符,
能够让心灵含混的梦呓突然凝固,
能把茵茵青草的幽香谱入诗篇;
这倒像丘比特的神鹰追逐乌云,
离开荒僻峡谷醉心于长空无垠,
转瞬之间能用利爪捕捉住闪电。
——费特:《我们的语言多么贫乏!……》(1887)
1842年3月21日,经过书报检察机关四个多月的刁难和折腾,《死魂灵》终于出版了。赫尔岑说:“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这是对当代俄国一种痛苦的、但却不是绝望的责备。只要他的眼光能够穿过污秽发臭的瘴气,他就能够看到民族的果敢而充沛的力量。”①的确,这是一部俄罗斯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伟大作品。它不仅包含着对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人的尖锐批评,也包含着巨大的净化力量和照亮幽暗生活的灿烂光芒。
1842年这一年,应该被命名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元年。《死魂灵》改变了俄罗斯文学前行的路向。从这一年开始,直面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诞生了,针砭现实的文学经验模式成熟了。俄罗斯作家谢德林指出,果戈理是“俄国文学的新倾向的鼻祖”,“以后所有的作家有意无意都是跟随着他的”②。赫拉普钦科则说:“……果戈理本人就是一个派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非常强大的派别的奠基人。”③他的确是一个开创性的、独特而强大的作家。
1842年,杜勃罗留波夫六岁,托尔斯泰十四岁,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四岁,涅克拉索夫二十一岁,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一岁,屠格涅夫二十四岁,冈察洛夫三十岁,别林斯基三十一岁。在最渴望阅读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们便能读到《死魂灵》这样的伟大作品,多么快乐和美好!对那些以批评为事业的人来讲,能以这样的作品作为评论的对象,更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
别样的作家与崭新的道路
真正的文学,既不甜蜜,也不轻松,而是苦涩和艰难的。它是严肃的责任和沉重的使命。作为人类生活的审查官,作家必须用更加严格的尺度来审视生活。作为人类精神病痛的观察者和诊断者,作为对命运不公和社会不义的批判者和抗议者,他们对人类的不幸和痛苦特别敏感,往往体验着比别人更多的疼痛,心理状况和人格状况也比其他人要更复杂一些。
那么,他,爱嘲笑的果戈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与别的俄罗斯作家比起来,他在个性气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学精神等方面,到底有何不同呢?
果戈理是情感丰富的感伤主义者,性格有些孤僻,不习惯群聚,但又常常被孤独的痛苦折磨着。他适应不了俄罗斯的气候,讨厌令人烦恼的社交和是非,以至于要适彼乐土,去国远游,但又发疯地爱着俄罗斯,去国愈远,思念之情愈浓。他是生活方式上的西方主义者,同时,又是情感方式上的斯拉夫主义者。他对俄罗斯爱恨交加,既嘲笑,又赞美。他尖锐地批判俄国官僚主义,却不仅很少怀疑俄罗斯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而且对沙皇、沙皇制度和东正教,还颇多认同,甚至一往情深。
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比起来,果戈理的写作显示出一种崭新的维度和品质。他比普希金更具丰富的现实感,更具介入社会的批判精神,正像别林斯基深刻指出的那样:“果戈理比普希金对于俄国社会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因为果戈理更加是一个合乎时代精神的诗人;他也更不容易在他所创造的客体的多样性中茫然自失,却更容易使人感觉到主观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应该是照耀我们时代诗人自觉的太阳。”④他比莱蒙托夫更开阔,更深厚——如果说,莱蒙托夫更多地满足于在月夜吟唱爱情的咏叹调,那么,果戈理则完全摆脱了叙事和抒情范围的狭窄性,坚定地将文学的触须伸向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广阔的领域,“勇敢而直率地注视了俄国现实”⑤。
他向往西方,在十二年的时间里(1836—1848),基本上都生活在意大利和法国,但又不是屠格涅夫与赫尔岑那样纯粹的西方主义者。他眷恋俄罗斯,感伤地抒发对它的思念,但是,又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是绝对的斯拉夫主义者。在对宗教和现实的批判态度上,他有点儿接近托尔斯泰,但又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具有反叛精神。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行为,更具异端性——他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并且敢于以尖锐而直接的方式,谴责政治腐败,质疑宗教体制,批判道德堕落;比较起来,果戈理对宗教的态度就更柔和、更虔敬:“我听命于那种不取决于我们,但按照那个人的意旨而产生的普遍要求。”⑥而且,对自己的道德修养,他也有着极高的要求:“我的心灵应该比高山上的雪更清洁,比天空更明朗。”⑦
他像契诃夫一样,善良而忧郁,幽默而悲观,只是,他比契诃夫更敏感和脆弱,也比契诃夫更热烈和外向。厌恶庸俗的心理和病态的人格,批判落后的前现代生活,是他与契诃夫的共同态度和立场。文明和教养,则是他们的几乎所有讽刺性作品共同的母题。面对现实,他们都一样地主要是从人格和教养的意义上批判它,而不是单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批判它。只是比较起来,果戈理的讽刺和嘲笑,却比契诃夫更辛辣、更尖锐。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作品中,他怀着一种深刻的焦虑、强烈的厌恶和深深的悲悯,来表现俄罗斯社会的不文明和没教养。
果戈理希望俄罗斯能实现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能变得更文明,但他却既不是别林斯基那样的民主主义者,更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看见欧洲“在流血”,“她让无谓的斗争搞得疲惫不堪,任何事情都办不成”⑧,并且确信,在俄罗斯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和悲剧,因为,“在我国,人们的兄弟结义甚至比血缘的兄弟情谊还要亲近,在我国还没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仇恨,没有在欧洲常见的那些给人们的团结和人们的兄弟友爱设置不可逾越障碍的恶毒凶狠的党派”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不切实际。俄罗斯人之间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亲近”。加之以诱惑,迫之以外力,他们之间也会产生“不可调和的仇恨”。
关于作家的修养和写作目的,果戈理有着成熟而高尚的理解,充满了现代的公民意识:他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要自我修养成为一个人和祖国大地的公民,然后才能动笔写作。否则一切都会驴唇不对马嘴”。“如果作为同卑劣与丑恶相对立的美好人物的理想形象在你本人心目中尚不鲜明,怎么能把它表现出来展示在大众面前,收到惊骇卑劣与丑恶的效益?如果不给自己提出什么是人的尊严这样的问题,并且给自己多少令人满意的回答,怎么去表现人的缺点和不足?”⑩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如果尚未完成作为“国家的公民”和“世界的公民”的修养,那么,他的活动就有可能是“危险的”:“他的要想与其说有益,不如说有害。在他的笔下无论写出什么东西,这种自我的完善一定要在一切里暴露出来。”⑪作为全新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开启了全新的文学道路,创造了全新的文学写作模式。在评论他的处女作的时候,别林斯基不吝赞词,说他“拥有强大而崇高的、非凡的才能”,“至少目前,他是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⑫;彼得堡大学校长普列特尼奥夫教授也同样高度评价果戈理:“果戈理不仅在艺术上超过了他以前的作品,而且他的天才也普遍高于现在的俄罗斯作家。”⑬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果戈理的确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为俄罗斯作家提供了伟大的文学经验。
在《死魂灵》的第七章,果戈理以他特有的充满激情和讽意的笔调,讨论了两种作家和两种文学。一种作家总是逃避现实,“不曾从高处降临到他的贫穷、卑微的同胞中间去,不曾接触过尘世,而始终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这样的作家“是幸福的”,有着令人羡慕的“好运气”;他的写作是轻松的,同时,“又声誉卓著,名满天下”。他讨好世人,“他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他遮蔽了生活中的愁苦,只向人们展示美好的人品,神妙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所有的人都向他鼓掌喝彩,尾随着他,跟在他的庄严巍峨的车辇后面狂奔。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说他高高凌驾于世间一切其他的天才之上,如同大鹏凌驾于一切能够振翼高飞的禽鸟之上一样。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一颗颗年轻的热情的心就会发生一阵阵战栗,一双双眼睛就会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在力量上是没有人可以和他匹敌的——他就是神明”⑭!显然,对于这种作家,果戈理是极其不满的,他们虽然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受到了读者和社会的消极意义上的认同和吹捧,但是,他们的写作,本质上是反文学的,无价值的。
相反,另外一种作家则是勇敢的、直面现实的,他“敢于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冷漠的眼睛所见不到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掩埋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淖,把遍布在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性格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容情的刻刀的锐利刀锋把它们鲜明突出地刻画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面前”⑮。然而,这样的作家,不仅不会有“好运气”,命运是“另外一种样子”,而且,他还会受到自己时代的迫害,“他必然逃脱不了当代法庭——虚伪而又冷酷的法庭——的审判,他所孕育的创作将被诬称为卑微的、低贱的东西,他将在一批亵渎人类的作家的行列中得到一个含垢忍辱的地位,他所描绘的人物的品格将被强加在他本人身上,他的心灵,他的良知,他的天才的神圣火焰,从此将被褫夺……他的处境是艰辛的、严酷的,他将痛苦地品尝着自己的孤独”⑯。针对那些希望作者“换一种写法的读者”,果戈理这样写道:“是的,我的善良的读者,你们很不愿意看见人的赤裸裸的可怜相。你们会说:‘看这个干什么?有什么用处呀?……您最好还是给我们看一些美好的、有趣的东西。最好让我们逍遥快活一会儿!’”⑰然而,正是这种不怎么招人待见的作家,才是稀有的、真正的作家。果戈理表达了自己对优秀作家和伟大文学的理解,也天才地预见了这种作家的诞生,预见了他们将要承受的充满痛苦和考验的命运。
果戈理无疑属于他自己所赞赏的那一类作家。他的性格和心理,比一般作家更为矛盾和纠结。他是羞怯的,又是勇敢的;是内向的,又是外向的;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喜剧的,又是悲剧的。在他的内心世界和文本世界里,讽刺与怜悯、批判与赞美、疏离与皈依,以一种既冲突又和谐的方式并存着。在文学生涯的最后阶段,他通过出版《与友人书简选》,谦卑地俯下身来,向沙皇鞠躬,向教皇致敬,向俄罗斯献上自己殷切的道德训诲和热情的亲吻礼。尽管如此,他仍然属于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开辟榛莽的伟大作家。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都贡献给了伟大的文学事业。1836年6月28日,他在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从来不曾为上流社会牺牲我的才华。任何娱乐,任何欲望都不能控制我的心灵于此刻,都不能诱惑我忘记自己的职责。”⑱他在文学写作上的艰辛努力,他对俄罗斯社会的冷静观察和尖锐批判,对文明生活的想象,对人物的宽容和同情的态度,全都以一种独特而诗意的方式凝聚在《死魂灵》这部巨著中。
果戈理的题材内容和写作风格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以故乡乌克兰的乡村生活为素材的充满浓郁诗意和浪漫情调的风俗小说,也有《旧式地主》式的朴素的含着同情和感伤的乡土小说,也有《外套》等以小人物的生活为题材的充满怜悯心的“底层叙事”,而他最伟大的作品,却不是这些,而是《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是那些充满反讽精神的现实主义杰作。
果戈理是爱笑的人。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笑声,这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因为,笑是一种高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品质。笑意味着精神的自由和想象的活跃,包含着反讽、嘲弄、否定和拒绝等复杂因素,能给人带来一种充满愉悦的解放感。果戈理是第一流的幽默的讽刺作家,也是第一流的感伤的抒情诗人。他打破了悲剧和喜剧的界限,消除了讽刺与同情的对立。他在作品中所批评和否定的,主要是庸俗的人格和腐败的前现代生活。他用幽默和讽刺,来表达对文明生活的祈向。更重要的是,他能憎也能爱,爱讽刺和嘲笑,但也同情和宽容,正像俄罗斯文学批评家珂德略来夫斯基(Kotliarevsky,今译“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作者注)在给《死魂灵》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这讽刺家其实是一个柔软的,温和的,倾向同情的人,并且知道对于在他的作品里缚到笞柱上去的人,给以公平的宽恕。他还替最邪恶者寻找饶恕和分辩的话,他绝不喜欢称人为邪恶者,就选出一个名称,叫作孱弱者,想借此使读者对于被弹劾和被摈斥的人,心情常常宽大。”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他培养了俄罗斯作家既讽刺又同情、既批判又怜悯的复杂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
然而,可悲的是,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有的充满“喧哗与骚动”的地方,果戈理所批评的那种作家不仅没有绝迹,而且实繁有徒,越来越多——他们是“幸福的”,有着“好运气”,而且“声誉卓著,名满天下”;同时,果戈理所赞赏的、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却并不多见,即便有,也如“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一样,“处境是艰辛的、严酷的”,也在“痛苦地品尝着自己的孤独”。
我们迫切需要果戈理这样的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需要《死魂灵》这样的真正伟大的作品。我们之所以重新阅读和研究果戈理的作品,就是想为自己时代的文学,寻求一些积极的经验支持。
解剖庸俗的前现代生活
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封闭而专制的农奴制国家。由沙皇和贵族阶层主导的官僚制度,依然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安排。对权力的崇拜,对金钱的崇拜,对虚誉的崇拜,是世俗生活中的庸俗不堪的三大“拜物教”。在这样一个滞后而混乱的社会里,特权阶级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腐败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严重现象;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沉闷压抑的状态,到处都是“死魂灵”,普遍缺乏活力和目标感;知识分子也分化为尖锐对立的不同阵营,各持一端,相互攻讦。果戈理将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过渡的时代”⑳。
由于果戈理曾经漫游欧洲,到过柏林、巴黎、罗马、耶路撒冷和那不勒斯等城市,长期居住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以,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照中,他对俄国社会在文明进步上的落后,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为深切的焦虑。如果说,随着抗法大军进入巴黎的俄国知识分子,带回了“十二月党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变革诉求,如果说,随着反击纳粹的红军进入欧洲的俄国军人和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的更加文明的生活,从而带回了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怀疑,那么,果戈理则将自己在意大利完成的、批判俄罗斯前现代生活的《死魂灵》带回了自己的祖国,从而引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界的强烈反应:有的惊喜,有的震怒,有的赞赏,有的诅咒。
前现代俄罗斯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残缺而庸俗的生活。果戈理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种生活的病态和可怕。他要通过尖锐的讽刺来嘲笑它。他希望自己的同胞们能在自己提供的这面镜子里,看见自己粗糙的灵魂,看见俄罗斯社会可笑的面影。米尔斯基说:“他在现实中所关注的层面是一个很难被翻译的俄语概念,即‘庸俗’,这个词的最佳翻译或许可以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自足的自卑’。”㉑果戈理将文学叙事的主题,革命性地转换到了生活的“幽暗面”,转换到了“庸俗”这一主题。他要把那些人们已经习焉不察的可笑、可鄙、可耻的生活放到文学的聚光灯下,按照米尔斯基的说法,“他使庸俗占据了从前仅为崇高和美所占据的宝座”。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将讽刺的锋芒,指向城市和乡村的上层社会,即政府部门里握有权力的官僚和乡村里拥有农奴的地主。这两个阶层的共同问题,就是缺乏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缺乏良好的教养和高尚的生活追求。他们盲目地生活,既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也缺乏对意义世界的向往。他们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吃吃喝喝等原始意义上的需求。例如,索巴凯维奇活着,几乎就是为了吃:“这些家伙开口闭口总是文明、文明,可是这种文明呀——呸!我可说出另一个词儿来了,只不过在饭桌上这么说未免有失体统。我家里可不兴这样做。要是吃猪肉,我就把一只整猪端到桌上来,要吃羊肉,就吃整羊,要吃鹅,就吃整鹅!我情愿只吃两道菜,但是要吃个痛快,心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㉒而乞乞科夫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就是要出人头地,就是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他虽然相貌堂堂,谈吐文雅,但是,从根本上讲,他既没有“发达的智力”㉓,也没有高尚的理想。虽然,他偶尔也能认识到官员们开舞会等所挥霍的,不过是“农民交上来的血汗钱,或者更糟,是咱们昧了良心捞来的钱”㉔,但是,他与他所往来的地主和官僚一样——他们的生活只有一个“中心”和“目标”,那就是占有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多的利益:“人人都在捞好处的呀……我只是吃了点残羹剩肴,在任何人都会伸手的地方伸了手罢了;如果我不趁机伸手,别人也会伸手的。”㉕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就打消了道德上的顾虑,便开始通过做“死魂灵的生意”的方式来骗取财富了。他似乎也没有错,因为,在一个缺乏文明教养的前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只看最终的结果,只崇拜最后的成功者,至于那些攫取权力和利益的成功者是什么样的人,为了获得权力、财富和声望,曾经用过什么样的手段,就不是人们所关心的事情。这样一来,虚伪、无耻和欺诈,成了常见的人格现象和普遍的道德现象。更为可怕的是,面对这样的病态现象,人们视之为一种“常态”,早已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见怪不怪了。
缺乏健全意义上的个性和精神生活,是生活在前现代社会的俄罗斯地主和官僚的共同问题。失去灵魂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非人的生活,甚至是一种“魔鬼”的生活。玛尼洛夫几乎毫无个性,他的性格是“甜的”,随时准备讨好人,甚至多愁善感,随时会涕泪涟涟;他缺乏行动的热情,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采取一种不作为的态度。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农奴有多少人死亡。他几乎毫无读书的热情,“他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本书,书签夹在第十四页,他把这一页经常翻读已经有两年了”㉖。显然,这是一种缺乏意义感和精神深度的生活,是一种缺乏活力的、死亡状态的生活。地主索巴凯维奇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果戈理曾这样分析和评价他:“……他脸上连一丝类似表情的东西都没有。在这个人的身体里仿佛没有寄寓着灵魂,或者他灵魂是有的,但是不在应该安放的地方,而是像童话里那个长生有术的恶毒老头的灵魂那样,不知远远地藏在哪座山岳后面,并且裹着一层厚厚的硬壳,以致灵魂深处无论翻滚些什么念头,都绝对不会影响到表面,产生一丝半毫的震动。”㉗因为没有灵魂,所以,他也就没有人性和同情心,竟然说死掉的农奴“不过是苍蝇,不是人”㉘。同样,吝啬鬼普柳什金只认识“物”的价值,而不理解精神生活的意义。他搜集和囤积一切拿到手的东西,但最终却不是有效地利用这些东西,而是让它们在闲置中腐烂:“所有这些东西全被堆进储藏室,渐渐烂掉,被虫蛀空,连他本人最后也成了人类身上一个被蛀蚀的空洞。”㉙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恐怖的生活状态。与索巴凯维奇和普柳什金在食物和外物上的贪欲不同,诺兹德廖夫的庸俗,主要见之于人格和心灵生活方面:他没有摆脱人格上的幼稚状态,举止粗野,言语粗鲁,随时撒谎,拼命吹牛,说起话来唠唠叨叨,缺乏最起码的教养和分寸感——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的行为,既不尊重别人,也是对自己的侮辱,所以,像索巴凯维奇和普柳什金一样,他也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心人。
在这样的前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人格上的平等。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下,是按照财富的多少和官阶的大小来划分的。果戈理在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比较中,批评了俄国人在对人的态度上所体现出来的市侩主义习气:他们会根据地主拥有农奴(“魂灵”)数目的多少,来调整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即便对两个拥有农奴“数字”接近的地主,他们的说话口气也会有“细微的差别”㉚。乞乞科夫因为收购“死魂灵”而成了空有其名的“百万富翁”,但是,整个N城的人们,却还是“真心实意爱上了乞乞科夫”——“百万富翁”这个字眼,“包含着一种魔力,它既能够刺激卑贱下流的人,刺激不好不坏中不溜的人,也能刺激好人,总之一句话,它能够刺激所有一切的人”㉛。本来,女士们很少谈起他,然而,自从他成了“百万富翁”,情况就大大地改变了。要不是诺兹德廖夫揭穿了他“做死魂灵的买卖”发财的底细,他很有可能会与省长的女儿喜结连理。
庸俗的市侩习气在官员身上也一样严重。遇到官阶比自己低的人,官员便“眼光严厉凶猛如兀鹰”,遇到官阶比自己高的人,则“立刻会完成奥维德所设想不到的变形:变成一只苍蝇,甚至比苍蝇还小,小到变成一粒沙子”㉜!这种面对权力的下作和势利,甚至不是只存在于某一个阶层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俄罗斯现象”:“俄国人便是这样的:他非常爱跟一个哪怕官衔只比自己高一等的人结识相交,和一位伯爵或者亲王的泛泛之交,在他看来也比其他任何亲密的朋友关系好得多。”㉝果戈理对这种毫无尊严的奴性人格深恶痛绝。他以高贵的批判态度审视贵族和权力阶层。他认为他们既不智慧,也不值得尊敬。1833年2月1日,他曾写信给学者和作家波戈津:“为了上帝,您应该给大贵族们增添蠢笨一点的外貌。为了让他们引人发笑,必须这样做。越是有名望,越是等级高,就越蠢。这是永恒的真理!”㉞
在前现代社会里,体制和权力是令人恐惧的怪物。它傲慢而自大,高高在上,睥睨一切,把自己当作社会和他人命运的主宰者,当作一切人间幸福的赐予者,完全不理解平等的意义,缺乏最起码的谦逊的美德和成熟的教养。乞乞科夫在民政厅办理“死魂灵”转卖手续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怪物。这个衙门是一个肮脏的地方,“无论在哪条走廊里,无论在哪个房间里,他们的目光都没有碰上惊人的清洁。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关心到这一层;所以,本来是肮脏污浊的地方原封未动仍旧是那样的肮脏污浊,没有蒙上一层漂亮诱人的外表”㉟。这个地方不仅外在的样子是脏的,而且它的精神也是脏的——上自厅长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下到普通的办事人员,都是一些庸俗而自私的冷血动物。果戈理用戏谑的笔调,描写了乞乞科夫见厅长的情景。厅长像“一轮太阳似的”端坐在宽大的圈手椅里,谈吐和格调与索巴凯维奇和玛尼洛夫们一样庸俗和无见识。他与这些地主和乞乞科夫都是熟悉的朋友,对他们的生活和正在进行的这笔交易,也都心知肚明,却不仅听之任之,竟然还赞赏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的欺诈行为:“好事情!说真的,是一件大好事情呀!”他清楚地了解手下索要贿赂的腐败行为,所以对乞乞科夫说:“一切都会办好的,不过,您不必给办事的人什么钱,这一点我现在就跟您打个招呼。凡是我的朋友,一律不该破费。”㊱在这里,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特权阶层肆无忌惮地掠夺别人的财富:民政厅长洋洋得意地向乞乞科夫炫耀说:公安局长“只消在走过鱼市场或者酒店的时候眨巴一下眼睛,咱们哪,你们可知道,就可以大嚼一顿啦”㊲。果然,没多久,几乎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市场上懂得“孝敬领导”的商人,送到公安局长家里来了。果戈理随即这样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察局长是全城的衣食父母和恩人。他和市民相处得亲如一家,视察起各色铺子和市场来就像在察看自己的库房一样。总之,如常言所说,他是得其所哉,并且对自己的职务再也精通不过了。甚至难以断定,是他为这个位子而生,还是这个位子为他而设。”㊳这样的反讽,尖锐而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俄罗斯社会权力腐败的真相,体现着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良心和勇气。
赫尔岑说:“《死魂灵》,这是充满一种深沉痛苦的史诗。《死魂灵》——题目本身就包含有令人恐怖的东西,否则他就不会这样叫。死魂灵,不是这些户籍登记册上的名字,而是所有这些罗士特莱夫、马尼罗夫以及tutti quanti(所有其他的人)——这才是死魂灵,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㊴是的,这种行尸走肉般的“死魂灵”,近两百年来,全世界到处都有。别林斯基说:“果戈理作为诗人的优点越大,他对于俄国社会的意义也越重要,也越是不能在俄国以外有什么意义。”㊵这回,别林斯基可是说错了,可谓大错特错!事实上,对于亚细亚社会来讲,果戈理以及他的作品,有着同样重要的“社会意义”——果戈理所揭示的前现代生活景观,不仅具有俄罗斯特性和时代特点,而且还具有普遍的人类性、世界性和超时代性。
对于这种落后的前现代社会的生活,无论人们试图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话语来美化它,都无法改变它阴暗而畸形、可悲与可耻的性质。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于缺乏充分的自由和权利,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和制约,有权阶级的生活是恣睢和腐败的,而无权阶级的生活则缺乏尊严和价值感,于是,几乎全社会所有人的生活,都具有非人的“魔鬼”的性质。唉!就像蟑螂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一样,这种庸俗而可怕的前现代生活,也有着惊人的“超稳定结构”,即便在进入数字时代的21世纪,人们还得挨过漫长而痛苦的煎熬,才能最后终结它。
①㊴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52页,第53页。
②米·赫拉普钦科:《果戈理的〈死魂灵〉》,付大工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页。
③米·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刘逢祺、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④⑤㊵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38页,第412页,第438页。
⑥⑧⑨⑪⑳果戈理:《果戈理全集》(与友人书简选),第6卷,任光宣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第204页,第275页,第321页,第319页。
⑦⑩⑱㉞果戈理:《果戈理全集》(书信卷),第8卷,李毓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第409页,第156页,第82页。
⑫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05页。
⑬袁晚禾、陈殿兴编选:《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⑭⑮⑯⑰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㉟㊱㊲㊳果戈理:《死魂灵》,满涛、许庆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67页,第167页,第167—168页,第306—307页,第123页,第165页,第219页,第301页,第24页,第125—126页,第129页,第149页,第55页,第201页,第56页,第19页,第181页,第183—184页,第187页,第188页。
⑲果戈理:《死魂灵》,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3页。
㉑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作 者: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