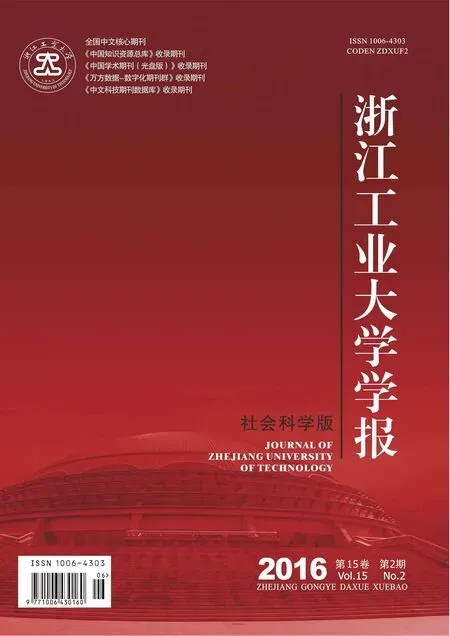微信公众平台著作侵权类型化分析及治理对策
2016-01-25刘承涛
刘承涛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微信公众平台著作侵权类型化分析及治理对策
刘承涛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微信公众平台作为目前互联网的主要沟通工具之一,其著作权侵权行为屡有发生,媒体界和法律界将原创鉴定难、短文易抄袭、作者多沉默和维权成本高等视为微信侵权泛滥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面相,真正的内相则是目前学界对其类型化分析缺乏,面对海量且变动不居的侵权形态,我们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对其进行严格意义上法律类型界定与分析,唯其方能在秉持法律规范相对滞后和保守既有路径中,探究规制和解决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第三方机构介入维权的治理对策。其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种方式能够将一个个原子式维权行为纳入到程式化、常态化的集体行为之中,实现平台著作权侵权的良性治理。
关键词:微信平台;著作权侵权;类型化;对策
我国所有手机APP(Application智能手机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中,即时通信领域使用率最高的是深圳腾讯公司所研发的“微信”软件。根据腾讯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30日,微信及WeChat月活跃账户已达6亿,同比增长36.9%[1]。腾讯公司于2012年在“微信”软件中增加了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在庞大的微信用户群的基础上,微信公众平台迅速发展为时下最受追捧的自媒体平台之一。“有光便有阴影”[2],与微博一样,微信也遭遇了严峻的侵权挑战。
2014年6月,广东省中山市的第一人民法院审理了第一例微信侵权案件;2015年3月深圳南山区法院也审理了深圳首宗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案,判令抄袭者赔偿著作权人(原创者)1万元[3]。但是,与司空见惯的微信著作权侵权事件比较起来,涉及司法程序的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诉讼案件还只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作品权利人在遇到著作权被侵犯时,并未诉诸法律,而是采取协商方式来处理,更不乏选择沉默的情形。媒体界和法律界将此视为目前微信侵权泛滥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面相,真正的内相则是目前学界对其类型化分析缺乏。本文借助类型化分析的视角,以探寻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保护的核心法律问题。
一、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研究综述
目前有关微信公众平台著作侵权的研究,主要从侵权行为认定,责任性质、承担和侵权问题的解决等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 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在对微信公众平台中的著作权侵权认定时,有学者认为首要的任务是作品的认定。美国Feist案所确立的“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相比,立足点不在于作品创作的本身,而在于作品与作者的人格联系;并认为,认定的关键是可以参考普通法系和罗马法系相应标准,才能准确地对微信作品的独创性做出判断;同时参照德法两国版权法修订草案将“数字化”复制纳入“复制权”范畴[4]。
第二, 侵权行为的性质和责任的承担上,对传播责任主体特别是微信平台的法律行为进行定性。
在责任性质上,主要研究考量免责事由的适用[5]。微信平台著作权认定一个较为复杂的方面是微信朋友圈的转发,因为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合理使用限度等侵权阻却事由,也是目前有关著作权侵权方面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各方最难统一的分歧点,为此,有研究者学者认为可以引入默示许可理论来阐释此类难题[4]。
第三,建立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维权方式[5]。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公众号所在平台作为空间有实行实名注册及建立投诉机制[6]。主要讨论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的保护路径,分别从原创作者、订阅号版主及粉丝、腾讯公司以及政府四个角度来阐述为减少侵权应做的努力,其中对于腾讯公司,在提出建议之前先对其已经采取的措施进行肯定[7]。针对纸媒微信订阅号新闻作品分享的失范现象,有研究认为可以借鉴西欧(德、法)以制定法方式对公众号平台转载报纸新闻进行强制收费做法,以维护新闻类著作权人利益[8]。
诚然,现有从侵权行为认定、责任性质和解决路径等三个方面展开的微信著作权研究进路和成果是必要的,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亦非常显然的是,这些研究进路基本还是传统著作权,特别是传统互联网著作权保护研究的延伸。目前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问题所面临的困境,也显示面对海量且变动不居的侵权形态,我们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对其进行严格意义上法律类型界定与分析,唯其方能在秉持法律规范相对滞后和保守既有路经中,亦能达至规制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最终目的。
二、 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的类型化分析
随着自媒体的崛起,各种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均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9]。适用目前的民法和著作权法解决相关纠纷时,不可能找到与之一一对应的法条和既有案例。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此类案件无法处理,因为在法理上,相关案例如果具有相同的主要特征,一般来说就可以适用相同的法条和法理、惯例来处理,这是法律类型化的要义所在。
首先,法律类型化的要义。类型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中一种[10]。确实,在法律适用的领域中,相较抽象的概念,类型更贴近具体案件事实,具有抽象的概念所欠缺的直观性和具体性,但又比案件事实更为概括和普遍。所以考夫曼才说,(以概念为核心要素的)法条作为一种应然,自身是不可能产生真实的法,需要添附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只有在类型化以后,才有可能与应然的法条对接产生实然的法[11]。换言之,类型是应然与实然的转换装置,类似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考夫曼进而更为剀切地指出,法律人(当然主要指司法者)的专长不仅仅在于识法——知道制定法的规定,更主要的任务在于在“法律的、即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11]。微信所负载的自媒体(社会化媒体)的生活事实是变动不居的,碎片化,甚至是原子形态的,但是法律规范天然的本性就是概括的、相对凝固的,二者处在一个坐标的两极。所以在把微信侵权的生活事实纳入到规范的、概括的法律事实中时,需要将微信的生活事实进行转换,即类型化后,方能接纳到相对滞后和保守的法律规范的既有路经中,实现法条规范生活事实的初衷。
为了更深入地诠释类型的机制,考夫曼引入了“本质”和“意义”的概念。考夫曼认为,是“意义”在调适着规范(应然)与事实(实然)之间互动机制,这个“意义”即为事物(案件)的本质。按考夫曼的说法“事物本质是证明自己是一种特殊中的普遍,事实中的价值的现象”。因为具有普遍的内涵,也就是说此类现象发生具有重复性,在司法上,具有重复发生的事物(案件)必然需要得到同等对待,或者说相同处理。于是“事物本质在实际的操作中便汇入类型难题中”,所以,通过借助某种“典型”或曰“标准形态”的设定,来诠释相关的类似情境[12]。类型是构成普遍与特殊的中点,是普遍中的具体者,特殊中的普遍者。与概念相比,类型比概念更接近具体生活,比高度抽象的概念更具直观性和具体性。拉伦茨曾指出,类型在法学中的意义首先涉及的是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13]。所以有法官指出,司法中运用类型化方法,借助归纳法,参照相似要件事实,提炼经验法则,可以总结裁判逻辑和固定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14]。类型在复杂新型的民事案件中,适用更为广泛[15]。此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微信等网络著作权保护中,为什么我们更应注重去发现和深描各种侵权类型,而不是传统实践中所看重的法律逻辑(即形式逻辑)。因为类型化分析的外延具有延展性,而前者则须有一个相对固定明确的前提。在时新日异的自媒体时代,固守一个明确的前提显然是一个奢望。所以要规制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的类型分析。微信公众平台的公众账号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服务号,一种是订阅号。由于微信服务号旨在为个人用户提供私人服务,相对较少有侵犯著作权的行为。2016年1月11日,腾讯公司在微信公开课PRO版现场正式发布的《2015年微信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显示,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微信收到针对微信公众帐号和个人微信账号的投诉超过2.2万件和1.2万件,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投诉,前者超过1.3万件,占比达到60%;后者仅有200多件,比例只有2%①资料来源:2016年1月11日,微信在微信公开课PRO版现场正式发布的《2015年微信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因此,包括著作权在内(实际上多为著作权侵权)知识产权投诉主要针对公众帐号,公众平台是微信著作权侵权的主要策源地。以下将针对微信公众平台中的订阅号著作权保护展开讨论。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用户普遍将微信公众平台视为共享的平台,没有意识到平台上会涉及著作权的侵犯或被侵犯。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平台所涉及的著作权侵权损害较小,导致权利人维权意识不足;再加上侵权行为主体难以确定,举证困难等多方面因素,维权难以进行实际操作[16]。这种情形又加剧了微信中著作权的侵权行为,直接导致“1人原创,99人抄袭”现象的泛滥。那些打着“转载”、“荟萃”为旗号的抄袭公众号借此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大量关注和粉丝,他们亦利用关注和粉丝来获取经济利益,而原创作者则成了淹没在抄袭浪潮中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贫女郎。所以有论者指出,若此种情形任其发展,将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即极大挫伤原创作者的热情,最终导致优质原创作品退出微信平台。
再次,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类型化之“类似”与类型。很多微信公众号用户会在朋友圈中大量分享与转发各种文章,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亦是造成微信著作权侵权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订阅号版主和用户应当树立尊重他人的著作权的意识,但前提是微信用户和订阅号版主需要对微信侵权的类型有一定的认识。认定类型化之“类似”要件目前学界有四种理论:构成要件说,实质一致说[17],同一思想基础说[17],和共同意义说等[18]。构成要件说,是将实然案件和应然案件(生活事实)的几个特征进行比较,归纳同类项,进而判断是否“类似”;而后面三种分别从价值、思想、利益等没有客观标准的主观因素方面归纳同类项,显然难于把握归纳进行研究。当然,仔细深思此四种学说,其实本质并无区别,却均有不周延的内在缺陷。特别是面对海量的色彩斑斓的微信著作权侵权行为来看,更是如此。因此,相较起来,第一类构成要件说,因为有相对具体的衡量标准,即能够依据这种学说从众多的微信侵权事实中提炼出具有类似性的特征[19],所以我们采纳其作为我们分析工具。
三、“合理使用”及“转载、转发”类型问题的法律构成要素
在上述类型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20]:一是“三无”类型。即无注明作者,也无来源出处,更无授权的转载行为。这种侵权类型非常典型,但也非常容易判断,属于赤裸裸的侵权行为。只要微信著作权人诉诸法律,基本上可以获得救济。二是“二有一无”类型。即在微信转载他人作品时有注明微信著作权人,亦有标注了作品来源,但无作者(或者媒体)的授权许可。这种类型一般也列入侵权行为。三是“非合理使用”类型。这种类型在微信侵权中虽然占的比例很大,但却隐蔽性最强,表现形态各异,有时还很难判断。最常见的表现为“不经允许摘录、整合”原创作者微信作品的行为,目前来看,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多通过这种方式形成。
第一、二种类型侵权方式比较容易判断,第三种类型在实践中判断起来相对复杂些,所以需要对第三种类型划分出三种相对容易混淆的次类型行为做出法律界定,然后对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保护提出相应建议。
首先,是合理使用问题。著作权由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发表权、署名权等,后者则为复制权、发行权、改(汇)编权等,现实中较为常见的摘录、整(融)合行为法律性质上属于著作财产权中的汇编权。所以,如果能够认定摘录、整(融)合行为属于汇编权,在未取得著作权人同意时,构成侵权应无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多引用《著作权法》第22条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进行抗辩,所以厘清“合理使用”行为至关重要。该条是这样规定“合理使用”的:“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确实,如果仅从条文看,并没有有要求行为人取得权利人同意的要件,而且条文中使用了“适当”这样弹性空间很大的用语,所以具体的实践中,在保证说明了所引作品的标题和来源的基础上,对何为“适当”只能依个案而定,不可能有一个显见的标准。当然如果这种使用达到了一定程度,即通常意义上的改编行为时,则必须取得微信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支付相应的报酬。有学者提出《美国版权法》第107条四要件分析对我们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即从是否为商业目的,作品性质,使用的程度(数量和比例),对潜在市场价值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判断何为适当[5]。但是对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改编使用时,权利人的同意须为默示形式还是明示形成则经历了一个过程。在 2006年之前,由于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不明确的原因,实践中对已经发表作品的使用(主要是上述的改编行为)多持默示许可的态度。不过自2006年7月1日起,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于2013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4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修订,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第2条“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的规定,至少在转载问题上,理论与实务界均认可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明示许可。
其次,是转载、转发问题。在微信平台上,涉及著作权行为的除了转载外,还有大量的转发行为,对转发行为的界定,意义非同小可。转载和转发行为内容都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对他人微信作品的转载介绍给第三方的行为。但是在微信行为中,却因为微信主体的不同,其法律性质的界定迥异。换言之,如果是微信公众号实施的话,就是转载行为;如果是范围较窄的普通个人微信使用者在朋友圈的行为,则是转发行为。一般认为,转发行为因多为限制在个人用户的相对封闭的朋友圈实施,不具有商业营利性质,更主要的是通常这种行为对微信著作权人不会造成损害;而且在权利人将自己作品通过微信形式发布时,对自己作品将被转发是有一定预见的,甚至是希望别人转发的[21]。所以我们说这种转发行为符合《著作权法》第22条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但是与仅限于私人朋友圈的个人微信账号不同的是,微信公众号是一个公共发布平台,多数都具有一定推广性质。二者不同就犹如一个人看到一篇好文章在自己的朋友圈中传阅和放到自己的公告栏甚至是大众传媒上,前者即是“合理使用”行为,后者则断难谓其合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超文本链接的方式介绍微信作品,并不是一种上述的转载方式,超文本链接就如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好书或在某杂志看到一篇美文,告诉公众这书在图书馆的索书号和哪本杂志上,根本不存在侵权问题。
毕竟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微信个人用户间的转发属于微信的通用功能,即这是微信平台常态运作和信息交流传播的当然要义。更主要的是,“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化,著作权法需要不断地在作者与作品的使用人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共享及快速传播和对创作激励的保护是著作权立法、司法者需要同时兼顾的”[21]。
四、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的法律治理对策
首先,传统著作权维权方式在公众号著作权侵权治理中的困境。微信自产生日起,公众号的抄袭现象就如影随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抄袭极易,维权却难。其原因在于,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微信作为一款综合性的即时社会化媒体通讯工具,其可以瞬间把海量的信息进行传播和分享,此亦型塑了依托在诸如微信这样的社会化媒体上著作权作品实际时效性很强,此直接导致了若依传统的方法和途径来保护著作权,不但实际操作繁琐,而且成本畸高;同时也面临着一个较为棘手的利益衡平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权利行使,目的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和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经济福利的方式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22]。在著作权上即为“著作权人利益和公众知情权利益与社会信息传播利益”间如何兼顾的问题[23]。
其次,兼顾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法律属性是公众号著作权侵权治理的内涵。人们从权利人、微信开发商和国家立法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的建议,即为了保护微信原创作者的著作权,人们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药方,这些药方看起来全面,面面俱到,既有权利人和订阅号版主及关注用户著作权侵权行为的保护的措施,又有完善微信开发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保护的规定,更有国家立法层面的设计等。但微信著作权侵权现象却似乎愈演愈烈,抄袭几乎成了微信公众号的“行规”。例如,腾讯公司虽已建立了举报平台和处理方法,但腾讯公司认为,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考虑到目前社会化媒体的海量信息、数据的特点,对于其作为平台的法律责任的基本要求是应当遵守“通知-删除”的避风港原则,即权利人如果发现平台上有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时,权利人向腾讯微信后台平台发出符合法律要件的通知,平台通过审查之后做出处理。但在实践中,权利人普遍的体会是,“举报程序繁琐,举证要求很多,而且没有时限承诺”;特别是个体诉讼高昂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更使权利人视为畏途。现在人们也找到了微信维权困境之所在:“发现难”、“确定难”、“利难计”、“周期长”、“成本高”[24]。其实核心只有一个——碎片化个人维权成本过高。因此法律上如何降低微信著作权人,特别是自然人身份的著作权人的维权成本是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保护的核心。因此,诸如微信这类的社会化新媒体及其相关平台,相关著作权集体组织,著作权主管机关如何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探索和设计出一条迅捷、易行、低廉微信平台著作权保护之道,以期既能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利益,又能在切实维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同时增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便捷性,即兼顾二者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法律属性[22]。
再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的治理对策:第三方机构介入维权。根据音乐著作权保护的经验和目前已有的微信著作权保护的实践,实施第三方机构介入维权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维权的短板在于“发现难”、“确定难”、“利难计”、“周期长”、“成本高”,所以面对海量的侵权事实和稍纵即逝的侵权行为,此前依赖传统的个人维权显得力不从心;但是效仿传统的音乐著作权维权方式,又面临微信侵权行为千姿百态,如何界定的问题。所以,通过将微信侵权问题纳入类型化分析后,就为第三方机构介入维权提供了条件。
第三方机构介入维权又称第三方机构代理维权,第三方机构代理维权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比如目前比较知名的社会媒体网站“一道网”,其较早开展了此类微信著作权维权公益项目。类似一道网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微信著作权维权的经验表明,这种实践性行为恰好弥补了微信著作权维权的最大短板,即由其大大降低并消解了权利人维权中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培育和引导类似“一道网”这样的专业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既能提高个人微信著作权维权的质量、又能减少相关著作权执法机构在执法中可能遭遇的执法抵制。作为社会力量的评估机构及其相关机制,如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的共享机制等的生成和完善,是保证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实效而稳定运行的润滑油。
综上所述,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浅层的原因是原创鉴定难、易抄袭、作者多沉默和维权成本高等。但是更本质的问题是,目前学界对其类型化分析研究缺乏,忽视相关研究,由此导致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侵权形态,我们现在无法对其进行严格意义上法律类型界定与分析,更无法将其治理策略纳入到既有的治理路径中。在类型化分析中构建的,解决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第三方机构介入维权的治理对策,其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种方式能够将一个个原子式维权行为纳入到程式化、常态化的集体行为之中,微信侵权行为被追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此,社会媒体时代,网络才应该不仅仅是侵权者的“狂欢节的广场”[25]。
参考文献:
[1] 腾讯公司.腾讯公布2015年第二季度及综合业绩[EB/OL].[2015-08-12].http://www.tencent.com/zh-cn/content/ at/2015 /attachments/20150318.pdf.
[2] 刘海洋.论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法救济[J].学术界,2014(9):177-185.
[3] 林园. 微信公众号抄袭赔偿原创一万元[N].羊城晚报,2015-07-02(A13).
[4] 杨延超.与微信平台有关的著作权问题研究[J]. 知识产权,2015(8):47-52.
[5] 郑莹. 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责任承担[J]. 怀化学院学报,2015(6):76-79.
[6] 张玉欣. 微信服务号“酷读吧”侵权行为分析[J]. 现代出版,2015(6):45-46.
[7] 唐然. 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及责任认定[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26-31.
[8] 冯松龄. 纸媒微信订阅号新闻作品分享失范现象研究[D].河北大学,2015:26-49.
[9] 刘海洋.论微信公众平台名誉侵权的程序法救济[J].学术界, 2014 (9):177-185.
[10] 黄建辉.法律阐释论[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28.
[11] 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台北: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40.
[12] 胡玉鸿.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兼论法学中“类型”的建构[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3-37.
[13]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39.
[14] 关倩.民商法实务精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5.
[15] 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J].法学研究,2006(6):11-20.
[16] 央视评论员组. 产权日:微信随手一转侵权吗[EB/OL].[2015-08-12].http://news.cntv.cn—04/26 /ARTI139851380 5196 525.shtml.
[17] 黄建辉.法律漏洞·类推适用[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8:110.
[18] 林立.法学方法与德沃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9.
[19] 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J].法学研究,2006(6): 11-20.
[20] 方堃.微信公众号主要的著作权侵权类型有哪些[EB/OL]. [2015-09-16]. http://daily.zhihu.com/story/3875421.
[21] 唐辰敏,陈明涛.微信公众号抄袭——著作权法新的谜题?[EB/OL].[2015-09-12].http://www.12reads.cn/29035.html.
[22] 冯晓青.论著作权法与公共利益[J].法学论坛,2004(3): 43-46.
[23] LRAY PATTERSON,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 Right[M]. Athens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15.
[24] 魏超,陈璐颖.微博与微信的著作权问题思考[J].中国出版,2015(16):70-74.
[25] 顾芳芳. 互联网时代网络平民话语构建途径探析[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0-114.
(责任编辑:王惠芳)
On the type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and managing strategies
LIU Chengtao
(College of Law,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WeChat public platform is one of the main communication tool of the current Internet in China and its copyright is infringed frequently, because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original, the text is easily copied, the author is habitually silent and the cost for right protection is rather high. In fact, these are merely the superficial reasons. The underlying reason is a lack of “type” analysis and defining analysis of current complex infringement. Copyright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issue for WeChat platform, and to solve it, third-party copyright protection agencies must be necessarily involved. And these managing strategies are hoped to offer guidance to deal with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ppropriately. More importantly, single copyright protection could be guided into a normal path in order to govern and standardize the platform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ssue.
Keywords:WeChat public platform;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ype; managing strategies
收稿日期:2015-03-02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 (CLS2015D009);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刑法重点学科项目(2016X30406)
作者简介:刘承涛(1975—),男,江西赣州人,讲师,博士,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6)02-01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