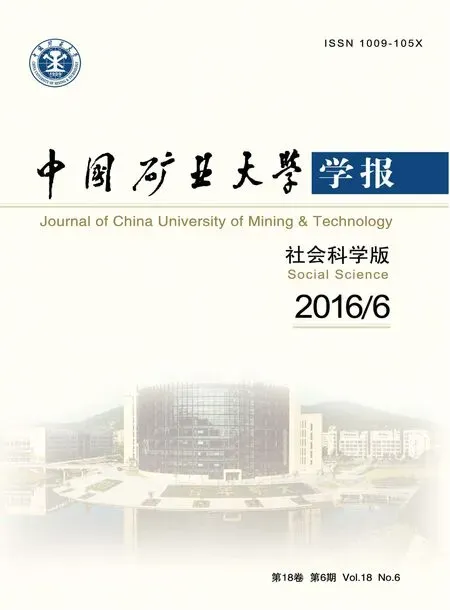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张光直神话研究述略
2016-01-23王倩
王 倩
(1.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张光直神话研究述略
王 倩1,2
(1.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多数读者倾向于将张光直先生视为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但事实上张光直先生同时也是一位神话学者,他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尤其是商周神话的研究集中在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一话题上。在该话题下,张光直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作为财富及其象征符号的神话图像如何建构权力象征体系;第二,神话宇宙论如何被统治者利用作为建构意识形态的工具;第三,英雄神话如何被宗族叙事改编进入历史叙事层面。以上三个问题反映了张光直先生将神话作为文化编码的神话理念,同时将神话研究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思想。
张光直;神话;历史;神话图像;宇宙论
对于多数学者而言,张光直先生首先是一位考古学者,李润权指出,“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1]4。陈淳先生则认为,“凡是在西方学过考古学的同行,都明白北美考古学界的同行们用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母K.C来昵称张先生的含义。”[2]529略懂人类学知识的学者都知道,在西方学界,考古学实际上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张光直先生以人类学的整体性视野探讨中国问题,质疑以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为代表的国家形成的人类学模式的普遍性观点,指出中国文明形态应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文明形态却是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光直先生不仅是出色的考古学者,还是杰出的人类学者、汉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
作为出色的考古学者,张光直先生的成果主要包括《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专题六讲》、《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国考古学论文集》、《青铜挥塵》、《考古人类学随笔》、《考古学》等专著。本质上说,张光直先生从来没有就神话而研究神话,他之所以研究神话,主要是基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以商代权力机制的探讨而出发的。但对于神话学研究者来说,张光直先生是一位卓越的神话学者,因为他在上述论著中探讨的关于中国神话与历史的研究,本质上就是神话如何建构意识形态,即神话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而这些依然是当下神话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神话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理论价值;并且其研究范式与理论,一直是当下中国神话学界所无法超越的。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关于张光直先生的相关研究中,尚未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本文从神话学视角出发,探讨张光直先生对中国神话研究的贡献,以及他给神话学带来的变革性贡献。
一、神话图像与权力建构
长久以来,史学界与神话学界一直在探讨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关联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历史的虚构性与神话的真实性问题。针对历史的诗学性质即虚构性这个问题,新史学学者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提出了神话历史(Mythistory)这个概念[3]1-10,以此强调历史书写的任意性与虚构性特征。新史学另一位学者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则强调神话在历史叙述层面具有的真实性问题:“一则神话无论多么富有传奇意味,它并不表示编造或纯粹的虚构,因为它通常包括共同体历史中所包含或涉及的关键问题,诸如共同体共同的祖先和边界的传奇。这些问题需要并能够催生关于历史的神话,因为它们不仅适于形而上学的神秘事物,诸如共同体的最初起源和命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实的叙事是共同体成员所信赖并经历的事实,即便(或者正好因为)它们是神话的而非逻辑的或历史演绎的。”[4]4“新史学研究者眼中的‘神话历史’概念与新史学关于历史属性的再界定密切相关,它要破除的是历史作为科学这样一种宏大历史观,强调历史诗学或阐释学的本质属性。”[5]尽管新史学承认历史书写的虚构性,以及神话在历史叙述层面发挥的塑造性作用,但西方学者关于神话与历史关联的阐释案例中并未涉及中国的历史与神话,不论是神话学还是新史学均如此。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的神话与历史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新史学倡导的神话历史概念亦不适用于中国。表面看来,这似乎与西方多数学者不大了解中国有关,但其背后隐藏的是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及其文明视为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异类或“他者”这样一种偏见。
作为一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虽然不是直接从事新史学研究的学者,但他深谙西方学界各种学术潮流背后的文化态度,在关于中国历史与神话的关联上,他作出了极其富有说服力的阐释,尤其是关于商代神话图像与王权建构的问题方面,后文会详细阐释。此处尚需加以说明的是,张光直先生关于商代神话图像与权力建构的探讨是建立在中国早期文明的根本属性这一基础之上的,只有了解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够理解张光直先生学术探讨的重大价值与意义。
文明是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概念,它由众多的要素构成,例如文字、艺术、仪式中心、技术、城市,等等。欧美学界通常以其历史经验为基础来界定文明,强调知识与技术在文明建构进程的重要作用。譬如,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认为,所谓文明,就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环境,他创造了这个环境并将自身从原始的自然环境脱离开来。”[6]11此种对文明的界定将非物质性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将人类与自然环境对立起来。张光直对伦福儒的文明概念提出了质疑,并再三强调:“其一,西方社会科学讲理论一般都是从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里产生的,而它们对非西方的经验也可能不适用。其二,更重要的一点,产生那种适用于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一般理论的那种西方经验,必然从它一开始便代表其余的人类所共有的基层的一种质上的破裂。”[7]510基于对西方学界文明概念的质疑与反驳,张光直先生指出,西方学者建构的文明模式并不适用中国早期文明。中国早期的文明形态是一种世界性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突破性的文明形态,并不具有普遍性。“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此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8]18张光直特别强调,在此文明框架下,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神话图像在建构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张光直将神话图像首先视为物质财富,认为神话图像首先是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的。神话图像的范畴极为宽泛,其载体包括石头、骨头、宝石、金属、陶瓷,等等。对于张光直先生而言,他探讨的神话图像载体只有两类,即青铜器与玉琮。在张光直看来,一方面,作为青铜礼器的神话图像由当时昂贵的锡料和铜料冶炼而成,需要先进的冶炼技术方可制造;另一方面,青铜礼器的铸造过程极为繁复,需要组织大量人力与物力,若非是拥有权力与财富的统治者,他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因而张光直断言,“青铜礼器是明确而强有力的象征物:它们象征着财富,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财富,并显示了财富的荣耀;它们象征着盛大的仪式,让其所有者与祖先沟通;它们象征着对金属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对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9]290至于玉琮,张光直先生并未将其列入财富之列,大概在他看来,在商周时代,玉器的制造技术并没有青铜礼器那样繁复。张光直先生此种关于玉琮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学界关于文明的界定,尤其是金属冶炼技术构成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这样一种文明观基础上。事实上,按照神话学关于神话图像的界定,神话图像的首要属性便是物质性,其能指指向了作为实物的神话图像。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神话图像的玉琮也应是财富,而不单单是财富的象征符号。
就内容而言,张光直先生探讨的青铜器物上的神话图像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写实的动物纹,如犀牛纹、猪纹、马纹、鸮纹、蚕纹、龟纹、鱼纹、鸟纹、蛙纹;另一类是神话中各类形象,如饕餮纹、肥遗纹、夔纹、龙纹、虬纹[10]47-53。张光直指出,这些铸造在青铜礼器上的神话图像并非仅仅是一种装饰性的符号,相反,它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功能,那就是沟通天地。“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沟通天地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10]73不难看出,张光直的观点非常明确,那就是,神话图像实际上是权力的象征,而这种权力乃是沟通天地的独特权力。在张光直先生看来,神话图像已被统治者视为一种建构权力的途径,神话图像借助于自身的象征意义而得以进入权力表述体系,神话由此通过图像而建构历史叙事体系。
前文已经讲到,新史学的学者们一直在探讨神话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但这些学者的阐释中仅仅只有西方的案例,甚至约瑟夫•马里在其论著《神话历史》中同样未将中国的神话考虑在内。这样看来,张光直先生关于商周时代神话图像的探讨实际上弥补了新史学长久以来忽略的东方神话尤其是中国神话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新史学的神话历史概念是在1986年首次由威廉.H.麦克尼尔提出,而张光直先生关于神话图像如何建构历史与权力的概念是在1983年提出的*张光直先生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83年,具体信息如下:Chang Kwang-Chih.Art,myth an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因此其理念与研究的前瞻性意义由此可见。从考古学界关于神话图像建构功能的探讨来看,从事东方文明研究的学者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诺曼·叶斐(Norman Yoffee)极力倡导高端文化(High Culture)理论,在他们的假说中,作为财富的图像具有建构权力象征体系的作用,但直到21世纪,他们的阐释案例中才出现中国神话图像[11]276-287。一旦将神话图像纳入通向政治权威的一种途径,就意味着神话在文明发展的早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塑造性作用,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建构因素便凸显出来。对于考古学、史学乃至于神话学的研究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理念性突破。
为何张光直先生会选择青铜器上的神话图像作为研究对象?换言之,神话图像有众多载体,为何张光直先生会将研究目光锁定在商代的青铜器上呢?缘由大致如下:第一,张光直的研究领域与兴趣使然。张光直在台湾读大学时,恰逢台湾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李济与在安阳从事过考古发掘的其他学者担任该人类学系的教师。这些学者年富力强,当时到台湾时还携带了大量精美的收藏品。“这是一支‘安阳队’,这只队伍包括所有由李济培训的、从1928年到1937年主持安阳发掘的、最优秀的考古工作者。”[12]208颇受李济影响的张光直,自然会选择以安阳遗址为中心的商文明作为研究对象。第二,在商代文明中,青铜器是出土最多的礼器,其价值自然被张光直所看重,关于这一点,张光直有明确的表述:“在早期中国,仰韶、龙山和三代,至铁器时代的开始,生产力没什么变化,就是技术没什么变化。商代青铜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却从未应用于农业,商代没有应用青铜技术去改进耕作方法,这是个我多年搞不懂的问题,但现在我认为我有了线索,这就是技术被用于我所说的‘国之大事’,即祀和戎,就是祭祀和战争,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12]221张光直先生选择商代的青铜器,这不仅仅是因为青铜器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还因为青铜器能够代表中国青铜冶炼技术的先进性。西方学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主流学派,将金属冶炼技术视为文明的建构性因素之一。这已经是考古学与史学的常识,我们从前文科林·伦福儒关于文明的界定中就能够明显看出来。第三,商代的神话图像多半出现在青铜礼器上,还有少量的神话图像出现在木器、骨器、玉器上。从这个视角来看,张光直选择商代神话图像出现频次最多的青铜礼器,亦为学术研究之需要。
只不过,张光直先生关于商代青铜器上神话动物功能的说法,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尤其是神话学者萧兵先生的批评。萧兵质疑的并不是张光直先生关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神话图像是巫师沟通天地的助手这样一种主张,他要批评的是张光直先生这种观点的普遍性。萧兵指出,“我们觉得,将这个理论适用于中国文物,十分牵强附会,不符实际。”[13]172基于此,萧兵还阐释了不少考古文物上的神话图像,并对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虎尊上的饕餮形象做了解释,认为此处的饕餮形象并非巫师沟通天地的助手,而是一个吃人的怪兽,绝不是沟通天地的使者。至于饕餮吞噬的对象,也绝不是和动物合为一体的巫师,而是另有所指:“被食者或为战俘,或是奴隶,或是玩物,或属被诬为鬼魅侏儒妖怪的‘异族’,却不是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或借助于另我而通灵登天的商人巫觋。”[13]178仔细分析便可发现,萧兵先生实际上误解了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他错误地将张光直先生探讨的商代青铜器上的神话动物形象扩展到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图像,同时将迄今没有文字记载的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像拿来作为反驳的证据。实际上张光直先生探讨的神话图像仅仅限于商周时代,并且仅仅针对青铜礼器,张光直先生从未主张此种观点可以适用于中国所有时期以及所有神话图像。因此萧兵先生的批评本质上是对张光直先生神话图像主张的误解,并不具有真正的批评性。
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神话图像通过象征建构政治权力体系的现象并非个别现象,相反,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国外众多学者近期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事多年考古发掘的考古学者南诺·马瑞纳托斯(Nanno Marinatos)的研究表明,甚至是地中海沿岸的文明,在其文明早期进程中,神话图像在创建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塑造性作用[14]。尚需指出的是,神话图像之所以能够进入叙事,并不取决于其载体,也不取决于其表述的内容,而是取决于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语境。这就意味着,神话图像的此种功能必须有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对于张光直先生而言,商代青铜器上的神话图像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叙事层面,乃是因为商代特殊的神话宇宙论,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区别于西方文明起源的重大因素之一。
二、中国古代神话宇宙论
世界各地文明中均有各自不同类型的神话宇宙论,尽管其表述内容各不相同,但却能够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从事文明起源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考古学者布鲁斯·崔格尔(Bruce G.Trigger)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早期文明的宇宙论的研究深受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影响。埃利亚德以对西伯利亚萨满教的研究著称。埃利亚德认为,所有早期文明都想象一个原始事件驱动现实世界,决定人类在宇宙的位置,以此理解超自然力量的运作。早期宗教仪式通过回到没有时间的时代,重演创世纪的方式,祈求神灵的出现。神祗最重要、最常见的表现为axis mundi,即位于大地中央、沟通上下超自然领域的神山或者神树。在神山或者神树周围,世界向四面八方铺展。埃利亚德认为,这种宇宙模式影响了作为宇宙缩影的城市、神庙、宫殿和房屋等的选址和布局。”[15]318对于张光直先生而言,他关于中国神话宇宙论的研究并非直接来源于埃利亚德,而是受益于另外一名从事玛雅萨满教研究的学者彼得·T·福斯特(Peter T.Furst),在一次访谈中,张光直先生这样说道:“我第一次读到福斯特的书,完全惊呆了。在那些大量的资料细节中,古代及现代玛雅人的萨满文明不用多加更改就可以适用于古代中国的符号形式。”[16]98正是基于这种影响,张光直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宇宙论的探讨几乎与福斯特关于萨满宇宙论探讨的细节完全相同,我们不妨一一分析。
福斯特的萨满教研究包括如下内容:萨满教的宇宙具有巫术性,自然环境与超自然环境中的诸多现象乃是巫术转换的结果;宇宙主要分为上中下三层,各个层面之间由宇宙之柱支撑;萨满教的世界是有生命的世界,万物皆有生命;人类与动物在质量上是对等的,人类为天界服务;人与动物之间可以彼此转换,主要是通过原始魔力而进行的;人类或动物的灵魂居住在其骨骼内,二者通过骨骼获得再生;灵魂与身体可以分离,灵魂同时能够到其他界面旅行,亦能被巫师或精灵捕获[7]149-157。仔细阅读张光直先生的相关论著便会发现,他关于商代神话宇宙论的研究实际上与福特斯的探讨如出一辙。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宇宙论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能够通天的人物主要是巫师,商代的国君即商王具有巫师通天之职能;巫师通天的媒介主要有神山、神树、神鸟、动物、占卜、仪式与法器、酒与药物、饮食乐舞[7]275-288。具体到商代,就表现为二分的宇宙论:“商人的世界分为上下两层,即生人的世界与神鬼的世界。这两者之间可以互通:神鬼可以下降,巫师可以上陟。”[7]289而通天的各种工具,则主要表现为各类动物,尤其是青铜礼器上的各类神话图像。
不难看出,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宇宙论的探讨基本与福斯特萨满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并无大的出入。那么为何张光直先生要这么做?换言之,其意图何在?实际上,若从文明探源的视角来看,张光直先生的这种探讨乃有意为之。他并非沿袭西方学者的萨满文明理论,而是试图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萨满文明的共同体之内,然后寻找中国文明发生模式的普遍性。
关于这一点,张光直先生自己有着明确的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基于巫术的宇宙观这种新的解释对这个古代基层内容的了解提供了新的基础。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古代的基层文化乃是中国与玛雅文明的共同祖先。中国与玛雅并不是非得要有文化上的接触才有拥有这些类似性的,它们乃是一个文化连续体的成员,这个连续体我们可以称为玛雅-中国连续体。玛雅-中国连续体的建立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1.它将古代中国和古代玛雅联系起来并且说明它们两者之间的类似性,而无须使用传播论;2.它强烈地暗示着这个亚美巫术文化基层不是东北亚洲的地方性传统而是具世界性的现象;3.它在一个新的框架里面提出资料用以研究说明它的领域之内的出现诸文明的演进原理。”[17]360这就回到了前文说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问题,即中国古代文明的本质在于其神话宇宙论,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是一种连续性的文明类型,而不是西方式的以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后者用金属工具将人类与自然分割开来,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类。说到底,中国古代神话宇宙论实际上是为定位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而提出的,张光直先生试图郑重说明,就像玛雅文明一样,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巫术色彩,这是一直有别于西方的文明类型,但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尤其是古代中国与中美洲的玛雅地区。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张光直先生所说的巫术宇宙论本质上为神话宇宙论,因为此种宇宙论模式本质上属神话式的,巫术仅仅是神话的一个叙述因素而已。在张光直先生所探讨的商代神话宇宙论中,缺少神话起源论,尽管他引用《山海经》叙述的宇宙创生神话,但《山海经》不是商代神话叙事文本,因此关于商代神话宇宙论的探讨在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中是缺席的。另外,神话宇宙论涉及方位模式,尤其是垂直方位模式与水平方位模式,这是世界各地神话宇宙论不可或缺的内容。根据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的研究可知,商代的神话宇宙论中并非只有上与下这两个垂直方位,还有东西以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些方位,垂直与水平方向围绕一个十字型的中心而一一对应[18]96-129。但张光直先生在探讨神话宇宙论时并未涉及水平方位中的东西方向问题,却反复强调垂直方位中的上与下这两个方向,并且重点探讨上与下两个世界与方向之间的沟通问题,即巫师借助各类神话形象与上面世界的祖先与鬼神进行沟通问题。这也是由张光直先生的研究目的所决定的,他要强调神话宇宙论的巫术性质,即要强调巫术在沟通上下两个世界中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上与下自然就是探讨的重点,至于水平方位的东与西这两个方向,与巫术的沟通并无多大关系,因此就被忽略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张光直先生的神话宇宙论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所决定的。毕竟,张光直先生最终要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他只研究与此相关的神话宇宙论,与此无关的问题不予关注。
三、神话的界定与分类
按照常理,考古学者探讨的是以考古实物为主体的实证性问题,对于作为虚构叙事的神话这类研究,多数考古学者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但考古学出身的张光直先生并未像多数考古学者那样,将神话视为文学研究者专有的研究领域,而是花了很多精力投入其中,从神话图像的阐释,再到商周神话分类研究,所有这些神话研究无不说明了张光直先生对于神话的重视。那么,为何张光直先生对神话研究具有如此高涨的学术热情呢?究其原因,还是他对神话的认知使然,即张光直先生对神话的认识与定位决定了他对中国神话研究、尤其是商代神话研究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目前的学科体系中,神话被划入中国文学范畴,甚至被部分高校的教学体制归类到民间文学。多数学者的认知因此一直停留在神话是集体创造的虚构性故事这种层面上,神话因此无法与具有现代性与宏大叙事性质的其他文学叙事类型相提并论。这种狭隘的文学式的神话理念导致了中国的神话研究多年无法摆脱形而下的研究,中国神话理论建构无法摆脱文学理论的模型影响。作为一名旅居海外的学者,张光直并未受到此种文学式神话理念的影响,恰恰相反,他采用了人类学将神话视为文化编码与基因的理念,将神话看作文化与历史的建构性要素而加以研究,从而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张光直特别指出,“稍微浏览一下神话学文献的人,很快就会发现:研究神话的学者对‘什么是神话’这个问题,提不出一个使大家都能满意接受的回答。再进一步说,我们甚至不能笼统地把神话的研究放在某一行学问的独占之下:文学批评家、神学家、哲学家、心理学者、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以及所谓‘神话学家’,都研究神话而有贡献。”[7]372这实际上是提倡跨学科的神话研究,并强调一种能够覆盖各个学科的神话理念。“照我个人的管见,神话不是某一门社会或人文科学的独占品,神话必须由所有这些学问从种种不同的角度来阐发。因此我就不同意若干学者对过去神话研究之‘单面性’的批评:神话的研究只能是单面性的。”[7]375在强调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神话的同时,张光直先生将神话视为文化编码,在历史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他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我同意大多数研究神话学者把神话当作文化与社会的一部分的观念:神话属于一定的文化与社会。为其表现,与其密切关联。譬如东周的神话在东周时代的中国为中国文化活生生的一部分,而可以,甚至应当,主要当作东周时代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加以研究。对商代的及西周的神话,我们所取的态度也是一样的。”[7]379作为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张光直先生早就意识到神话在历史叙事建构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个中国学术界神话研究的状况,他仅仅强调了神话作为文化与历史因素这种属性,而没有在理论上强调神话作为文化建构要素的性质。
在论及神话概念时,张光直先生并未给出神话的确切定义,但规定了神话的叙述内容:“第一,我们的神话材料必须要包含一件或一件以上的‘故事’。故事中必定有个主角,主角必须要有行动。……其次,神话的材料必须要牵涉‘非常’的人物或事件或世界——所谓超自然的,神圣的,或者是神秘的。……但神话从说叙故事的人或他的同一个文化社会的人来看却决然不是谎?!他们不但坚信这‘假’的神话为‘真’的历史——至少就社会行为的标准而言——而且以神话为其日常生活社会行为仪式行动的基础。这也是我给神话材料所下的第三个标准。”[7]373-374从张光直先生关于神话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尽管他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他却将神话视为一种真实而神圣的叙事,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话叙述者的神圣信仰。这绝非文学式的神话界定,而是人类意义上的神话概念,因为神话的功能与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叙事意义,它是人类生存的原则与基础。
就神话研究的独创性而言,张光直关于神话的定义并未脱离人类学的范畴,但他关于商周神话分类的研究却是对中国神话研究,尤其是商周神话研究的独特贡献。因缺乏相关的研究资料,商周神话研究向来是中国神话研究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个学术难题。在张光直之前,商周神话研究一直在进行,但关于商周神话的体系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即便是陈梦家先生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也未能解决商代神话的体系建构问题[19]486-576。张光直先生根据商周神话叙述的内容,将其分为四类:自然神话、神仙世界及其与人间世界分裂的神话(分裂神话)、天灾与救世的神话、英雄世系神话。这四个体系组成商代神话的叙述内容,同时奠定了商代神话的基本结构。从中国神话的体系来看,张光直先生关于商代神话的分类研究虽然看上去比较保守,仅仅对叙事内容做了简单的划分,并未就其内部的深层结构做系统分析与阐释。但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当下,商周神话的分类与结构问题一直未有成体系的研究,张光直先生的分类依然是最为完整的。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代神话的资料较少,多半限于甲骨文与青铜礼器,能够对二者进行深入的阐释解读的,恐怕没有几人,能够超越张光直先生的暂时还未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光直先生关于商周神话分类的研究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张光直指出,商周神话中自然神话的数量极其有限,但英雄神话却极为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神话的历史化问题。在张光直看来,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具体到英雄本身就是,诸多英雄是由古代的神明或者是动物精灵转化过来的。用当下神话学的学术话语表述就是,古代神话世界的主角转换到真实的历史时期,由虚构的形象转换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形象,这种现象或问题即为神话的历史化问题。神话的历史化问题本质上探讨的还是神话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研究的问题具体落实到了英雄这样一类特殊的形象上。神话的历史化问题并不是张光直首先提出来的,茅盾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个问题在茅盾先生那里被抽取了具体的时间背景,神话的历史化问题因此成为一个无法探讨的抽象话题。与茅盾先生有所不同的是,张光直先生将神话的历史化问题放在了具体的历史时期加以探讨,并指出商代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英雄神话,乃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也是商代自然神话不够丰富的主要原因。“神话之历史化是在各国都有的一个程序,但在古代的中国特别发达,而这也许就是关于自然与神的世界的神话不多的主要原因。”[7]395张光直先生还指出,商周神话中的英雄多半为各个氏族的始祖兼文化英雄,集中反映了英雄即是祖先这样一种理念,隐藏在背后的原因则极为功利:“中国古代的神话在根本上是以亲族团体为中心的;亲族团体不但决定个人在亲族制度上的地位,而且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从商到周,亲属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神话史上的演变是这种政治与亲属制度之演进所造成的。”[7]405
四、结语
从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个角度来看,张光直先生的中国神话研究实际上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第一,就神话图像而言,商周时代的神话图像首先是作为财富而出现的;其次,商周时代的神话图像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符号,它在文明进程中发挥着建构权力机制的作用;第二,神话宇宙论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统治者独占沟通天地的工具就等于掌控了沟通天地的权力,进而独占了知识与权力;第三,通过将神话英雄历史化的叙述方式,神话将虚构的英雄形象转化为历史上真实的各个族群或权力集团的祖先,进而将其转换为文化英雄,神话从而进入历史叙述层面。在上述三个层面,神话成为历史叙事的方式,同时又成为历史叙事的一个建构性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神话如何进入历史一直是神话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在理论上给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却鲜有人从中国神话与历史的角度给出具体的阐释。作为一位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张光直先生从具体的中国神话研究为神话如何进入历史问题提供了独特而颇具价值的答案。
[1] 李润权.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J].中原文物,2002(2):4-6.
[2]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 McNeill W H.Mythistory’ or truth,myth,history and historians[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6,91(1):1-10.
[4] Mali J.Mythistory:The making of a modern historiograph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5] 王倩.探寻中国文化编码:叶舒宪的神话研究述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9.
[6] Renfrew C.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M].London:Methuen &Co,Ltd,1972.
[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2013.
[8]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三联书店,2010.
[9] 张光直.青铜挥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0]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郭净,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
[11] 叶斐,李昊.王权、城市与国家:比较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城市[M]//唐际根,高嶋谦一.多维视角: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2]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M].上海:三联书店,2013.
[13] 萧兵.中国上古文物中人与动物的关系——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J].社会科学,2006(1):172-179
[14] 南诺·马瑞纳托斯.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 [M]. 王倩,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
[15] 布鲁斯·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M].徐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6] 海基·菲里.与张光直交谈[J]. 冷健,译.华夏考古,1997(01):94-110.
[17]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2013.
[18] 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9]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J].燕京学报,1936(20):486-576.
How Myths Come into Histories: A Review on Chang Kwang-Chih's Myths Research
WANG Qian1,2
(1. Faculty of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2.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Mr.Chang Kwang-Chih is regarded as an archae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by most readers. He is also a mythologist, and focuses on how myths, especially myths of Shang and Zhou Period in ancient China, come into histories. On this topic, Mr.Chang Kwang-Chih discussed three issues: the first is how mythic images such as wealth and the symbols of wealth construct the powerful symbolic system; the second is how mythic cosmologies are used as the tool by rulers to build up the ideological system; the third is how myth heroes come into historical narratives by adaptation from religious narratives. The above three issues reflect Chang Kwang-Chih's idea of myths that myth is the cultural code and we should study myths by means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Chang Kwang-Chih; myth; history; mythic image; cosmology
2016 - 06 - 13
王 倩(1974—),女,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I207.7
A
1009-105X(2016)06-0045-07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