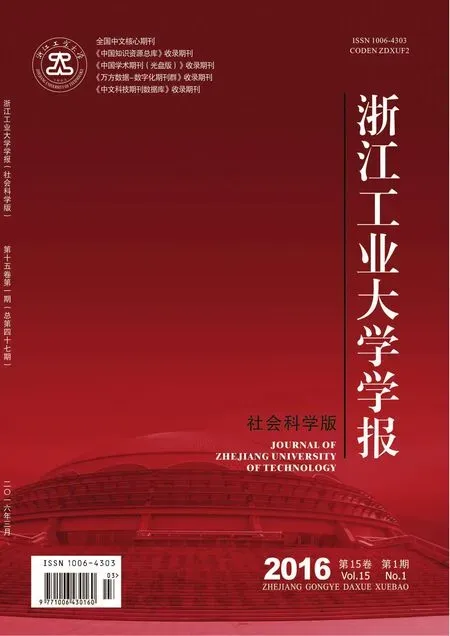“再说”语用功能探究
2016-01-23楼荷英冷荟姣
楼荷英,冷荟姣
(1.浙江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2.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再说”语用功能探究
楼荷英1,冷荟姣2
(1.浙江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2.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现代汉语中的“再说”,频繁运用于会话交际中,在长期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中,以动词性短语为演变源头,衍生出三类词性:动词、连词、句末助词,这些词性各自承担着相应的语用功能。根据不同词类在语境中的作用,对“再说”的语用功能进行重新分类,并逐一进行论述。当“再说”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时,两者语法功能相当,属于实词中的动词范畴,在会话交际中表示实际的语言意义,同时在不同语境中蕴涵不同的语用功能。当“再说”为连词或句末助词时,属于虚词范畴,其中连词“再说”具有话语标记功能,句末助词“再说”具有情感强化功能。
关键词:再说;实词;虚词;语用功能
现代汉语中“再说”已成为一个热点词,时常出现于人们的会话交际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词汇化和语法化后,“再说”由动词性短语衍生出动词、连词、句末助词三类词性。近年来,语言学界从本体方面以及习得偏误方面对“再说”一词进行研究。
已有的“再说”本体研究主要针对该词的语法和词类功能展开。语法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对“再说”语法化和词汇化历程与机制研究,有的单独选取单个词类进行分析,有的则从整体角度加以论述。余诗隽、柳春燕[1]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出发,针对句末“再说”语法化历程进行分析,并认为主观化、去范畴化是其语法化机制。胡斌彬、俞理明[2]分别阐述不同词类“再说”其语义功能和句法特点,并分析“再说”语法化与词汇化的历史演变历程与特点。罗耀华、牛力[3]从语义角度对“再说”进行分类,整体分析其语法化过程,并从句法、认知、语用三个角度分析其语法化机制。戈红[4]分析短语、连词、句末语气助词这三类“再说”,从共识的角度讨论这三类“再说”在语法分布和语法功能上存在的差异。
“再说”的词类功能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作为连词所承担的功能上。郑贵友[5]针对连词“再说”进行描写分析,重点从话题相同、相近、相关、相异以及预示功能方面,对连词“再说”的篇章功能进行分析和论述。周威兵[6]从“命题与话题”基本形式出发,依据“虚”、“实”、“动”、“静”四字原则,对连词“再说”语段功能进行分类论述。再以“转喻”和“隐喻”概念为标尺,从显隐角度,讨论“再说”所承担的语义关系。还有芜崧[7]分析连词“再说”所承担的语义关系,并将其进行归类。
综上所述,“再说”本体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语法化和词汇化以及词类功能方面。对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分析,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基本是在词类角度展开后,对其历程梳理以及机制分析。而词类功能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连词“再说”的篇章功能研究,但尚未有关于“再说”其他语用功能方面的研究,而“再说”一词现已成为人们语言交际尤其是会话交际中的高频词,在关注其篇章功能的同时,关注其更多的语用功能显得非常必要。根据“再说”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关研究,“再说”具有从动词性短语、动词向连词、句末助词演变的一般规律。从词类角度划分,动词性短语和动词属于实词,连词和句末助词属于虚词,本文将从实词和虚词的范畴讨论“再说”的语用功能。“实词类‘再说’”具有语言意义,但在语境中语用功能不尽相同;“虚词类‘再说’”中的连词“再说”在句中具有话语标记的性质,承担话语标记语的功能;句末助词“再说”具有情感强化功能。
一、实词类“再说”
动词性短语“再说”和动词“再说”其语法功能与动词相当,属于实词中的动词类(以下简称为“动词类‘再说’”)。它们都作为谓语承担句中主要成分。
“动词类‘再说’”,不具有句子联结功能,如果将其删除,句子命题的真值性以及句法合理性就会受到影响。
动词性短语“再说”作为主要谓语时,“再”作为副词修饰动词“说”,意为“重复地讲”、“再一次说”等,“再”与“说”分别具有实际的语言意义,“再说”一词在句中主要表示词语本身的动词意义,语用功能相对较弱。
动词“再说”作为主要谓语时,“再”的意义已被虚化,“说”保留部分词汇意义。一般在句中有三类表达形式,分别承担三种不同的语用功能:第一类承前省略主语,单独使用,独立成句。有时也以其变体形式:“再说吧”、“再说再说”“到时再说”、“这个再说”等呈现。此类“再说”起到缓和语气的作用;第二类常位于具有完整句法成分的句子末尾,偶尔也独立成句。具有暂缓某一行为的语用功能;第三类多出现在书面表达中,常位于句首,后接宾语成分,主要作为语篇衔接成分,具有话题转换功能。
(一) 语气缓和类“再说”
“再说”可作为面子威胁缓和语[8],起到委婉语气的作用。在会话交际中, 当说话人打算拒绝,但为遵循礼貌原则,不方便直接了当表示拒绝时,就以“再说”回应。说话人从字面上表达“再议某件事情”的意思,而实际上只是搪塞一下,并无真正再议某件事情的意愿。例如:
(1)A:“小张,周五空吗?约片吗?”
B:“周五可能没空诶,最近都挺忙的。”
A:“那你什么时间有空哦?我们约。”
B:“再说吧。最近读书报告、课程论文、还有我的工作室的事情,分身乏术。”(来源于现实交流中)
在这段会话中,A首先向B发出周五约片的请求,而B以“可能没空”、“挺忙”表述委婉语气,表达“拒绝”的语境效果。A在接受拒绝的信息时,选择性地接受了对时间的拒绝,但没有接受对事情的拒绝,所以A开启了下一个话轮,询问B什么时间有空,然而B没有直接回复,而是承前省略主语“约片”这件事,单独使用“再说吧”回复A的询问。根据后续的话语,分析得出B不仅表达对时间的拒绝,而且表达了对事件的拒绝,但为遵循礼貌原则,运用“再说吧”,在表示“拒绝”的语境意义的同时,给听话人和自己保留面子,委婉话语语气。
(二)行为暂缓类“再说”
1.位于句末,在句子中承担谓语成分。该类“再说”根据不同的语境或语境假设,表示延缓某一言语行为[9]。例如[1]:
(2)吴长贵说:“咱们现在只顾畅饮,婚事到明天再说。”(陈忠实《白鹿原》)
该句中,句末动词“再说”具有表达延缓“考虑婚事”的言语行为义的语用功能,隐含“不顾其他,先做某事”的语气。该句中“再说”的词性介于从动词性短语“再说”逐渐虚化到句末助词“再说”的过渡阶段。
2.单独使用,与语气缓和类“再说”表达形式相似,作为回应延缓语。当说话人无法立即做出明确决定,但在礼貌原则的驱使下,又不得不给予回应时,以“再说”作为模棱两可的回复,暗示对方还没有确切可提供的信息,同时为自己争取考虑的时间,为将来回复留有余地。此类语用效果出现在会话结束后,说话人仍会向听话人提起该话题,并给予明确的回复。例如:
(3)A:“那个研讨会你去吗?这边要统计人数。”
B:“再说吧。”
……
B:“研讨会我决定去了。”
A:“好的。”(来源于现实交流中)
当A问B有关研讨会是否参加的事宜时,B无法马上给出明确的决定,于是使用“再说吧”回复,表达自己“未最后决定”的语境意义,因此A在理解了B的语境效果之后,不会草率地判断其是否参加会议,而会等待B的明确回复。此类动词“再说”常用于回答选择题时,体现“争取时间做决定,稍后将回复”的语用效果。
(三)话题转换类“再说”
“再说”位于句首时,后接宾语成分,与之充当话题成分,起到话题转移的作用。该类“再说”多出现于早期书面语表达中,作为一个故事与另一个故事之间的衔接成分,可以被看做是“(我们)再(来说)说(宾语)”省略形式。例如[3]:
(4)“只说,鲁提携回到经略府前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问他。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女儿…… ”(施耐庵《水浒传》)
“再说”位于句首,后接宾语“金老”,充当两个故事的衔接成分,将话题从“鲁提携”转移到“金老”。开启有关金老的话题,描写其与他人分离后的境况。
(5)“三嫂羞惭,还房自缢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这话阁过不题。再说田大可惜那颗紫荆树,再来看时,其树无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烂漫。”(《醒世恒言》)
“再说”与宾语“田大”相连充当话题成分,“田大”为话语所描述内容的主语。“再说”将话题从“三嫂”转向“田大”,使得语篇连贯,具有衔接性和连贯性。
此类“再说”的用法与郑贵友[5]提及的连词“再说”用法类似,都位于句首,可连带其他成分,如呼语,充当话题成分。但两者的用法又略有不同,连词“再说”,多出现于口语表达中,其主要语用功能在于强化明示其语义逻辑关系的作用,与所带成分充当插入语,吸引听话人的注意;而话题转换类“再说”,大多出现在书面表达中,后接宾语,且该宾语为之后话语内容的主语,不可删除,其主要语用功能在于开启新话题并转移话题。
可见,“动词类‘再说’”,位于句末时,多出现在口语表达中;位于句首时,多出现于早期书面表达中。当位于句末时,分别承担缓和语气、暂缓行为的语用功能。当位于句首时,承担开启与转移话题的语用功能,“再说+宾语”为话语的主要内容与成分,不可删除。
二、虚词类“再说”
“再说”逐渐虚化到具有连词和句末助词功能时,在句中已发展为没有完整意义的词,不表达命题意义,不影响句法结构,本文将其统称为“虚词类‘再说’”。此时,连词“再说”在句中承担话语标记语的功能;句末助词“再说”黏附在句末,具有情感强化功能。
(一)连词“再说”
1.连词“再说”的话语标记性质。话语标记语[9-12]在本文中是指标示语义逻辑关系,可通过语音辨别,与语境密切相关的词或短语,它具有一定的语用功能,但不具有命题真值意义,不影响句法的合法性,其位置相对灵活,可位于句首、句中和句末。
本文认为,连词“再说”符合上述定义,实质上在句中充当话语标记语。
连词“再说”作为两个分句的联结词,常分布于第二个分句句首,作为句中衔接语。在口语表达中,常通过语音的停顿或改变音强来加以强调与辨识。假设去掉“再说”,两个分句的真值条件和句法合法性不受影响。有时,连词“再说”以“再者说”或“再则说”等变体形式出现在表达中。例如[5]:
(6)红路不说了, 小心翼翼地看着丈夫,“你真的不吃醋?”
“不吃——”徐白拍拍红路的肩,“(S1)你一个堂堂舞蹈学校高材生, 总不至于跳一辈子堂会,再说,(S2)再过几年, 你想跳也跳不动了。”(王旭峰《平湖秋月》)
例(6)中“再说”为连词,连结S1与S2,位于S2句首,充当S1与S2的连接语。假设该“再说”被删除,S1与S2的命题仍为真,并且在句法上仍然成立。同时,在会话中,说话人时常通过停顿和音调的变化等,对其进行强调,符合话语标记语特征,因此连词“再说”具有话语标记语的作用。
2.连词“再说”的话语标记功能。何自然、冉永平[13]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讨论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制约问题时,认为在话语理解的动态过程中,说话人通过明示与隐含手段表达话语的意义和说话的意图,听话人则是根据所接收的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结合语境或语境假设进行推理、处理新信息,以寻找话语的关联性。这说明,“一方面说话人应提供与听话人认知语境有关联性的信息;另一方面在解码过程中,听话人也倾向于理解那些关联性强也有必要关注的信息”。而“为了交际的成功,说话人会制约听话人对话语的理解,以达到:(1)最大限度地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2)最大程度地增加话语的语境效果。”连词“再说”在句中充当话语标记语,在使用过程中也具有对话语的语用制约功能,具体表现为两点:明示功能:明示语义逻辑关系,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找,以便其理解话语间的关联性。强化功能:强化语境效果,促进听话人对话语隐含意图的理解与把握。
明示功能。基于何自然、冉永平[13]对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制约问题的探讨,又根据郑贵友[5]、芜崧[7]等人对连词“再说”所承担的语义逻辑关系的论述,本文认为连词“再说”承担四类语义逻辑关系,即“并列关系、递进关系、因果关系、让步关系”。在口语表达中,说话人通过连词“再说”将两个逻辑上并无直接关系的话语联结在一起,明示其语义逻辑关系,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找。例如[2]:
(7)不行呀,(S1)他已是白发老头儿啦。再说,(S2)他家有几房婆娘,我女儿过去受虐待呀。(王晓光《康有为晚年的三位夫人》)
单独看S1与S2,二句谈论的内容相异,并无直接关系,而连词“再说”将两句话联结起来,使S1与S2呈并列关系。当听话人接收到该新信息时,由于连词“再说”则更易于发现S1与S2的语义逻辑关系——并列关系,达到“最大限度地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13]的目的,充分表达“听话人对说话人所提建议的否定态度”,同时也缩短了下一话轮中听话人的理解时间,起到提高会话效率的作用。
强化功能。语境效果分为三种情况: (1)新信息与现存的语境假设相互作用,产生语境含意;(2)新信息进一步加强了现存的语境假设;(3)新信息与现存的语境假设相互矛盾,或否定放弃现存的语境假设[13]。将“再说”之前的句子看作是现存的语境假设,“再说”引出的句子为新信息,那么,当连词“再说”承担并列、递进关系时,其体现的语境效果为新信息与现存信息相互作用,共同产生语境含义;而当连词“再说”承担因果、让步关系时,其体现的语境效果为新信息进一步加强了现存信息。无论是相互作用还是加强作用,都体现了补充性的特征,即对命题或潜在命题以及语境含义或说话意图的补充说明,达到强化语境效果,促进听话人对话语隐含意图的理解与把握的目的。例如[3][5][7]:
(8)票还是要买的嘛!(S1)他们个体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嘛! 又是丰富群众业余文学生活, 我们应该支持嘛!再说(S2)还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 (王朔等《海马歌舞厅》)
(9)(S1)好好的一个人又不是狗, 为什么大路不走非要钻那个墙洞? 再说(S2)那个墙洞说不定马上就能修补好的……(王朔等《海马歌舞厅》)
(10)(S1)安雯, 谢谢你, 我没事。再说(S2)你爸爸的确为学校做了件大好事, 我今天也高兴!(《故事林》)
(11)(S1)人家逢时现在是工程师, 要模样有模样, 要本事有本事, 哪点儿比金枝差了,再说呢,(S2)金枝又出了这档子事, 我倒担心对人家逢时不合适了呢。(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例(8)、(9)中,连词“再说”分别强化了S1与S2两个句子之间的并列关系和递进关系,使得S1与S2共同作用,增强了整个话语的语境效果。例(8)的S1与S2两者互为平行补充条件,论证了“买票”的必要性,增强“说服听话人赞同买票”的语境效果。例(9)中S2是S1的纵深补充条件,增强“反对走墙洞行为”的语境效果。
例(10)、(11)的连词“再说”分别强化了S1与S2两个句子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让步关系,S2补充加强了S1的语境效果。例(10)中S2是S1的补充原因,加强S1“表示感谢和让听话人不必担心”的语境效果。例(11)中S2是对S1退一步的补充说明,加强表达对“主语‘逢时’肯定态度”的语境效果。
在话语交际中,无论连词“再说”承担怎样的语义逻辑关系,它都对该关系起到明示作用,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关联性的搜索;同时对整个语境效果起到积极强化作用,使得原本两个无直接关系的句子,放在同一语境中,相互补充,共同表达说话意图。
总的来说,连词“再说”的明示功能与强化功能共同作用于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的理解过程中,使听话人易于理解话语的关联性,促进听话人对话语的隐含意图的理解与把握,增强话语交际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二)句末助词“再说”
当“再说”处于语法化词汇化程度较高的阶段时,衍生出句末助词的词性。句末助词“再说”不充当句中的主要成分,位于谓语成分之后。一般情况下,基本表达形式为“主语+先+做某事(谓语成分)+再说”,有时说话人也会省略主语或状语成分。与连词“再说”相比,句末助词“再说”的语用功能相对比较单一,其黏附在句末,具有情感强化功能,主要作用为强化“先做眼前的事,其他事留待以后考虑或处理”的语气或情感,引导听话人充分理解说话人的建议,暗示其接受并给予肯定回应,具有主观性的特征。例如[2]:
(12)这不是下决心了嘛, 向金枝学习, 不管老爷子生气不生气, 咱俩先结婚再说! (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句末“咱俩先结婚再说”,明示“结婚”的言语行为义,强化“其他的事情留着以后考虑,结婚最重要”的语气,引导听话人理解说话人所提出“结婚为当务之急”的建议,暗示其接受,并期待肯定答复,隐含说服义。删除“再说”句子仍然成立,但语气相对减弱,说话人的情感表达以及话语的说服力也相对不足,影响听话人的理解效率。
概言之,虚词类“再说”,其语用功能主要集中于明示强化作用。连词“再说”作为话语标记语,起到明示话语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强化语境效果的作用;句末助词“再说”起到明示言语行为义,强化话语表达的情感和语气的作用,从而提高听话人理解说话意图时的效率。
参考文献:
[1] 余诗隽,刘春燕.句末再说语法化倾向[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10):27-29.
[2] 胡斌彬,俞理明.“再说”词汇化和语法化[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2):28-32.
[3] 罗耀华,牛力.“再说”语法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1):73-80.
[4] 戈红.说“再说”[J].语文学刊,2009(10):152,164.
[5] 郑贵友.连词“再说”及其篇章功能[J].世界汉语教学,2001(4):32-38.
[6] 周威兵.连词“再说”功能浅议[J].语言文字应用,2005(9):171-173.
[7] 芜崧.也说“再说”[J].汉字文化,2002(2):63-64.
[8] 冉永平.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J].外国语,2003(3):58-63.
[9] 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2.
[10] 陈君均.话语标记与研究综述[C]//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福建:外国语文学会,2010:496-503.
[11] 刘丽艳.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D].浙江:浙江大学,2005:23-25.
[12] 冉永平.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J].外语研究,2000(4):8-14.
[13] 何自然,冉永平.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3):1-8.
(责任编辑:薛蓉)
A study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Zai Shuo”
LOU Heying1,LENG Huijiao2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2.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Zai Shuo” in modern Chinese is frequently used in daily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in oral communication. With long-tim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Zai Shuo” has developed into four kinds of part of speeches. It can be used as a verbal phrase, a verb, a correlative or an auxiliary. When us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Zai Shuo” has different pragmatic functions. This paper reclassifies “Zai Shu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ology and then analyses its pragmatic func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hen“Zai shuo”is used as a verb or a verbal phrase, it carries lexical meaning. When “Zai Shuo”is used as a correlative or an auxiliary, it doesn’t carry real meaning. As a correlative,“Zai Shuo” acts as a discourse maker . As an auxiliary,“Zai Shuo” has the emotional function.
Keywords:Zai Shuo; content words;form words; pragmatic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6)01-0080-05
作者简介:楼荷英(1965—),女,浙江诸暨人,教授,博士,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冷荟姣(1992—),女,浙江建德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