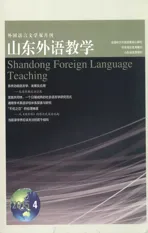从汉语新词看意义的演变进化及其动因
2016-01-22刘晓环王军
刘晓环, 王军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王军(1966-),男,汉族,山东荣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摘要] 本研究基于汉语新词,以Halliday的意义进化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提出了“意义基因”的概念,指在意义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复制,大量创造新词的最基本的意义单位。研究表明,汉语意义的演变与进化主要体现在意义基因突变和意义基因变异两个方面,并受到语言自身的微观生态环境和语言生存的宏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关键词] 汉语新词;意义进化论;意义基因突变;意义基因变异;动因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05 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06
从汉语新词看意义的演变进化及其动因
刘晓环, 王军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王军(1966-),男,汉族,山东荣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汉语新词,以Halliday的意义进化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提出了“意义基因”的概念,指在意义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复制,大量创造新词的最基本的意义单位。研究表明,汉语意义的演变与进化主要体现在意义基因突变和意义基因变异两个方面,并受到语言自身的微观生态环境和语言生存的宏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关键词]汉语新词;意义进化论;意义基因突变;意义基因变异;动因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05 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06
收稿日期:2014-12-2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概念匹配、释义与连通的衔接功能语用研究”(项目编号:13BYY1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环(1981-),女,汉族,甘肃定西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 1002-2643(2015)04-0034-06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Chinese neologisms and Halliday’s evolutionary theory of meaning, this paper aims at 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eaning gene”, which refers to the basic unit of meaning that can create abundance of neologisms by copying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meaning.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meaning mainly shows in meaning gene mutation and meaning gene variation and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micro-ecology environment of language itself and the macro-ecology environment in which language survives.
On the Evolution of Meaning and its Mo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Neologisms
LIU Xiao-huan, WANG 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neologisms;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meaning; meaning gene mutation; meaning gene variation; motivation
1.0引言
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研究的终极问题。从公元前五、六世纪古希腊时期的“名实之争”到先秦名家的“诡辩论”,从语义等于简单的编码和解码的语码论(the Code Theory)到语义属于非论证性的推理(nondemonstrative inference),从Frege的语义组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到认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语义整合性(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从意义等于大脑中的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到社会中一组可供人们选择的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意义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意义的变化,传统语言学家主要通过历时的对比,研究个别词意义的扩大、缩小或转移,无法解释和揭示出意义变化的本源。近年来,为了加深对各种语言现象的认识,语言学家们开始不断从边沿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领域获得新启发(桂诗春,2004)。鉴于此,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意义变化的规律,深化我们对意义的认识,本文拟借助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的相关思想,将汉语新词置于意义进化论和生态语言学的大框架中,分析意义演变进化的机制及其背后的动因。
2.0意义进化论与意义的演变、进化和传承
意义进化论最早由Halliday(1992)提出,其核心思想是从种系进化(phylogeny)、个体进化(ontogeny)和语篇进化(logogeny)三个层面阐述人类语言从原始语言向现代语言进化和传承的结果。意义进化论认为,原始语言的表达层面(the plane of expression)和内容层面(the plane of content)是一对一的关系。在其后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两个层面逐渐分裂,通过词汇语法系统(the lexico-grammatical system)使人类语言的使用脱离了直接的情景(immediate situation),最终使人脱离了大自然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知主体(严世清,2002)。
与其他印欧语言相比,意义的演变和进化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受汉字语符形式的制约,汉语不能像英语那样灵活造字,而只能通过意义的演变,与其他字/词相结合来满足语言灵活使用的目的。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曾采用生物科学上的一对术语“转化(transform)”和“转导(transduct)”来表示语言进化的方式。在生物学上,转化会导致基因突变从而产生新的细胞形态,而转导所导致的变异不是根本性的,不会造成原有细胞形态的改变(严世清,2012)。我们借鉴这对术语,在本研究中提出“意义基因”的概念,指在意义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复制,大量创造新词的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并以此将汉语意义的演变进化方式分为意义基因突变和意义基因变异两类。前者指一个原始词的表达层和内容层分裂,与其他词的表达层或内容层重组,构成一个新词语,表达一个新概念;后者指一个原始词的意义在新词中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还不至于导致原有表达层和内容层的分裂,与原始意义仍然有很大的联系。
2.1 意义基因突变
语言符号产生之前,实物就是意义的媒介。后来随着语言符号的出现,意义才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Harder,2010)。但是,语言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如同生物学上物种的进化过程一样,受语言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如“门”原来指建筑物的出入口,具有指称功能,是一个表达层和内容层(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所指和能指)的统一体。作为一个意义基因,“门”具有遗传性,可以进行正常复制,如“房门”、“校门”、“工厂门”等等。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新事物应运而生,出现了诸如“冰箱门”、“汽车门”等等。此时,虽然“门”的所指已经与最初的所指完全不同,不再表示建筑物的出入口,但其最基本的意义和功能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仍然起着“出入口”的作用。因此,只要是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充当“出入口”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门”,如“烤箱门”、“衣柜门”等等。但是,自从1972年美国的“水门事件(Watergate)”之后,英语中的“-gate”开始成为一个表示“社会或政治丑闻”的构词成分。受此影响,汉语也使用“门”来直接意译西方具有轰动性和爆炸性的一些政治丑闻,如“拉链门(Zippergate)”、“伊朗门(Irangate)”等。2003年“肉松门(用老母猪、病猪和死猪肉做肉松)”和“火腿门(为防蝇把半成品火腿放在剧毒农药里浸泡)”事件之后(刘桂兰、李红梅,2009),中国式的“X+门”开始迅速传播,如“手机门”、“月饼门”、“回扣门”、“捐款门”等等。在这些新生的“门族词”中,“门”的意义基因发生了突变,其最原始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能指与所指分离。“门”只保留了原始的能指,所指突变为“社会或政治丑闻”。后来,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和类推造词的大量出现,“门(社会或政治丑闻)”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很强复制功能的意义基因,被语言使用者迅速模仿,大量传播。
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出“门”的意义演变与进化过程,我们借助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的语符进化太极图,结合Collins & Loftus(1975)激活扩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的相关思想,试将“门”的意义演变与进化过程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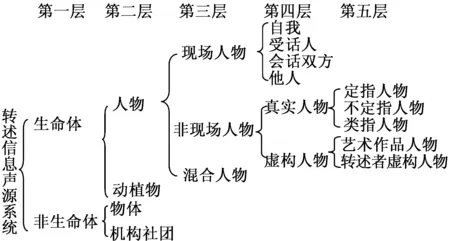
在上图中,一个完整的太极图表示一个所指和能指的统一体,“黑色半图”和“白色半图”分别表示所指和能指,“箭头”表示意义进化的方向。“X+门所指”和“Y+门能指”表示构词潜势,即可以以此进行大量的正常复制。其中,“X+门所指”的两个构词成分均为常规用法,而“Y+门能指”的两个构词成分均为非常规用法。该图表示,在语言产生之初,原始语符的意义与符号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门”作为一个所指和能指的统一体,只指建筑物的出入口。后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对事物分类的精密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用不同的概念去表达这些新生事物或新社会现象,但同时又受到语言符号有限性和人类认知经济性的影响,原来单一的符号开始裂变,所指与能指分离。分裂后,不同词的所指和能指又重新组合,构成像“车门、冰箱门”、“手机门、月饼门”这样的复合词。在第一组词中,“门”仍然有所指。但是在第二组词中,“门”的意义基因发生突变,只保留了它的能指,然后与其他词的能指或所指相结合,组成新的统一体,表达新意义。
再比如“山寨”,其原意表示“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如《水浒传》第五十一回:“吴学究道:‘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后来,随着新生事物的出现,能指与所指分离。在以下例子中,山寨只保留了它的能指,与其他词的能指或所指结合在一起,表示“盗版、不正规”,如“山寨剧”、“山寨机”、“山寨版”等等。
总之,意义基因突变会导致原始语符所指与能指的完全分裂。在意义基因突变后组成的新词中,尽管该语符与原始语符共享相同的能指,但它们的所指却各不相同。这种由意义基因突变引起的不同词的所指与能指的重组,类似于生物的遗传和进化现象。语言的意义就这样像生物的进化一样得到进化(刘辰诞,2012)。
2.2 意义基因变异
除了意义基因突变之外,汉语产生新词最常见的手段是意义基因变异。意义基因变异指一个原始词的意义在新词中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还不至于导致原有表达层和内容层的分裂,与原始意义仍然有很大的联系。如成功入选2013年度流行语的“土豪”,原指旧社会乡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和结构中,表达相关却非常不一样的意义。如:
(1) iPhone 5s/5c自取预定开启:土豪金最抢手。(光明网,2013-09-17)
(2) 四川达州现“土豪楼”,12户业主凑45万装观光电梯。(光明网,2013-12-20)
(3)土豪贼穿皮草专偷商场蔬菜肉类,称为掩人耳目。(中国新闻网,2013-12-23)
(4) 成都土豪羊肉160元一斤,食客边吃边骂。(中国新闻网,2013-12-26)
在以上由“土豪”与“金”、“楼”、“贼”、“羊肉”等组成的新的统一体中,“土豪”的意义基因发生了变异。它不再指旧社会在乡里凭借财势横行霸道的坏人,而是生动形象地映照出了新富群体土气粗野而又显赫华丽的“暴发户”心态或带有炫耀倾向的产品。尽管如此,这些新词的出现还没有导致“土豪”原有表达层和内容层的完全分裂。“土豪”在新词中的意义与原始意义之间仍非常相关,都含有钱多、奢华之意。再比如,汉语新词中的“屏奴”、“房奴”或“学霸”、“考霸”等都属于后面一个构词成分的意义发生变异的新词。如“奴”的本意是“受人役使,没有人身自由,心甘情愿供人驱使”。在新词中,“奴”的最基本的意义仍然是“被控制、被束缚的人”,只不过是被没有生命的“屏”、“房”等控制束缚而已。
总之,与意义基因突变相比,意义基因变异不会导致原始语符能指与所指的完全分裂。在意义基因变异产生的新词中,该语符不但与原始语符共享相同的能指,而且它们的所指之间虽然非常不同但仍然有很大的联系。变异后的意义往往是新旧内容的混合体,旧的内容不会完全丧失,而是部分地保留在新词中(杨婕,2014)。
综上所述,意义基因突变与意义基因变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符所指的不同上。在意义基因突变组成的新词中,该语符与原始语符尽管共享相同的能指,但它们的所指之间毫无联系。而在意义基因变异组成的新词中,该语符与原始语符不仅共享相同的能指,而且它们的所指尽管非常不同但仍有联系。总之,当一个词的意义基因发生突变或变异,可以通过大量复制广泛传播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意义基因,具有了构词的潜势。这些由意义基因发生突变或变异产生的新词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是普通大众的心理反映,由语言使用者构建而来。因此,只要它们能够被言语共同体普遍接受,就会在语言生态系统中获得生存权。但需要注意,尽管原始语符的意义基因发生了突变或变异,但是它的原始意义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突变或变异后产生的新意义并存。
3.0意义演变进化的动因
意义的演变与进化受到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既来自于语言自身的微观生态环境,也来自于语言赖以生存的宏观生态环境。
3.1 语言自身的微观生态环境
生态语言学(Haugen,1972;Makkai,1993)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相似,都是由多元因素组成。这些因素之间既相互竞争又密切合作,共同促进有机体的发展。语言全息论(钱冠连,2002)也认为语言与宇宙同构。语言的级阶(rank)——“语篇-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词”与生物界的“门-纲-目-科-属-种”都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呈现出不同层级性的一个全息的(holistic)系统。而且,每个层级都由更小的微系统组成,比如每个语言单位都是形、音、义三者组成的统一体。
首先,就汉字的构造方式来讲,汉字的部首具有与英语字母类似的造字功能。它们都是数量有限的、最基本的结构单位,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正字法规则进行组合造字/词。但是,与英语字母相比,汉语属于非线性文字,汉字的笔画以及由笔画组成的部首的位置不像拼音文字的字母那样可以灵活地出现在一个单词的任何位置(如词首、词中和词尾)。在汉语526个常用部件中(潘钧,2004),只有极少数的部件位置比较灵活,能够出现在汉字的上、下、左、右、中。如 “口”可以出现在“呆”、“杏”、“吃”、“扣”、“周”等字中。除此之外,汉字大部分部件的位置都非常固定。如“讠”、“饣”、“扌”等只能出现在汉字的左边,“卩”、“攵”、“刂”等只能出现在汉字的右边,“”、“艹”、“”等只能出现在汉字的上面,“灬”只能出现在汉字的下面。因此,受正字法规则的影响,汉语不能像英语那样灵活造字,这就使得汉字的常用语符数量非常有限。
其次,就汉语的语音来讲,现代汉语普通话一共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假如每个声母都可以和所有的韵母拼合,再分别配以四个声调,那么就可以产生836个声韵结合体,3344个音节。然而,实际上音节的基本形式只有406个,而能与四个声调相拼的只有180个,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其他的都只能与四个声调中的某一个、两个或三个相拼。这样,实际存在的基本音节就只有1265个(卢偓, 2001)。若以6763为汉字的总数(计算机标准字库字数)(王寅,2001),那么平均每个音节就要表示5.38个汉字。因此,汉语语音系统决定了汉语不能给每个汉字赋予不同的发音。
然而,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新事物和新现象的出现势必会产生概念上的需求。但不论从正字法规则还是从语音系统来讲,汉语都不能像英语那样可以通过派生或屈折变化的方式产生新字,或者为每个新生事物专门创造一个新字。因此,为了满足不断产生的概念表达的需要,在音、形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只有相对开放的语义系统被迫发生突变或变异,才能适应新的表达需求,维持整个语言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
3.2 语言生存的宏观生态环境
生态语言学认为语言既是动态发展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同时它也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受到语言使用者以及外界的物质环境、社会文化等宏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约(Fill & Mühlhäusler, 2001; Mühlhäusler,2003)。因此,语言意义的演变与进化不是自足的,而是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如果离开语言的使用环境和语言的使用者去谈意义,“意义”就毫无意义。
首先,意义基因的演变与进化由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的影响使新事物和新现象不断涌现,由此也就产生了新的概念需求。但是,因为受到语言自身的微观生态环境,即汉语正字法规则和语音系统特殊性的影响,已有词汇的意义不得不发生突变或变异来维持语言系统与外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现代发达的传媒技术也大大加速了意义演变与进化的进程。与语言的模因(Dawkins,1976)类似,意义的演变与进化也必须经过大量的传播和复制才能够传承下去。媒介的发达程度与意义基因的传播和复制速度成正比。互联网的普及使突变或变异后的意义在新词中迅速传播出去,并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逐渐稳定下来,最终演变成为字典中的一条概念义。因此,每一次意义基因的突变或变异都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发展,每种意义基因的变体都负载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其次,意义基因的变体能够在语言中得以复制和传承主要依靠语言的使用者。语言的本身不会发生演变,是人通过自身的行动使语言发生变化(Croft,2011)。模因论(Blackmore,1999;何自然,2014)认为语言模因的触发、复制与传播受到语言模因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以及模因宿主(人)的能动作用的影响。语言意义的演变与进化亦是如此。人处于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内部的语言心理表征的界面上,是人推动着意义的演变与进化。意义的演变与进化必须要遵循人类的认知规律。由于人类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在语言的变迁与发展中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总是以经济省力为最主要的法则,所以当认知和表达之间出现空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填补时,人们更倾向基于已有的词汇形式或语法形式拓展原有词汇的语义以表达新概念,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发明新符号去标记。
总之,如同生物学中的生态因素一样,意义的演变与进化受到言内和言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汉字语符形式和语音系统的特殊性使汉语的语义系统被迫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加速了意义基因的突变或变异,语言的使用者对其广泛传播和复制,使意义的演变与进化成为可能,并使突变或变异后的意义基因能够传承下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尽管语言的意义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但是意义的演变与进化总是缓慢有限的。因此,只要发生突变或变异的意义基因个体数量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整个语义系统还是能够抵制突变或变异的影响而保持稳定。
4.0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意义的进化与演变既要受到语言自身的微观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要受到来自语言生存的宏观生态环境的影响。当一个词语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表达的需求时,它的意义就会受到来自语言生态系统内外压力的影响,或突变,或变异。社会交际的需要为语言意义的演变提供了环境,已有的正字法规则、语音系统和人类的认知规律支配和制约着语言意义的演变。语言意义的演变如同生物学上的有机体为了适应新的生态环境而发生演变的过程一样,具有较强复制功能的意义基因会在意义的演变进化中遗传下去,而那些不能很好地为人们交际服务的意义,会随着使用频率的降低被其他强势意义基因替代而逐渐消亡。本研究借助进化生物学的相关思想,将汉语新词置于意义进化论和生态语言学的大框架中,分析了意义的进化演变及其动因,这将会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意义演变的规律,深化我们对意义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Blackmore, S.TheMemeMachin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Collins, A. M. & E. F. Loftus. A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J].PsychologicalReview, 1975,(6):407-428.
[3] Croft, W.ExplainingLanguageChange:AnEvolutionaryApproach[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4] Dawkins, R.TheSelfishGen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5] Fill, A. & P. Mühlhäusler (eds.).TheEcolinguisticsReader:Language,EcologyandEnvironment[C].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6] Halliday, M. A. K. How do you mean?[A]. In M. Davies & L. Ravelli (eds.).AdvancesinSystemicLinguistics:RecentTheoryandPractice[C]. London: Pinter, 1992.20-35.
[7] Halliday, M. A. K. & C. Matthiessen.ConstruingExperiencethroughMeaning:ALanguage-basedApproachtoCognition[M]. London: Continuum, 1999.
[8] Harder, P.MeaninginMindandSociety:TheSocialTurninCognitiveLinguistics[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0.
[9] Haugen, E.TheEcologyofLanguag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0] Makkai, A.Eco-linguistics:TowardsaNewParadigmfortheScienceofLanguage[M]. London: Printer, 1993.
[11] Mühlhäusler, P.LanguageofEnvironment,EnvironmentofLanguage:ACourseinEcolinguistics[M]. London: Paul & Co Pub Consortium, 2003.
[12] 桂诗春. 外研社当代语言学丛书总序[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13] 何自然. 流行语流行的模因论解读[J]. 山东外语教学,2014,(2):8-13.
[14] 刘辰诞. 句法结构创新的社会与认知心理动因——语言基因变异遗传的一般机制[J]. 外语研究, 2012,(5):8-14.
[15] 刘桂兰,李红梅. 从模因论角度看“XX门”现象 [J]. 外语学刊,2009,(2):70-73.
[16] 卢偓. 现代汉语音节的数量与构成分布[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6):28-34.
[17] 潘钧. 现代汉字问题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18] 钱冠连. 语言全息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9]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0] 严世清. 论韩礼德的语言哲学思想[J]. 外语研究,2002,(2):7-19.
[21] 严世清. 意义进化理论溯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1):45-53.
[22] 杨婕. 模因论视角下群体类流行语的词缀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14,(2):20-24.
学术英语教学改革专栏(主持人:蔡基刚)
主持人按语: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高校“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教育部要求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要“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如何使高校新生从高中学习的通用英语过渡到用英语学习他们的专业,继而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国际竞争力,学术英语是必然的选择。学术英语教学不仅学习以下3种学术技能:(1)用英语听讲座/讲课、记笔记、阅读专业文献;(2)用符合学术规范和格式的英语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大会摘要和学术文章;(3)用英语宣读论文,陈述演示研究成果,参加学术讨论。还培养以下4种学术素养:(1)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的能力;(2)分析和综合从各个渠道搜索来的信息,并对此进行评价、提出问题,形成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3)规避剽窃,遵守普世的学术规范能力;(4)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开展基于项目研究的沟通能力。因此,学术英语不仅适合本科生,也适合高职高专的学生。在经济结构和模式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没有经过学术英语训练的学生无论在自己的专业学习还是职业生涯中都走不多远。正因为如此,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顺应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潮流,第一次在指导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文件中把学术英语(EAP)纳入了大学英语教学主要内容。一轮以学术英语为核心内容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正拉开大幕。专栏中有3篇论文是2015年全国学术英语教学研讨会的主旨发言,另外一篇是介绍上海高校学术英语教学情况的。我们希望这些论文对全国开展学术英语教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