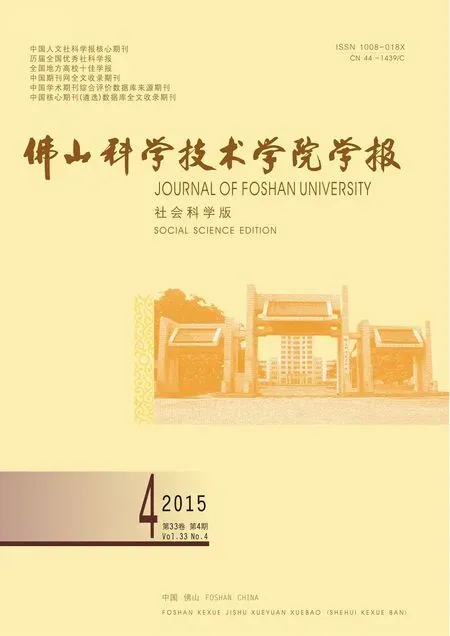解读《骨》中三姐妹的身份建构模式
2015-12-30余星蔡永贵
余星,蔡永贵
(1.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广东梅州514015;2.嘉应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解读《骨》中三姐妹的身份建构模式
余星1,蔡永贵2
(1.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广东梅州514015;2.嘉应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用女性主义理论、离散理论和翻译理论对女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骨》中三个女儿的自我身份建构模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到《骨》为美国华裔女性提供了摆脱二元文化以及性别对立的束缚,在“第三空间”内确立女性自我主体性和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的有效途径。
伍慧明;《骨》;文化冲突;身份建构
小说《骨》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描写的是一个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三个女儿家庭的故事。《骨》自1993年出版以来,迅速畅销全美,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获得过多种荣誉和奖项,并入选1994年福克纳笔会决选书单,被收录进“手推车奖”文选中。作者伍慧明也因此被称为美国华裔文坛的后起之秀。本文用女性主义理论、离散理论和翻译理论对作品中三个女儿的自我身份建构模式进行分析,证明《骨》为美国华裔女性提供了摆脱二元文化以及性别对立的束缚,在第三空间内确立女性自我主体性和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的有效途径。
一、身份危机的产生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即地位。基尔·克鲁斯和尼尔·瑞维克认为:“身份的建立,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是社会生活一个普遍、重要的方面”[1]。实际上,身份涉及诸如“我是谁?”、“我属于哪儿?”、“我该去向哪儿?”等等问题。在广义上,“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2]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经常受到中西文化的冲击,他们在美国受教育、竞争求生存,在思想上也更倾向于接受美国文化与价值观,他们把自己当作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这使得新一代华裔极易产生一种身份危机感:“我究竟是谁?”这种“我究竟是谁”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身份危机感导致了许多新生代华裔的人格分裂,他们抑郁、烦闷、迷茫。这种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感和孤独感促使他们在两种人格倾向中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只有当他们最终接受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才能真正解决自身的身份危机。
二、三姐妹的身份建构模式
伍慧明的小说《骨》描述了美国第二代华裔们对身份的求索,正如其它生活在美国的少数族裔的女性一样,《骨》中的三个女儿莱拉,安娜和尼娜也经历了如何构建自我身份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儒家思想统治着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影响深远。传统的儒家思想要求个人以家庭和集体利益为重,子女只有对父母顺从才算是孝顺。妥协和退让是维持和谐,避免争斗的必要处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的儒家集体主义文化往往过分强调‘大我’而忽略和压制了‘小我’”[3]。相反,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推崇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选择的自由,往往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当第二代华裔接触到与传统的中国儒家集体主义文化不一样的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时,“大我”和“小我”之间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此外,封建思想倡导的是父权社会,女性的自我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唐人街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受到父权话语的影响。正如《骨》一书的开头揭示了唐人街父权社会对女子的厌恶态度。而新一代的华裔女性深受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勇敢地挑战父权社会,敢于打破沉默和消音,释放被父权话语压抑很久的女性自我。在小说中,安娜在两种文化冲突和父权话语的压抑下最终选择了自杀来向生存困境发出最悲壮的抵抗。
在梁家的三个女儿当中,二女儿安娜是跟父亲利昂和中国文化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作为妈妈和利昂的第一个孩子,安娜是“妈妈的血,是父亲的骨”。她的到来对于延续父母的婚姻和帮助父母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带来了希望。安娜很聪明,特别讨人喜欢,且很贴心。安娜和利昂的关系很好,在利昂出海后她会一天天的数日子等他回来。此外,安娜还是家庭的调停人。当利昂因为妈妈和汤米洪的绯闻搬出唐人街时,是安娜用她的坚定与耐心把利昂找回家。安娜是唐人街社区跟中国传统礼仪连接的体现,在新年安娜和利昂会进行祭拜的仪式。对父母来说,安娜是顺从和孝顺的,而她与利昂之间的对某些中国传统仪式和文化的继承使得安娜和整个家庭紧密相连,使得她在唐人街找到归属感。
但是,安娜与奥斯瓦尔多的恋爱改变了她与父母的关系,特别是与利昂的关系。由于在与翁家合作开洗衣店失败后,利昂把怒气迁怒到翁家儿子奥斯瓦尔多身上,利昂反对安娜与奥斯瓦尔多的相爱,要求安娜与他分手,当安娜拒绝时,利昂甚至用断绝父女关系来威胁安娜:“你再也不是我的女儿,我再也不是你的爸爸了”[5]203对于安娜来说,传统的中国文化教导她当家族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家庭的一分子理所当然地应该放弃自己的利益,顾全家族的利益和面子。但是在美国学校接受的教育和文化又向她灌输了自身利益为上的个体主义思想。尽管安娜跟利昂关系亲密,但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独立女性,她并不能忍受父母对她追求爱情的控制。安娜做出了自己的抵抗:“利昂逼得越紧,她和奥斯瓦尔多的关系就越好”[4]204。安娜辛苦地在夹缝中挣扎,找不到突破口。在离开家与男朋友住在一起后,安娜也并没有得到平静,她选择脱离在唐人街的家,但却又无法融入外面的世界。在她像永远没有归宿的漂流瓶一样漂浮时,她选择了一种激进的方式终止她孤苦的灵魂无止境地游荡。此外,是安娜在家庭中的位置决定了她尴尬的境地。安娜无法像姐姐莱拉一样顾全大局,暂时放弃个人追求,照顾父母的感受;她也不可能像妹妹尼娜一样彻底地与家人决裂,离开唐人街去追寻自己的快乐。安娜出生就是夹在中间的孩子,在生活中她也扮演着文化居中人的角色,也就是这样一种属性给她带来的苦痛与压力,最终将她推向绝望的深渊。
安娜的死亡使整个家庭陷入悲伤和自我谴责当中。获知安娜死亡,利昂痛苦的选择随船出海去好望角。利昂还把安娜的死亡归咎到他没有兑现对梁爷爷的许诺把他的遗骨送回国。因此,利昂试图在中国公墓寻找梁爷爷的墓碑,正如莱拉所说“利昂正在寻找他失去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更多的还是寻找安娜”[4]108。利昂没有意识到,是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思想毁灭了安娜。利昂爱安娜,但他的爱是自私的,他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女儿,剥夺了安娜追求幸福的权力。安娜的死使利昂陷入自责、抱怨当中,但最终他还是意识到他对家庭的责任、更加珍惜家庭和家庭里的其他成员。正如利昂告诉莱拉的一样,构成家庭的是时间,不仅仅是血缘。安娜为了成为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主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离散”(diaspora)一词本来是用来形容流落各国的犹太人,可以上溯至《圣经》里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下的“出埃及记”。现在,“离散”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5]伴随离散而来的是离散者所经历的文化冲突,个人的文化认同,身份的模糊、困扰、危机和自我分裂等。而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斯图亚特·霍尔说,移民群体是通过改造和差异的不断生产来更新自身的身份的。作为第二代美国华裔,他们的离散经历导致了归属感的缺失。在《骨》中,最小也最叛逆的三女儿尼娜离开唐人街,把自己放逐到东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自我。
在利昂家的三个女儿中,尼娜是最叛逆也最美国化的一个。尼娜拒绝接受自己有中国血统的事实,也不愿理会在唐人街发生的任何事。在尼娜心中,她永远把家人摆在最后一位。尼娜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把自己当作家里的一分子。她对家中的困境与忧虑冷眼旁观,因为她认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与选择。尼娜一味地迎合美国的价值观,力争与中国传统文化划清界限。她不愿住在唐人街,而只乐意去美国餐厅。对中国的传统礼仪,尼娜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当利昂计划为安娜筹备葬礼时,尼娜对此嗤之以鼻。尼娜完全排斥中国文化而接受美国文化,为了逃避家庭的不幸,她选择远走高飞去纽约生活。
虽然尼娜远离了唐人街的家,她的内心仍然充满矛盾和孤独。当她与莱拉谈论到父母时,尼娜内心是不安的,她还在与自己身上流淌的中国血脉做斗争。莱拉曾这么描述尼娜,她拥有母亲的头发、利昂的笑容,但她看起来脆弱了许多。由于尼娜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尼娜的身份已经出现了危机,接下来等待她的是比跨越太平洋艰难得多的旅程,因为“试图抛弃自己所属的社群的人将要严重地迷失方向。他们的世界会被认为失去意义,失去任何有意义的可能性。这种痛苦而可怕的状态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6]
陷在两种文化冲突的压力中,尼娜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己的属性认同。霍米·巴巴认为,离散者是离家者(un homed),但是因为有“非家幻觉”(the homely)的伴随,离家者事实上并非无家可归(homeless)[7]。处于离散身份的人很容易在面对两种文化空间和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时遇到困惑。为了从这种纠缠中释放出来,尼娜当了空姐在空中寻求自由和独立。飞行可以给尼娜一种自由感,因为“飞行航班可能会打破单纯是美国或中国的‘家’这一空间界限”。[8]因此,为了获得个人属性,一个人必须寻求“飞行”来摆脱二元对立以此在一个可协商的空间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尼娜在两种文化和两个世界当中协商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一名离散者,尼娜从未定居在中国或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而是经常飞来飞去。通过移居,尼娜不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当中,因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可以帮助她拓宽视觉,而这有助于她接受和继承中美文化。于是尼娜从唐人街搬到纽约,从地面到空中,从美国到中国。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下,身份属性,特别是离散者的身份属性,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他们在多元文化背景的移动而改变的。离散群体的家园是动态的,家随人动。对于尼娜来说,她的身份属性也是随着她更换地理位置而短暂改变的。“离散族裔的家,与其说是一个地理位置,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感情空间”[9]。通过不停地迁移,尼娜的文化属性不再固定在是一个美国人、中国人还是其他族裔的人,而是具有变化性和流动性的。因此,身份属性是由个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决定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尼娜在不停地迁徙中不断地重构自己的身份属性,并最终实现流动身份。

霍米·巴巴在其代表专著《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在两种不同文化接触的地方存在一个“第三空间”的观点。这一空间是一片“间隙性空间”、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10]。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是一个混杂的、模糊的、中间性的表意空间。而这个新兴的文化空间,无论是对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颠覆性,使双方的文化和话语都无法保持其内在连续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多元文化并存状况下的身份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骨》中的大女儿莱拉与其他美国华裔一样都面临着少数族裔自我身份建构的问题。莱拉起初受到双重文化冲突困扰,但她选择积极的协调,采取了超越二元对立的方式,在“第三空间”中重新建构了自己的身份。
作为长女的莱拉在家庭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她非常好地维系着与继父利昂之间的关系。她能够充分理解父母内心的苦痛,并承担起长女的责任。在应付警察因利昂使用多个化名而对他身份进行盘查时,莱拉翻遍了利昂搜藏的所有文件后,她了解到老一代移民的辛酸,知道利昂这位膝下无子的父亲不仅在唐人街得不到任何尊重,甚至在美国社会也是无足轻重,始终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但这并没有消减莱拉对利昂的尊重和爱。尽管他们不是亲身父女,但胜似亲身父女。另一方面在对长辈尊重,照顾的同时,莱拉也并没有疏远她的妹妹们。她理解她们,对她们抱以宽容的态度。由于个性上的差异,三姐妹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由于双重文化背景的冲突,美国华裔极易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扰。在莱拉看来,她是地道的美国人,旧金山是她唯一的故乡,中国只是别人口中的一个遥远的故国。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与在美国接受的文化与价值观使得莱拉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妹妹安娜的死让莱拉自责和痛苦,觉得自己被分裂开来了。而父母对莱拉的忽视使得莱拉意识到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是模糊的。更令她纠葛的是她还在母亲与男友梅森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莱拉既想做孝顺女儿在家照顾母亲,另一方面又想离家寻求自己的新生活,这种矛盾的心理使莱拉纠结徘徊,无法定义自己。当有人问到莱拉是不是中国人时,她回答不是,但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当一些人在开中国人的玩笑时,她内心却觉得刺痛。
莱拉深陷于两种异质文化身份的困境中,经过一番挣扎,莱拉最终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的方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有效地解决了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身份。
首先莱拉是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翻译者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莱拉同时懂得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在学校,她的工作就是做一些咨询与翻译的工作,将外来移民与他们孩子的意愿与想法传达给学校。在家中,她扮演着父母的传声筒的角色,将只会用汉语说话与思维的父母的意见转述给美国社会。作为专业翻译,莱拉在翻译中不拘泥于原意。相反,她会试着解释与修正双方的意思,使它们更容易接受,也使得父母的生活更加容易。例如,当警察问到安娜的死因时,莱拉避重就轻,并没有将父母的说法如实地翻译,因为她觉得以西方的思维方式,警察肯定无法理解这些解释。当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与经历碰撞到一起时,其理解与调和的难度可想而知。作为两种文化的媒介,莱拉无意去强调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她努力地运用自身双语与双文化的优势,过滤、涮选、剪切,使不可理解的变成可理解的,不可说的变成可说的。这使得两种语言与文化得到更好的理解与沟通,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冲突与矛盾。莱拉作为两种文化的中间人,不仅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而且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话语。
另一方面,莱拉对于安娜的死也曾一度自责不已,她想要一种新生活。莱拉清醒地意识到女性对命运的选择也是表示存在的一种方式。女性应有自己的选择、要求与主意。安娜的自杀是她自己的决定,“我该接受,我当时是救不了安娜的,能救她的那个人不是我。我必须相信那是她自己的选择”[4]65。
在小说的结尾,莱拉最终决定离开唐人街在外面的世界寻求更广阔的生活。唐人街上发生的一切已深深地烙入她的脑海中,成为她永远的记忆,并融入了她的生活。她会带着这些传统记忆继续自己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经历与记忆已渗透进莱拉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造就她的思想、文化和身份的重要部分。经过努力,莱拉最终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的方式,在“第三空间”重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身份。
三、结语
对于夹杂在多元文化冲突与矛盾中的美国华裔来说,身份建构问题一直是个困惑已久的话题。在《骨》中,伍慧明描述了处于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第二代华裔美国女性所经历的身份危机以及寻求自我身份的不同经历。批评家一直在理论上寻找一个“居中的空间”来消除文化对立,而伍惠明则用鲜活的形象证明了此理论的可行性。《骨》为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提供了摆脱二元文化以及性别对立的束缚,在“第三空间”内确立女性自我主体性和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的有效途径。这也正是《骨》被认为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杰出作品的原因之一。
[1]KRAUSE J, RENWICK N. Id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M].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1996: 39.
[2]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J]. 外国文学, 2004(2): 37-39.
[3]程爱民, 邵怡, 卢俊. 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8
[4]伍慧明. 骨[M]. 陆薇,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11.
[5]钱超英. 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J]. 中国比较文学, 2006(2): 77-89.
[6]丹尼尔·贝尔.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92.
[7]童明, 飞散,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国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23.
[8]HUANG S. Mobility and Home: Shifting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Race, and Nationality in Chinese Diasporic Litera ture[M].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06:66.
[9]徐颖果. 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12.
[10]生安峰.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0.
(责任编辑:张惠fszhang99@163.com)
A Probe into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Models of the Three Sisters in Bone
YU Xing1, CAI Yong-gui2
(1. Meizhou Normal School,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By applying feminist,diaspora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models of the three daughters,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e that Bone provides the ethnic minority women in America with an inspiration to dispel the binary opposites of the cultures and genders and therefore establish their women subjective identity in the“Third Space”.The novel finally depicts vividly the identity crisis caused by Sino-western cultural conflicts for the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daughters and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establishing self-identity.
Fae Myenne Ng;Bone;cultural conflicts;identity construction
I712.074
:A
:1008-018X(2015)04-0056-05
2015-04-20
梅州市社科联、嘉应学院201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4SKB02)
:余星(1983-),女,广东梅县人,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讲师。蔡永贵(1982-),男,广东新丰人,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