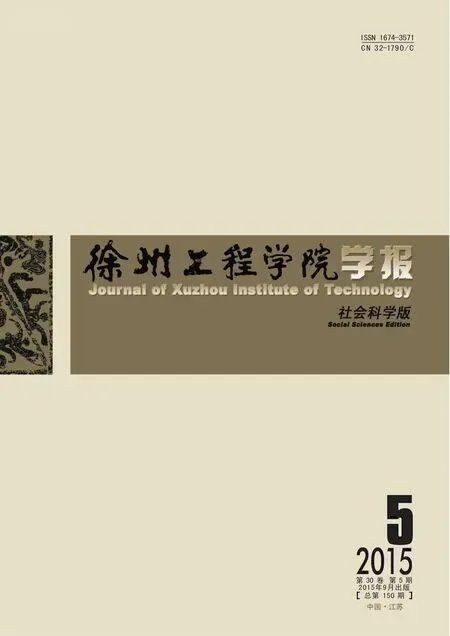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初探
2015-12-28胡安徽
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初探
胡安徽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摘要: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是该区内部各地域之间以及与外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其主要特点是相对发达。表现有三:一是有水路的县数量较多;二是一条水路贯穿数县,水上交通网络稠密;三是水路流经许多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特点在宋元明清时期仍得以继承和发展。尽管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相对发达,但险滩和季节性降水等因素一定程度影响了水路交通的通畅。
关键词: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特点
收稿日期:2015-05-22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重大招标项目“明代贵州官修省志生态资料辑录与研究”(2013ZD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安徽(1971- ),男,河南唐河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史和历史地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志码:A
武陵民族地区是位于我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过渡带上的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处在华中和西南地区的交界处,面积约11.7万平方公里。学界关注本区的著述很多,但对该区唐代水路交通的专题研究却相对较少,涉及该研究的有: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1]、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2]、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3]等。由于侧重点不同,上述论著对唐代本区水路交通的研究着墨不多,仍有开拓空间,故拙文即对此略作探讨。
一、武陵民族地区水路概况
武陵民族地区以山地为主,平均海拔在1 000米左右[4]152,陆路交通比较困难、落后,对本区内部以及本区与外界的商贸往来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与陆路交通情况不同的是:由于本区年均降水量在1 200~1 700毫米之间[5]91,降水丰富、河流众多,本区水路交通相对便利,除长江干流外,还有乌江、清江、沅江、澧水等支流,支流的支流更是不计其数,它们共同构成了武陵民族地区密集的水路通道。
长江干流流经本区的石柱和巴东,虽然流经区域的面积不大,但由于武陵民族地区的河流多最终注入长江干流,因此,长江干流在本区水路交通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乌江,又称黔江,是武陵民族地区的重要河流。本区的思南、沿河、印江、务川、石阡、德江、黔江、彭水、酉阳(部分)等县都属该流域,在本区流域面积约1.12万平方公里,接纳的主要河流有印江河(木黄河)、甘龙河、濯河(唐岩河)、洪渡河、郁江、芙蓉江、大溪河,在重庆市的涪陵汇入长江。乌江流经本区的河段均可通航。
沅江,又称沅水,是武陵民族地区的又一重要河流。本区湘西州和怀化市所属政区及重庆秀山、酉阳(部分)均位于沅江流域。沅江主要流经芷江、会同、洪江、怀化、溆浦、辰溪、泸溪、沅陵等县市,经桃源、常德、汉寿注入洞庭湖,主要支流有舞水、辰水、武水、酉水、渠水、巫水、溆水等。沅江在洪江以上为上游,地属贵州高原,峰回水转,河道弯曲,水势湍急。洪江至沅陵为中游,滩陡礁多浪险,怪石巉岩雄峙江面,过去船家视为畏途。沅陵以下属下游,山势低落,至桃源入平原,江阔波平,舟行通畅。
清江,古名夷水,亦名圤水,是武陵民族地区的另一主要河流,发源于湖北恩施州利川市齐岳山龙洞沟。清江流域地跨恩施州的利川、咸丰、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鹤峰与宜昌市境内的五峰、长阳、宜都等10个县(市),流经利川、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长阳,在宜都市陆城镇注入长江,全长440公里,流域面积达1.7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0%以上。清江支流众多,左岸各级支流有49条,右岸有56条,河长一般较短,主要支流有忠建河、马水河、野三河、龙王河、招徕河、丹水、渔洋河等。清江两岸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峰峦叠峰,其干流及渔洋河部分河段可通航。
澧水也是武陵民族地区的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湖南桑植杉木界,流经桑植、永顺、张家界、慈利、石门、临澧、澧县、津市,注入洞庭湖,干流全长约390公里,总落差约620米,平均坡降1.59‰,流域面积1.85万余平方公里。桑植以上为上游,崇山峻岭,山峰海拔2 000米左右,峡谷壁立,河床陡峻,滩多水急。桑植至石门为中游,峡谷与盆地相间,大部为丘陵。石门以下为下游,两岸山势较低,为洞庭湖冲积平原。接纳的河流主要有茅岩河、上岩河、中岩河、下岩河、溇水。澧水流域森林资源较丰富,航运较发达,干流津市以下终年可通航小型轮船,桑植至津市中水期可通行14~30吨木船,枯水期仅能通航3~10吨木帆船。
综上可知,长江干、支流几乎流经武陵民族地区的每一个县(市、区),将该区的几乎所有政区通过水道连接起来,同时,也正是通过水道,武陵民族地区与外部区域的联系更加便利。
二、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特点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唐代武陵民族地区的水路通道亦相当发达。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乌江、沅江、清江、澧水等水系和河流将许多府(州)、县联系起来,构成了较为发达的水运交通网,为武陵民族地区各类商品的外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书》[6]《元和郡县图志》[7]《太平寰宇记》[8]等文献记载了历史时期武陵民族地区的河流状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汉书》所列水道在唐代仍然存在,故将其视为唐代资料的一部分;《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以前(见《四库总目提要》卷68《史部地理类一》),宋朝从建隆元年(960年)建国到太平兴国九年,仅经历24年,在没有大的地质变动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河流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含五代十国时期)发生重大变化,故《太平寰宇记》所载河流,可视为唐后期的材料。现据上述三书列“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河流分布表”如下。

表1 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河流分布表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六》载:“溆浦县,本汉义陵县地”。《汉书》卷28上《地理志八》载,义陵,“序水所出,西入沅”,说明汉代义陵县有序水(即溆水)。宋代《元丰九域志》卷6《荆湖路》载,溆浦县,“溆水,县西三十里,汉志作序水”,说明宋代溆浦仍有溆水。既然汉代和宋代文献记载溆浦县均有序(溆)水,且溆浦县治所未有变化,那么唐代溆浦县也当有溆水存在。

续表1 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河流分布表
由表1可知,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最主要的特点是水路发达,具体表现如下。
1.有水路的县数量较多。唐代本区有河流分布的县33个,约占本区38县的87%*这38县分别是:辰州的沅陵、卢溪、麻阳、叙浦、辰溪(5县),奖州的峨山、渭溪、梓薑(3县),施州的清江、建始(2县),溪州的大乡、三亭(2县)、叙州的龙标、朗溪、潭阳(3县),锦州的卢阳、洛浦、招喻、渭阳、常丰(5县),思州的务川、思王、思邛(3县),费州的涪川、多田、城乐、扶阳(4县),黔州的彭水、黔江、洪杜、洋水、兴宁、都濡(6县),以及峡州长阳、忠州南宾、归州巴东、澧州石门和慈利,合计38县。,且遍及本区所有的州,其中5州所属县域全部有河流,如黔州所管6县(彭水、黔江、洪杜、洋水、信宁、都濡)均有河流分布,叙州所辖3县(龙标、朗溪、潭阳)、思州所属3县(务川、思王、思邛)、费州所属4县(涪川、多田、城乐、扶阳)和施州所管2县(清江、建始)亦都有河流。所辖县全部有河流流经的州占全部9州(即施、黔、思、锦、溪、辰、叙、奖、费)的约56%。另据《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统计,唐代武夷山区(位于今江西、福建交界)16县有水路*即信州辖5县(上饶、玉山、弋阳、永丰、贵溪)、虔州辖7县(赣、南康、信丰、大庾、雩都、虔化、安远)、建州管5县(建安、浦城、邵武、将乐、建阳)、汀州管3县(长汀、沙、宁化)、抚州辖4县(临川、南城、崇仁、南丰)计24县。其中贵溪、上饶、玉山、弋阳、赣、雩都、安远、虔化、信丰、建安、浦城、邵武、将乐、建阳、长汀、沙等16县有河流记载。按,统计时以《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县级政区数为准,综合统计《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的相关道、州的河流数。,有水路的县占唐代武夷山区24县的约67%。显然,与武夷山区水路交通相比,武陵民族地区有水路的县数量较多,显示出本区水路交通相对发达。
2.一条水路贯穿数县,水上交通网络稠密。如涪陵江(即乌江)流经涪川、多田、扶阳、城乐、务川、洪杜、彭水、信宁等县,又如夷水(即清江)流经建始和巴东等县,渭溪水经过峨山、渭溪和渭阳等县,再如思邛水(即印江河)流经洛浦、思邛、思王诸县,还有沅江及其支流溆水流经溆浦、辰溪、沅陵等县,卢水则经过卢阳、卢溪2县。由于武陵民族地区的河流最终分别注入长江及其支流乌江、沅江等,因此,这些流经数县的河流实际是将不同的县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相对稠密的水上交通网络。
3.水路贯穿了许多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武陵民族地区共有9州5县,其中有8州(黔、辰、施、思、奖、费、锦和叙州)的治所有河流经过,约占所有州数的89%,如辰州治所沅陵、黔州治所彭水、奖州治所峨山、锦州治所卢阳、费州治所涪川、思州治所务川、叙州治所龙标和施州治所清江等,而且部分州、县的治所就建在江河边。如思州治所务川县,“涪陵水,在县西四十步”,辰州治所沅陵县,“沅江在县南二十里”,费州治所涪川县,“内江水经县北一百五十步”。再如思邛县,思邛水“经本县四十步”,多田县,“涪陵江水,经县南五十步”,辰溪县,“沅江在县南二百步”,信宁县,“涪陵江水去县二里”,潭阳县,溪水在县南二里。古代,州、县治所一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河流连接州县的治所,实际是将州、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联系起来。
三、唐以后武陵民族地区水路变化
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的特点在宋元明清时期仍得以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河流流经的行政单位数量增多。如宋代沅州麻阳县(治今湖南怀化市麻阳县东),“有辰水”,诚州渠阳县(治今湖南怀化市靖州自治县),“有胜山、渠河”[9]276-277。又如明代石砫宣慰司(治今重庆石柱县),“又有三江溪,即葫芦溪之上游也”,酉阳宣慰司(治今重庆市酉阳县),“东南有酉水,流合平茶水,至湖广辰州府合流于江”[10]1049。再如清代古丈坪厅(治今湖南湘西州古丈县),“城河自蝦公潭发源流经百里绕城而行,迳出罗依溪市入酉水,……春夏可行小舟转输土货,于外亦便”*光绪古丈坪厅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铅印本。。有江河流经的行政单位数量的增多,反映了水上交通网络的扩大。二是不少村镇成为水上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位于猛峝河(酉水支流)的永顺府王村(今湖南湘西州永顺县王村镇,又称芙蓉镇),“上通川黔,下达辰常诸处,为永郡通衢,水陆码头”*乾隆永顺县志,乾隆十年(1745)刻本。,显然王村成为猛峝河上水路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又如长乐县(治今湖北宜昌市五峰县)渔阳关,地处清江支流渔洋河,自清代建成码头以来,“水陆交通,商贾云集,四乡各市货物多从此拨卖”、“轮广周回约计二百余里,人烟聚集,不下千百之家”、“舟秋船便捷,直下清江峡口”*光绪长乐县志,光绪元年(1875)增刻本。,可见,渔阳关成为清江流域水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码头。再如会同县洪江镇(今湖南怀化市洪江市),“县东一百二十里,其水源出楚粤界佛子岭,历渠阳,纳清水、芷水、若水,合流于此,上通滇黔粤蜀,下达荆扬”*光绪会同县志,光绪二年(1876)刻本。。显然,洪江镇也成为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
四、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的制约因素
毋庸讳言,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也有不少制约因素。首先是险滩对水路的阻碍。如辰州府(治今湖南怀化市沅陵县),“水行则石峻湍急,舟楫多阻”*大清一统志,乾隆九年(1743年)武英殿刻本。。清代诗人石文成《辰州上滩歌》对辰州府的险滩进行了尤为形象地描述:“上滩下滩心胆寒,就中最险清浪滩。乱石峨峨剑戟攒,滩过击楫发三叹:人生休歌蜀道难。牵夫如蚁走山脊,半天进步不盈尺。过得一滩度一厄,一丝崩断船倒飞:全舟性命供一掷。”*同治沅陵县志,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印本。诗人寥寥数笔,从乘船者的“心胆寒”和叹息“人生休歌蜀道难”以及牵夫的艰难行进,刻画了辰州一带险滩对水路航运带来的危险。辰州水道艰险不是个案,如黔江县四十八渡水,“滩碛鳞比,舟楫不通”[17] 3284。彭水县,“县北有木梭滩、上新滩、鹿角滩、石蛇滩,黔江经此,水势最险,舟行必出所载,然后可行”[11]3298-3300。巴东县,“清水滩,在县西十里,江中迅急,触而为漩,舟行不戒,必至覆溺。县境诸滩,此其险者”[11] 3694。铜仁府玉屏县平江,“在城北,中有显灵滩,水势最为险恶*乾隆贵州通志,乾隆六年(1741)刻本。。也同样显示了险滩对水路的障碍。即便到民国时期,个别地方的水运还受到险滩的阻碍,如贵州沿河县,乌江为其主要交通线,“惟在重山叠岭中河狭流急,险滩甚多。自思南至龚滩一百五十九公里中,有大小险滩八十二处,自龚滩至涪陵一百八十九公里中有大小险滩九十四处,统计思南至涪陵三百四十八公里,中有大小险滩一百七十六处,小滩不计,外有险滩八十三处,航行之险不言而喻。其中潮砥、新滩、龚滩为乌江三重天堑,上下不通舟楫。潮砥、涪陵间最大船只载重为三百八十四担,中船二百五十担,小船一百担。潮砥、思南间以水深浅不一,通行船只不过八十担,思南至文家店尚能行船。上至雷洞伏流数十里,舟楫绝迹”*民国沿河县志,1943年铅印本。。可见,乌江航道在民国时期还有重重险滩,个别航段有吨位限制,甚至不能通航。其次是季节性的降水的制约。如猛峝河,“如遇春夏水发,陡然而至,竟有四五丈至七八丈深不等,虽旋发旋退,而平处蓄水常有六七尺深……船不能行”,“而七八月起至十二月并次年正月,山水未发时,往来舟楫绝无妨碍”*同治永顺府志,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显然,猛峝河水路是否通畅直接受降水的限制。
武陵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地区之一,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区域。制约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滞后,因此,探讨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的发展状况,既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该时期本区水路交通的认识,又能够为当代武陵民族地区进一步开辟水路交通以发展经济提供历史参考。
参考文献:
[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黎小龙,赵毅.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王明业,朱国金,贺振东,等.中国的山地[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5]湖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湖南省农业区划2[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8]乐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9]王存.元丰九域志[M]. 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张廷玉,万斯同,王鸿绪,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49.
[1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On the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in Wuling Minority Region in Tang Dynasty
HU An-hui
(Marxism Institut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China)
Abstract:In Tang Dynasty,the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was the important channel for Wuling minority region to contact within and outside their areas.It was well-develop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ly,many counties possessed the waterways;secondly,generally one waterway run through several counties with dense networks;thirdly,the waterway flowed through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s of many counties.These features wer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Song-Yuan-Ming-Qing Dynasties.However,rapids and seasonal precipitation were the main factors to affect the fluid of the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Tang Dynasty; Wuling Minority Region;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features
(责任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