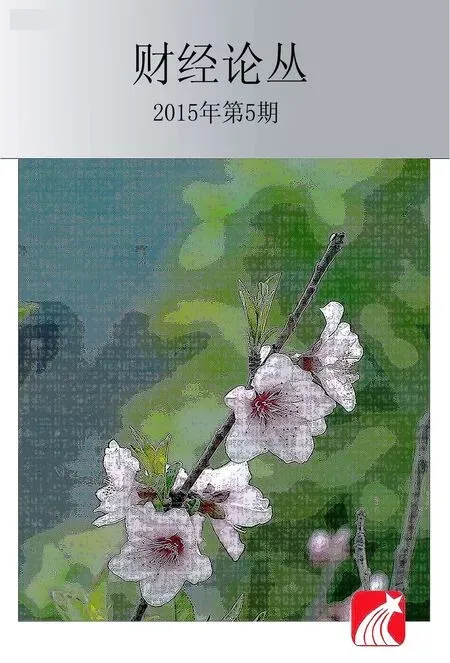农村留守与非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来自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2015-12-19伍海霞
伍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农村留守与非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来自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伍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本文再界定农村留守老人概念,利用调查数据比较分析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探析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子女的供养水平低、生活水平低是农村留守、准留守与非留守老人共同存在的问题,留守和准留守老人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来自子女的非正式支持、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的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现状;社会支持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乡人口流动逐步由分散的个人流动转变为家庭流动,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孩子加入流动人口队伍,家庭中的老年人固守农村,进而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留守老人[1]。调查发现,截止2012年底农村留守老人已达5000万[2]。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农村留守老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诸多学者考虑农业户籍子女城乡流动特征,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了界定,并对其居住安排、健康、养老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1][3][4][5][6][7][8][9][10][11][12]。在现实生活中,农村老年人的长期外出子女有农业户籍者,也有非农业户籍者,仅从农业户籍子女流动角度界定农村留守老人不免有失偏颇。另外,留守老人仅为农村老年人中的一部分,仅单一分析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缺乏对留守与非留守老人生存现状差异的比较,不足以全面认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全貌。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劳动能力下降,社会支持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凸显。社会支持通常指个体从他人、群体和社区等获得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13][14][15]。从支持供给者角度看,社会支持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支持两类,前者主要来源于政府、机构、社区等正式组织,后者主要来自家庭成员、邻居、朋友等[16][17]。在我国农村,子女提供的非正式支持一直是绝大多数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资源[18]。近年来,国家在农村逐步推广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制度,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正式社会支持[19][20]。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13][21][22][23][24]。国内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有助于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1][7][8],也有研究认为外出务工提高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供养能力,但总体上留守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25]。在家庭养老支持、新农保与新农合等非正式与正式的社会支持下,农村非留守、准留守与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尚需进行深入探究。
本文关注子女户籍与居住地两个因素,重新界定农村留守老人概念,在比较分析不同老年群体生存现状的基础上,探析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较全面地认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全貌,把握社会支持对当前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的影响,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二、农村留守老人概念的再界定
杜鹏等(2004)、高娜(2011)、唐钧(2008)、王乐军(2007)、张艳斌和李文静(2007)、周福林(2006)等先后给出了“农村留守老人”的概念[1][5][26][10][11][12]。他们一致认同留守老人年龄在60岁及以上、有农村子女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务工且时间在6个月或1年以上。虽然“留守老人”的出现源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但一直以来农门子弟大学毕业、参军或婚后随迁进入城市就业、生活也同样造就了大批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另外,一些农村老年人虽然有子女长期在外,但本人(及配偶)一直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在直系家庭甚至复合家庭中。如不考虑亲子居住安排,将只要有子女外出流动的老年人即视为留守老人,不免会将有子女长期在外生活、但又与未外出已婚子女共同生活的老人也列入留守老人之列,在“夸大”留守老人数量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留守老人可能的生活窘境。为较准确地把握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与特征,客观地认识受子女迁移流动影响的农村老年人,本文引入“准留守老人”概念,以区分处于“留守”与“非留守”之间的中间人群,从而将农村老年人划分为非留守老人、准留守老人和留守老人三类(见表1所示)。

表1 农村老年人类型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北、吉林、浙江、安徽、广东、陕西和广西等七个省区实施入户问卷调查。经数据录入、清洗后共得到有效样本4425个,其中60岁以上有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样本492个。依据本文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界定,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老人样本数分别为262、172和58。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比较分析农村非留守老人、准留守老人和留守老人的居住安排、生活费用来源和生活水平的差异,进而采用序次逻辑斯蒂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分析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影响因素分析的因变量为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并划分为困难、一般和富裕三级。自变量包括老年人的类型、子女是否给予经济支持、是否参保新农合、是否参保新农保、有无独立经济能力、有无产权属于自己的住房和子女户籍类型。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子女数和子女性别构成。另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也会对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分析中纳入老年人所属调查区域因素,并依据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27],将其划分为中部(包括安徽省)、东部(包括河北、广东和浙江三省)、西部(包括陕西和广西两省)和东北部(包括吉林省)。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农村留守与非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
1.居住安排。居住安排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和福利。由表2可知,非留守老人主要生活在三代直系、夫妇家庭和二代直系家庭,单人户也占有一定比例;准留守老人大多生活在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家庭;留守老人则多居住在间隔家庭、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家庭。生活在间隔家庭的留守老人的比例远高于非留守老人。极大似然检验结果表明,非留守老人、准留守老人与留守老人的居住安排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当前农村老年人在居住方式上呈空巢化趋势,由于子女的迁移流动,留守老人比非留守老人更多地生活在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

表2 农村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老人的居住安排 单位:%
注:其他核心家庭包括标准核心和缺损核心家庭两类;“*** ”p<0.001,“** ”p<0.01,“* ”p<0.05,ns不显著。下表同此。
2.生活费用来源。由表3可知,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老人的生活费用均主要来源于子女或本人(及配偶)的劳动所得。非留守老人中依赖子女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依靠自己劳动收入者;依赖自己(及配偶)的工作收入的留守老人所占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老人。依靠政府低保等方式生活的老年人比例较低。三类老年人生活费用来源在统计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子女的迁移流动并未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费用来源产生影响。政府或村集体等正式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养老的帮助非常有限,家庭仍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经济依赖。

表3 农村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老人的生活费用来源 单位:%
表4中,过去12个月约22.3%的子女从未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留守老人得到的经济支持额最高,其次为准留守老人,非留守老人最低。总体上,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水平相对较低。t检验结果表明,非留守老人得到的经济支持与准留守老人、留守老人存在显著差异,而准留守老人与留守老人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可见,子女的迁移流动带来了非留守老人和留守、准留守老人经济支持的不同。但现实生活中,部分隔代家庭的留守老人得到的经济支持包括了与其共同生活的孙子女的生活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虚增了留守老人的经济支持。

表4 子女给予农村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老人的经济支持
3.生活水平。由表5可知,多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处于中下水平。留守老人中生活水平一般者所占比例最高,较富裕者甚少,生活困难者所占比例略低于非留守与准留守老人;准留守老人中生活较困难、困难者所占比例相对最高,但留守、准留守和非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在统计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子女迁移流动后其经济收入的普遍增加并未带来留守老人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留守老人并不是子女迁移流动的主要“受益人”。

表5 农村非留守、准留守与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 单位:%
总体上,子女的迁移流动影响了留守、准留守与非留守老人的居住安排,但并未引致三类老年人生活费用来源与生活水平的差异。
(二)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6显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影响因素分析的变量描述性信息可知,被访者以中低龄老人为主,男性、配偶健在、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老人比重较高,多数老年人健康状况良好。子女全部为农业户籍、儿女双全者所占比重较高。绝大多数子女能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新农合的参保率明显高于新农保参保率,正式的社会支持在农村地区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老年人生活水平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留守老人、准留守老人生活较为富裕的几率显著低于非留守老人,二者分别为后者的49.7%和59.9%。与未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相比,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过上较富裕的生活,这种可能性约为前者的2.74倍。与不参保者相比,加入新农保、新农合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后者分别为前者的2.05和2.52倍。是否有独立经济能力、是否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住房对老年人生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过上较富裕的生活。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生活水平高的几率显著低于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仅有女儿的老年人生活困难的几率明显高于儿女双全的老年人。子女全部为农业户籍的老年人过上富裕生活的几率显著低于子女全部为非农业户籍的老年人,前者仅为后者的44.6%。地处中部省区的老年人过上富裕生活的可能性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的老年人。

表6 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注:以括号中的变量类型为分析基准;“*** ”p<0.001,“** ”p<0.01,“* ”p0.05,“+”p<0.1,ns不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0年七省区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农村留守、准留守与非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生活水平低是农村留守、准留守与非留守老人共同存在的问题,留守和准留守老人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一方面,当前农村子代的收入明显高于亲代,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部分非留守老人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非留守老人群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留守与准留守老人自养能力弱,子女迁移流动后虽收入大幅增加,但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仍处在较低的水平,未能有效地促进亲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有显著影响。首先,非正式支持中子女的经济支持对亲代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特别地,由于中国城乡巨大的收入差异,相对于农业户籍子女,非农业户籍子女收入普遍较高且较为稳定,他们的经济支持更有助于农村父母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嫁娶方式下公婆是女儿的主要赡养对象,女儿对自己父母的供养大多仅限于年节的礼物性支持。因此,仅有女儿的老年人生活富裕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儿女双全的老人,当前农村依靠儿子的家庭养老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其次,新农保和新农合作为当前农村老年人可得性的正式支持,对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新农合自2003年开始试点,2005年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进,2012年参合区县数达到2852个,参合人数达8.03亿[28]。至今,参合人数、参合率逐年提高,尤其是人均筹资、补偿力度与补偿受益人次数等明显提高,对保障农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29]。相对而言,新农保实施时间较短,但由于推进速度较快,2009年覆盖全国10%的县区,2010年达24%的县区,2011年已扩大至60%的县区[30],参保人数也从2010年1.03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3.26亿人[28]。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将新农保制度每人每月至少55元的基础养老金视为持久收入的增加,贴补了日常生活之需[30]。总体上,就社会支持而言,家庭养老与新农保、新农合、土地保障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
中国约57%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水平远高于城镇[31],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仅关系着老年人自身的福利和生活质量,也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村父母大多将家庭资源主要用于抚养子女、支持子女接受教育及为子女操办婚事,无暇顾及自己的养老,待年老时则缺乏应有的积蓄以应对自身的养老需求。虽然农村老年人对家庭养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老年人大多竭力自养,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仅限于“填补”老年人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金额与其各种非子女经济供给金额之间的缺口[32]。从非正式支持角度看,解决农村留守、准留守与非留守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一方面需在家庭层面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进行自我积累,实施自我储蓄养老,增加非子女的经济供给,提高自身养老能力;另一方面家庭养老还需在较长时期内发挥其职能,在农村青年子代中倡导“崇老敬老”观念,强化其“填补”意识,自愿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政府应重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加强农村现有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青少年的科技文化水平,为农民子弟获取较高的劳动收入、增强其“填补”能力奠定基础。另外,关注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的返流及其现实需求,通过小额信贷等方式支持外出劳动力人口回乡创业,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增长、增加相关群体家庭收入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需求。
统计数据表明,仅2011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基金年支出额已达587.7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支出1710.19亿元,补偿受益人次达13.15亿[29],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已在老年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新农保覆盖范围较小、参保率低,养老金给付水平低,新农合也存在着补偿水平低、抗风险能力低等问题。鉴于此,国家应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逐步健全农村养老保障支持体系,扩大其覆盖面,提高参保率,作为家庭养老的有力补充,适时地分人群、分区域提高农村老年人基础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切实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为经济上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保障。基于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与公平原则,逐步实行城乡统筹,将农民医疗保险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提高农村老年人就医的补偿水平与抗风险能力。在农村地区逐步形成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障并行,个人、家庭和社会三维支撑的养老模式,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1] 杜鹏等.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4,(6):44-52.
[2] 吴玉韶,党俊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 陈铁铮.当前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来自258位农村老人的调查[J].湖南社会科学,2009,(8):57-60.
[4] 杜娟,杜夏.乡城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的探讨[J].人口研究,2002,(2):49-53.
[5] 高娜.中国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研究综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5):112-115.
[6] 贺聪志,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46-53.
[7] 孙鹃娟.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14-18.
[8] 张文娟.成年子女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J].人口研究,2012,(3):68-80.
[9] 张福明,郭斌.发达省份农村留守与非留守老人养老之比较——基于山东省聊城市386位农村老人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71-77.
[10] 王乐军.315名农村留守老人生存质量相关影响因素研究[J].济宁医学院学报,2007,(1):66-67.
[11] 张艳斌,李文静.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研究[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6):105-106.
[12] 周福林.我国留守老人状况研究[J].西北人口,2006,(1):46-49.
[13] Cobb,Sidney.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J].Psychosomatic Medicine,1976,(38):300-314.
[14] Hall A.,Wellman B.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A].S.Cohen & S.L.Syme.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C].Orlando:Academic Press,1985,pp.23-41.
[15] Lin,Nan,Alfred Dean and Walter M.Ensel.Social support scales:A methodological note[J].Schizophrenia Bulletin,1981,7(1):73-89.
[16] 徐勤.我国老年人口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J].人口研究,1995,(5):23-27.
[17] Namkee G.Choi and John S.Wodarski.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health status of elderly people:Does social support slow down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deterioration?[J].Social Work Research,1996,(20):52-63.
[18] 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J].人口研究,1998,(4):51-57.
[19] 曹文献,文先明.集体补助视角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力支撑研究[J].金融与经济,2009,(8):63-64.
[20] 赵素梅.基于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的养老保险制度探究[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5):87-88.
[21] Cohen S.& Wills T.A.Stress,social support and buffering hypothesi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8(2):310-357.
[22] Turner R.& Noh S.Class and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 among women: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 control[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83,(24):2-15.
[23] Vicki S.Helgeson.Social support and quality of life[J].Quality of Life Research,2003,(12):25-31.
[24] 李建新.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增刊):43-47.
[25] 叶敬忠,贺聪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9,(4):44-53.
[26] 唐钧.农村“留守家庭”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长白学刊,2008,(2):96-103.
[27] 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l[Z].2011-06-13.
[28] 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Z].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29] 王俊华,任栋,马伟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迈入全民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可行性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3,(1):85-88.
[30] 沈毅,穆怀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乘数效应研究[J].经济学家,2013,(4):32-34.
[31]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变化[J].中国社会保障,2013,(11):13-15.
[32] 桂世勋,倪波.老年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J].人口研究,1995,(5):1-6.
(责任编辑:化 木)
Living Status of Rural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Elderly:Finding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Seven Provinces
WU Hai-xia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This paper redefines the concept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and analyzes the living status of the left-behind, quasi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elderly using sampling survey data. The determinants of living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re also disclosed.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quasi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elderly are low. Left-behind and quasi left-behind elderly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poverty. Economic support from children as the main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new type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s the main formal social suppor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living status; social support
2014-11-03
伍海霞(1972-),女,宁夏永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C924.24
A
1004-4892(2015)05-00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