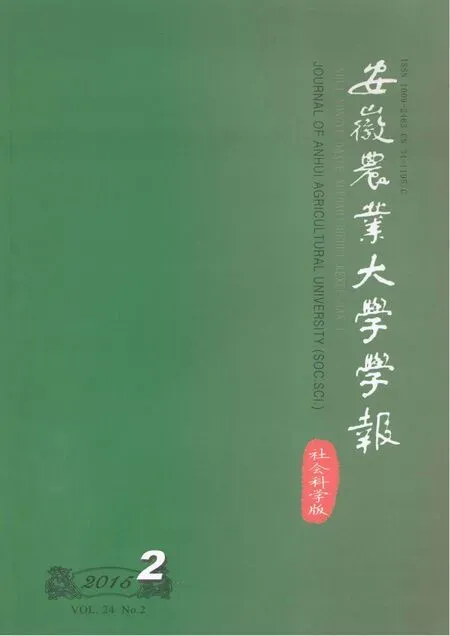叶适《诗经》研究释论
2015-12-18陈光锐
陈光锐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职教研究所,安徽 滁州 239000)
叶适《诗经》研究释论
陈光锐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职教研究所,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叶适的学术思想不同于正统的道学派,他的学术思想融合了事功和义理,他对《诗经》的研究和解读多有独特见解,立论新颖,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他力辩孔子删诗说;关于《诗经》小序,也不盲目遵从和反对;主张以《诗经》立教。叶适的《诗经》学研究是宋学精神张扬的典型表现。
关键词:叶适;《诗经》;研究
一、对孔子删诗说的批驳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全书总共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关于《诗经》的编订成书,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献诗”“采诗”和孔子“删诗”之说。“献诗”和“采诗”之说易于为人理解和接受,孔子“删诗”之说起自汉人,但从唐代开始就遭受质疑。《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趋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1]1936唐代孔颖达开始怀疑“删诗”说,他说:“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首未可信也。”[2]263清人崔述说:“子曰:‘诵《诗》三百……’子曰:‘《诗》三百……’玩其词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所歌之‘风’无在十五国外者。……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3]309崔述辨“删诗”说之理由,确实有力,并且自认为是一己之独见,殊不知早他几百年前的叶适已经详细地辩析过这个问题,崔述所言“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连宋代大儒叶适的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实属他个人见闻不广。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6“毛诗”云:
《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亦言“删诗为三百篇”。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又《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之学自孔氏而始者则为有间矣,次第之义当然尔[4]61-62。
叶适在接受孔颖达观点的基础之上,又能细致地感觉到孔子不可能称自己删后之诗为“诗三百”,崔述如果不是看到叶适的这番话却故意秘而不宣的话,那么叶适可谓几百年前就已经先他而知了。另外叶适进一步说明自己之所以辨明“删诗”说之伪,并非故意标新立异,因为他想借此纠正一种不正确的思路,那就是主观地认为孔子之前无圣贤,“学自孔子而始”,叶适认为这是极为不客观的,是对孔子的盲目尊崇。他在《毛诗·总论》中还有更为细密的推论:
按《左氏》载逸诗,有事本者惟《祈招》。以《诗》考之,独文、武、成王、幽、厉者有诗,康王则已无诗,而美诗多作于成王之时。盖集诗之凡例,专以治乱兴亡两节及中兴为断,而义归于一君之美刺及美刺兼焉者,故康穆以下至夷王,虽有诗皆不录;疑此西周之后,东周之时所衺次也。周以诗为教,置学立师,比辑义类,必本朝廷,况《颂》者乃其宗庙之乐乎!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故《匪风》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简兮》思西方之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远数百年之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且又有甚不可者,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掩前闻,一归孔氏,后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4]80。
此番议论其实是有为而发,道学家虽然表面上尊奉尧、舜、禹、汤,实则将孔子列为所谓道统之源头,这种做法带来了过分尊孔的偏失。叶适以为周代以诗立教,对诗的增删去取应该主要是周室的意愿,孔子后生几百年,而且地位卑微,不太可能对流传应用了几百年的立教之诗进行十取其九、大刀阔斧地删削。另外,叶适还揭示了一个近乎常理的事实,那就是“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孔子只应该是古圣贤传承链条中的一环,而不可能是源头之人。叶适真实意图是要破除当时学术界对孔子近乎神话的顶礼膜拜,认为孔子也当是学有所承,如果将叶适的观点继续向上推演,那就是创造人类文化精华诗歌的原初力量乃是人民大众,也就是叶适所言之“生民”。
叶适对删诗说下了如此大的力量予以辩驳,是叶适论学论文追求独立思考、不随时翻覆的结果。《直斋书录解题》说他:“大抵务为新奇,无所蹈袭。”《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这些评论并非都出于赞赏,但却是道出实情,不过叶适并非刻意求奇,而大多为有的放矢,务求事实真相。
二、关于《诗经》“小序”的观点
关于《诗经》“序”的问题上叶适同样能不囿于流俗之见,高出众人一筹。
东汉以后,原本激烈角逐的齐、鲁、韩、毛四家《诗经》学派之剩下《毛诗》一家,成为定于一尊的诗说权威。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集合《传》和郑《笺》,虽也间出新意,总体上还是遵从旧说,《毛诗正义》就成为汉学诗说的代表之作,自唐初至五代被学者尊奉,无有异词。
较早开始怀疑《毛诗》的是北宋的欧阳修和苏辙,这种怀疑主要是针对《毛诗》 “小序”的质疑。可谓开了宋代疑“序”、反“序”的先河,并且由此引发遵“序”和反“序”之间的辩争。比较极端的攻“序”学者为南宋初年的郑樵和王质,分别著有《诗辨妄》和《诗总闻》,前者认为:《诗序》皆出汉人之手,而且鄙之为“村野妄人所作”,[5]2069极尽全力驳斥“小序”。王质直接主张废除诗序,自出己意来说诗。与废序、攻序之说针锋相对的是遵序说,这些学者往往认为攻序派是离经叛道,首先发难的是北宋道学家程颐,他说:“问:‘《诗》如何学?曰:只在《大序》中求。《诗》之大《序》,分明是圣人作。’”“问:‘《诗》“小序”何人作?曰:“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道,盖国史得于采诗之官。’”[6]241南宋时期遵“序”派开始占据上风,范处义和吕祖谦等人分别写成《诗补传》和《吕氏家塾读诗记》,宣扬遵序之说。但是朱熹却最终采取了否定《诗序》的态度[7]210。
叶适对《诗序》没有一概地简单肯定或否定,他说:
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多矣[4]61。
乍读此段觉得似在采取折中说法,对攻序说、遵序说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不是这样,实则叶适对遵序和攻序两说之偏颇已经洞察,再次详为开说,意在了却这桩公案。他首先指出作《诗》者必是有为而作,集《诗》者也当是有所寄托,揣摩《诗》序对理解诗意是有必要的。但是研究诗序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既当“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刻舟求剑,亦不可离开文本自说自话。盲目遵序和不加分析的攻序、废序都不能真正理解诗意。这种知人论世地解读诗《小序》的主张无疑是客观的批评方法。
三、以诗立教说
叶适《诗经》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是以诗立教说,并且明确地说以诗立教是从周代开始的,这也是《诗经》存诗从周朝开始的原因。他说:“自有生民,则有诗矣,而周诗独传者,周人以为教也。诗一也,周之所传者可得而言也,上世之所传者不可得而言也。”[4]62叶适承认自有生民便有诗歌即是间接地承认了诗歌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此种认识难能可贵,但是对诗歌的利用却只能由古之圣贤来完成,他认为诗歌之所以在周代被第一次当做教化黎民的手段,是因为“《诗》之道至于周而后备也”[8]700,那么《诗》之道的内涵如何,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叶适在《进卷·诗》对此有解说:
诗之兴尚矣。夏商以前,皆磨灭而不传,岂其所以为之者至周人而后能欤?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乱也。是故古之圣贤,养天下以中,发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絪缊芒昧,将形将至,阴阳晦明,风雨霜露,或始或卒,山川草木,形著懋长,高飞之翼,蛰居之虫,若夫四时之递至,声气之感触,华宝荣耀,消落枯槁,动于思虑,接于耳目,无不言也;旁取广喻,有正有反,比次抑扬,反复申绎,大关于政化,下极于鄙俚,其言无不到也。当其抽词涵意,欲语而未出,发舒情性,言止而不穷,盖其精之至也。言语不通,嗜欲不齐,风俗不同,而世之先后亦大异矣;听其言也,不能违焉,此足以见其心之无不合也。然后均以律吕,陈之官师,金石震荡,节奏繁兴,羽旄干戚,被服衮黼,拜起揖逊,以祭以晏,而相与乐乎其中。于是神祗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孙协其明,福禄寿满,横畅旁浃,充塞宇宙,熏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后世言周之治为最详者,以其诗见之。然则非周人之能为诗,盖诗之道至于周而后备也[8]700。
此段议论作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此时叶适的思想既有永嘉事功学派的影响,也受到吕祖谦理学的熏陶,因此他的对“诗之道”的内涵及古之圣贤以诗立教的解说就显得比较复杂。有学者认为开头关于物、情、理关系的探讨只是叶适事功思想的反映[9]131,这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天地之间的“物”各有不同的“情”,这里的“情”似应理解为情状,情状万千而其“理”则一,“理”是对“物”的本质性定义,叶适认为还不止如此,“理”不可乱,“物”和“情”当然就各得其所。古之圣贤就是由此得到启发而借诗立教,调解人伦秩序、社会政教,具体的方法还是儒家传统的中和说,所谓“养天下以中,发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即《中庸》所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诗的教化作用还需要通过乐来辅助方能完成,最后达到“于是神祗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孙协其明,福禄寿满,横畅旁浃,充塞宇宙,熏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当然叶适也知道“言语不通,嗜欲不齐,风俗不同,而世之先后亦大异矣”。总的来看叶适的这番话并没溢出《诗大序》的范围,(叶适对《诗大序》是总体肯定的),不仅如此,相比之下,叶适的诗学思想似乎更为温柔敦厚,孔子诗教说中“怨”的成分没有被叶适突出,比如他对《诗经》中的变风、变雅是这样去理解的:
论风雅者必明正变,尚矣。夫自上正下为正,固也;上失其道,则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虽变,正也。《小序》谓“政教失而变风发乎情”,审如其言,则是不足以自正,岂能正人哉!今之所存者,取其感激陈义而能正人,非谓怨愤妄发而不能自正也[4]61。
《诗大序》都说过:“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叶适却根本上否定“变”的说法,看似新奇,但是相对《诗大序》来说都是一种退步的诗学观了。他的意思无非是说,即使王道衰落,作为臣民自己也不能发自怨刺地创作变风变雅之作,亦如他所言只能“感激陈义”,而不能“怨愤妄发”。否则就是不能自“正”,此种论调显然无视人情的自然发抒,不能认识,或者是不愿认识臣民有在王道失、政教衰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发出怨愤之声。这是叶适《诗经》批评中的瑕疵,这种过分强调政教功能的批评观遮蔽了他观照文学作品中人的真情实感,即使心中实有体会但却口中不言,造成叶适文学批评中会有较多对同一文学文本的存在相互矛盾的双重批评现象。
在《进卷·诗》一文的最后,叶适这样说:
《离骚》,《诗》之变也;赋,《诗》之流也;异体杂出,与时转移,又下而为俳优里巷之词,然皆诗之类也。宽闲平易之时,必习而为怨怼无聊之言;庄诚恭敬之意,必变而为侮笑戏狎之情;此诗之失也。夫古之为《诗》也,求以治之;后之为诗也,求以乱之。然则岂惟以见周之详,又以知后世之不能为周之极盛而不可及也[8]700。
关于《离骚》和赋,叶适认为它们是《诗经》的流变,这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但是,依然是从政治教化的价值角度评判,叶适认为它们并不是《诗经》的正向发展,而是“《诗》之失也”。称之为杂出的异体,与古时以诗立教的初衷背道而驰,主要理由就是,《离骚》属怨怼无聊之言,赋为侮笑戏狎之情,末尾一句透露出叶适认为后世也有可能出现像周朝那样的极盛之世,因而也就有可能出现像《诗经》一样的文学作品,这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表述反映出叶适并非是一味地厚古薄今。不过,对诗歌教化功能近乎偏执的追求确实妨碍了他对古代文学史上优秀作品的品鉴。在《汉阳军新修学记》中,对竭忠尽智而被流放楚地的屈原,叶适虽然承认《离骚》是楚地文词之盛的标志,但是没能对屈原的奇冤重怨抱以同情,没有对楚辞的华美精致给予赞赏,却依然将屈原看作造成楚人“悲愤刻约,逐外巧之卉木,遂变《风》《雅》而为丽淫者,亦不悟其失也”[8]140的祸首,实在令人为之叹息。
叶适的这种观照文学作品的方式是宋代儒家重理节情的极端表现,宋代文人的主体精神高扬,对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孜孜探求,追索的结果是,对国家、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空前高涨,理学家张载的话可作为这种信念的注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1056个人的欲望情志都必须压抑和节制到最低限度,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学同时要求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化为主体的自觉行动方式,作为实现最高理想的途径,这又造成了人的主体性的灼伤。因而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人的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和依附性被奇妙地扭结在一起。”[11]19这种人性灼伤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在对待最能反映真实人性和情感的文学作品时,表现得谨慎而警惕,在对它们进行评判的时候,变得挑剔而严苛,这种情况到了南宋尤为突出,最具文学特质的部分往往被当做最为有害的而遭到忽略和抛弃,“义理”充实是第一位的, “文字”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6.
[2] (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3.
[3] (清)崔述.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09.
[4]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61-62,80.
[5] (宋)朱熹.朱子语类[M]. 黎靖德.编.王星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69.
[6] (宋)程颐,程颢.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1.
[7] 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0.
[8] 叶适.叶适集[M].刘公纯,王孝渔,李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140,700.
[9] 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31.
[10]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56.
[11]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19.
An Interpretation of Ye Shi’ Research onTheBookofOdes
CHEN Guangrui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Chuzhou Vocation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uzhou 239000, China)
Abstract:Ye Shi’s academic thought integrated practical use with doctrin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thodox Taoism. He had some original ideas on The Book of Odes, which can be proved with sufficient arguments. He insisted that Confucius had not bowdlerized The Book of Odes and did not blindly follow the predecessors’ views. He claimed that The Book of Odes must be used in education. Ye Shi’s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Odes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Song learning.
Key words:Ye Shi; The Book of Odes;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5)02-0096-06
作者简介:陈光锐(1970-),男,安徽明光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14-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