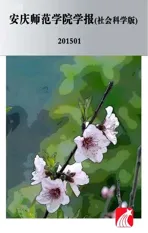“桐城三祖”视域下的姚范及其地位平议
2015-12-17汪孔丰
汪 孔 丰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桐城三祖”视域下的姚范及其地位平议
汪 孔 丰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姚范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桐城派立派者姚鼐的伯父与业师,还与方苞、刘大櫆颇有关联。他洞察前辈方苞为学之不足,讥议其“义法”说之陋弊;与挚友刘大櫆志同道合,情深意切,亲近其“神气、音节、字句”说;精心栽培胞侄姚鼐,倾力传授其学术、辞章。而他自身对唐宋诗家的称誉以及创作实践中兼融唐宋,也奠定了桐城诗派的家法内涵。姚范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肇基者之一,在此派谱系中至少可与刘大櫆相比肩。
关键词:姚范;桐城三祖;桐城派;平议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1.021
姚范(1702-1771),字南青,又字凫青、南菁、已铜,号薑坞,安徽桐城人。他是麻溪姚氏十五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家族文化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他对桐城派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钱钟书先生说他是桐城诗派的发端者[1],还有人称他是桐城文学承前启后的津梁[2]。这些论断值得深思。当前,学界虽对姚范的诗文及其地位已有一定研究,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鉴于姚范不仅是桐城派创建者姚鼐的伯父和业师,而且还与方苞、刘大櫆颇有关联,兹从他与“桐城三祖”之间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和评估他在桐城派中的特殊地位。
一、讥议方苞
方苞对桐城派的形成有重要奠基作用。他晚年在京师仕宦三十余年,门下弟子甚众,不仅扩大了桐城文章的影响,同时为桐城派的创建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尤其是他提出的“义法”说,更是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基础与柱石。他可谓桐城派的奠基者。
从年龄上看,姚范比方苞小三十四岁。当姚范在乾隆七年高中进士、初露头角之时,方苞早已是台阁重臣、名满天下了。作为晚生后辈,姚范岂敢比肩学坛巨匠?不过正所谓后生可畏,姚范因勤于治学,于书无所不窥,学问亦相当精湛。不然,他何以能在京师先后担任武英殿经史馆校刊官、三礼馆纂修官、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何以能赢得天台齐召南、山阴胡天游、常熟邵齐焘、仁和杭世骏等人的推重,称誉“姚君之学不可涯涘矣”[3]342?
应该说,在学术取向上,方、姚二人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方苞笃信程朱,说经之书大抵推衍宋儒之学而多有心得。而姚范曾得桐城宿儒周大璋指教,得其法门。他曾写信对周氏说:“某年十五六时,即诵读先生刊布诸书,迩时私心已自响慕。其后先生往还城中,亦时获亲教。”[4]周大璋精研性理之学,因《四书大全》所辑内容纷错百出,于是以朱子为宗,撷取精华,成《四书精言》四十卷、《四书正义》十九卷。又病学者徒骛华藻,文日工而身心日益丧,以为朱子文与道兼至,故潜心辑编《朱子古文读本》六卷[3]259。显然,周氏是一位尊崇程朱的饱学之士,对姚范信奉程朱应有一定影响。然而,姚范并未固执独守宋儒之学,他在博览经史、考校群书的过程中又亲近了汉学。这种汉宋兼宗的治学取向使得他的学术根基深厚扎实,从而避免了独守宋学流于空疏之弊。这也是他与方苞的不同之处。
姚范的学问甚至引起了方苞的关注和敬畏,方苞自称论“学问详博,不如姚南青”(《先世遗事·先编修公》[5]卷四)。吴德旋《姚薑坞先生墓表》亦说:“雍正、乾隆间,桐城方灵皋侍郎负盛名,海内顾于同邑畏二人焉。其一刘才甫,其一则姚薑坞先生也。才甫以其文,而先生兼以学重,称为通儒。”[6]卷八正是因为姚范才学兼重,故能对方苞为学为文之利弊洞若观火。
姚范对方苞的经术之弊有所认识和驳正。叶酉既是姚范好友,又是方苞弟子。方苞“治经多取心裁,不甚资佐证”[7],叶酉得其传,守其说。姚范在与叶氏交往过程中,龂龂争辩,时见驳正。这种“驳正”反映出姚氏不因私交而苟同学术之异,也映照出他与方苞在经术上的功力深浅情况。
姚范批评方苞的《周官》研究,更显示出其精湛的经学造诣。方苞对《周官》颇有钻研,能融会旧说,断以己意,有《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辨》(一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等著作。方苞对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给予了批评,在他看来,“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8]17。不过,他也承认《周官》一书“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8]17,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是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政需要而窜入的缘故。故而,他严厉斥责刘歆“诚万世之罪人也”[8]21。但是,姚范对方苞的《周官辨惑》颇有微词,他认为“方氏卫经之心,可谓至矣。然心所不安,及前贤辨及之者,尽委之刘歆之伪窜,过也。”“方氏笃好是经,往往推高圣人之旨,又或索之过深,而矫合以就其说,皆贤者之过也。然所为《周礼析义》,遇其至者卓出于前儒之上,若此书为以己意所欲芟薙之文,而姑托于歆之妄窜,以杜夷斥经文之咎,则可谓蔽矣。欲辨世人之惑,而不知其惑之愈甚也已” (《复某公书》[4]卷二)。姚范此处如此批评方苞,关键原因在于方氏犯了宋学家们治学易犯的毛病,即过度阐释,流于空疏无据。类似毛病还存在于方苞《与鄂少保论丧服之误书》《答礼馆诸君子书》等文中,它们也没有逃过姚范的指摘。
姚范对方苞之文有所评点,有《评点望溪集》八卷、《评点望溪文集》[9](原本藏姚永概家)。他说:“望溪文,于亲懿故旧之间,隐亲恻至,亦见其笃于伦理而立身近于《礼经》,有不可掩者已。”(《评文集》[8]902)他指出了方苞之文在思想意蕴上的长处,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不过,望溪文章并非篇篇无懈可击,姚范对其《李刚主墓志铭》一文就有所批评,他不仅对叙述内容有所不满,还对此文结构予以抨击,说:“此文断续皆不联属,以不知古人神理融结之妙,而求之于所谓义法,少自离局,即菑瓜相诡,筋胍弛散矣。”[10]107这个批评切中要害,以至于方东树在整理《援鹑堂笔记》时,虽在按语中极力为此文内容辩驳,但也不得不承认“此文之弛散,则望溪亦无可辨”[10]107。从姚、方两人的批语看,这篇文章在“义法”上存在严重问题。这对鼓吹“义法”的方苞来说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实际上,姚范对方苞的“义法”说并不以为然,如方苞评韩愈《赠太傅董公行状》说:“此韩文之最详者,然所详不过三事,其余官阶皆列数,而不及宦迹,虚括相业。其为人则于序事中间见一二语。北宋以后,此种义法不讲矣。”[11]1227而姚范却说:“此等何足以跨压北宋人。望溪沾沾于详略讲义法,非笃论。”[11]1227又如方苞极诋欧阳修《有美堂记》,认为是随俗应酬而作。而姚范却认为此文“虽宋体,然势随意变,冲融翔逸,诵之锵然”[10]卷四十四。这些泾渭分明的批评差异,也从侧面表明出姚范的文学理念是有别于方苞的。
如前所述,方苞虽然是长辈,有着巨大的声名与威望,但姚范并未因此盲从附和于方苞。相反,他凭借精湛才学,独立思索,走出一条与方苞不同的治学之路。他对“义法”的批评,也反映出方苞文论的不足。这些当对他的胞侄姚鼐最终开创桐城派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二、契合刘大櫆
刘大櫆是桐城派形成期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上接方苞,中联姚范,下启姚鼐,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批评都对桐城派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姚范与刘大櫆关系密切,情同手足。刘大櫆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而姚范则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刘年长姚四岁。两人相识甚早,结交殆在垂髫之时。刘大櫆有诗多次表露,如云:“念与子结交,双髻绾青螺。”(《姚大南菁寓斋信宿却寄》[12]367)“情亲手足并垂髫,路隔东西相望遥。”(《怀姚南菁》[12]564)等等。两人友善深契,亦与里中方泽、周汝和、王洛、叶酉、江若度、张顾岩等文士声气相求,为举世不好之文,闻名乡邑。在这些青年才俊中,刘大櫆认为“姚君独知己”,二人都有“抗志怀古贤”[12]379的高远追求,这种志向甚至还引起了乡人的不解与诃诋。姚范诗集中,与刘大櫆有关的诗所存不多,如《登楼怀刘三耕南》云:“水烟寥廓数峰青,何处孤鸿入杳冥。一夜梅花江上落,天涯曾向笛中听。”[13]卷一此诗借景抒情,道出了姚范对好友刘大櫆的深切怀念之情。两人间这种深挚情感在刘大櫆《哭姚南菁》一诗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我归值君殁,无复旧知心。次第交游尽,平生爱慕深。披文怜锦衣,见月想芳襟。讵可重闻笛,从今罢鼓琴。”[12]610姚范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正月初八,刘大櫆也在这一年辞去问政书院山长归里,他闻此恶讯,感叹“无复旧知心”,并以山阳闻笛、伯牙绝弦两个典故表达了他对知己永诀的沉痛追悼。
刘大櫆有诗说:“茫茫斯世内,与尔分偏亲。”(《正月一日有怀姚南菁》[12]606)两人的亲密契合还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刘氏文论集中反映在其《论文偶记》中,他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14]3,而神气则又体现在音节、字句之中,“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14]6。此外,他还提出文有“十二贵”:“文贵奇”、“文贵高”、“文贵大”、“文贵远”、“文贵简”、“文贵疏”、“文贵变”、“文贵瘦”、“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文贵品藻”。他的这些论文主张与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文史谈艺”中的一些观点相近,如姚范说:“字句、章法,文之浅者也,然神气、体势皆阶之而见,古今文字高下,莫不由此。”[10]卷四十四他又说:“朱子云韩昌黎、苏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从古人声响处学。此真知文之深者。”[10]卷四十四这些都近似于刘大櫆强调的因声求气之法。此外,姚范还说“文字自是贵藻丽奇怪”、“凡文字贵持重”、“凡作文须令丘壑万状”、“文字须有入不言兮出不辞”等等,这些观点与刘大櫆所论文有“十二贵”多有相近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方东树曾说姚范“文史谈艺”中“内多海峰刘先生语”,由于姚范与刘大櫆“同术相友善,或识论素合”[10]卷四十四,这些论文之语已难辨泾渭。尽管如此,至少可以说明姚、刘两人论文理念是一致的。
刘、姚两人在诗歌方面也有相知、相通之处。刘大櫆论诗亦重音节与神气,其《张秋浯诗序》说“气之精者,托于人以为言,而言有清浊、刚柔、短长、高下、进退、疾徐之节,于是诗成而乐作焉。诗也者,又言之至精者也”[12]88,又说“且夫人之为诗,其间不能无小大之殊。大之为雷霆之震,小之为虫鸟之吟,是其小大虽殊,要皆有得于天地自然之气”[12]88。这种重音响、神气的论断还散落于其它诗序中,如《左仲郛诗序》《皖江酬唱集序》等。姚范论诗多用“音响”、“气势”,以其作为评判诗歌优劣的相关标准,他说“阮诗高迈,宋诗气势已不及晋”[10]卷四十四、“康乐诗颇多六代强造之句,其音响作涩,亦杜韩所自出”[10]卷四十、“音响峭促,孟郊以下似之”[10]卷四十,等等。从前面刘、姚二人的论文话语来看,他们俩实际上都是以文论诗。尤需提及的是,姚范、刘大櫆曾合选明代诸家诗[15]113卷五《跋薛考功奏议》,这些诗或许收入刘氏编选的《历朝诗约选》。在这部诗选里,明诗部分以李梦阳、何景明诗居多,其中收李诗二百二十六首,收何诗一百二十八首,表现出重何李的鲜明倾向[16]。姚范对李、何二人颇有好感,不仅批评钱谦益、冯班等人贬斥七子之论,还说:“十九首浑然天成,兴象神味旨趣,岂可以摹仿得之,然观何、李诸公诗,转复读之,其妙愈出,正如学书者,只见石刻,后观真迹,益见神骨之不易几也。”刘、姚都推崇李、何,与李、何二人的复古理念有关。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学诗主张模拟,重视体格与音调,这契合刘、姚二人的学诗脾胃。他们对明七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桐城诗派学诗取向的基础。
姚范与刘大櫆二人的密切交往对姚鼐颇有影响。姚鼐《祭刘海峰先生文》说:“昔我伯父,始与并兴。和为文章,执圣以绳。剧谈纵笑,据几执觥。召我总角,左右是应。”[17]246年幼的姚鼐曾侍奉刘大櫆,以刘氏状貌言笑为奇,还常常效仿[17]114。这种效仿虽是儿戏,但也反映出姚鼐对刘大櫆早有深刻的印象。这为他长大后师从刘大櫆奠定了情感认同的基础。
平心而论,刘大櫆与姚范虽志趣相投,观念相通,但各有所长,各领风骚。以才气而言,刘才气横溢,汪洋恣肆,而姚颇显拘谨,才气内敛。以学问而言,刘治学少涉考据,学不精博,而姚博览经史,探涉奥窔,学术精湛。他们各有胜人之处,这让后学姚鼐能够兼取两家之长,助其成长为一代文学宗师。关于这一点,方东树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薑坞、惜抱三先生者。薑坞所论,极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诠,直与古作者通魂授意;但其所自造,犹是凡响尘境。惜翁才不逮海峰,故其奇恣纵横,锋刃雄健,皆不能及;而清深谐则,无客气假象,能造古人之室,而得其洁韵真意,转在海峰之上。海峰能得古人超妙,但本源不深,徒恃才敏,轻心以掉,速化剽袭,不免有诗无人;故不能成家开宗,衣被百世也。”[18]
三、陶育姚鼐
姚范与姚鼐是伯侄关系。姚范之父为姚孔锳,是罗田公姚士基第二子。孔锳生有二子:长子姚范、次子姚淑。姚淑是姚鼐之父,生有三子,除长子姚鼐外,还有姚訏、姚鼎两人。在子侄中,姚范独喜姚鼐,期许甚高,赞其为“吾家千里驹”(《梦榖先生传》[19]卷二)。姚鼐自幼得到伯父教诲,敬爱有加,情非一般。这种密切关系在其文艺祈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按,姚鼐的人生道路选择,与姚范也颇为相似。读书—仕宦—退归—从教,这是他们相近的人生轨迹。姚莹《识小录》中《吾家两公》对此颇有阐述。这方面内容,杨怀志《桐城文派概论》(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中多有论述,兹不赘言。。
姚范虽不以诗文名家,但深知诗文之深趣奥旨。清末桐城萧穆就说:“乡先辈不屑以诗文名家,而真知古人诗文之枢奥者,前有姚姜坞先生,后有左叔固先生。”(《跋左叔固先生删订海峰文集》[15]177)姚范在文论批评上的真知灼见对姚鼐有所影响,如姚范认为韩愈文风受司马相如赋影响较多,说:“昌黎《南海庙碑》,壮丽从相如来,岂宋人所能及?”[10]卷四十四姚鼐亦有类似观点,他在给张翰宣的书信中说:“昌黎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庙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20]此外,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篹》,对姚范的考证、阐释、评文之语也多有参考引用。如《古文辞类篹》所选东方朔《答客难》、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解嘲》、班固《两都赋》、韩愈《河南府同官记》《祭河南张员外文》、柳宗元《零陵郡复乳穴记》、欧阳修《菱溪石记》《有美堂记》、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等文,姚鼐评点时就直接引用伯父姚范的批语,如评东方朔《答客难》,引范批云:“瑰迈宏放之气,如蹑云而上驰。”[11]2074评扬雄《解嘲》云:“雄伟瑰丽,后人于此不能复加恢奇矣。”[11]2176评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云:“凄丽处独以健倔岀之,层见迭耸,而笔力坚净,他人无比也。”[11]2409由此看来,姚范对前贤文章的评点,深得鼐心。方宗诚《节录姚薑坞先生论文语跋》亦说姚范“论文之言为最精妙,洵能发前人未宣之蕴。同时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所论不能过也。惜抱先生盖深得其旨,故能卓然成一家言”[21]卷五。
姚范的诗学观对姚鼐也有所泽溉。姚范学诗不主门户,转益多师。对待明七子学唐,既肯定其摹仿路径,又洞见其复古弊病。对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诗人多有好评,如他赞誉“东坡先生诗词意天得,常语快句,乘云驭风,如不经虑而出之也,凄澹豪丽,并臻妙诣。至于神来气来,如导师说无上妙谛,如飞天仙人下视尘界”[10]卷四十,称扬“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荃,自得意表”,自己“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10]卷四十;等等。姚鼐得其亲教,平生论诗宗旨就是“镕铸唐宋”(《与鲍双五》[22]),作诗有“山谷之高奇,兼唐贤之蕴藉”[23],“七古正统,受东坡影响较多”[24]。再以姚范评阅王士禛《古诗选》为例,姚范“所阅阮亭《古诗选》,凡数本”,但详本佚失。方东树在整理《援鹑堂笔记》时,就以其父方绩旧所传校以及自己所录记为基础补编而成,“其中厕有惜抱先生语”。不过,在方东树看来,“惜抱与先生所论,固为一家之言”[10]卷四十。可见,姚鼐的诗学思想与姚范的论诗主张是保持一致的。
姚鼐于学亦得自于伯父姚范。据姚莹撰姚鼐行状记载,姚鼐少时,姚范曾问其为学志向,姚鼐回答说:“义理、考订、文章,殆阙一不可。”姚范闻后大悦,决定将经学传授于姚鼐[25]。众所周知,乾隆年间,学人或宗汉学,或主宋学,各执一端,争辩激烈。姚范为学精博严谨,虽潜心于考据,但亦“病近代诸公或竞谈考据,以攻诋宋儒为能也,谓此人心之敝,充其说将使天下不复知有身心伦纪之事,常慨然欲有所论著以明其义”(姚莹《闽刻原后序》[10])。姚范于学无所偏主,对汉、宋学通达宽容的学术理念也影响到了姚鼐。姚鼐固然笃守程朱理学,但也曾留心于汉学,为学主张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收并重。兹以姚氏《庄子》学为例,来说明姚范对姚鼐的影响。姚范认为读《庄子》一书不必拘泥于郭象注,“郭注政当自为一书。以郭注读《庄》,则于《庄子》文义有阂而不明者”,还认为“郭注亦不过数篇数处措意,然亦多建立宗旨,排入章句于消帖,文义有龃龉不惬之病也”[10]卷五十。姚鼐撰有《庄子章义》,其自序认为郭注“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庄)周之意十失其四五”[17]33。这与姚范之观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姚鼐在《惜抱轩笔记》中也多取资于姚范的读书笔记。如他批评钱谦益笺注杜诗“议论之颇僻,引据之舛错,纷然杂出”[26]614时,就引用了伯父的读诗灼见。他举杜甫《病后遇王倚饮赠歌》诗句“麟角凤觜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说:“薑坞先生云,二句谓人固不易知,惟深相契合,乃识之耳。而笺谓王生以美馔愈疾,如仙胶之续弦,少陵即老饕。不至如此笺之陋。”[26]614又举《幽人》诗句“内惧非道流,幽人见瑕疵”,说:“薑坞先生云,此如谢客以心杂远公屏,不入社义。笺以强附李泌为李辅国所僭事,大非。”[26]614姚鼐对姚范读书笔记的撷取,既表现出他对伯父之说的拳拳服膺,又鲜明体现了姚氏家学的代际传承。
陈作霖有诗云:“海峰薑坞夙追溯,文采风流赖主持。”(《论国朝古文绝句二十首》十三[27])这指出了在姚鼐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刘大櫆、姚范二人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姚范,在处世、学术、诗古文辞等方面对姚鼐的影响更为突出。
如上所述,姚范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必要进一步重估。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桐城三祖”的桐城文系的建立,固然有利于揭橥桐城文章承传的一脉性和统序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与“桐城三祖”相关文士在建派过程中的贡献与价值。姚范就是被遮蔽的典型代表。忽视他,不利于我们清晰、正确地认识桐城派演进之具体史实。实际上,他服膺程朱与不废考据,催发了姚鼐治学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志趣。他讥议方苞的“义法”说与亲近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可对姚鼐整合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资源有所帮助。他对唐宋诗家的称誉以及创作实践中兼融唐宋,奠定了桐城诗派的家法内涵。这些足以表明,姚范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肇基者之一,在此派谱系中至少可与刘大櫆相比肩。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3:145.
[2]周怀文.桐城文学的津梁——姚范[J].船山学刊.2009(2):157-161.
[3]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毛伯舟,点注.合肥:黄山书社,1990.
[4]姚范.援鹑堂文集[O].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5]姚永朴.旧闻随笔[M].张仁寿,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89:206.
[6]吴德旋.初月楼文钞[O].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7]徐世昌,等.清儒学案[M].沈盈芝,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2055.
[8]方苞.方苞集[M].刘季高,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M].合肥:黄山书社,1989:480.
[10]姚范.援鹑堂笔记[O].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11]吴孟复,蒋立甫.古文辞类篹评注[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2]刘大櫆.刘大櫆集[M].吴孟复,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姚范.援鹑堂诗集[O].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14]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5]萧穆.敬孚类稿[M].项纯文,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2.
[16]刘大櫆.历朝诗约选[O].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文征阁刻本.
[17]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8]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6.
[19]左眉.静庵文集[O].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20]姚鼐.姚惜抱尺牍补编[O]//惜抱轩遗书三种.清光绪五年(1879)桐城徐宗亮刊本.
[21]方宗诚.柏堂集后编[O]//柏堂遗书.清光绪桐城方氏志学堂刻本.
[22]姚鼐.姚惜抱尺牍[M].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33.
[23]姚永朴,训纂.惜抱轩诗集训纂[M].合肥:黄山书社,2001:1.
[24]魏中林.钱仲联讲论清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45.
[25]姚莹.东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1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8.
[26]姚鼐.惜抱轩笔记[M]//惜抱轩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614.
[27]陈作霖.可园诗存[O].清宣统元年(1909)刻增修本.
责任编校:林奕锋
网络出版时间:2015-03-02 2:51:2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302.0952.021.html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1-0086-05
作者简介:汪孔丰,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家族视域下的桐城派研究”(13CZW051)。
收稿日期:2014-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