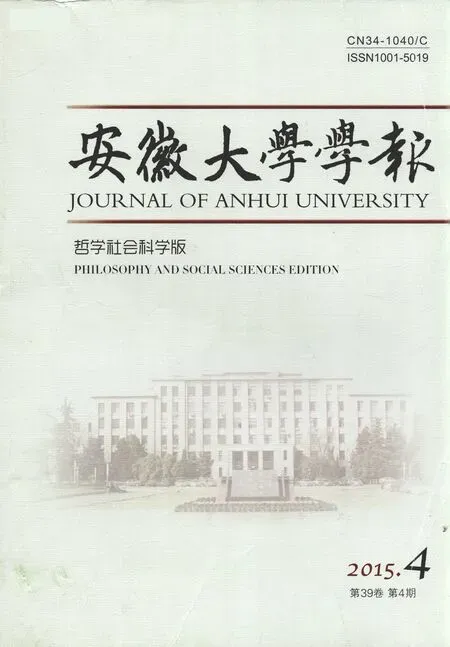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2015-12-17张锦波
张锦波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虽然不是朱熹最早使用,但是,在他的文本中保存了大量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就朱熹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以及大量讨论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从朱熹对于“性”的概念的界定及其有关“性”的问题的思考角度来看,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可见朱熹所要界说的“性”的概念以及关于“性”的问题的思考有需要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来彰显的必要性;第二,从朱熹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本身来看,朱熹能够使用“气质”来限定“性”,可见在朱熹那里,“气质”能够充分说明他所要言说的“性”的概念,也能够充分表达他对于“性”的思考立场、观点等,或者说,“气质”这一表述使朱熹有可能实现其关于“性”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第三,从朱熹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在表述上的实现以及大量讨论来看,这也体现出朱熹哲学的某种立场或某种特质。我们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思考也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察。
一
“性”之本义是“生”,以往有学者为了凸显“性”在理学语境下的形上特征,尤为强调“性”与“生”的区别。其实,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性”的形上性与“性”的“生”之本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二者也无法截然分立,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生”的理解。这是因为,“性”的本义虽然是“生”,但是,作为“性”的本义的“生”却在不同的语境和哲学体系下获得新的诠释空间,而在意义指向等方面体现出新的变化。因此,在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性”那里,始终存在这样的诠释张力:一方面,在理学语境下,“性”即“理”,“性”与“理”有着重叠的意项、内涵,从而“性”也突破了原先“生”之本义的樊篱,彰显出理学意义上的形上特征;另一方面,作为“性”之本义的“生”也没有随着“性”的升格而消失,它在将自身理学化的同时仍然规定着“性”在意义表达、理论构建等方面的发展方向,或者说,“生”在将自身升格为“生之理”的同时,也使得“性”在“生之理”的意义指向上彰显出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价值,使得“性”与“理”在意义有重叠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即“性”是“生之理”,而非完全等同于“理”。而在“生之理”这一意义上,“气质”这一表达正好可以彰显出“性”的内涵,朱熹也正在此意义上以“气质”来限定或言说“性”字内涵的。
朱熹关于“性”的讨论,首先是对程颐“性即理”这一命题的继承,但是,在他那里,“性”与“理”也是有所区别的。“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而是“生”之“理”,是“为万物所得以为生者”的“理”,是“禀得来便为我所有”的“理”。这也就是说,“性”与“理”的区别的关键就在于这个“生”字,“性”字必须兼着“生”来说,“性”也必须落实于具体事物之上来说。《朱子语类》载有:
问:“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禀得言之否?”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理,在天曰‘命’,在人则曰‘性’。”①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3页。下引该书只随文夹注页码。
生之理谓性。(第82页)
在朱熹看来,“性”即“理”,但是“性”又不同于“理”,因为“性”须得落实到具体的事物上来。只有“生物得来”的,才可称之为“性”(“方始名曰‘性’”)。因此,在朱熹看来,“性”虽然与“理”相同,但较之“理”,“性”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生”的意蕴。
“性”字与“生”字相联系,这在“性”字的造字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性”字本义就是指“生”,“性”字的字形、字义也都是由“生”字孳乳而来。另外在先秦典籍中也多有“性”“生”互用互训的现象。傅斯年曾在《性命古训辨证》一书中详细考证了在金文和先秦典籍中“性”“生”互用互训的情况。他说:“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至于生字之含义,在金文及《诗》、《书》中,并无后人所谓‘性’之一义,而皆属于生之本义。后人所谓性者,其字义自《论语》始有之,然犹去生之本义为近。至孟子,此一新义始充分发展。”②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0页。然而,“性”虽然从“生”字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汉字,但是“生之本义”却没有随着这一分离而消失,而是作为“性”字的基本义项影响甚至决定着“性”字字义的形成和发展。如“生之谓性”(《孟子·告子篇》)、“天命之谓性”(《中庸》)、“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等,这些关于“性”的解释都与“性”的“生之本义”密切相关。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经过理学家的重新诠释,“性”字在意义和功能上都有了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仍是沿着“生之本义”的方向进行的。这就是说,宋明理学家所说的“性”字仍然与“性”的“生之本义”密切相关。如在朱子那里,“性”虽然已经上升到“理”的层面,但这个“理”也须得落实下来,体现“生”之意义,成为“生之理”“为我所禀得”的“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生”字,我们也不能作局限性的理解。最初的“生”字,指“出生”“生长”,表征具体性的、时间序列上的某一活动,仅仅局限于宇宙论的意义层面。而在宋明理学那里,“生”字的内涵也随着“性”字意蕴的升格而获得了新的解释空间,其往往兼有宇宙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意蕴,表示出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成”“具有”,如“生之理”的“生”则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朱子语类》中载有许多讨论“性”的“生之本义”的条目。如:
问“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段。曰:“‘人生而静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时。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说性未得,此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者,言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谓‘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识矣,如孟子言‘性善’与‘四端’是也”。未有形气,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谓之理;已有形气,是理降而在人,具于形气之中,方谓之性。已涉乎气矣,便一能超然专说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第2430页)
这段文字就程颢“‘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的观点展开。程颢说:“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①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页。。朱子则进一步解释:“性即理”,但“性”并不等同于“理”,“性”也有其独立的意蕴,即“性”具有“生”之内涵,“性”必须落到“生”之层面来说。而“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说性不得”,因为“人物未生时”的“性”还没有“降付”到具体事物之上,这也就是说“人物未生时”或“人生而静以上”的“性”还没有展现出“生”的意思,而只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理”的特质,与“理”在意义上相重叠。一旦“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理降而在人,具于形气之中”,“性”与“理”才在意义上相区别,“理”不再只是表现出其形而上的“事事物物各有其则”意思,而是有了“为我所有”的“生之理”的意思。“理”开始降付到具体事物之时,我们才把它叫作“性”,这也是我们讨论“性”的起点。这个“性”也就是“气质之性”。但是,“理”一旦“降付”到具体的人或物上来,“为我所有”,则“理”也自然有了偏全、纯杂等的差异。而“性即理”意义上的“性”也自然表现出同样的差异性,于是“为我所有”的、“生之理”的“性”不再是“性之全体”,不再是本来状态的、“人生而静以上”的“性”,即超然于具体事物之上的、体现绝对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性”或“理”。因为“降而在人”的“性”“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讨论“性”或“理”则无法回避“性”或“理”之“降付”处的“形气”“气”或“气质”的影响,“已涉乎气矣,便不能超然专说得理也”。因此“性”必须着落于“气”“气质”“形气”上来说。在《朱子语类》中还有表达这层意思的话,如:
“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此是理;“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是气质。要之,假合而后成。(第2431页)
“人生而静”,已是夹形气,专说性不得。此处宜体认。(第2431页)
然而按照这种以“人生而静”为界限来区分“性”,则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人生而静”以上的为“性之本体”,“人生而静”以下的则为“气质之性”,那么,这里是否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性”呢?在朱子看来,“性”只有一个,只有“气质之性”。如:
问“人生而静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说性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人具此形体,便是气质之性。才说性,此‘性’字是杂气质与本来性说,便已不是性。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说气质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静’以下,方有形体可说;以上是未有形体,如何说?”(第2431页)
问:“《近思录》中说性,似有两种,何也?”曰:“此说往往人都错看了。才说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堕入气质中,便薰染得不好了。虽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旧在此,全在学者着力。”(第2432页)
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第67页)
在朱子看来,根据“人生而静”来划分“性”,看似有两种“性”:一是“理之性”或“本然之性”,二是“气质之性”,但事实上“往往人都错看了”。“性”与“理”的最大区分在于“性”有其“生之本义”的基本内涵,所以“性”必须着落于“气质”“形气”“气”上来说,因此,只有“气质之性”。但是,“气质之性”除了“生之本义”的内涵之外,它也是“理”,是“生之理”。因此,“气质之性”是兼“气质”与“理”来说的,“性即理也”,这里的“性”是指本然的“性”,是与“理”同义的“性”。因此,“性”只有一个,而“理之性”(或“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在于两者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而已。“理之性”或“本然之性”更加强调“性”的本然状态,更加强调“性”在本然状态上是至善的,“性”即是“理”。而“气质之性”更加突出“性”的“生”的意蕴,更加突出“性”在具体事物和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突出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将“性”认作是两种“性”,将之视为同一个“性”的两种不同研究视角较为妥帖。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子看来,“性”虽然不免“降付”于“形气”“气质”“气”之上,也不免会受到“形气”“气质”“气”的“薰染”,从而无法崭露作为本然状态的“性”的全部功能和全部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气质之性”是“杂”的,而只是说“本然之性”由于受“形质”“气”“气质”的影响而无法在功能上发挥其全部的作用,这种“薰染”应该是就“性”的“用”的层面来理解,而不应该从“体”上来理解。如果就“体”上来看,“本然之性”与“气”的关系应该是不离不杂的。朱子也说:“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是为性之本体也。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
因此,在朱熹看来,“性”虽然在意义上与“理”有重叠的地方,“性”也在此意义上与“理”同义,但是,“性”就其概念来看,它又是与“理”相区别的,这种区别之于“性”是根本性的,这主要反映在“性”的“生”之本义上。“生”之本义,就概念使用上来看,使“性”与“理”相区别,彰显“性”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独立性;而就概念的内涵来看,它也使得“性”的基本内涵需要放到“降付于形气之中”“堕于气质之中”,因而“‘才说性时’,便只说得气质,不是理也”。也正因此,“气质”正是“生”之本义在理学语境中的体现,它凸显了“性”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独立性。
二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并不是要说有二种“性”,也并非只是纯粹为了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存在状态。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与其说是在描述或限定“性”的内涵或表达,倒不如说是朱熹在规范自己关于“性”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而以“气质”来限定“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性”具有能够以“气质”来表达的基本内涵,即“生”之本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气质”这一表达能够表现出“性”的“生”之本义。
那么,“气质”这一表达何以能承担限定、规范之责呢?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从“气质”这一表达本身说起。
“气质”不同于“气”“气禀”,以往我们多将三者混同,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三者的区别,也没有充分注意到“气质”这一表达的独特性,自然也无法很好地理解包括朱熹在内的理学家以“气质”限定“性”的深刻用意。“气质之性”的“气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形象气质”的“气质”,它是指“气”化而成的“有形之质”,是“气”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状态的“气”或“气”的集合。“气质”与“气”“气禀”在意义上有重叠,但又有所区别。与“气”相比,“气质”虽然在本质上也是“气”,但是,它又与一般意义上的“气”不同,它不是本然状态的“气”或“气”的本然状态,而是可以形成“有形之质”的具体的“气”,是通过特定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或运动态势的“气”或“气”的集合。与“气禀”相比,“气质”虽然是“气”化而成的“有形之质”,有赖于“气”的化生过程,但是“气质”在涵盖“气禀”内涵的同时更侧重于“气禀”过程或活动的完成,它是“气禀”而生的“有形之质”。
在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最先使用“气质”“气质之性”这些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学体系。还可以看到,张载已经将“气质”与“气”“气禀”相区别使用。如他说:“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①张载:《张载集·正蒙·太和篇》,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9页。“游气”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本然状态的“气”,这种状态的“气”虽然具有了阴阳、清浊、轻重等特征,并且具有了化生天地万物的可能性,但是,它却不直接就是天地万物,只有当它“合而成质”时,当它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形成“有形之质”时,天地万物才由此化成。同样的意思,张载还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②张载:《张载集·正蒙·太和篇》,第7页。“气”化生天地万物,而“气”的化生功能就体现在“聚”“散”上,当“气”聚时,万物则生,当“气”散时,万物则灭。在此意义上,“万物”不过是“气”的暂时的、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或运动态势,是“气”或“游气”化生而成的“有形之质”。
在朱熹那里,关于“气质”,《朱子语类》也有以下几条记载:
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气,所以做得物事出来。五行虽是质,他又有五行之气做这物事,方得。(第9页)
质并气而言,则是“形质”之“质”;若生质,则是“资质”之“质”。(第76页)
气,是那初禀底;质,是成这模样了底。如金之矿,木之萌芽相似。(第259页)
“游气”、“阴阳”。阴阳即气也,岂阴阳之外,又有游气?所谓游气者,指其所以赋与万物。一物各得一个性命,便有一个形质,皆此气合而成之也。(第2508页)
在朱熹看来,“气质”之“质”是“形质”,而非“资质”“生质”,所谓“形质”就是指“有形之质”。“质并气而言”,也就是说,“气质”是指“气”化而成的“有形之质”,而不是指以“气”为“生质”“资质”,即强调“气”的属性或特征。“气”化而成“有形之质”,“气”自然是构成天地万物的质料或原始材质,是“那初禀底”。但是,有“气”却不代表就是天地万物了,而必须“气”以质之,通过“气”的“聚”“散”等活动形成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或运动态势,如此这般,“气”才不是“游气”,方才可以真正形成天地万物,即“质,是成这模样了底”,如此,天地万物才有了“一个形质”,这“形质”都是“此气合而成之也”。
总的说来,无论是在张载那里,还是在朱熹那里,“气质”都与“气”“气禀”不同,它指的乃是“气”化而成的“有形之质”,而这“气”化而成的“有形之质”就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这点我们通过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到。在此意义上,“气质之性”就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之“性”。那么,以“气质”来限定“性”又与以“物”“人”来界说“性”的区别在哪里呢,包括张载、朱熹在内的理学家以“气质”限定“性”的深刻用意又在哪里呢?
首先,“气质”能够表达“性”的内涵,尤其是“生”的内涵。“气质”指的是“气”化而形成的“有形之质”,即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于此,以“气质”来限定“性”,则意味着“性”必须“降付于形气之中”,必须着落于人和物之中,即:“性”指的乃是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的“性”,是“人之性”或“物之性”,而非某种形上的、抽象的实体或本体,这既使“性”与“理”相区别,又凸显出“生之理”的内涵。因此,朱熹说:“气积为质,而性具焉。”(第2页)只有“气”化生而成“有形之质”,才有“性”之存在,才有“性”之被言说、被讨论的可能。同样的意思,朱熹还说过,“人生而后,方有这气禀,有这物欲,方可言性”,“‘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是气质”(第2431页),等等。
其次,“气质”不仅仅只是表达了“性”的内涵,还深化了“性”的哲学意蕴,并且拓宽了对“性”的问题的研究视域。“气质”虽然指的就是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但理学家使用“气质”来“替换”具体事物(人和物),使我们对有关“性”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不再仅仅局限于具体事物的差异性,也不必再纠结于人、物的差异。虽然这些层面上的“性”的探讨不乏其研究价值,但是“性”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而应该在更高层面或更广阔的理论视域下进行。于此,讨论“气质”则比单纯讨论人、物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它将人、物等具体事物在“气”的语境下或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提升,人、物之别于此被消融,具体事物的有限性也于此被消解,有的只是“性”的问题的哲学思考。在此意义上,“气质”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性”的内涵,也更有利于“性”的哲学探讨,同时也展现出理学家“万物一体”“万物一理”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情怀。
另外,就“气质”这一表达来看,“气质”指的乃是“气”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来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或运动态势,这里的特定的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的差异性则直接决定着这种最终形成的“气”(或“气”的集合)的存在状态或运动态势的差异性,或者说,“气”的聚散作用之不同直接决定着“气质”(即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如何,就像碳分子的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之不同决定着最终“有形之质”或为石墨或为金刚石一样,而这不同的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正是“性”“理”的具体表现。这也就是说,“气”在“性”“理”的规范下形成具体的、具有差异性的“有形之质”。或者说,“气”是质料因,是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之形成的原始质料,而“性”“理”则是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正是在“性”“理”的规范下,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才得以生成,并且以“如此这般”的存在状态或运动态势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气”与“性”“理”也并非二物,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故朱熹说“气即性,性即气也”。也正如此,“气质”这一表达凸显的不仅仅是“性”的“生”之内涵,其更能表达出“生之理”的意蕴。诚如张载所说“游气纷扰,合而有质者,生人物之万殊”。纷扰的、具有阴阳等不同特征的“游气”聚合而形成“有形之质”,人、物的各种差异性也体现于此。就人与物来说,它们都是生于“气”,都是“气”或“游气”的聚散活动而形成的,但是,聚散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最终聚合的效果,即“有形之质”的差异性,“人物之万殊”也正表现于此。同样的意思,朱熹也说:“气积为质,而性具焉。”“气”通过聚、散等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而形成各具差异性的“有形之质”,而“性”具于其中,一方面体现于“有形之质”上,另一方面也体现于“有形之质”的形成过程中,即“气积为质”的过程中。就前者而言,相比于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性”是先天的,从而关于“性”的诸多讨论需要放置到“生”的语境之下,即“性”是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的“性”,是具体的、实践的,而非某种纯然的、抽象的本体;就后者而言,“性”彰显出其“生之理”的理学内涵,具体事物本身的存在就是“性”“理”的具体体现,它们都是“气禀”的特殊组合方式或运动方式的具体彰显,“性”之于具体事物的存在来说则不仅仅是先在的,而且是具体事物的“生之理”,“性”的理学内涵在“气质”这一表达中得以体现,而这比纯粹说“人之性”“物之性”更具哲学意蕴,同时这本身也将我们对于“性”的探讨引入到更为广阔的理学视域。
总的说来,以“气质”言“性”,就“气质”这一表达本身来说,它不仅足以彰显出“性”的内涵,还将“性”的言说语境“替换”到理学视域之下,使“性”的理学内涵(即“生之理”)得以充分地彰显。
三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关于“气质之性”概念的讨论和使用,绝非只是对传统理学概念的简单沿袭或顺带性研究,而是根源于其理学体系的特定需要,即“气质之性”这一概念有利于其理学体系的构建及其理学思考的开展。在此意义上,尽管“气质之性”概念早在北宋张载那里就已经使用了,但是,朱熹所论之“气质之性”仍然是属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专有概念,或者说,朱熹在其理学语境下赋予“气质之性”以新的诠释意义和解释语境。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朱熹和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张载那里,对“气质之性”的使用有着不同的理论语境和思想诉求。概括而言,张载对于“气质之性”的使用和讨论更多的是在其“气本论”语境下进行的,“气”“气质”是他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他更关注于“性”能否以及何以能够在“气”的层面或视角下被讨论,从而为他“气本论”语境下的关于“性”的研究提供某种思考视角或理论依据,他的“变化气质”工夫论主张也是在此意义上被提出来,即:“性”可以被放置到“气”“气质”的层面上研究、讨论,所以,“变化气质”才可以达到“化性”成德的目的和效果。朱熹则不同,他对于“气质之性”的使用和讨论是在其“理本论”语境下展开的,“性”是其关注的重点。在朱熹理本论语境下,“性”既是一,又是多。“性”是一,它与“理”一样,可以在本体论或形上层面上与“气”“理”等概念一道被“整体性地”思考。同时“性”也是多,“性”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形上实体,而是面向现实世界敞开其意义,它可以在现实世界之中、在具体事物之中“具体地”“分殊式”地呈现。而就“气质之性”这一表达来看,以“气质”言“性”,一方面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在“气质”这一表达下得以被“整合”起来,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特殊性在“气质”这一表达中得以被“消解”掉,人和物、人和人、物和物之间的差异性也在“气质”这一表达中得以被“悬置”起来,在此意义上,“气质之性”保证了“性”可以在形上层面上被“整体性地”思考。另一方面“气质”这一表达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整合”本身也意味着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这一具体性、特殊性“事实性地”“现实性地”“客观性地”存在,在此意义上,“气质之性”也保证了“性”本身在形下层面上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朱熹对“气质之性”的使用和讨论,正是顺承着他对“性”的问题的研究需要而来,也是其“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理学思维方式的具体呈现。
也正因此,我们说,当朱熹使用“气质之性”概念并思考心性论问题时,这一概念及其使用本身彰显出朱熹哲学的某种特定的立场或特质,也正因为这种特定的立场或特质的需要,朱熹才会在传世文献中留下大量关于“气质之性”的使用和讨论。这一特定的立场或特质就是:理学关于“性”的问题的考察或心性论问题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于形上层面的考察,而需要放置到现实世界来加以考量,而也唯有将“性”放置到现实世界加以考察,“性”的问题才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并且也只有将“性”始终放置在现实世界加以思考,才是儒家或理学所要讨论的“性”。在此,朱熹承接二程“论性不论气,不明;论气不论性,不备”的话头,在“气质之性”概念中将“性”与“气”兼着讲,从而使理学家关于“性”的思考始终葆有对现实世界的关怀。这一点彰显出朱熹哲学的实践品格,也呈现出其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和价值追求。
责任编校:余 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