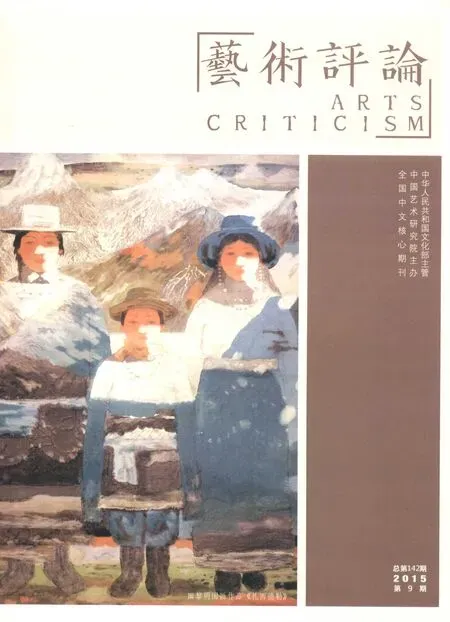依托经典 展世态图卷
——评歌剧《日出》
2015-12-16丁旭东
丁旭东
依托经典 展世态图卷
——评歌剧《日出》
丁旭东
非常期待歌剧《日出》,有三个原因。一是经典名作,曹禺三部曲之第二部,话剧从复旦大学首演一炮打响,到复演走红东瀛,再到“北京人艺”保留作品,一直都有大量粉丝追捧,这次“变身”成歌剧,又会呈现怎样的精彩?二是作曲金湘耄耋老年,身患恶疾,抱病用生命创作,定是其不容置喙的晚期风格,该是怎样的炉火纯青?三是此次创演团队还包括了原著作者女儿万方(编剧)、擅长人性挖掘的李六乙(导演)、冉冉新星宋元明(女一号)、中国著名男高音戴玉强(男一号)、剧院首席指挥家吕嘉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出演),等等,如此超高的配置,会带来什么样的审美震撼?
怀着满满的期待,笔者观看了2015年6月18日歌剧《日出》的演出,这是其世界首演后的第二场演出。下面我们就以这场演出为观照对象简要做个评介。
一
歌剧《日出》是一组故事。核心是一个二十来岁貌美如花的著名交际花陈白露小姐从沉沦到部分人性被唤醒再到继续沉沦,最后绝望自杀的悲剧故事。与之相伴的是与陈白露有直接关联的两个人的故事。第一个人是她的初恋情人,一个诗人,一个正直善良、有“绝对理想”的堂吉诃德式人物。他深爱着女主角,试图带她离开昏暗污浊的生活,也曾用真爱打动对方,唤醒其未泯的人性,但此时的陈白露已经不是过去的“竹筠”(陈的过去名字),而是那种享受安逸奢靡惯了的没翅的“金丝鸟”,已经无法走出“鸟笼”,诗人的空洞理想终归无法成为现实。第二个人物是包养女主角的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一方面一掷千金为红颜,包养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交际花陈白露,过着淫荡堕落、声色犬马的生活;一方面苛刻压榨着以李石清为代表的雇员;同时依靠发行公债、向黑恶势力“金八”押借巨额贷款,危机四伏地经营着自己的泡沫产业。当然,泡沫终有破碎的时候,那时候悲剧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性地发生了。第三个插入的一段故事,讲的是曾被女主角施救的孤儿“小东西”,暂时逃离“黑八”魔爪,但她依靠的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陈白露,所以,等她被抓回,沦入人间地狱——淫窟后,坚贞的她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人间地狱”的生活。
二
与话剧《日出》相比,万方的编剧主要有三方面调整。一是精简了人物角色。把追求陈白露的方达生和陈白露的前夫——一位写下诗集《日出》的诗人进行了角色合并,创造了诗人角色;把大丰银行书记(抄写员)黄省三的戏份删除,另外去掉了张乔治和王福升两个奴才角色。二是把许多脱离主要角色的枝蔓繁多的戏浓缩,如和小东西一起在叫“宝和下处”的妓院做低档妓女的翠喜卖身养家的内容简化为老年妓女翠喜对自己身份的悲述;把小东西父亲在潘四爷工地出现工程事故被柱子砸死的戏隐入到“小东西”的身世自我介绍中。把富孀顾八奶奶和胡四的戏份减少等。三是增加或突出了一些新场景,如诗人和陈白露对“小东西”的悼祭以及最后陈白露自杀后的“日出”场景等。
通过现场观演效果来看,改编之后的剧情更加紧凑,主题突出,结构简洁,可是仍有观众提出异议,集中在关于剧的思想性问题的讨论。有人认为,这部剧脱离现实。而另外有人认为,这部戏很当代[1]。其实,这个问题在1979年前就激烈地辩论过[2],当时,戏剧史学家黄芝冈认为,这部戏“鬼气森森,他们为甚么不起来反抗旧势力,为新生活而奋斗?”周扬反驳说,这样的评价对作家这是不公允的。(曹禺)创作动因是他从报纸上读到了两则关于家庭惨案和交际花服毒自杀的新闻,于是拿起笔来,对这两个社会事件大加抨击。文艺是一面镜子,如果镜子照出丑恶来,你不能说是镜子的问题。批评家没有理由反对作家描写社会中的黑暗的消极的现象,他所要检阅的只是被描写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的哪些侧面,反映得真实到甚么程度。[3]曹禺回应“批评”,写了篇万字文章,其中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创作动机,“一件一件,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我按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我绝望地嘶叫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忍耐不下了,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4]从曹禺和周扬的话可以看出,《日出》的原形是真人真事,《日出》体现了作家对这种社会的义愤与不平,可见至少此剧曾是一部具有高度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当然,这部剧的伟大,不仅在于此,更在于它在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揭露社会黑暗、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当时,敢于写出这样的作品,是需要有非常的社会担当、非常的正义感与非常勇气的!资华筠说,做文艺工作要有“三真”精神,一是真实的感受,二是真切的表达,三是揭示艺术的真谛。而《日出》给我们的启示是,可再加上一条,“真正地反映”(社会)。其实,这部剧本身对我们现在文艺界就有镜鉴意义。当然,如李六乙导演所说,该剧反映的“人与环境”“人与自我”之间,人的心理存在的“尴尬”“困境”也是现在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具体来说,当前社会,像陈白露那种甘于做腐官巨贾的“小三”“情妇”还少吗?像诗人那种空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还少吗?像潘月亭那种投机商人还少吗?……所以说,这部戏具有现实意义,只不过浅尝辄止时看不到罢了。
其次,谈谈剧的结构问题。有人认为,这部戏内容散,像“拉洋片”。而另外有人认为,“《日出》中所描述的情景是社会的横断面,从中可看到当时的社会中各阶层的生活状态。”[5]为什么人们的判断会产生如此差异?这可能与该剧的结构有关。歌剧的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结构,二是内在结构。先说外在结构。该剧分为四幕。开始是两段引子。第一段是表现体力劳动者积极乐观精神状态的《夯歌》。第二段是表现女主角陈白露自杀前心理告白的咏叹调《你是谁》。接下来是女主角陈白露的往事回忆,也就是四幕内容。最后结尾是陈白露自杀的情景,用的音乐还是合唱《夯歌》。从以上简要分析来看,该剧采用的是“包饺子”的手法,前后呼应,中间的“馅”即是该剧四幕内容,应是陈白露的心理回顾过程。可见,剧的外在结构合理。
再说说内在结构。内在结构指剧情的事理逻辑。按事理逻辑来说,中间四幕主要呈现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交际花陈白露在花天酒地的大旅馆中被早年恋人“诗人”找到,诗人要带她远走,她经过考量,最终选择过被人包养的生活。这段情节中,陈白露放弃跟诗人远走的原因体现在陈白露对诗人的问话中——你拿什么来养我?诗人不可能给出她想要的回答,因为诗人是“堂吉诃德”,所以,这一情节安排是合乎逻辑的。不过这也体现了陈白露扭曲的人生态度,即男人就要养她。她把自己定位成了依靠他人养活的“金丝鸟”。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的懦弱本性,即接受事实,默许自己“恋人”被包养。第二个故事是被陈白露和诗人称为“小东西”小姑娘,她是孤儿,从父亲给他唱的歌可以看出,他是建筑工人的后代,出身于贫寒。当她被黑帮老大黑八抓去,黑八要霸占她时,她誓死不从,曾被虐待、毒打,最后,抓住时机逃跑了,逃到了陈白露的包房。这说明“小东西”是一个性格刚烈、品性高洁的女孩,这为后来她的自杀做了伏笔。因此,当她又被黑八手下抓去,遣到“宝和下处”卖身时,她不堪忍受走上绝路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堂吉诃德”式的诗人曾去解救她,但这种空有理想的人当然是难成大事的,所以“小东西”的死是必然的。第三个故事是包养陈白露的潘四爷,这个靠投机、欺诈营生的“泡沫型”资本家,他发行公债,利用浮躁、期望一夜暴富的社会人群获得供己挥霍的资财,现实社会中这种人是不少见的。但等他经营不善要靠抵押正在建设的大丰银行大楼来获得恶势力黑八的支持来解决资金断链的时候,他就是成了一个任黑八摆布的傀儡,傀儡被人丢弃是必然的,所以黑八撤资、潘月亭破产也有必然性。以上三个故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旦有一张倒下,就会作用到下一张,所以,陈白露失去潘四爷的包养后,选择自我毁灭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的[6]。可见,该剧的内在结构也是基本合理的。
但是,我们通过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比对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性。具体说,如果所有剧情是陈白露的回忆,那么表现“小东西”在“宝和下处”的生活处境和潘四爷与其下属李石清的矛盾冲突的情节统一到外部结构框架中是有些牵强的,通俗点说,作为该剧“饺子皮”的大框架是无法把全部剧情容纳。如果要容纳进去,该剧就要以陈白露经历为线索,也就是说以上两段情节,陈白露应是在场的。但实际上,陈白露是不在场的。所以,我们说,本剧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之间的统一性方面存在部分冲突。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和这部剧类似的《茶花女》就会看出,茶花女也是一个高级妓女,但在剧情发展中她是贯穿始终的。
当然,我们不能轻易否定《日出》的结构问题。实际上,曹禺在原创之初是有他的想法的。他说:“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的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显然,其对法国作家雨果《克伦威尔》的戏剧结构予以了借鉴。该剧又称“世态图卷剧”,“像一幅规模异常庞大的画面”或者“像一棵巨大的橡树”。它和“老一派的戏剧” 不同, 不是只拘泥于一、二个主人公写戏, 而是写出“一大群人物”, 其所容纳的情节和细节也极其丰富多样, 反映出了“无比宏伟的时代全貌”[7]。可见,这部剧的外部结构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线性特征,而在内部结构方面则体现了横向铺陈的面状特点。这大概就是一些观众从结构上提出异议的原因所在。
三
下面我们来探讨剧作艺术表达方面的几个问题。
先说音乐。歌剧《日出》的音乐创作是相对来说是成功的。首先,音乐贴合了角色人物的性格与内在的心理。如开场,交际花陈白露自绝前的一刻,作曲家用极具张力的咏叹调《你是谁》表现陈白露内心绝望与挣扎。当视线回到从前交际花的“辉煌时刻”——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音乐的笔墨着力在富孀顾八奶奶和她的“面首”胡四这两个封建“遗瘤”身上,音乐用京剧皮黄腔写出轻佻的音乐——《叭哒采》。当包养者潘四爷来到大旅馆,音乐冷峻低沉表现主人公的道貌岸然。当诗人出现,音乐又变得抒情明快表现了主人公的“单纯”与浪漫,其中采用不断的反复且急促的音乐来表现诗人心中对爱的呼唤。当“小东西”倾诉自己的身世时,音乐采用类似《江河水》的民歌哭腔音调,加入二胡等民族乐器,体现主人公的纯朴与身世的凄楚。其次,音乐成功营造了场景气氛和典型人群的心理,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如开场的《夯歌》,以中速、雄壮有力的号子般的曲调唱出“老阳哎出来啰”,点明了主题——不足者,说明的寓意——他们才是“太阳”,才应是社会的主人,才可能带来真正的“日出”。音乐的表义功能在这里凸显,因为许多观众认为该作品写《日出》,但整部剧都是在写“日落”,处处充满着没落、死亡和黑暗。其实,这一误解就是缘于审美观照的片面性,忽视了音乐对作品内涵的揭示。可与此相佐证的是,该剧中还有两处再现《夯歌》或其部分曲调的情况。如可怜的“小东西”在跟陈白露和诗人倾诉的时候,唯一的一处充满了阳光、幸福和向往的表情出现在她唱起父亲常常唱的歌“老阳哎出来啰”,这就表明了“小东西”真正的心理依靠就是他的父亲,以及以他父亲为代表的广大底层劳动者,他们是“太阳”!最后,该剧结尾处,也就是陈白露自杀后,《夯歌》再起,也再次点名主题——作为“不足者”才可能给社会带来“日出”。与《夯歌》相对应的,剧中的另一合唱《这城市》采用了快板、融入了重金属摇滚乐的风格,加入了爵士鼓等流行音乐特性乐器,使整个音乐充满了似乎不可遏抑的高昂激情,非常传神地揭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被物质、权力、金钱的欲望所“绑架”,不择手段,往上攀爬的躁动亢奋的心理景象。可见,单从音乐上来说,这部剧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举例来说,当“小东西”逃到大旅馆,被陈白露和诗人接纳,“小东西”和陈白露、诗人用广板速度唱出富有五声性民族风格的三重唱《我想有个家》,这段音乐舒缓、深情、充满着向往,唱出了三个人共同的心声,也唱出了所有社会底层人民的心声,相信在许多房价已成天价的现代都市,每个城市漂泊的人听到这段音乐,都会不由落下心酸的泪水。这段音乐,使该剧的情感表达达到一个小高潮。同时,也隐喻出一个深刻的人生命题:幸福的生命体验是建立在物质的基本满足和安全感上的,“家”是人们起居场所,也是物质生活和让心灵安顿的基本保障。这段音乐的立意之高,堪与杜甫之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相媲。三是凝练精准、个性突出、富有神韵的主题动机的贯穿始终,是音乐表达明确清晰。该剧,音乐主题动机十分清楚且个性特点突出,具有很强的识别度和内涵的概括力,如“不足者”底层劳动大众的号子风格主题动机,柳巷妓女具有江淮一带民歌风韵的主题动机,“黑三”与其帮凶无调性极不协和的音乐主题动机等。在这种鲜明的主题动机的贯穿下,音乐又凸显了其叙事功能,如第三幕《妓女/黑三之歌》中,当底层妓女唱出缠绵婉约的五声性江淮民歌风格的音乐时,突然会听到黑帮主题动机的粗暴闯入,生动隐喻了其被控制、践踏以及含泪卖笑的生活基调。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的间奏曲内涵丰富(几乎可以囊括整部歌剧的戏剧内涵)、乐思流畅、写作精致、非常具有可听性,是一首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交响乐精品。这在近年来我国原创歌剧中是较为少见的,此可算是歌剧《日出》带给中国艺术又一意外惊喜。
再说表演。表演是二度创作。歌剧的表演不仅包括形体表演也包括演唱等方面。实际上,歌唱家走上舞台,应该就不存在其本人,只有角色,塑造角色的成功标尺之一是使人忘记表演者演唱技巧,甚至忘记表演者本人。从这个标准来说,“小东西”的扮演者王一凤演唱音量适中、音色纯净、吐字清晰、处理简约,仿佛一个参加音乐学院的艺考生,但这种声音形象恰恰符合了剧中人物角色的身份:年龄十五六岁、身世可怜的小姑娘。“小东西”虽是戏份不多,但表演者分寸拿捏恰到好处,角色塑造十分成功,让人印象深刻。戏份最重,角色内在性格变化幅度最大,唱段技巧难度最大的莫过于交际花陈白露的咏叹调了,没有深厚的演唱功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个角色的,旅奥歌唱家宋元明不负众望,从歌唱到表演都较好地完成这个角色的艺术形象塑造。但美中不足的是,歌唱家在咬字吐字方面稍显含糊。本场最为出彩的角色非戴玉强扮演的“诗人”莫属,戴玉强的演唱饱含情感,高亢明亮,挥洒自如,具有很强的声音穿透力和感染力,打动了无数观众。但可能是选角的缘故,戴玉强健壮的身材和英雄男高音的音色和自信的表演,容易让人容易误认为这是位笃定的英雄而不是那位多情、满腹空想的诗人,甚至一度让人误以为他会扭转悲剧进程。所以,笔者窃以为,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戴玉强的表演如能略加收敛可能会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最让人感到“惊艳”的是“面首”胡四的扮演者肖玛,他把一个不阴不阳不男不女的社会“浊物”简直演活了。另外,这个角色采用了超男高音唱法,这对于中国歌剧舞台角色多元化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不过,与肖玛精湛的形体表演相比,其演唱略微逊色,以至笔者看来,此剧未来复排,如直接由戏曲中的男旦进行混搭表演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以尝试的选择。由此可见,总体来说演唱与表演充分体现了歌唱家们深厚的艺术功力,但从表演者通过声音对角色的塑造方面,尚有进一步雕琢完善的空间。
最后说说舞美设计,有三点特别值得提出地方。一是斜升式舞台的设置。这一设置,不仅在视听方面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受,而且体现了特别的艺术意味:舞台象征着社会,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攀登,但无论走的多高多快,最终要的是有固定的依靠,否则就会必然地滑下。同时,也隐喻了舞台上的戏剧人生。陈白露身为第一当红交际花,风月场上,风光无限,可是当包养她的潘四爷破产后,她就只有走向灭亡。即使她继续接受黑八等人的包养,待来日年老色衰、人老珠黄,其命运归宿也是一样。那位穷尽心机、奸招使尽、一心向上攀爬的利己主义者潘四爷襄理李石清也是一样,到头来也是落得个两手空空、一片苍凉。究竟什么才能成为真正的依靠?该剧没有给出结论,却通过这一设置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二是最后“日出”场景设置。舞台一片血腥的红色,色彩由浅入深,这就是该剧创作者理解的日出。这一设置非常巧妙。血红代表着陈白露的毁灭,并选择了太阳即将喷薄而出大地一片通红的时刻,具有合理性。同时,又表达了观点:只有流血牺牲才可能还来光明,从而深化了这部剧反帝反封建的宏大主题。三是其他一些场景布置。无论体现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夜生活的大旅馆,还是“别样风景”的烟花柳巷,等等,都用寥寥几个简单设置体现出来,并且具有较为丰满的意境,可谓匠心独到。不过用一个欧式软包长沙发来象征高级交际花陈白露的包房未免太简单了点,至少不能让人不能直接联想到剧中故事的发生环境,应该说这是玉中之瑕。总体来说,整场的舞美设计简约而不简单,意境创设丰满而不繁缛,在不需超大制作投入的前提下艺术家用独到而精心构思提高了歌剧艺术的审美观赏性,值得称赞。
总体来说,歌剧《日出》的编创“移步不换形”,忠于原著,是一部具有时代跨越性体现讽喻原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剧作的结构方面,没有采用单纯的线性陈述,而是同时横以多个侧面,多视角展现了世态图卷。这在对未来中国歌剧的创作具有探索与启示意义。在音乐方面,作曲家博采约取,用中西多元音乐元素,塑造了个性鲜活的音乐角色,并运用交响化的音乐语言、典型化的主题动机和张舒有驰的流畅乐思细腻刻画了人性复杂各异的精神世界并有力地推动戏剧的发展;同时结合具有意境美感的场景设置,创造了多维度的艺术审美空间。无疑,该剧是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上乘之作,但也不可回避的是在局部内容的结构统一方面,在表演处理的细节雕琢方面,还有一定提升完善的空间。
注释:
[1][5]杨杨.复杂音乐刻画都市群丑[N].京华时报,2015年06.21。
[2]二十六岁的曹禺创作的话剧《日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九月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之后,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即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分两次刊出对该剧的“集体批评”。针对一些批评意见, 曹禺专门撰写了《我怎样写〈 日出〉》一文作为答复,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大公报》。
[3]《光明》第2卷第8号,1937年3月25日。
[4]田本相( 编).《日出》剧本及《〈日出〉跋》[C]./《曹禺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6]小仲马《茶花女》中的主人公玛格丽特实际上是和陈白露相似的一个角色,都是高级妓女,都是被人包养,都有一个试图解救自己于水火的人,一个是诗人,一个是阿芒,但二者同样走向死亡,一个走向自绝,一个是病死。笔者以为后者更具有合理性。陈白露依靠自己头牌交际花的声名,再找一个包养她的金主不是不可能。因此,我们说陈白露的命运归宿有一定的合理性。
[7]柳鸣九译.雨果论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80.
丁旭东: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中国音乐学院美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