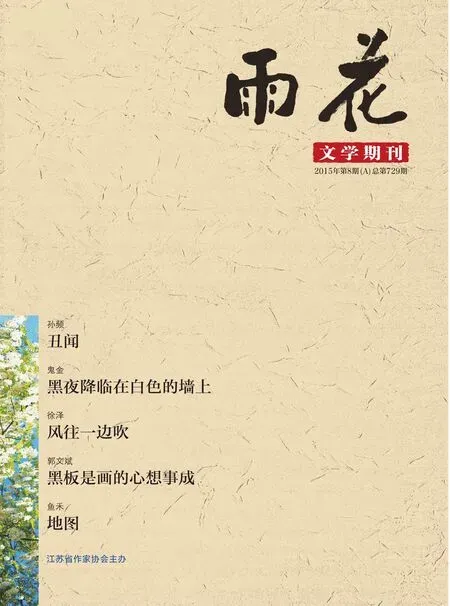胆结石
2015-12-16庞余亮
■庞余亮
胆结石
■庞余亮
胆结石:胆囊或肝内、外胆管发生结石的一种疾病。胆结石的形成与代谢紊乱、胆汁淤滞和胆道系统感染有关。胆石可分为纯胆固醇、胆色素钙盐及混合性。我国以胆管内胆色素结石最多见,常伴有胆囊炎及胆管炎,两者互为因果。发病时突然发生剧烈难忍的右上腹阵发性绞痛,称为胆绞痛。——《辞海》1702页
还记得那棵全庄最高大的榆树还在,就在我家院子里。母亲在大榆树下对我说,一个妈妈可以养十个儿子,十个儿子不一定能养一个妈妈。当时不懂,但后来的生活全被母亲说中了。全身是病的母亲一个人只能留在老屋生活。
父亲去世后六年,我准备离开家乡,去做一个乡下人做了多年还没有做成的“城里人”梦。我劝母亲一起走,母亲不同意。一直到离家之前,我都努力想让母亲改变主意,可母亲一直没有松口,她坐在靠着有她照片的墙下捻线坨。
本来墙上有两幅照片的,父亲的,母亲的,在替父亲化牌位的时候,大哥主张把父亲的遗像烧了。那挂父亲照片的那块墙上就多出了一块白,而一旁母亲的照片显得很孤单。但母亲总在有她照片的墙下捻线坨。照片里的母亲比捻线坨的母亲年轻许多。
其实母亲捻的线坨一点用也没有了,可是她爱捻线坨。一捻,那线坨就转,转得飞快,都看不见线坨了,只有一束倔犟的光晕。
母亲最好的借口是晕车。闻不得汽油味,闻一下黄胆都要呕出来了。母亲对我不断的劝说还是很坚决,你走你的,我哪里也不去。母亲说,你是想让我去坐牢。母亲甚至说了一句绝话,你叫我去,是存心想让我早点闷死。母亲还说,人家能过我就能过。
母亲的固执有如我老家许多老人的固执。老家空荡荡的村庄里除了房子,就是老人了。到了晚上,老人们哪里也不去,猫到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睡觉。他们的子女基本上全在南边打工,除了春节回家才能见到子女一次。
我说多了,母亲不拒绝了,说出了一个大理由:“等我发了大财了”再去。这个问题就把我难住了,令我羞愧,我也暗暗有了雄心。可是雄心只是瞬间的事,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发大财,什么时候才能发大财,出外谋生的乡下人有多少发了大财的?
母亲全身都是病,她患了十几年的高血压,还有心脏病、骨质增生。高血压和心脏病都有常用药对付。只有骨质增生令我们头疼。我们问过医生,骨质增生疼起来是非常疼的。可是母亲说不碍事。村医院的医生也说她老了,零件也朽了,都是老毛病。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母亲的鬏。
母亲的生活费是我们仨兄弟均摊的,医药费也是如此,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母亲如果不生病,自己是能够照顾自己的。比如烧饭。比如洗衣服。比如倒痰盂。可最大的问题是母亲每天一定要梳头,还要“窝鬏”,就是老年妇女的那种鬏。
“窝鬏”是一件非常费时的事,母亲发了心脏病,医生劝她把后面的鬏剪了,母亲没有同意。母亲的鬏有三十年历史了,我妻子曾在一个地摊上买到了几副织得不错的“网鬏”,是五彩丝线编的。我带给母亲的时候,母亲很是高兴过一阵子。至于鬏上的一根簪子,她说是父亲买给她的,父亲没有舍得买足金的,是包金的,上面的金水早掉了,只剩下铜色了。母亲的鬏也没有以前大了,但是母亲还是每天打开那生了锈的铁皮梳妆盒,用缺了齿的牛角梳梳她的长发,窝好鬏,然后上网鬏,然后插铜簪。一步不能少。
母亲的心脏刚好些,她又开始准备窝鬏,可是她还没有梳好,疼痛的心脏又快速地跳了起来,医生把我们骂了一通。后来还是我帮她粗略地窝好。母亲很不满意,夜里就把它重新散开了。就在陪床的我睡着的时候,她又重新把头发梳好了,窝好鬏。早晨我对母亲发了火,我说我工作很忙,你自己不爱惜自己,你拿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怎么办?母亲不说话,她躺在病床上,不说话,也看不出她生气的样子。她肯定满意自己的这次梳妆。
母亲头发后面的鬏终于还是没有保住,还是她自己主动剪掉的。原因就在于她得了胆结石。由于出差,没有得到消息,等得到消息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住进了县城人民医院了。
胆结石的疼痛我是知道的,胆结石之疼是要命的,把人往死里疼。那疼,把一个人所有的神经全部抓住,一旦发作起来,经常是疼得在床上打滚,嘴唇都咬破了。这样的场景我见得太多了。老家水质不好,每个人的胆囊负担都重,什么胆囊炎胆结石似乎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外面作为大手术的胆结石开刀,放在我们那里的乡镇医院都只是小手术,更不谈县城的人民医院了,据说县城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开胆结石在全国都很有名。
我看到了母亲,她脸色很差,她见到我,似乎很不好意思。她说,医生说我胆大。我不说话,我觉得母亲有点怪,她怎么老是低着头,后来我看出来了,她头上窝了那么多年的鬏给剪了,剪成了齐耳短发。她有点不好意思呢。母亲依旧说,医生说我的胆大,胆里面还有石头,你说石头怎么会钻到里面去了呢。我怎么回答?
母亲又抓了一下后脑,说,这下梳头很顺手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一点不像我父亲,她还是那样,从来不想让子女为她麻烦。临出院,母亲给我提了一个要求,叫我替她买一顶“扎头布”,也就是方巾。可是现在的县城不是过去的县城了,现在的县城不卖过去农村妇女扎的方巾,而是卖一些时髦的丝巾,或者纱巾。最后我买了一只发箍,她戴上去,对着玻璃照了照,怎么也觉得别扭,还是取下了。
我没有问母亲剪下的鬏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没有问那根铜簪子。没有鬏的母亲头发就容易乱了。有时候我回家,远远看见母亲,总觉得她心里有个保存了很多年的东西被剪去了。
每次抽空回家一次,庄上的几个老太太见我回来,总是喜欢跟我说话,说她们的孙子孙女。这些留在身边的孙辈总是不听话的多,有个叫宁娣的老人还把她的孙子拖到我的跟前,意思是叫我“传达他父母的话”,帮助这个老人撒谎。看着老人的表情,我只好撒谎。
我的撒谎肯定是不管用的。后来听母亲说宁娣还和整天沉湎于游戏机室的孙子打架。追了全庄。后来打油了,这个常常逃学的孙子还和他奶奶对骂,直到把他的奶奶骂哭了。
这个还不算惨的,邻庄有个老人帮助儿子带孙子,结果孙子下河钓龙虾溺死了,他自己只好也喝了农药。那个喝农药死的老人的葬礼,母亲也去看的,眼泪鼻涕淌了一大把。你说怪谁?其实能怪老人吗?
还有一对老人,儿子和儿媳双双在外面打工遇难,他们现在只好重新种田,包了人家不种的十亩田,头发都忙白了,老头还问我外面有没有需要他做的活。
老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我往往心里觉得很内疚,后来就忙忘掉了。只是在打电话的时候才想起自己的不是。我在电话里经常劝我母亲,不要舍不得钱,要舍得买东西吃。不要老是一天三顿粥。
由于俗事,我每次都像点火一样回家。为了减轻我的愧疚,我会从超市里买了一大堆东西带回去,母亲会骂我,我又不吃的,你真的发了广东了。你什么时候把房子买下来再这样做。
我以为母亲责怪完我之后就会吃的,后来我又回家,她真的没有吃,她说,我吃不惯。其他的老太太也过来看我,七嘴八舌的,她们的意思也是不要把钱被人“洋盘”(意思是被人骗了)。她们说得非常肯定,弄得我的母亲也以为我被骗了。母亲很相信她的老伙伴。
母亲的伴中还有过去和母亲有过隔阂不说话的人,比如我家前面的稻香大娘,母亲曾为她独生儿子砌房子而吵过架,原因是前面房子砌得太高,挡了我家的阳光了。去年我回家时我母亲说“稻香还争呢,一个儿子还和她分家呢。”分家后的稻香大娘老俩口住到了过去知青住过的草棚里。现在他们又住回来了,原因是一样的,儿子出去打工了,老俩口现在住四间大瓦房,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有得住了,反而觉得太旷了。
母亲和那些伴在一起,在老家活动的范围变得很大了,使得我每次回来总找不到她。母亲的伴中并没有打麻将的、玩纸牌的和吃素念经的。母亲不会打麻将,也不会玩纸牌,同样她也记不住那些难记的经文(念经的二姑曾经叫她就跟在里面哼哼也行,可母亲不同意)。母亲的爱好就两个,一个是“拉呱呱”,一个是去看人家办丧事。
老家的丧事是很费财费时的,送葬,“六七”,以及“化牌位”,大的一共三次,每次都要花上万元的。和尚要请。丧乐队要请。哭丧队要请。现在吃饭也改革了,过去只吃一顿荤,其余是素。而现在只一顿荤已经没有人来吃了,必须每顿都有荤,三顿都是酒。热闹。还气派。
母亲和她的伴喜欢看,看完后还评价,谁家是请了“七大师”坐台,还是“九大师”坐台。谁家还请了“十一大师”呢。有派头。谁家的花圈那么多,女儿“浇花水”都浇不过来了。谁家还请了丧乐队。哭丧队。有时候我听到她们津津有味地谈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总不可能对母亲许诺什么吧。
母亲说,我宁可不要什么哭丧队,我也不希望兄弟们将来为了钱不和。我以为母亲说过一次就罢了,可是母亲在一次腊月里我回家时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她心里已经把这个问题想了好多遍了,不然她不会把这个问题反复地强调。
有一次回家,母亲却不在村庄。村支书还帮我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我等了母亲足有二个小时,门口的人基本上都被我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我母亲的踪迹。最后只好动用了老家的大喇叭,那是为了喊人接公用电话时用的,支书在大喇叭里喊,“庞余亮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快回家,你家庞余亮回来了。”
半个小时后,母亲出现了,一脸的歉笑,她还责怪我,你怎么今天有空回来了?母亲是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去看人家“信耶稣”的人家怎么做后事的,一脸的兴奋,“不用钱”,“人家自带干粮来唱歌”,“不烧纸”,“也不念经”,“还不要丧乐队”,“省钱”。
她们是真正的羡慕,这几年,村里信耶稣的人多了起来,“作光作盐,服务社会”,村里已经有人家在贴这种带有十字的画了。难怪找不着她们。
我一直担心着母亲的身体,我叫她定时吃药。但我母亲的身体还是又一次垮了下去,心脏又出了问题。我回家的时候,她又怪罪于我死去的父亲,她说,不是那个老东西总是拿别的女人气我,我也不会得心脏病。
我在老家呆了几天,母亲和我谈了很多,她后来也不骂我父亲了,而是开始怀念我父亲了。我父亲的聪明。我父亲的勇敢。我父亲的能干。
老家清理坟地,需要为父亲移坟,我们弟兄三个一起回家,母亲照例没有去父亲的坟地,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我们还在父亲的坟前立了一块碑。母亲其他的话没有问,只是问了我,有没有她的名字?我说,当然有。她又问,是什么颜色?我说,当然是红色的了。母亲不说话了。
母亲在面对死亡的事情上很乐观,在父亲死的那一年,母亲就自己买布料,找一群会做老式盘扣衣服的老太太裁剪,然后她就自己给自己做“寝”。“寝”的意思是为母亲去世的时候穿的衣服。我不明白为什么叫“寝”?母亲说,就是“老衣”。当时妻子还有意见,不吉利。但是母亲说,过去还有老人置“老材”在家呢。
母亲一针一针地把“寝”缝好,自己试穿了一下,她说,只有活着穿了一下才能算自己的。母亲还吩咐我说,她“老”了之后火化之前一定要给她带上一瓶麻油。主要是用于治疗火化时被“大炉”烧烫的伤口。
母亲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方法的?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相信了,并说给我们做儿女的听了。
夏天到了,老家的老人最重要的事就是晒“寝”,晒他们百年之后的“寝”。死亡对于他们就是一场睡眠吗?或者他们这样做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子女吗?老家的老人们把针脚很好的“寝”晒在门板搭成的晒台上,她们不再“拉呱呱”了,眯着眼睛看着门外,由于剩下了门框,阳光就大把大把的涌到她们的眼睛中了。我说,疼。有时候疼得要命。他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好像很有意味。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是说我不像,我脸色不像,我这样做是捣蛋。医生最后下了结论,你的胆囊是有问题,胆囊有点发炎,吃点消炎药吧。然后他就哗哗地给我开了一大堆消炎药。还说,只能算作“疑似胆结石”了。你如果再疼的话,就要输液。但我还是疼,就像那些被不断砍伐的榆树的疼。
现在老家最多的植物榆树早已被意杨代替,虽然意杨很值钱,可我还是喜欢榆树。记得有一次,母亲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奖励我一只鸡蛋,我坐在我家门口的大榆树下慢慢地剥着吃。榆树在风中摇来摇去。榆钱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母亲说,过生日钱打头,看样子,你将来是要发财的。
可到了今天,我没有发财,更没有达到母亲开玩笑所说的“发了广东”。但每当想到老家的榆树,就总是觉得母亲还在。可母亲的确不在了,老家的那些榆树也不在了,母亲也过世12年了,到了我的梦境中,母亲的发式总是那没有鬏的凌乱的样子,来不及询问母亲,就疼醒过来……我们这些不孝子啊。
大哥和二哥现在都像父亲母亲一样有了高血压了。大哥告诉我要注意,这是遗传。我知道遗传的厉害。可我总是觉得我遗传了母亲的胆结石。右上腹有隐疼。
但医院出来的体检结果很快,医生说我没有胆结石,我并不相信。再后来,我不放心,又找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找了一个熟人,医生看了我的B超报告,又摸了摸我的右上腹,很惊讶地看着我,问我,疼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