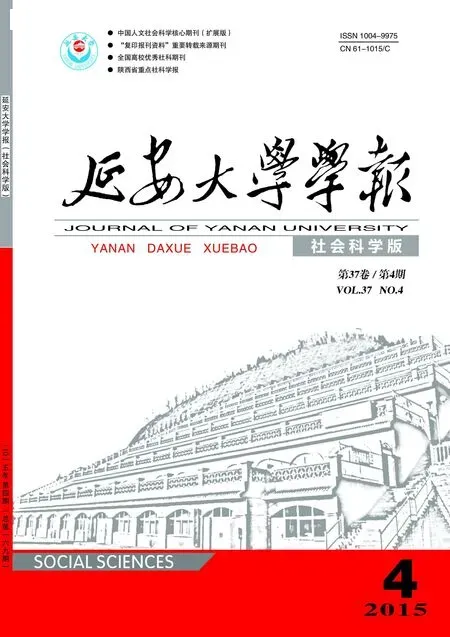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个人化书写
——再读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
2015-12-08张文诺
张文诺
(商洛学院文传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个人化书写
——再读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
张文诺
(商洛学院文传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以个人化记忆的方式叙述了天堂县“官逼民反”的蒜薹事件,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另一种现实。这是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的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现状的个人化书写,它颠覆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符号化记忆。莫言的个人化书写可以让一些个人记忆重新浮出水面,揭开被集体记忆所压抑的部分记忆。
个人化书写;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天堂蒜薹之歌》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率先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解放了中国农村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几年之后,农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做了近距离的跟踪与表现,通过中国农民与农村的巨大变化来演绎社会、历史的变迁发展,如高晓声的《陈奂生包产》、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这些小说主要关注农村的现实生存层面与物质需求,揭示了农民只有获得经济的自主权才能得到真正解放的主题。有的小说也表现了作家对于农民命运的深入思考,揭示了农民的国民劣根性,从整体上说,这些小说大都格调明朗乐观,对农村的光明前景充满了期待。这些小说的另一目的是通过农民和农村的变化佐证中国新时期政治的清明,为改革开放的深化鼓与呼,它们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农村未来的设计,建构了我们对80年代中国农村与农民的集体记忆。
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以个人化的记忆的方式叙述了天堂县“官逼民反”的蒜薹事件,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另一种现实,这种个人化记忆有助于我们发掘集体记忆中被遮蔽、压抑的内容。莫言的创作很多出自对个人经验的发掘,这种经验深植于他的记忆深处,他的叙事直接而自信,真实而饱满。
一
莫言说他这部小说的创作由一则新闻报道引起。其实,这则新闻报道只不过是触动作者灵感的偶然机缘而已,这部小说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农村的个人记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秘密地去那个发生了蒜薹事件的县里调查采访。我所依据的素材就是一种粗略地报道了蒜薹事件过程的地方报纸。但当我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适合扮演的角色。……书中那位惨死于乡镇小官僚车轮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为原型的。”[1]显然,这则报道激活了莫言对农村的个人记忆,与其说莫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蒜薹事件,还不如说是莫言写的是他个人的记忆,郁积日久的激情显示了莫言对农村的关注,也说明了这种记忆对莫言来讲也是一种创伤性记忆。“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2]蒜薹事件对于社会来讲是个小事件,但对于牵涉其中的农民来说,却是一个改变了人生走向的大事件,足以给个人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莫言不一定经历过天堂县蒜薹事件,但他经历过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成了莫言的创伤性记忆,这种创伤性记忆决定了《天堂蒜薹之歌》的独特书写方式。
读完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我感觉这部小说描述的农村现实、农村事件、农民形象都很熟悉、真实。我在故乡山东农村亲眼目睹过农村群体性事件,也深深了解农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莫言没有回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连年丰收的景象,但莫言还是通过人物的故事来呈现农民的血泪、苦难与死亡,从独特的视角表现农民的无奈与无助。
天堂县政府鼓励农民种植蒜薹,天堂县农民蒜薹丰收,但蒜薹没有销路卖不出去,在农民家里散发出阵阵恶臭。小说通过四婶和高羊的回忆写出了天堂县农民卖蒜薹的艰难与心酸,天堂县农民把一年的希望寄托在蒜薹之上,希望卖掉蒜薹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尽早卖蒜薹,全县农民不得不一次次起早摸黑去县城。当高羊披星戴月赶着驴车走到半道时,四叔早已经走在他的前面了,在他们身后,蜿蜒着一条由马车、驴车、牛车、人拉地排子车、手推车、拖拉机、汽车组成的车马长蛇,四面八方的蒜薹涌向县城。向东的路向西的路都是一片黑压压的车,半上午的时候,他们距离冷库还有三里远的距离。蒜薹还没有卖,就要交纳交通管理费、工商交易税、环境保护费、卫生费等各种名目的费以及罚款。到了傍晚,他们挨到了蒜薹收购点,四叔和高羊很是欣慰也有点局促不安,果然,他们心里的不安成了现实,冷库已满不再收了,他们只好往回走。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卖蒜薹农民的心理状态,他们排在长队后面时非常担心,当轮到他们时,他们倍感欣慰却又局促不安,担心夜长梦多而卖不上蒜薹白跑一趟,这种坐卧不宁、焦虑、紧张的心理状态真实地揭示了处于底层的农民们的困窘处境。当四叔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赶时,被王安书记的小轿车撞死。四婶去乡政府要求赔偿竟被工作人员的几句话应付过去。金菊因为反抗强加于她的换亲竟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农民在政府的号召下大量种植大蒜,导致蒜薹滞销、烂掉,还不能卖给外县的商贩,农民开始到县政府门前讨要说法,由于政府人员处置不当,愤怒的农民冲进县政府办公室,砸坏了办公设备,闹事的农民高马、高羊、四婶、郑老汉等被法院判以重刑。在监狱里,犯人受到了残酷的虐待,狱警凶神恶煞、草菅人命,不管犯人死活。
这部小说真实地呈现了80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令人触目惊心。莫言非常熟悉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非常熟悉农民的内心,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立场上替农民发出痛苦的呐喊。
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活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连年丰收,短短几年就基本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可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活力的挖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富裕问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农村生产必须要上一个新台阶,农村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非常困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在农村,基层政府开始引导农民致富,由于当时没有多少企业来容纳农民就业。农村基层政府开始发展大棚种蔬菜、种棉花、栽果树等经济作物,然而,由于他们没有考察市场便盲目推行,导致了“谷贱伤农”的后果,再加上某些干部的腐败以及工作作风问题,于是发生了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应该说,基层政府引导农民致富无可厚非,很多地方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关键是他们没有预见到实施后的问题,也没有做好后续的服务,惠农事件反而成了伤农事件。
1980年末,“三农”问题开始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由于各种费税繁多,农民负担非常沉重,农民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寄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3]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艺术地反映了1980年代农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莫言的个人化记忆揭示了水平面之下农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消解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超越了记忆研究的个体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路径,认为在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个体的记忆必然置身于这个框架来理解,特定的记忆能否被唤起和以什么方式被唤起、被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4]换言之,个体记忆总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建构,官方文件、报纸、电视、广播、主流文艺作品等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当一个大事件发生以后,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学历背景、家庭出身、世界观、价值观、政治倾向做出反应,形成个体记忆,官方也会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文艺形式对事件进行分析、评价、判断以清正视听,形成“正确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5]这里的集体是指在社会上处于强势的力量,他们掌握着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对社会记忆进行重构、再构,形成有利于自己合法性的集体记忆。
比如说,笔者在山东家乡也亲眼目睹过类似“蒜薹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在当时也颇为农民的痛苦而感到忧心忡忡,可是,当看到了电视、报纸等官方报导、分析、判断之后,就认为那不过是生活中的细流而已,那些事件并不值得关注。农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慢慢在自己头脑中模糊起来逐渐遗忘,而政府工作人员的辛苦、无奈与可怜在自己的头脑中清晰起来并形成记忆。“社会记忆也为个体记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以相对强势的记忆影响个体记忆的整个过程。”[6]73记忆不仅是一种内容的记忆、内容的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自然就意味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个体记忆也不总是处于被影响、被建构的地位,反过来它也对集体记忆产生影响,或支撑、或建构、或消解、或重构,尤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个体记忆更是如此。“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7]个体记忆可以唤醒、重构个人记忆并形成对集体记忆的反抗,可以揭示被集体记忆压抑、掩盖的私人化记忆。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唤醒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个人记忆,重构了8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记忆,丰富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记忆。
二
《天堂蒜薹之歌》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天堂县农民蒜薹丰收、卖蒜薹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是高马、金菊反抗包办换亲的故事。无论是农民的经济生活还是感情生活,都处于极端困窘的状态,从天堂县农民的遭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巨大作用。我在这里不分析这篇小说是怎样叙述这两起事件的,而是分析权力在这两起事件中的权力机制以及农民对权力的反抗。
根据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权力不仅仅是压迫、控制的机制,也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泛权力论,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表现为一种压迫、控制关系,在农村,我们就更清晰地看到权力在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农民卖蒜薹而不得其正常权益得不到保护,高马、金菊反抗强加的换亲婚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农民一是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二是受到习俗文化权力的规约。在旧中国农村,乡绅以及一些合法的民间组织在农村占有重要地位,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管理主要通过它们来贯彻实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农村,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起来参加革命,为了政令畅通,取消了乡绅、民间组织、宗法权力在农村的合法性,弱化了农民们的迷信鬼神思想,在农村建立了村级政权,确立了自己在农村的唯一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8]从根据地政权之后,在中国农村,政治权力占有绝对的地位,基层政权的干部掌握着主导话语权。他们处处以国家政权的代表自居,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国家政权的管理者,你如果不听从他的话,就是反对国家政权,任何人如果被扣上这顶帽子,就将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坑,即使他的号令并不正确。
在旧社会,掌握着农村话语权的是士绅,他们有较丰厚的财富,知书达礼,在村中能处理村务,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地位是自然形成的。
在新政权体制下,基层干部是上级任命的,即使他们没有文化、没有财富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忠于新政权,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要勇敢、要彻底。村主任把村民当作自己的下属,因而,村主任高金角对高羊焦灼地吼叫,而高羊一听到是村主任的声音,匆忙放下碗,大声应着,往院里走。高羊的不敢怠慢,显示了村主任无上的权威。方四叔被乡党委书记王安撞死之后,方家全家去乡政府讨要说法,乡政府无人理会。一个小小的杨助理几句话就把方四婶说得无言以对,心服口服。
杨助理最后这样说:“是你爹死了,不是我爹死了,告不告是你们的自由。不过,这事要轮到我头上,我就不告。人反正死了,一切都要考虑活着的人。说穿了,就是钱!怎么多弄点钱,就怎么弄。你们去告了状,说到最狠处,把司机判刑,你们又有什么好?公家可是依法办事,顶多给你们几百元殡葬费。王书记在县里关系四通八达,就算把司机判了刑,过不了几个月就会出来,照开他的车。农民得罪了王书记,还落一个混账人家的恶名,老大和老二就甭说媳妇啦。……王书记也说了,只要你们答应私了这件事,他保证对得起你们。你们掂量掂量,该怎么办自己拿主意。”这些话滴水不漏、巧舌如簧。表面看来,杨助理处处为亲戚考虑、有理有据,实则是糊弄欺骗、走一步算一步。他利用了农民不懂法、怕麻烦、怕官的心理,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说服了方家一家人。
农民缺乏必要的知识是农民在与基层官员的较量中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此,福柯精辟地指出:“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9]正是因为方家兄弟的愚昧、无知才显示了杨助理那一席话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在农村,政治权力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农民还受到习俗文化权力的规约,并且这种权力已经内化为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当事人不易觉察。宗教信仰、宗法观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构成了农村的习俗文化权力,敬天畏地、孝敬父母、尊敬祖先、讲究义气、传宗接代等思想观念是习俗文化权力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家庭是父子轴线型的,女子只是服从,农民也不例外。传统伦理要求女子‘三从’(在家从父兄,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农家子女也难逃此厄。一般父系家庭结构,在性方面是男性至上的,为维护男性的权益和血统的纯正,对女子的要求比较严格,在中国士大夫则衍化出一整套单方面约束女子的‘男女之大防’的规矩和程式。”[10]
习俗文化权力对农民的控制最能体现于它对农民爱情婚姻观念上,方四叔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来维护方家的尊严,就让金菊换亲嫁给四十多岁的刘胜利为妻,完全不顾及自己女儿金菊的感受,漠视自己女儿的存在。“换亲、转亲是在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陈腐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以牺牲女儿为代价,来成全儿子的行为。”[11]37高马与金菊的恋爱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同情与支持,在别人看来,金菊嫁给刘胜利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合乎礼仪的,作为女儿必须遵守父命,他们根本不考虑这桩婚姻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高马和金菊恋爱是胡来,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应该严惩。高马去乡政府告状,被驳回,二人只好私奔,但又被抓了回来。“逾矩偷情是一回事,私奔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往往闹得家破人亡。”[11]27金菊目睹父亲惨死,丈夫被抓,心中绝望,上吊自杀。
在莫言的笔下,乡村的爱情故事没有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浪漫与美丽,高马和金菊似乎不是一见钟情,也非两情相悦,只是一种欲望的推动。乡村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优美,没有卿卿我我的甜蜜,也没有山盟海誓的温柔,高马与金菊的约会是在漆黑的夜里,那里坎坷不平,他们之间没有甜蜜却有一种紧张感。与政治权力不同的是,你对习俗文化权力知识知道的越多,你越容易受其控制、操纵,高马敢于反抗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无端刁难,面对方家一家人对自己的暴打没有丝毫反抗。习俗文化权力被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所包裹,以一种亲情的形式出现,让人处于无物之阵,找不到反抗的对象。
自从根据地政权之后,政治权力便确立了在农村的独尊地位,驱逐了习俗文化权力并把其置于边缘地位。习俗文化权力也逐渐适应这种地位,并不和政治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矛盾,而是与政治权力进行合谋或者同构,以便加强自己在农村的存在,当然,政治权力也愿意对习俗文化权力进行解构、重构、再构,更好地巩固自己在农村的地位。
孟悦在分析《李双双小传》中说:“如果说喜旺的大男子主义显然是父权社会男性‘性别意识’的产物,那么李双双正是秉凭‘党法’对他进行惩戒和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李双双夫妻之间的高下之争预示着一场‘父法’——‘党法’之争,‘父法’之所以妨碍了‘党法’,与其说是因为欺压了女性,毋宁是因为‘大男子主义’这样一种性别专权势必分散党的全面控制。”[12]小说更为惊心动魄的一笔是叙述金菊死后、高马入狱后的情形,方家兄弟利用自己对金菊尸体的处置权,在杨助理的哄骗下私自做主给金菊与刘家做了阴亲,这真是沉重的一笔。
习俗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谋不仅能控制人的生前,还能操纵人的身后事,两种权力的合谋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
三
从总体上看,莫言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进行讲述故事,但其间穿插着人物的回忆、闪回、梦境、无意识、心理活动等,这些生活片段与叙述人的讲述时空颠倒地构成整个故事。这些生活片段是以每个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形成了与叙述人不同的叙述视角与叙述语气,因而,在故事进行中,存在多种语调、多种视角、多种话语嬉戏的多声部态势,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并置、杂陈、嬉戏,使得小说的意蕴主题非常复杂、含混。
在小说中,官方话语主要有各级干部的讲话、训斥,报纸的报道、报纸的评论等,这类话语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盛气凌人、不容置疑、生硬威严,令人不寒而栗。即使是一个平实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村支书的话都让农民感到非常严厉,如芒在背。官方话语处于独白的霸气地位,它说话时,不容许别人插话,这种位置赋予话语主体向听众一种单向表述的力量。“独白是霸权话语的一个同时具有极端意义和宽泛意义的表现,霸权独白是政治权力为保卫其权力和秩序而必然使用的强势的话语述说形式,独白者常常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6]136
当官方话语言说时,周围一片安静、鸦雀无声。高羊与村支书的对话不是一种平等、亲切的交流,而是充满了斥责、等级、严厉的意味,村支书是声色俱厉,高羊是毕恭毕敬;村支书是发号施令,高羊是点头哈腰。在法官审理高羊时,双方的对话非常简单、直接。
“你叫高羊吗?”
“是。”
“年龄?”
“四十。”
“职业?”
“农民。”
“家庭出身?”
“这……原来,俺爹娘是地主,后来,政府给四类分子摘帽子时,他们都早死了,俺也不知道俺是不是地主分子……”
这里的“你叫高羊吗?”显然审讯人员知道他是高羊,这样问不是询问,而是明知故问,是再次确定双方的身份,让被审问者明白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话语制造了一种威严、公事公办的气氛,让被审问者感到自己有罪在身、低人一等。
《天堂蒜薹之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章的开头都有一段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歌谣后面还有一些介绍歌谣背景的简短文字。这些文字与本章内容并无直接联系,如果把这些文字独立出来,也相对完整,也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说唱故事。这些文字既叙述了瞎子张扣的故事,也是对小说正文的一个补充。瞎子张扣既是蒜薹事件的亲历者,也是蒜薹事件的叙述者,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张扣用歌谣为武器,或者揭露基层政权的横征暴敛,或者鼓励天堂县农民起来抗争,或者批判农民胆小自私。当读者看到他的故事时,张扣已经死去,他再不能叙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他通过他所创作的歌谣实现了缺席的在场。叙述者也在讲述他所听说的张扣的故事,所叙述的张扣的故事与歌谣中的故事形成互文间性,瞎子张扣的歌谣的存在增加了文本本身的多重、含混与纠结。
瞎子张扣无儿无女,靠吹拉弹唱为生,他既给农民说传统戏文唱段,也把现实生活编成戏文演唱,他的歌谣是真正的民间话语,感情真挚、自由自在,形式活泼,“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们的情绪世界,”“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3]所以瞎子张扣的歌谣深受百姓的喜爱,他本人深受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民间话语以自己的自由自在、粗俗、野性与官方话语的严肃、高雅、理性并置,两种话语互相冲突、排斥、消解,对官方话语形成了解构与颠覆。小说最后以《群众日报》对蒜薹事件的报道及一篇社论作结,作者表面上是让官方报道做了结论性的陈述,官方话语表面上处于强势地位。从报道及社论内容看,上级主管部门对蒜薹事件做了客观、公正、公开地处理,处理结果也比较公平。主要负责人被依法处理,对少数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了严惩,为老百姓伸张了正义,民愤得以平息,读者也松了一口气。不料,作者又让张扣的徒弟讲了一个小道消息,说被免职的主要负责人纪南城、仲为民到异地做官,并说小道消息总是准确的。作者把这则小道消息置于小说最后,这则小道消息与小说主体内容形成异质的存在,它和“正文纠缠不休,它们常常以调侃和顽皮的方式挤弄和瓦解正文的严肃性”。[14]这则谣言式的漫谈彻底暴露了报道、社论的虚假、欺骗,给以极大的嘲讽,它可以瓦解人们的社会共识,消弱官方文件的影响力,因为“它是一种反权力”[15]。即使这种漫谈不是真实的,它都可以动摇人们对官方文件的信心,因为人们有时更愿意相信小道消息的准确性。
小道消息总是从一些了解内幕的人士传出来的,只不过它在时间上较早,更直接、更真实而已,这两种话语的并置嬉戏深刻地揭示了基层政权对农民的压迫、欺骗的现状。“这种混响的‘声音’,杂芜的文体,开放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狂欢化的风格,既是感觉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制度化的话语秩序。”[16]
在小说中,知识分子有叙述者、高马以及青年军官等,叙述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议论表达的自己的观点,但我们还是根据他的叙述语气与视角看出他对农民的命运深深同情,同时又对农民的弱点给以严厉的批判。
高马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他比一般农民的见识多。他身材魁梧,敢爱敢恨,敢于伸张正义,敢于控诉基层政权工作人员的暴行。青年军官眼光敏锐、阅历丰富、了解下情、同情农民的疾苦,他在法庭上敢于慷慨陈词,为农民辩护,把法官驳斥得张口结舌。但是,知识分子不像民间艺人张扣那样勇敢无畏而义无反顾,他们知识丰富,洞察力强,但面对强权时显得信心不足。当青年军官的辩护非常激烈时,审判员让书记员一字不漏地记下他说的话时,他显然也意识到刚才的发言有点过于激烈,“青年军官脸色苍白,脸上浮现出可怜相来。”他发完言后,“疲疲沓沓地坐在辩护席上。”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民族精英、启蒙者、领导者的角色出现,但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让他们失去抗衡强权的正当性与自信,让他们难以在权势面前讲真话,在实际的斗争中,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软弱性。
小说的叙述线索较为分明,但又不是按照故事顺序来安排情节,而是以一种明确的非线性叙事。既有叙述者的第三人称叙事,也有小说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既有顺序,也有倒叙,还有人物的回忆以及意识流动。小说的第一、三、五、七、九章叙述高羊被抓住之后在看守所的故事,小说第二、四、六、八、十倒叙高马与金菊的爱情悲剧。从第十一章开始叙述众犯人在看守所的故事,中间又通过人物的回忆、梦境、无意识叙述了四叔卖蒜薹、方家兄弟分家、高羊埋葬母亲、愤怒的农民打砸县长办公室等故事。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不可预见的,又必须通过其他人物的叙述或回忆来补充完整,这样的叙述技巧增加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既让人感到支离破碎、山重水复,又让人感到余音袅袅、柳暗花明。
小说的结构复杂、模糊,各个细枝末节相互关联,形成了交替、纠缠、多头、变幻、立体、多视角的态势,众声喧哗,多音共鸣。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结构很混沌,表面上看是双线索结构,却又镶嵌着人物的回忆、无意识、闪回,既有顺序,又有倒叙,时空倒置。“情节被切割,并被颠倒顺序;不同的看似无关的材料,互为镶嵌,被随意地放置在小说的空间之中;人物形象是飘忽不定的并且同样是不完整的”。[17]这种杂乱无章、犬牙交错的叙述方式恰恰能展示出复杂、混沌的生活空间,能反映出中国农村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
莫言说:“文学家应该积极地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用文学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学家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和立场上,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并发出自己的声音。”[18]
20世纪80年代农村、农民的历程、细节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从有史官的时候开始,历史就在不断筛选它应当记载的东西,记载和忽略、记忆和遗忘始终相伴,因为历史时间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和曾经存在的人物太多,历史学家没有办法一一登录在案,就连给皇帝写‘起居注’的官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笔笔入账。”[19]80历史叙述者总是秉承一定历史理念,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叙述历史,原来纷繁复杂的生活事件被条理化、清晰化,更容易被我们记住,可是也失去了丰富的细节,这种记忆是以我们对某些事件的遗忘为代价的。
时间也容易让我们变得更理性,逐渐失去热情。比如像小说中的蒜薹事件,如果我们从历史书阅读,我们不会再有当年亲历者那样的刻骨铭心之痛,我们对农民的遭遇也变得很冷漠,对农民所遭受的欺骗、压迫也没有当年亲历者那样的痛心疾首,对农民的爱情悲剧可能仅仅是皱眉而已,或许我们对基层官员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时间的流逝把丰富的历史和刻骨的心情渐渐过滤成了书本和文字,使历史与读者之间仿佛加上一层模糊的玻璃,使读者与历史有了一种‘疏离感’,人们不再直接感受到历史,却仿佛是隔岸观火,把历史变成了一出出上演的戏文和小说。”[19]88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是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的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现状的个人化书写,它颠覆了我们对与80年代中国农村的符号化记忆。
中国农村远远不是沈从文等乡土小说家所塑造的化外世界:没有见利忘义之徒,不见尔虞我诈之辈。农民也并非是安贫乐道、好善乐施的一群,他们是普通人的一员,他们有自己的优点,也有不可原谅的弱点。他们勤劳、善良、淳朴、老实,但他们对异端却极端仇视,他们自私、无情、目光短浅、贪图小便宜。方家兄弟很勤劳、坚韧,但对自己的父母与妹妹毫无情义。高羊虽然对基层官员的欺压不满,但他不想反抗,他是想借着别人的反抗得利。“读者从这部作品中获得一种明确的意识,可以理解中国农民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他们的爱、恨、善良、残忍、文雅和粗俗,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这一切。
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作农村题材的20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20]80年代的中国农民不像其它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想象的那样,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农村的一切问题,中国农村依然与苦难为伴,农民的生活依然痛苦。个人记忆总是受到集体记忆的建构,“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对记忆和传统进行支配的争斗,即操纵记忆的争斗,在社会记忆为口述记忆的社会里活在书面的集体记忆站在形成的社会里最容易被人所掌握。”[21]因而,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虚假性,莫言的个人化书写可以让一些个人记忆重新浮出水面,揭开被集体记忆所压抑的部分记忆,揭示一些被历史所掩盖和遮蔽的真实。
[1]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新版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30.
[2]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C]//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1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3]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J].山东农业,2000(10):4.
[4]陶东风.编者的话[C]//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
[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台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418.
[6]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7]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1.
[8]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07.
[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07:32.
[10]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6.
[11]王义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9.
[13]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7.
[14]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16.
[15]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74.
[16]张闳.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J].当代作家评论,1999(5):64.
[17]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5.
[18]莫言.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J].创作与评论,2012(6):53.
[1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0]杜迈克.论《天堂蒜薹之歌》[J].季进,王娟娟,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6):55.
[21]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1.
[责任编辑 王俊虎]
The Individual Writing on Chinese Country in 1980′s:Discussion ontheSongsofGarlicinHeavenCountry(《天堂蒜薹之歌》)
ZHANG Wen-nuo
(Literature College,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Shaanxi)
Mo Yan narrates the group event of garlic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memory in “thesongsofgarlicinHeavenCountry”,presenting another kind of reality on Chinese country in 1980′s.This is the individual writing on Chinese country and peasants in 1980's basing on individual memory and it overturns our symbol memory on Chinese country in 1980's.The individual writing makes the personal memory floating above the water and discloses the personal memory being depressed by collective memory.
the individual writing; Chinese country; 1980′s;thesongsofgarlicinHeavenCountry
I206.7
A
1004-9975(2015)04-0071-07
2015-03-23
张文诺(1976—),男,山东阳谷人,商洛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