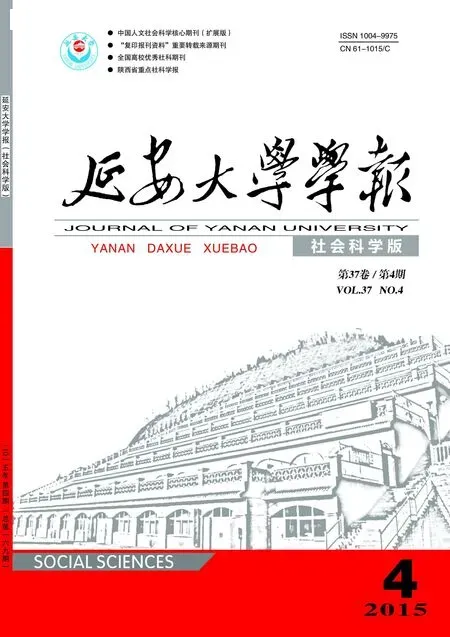论阎连科小说的乌托邦化叙事策略及其审美功能
2015-12-08徐美恒
徐美恒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191)
■现当代文学研究
论阎连科小说的乌托邦化叙事策略及其审美功能
徐美恒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191)
阎连科的不少小说,特别是“耙耧山”系列乡土小说,营造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奇幻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他的乌托邦化小说相一致的是乌托邦化叙事策略,是一种特别的创作方式,为小说的审美开拓了新的境界。乌托邦化审美策略更便于创造出超越现实与批判现实巧妙结合的文本,在空幻的传奇故事中营造出凄惨的理想主义氛围,通过对生活的荒诞化处理,更深刻地剖析人性,以达到救治人的精神之目的。
阎连科;乌托邦化小说;叙事策略;精神救治
“乌托邦”这个词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写的著作《乌托邦》,该书有多个版本,“初版于1516年出现在比利时的卢万城,当时莫尔的朋友伊拉斯莫斯居住在卢万。主要的出版监督人,除伊拉斯莫斯外还有彼得·贾尔斯”[1]157。“书中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都是杜撰。‘乌托邦’这个词本身就是据古希腊语虚造出来的,六个字母中有四个元音,读起来很响,指的却是‘无何有之乡’,不存在于客观世界”[1]3。由于该书有对理想社会的空想描写,莫尔因此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书里描写了他所想象的实行公有制的幸福社会,并把这种社会叫做“乌托邦”,意即“没有哪里”有的地方,“不存在的地方”[2]60。从此,“乌托邦”成了空幻、理想、不切实际的代名词。乌托邦本身的魅力使它长期以来成为思想界、哲学界、文学界关注的话题,不同的思考层面对乌托邦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乌托邦,既指莫尔刻画的理想社会,也指乌托邦思想,同时还指称乌托邦这种独特文类”[2]235。乌托邦作为一种独特文类,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乌托邦小说是指具有乌托邦思想、精神或境界的小说。
那么,什么是乌托邦思想,如何概括乌托邦精神,怎样判定一篇小说具备了乌托邦境界?有人说,“把这种超越当下可感的现存状态、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精神,称为‘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因而是人的根本精神”[3]。问题是,有永恒的、超验的、绝对的“真善美”价值理想吗?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既有人类普世的、千百年来相对稳定的价值理想,也有尖锐的价值冲突。所以,所谓的“真善美价值理想”应该是多元的,相应的乌托邦精神也应该是多元的,小说中的乌托邦境界自然也是多样化的。由此说来,乌托邦小说是人们按照各自的认识指定的。
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下,曾经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社会实践探索如果被指认为乌托邦,那么,支撑其实践的思想可以认为是乌托邦思想,由此衍化出的那种狂热、躁动的社会情绪,那种人的意志极度膨胀的思维方式和改造社会的追求,就是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是极具煽动性的,因为它要创造“从来没有的世界”,给人们一个空幻美丽的许诺,召唤人们以飞蛾赴火的勇气追求和体验那“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来自德行的实践以及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的“精神的快乐”[1]80。
阎连科的不少小说,特别是“耙耧山”系列乡土小说,营造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奇幻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可以把他的这类作品作为一个类型讨论,其类型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乌托邦化叙事策略”。也就是说,阎连科的小说虽然创造了乌托邦世界,但这只是一种叙事策略,他不是为了追求乌托邦精神而创造乌托邦,也不是为了赞美乌托邦而创造乌托邦,他的目的在于反讽,就是讽刺乌托邦。所以说是一种乌托邦化叙事策略,就是借乌托邦反乌托邦。可见,他的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反乌托邦小说。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创作方式,因此形成的乌托邦化叙事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
一、超越现实的审美策略与批判现实的巧妙结合
按照常理,小说若要批判现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揭示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通过人物的情感体验传达出批判的态度。阎连科的小说总体上是批判现实的,但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选择了一个更有深度的思考点,就是关注人性、思考生命意义、评价生活理想及其追求手段,而且,在思考的方式上选择了大胆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化手法。正是因为这种选择,使他的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时不得不超越现实,走向乌托邦化,从而在变形、极端化、漫画化的情境下展示人性的复杂性,揭示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人性本质。人性在庸常的情况下,善和恶、真与美都容易被掩藏起来。人往往是中性的,有千姿百态的外貌,但难见心理世界的深层波澜。阎连科为了突破这种状态或局限,在小说中逐渐地、越来越多地运用超凡想象,创造出超现实的乌托邦世界。比如《受活》中的“受活庄”,位于豫西“耙耧山脉”间的一条峡谷深沟,其发迹的历史源自传说中的明朝初年人口大迁徙,先由“一个哑巴、一个盲人、一个瘫子在这儿三人合户,把日子过得宛若天堂之后,四邻八村,乃至邻郡、邻县的残疾人便都拥了过来。瞎子、瘸子、聋子、缺胳膊短腿、断腿的残人们,在这儿都从老哑妇手里得到了田地、银两,又都过得自得其乐,成亲繁衍,成了村庄。虽其后代也多有遗传残疾,然却在哑妇的安排之下,家家人人,都适得其所”[4]。
阎连科作为一个十分看重乡土的作家,在描写乡村社会生活的小说里,不可能完全抹去对故乡山水的记忆,他的多部小说里反复出现“耙耧山脉”这个背景,以至形成“耙耧山系列”乡土小说。“耙耧山脉”是他故乡实有的山名,他也想借写小说宣扬自己热爱的故土。然而,故乡在他的眼里是有残疾的,这显然是一种理念先于生活的假设。也就是说,他认为耙耧山里的故乡是有残疾的,因此创造出了“受活庄”这样一个乌托邦世界。这个乌托邦世界除了有豫西“耙耧山脉”、豫东平原这样的真实的宏阔背景外,微观的世界就完全是子虚乌有了。也就是摆脱实有,创造虚无,营造一个乌托邦世界,让想象更自由,让批判更犀利,让艺术更空灵。毫无疑问,“受活庄”是不存在的,找遍天下,也不会找到这样一个大山深处的残疾人的天堂。然而,当阎连科讲述了这些残缺者的生活和追求,特别是把他们跟“圆全人”形成对照(《受活》的后半部基本是在描写残缺人如何被种种圆全人利用、捉弄、压榨、控制与盘剥及他们的摆脱努力),这就促使人禁不住要思考,人的心智健康与身体残缺究竟哪个更重要?种种社会体制建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显然,阎连科是在借用残缺者的荒诞的乌托邦世界反抗和嘲讽所谓的健全人,包括健全人的乌托邦理想。如果阎连科不用这种所谓的“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5]298,拘泥于实有的生活,很难达到深刻揭示人性之善恶美丑的震撼人心境界。
正是这种夸大和变形的荒诞策略,使人们看清了一些生活现实的本质,使柳县长的种种宏大理想和行径变得丑陋不堪。诸如“列宁纪念堂”这样的宏大工程,表面上是要造福民众,通过发展旅游业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个宏伟蓝图从被谋划到运作实施,其实背后隐藏着柳县长不可告人的私欲。甚至可以说,美好的乌托邦景象只是柳县长欺世的幌子,当那些残疾人发现“列宁纪念堂”实际上也是柳县长安葬自己的秘宫时,故事的反乌托邦价值也就确立了。还有柳县长的“敬仰堂”的秘密,以及柳县长的举着铁锹“指挥”“云开日出”的描写,让极度膨胀的私欲与胆大妄为、疯狂的个人意志膨胀与不知天高地厚这样的人性本质暴露无遗。
阎连科的小说较早流露出这种超越现实的审美策略的作品是发表于1992年的中篇小说《夏日落》。这篇看似描写比较严肃的军营生活的作品,其实已经流露出乌托邦化的追求。
自杀新兵夏日落通过信件关于云幻之景“河”的描写,已经流露出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倾向。这个彼岸世界不是宗教的,而是个人心理幻觉,它召唤着一个十七岁的年轻军人盗枪自杀。云幻之景“河”是纯粹之美,它反衬了赵连长和高指导员的现实生活的令人厌倦之态。这种有点过分隐晦的批判现实性其实是十分沉重的。一条美艳的空幻河,成了一个年轻人抗拒龌龊现实的乌托邦归宿。那空幻的河,与其说它是乌托邦,不如说它象征了美好的人生理想,代表了纯净的灵魂世界,它让一个沉醉其中的年轻生命勇敢前往,于是,死的悲剧就成了对生的悲剧的最严峻的反抗和最沉重的批判。
阎连科的小说通过乌托邦化处理,看似有意地、巧妙地回避了现实,实际上却能够把现实生活中深重的隐痛揭示出来。比如《丁庄梦》结尾的描写:“爷累了。累极了,进了屋,……倒在床上爷就不想再起来。睡着了。睡着后去了丁庄周围的柳庄、黄水、李二庄、古河渡、二河渡、三河口和上杨庄、明王庄,跑了几百里的路,看了上百个村庄和镇子,发现平原上百里千里的村庄和集镇,都和丁庄一模样,没有人,没有畜,可各庄各村的房屋都还在,树却都没了。都被做棺材砍得净尽了。……平原上光光秃秃了,人畜绝尽了。好在那一夜,又下了一场雨,在那倾盆大雨中,爷看见平原上一马平川的泥地里,有个女人手持柳枝去泥里沾一沾,举起柳枝甩一甩。她一甩,地上就有了好多泥人儿。又一沾,再一甩,地上又有成百上千的泥人儿。不停地沾,不停地甩,一片一片的泥人儿蹦蹦和跳跳,多得和雨地里的水泡一模样,爷就看见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平原了。新的蹦蹦跳跳的世界了。”[6]284-285这个梦幻式的结局描写,显然是一种大悲大痛的嘲讽,是一种沉痛至极的批判,它借用中国远古的女娲造人的乌托邦化的神话传说,传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深重忧患,对“丁庄”乡村人命运的极度恐慌,也是对人类命运的极度恐慌。难道地球上的物种不是天天都在减少吗?难道繁华都市的日渐膨胀和贫困乡村的不断荒芜不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吗?如果人类不懂得自珍自爱,难道他们在经历了万劫不复后,真的还会有一个女娲轻而易举地拿一根柳枝沾上泥水甩一甩,他们就又满世界滋生出来了吗?如此宏大的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如果简单地拘泥于现实生活的表面,放弃深厚文化根基蕴含的丰富想象,是很难创造出大气磅礴的审美意蕴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深深地感动人,从而实现批判生活、警示社会的目的。应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越来越感到,真正阻碍文学成就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而是过于粗壮,过于根深叶茂,粗壮到不可动摇,根深叶茂到早已成为参天大树的现实主义。”[5]297他甚至认为:“我们几十年所倡导的那种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元凶。”[5]297主张“把它当做写作的最大墓地”[5]299。
对于阎连科来说,他的小说超越现实只是一种审美策略,批判现实、省察人性才是真正的归宿。这种奇特的文本令人想到鲁迅的《故事新编》,幽默与嘲讽、荒诞与寓理、鞭挞与警策、乌托邦与现实,融合混杂,古今贯通,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大气磅礴。
二、空幻的传奇性与凄惨的理想主义氛围营造
阎连科小说的乌托邦化策略给故事带来空灵之气和传奇色彩,特别是当乌托邦文本作为一种小说境界,承载起反乌托邦的批判功能时,传奇的表象之下必然流淌着理想主义精神,也就是一种乌托邦精神。阎连科更善于让这种以所谓超越主义得以表现的理想主义具有凄惨的悲剧美,以震撼人心。就《丁庄梦》、《受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几部长篇小说来看,其中的传奇因素各不相同。比如《丁庄梦》,整部小说并无特别的传奇人物,但故事却是超乎寻常的、具有传奇性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很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叫丁庄的乡村,村民们为了过上好日子,也就是住进“政府规设的”“盖成两层楼”的贴瓷砖的砖瓦房里,过上“各家每天到了烧饭时,就到村委会里去领菜,想要菠菜去菠菜架上取菠菜,想要韭菜就去韭菜架上取韭菜。说想吃猪肉就去领猪肉,想要吃鱼就去鱼塘捞条鱼”[6]28的“大同日子”,为了这个富裕目标,丁庄人效仿上杨庄人开始卖血,以至于卖血疯狂到私采滥卖,终于在“十年后,……卖过血的人他就都染着热病啦。死个人就像死条狗,就像死了一只蚂蚁了。”于是,“丁庄”开始肆虐各种疾病,主要是“艾滋病”,开始大范围死人。在死亡的威胁下,演绎了种种传奇人生和传奇景象:有同病相怜的爱情,有奇幻的花海和黄金梦,有丧心病狂的利益追逐,有鬼迷心窍的权力争斗,有荒诞的阴亲攀附和鬼使神差的杀子悲剧,终至丁庄的四野荒芜死寂。这是一个悲愤的寓言,丁庄当然是个乌托邦世界,是个空幻离奇的世界,但它象征了现实生活中种种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和饮鸩止渴的生存方式,因此,丁庄的毁灭就成了一个警示。
如果只看到这些人生的哀伤与悲痛,那么,“丁庄”传奇就只是一个嘲讽现实和批判生活的文本,与凄惨的理想主义无关。事实上,“丁庄”还有“梦”,这个梦就是人们对富裕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尽管这个梦破灭得十分惨痛,足以令人警醒,但它毕竟展示了一种理想主义追求,它以凄惨的失败营造了一种理想主义氛围,惨烈而发人深省。而且,丁庄的“梦”很多,远不只这一个失败的梦;也有成功的梦。比如,代表良知和正义的“爷”棒杀了代表不择手段、无知妄为、良心丧尽的“爹”,这应该算是一个正义的、理想主义的梦。然而,“爷”作为一个断子绝孙的老人,他即使以正义之激情(也可能是理性瞬间丧失的狂乱)胜了邪恶,终究还是失败,因为他后继无人。所以,这依然是个凄惨的理想主义终结。小说写到此,的确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震撼心灵的绝望。
正如阎连科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所说:“内心的那种无所依附的苦痛和绝望,在1997年年底写完《日光流年》时曾经有过,2003年4月写完《受活》时也曾有过。但那两次都没有这次写完《丁庄梦》来得强烈和难以让我承受,让我难以言说”[6]286。看来,写作的确是呕心沥血的事情,作家要写出感动人的作品,首先要感动自己。阎连科毕竟是一个挚爱土地的人,他在凄惨的理想主义幻灭中,又为丁庄营造了新的“梦”,让“爷”看见了女娲造人的幻景。然而,给丁庄安上这样的复兴理想,终究只是乌托邦幻想,它可以让小说具有空灵美,具有奇幻色彩,却不能改变文化自慰式的理想主义终归是乌托邦幻想、必将凄惨失败的本质。因为女娲只是个传说,当女娲造人的梦破灭了,“丁庄”还能有梦吗?“丁庄”还能有未来吗?这是多么凄凉、悲惨的氛围!可见,《丁庄梦》中的“梦”实际上成了反乌托邦的手段。
再比如,《受活》中的传奇因素也不少,受活庄的历史传奇、茅枝婆的革命传奇、柳县长的种种非同凡响的传奇、残疾人绝术表演团的传奇等,这些传奇因素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乌托邦境界,隐含着以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意义。比如受活庄的起源历史,哑妇应该可以代表母性与爱,胡大海代表强权与专制,因为哑妇对胡大海有恩情,受活庄才获得了去权力化的机会,成了乌托邦天堂。这显然是小说对受活庄起源的乌托邦假定,营造了一种乌托邦理想气氛。茅枝婆的革命传奇被自己的“退社”终结了,她实际上由革命者走向了无政府主义者,由革命乌托邦走向了自由主义乌托邦。也就是说,茅枝婆颠覆了自己的历史,不论她这种举动是为了抗拒柳县长的“瞎折腾”,还是为了尊重受活庄的民意,或给自己的历史流下清白,毕竟,她在年老的时候穿上寿衣讨到了一纸盖有公章的“退社文件”,算是欣慰地把自己曾经“折腾”过的受活庄恢复了历史的原样。柳县长及其奋斗的历史,尽管私欲是原动力,但表面上还是有乌托邦理想的,然而,他本人最终也残废了,遁入茅枝婆还原为自由自在状态的受活庄。这既是嘲讽,也是象征。柳县长的奋斗史象征了私欲与权力结合后的疯狂与自我毁灭。所以,他最终也身体残废去了受活庄,这是对个人意志极度膨胀后的权力乌托邦的嘲讽。柳县长终于在秘书的“谎言”的帮助下,用空幻的乌托邦换取了民众的愚昧的“尊重”,但是,他从没有像哑妇和茅枝婆那样真正享有权威,只因他的权力和私欲混杂,他追求的乌托邦不再是纯粹的理想。欺瞒、疯狂的个人欲望不仅破坏了受活庄的乌托邦生活,也摧毁了柳县长平常的个人生活。他用个人命运的凄惨悲凉,颠覆了他编造的乌托邦。残疾人绝术表演团及其表演的种种绝术,其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设想,借用这种乌托邦化的绝术,来创造乌托邦者的辉煌,结果是以空对空,一切皆空。这就是超越主义通过传奇营造的理想主义氛围,它否定了荒诞的谎言乌托邦,试图营造出自由、平等、民主、友善、合作、超越的新乌托邦。小说结尾的受活歌渲染的就是这种气氛。
可见,乌托邦化传奇作为小说的一种境界,具有两面性。当一些因素承担了批判生活的功能时,它是反乌托邦的利器,制造的是凄惨与悲凉的气氛;当另一些因素作为正面的乌托邦精神资源被张扬时,又能给小说带来超越与和美的理想主义色彩。
三、对生活的荒诞化处理与深刻的人性剖析
由于阎连科自觉地“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他小说中的现实生活往往充满荒诞色彩,然而,恰恰靠了这些不真实的故事、不近情理的情节,使他对人性的思考更加游刃有余,对人性的剖析更加深刻。
比如,《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位于“耙耧山脉的深皱之间”,“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7]11,但人们依然“死不离窝”地活着。三姓村人的祖先都是逃难聚到大山里的苟且偷生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先辈竟然稀里糊涂、心甘情愿、主动上门给日本军队的烧伤医院出卖自己腿上的肉皮,因为他们看见日本烧伤的士兵就灵机一动,发现了发财的机会。他们需要钱,要用钱买了毛驴去青岛驮盐和海带,希望“吃了青岛的盐和海带,也许就能和别的耙耧山人一样活到五十、六十,甚或七十、八十,不得喉咙病”[7]19。把自己的小命活长,成了他们活的惟一目的。什么民族意识,什么名节伦理,什么人生价值,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只要活着,就是他们的全部意义。司马蓝是村长,三十九岁了,为了多活几年,他让自己的兄弟卖人皮,让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蓝四十带上他的女儿到大城市卖淫挣钱,挣来钱给他做手术;终致蓝四十染了性病而自杀。为“引灵隐水以延年益寿”[7]12,三姓村全村男人都去卖人皮集资,然后都到大山里去艰苦卓绝地开那延年益寿的引水渠,结果渠修成了,水引来了,引来的水却已经被“堆满了洋楼和工厂”、“山坡上的楼房比山顶还要高”的大城市污染了,水“和屎尿一样脏”[7]138。司马蓝也在四十岁没能逃过宿命而死。现实的中国人的生活应该还没有堕落到如此地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这么多荒诞的故事集中在一个村落里,这显然是作家对生活的荒诞化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把三姓村人的愚昧、残忍、不择手段、不知廉耻、从众苟且、追逐蝇头小利、顽强、不怕牺牲、敢于吃苦、统一团结、重情义等等的人性之善恶都一股脑儿地表现出来,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姓村是个乌托邦世界,是个象征世界,它以荒诞化的集中和概括,表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百年历史,诉说了乡村人的苦难和抗争,展现了他们生的悲壮与轻贱,死的凄凉与无奈。三姓村人活得十分荒唐,连一家一户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也可以由村长开会布置,然后集体统一行动,以制造出繁盛的人口。这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乌托邦化的小说里却是可以的,通过这种荒诞化的处理,深刻地揭示出三姓村人的无个体性、村长的绝对权威性、个人对整体的无条件依附性,等等。
总之,阎连科通过对生活的荒诞化处理,形成了一个乌托邦化的意义丰富的文本,把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中国人的人性进行了整体的分析与批判。所以,读阎连科的小说,总能读出鲁迅小说的那种思索国民性与救治国民精神的味道,尽管小说中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问题有了很大不同,但人的精神世界却是有那么多的相似性。这应该正是阎连科小说的价值所在,他抓住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的精神世界改造问题。物质的世界可以在短时间内赶上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比如让城市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车水马龙、西餐馆随处可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火车跑得飞一样快,但是,芸芸众生们的精神品质能否也迅速地与城市化的步伐同步发展?看看阎连科小说展示的种种现象,的确令人堪忧。
忧患兴邦,时代需要文学的忧患意识。阎连科借用荒诞和乌托邦化构筑的小说世界,其实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历史象征,正如《坚硬如水》那样,他不惜用历史的乌托邦语言来增强这个象征世界的原生态情状,其目的就是反省和批判曾经有过的乌托邦社会的所谓理想主义人性,对种种乌托邦式的改造社会运动提出质疑,从而构筑出一个反面的乌托邦世界,警醒社会。应该说,乌托邦本身未必就是灾难性的,也许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招引社会变革,而反面乌托邦十分有助于人们建构实实在在的未来。
[1][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美]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M].姚建彬,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6.
[4]阎连科.受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5.
[5]阎连科.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代后记)[M]//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6]阎连科.丁庄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7]阎连科.日光流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王俊虎]
Discuss Utopia Narrative Strategy along with Aesthetic Function of Yan-Lianke′s Novels
XU Mei-heng
(Chines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Tianjin Radio and TV University,Tianjin 300191)
Yan-Lianke's some novels,especially “Balou Mountain”(耙耧山)series local novels,construct wonderful world having utopia character,and form particular artistic style.In accord with his utopia novels,the utopia narrative strategy is a kind of particular writing manner,and it exploits new bourn for novel's esthetics.Utopia esthetics strategy more convenient for to create a text of combining beyond the reality and critical reality artful,and to build deplorable idealism atmosphere in dreamy and romantic stories,through rebuilding life grotesquely,more thoroughly construe humanity,so as to achieve the intend of curing the inner man.
Yan-Lianke; Utopia novel; narrative strategy; a spirit cure
I206.7
A
1004-9975(2015)04-0066-05
2015-04-24
徐美恒(1964—),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